22歲,他做出了中國最驚豔的方言音樂_風聞
摇滚客-摇滚客官方账号-有态度地听歌、看剧2022-03-11 09:11
來源 | 搖滾客
舊社會頂窮的人音樂:還潮 - 老酒日日醉,皇帝萬萬歲(The Ningbonese Art of Renunciation)
今日BGM,《舊社會頂窮的人》,還潮
#樂隊與城市#是搖滾客2021年10月發起的講述項目。
我們關注那些紮根在某座城市的樂隊們。他們的音樂是一羣人、一座城市、一個時代的存在側面。音符激盪,歌聲繞梁中,或許你也能看到自己以及祖輩的影子。
系列已進行到第八篇,前七篇分別為景德鎮、南京、普洱、上海、蘭州、大涼山、哈爾濱。
文章可在文末查找。
以下是正文:
大家好,我是馬拉松。
寧波,一個對上海影響大到改變它第一人稱的城市。
“阿拉上海人”中的“阿拉”,指的是“我”的意思,來源於寧波話。
寧波人也是上海人的主要來源之一,三分之一左右的老上海人,祖籍或者祖上是寧波人。
他們來到上海開銀行,做百業,輪船、五金、鐘錶、服裝、製藥、糖業,還有風花雪月的電影業,之前可都是寧波人的江山。
在上海街頭,路邊梧桐樹下搖着蒲扇、穿着白色背心的阿爹並不在乎你那口流利的法語與倫敦味道的英倫腔。
可當你嘴巴里漫不經心地飄出幾句寧波話,他一定會豎起耳朵,忍不住兩句便會上前套近乎,跟你開幾句寧波腔過過癮。
而今天我向大家介紹便是寧波的獨立音樂人,還潮。
即使只有25歲,但他的音樂就像八十年代遺留下來的老式收音機,擺在寧波不知名小店的角落裏,偷偷收錄着每個過路人嗦面的聲音。


寧波話讓還潮着迷,但一開始他其實並不確定要不要用寧波話來做音樂。
他曉得自己鍾愛的上海方言樂隊“頂樓的馬戲團”,十幾年前已經把自己能想到的都寫過了,而且頂馬也是吳語。
“我想要説的,前人們都説過了”,二十出頭的還潮懷疑自己。
他給**“週二下午誰沒來?”**的老彭發郵件,講自己的不自信,並附上了自己剛做的音樂demo。
插句嘴,江湖傳説般的樂隊“週二下午誰沒來?”共六人,分別為:彭、趙、王、馬、張、孫。
其中彭和馬有個分支計劃,名為“水仙鬥活佛”。
不知姓名,也從不露面,近乎俠隱的老彭聽完他的音樂後回信:
“寧波話這個事情沒有人做過,你有這個想法,趕緊去做。”

“週二下午誰沒來?”唯一專輯,歌詞近四萬字,合為一部押韻、分行的小説。
他甚至從未接受過系統的音樂訓練。
1996年,還潮出生在浙江省寧波市,初中時開始學吉他,當時覺得重金屬聲音很響,流汗很多,更酷。
高中時接觸民謠,慢慢發現鮑勃·迪倫的吉他永遠是很簡陋的,但彈出來的東西卻遠遠超出複雜編曲後的表達。
2014年,當時寧波可以直接通過高考申請台灣學校。
還潮想着自己喜歡的羅大佑和胡德夫,難掩激動,這一年他離開寧波去台北上大學,18歲出門遠行,打算走得越遠越好。
台灣的生活由三件事構成,上課,睡覺,閒逛。
羅大佑歌裏唱過的地方,楊德昌電影裏拍過的地方,還有白先勇小説裏寫過的地方,一個個蕩過去,像一場又一場短暫的美夢。
一天在市區附近溜達的時候,他不知不覺逛到寧波東路,又不知不覺又走進一家寧波生煎包,生煎包的湯汁在嘴中破皮而出,那一刻覺得特別恍惚。
耳旁又傳來眷村人曬太陽、打麻將的閒聊,竟是熟悉的浙江鄉音,眼神忘了聚焦,耳朵不自覺地豎了起來。
台北和寧波,在某個時空上緊緊關聯在一起。
生活如同一盞風箏,寧波在趁其不備之時用鄉音拉了拉手中的線,牽動了一顆漂洋過海的心。

2018年,大學畢業後,還潮選擇繼續深造,到香港讀研。
住在不太寬敞的房間裏,他發現周圍的人來自五湖四海,口味不同,口音也不同,生活習慣和思維方式都不太一樣,想交一個朋友蠻難。
交朋友其實就是把自己的一部分託付出去,但在這個陌生的環境中,他不知道應該把自己的這部分託付給誰。
他突然回憶起已經拆遷的老家與小學,童年已經沒留下什麼存在過的實質性證據,青春好像更加沒有,常去的聯和墟街菜市場,賣的海鮮也沒有海風習習的鹹腥味。
只好在香港想念寧波外灘碼頭悠長的笛聲,年糕捶出的鼓點和天童寺外散落滿地的銀杏葉。

寧波,天童寺
他開始翻起《寧波方言字典》和《阿拉寧波話》,飛得很高的風箏朝起飛的地方回頭望了望。
這時才猛然發現,聽上去兇猛的寧波話,寫下來卻是那般含情脈脈:
比如寧波話説“晚來了一步”叫“晏了一步”,“晏”字上面一個日下面一個安,意思是日子輕快,沒必要跑太快。
老一輩記時辰一般不説下午幾點,而講三江口漲潮、退潮到了。
螃蟹是每個寧波人愛吃的,它便出現在各種比喻中:
“阿叔的股票虧了,像人家菜場裏揀了半日揀來只死蟹。”
形容人和事情蔫不拉幾,是“死蟹一隻”。
動情了,天雷勾地火,叫“咕咕雞碰着石蟹”。
比如,“我忖你”就是“我想你”,濃烈的感情,寧波話要拐個彎才好意思説出口。
再比如,“我愛你”寧波話裏沒有直譯,語不達意之時只好用一句“阿拉沒道理講了”(我沒辦法講下去了)擱淺。
這些話要是用普通話講出來,會肉麻死。
但它本身又是那樣浪漫,幾個詞裏不知道藏了多少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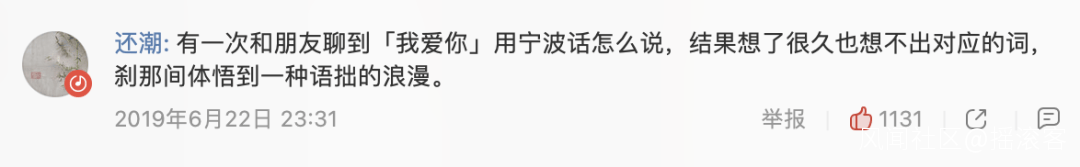
之後“週二下午誰沒來?”給他的鼓勵很大,時年22歲,他用寧波話寫下自己的第一張專輯《寧波人有三譬好譬》上傳到蝦米。
這些歌像蒲公英的種子一樣散開,傳播到各地,沒人知道這位神秘的還潮是誰,只聞見他的歌聲中泛起的淡淡江水味。
不少在外漂泊的寧波遊子,深夜聽着他的歌淚流滿面,幻想自己又回到了歌聲中唱的、自己遠行前嬉鬧着長大的土地。
舟宿渡夏目漱石音樂:還潮 - 老酒日日醉,皇帝萬萬歲(The Ningbonese Art of Renunciation)
頂馬的靈魂人物陸晨,在朋友圈聽到了還潮的歌。
陸晨喜歡吃寧波的糕,他説:
“寧波總讓我想起黏黏的糕,他的歌也有一種黏黏的、擰擰的韌勁,很有韻味。”
他甚至有不少朋友,聽了歌忍不住前往寧波,按圖索驥,尋訪歌聲中的一個個地名。

香港回來之後,還潮在杭州工作了半年,八月份的夏天,有一天加班到8點半,把寫了兩天的方案交給老闆,老闆看都沒看就説不要。
加完班回來,走在工地一樣的小路上,他突然聞見一陣桂花香。
他知道自己不能再待下去了,再待下去,杭州會把他這顆樹上的桂花全部搖光。
如今,還潮在寧波開着一家茶館,取名“下半日咖啡館”,一邊開茶館,一邊做音樂,勉強維持着收支平衡。
2021年年初,還潮作為頂馬主唱陸晨的特邀嘉賓,首次登台演出。
演出之前調音,還潮鼓手商量:能不能鼓打得再土一點?
“土”是一種温暖,不太冷,也不時髦,像整個80年代。
最後演出聽上去像他茶館裏售賣的“八月夜桂花”,安靜又靦腆。

2021年年末,他的作品《舊社會頂窮的人》選入電影《愛情神話》的插曲,第一次走入大眾視野,讓無數觀眾驚豔。
電影講述的中年愛情故事就像還潮的歌,不在乎遙遠的明天,只在乎眼前的一頓頓飯,“只想着現在碗裏有口酒”。


“還潮”,吳語中是受潮的含義,也形容小孩子又恢復了壞習慣。
而他的壞習慣,大概是將肉身委身於三餐小飯,在日常生活中綿綿,在玻璃上掛滿霧氣的舊時光裏徘徊不去。
第一張專輯是寫對寧波當下生活場景的平鋪式回憶,整張專輯充滿了白描。
你能聽見粗陋的配器,簡單的旋律,以及寧波英文交織的歌詞下,一眾心有不甘卻仍不忘排憂解悶的人們:
慈城公園跳交誼舞的伯伯阿姨,撞掉門牙的阿超,買香煙的阿斌,騎着電瓶車四處兜風的阿叔…
高三的一個晚上,還潮身體不太舒服,在晚自習的時候請假去醫院,路過慈城公園看到有人跳交誼舞,放的是鄧麗君的《何日君再來》。
那天他沒去醫院掛鹽水,坐在長凳上看了一整晚露天舞蹈,感覺渾身輕鬆。
這天晚上看到的場景在多年後,被他寫進《慈城公園交誼舞》:
慈城公園交誼舞音樂:還潮 - 寧波人有三譬好譬(The Ningbonese Philosophy of Consolation)
每天四五點鐘吃完晚飯,鎮裏面角角落落的dancer在慈城公園會合。
雖然大家都説這個社會烏漆麻黑,但跳舞的伯伯的心仍舊鋥亮,最歡喜跳“Jambalaya”。
衰老讓他們的肚子變大,小腿變得僵硬,甚至年紀一把了也沒搞清楚世界的方向。
但沒關係,只要抽出一個晚上,去公園和阿姨跳個舞,一切就都不是問題。

如果説第一張專輯是白描式的眾生相,第二張專輯展開的便是時間上的縱深。
通過一個具體的人,不同階段的的經歷,去講一個完整的故事,專輯的概念就是寫一個人的時間線。
主人公是還潮小學時的乒乓球友,老年活動室結識的忘年交阿叔。
阿叔沒事喜歡跟這個小自己三十幾歲的小孩打乒乓、吹牛逼。
話題不限於打架、練霹靂舞、教唱“流氓歌曲”,以及那些永無盡頭的愛情。
阿叔年輕時給姑娘寫情書,筆名叫“北方的狼”,邊用老式雙卡錄音機聽歌邊寫信,時不時借鑑齊秦與羅大佑,台灣情歌十二首,處處生髮在他的愛情。
和小姑娘划着船談情説愛,拐彎抹角的情話從新江橋講到舟宿渡,身無分文卻渾身是勁。
永無盡頭的約會音樂:還潮 - 老酒日日醉,皇帝萬萬歲(The Ningbonese Art of Renunciation)
還有神秘的情人Monica,或許她來自國境線的更北邊,或許他們只享有一晚的春風,但阿叔始終記得她在三伏的冰場回舞,他偷摸了她的腰。
有些味道啊,嘗過一次,能記上一輩子,像牙縫裏塞進的肉絲,足夠用來回味那一晚的盛宴。

阿叔常常夢見自己回到八十年代,夢見河裏有抓不完的蝦蟹,夢見煙草廠裏堆得山一樣高的香煙,夢見鋼鐵廠比金箍棒還高的大煙囱。
上世紀末,時代的愁雲與新的生機形成了阿叔人生的十字路口,他在茫茫然中不幸被前者籠罩。
當時代以一種不可理喻的方式與他分道揚鑣,他學會了放棄一些東西,包括自己。
時代大張旗鼓地向前狂奔,他追趕無望,慶幸留在身邊的還有香煙、老酒跟茶葉。
就這樣,還潮把阿叔講的故事寫成第二張專輯《老酒日日醉,皇帝萬萬歲》。
年輕時風流倜儻,年老時泯然眾人。現實生活雖然密不透風,但在傍晚的燒烤攤脱下背心,身上的傷疤依舊泛起榮光。
一生像一支漫長的紀錄片,凝結着時代的變遷和個體命運的潮起潮落,映射出許多寧波人幾十年的倒影。
專輯名也是寧波俗語,意思是“只要天天有酒可以喝,世上發生的一切都與他無關了”。
明明是灰色膠底的時代,可阿叔回憶中的喇叭褲卻從來不沾灰,連衣裙永遠是玫紅色,心愛的女孩像林青霞,雙卡錄音機要擰到最大聲。
懷舊啊,是對現世無聲的反抗。

還潮的前兩張專輯是對過去時光的白描與敍述,第三張專輯終於抵達到當下。
他説,自己知曉的寧波故事差不多已經寫完,本地的年輕人已經沒那麼“寧波”。
他們不太會説寧波話,普通話慢慢消滅了那些加密的情話;也不愛吃那些本地菜,外賣軟件裏輕鬆裝下了五湖四海。
可在一切都順心意的温和下半日,崩潰來的毫無預兆,身體在高架橋擱淺,像一隻蝦乾。
温和下半日音樂:還潮 - The End of Delusion and the Last Ningbonese
青春好像從未如同父輩般暢快淋漓過,還沒竭盡全力,就開始無聊。還沒愛夠,又泄了力。
第三張專輯《寧波人狂想終曲》,寫的是這種一點點消失的感覺,從舊日場景到現代個人生活,從生長湧現到難以挽回的消亡。
《寧波人有三譬好譬》,實體唱片設計靈感來自於一家老寧波大食堂。
還潮拍攝取材之前,提前跟老闆打招呼 :
“幫你們飯店推廣推廣。”
誰知老闆説:
“我們飯店還需要你們推廣?你們得去推廣寧波話。”
還潮聽完,內心感動又酸澀。


在錄製第一張專輯時,還潮翻寧波方言字典剛好看到的一句話:“寧波人有三譬好譬”,覺得這些歌都可以歸在這個主題之下,於是它成了第一張專輯的名字。
這句話意思是寧波人的一種精神勝利法,碰到糟糕的事情,用某種想法安慰自己。
丟了錢,往往説:“譬如撥搓麻將輸掉仔,譬如上交給老婆……”(比如打麻將輸掉了,比如這個錢交給了老婆)。
凡事作了三種譬如之後,也就心平氣和了。
寧波人靠海,深諳順應自然,適宜分寸才是謀生之道,堪稱當代阿Q精神。
阿Q生長在“未莊”,也就是今天的紹興。
“譬如”這個作為阿Q精神的象徵詞,在寧紹平原間流傳,跟着寧波移民四處在吳語區紮根。
活在這個時代,當初被魯迅先生批判的阿Q精神,如今卻成了自我療愈的法寶。

還潮形容自己的家鄉像一個**“失落的貴族”**。
90年代的時候,寧波比杭州經濟更發達,中山路也被稱為浙東第一街,當時所有寧波人的自豪感都非常強,覺得**“走遍天下不如寧波江廈”**。
工作日的上午,在月湖公園附近生活的寧波老貴族們聚在一起散步,聊天,下棋,唱歌,踩着鴨子船緩緩地在湖裏盪漾,覺得此地就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
這讓寧波這個瀕臨東海的浙江老城,11次入選“中國最具幸福感城市”。

金華特味牛雜麪館,來這兒吃飯都是當地的老炮,第二張專輯結束曲便採樣於此。
老酒日日醉,皇帝萬萬歲 - outro音樂:還潮 - 老酒日日醉,皇帝萬萬歲(The Ningbonese Art of Renunciation)
2018年冬至,吃了酒的老炮們開始用寧波話胡言亂語地吹牛:
“我們這坐着的人在寧波市名氣算大的
老流氓裏面我名氣算挺大的
你放心好了,問我老婆好了
寧波市最大的流氓 我們都是一起混的
我也算是,他們説我不是,我怎麼可能不是?
我就是老流氓啊 我怕什麼?”
打電話喊女人出來,一個也叫不出來,騷動了半晌,到頭來還是隻有三張嗓音粗獷、滾着老痰的喉嚨。
有聽友説,歌曲1分40多秒的那聲咳嗽,讓他想起了爸爸。那是一種,吃麪吃得太快,抽了很多年煙的嗓子發出來的咳嗽。
酒過三巡的寧波爺叔想不到,旁邊桌的青年還潮竟然偷偷錄音,把他們流氓遲暮、口齒不清的對話變成可重複播放的一首歌。
“江風習習,蟹腳剝剝,老酒眯眯,大興發發”(吹吹江風,剝剝蟹腳,喝喝老酒,抒發興致),是寧波人走過半生的中年況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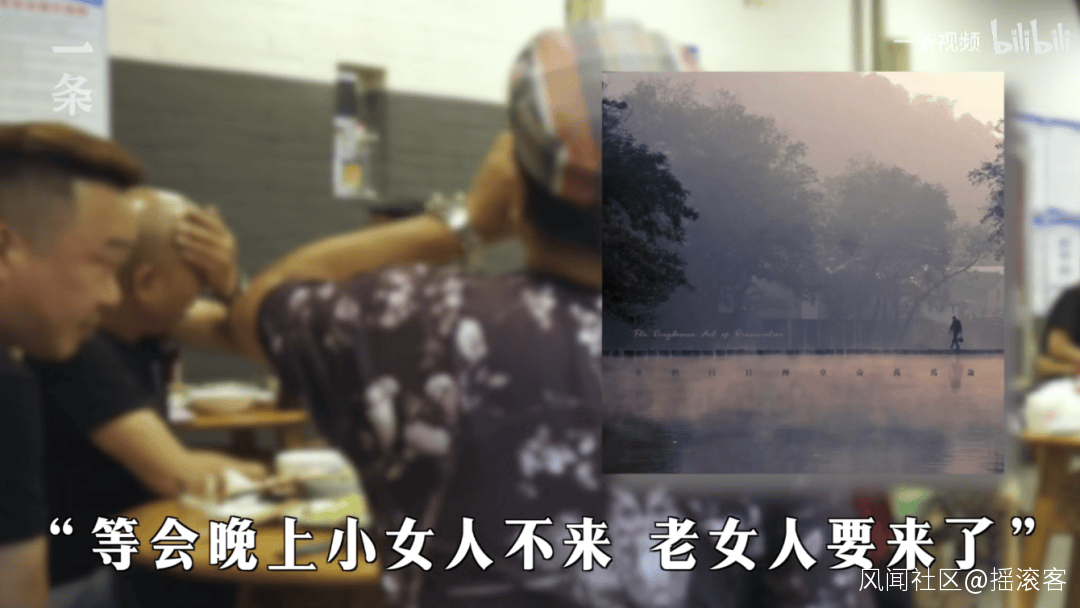
幸好有還潮用寧波話記錄下這一切,讓“舊社會頂窮的人”也能書寫自己的歷史簿。
他告訴我們:
“只要你想得足夠開,依舊可以在這個正好不屬於自己的時代裏活得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