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故而知新:回望中美蘇“戰略三角” || 大視野_風聞
秦朔朋友圈-秦朔朋友圈官方账号-2022-03-14 09:44

秦朔 | 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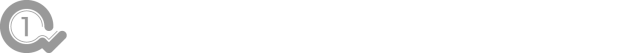
歷史的進步總是曲折的,因為進步是真知驅動的,而真知在很多情況下會被狂熱、偏執、膚淺、自以為是和似是而非淹沒。
投資家查理·芒格經常講一個關於德國物理學家普朗克的笑話。1918年普朗克獲得諾貝爾獎後應邀到德國各地演講,由於每次講的內容大同小異,都是關於新的量子物理理論的,時間一久,他的司機也記住了講座的內容。
司機説:“普朗克教授,我們老這樣也挺無聊的,不如到慕尼黑時讓我來講,你戴着我的司機帽子坐在前排。”
普朗克説:“好啊。”於是司機走上講台,就量子物理發表了一通長篇大論。後來一位物理學教授站起來提了一個非常難的問題。演講者説:“哇,我真沒想到,我會在慕尼黑這麼先進的城市遇到這麼簡單的問題。我想請我的司機來回答。”
2007年芒格在南加州大學法學院畢業典禮的演講中説,講這個故事不是為了説明演講者的機敏,“我認為這個世界的知識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普朗克知識,它屬於那種真正懂的人。他們付出了努力,他們擁有那種能力。另外一種是司機知識。他們掌握了鸚鵡學舌的技巧,……但其實他們擁有的是偽裝成真實知識的司機知識”。
普朗克的司機是明智的,因為知道要把問題交給真正懂的人去解決。而假如世界上的大量“司機”真以為自己擁有“普朗克知識”,那麼,真正的普朗克就可能“黃鐘譭棄”,而司機們則聲如雷鳴。
互聯網輿論場不乏此種情形。我在之前一篇文章中説,俄烏之戰在中國輿論場引起巨大紛擾,相互指責中的“敵意”是如此之強,好像是我們自己在“打仗”。但付出瞭如此多時間精力,能獲得多少真知呢?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立場,眾聲喧譁多元雜陳也是輿論場常態。但多元仍需共識,這就是基本規則,比如用事實説話,事實要準確、全面,要聽得到當事各方的聲音;對與自己不同的觀點,怎麼辯論爭鳴都可以,但不能侮辱謾罵造謠貼標籤。如果堅持這樣的基本規則,真知將贏得越來越多的人,否則輿論場的贏家只有一個,那就是情緒。
輿論場上還有一種特別不好的現象,就是臆想政府會站哪邊,然後把和自己不同的觀點“安置”在政府對立面,上綱上線,比如這一次,挺俄者給反戰者所帶的帽子就是“聖母婊”“文青幼稚症”“帶路黨”等等。
反戰求和平,作為一種基本立場,有錯嗎?
中國領導人3月8日在和法國總統、德國總理舉行的視頻峯會上説,中歐在謀和平、求發展、促合作方面有很多共同語言。中方對歐洲大陸重燃戰火深感痛惜。中方主張,各國主權、領土完整都應該得到尊重,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都應該得到遵守,各國合理安全關切都應該得到重視,一切有利於和平解決危機的努力都應該得到支持。
聯合國憲章《序言》開篇,就是“我聯合國人民同茲決心,欲免後世再遭今代人類兩度身歷慘不堪言之戰禍”。為達此目的,“力行容恕,彼此以善鄰之道,和睦相處;集中力量,以維持國際和平及安全;接受原則,確立方法,以保證非為公共利益,不得使用武力;運用國際機構,以促成全球人民經濟及社會之進展……”
中方堅持根據烏克蘭問題本身的是非曲直決定自己的立場,也就是説,對烏克蘭問題演化到現在的原因有自己的判斷。但從戰爭一開始中方就強調,各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都應當得到尊重和維護,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也都應當得到共同維護,這是中方一貫秉持的原則,也是各國都應該堅持的國際關係基本準則。
這不是反戰又是什麼?如果這一點都不講,還談什麼人類命運共同體?
中國領導人在3月8日的視頻峯會上還説,中方樂見歐俄美及北約開展平等對話。
中國的輿論場,也亟需平等對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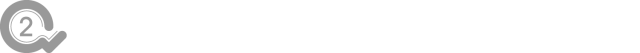
在俄烏之戰的爭論中,一個若隱若現又揮之不去的主題是中國、美國和俄羅斯的關係問題。這是一個貫穿於中國近代、現代和當代的重大歷史和現實問題,也關係着中國的未來。
回首歷史,中國和蘇聯(以及繼承了蘇聯的國際影響力的俄羅斯)、美國的關係充滿了複雜多變性,但大的邏輯是不可能截然分開、長期對立,終需在建設性互動中找到相處之道。
先談一下中蘇關係。不談更為久遠的沙俄和清朝關係史,從1919年開始,中蘇之間的關係大致經歷了以俄為師、為鑑、為敵、為戒、為伴的五個階段。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以李大釗為代表的覺醒者高呼“俄羅斯之文明,誠足以當媒介東西之任”,中國共產黨“以俄為師”“走俄國人的路”,是那個時代的必然。儘管一味照搬照抄蘇聯的道路和經驗,以及在一定程度上唯共產國際命令是從,使中國革命也付出過代價,但“以俄為師”對黨和革命事業的發展有着重要推動作用。
新中國成立後,中國學習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因為我們不懂,完全沒有經驗,橫豎自己不曉得,只好搬”,“在全國掀起一個學習蘇聯的高潮,來建設我們的國家”。同時,在外交方面,《論人民民主專政》明確宣告,中國要奉行“一邊倒”的外交政策,即倒向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一邊。“以蘇為師”以及蘇聯對中國的援助,對中國的工業化功不可沒。
1956年蘇共二十大召開,當年毛澤東發表《論十大關係》,標誌着中國開始“以蘇為鑑”。毛澤東指出要聯繫本國實際,“要按實際情況辦事,不受蘇聯已有的做法束縛”,“應當更加強調從中國的國情出發……努力找出在中國這塊大地上建設社會主義的具體道路”。毛澤東反思了蘇聯片面重視重工業、忽視發展輕工業和農業、導致物價和貨幣不穩定的問題,“從農民那裏拿走的太多,給的又太少”的問題,“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點機動權也沒有”等問題。
《論十大關係》在談到國際關係時提出,要向外國學習,要承認每個民族都有它的長處,不然它為什麼能存在?為什麼能發展?同時,每個民族也都有它的短處。我們的方針是,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政治、經濟、科學、技術、文學、藝術,一切真正好的東西都要學。但是,必須有分析有批判地學,不能盲目地學,不能一切照抄,機械搬用。“將來,我們國家富強起來了,我們還要保持革命的立場,還要謙虛謹慎,還是要向外國學習,不能把尾巴翹起來。”
**1958年,蘇聯提出要在中國領土和領海上建立中蘇共有共管的長波電台和共同艦隊,遭到中國堅決拒絕。毛澤東後來説:中蘇鬧翻實際上是在1958年,他們要在軍事上控制中國,我們不幹。從此,中蘇關係逐漸惡化。**1968年蘇聯《真理報》發表《社會主義國家的主權和國際主義義務》,勃列日涅夫推出“有限主權論”,提出社會主義大家庭的利益高於國家利益,實質是賦予蘇聯干涉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主權的權力。中國堅定進行反制,蘇聯則向中國施加更大壓力。1969年中蘇邊境爆發了珍寶島自衞反擊戰和新疆鐵列克提之戰,雙方水火不容,蘇聯在中蘇邊境陳兵百萬,勃列日涅夫甚至一度想對中國實施外科手術式的核打擊。
改革開放後,中國取得了長足進步。進入20世紀80年代後,中國也開始“爭取中蘇關係有一個大的改善”,中蘇關係1989年實現了正常化。而蘇聯則在1991年解體。中國“以蘇為戒”,上半場主要是以蘇式計劃經濟體制為戒,強調“我們不能再像蘇聯那樣,認為只有資本主義制度才能用市場經濟,社會主義制度就只能用計劃經濟”;在下半場主要是以蘇共亡黨的教訓為戒,擁有1900萬黨員和74年執政經驗的蘇聯共產黨極其平靜地自行解散,這引起了中國對人心向背、理想信念、意識形態工作重要性等方面的深思。
最近若干年,尤其是2017年後美國諸多安全、國防和軍事戰略報告都將中俄作為美國的主要安全威脅和全球戰略對手,中俄之間在建立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方面越來越緊密,進入了以俄為伴的新階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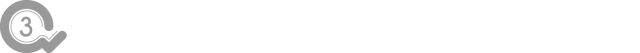
再談一下中美關係,其實也是在不同歷史時期,為師、為伴、為鑑、為戒、為敵等多重情結的複合體。
以“革命先行者”孫中山為例,他13歲就去了美國檀香山,早期追求的就是美國政治模式,他特別關注自由、平等、自治。民國初建,南京政府仿照美國推行總統制,孫中山説“中國各大行省有如美利堅合眾國諸州,我們所需要的是一位治理眾人之事的總統”。1924年他在黃埔軍官學校的告別講話中説:“美國之所以富強,不是由於各邦之獨立自治,還是由於各邦聯合後的進化所成的一個統一國家。所以美國的富強,是各邦統一的結果,不是各邦分裂的結果。”他對美國以陪審團制保障人權的做法也很肯定,説“大小訴務,仿歐美之法,立陪審人員,許律師代理,務為平允。不以殘刑致死,不以拷打取供”。
但孫中山也不是一味模仿。他在1906年同俄國人的談話中指出:美國的國務是勝利的執政黨一手包攬,某個黨派勝利贏得選舉後,從上面的主要官員到下面的低層官員都要更換,不但非常麻煩,而且具有很大的弊端。“只從選舉來任命國家公務人員,……那樣往往會讓有才能的、不善於言辭的人進不了政府的門檻,而那些誇誇其談,只會演講的人反倒進了政府。……美國政府議會就有不少庸才,只能大放厥詞,這是其最大的弊病。”
從1894年到1923年,孫中山一直效法美國,創建共和國,但始終沒有得到美國的實質性援助,最後轉向蘇俄。1923年他在與中共和蘇俄代表的商討中,逐漸確定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並在1924年1月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發佈。
對中國共產黨來説,儘管建黨後就以俄為師,但也根據國際形勢的變化,不斷調整和美國的政策。抗戰時期,毛澤東呼籲“應與英美作外交聯絡”,建立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1944年7月美軍觀察組訪問延安,標誌着雙方半官方關係的建立和軍事合作的開始。
毛澤東提出“放手與美軍合作”的方針,強調“處處表示誠懇歡迎”。但由於美軍觀察組在美國對華政策方面所起的作用有限,以及國民黨的阻擾,這種戰時友誼並無牢固基礎。中共七大前後,對美態度已從“放手合作”變為“中立美國”,希望在抗戰勝利後藉助美國調停避免內戰。而到1946年6月國民黨大舉進攻解放區,7月內戰全面爆發,8月10日馬歇爾和司徒雷登發表聯合聲明承認調停失敗,美國在對華援助、運兵等方面站到國民黨一邊,中共與美國在抗戰時的半官方外交關係畫上了休止符。
新中國成立後,中美之間先是對抗,美國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回應以“擠走”的對策,即徵收美國在華兵營、物資,擠走在華外交人員。抗美援朝,更是“打得一拳開,免得百拳來”。
接着是中美之間長期的隔絕,但隔絕中也有一定溝通渠道。從1955年8月中美開始大使級會談,談而不速,談而不破。**1966年3月第129次會談中,美方大使格羅諾斯基在發言中使用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説法,是中美大使級會談以來美方第一次使用這一特定詞語。**但“文革”開始後,中美大使級會談逐步降温,美方也隨之後退。
1960年代後期到1976年,是中美的接近期。“小球推動大球轉”,開啓了中美關係正常化的歷史進程。1972年2月28日,中美在上海正式發表《中美聯合公報》,指出“中美兩國關係走向正常化是符合所有國家的利益的”。
所謂中美蘇“戰略三角”的提法,源自1969年2月陳毅、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四位元帥根據毛澤東的要求所做的國際形勢和戰略問題的研究。在他們最終向中央提交的《從世界的森林看一棵珍寶樹》和《對目前局勢的看法》兩份書面報告中,分析了中美蘇三大力量之間的矛盾,認為在中美蘇“大三角”關係中,中蘇矛盾大於中美矛盾,美蘇矛盾大於中蘇矛盾,在美蘇兩國都急於打“中國牌”的情況下,中國處於戰略主動地位。
改革開放後,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實現了歷史上的偉大轉折。鄧小平説,“同心同德地實現四個現代化,是今後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全國人民壓倒一切的中心任務,是決定祖國命運的千秋大業”。而要確保“千秋大業”順利進行,在安全方面要解決中蘇對立、蘇軍壓境的問題,否則無法安心。在經濟方面則要解決資金、技術和市場等問題,而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是中國商品出口的潛在重要市場,也是所需資金、技術的主要來源地。
基於此,黨內形成了比較一致的認識:要維護中國的國家安全,就必須堅定地構築反對蘇聯霸權主義擴張的“一條線”;要實現現代化,就必須搞改革開放,必須改善同美國等發達國家的關係。鄧小平總結説:“我們的對外政策,就本國來説,是要尋求一個和平的環境來實現四個現代化。這不是假話,是真話。”“我們對自己有清醒的估計,我們實現四個現代化,需要同西方世界合作。更重要的是,在政治上對付超級大國,我們更需要合作。”
沿着這樣的大邏輯,則中國與美建交,始終堅持開放,加入WTO,等等,也就不難理解了。
還要看到的是,中國為了自己的千秋大業致力於推進中美關係發展,但在涉及國家根本利益的方面始終沒有放棄。
中美建交前,鄧小平説中美關係正常化的關鍵問題是台灣問題,台灣問題是主權問題,主權問題是沒有談判餘地的。針對美國輿論中“中國很弱很窮,裝備又落後,所以中國無足輕重”“中國現在有求於美國,美國無求於中國”等觀點,鄧小平指出:“中國儘管窮和弱,但需要中國自己做的事情,中國是敢於面對現實的。”“中國是很窮,但有一個長處,就是中國本身的生存能力比較強,還有就是窮日子過慣了。……以為中國有求於人的判斷,會產生錯誤的決策。”
鄧小平斬釘截鐵地説:“中美關係現在可能處在一個考驗時期,考驗的題目是台灣問題。在這個問題上,我們知道在美國有個論點,就是隻要美國對蘇聯強硬,美國不論怎麼做,中國人都會吞下去。這是不可能的。”
1982年的十二大提出了新時期中國對外政策的目標。“加緊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爭取實現包括台灣在內的祖國統一,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是我國人民在八十年代的三大任務。這三大任務中,核心是經濟建設,它是解決國際國內問題的基礎。”
把經濟建設作為核心,事實上也就告別了以“階級鬥爭”“反帝反修”等作為主線的國家觀。外交服務於新國策,十二大報告強調中國“堅持執行獨立自主的對外政策”。在處理大國關係時,中國果斷放棄了“以蘇劃線”和“以美劃線”的傾向,“中國決不依附於任何大國或者國家集團,決不屈服於任何大國的壓力”。
不以蘇劃線,不以美劃線,也標誌着中國糾正了單純以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來論親疏遠近的偏向,確立了不與任何大國結盟、不參加任何集團的“不結盟”的對外政策。
在百年未遇之大變局下,20世紀70年代的中美蘇大三角的提法在今天已經很不確切,中方也多年沒有過這樣的提法。
但回顧歷史,還是可以清晰地體會到中國從無數極具挑戰的實踐中獲得的真知,那就是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重要性。它為中國發展營造了良好外部環境,也為人類進步事業作出了重大貢獻。
今天,推動建設新型國際關係,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弘揚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全人類共同價值,引領人類進步潮流,是中國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選擇。新時代外交工作大局的主線依然是“緊扣服務民族復興、促進人類進步”,中國要繼續高舉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旗幟,推進和完善全方位、多層次、立體化的外交佈局,積極發展全球夥伴關係。
中國領導人説,中國走和平發展道路,不是權宜之計,更不是外交辭令,而是從歷史、現實、未來的客觀判斷中得出的結論,是思想自信和實踐自覺的有機統一。和平發展道路對中國有利、對世界有利,我們想不出有任何理由不堅持這條被實踐證明是走得通的道路。
中國希望和世界一道共謀和平、共護和平、共享和平,但也有自己的底線,無論誰侵犯到底線都堅決反對,“任何人不要幻想讓中國吞下損害自身利益的苦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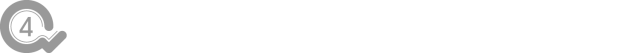
實踐出真知,而實踐需要時間。
讀史使人明智。歷史的鐘擺讓我們看到,大國關係中充滿了基於國家立場的博弈,而隨着力量消長,博弈的形態會不斷更新。中美俄之間的關係不是等邊關係,在特定歷史條件下,有時兩點之間的距離可能會近一點,但長期來看,多邊均衡才是趨勢。這包括中美之間的關係均衡,中俄之間的關係均衡,也包括俄美之間的關係均衡。而且從歷史看,再大的矛盾也不是不可調和的,只要有更大的大局觀和未來觀,以蒼生福祉為念。
烏克蘭危機從根本上與俄美的纏鬥相關,且未來可能還會有各種纏鬥,中方之所以促和為先,冷靜表態,是為了防止纏鬥升級,把世界帶入更難預料的局面,影響中國和平發展和民族復興的大局。
中國的文化和美國不同,和俄羅斯也不同,本質上是一種講求和諧、均衡、中道的文化,是不武不霸的,那種二元對立的模式不是也不應該是中國的選擇。
回到本文開頭提到的芒格在南加大的演講。他在演講中引用了哲學家懷特海的話——只有當人類“發明了發明的方法”,社會才能快速地發展。
順延之,也可以説,只有當人們“思考了思考的方法”後,才能明智地思考和言説。
在我看來,要成為普朗克那樣“真正懂的人”是非常困難的。一個人能“真正懂的”知識是很少的,可能只是在少數地方比別人更懂一些而已。即使是為了這一點“更懂”,都要付出極大努力。
芒格曾説,“我這輩子遇到的聰明人,沒有一個不是每天都堅持閲讀的”。他談到自己的夥伴沃倫·巴菲特,如果你們拿着計時器觀察他,會發現他醒着的時候有一半時間是在看書。他把剩下的時間大部分用來跟一些非常有才幹的人進行一對一的交談。“仔細觀察的話,沃倫很像個學究,雖然他在世俗生活中非常成功”。
除了不停努力,要成為“真正懂的人”,還要時刻保持獨立和清醒。經濟學家托馬斯·索維爾在《知識分子與社會》一書中説:“知識分子的擔當,不僅體現在反抗權力的蠻橫上,也同時體現在抵制羣氓的愚蠢上。”
芒格就是一位這樣既不媚權也不媚俗的智者。他在演講中説,那個司機的形象“實際上描繪了美國所有的政客”。去年11月,他在接受CNN採訪時説,“我不認為我們應該設想世界上每個國家,無論他們各自面對什麼問題,都該有我們這樣的政府。我認為這是自以為高人一等、以自我為中心的想法。”談到中國,他説“他們的制度更適合自己”。中國在經濟繁榮時就着眼於調控,而不是等到泡沫破裂再採取措施,“我很欽佩這一點,在這方面他們比我們明智”。
在不媚俗方面,芒格指出,要避免的是極端的意識形態,因為它會讓人們喪失理智。“如果你們想要成為明智的人,嚴重的意識形態很有可能會導致事與願違。”他提醒,“年輕人特別容易陷入強烈而愚蠢的意識形態中,而且永遠走不出來”。
“每當我感到自己有陷入某種強烈的意識形態的危險時,我就會拿下面這個例子來提醒自己,有些玩獨木舟的斯堪的納維亞人征服了斯堪的納維亞所有的激流,他們認為他們也能駕駛獨木舟順利地征服北美洲的大漩渦,結果死亡率是百分之百。大漩渦是你們應避開的東西,強烈的意識形態也是。”
意識形態並不是貶義詞,它指的是觀念的集合,對事物的理解與認知等等。但那種非此即彼,一定要分出尊卑高下,甚至毫無依據也一定要用口水置對方於不仁不義或加以簡單化、道德化、政治化批判的極端意識形態,必須反對。我們這樣一個文明古國,一個邁向偉大復興的民族,如果聽任輿論場裏充斥着種種這些不文明,卻無動於衷,任其蔓延,未來會通向哪裏?
根據七普數據,截至2020年11月1日零時,我國的高中(含中專)受教育人口占整個人口的15.1%,大專及以上受教育人口占15.5%,59.3%的人口為小學和初中受教育程度,這裏包括各類學校的畢業生、肄業生和在校生。這些數據説明,儘管國民受教育程度已有明顯提高,但高中以上的也只佔30%多一點。
十九大報告強調“優先發展教育事業,建設教育強國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基礎工程”。其實,我們不僅要提高國民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也要培養國民的健康思考習慣和表達習慣。
這篇文章的標題是“温故而知新”,是因為我讀書時老師教育説,不温故而知新曰妄,温故而不知新曰愚。妄加愚,也就是芒格所説的“強烈而愚蠢的意識形態”吧。
孔子説,温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本文勉力梳理中美蘇“戰略三角”的一些歷史,也是希望從歷史中學習,讓歷史啓示我們,應該創造一個怎樣的未來。

參考資料:
中國共產黨的“蘇聯觀”,崔冰,張乾,當代世界社會主義專業委員會2016年年會論文集
孫中山的美國觀,郭白晉,北京日報2016年11月07日
抗戰時期毛澤東應對美國對華政策的策略,李振,湘潮,2015(08)
十二大前後中美蘇“大三角”中的鄧小平,董振瑞,《黨的文獻》,2014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