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評價 DC 電影《新蝙蝠俠》?_風聞
segelas-自由撰稿人-电影学硕士已毕业,但仍旧略懂皮毛2022-03-18 09:57
羅伯特·帕丁森主演的新蝙蝠俠不知道各位大佬對這部電影有何看法 對這部電影的劇情 人物塑造 場景運用 音樂 都有什麼獨特的看法
談一談純屬個人的初步看法。
在接受採訪的時候,本片導演馬特里弗斯坦誠表示,自己在準備期觀看了很多美國70年代的電影。而在作品之中,我們也確實能看到相應元素在導演手中的應用落地。
美國的70年代社會,充滿了越戰影響下的嬉皮、墮落、對於暴力和性慾的野蠻伸張,這也必然地影響了同時代中的電影創作,讓其中的社會環境無論設定時代,都有着相關的黑暗傾向。並且,在這一時代的新黑色電影之中,相關的表達則更加豐富。男主角往往身處於一個墮落的社會之中,自身也受其影響而不信光明,但又由於對某一積極因素------特別是對與“黑暗”直接對立的“金髮”美女----產生愛情,從她身上看到社會的積極希望,從而對未來的一線光明產生憧憬。但在最終,這種希望又會被無情地破壞,因為金髮美女的背景並非表面上那般單純,自身往往就帶有了黑暗的色彩,將男主角帶往的也是一個巨大的陰謀,而男主角也會被隨之毀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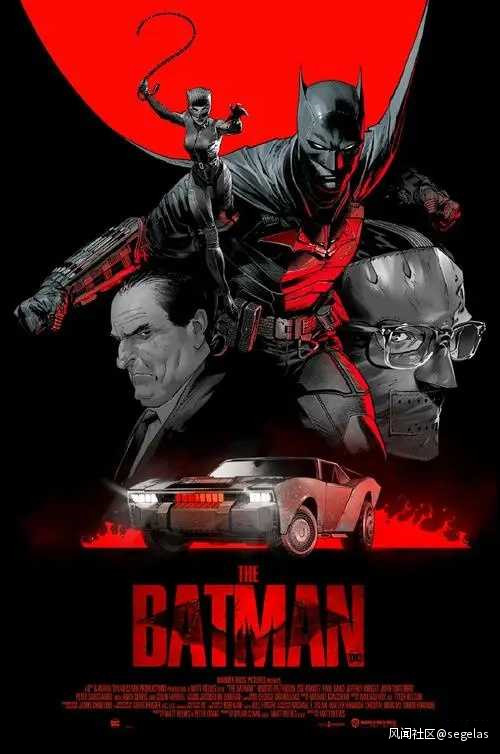
對於社會環境的表達慾望,整體的悲觀傾向,是《唐人街》這等70年代新黑色電影----以及《白日焰火》《洛城機密》《黑色大麗花》等後代的同類作品---的特徵,也或多或少地存在於《教父》和《出租車司機》等非黑色電影裏。《教父》里老教父維託對麥克、麥克對自己的人生期望,在社會現實面前凋零,引導着麥克成為教父,與凱一門之隔、黑白分離,繼而毀壞了麥克維系家庭的美好願望,讓兄弟、女兒都因他而去,給家族生意洗白的目標也沒能實現,與第二部中維託的起點完全逆反過來---身處黑暗、沾手罪惡的教父,始終於不同階段中爭取希望的心理,最終的徹底失敗。而《出租車司機》則更為明顯,特拉維斯對於美國社會之墮落的絕望,讓他如那些犯罪分子一樣,試圖暗殺總統候選人,毀掉這個世界,而又先後在貝茨和雛妓這兩位金髮女性的身上,找到了對“政治腐敗”與“沉淪色慾”的希望,而後又被二人對自己行為的逆反而破壞-----他以為自己拯救了不願做妓女的孩子,卻無視了對方與皮條客的感情存在,而當他似乎放鬆地駕駛在街區之中,後視鏡中的街景卻再次陷入暗紅色,而後更是完全的黑色。
《新蝙蝠俠》顯然對這些作品借鑑頗多。他同樣提供了一個與新黑色電影任務有所吻合的男主角,而在具體執行環節,又有了自己的變化。並且,在呈現手法上,無論是對社會環境的表現,還是對色彩的使用,以及“金髮女郎”功能的設計,都對新黑色電影有了一定更新後的挪用。

這個版本中的布魯斯韋恩,與犯罪一側的距離相當近,自身在暴力、仇恨之中的掙扎程度,也遠勝於往昔各作。在序幕之中,馬特里弗斯就利用了社會環境,傳達出了這一點。在一組蒙太奇的鏡頭之下,哥譚街區的墮落程度顯露無疑,街角處蒸騰而出的水汽、詭異黃黑色的街道,與《出租車司機》的開場如出一轍,後者那個“于越戰失利、毒品氾濫的墮落絕望中沉淪的紐約城市”,也就成為了此時的哥譚。並且,馬特里弗斯更是非常大膽地,直接將《小丑》個人電影的高潮處借用了過來-----街頭巷尾中,無所事事的人羣臉上,皆帶着小丑的彩妝。無論是《小丑》結尾處的“人人都是小丑”,還是《黑暗騎士》中小丑試圖展現人性本惡、“眾人皆我”的罪犯輪船炸彈計劃,小丑這一存在在蝙蝠俠相關電影中的動機,都是讓---包括蝙蝠俠本人在內的---社會全體之人,都展露出內心中的罪惡本質。而在本片的第一段中,哥譚社會的全貌,顯然已經變成了這個狀態。
而身在其中的蝙蝠俠,則同樣地融入了大環境中,並無太多突兀之處。“讓恐懼無處不在”的唸白,昭示着蝙蝠俠與這座恐懼之城的高度契合-----罪犯流竄,讓每一個街角都充斥了恐怖,而蝙蝠俠則同樣將其籠罩全城,唯一的區別,只是恐懼施與對象的不同。在這一段中,罪犯們對地鐵中男子的逼近到追趕,從“恐懼施加”到“暴力施加”的過程,與緊隨其後的蝙蝠俠產生了對應:先是劫匪看向黑暗處後的恐懼停步,而後是“小丑”們前面搖晃着的黑暗車廂,再是站台的深處,他不現身時,彷彿存在於黑洞一般的陰暗之中,給予所有罪犯以恐懼,而後在站台出現,給予暴力。當他從黑暗中走出,盔甲與周遭的色調融為一體。而後的打鬥,馬特里弗斯則使用了大量的遠景固定鏡頭,讓蝙蝠俠與畫着小丑妝的罪犯們同樣地處於陰影輪廓的狀態,很難分清二者區別。一系列的手法,都暗示了蝙蝠俠與罪犯的內在共性----過激的手段,極端的心態。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遠景中難分輪廓、混為一體的一對多武鬥”構圖,更是貫穿了全片,讓蝙蝠俠在罪犯打鬥、警察衝突的兩個極端之中,同樣地與對方模糊彼此,甚至與貓女初次見面時的打鬥,都是如此。無限接近於犯罪的黑暗旋渦,讓他成為了真正罪犯眼中的敵人,卻也是警察眼中與罪犯無甚兩樣的暴力者,夾在了二者中間的尷尬狀態,既不是罪犯也不是警察,卻又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共性。
這一點,當然是蝙蝠俠其角色在漫畫原作中的基礎設定,但由於本片中對哥譚整體“小丑化”的強調,這種心態就衍生了後續的內容-----所有人都成為了墮落者,蝙蝠俠的“極端”必然施加到更多人的身上,他的行為便也與犯罪無異。在序幕中的“融入黑暗社區”,到序幕結束時於墮落街道中的摩托飛馳,他的身影從代表着虛假政治的政客宣傳牌之前掠過,揚起地面上散亂的廢報紙,儼然墮落街道中的一份子,就像他身穿的黑色皮衣對未明色調的融入一樣。這種駕車駛過骯髒街區的鏡頭,在全片裏並不少見,強調着人物之於環境的“黑暗”融入度。此外,序幕裏,蝙蝠俠第一次出場,走在小丑裝扮的人羣中,深聚焦之下的他並未被突出,而是與其他人無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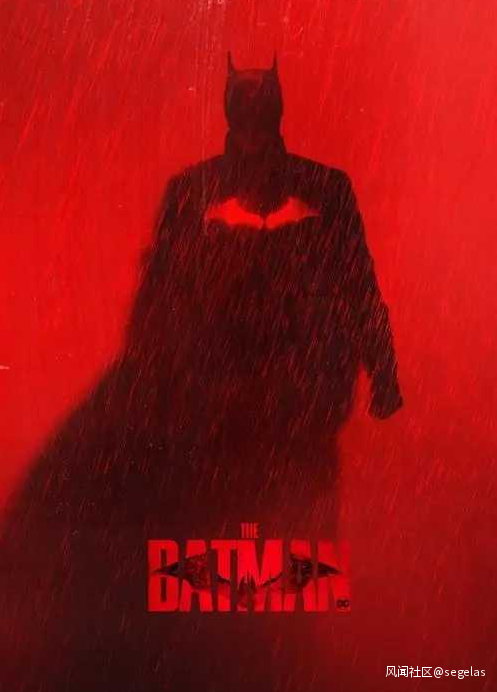
並且,馬特里弗斯也設置了謎語人這個角色,讓他成為了《黑暗騎士》中的“小丑”,起到同樣的功能-----成為布魯斯韋恩的“完全墮落”之化身。為了強調二人的共性,馬特里弗斯安排了一個貫穿作品的“望遠鏡主觀視角”。通過觀察情勢的望遠鏡視角,給出第一人稱感極強的鏡頭。對蝙蝠俠的行動、謎語人的行動,都是如此。這不僅僅是暗示了二人在概念上的粗淺對等,更發揮了“第一人稱鏡頭”的表意功能:對於人物內心的揭示。謎語人眼中哥譚的犯罪市長與法官,蝙蝠俠眼中哥譚的復仇者貓女,便是引導他們形成如今心理的關鍵,也是他們人生經歷的一種象徵性展現。
而在序幕中,望遠鏡的視角之中,市長與女兒其樂融融,假裝被其殺死。但隨之而來地,謎語人站到市長身後,被給到一個“注視”鏡頭,他眼中的市長,開始給同夥打電話-----對於表面美好的毀壞,對於黑暗內裏的展露,正是謎語人看到的哥譚,也是他感受到的人生,讓他走向了徹底犯罪的仇恨之路。而市長先被兒子玩鬧地“假裝殺死”,而後被謎語人真正殺死,也是謎語人對“希望”破壞的暗示,將親情的假死變成真死,讓慈愛的父親變成被制裁的貪官。隨後,謎語人又用望遠鏡觀察了受賄的法官,並再次施加了報仇。
在全片中,主觀性較強的鏡頭也屢屢得到了應用。蝙蝠俠駕着摩托車、蝙蝠車、空中滑行時的第一人稱與車側角度的鏡頭,讓他的運動與飛馳的街景同步起來,從而強化了他對於黑暗社會實況的感受性-----墮落到全員惡人的社會,被人物親身體驗,並讓其走入絕望。由人物飛馳於街頭、觀察街景百態的鏡頭,強調街景對人物的影響,正是《出租車司機》的主要手法。而屢屢出現的“眺望哥譚”鏡頭,則是對此表意的延伸。由此,作品主線得以展開。
而蝙蝠俠,也在一個側面上吻合了謎語人。首先,序幕的二人便有了高度的對等:謎語人殺死了有罪的市長,蝙蝠俠則對有罪的惡徒使用電擊棍的暴力,且二人甚至都用了“猛砸頭部”的狠辣招數。此外,在電影中,圍繞他的“觀察”、以及延伸出的“眼睛”,馬特里弗斯做出了相當多的設計。序幕中,他走在小丑們的街頭,便給到了他眼睛的特寫,而後則是給眼睛抹上黑色、摘下隱形眼鏡攝像機的先後特寫。自然,也會有他的望遠鏡視角,讓他觀察着企鵝人夜總會中的罪犯。

而他的隱形眼鏡攝像機,則是對望遠鏡要素的延伸,成為了對他的主觀表現。它拍出了他對小丑扮相罪犯的暴力毆打、對方的痛苦哀嚎,也拍出了一系列的犯罪行為。這便是他觀察到的哥譚世界,讓他產生希望不存的感覺,吻合着他從電影隱去的父母之死即開始的具體經歷---在本片的敍述內容裏,市長意料之外的墮入犯罪、政府官員隨着調查而漸次浮出水面的罪犯真相,都構成了對蝙蝠俠“絕望於哥譚”的推動。在另外一些時刻,他也在望遠鏡中看到了想要報仇的貓女,更在隨後與貓女合作、深入夜總會的時候,看到了呈現在隱形眼鏡畫面中的景象---貓女一意孤行,摘下隱形眼鏡,合作失敗,她欲取他人性命的復仇之心,似乎只是又一個被哥譚吞沒的存在。
此外,“眼睛”還有着更多的運用部分。在很多觀感中,“布魯斯韋恩的淡化,蝙蝠俠的強化”都是共識。本片之中,他以蝙蝠俠裝扮的出現次數,要遠遠大於身穿西裝的“布魯斯韋恩”。並且,馬特里弗斯還用一組“給眼部塗上黑色化妝”與“洗掉黑色眼妝”的鏡頭,特意強調了其與蝙蝠戰衣融為一體的眼睛。隨之,當他難得地以韋恩的身份出現時,也往往是“黑色”的眼睛,有時候是墨鏡、頭盔,有時候則乾脆是不去掉眼妝。這種日常狀態下的“蝙蝠俠化”,表現出了他此刻對於“蝙蝠俠”這一暴力極端的完全傾倒,而作為制衡的“布魯斯”則已然淡薄----在阿爾弗雷德建議他穿上西服,應付一下公司股東們、維持瀕臨破產的家族企業的時候,他説“我不在乎那個”,明確地與“布魯斯韋恩”的人生做切割。在大部分作品裏,“大富豪布魯斯韋恩”都是他的掩護身份,但在本片中,他根本不想要這層掩護,也更不需要其提供的“日常”去平衡內心,而是徹頭徹尾地扎入“蝙蝠俠”之中,走向不加遏制的極端暴力。
而在另一方面,蝙蝠俠卻又想要獲得一線希望,他試圖從各種人身上看到光明。“青少年”這一年紀輕輕、象徵“未來”的存在,成為了第一個。在序幕中,那個只畫了一半小丑妝的少年,暗示着其內心的良心未泯,並沒有對受害者動手,也自然地被蝙蝠俠放過。而市長的小兒子,則由於其人生經歷,成為了蝙蝠俠的一次自我回溯-----他與蝙蝠俠一樣,都在少年時代因暴力犯罪而失去了父親,且隨後可知,二人父親都有着不為所知的非正義一面。蝙蝠俠看向他,無疑感到了其與自身的共性。而後,蝙蝠俠對他的一系列“拯救”,從市長葬禮上幫他躲過汽車衝撞,是對於曾經自己的二次機會給予。這是他對於哥譚未來的一線希望,同樣也是對自己人格的一種期待:如此經歷的人,並不一定會墮落。

電影中,貓女當之無愧地成為了一個非常明顯的“金髮女郎“----二者隱約之間的愛情,蝙蝠俠試圖將她帶回光明面的“拯救”意圖,自身與黑暗關聯,擁有着對於男主角的“秘密”。然而,出於具體作品的需要,貓女顯然不會真地執行到“讓男主角深陷陰謀,墮入黑暗旋渦”那一步,那是謎語人的職責----一個更加接近本質的“金髮女郎”。“金髮女郎”的功能被分割為二,分別被不同角色承擔了一個側面。
馬特里弗斯充分地利用了謎語人“給蝙蝠俠猜謎”的漫畫設定,讓他自己完成着對一個又一個貪官污吏的制裁,又用謎語對蝙蝠俠做出“引導”的具體行為,帶着蝙蝠俠一步步地走進黑暗,跟隨自己。實際上, 謎語人便是黑色電影裏“金髮女郎”的邪惡本質化身,讓蝙蝠俠情不自禁地被他的謎語“吸引”,走向最終的絕望墮落,只是出於本片要求,而不會完成那最後一個環節。而在另一方面,由於謎語人與蝙蝠俠的高度共性----甚至在裝扮上,本版的謎語人都戴上了與蝙蝠俠類似的面具,而不是原漫畫的禮帽形象-----,他又成為了蝙蝠俠在黑暗一側道路上的“終點”,讓後者逐漸走近自己,觀看到一路上的政府墮落之相,意識到世界的全盤邪惡、無可救贖,從而成為自己。
《出租車司機》之中,導演馬丁斯科塞斯用了暗紅色,作為對墮落社會之“地獄景象”的象徵。這一個用法,也被搬到了本片之中,對應人物對於社會的絕望、隨之產生的極端。蝙蝠俠的出場打鬥段落裏,無論是夜總會,還是地鐵站,甚至微型攝影機的“眼睛”鏡頭裏,都會充斥着濃厚的暗紅色。而當貓女兩次前往夜總會、欲報私仇,她的假髮同樣是暗紅色。 並且,暗紅色與黑色混合,遍佈了大部分場景裏的午夜哥譚,提供了與《出租車司機》的夜晚紐約——以及新黑色電影們——如出一轍的地獄氛圍,讓蝙蝠俠身處於這等犯罪的天堂中,自身融入併為之影響、同化,就像他對所有的官員警察都全無信任,在對抗世界之中愈發極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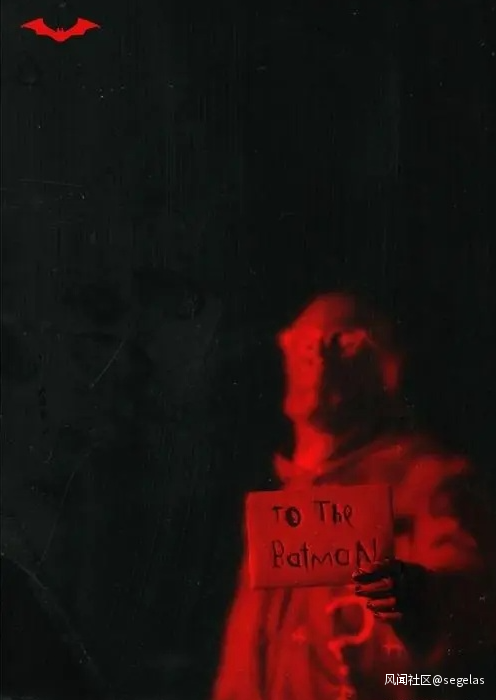
第一小時中,馬特里弗斯完成了種種的鋪墊。而在敍事層面上,一個真正的重擊,則是市長的葬禮段落。主角難得地----如阿爾弗雷德所説-----換上了西裝,衣冠楚楚地成為了布魯斯韋恩,參加市長的葬禮。而當他步入葬禮現場時,聖潔的宗教合唱, 教堂穹頂上透入的明亮陽光,也加成了“希望”的氛圍。然而,隨之而來的,卻是一系列的破壞。先是黑幫大佬法爾科內對自己曾被布魯斯父親拯救的敍述,讓布魯斯意識到了父親善良之舉只是救活了一個罪犯的無意義,而後則是警察對自己的殷勤招呼,曾經其人卻對作為蝙蝠俠的自己阻攔惡語,十足地趨炎附勢。
這兩處小的鋪墊,被隨後的高潮引爆。謎語人站在逆光的地方,挑釁着這種“聖潔”,並用犯了罪的法官徹底毀壞了葬禮。此時,在謎語人拿着炸彈的謎語逼問之下,法官被迫承認了自己的受賄,就此完成了對布魯斯朝向黑暗的“引導”。而巧妙的是,在謎語人和布魯斯的相繼發問之下,二人彷彿合為了一體,施壓法官,暗示着布魯斯此刻對暴力一側的極度傾斜----第一個謎語中的“極端暴力的正義”之答案,結合着上述一切,已經足以讓布魯斯動搖。
而在葬禮之後,布魯斯的傾倒於黑暗,則更加直觀。他被警察用槍指着,隨後更是被關了起來,大打出手,已經完全是一個"罪犯"。並且,當他逃出警局時,滑行到一半的倉促摔地,也展現出了他此刻作為“義警”的極度動搖。這種動搖,在他與貓女看到了貓女希望拯救的朋友被殺死、感到自身的無力後,又更進了一步。與之同步,貓女的“絕望“也在又一次的喪失親友後,繼續加深。
伴隨着這種進展,蝙蝠俠的暴力極端一面也就愈發明顯。當他追擊企鵝人的車時,無數個企鵝人的“回望”鏡頭,從蝙蝠車點火於黑暗角落,到蝙蝠俠窮追不捨的碰撞尾隨,再到逼迫企鵝人迎上罐車,始終出現在後視鏡裏的陰魂不散,都讓企鵝人恐懼大叫。他成為了完全的“黑暗之子”——追車時始終存在的暗紅色與黑色,就像《出租車司機》裏特拉維斯駕車遊蕩的“墮落紐約”,而最後衝出火焰的車形,則宛若衝出地獄,倒地的企鵝人視角下的背向火焰、緩緩走近,更是讓他的地獄形象加深。企鵝人眼中的被倒置,正是對此刻蝙蝠俠“正義英雄的反面”屬性的強調。

而與此同時,謎語人與此刻蝙蝠俠的高度共性,也得到了推進。他留下的謎語顯示了他的孤兒身份,與蝙蝠俠擁有承受暴力犯罪的同樣人生經歷,而他少時所在的韋恩孤兒院,更明確了與布魯斯韋恩成長環境的關聯。邀請蝙蝠俠進入孤兒院,是他對後者向“極端暴力的布魯斯韋恩”之自己的引導。這樣的引導之下,蝙蝠俠對於哥譚中人的善惡判斷,逐漸被帶上了極端的道路----“眼中的世界”式的鏡頭,強調着他對於世界的觀察與感受,而如上所述,他觀察到的東西,從序幕裏的“到處是犯罪”,到跟隨謎語人腳步發現的被制裁對象們,正是一個個的好人黑化、壞人更黑,也是貓女的難以拯救,從而對這樣的純黑世界徹底喪失信心,自身融入黑暗環境,成為了一個等同於”謎語人“的存在。而隨着謎語人引領他來到孤兒院,自身與蝙蝠俠開始在個人背景上明確吻合,而他對蝙蝠俠的”毀壞希望“也開始明確化----播放了布魯斯父親”激情演講“的錄像,並寫出一句”父親的罪惡“,提示了托馬斯韋恩“並不那麼絕對正義”得一面。
謎語人讓蝙蝠俠看到了自己最崇拜之人的另一面,對他造成了最大的打擊,並重傷了阿爾弗雷德。父親作為黑暗中光明的”隕落“,以自身信條而無法保護家人,雙重打擊了蝙蝠俠,動搖着他作為”非極端義警“的自覺。在這一段中,蝙蝠俠褪下戰衣、洗掉眼妝,變回了非極端的”布魯斯韋恩“,但他的動搖姿態看上去無比軟弱。”蝙蝠俠“與”布魯斯韋恩“,分別代表了他”非黑暗“與黑暗的兩個側面,此時”布魯斯“的軟弱,便意味着”蝙蝠俠“的上升,比之後者已然存在感爆棚的前半部而言,”得寸進尺“地愈發有力起來。
在此時,馬特里弗斯依然留下了希望一面的存在——蝙蝠俠與戈登逼問企鵝人,後者一句“你們在唱雙簧嗎”,讓二人與此前逼問法官科裏森時一唱一和的蝙蝠俠與謎語人,構成了一些呼應:那時的蝙蝠俠是“謎語人”,此時則是“戈登”,兩面性依舊存在。更重要的是,當他與阿爾弗雷德對話,瞭解到父親“保護家庭”的初衷,變得平靜下來,承認了自己作為布魯斯依然存在的、對失去家人的恐懼感,與後者的雙手緊握,象徵着他作為與後者關聯密切的“布魯斯韋恩”的強化---直到此時,不帶有蝙蝠俠痕跡的“布魯斯韋恩”形象,才在電影裏首次展現了不軟弱、無力的一面,與此前從法爾科內口中得知父親真相時的失魂落魄對比明顯。

對於布魯斯父母被殺的不做呈現,是本版比較大膽的設計,這是由於父親形象在本片中的獨特作用。在表面劇情上,父親是為了保護妻兒,擋住了匪徒的子彈,從而率先死亡,這是一個絕對正義的形象。然而,在馬特里弗斯的設計裏,父親的形象並非絕對正義,有着搖擺模糊的本質,動機善良而手段曖昧。另外,在前半部中,蝙蝠俠的初始傾向已然較為極端,而布魯斯韋恩的存在感較為淡薄,直到後半部才有所好轉。因此,電影並未給出直觀的正義形象,只是讓其作為背景設定出現,讓人物作為”布魯斯“的日常身份淡化,突出其作為”暴力極端者“蝙蝠俠的屬性,同時也為後續父親的非絕對正義做了鋪墊。
事實上,也正是父親的非絕對正義,形成了對蝙蝠俠自我開解的關鍵------阿爾弗雷德的話,讓他明確了“維護正義”時中間狀態的存在,讓自己的手段暴力與內心正義,找到了對標典型。隨着二人的一席談話,布魯斯韋恩的存在感首次堅定起來,隨後前去阻止再次戴上暗紅色假髮的貓女,讓她不要走向徹底的殺人報復之路。
可以看到,與蝙蝠俠有着同樣“親人被殺”經歷的貓女,是他的又一個對應。她從一開始的“暗紅色假髮”一面,滑向復仇殺人的極端,成為了蝙蝠俠在片頭自稱的“復仇者”。而蝙蝠俠最終從她手上帶走法爾科內,拯救了她,也意味着自己的轉向。此時,蝙蝠俠救下了貓女的性命,也阻止了她“想要殺人復仇”的墮落——他挽回了與自己類似的復仇者,也就是挽回了自己,制止了自己對法爾科內同樣的殺欲。
可以看到,同樣的親人被殺、自己被拯救、與蝙蝠俠經歷吻合,讓貓女成為了前半部裏市長兒子的一種延續,成為了蝙蝠俠的又一個側影。前半段,蝙蝠俠救了孩子,卻對社會更生失望。而到了結尾,他救了貓女,對社會則生出希望,同樣也是“救了自己”。這不僅是戲劇結構上的呼應,也是對於蝙蝠俠人物塑造的加成。

在高潮段落中,貓女與謎語人,作為蝙蝠俠在兩個方向的化身,形成了對立的關係。蝙蝠俠拯救了貓女,留住了“積極的自己”,也必然要去擊敗那個“消極的自己”。這就帶來了那個看似略顯疲軟的“高潮大戰”——並沒有直接對戰謎語人,而是讓他早早被捕。無疑,只有讓謎語人與蝙蝠俠形成對話,才能讓他的“引導”升級,從猜謎變成直接的撩撥,從而給後者以極端一側的最大考驗。他先殺死了蝙蝠俠與貓女想報私仇而壓抑下來的法爾科內,讓蝙蝠俠看到“信條”的無意義,宛若之前的貓女閨蜜之死、阿爾弗雷德重傷,加上刑訊室裏的勾引挑逗,讓蝙蝠俠暴怒,滑向“復仇者”的方向——他餵養蝙蝠,並將自白書放進蝙蝠籠,暗示着自己與蝙蝠俠的合一。“代替蝙蝠俠,執行對犯罪者的大清洗,並讓蝙蝠俠也成為這樣的自己”,正是謎語人的目標。
顯然,到了最後,電影的一切終究要落回到始終強化的“對社會的感受”層面上——謎語人要讓表面光鮮的大選坍塌,讓人們露出黑暗的內裏,展現這一切給蝙蝠俠看,讓他明白“眾生皆罪惡”,從而來到自己的這一側。只有如此,才能托住全片延續的人物與環境之交互,給予主題層面——而非漫改傳統模式的“動作”層面——的高潮。
結尾處,蝙蝠俠對人們的拯救,暗紅色火折變成明亮火焰的變化、一掃開頭“黑暗街頭的自語”的“陽光城市裏的自語”,包括更早前段落裏、與片頭“走過敵視警察”對應的“走過敵視流氓”體現的歸屬陣營轉變,也讓蝙蝠俠終究經住了考驗,成為了遠不同於“復仇者”的英雄。警察為他展現出的“並不是全部被法爾科內收買”,讓他的希望有了發芽的基礎。“對貓女的個體拯救”,擴大到了“對社會的羣體拯救”。而謎語人在陽光中的虛化,也象徵了蝙蝠俠這一側人格的淡去。
無論是刑訊室的勾引,還是最後對蝙蝠俠引導入絕望的“展現人性”,以及對蝙蝠俠“成為自己”的目標,電影對謎語人的設計,都有着《黑暗騎士》的影子。然而,稍遜一籌的是,後者裏的小丑,讓蝙蝠俠經受了初戀被殺、白色騎士哈維丹特墮落的巨大打擊,從而生出了不可遏制的報復之心,而對船上囚犯的考驗也更加深刻。這樣一來,蝙蝠俠的“殺”更有動機,“不殺”更加困難,而囚犯們展示給他的“社會希望”,也更加明確。

到了本片裏,他的不墮落,起始於對父親“非絕對正義,卻也非邪惡”的理解,讓他重建了對“光明仍然存在”的信心,進而有了對如今這座哥譚市的一種接受——一迎接他的是被法爾科內收買之外的那部分警察,而在結尾處的企鵝人也同樣沐浴在了陽光裏。世界被黑暗籠罩,但仍有希望之光,人心並非絕對正義,但也絕非全體的徹底邪惡。任何作品中的蝙蝠俠,都在糾結於自己行為的正邪定義,也會迷惑於被拯救者們的價值幾許,而本作給出的開解出路,或許是較為接近現實狀態的。
遺憾的是,這種“由家人到世界”的信念傳導,在片中的展現顯然太短了。作為開解關鍵的父子情感線索,出現、發展、收尾有些倉促。當然,重中之重的“對社會的感受”層面上,蝙蝠俠眼中的社會管理羣體,其對於蝙蝠俠的反饋,還是得到了比較完整的表現,前者對後者從“全員皆黑”到“看到正義”,後者對前者從“排斥牴觸蝙蝠俠、只接納布魯斯”到“支持蝙蝠俠”,串聯起了整個作品,構成了蝙蝠俠看待社會的心緒轉變過程。然而,作為直接轉折的父親,是布魯斯心中的絕對正義者,也在其光環打破後將布魯斯直接推向極端方向,又由阿爾弗雷德的“為了家庭”而演生出對“正義”的最終理解,是對於世界看法之變化的凝聚存在,其信念的變化直接影響到對世界的看法。這種設計本身是恰當的,但在片中卻被表述“人對世界的感受”“感受的直觀呈現”等環節搶去了風頭,有些過於輕飄了。

比起諾蘭,馬特里弗斯給出來的東西,顯然單薄了很多。本作以蝙蝠俠個人為中心,展現他感受社會而生的心理變化過程。貓女、謎語人、市長兒子,諸多的角色都以他的“某一側面的化身”而存在,通篇的氛圍、腔調,也都極其出色地調動起了觀眾對其的直接感知。但是,在關鍵的轉變推動環節上,本作卻不幸地差了一口氣。它的情緒表達非常飽滿,就像通篇裏執行相關功能的暗紅色一樣飽滿,但在文本架構上,卻相對不那麼紮實了一些。過度聚焦於單線、配角功能化、情緒濃重而導致時間拉長後的疲憊,於本片圍繞“主角感受”的出發點下,都不是問題。但是,關鍵環節的單薄,卻是不可彌補的。
這讓它成為了一部表達欲極強的個性化漫改電影,但卻離“它應該拿奧斯卡”的《黑暗騎士》,終究還是拉開了一段距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