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2022年看“DC 超級英雄比漫威超級英雄更有深度”還成立嗎?_風聞
segelas-自由撰稿人-电影学硕士已毕业,但仍旧略懂皮毛2022-03-24 09:14
借用之前關於扎克施耐德版《正義聯盟》的內容,圍繞電影層面的“DC角色深度”,談一談個人的看法。
這部作品的掌舵人,是以“挖掘人物內心”為重點的扎克施耐德,在完全掌握創作自由度後的成品,也是他掌管的DC電影”閉環“的收束之作。體量之龐大,讓它成為了理論上的“扎式深度超級英雄”的完全體。
而從成片上看,扎克基本上證明了他在獲得充足自由度與資源支持後的能力,終於完成了自己從《鋼鐵之軀》便開啓的個人主題。然而不幸的是,在另一方面,扎克也又一次、甚至更加地證明了他的創作侷限----只有在充足自由與資源下,他才能完成作品,而這樣的作品也只是表達完整,而談不上頂級。而伴隨出現的,便是DC電影----至少在目前階段之下-----的“人物深度”證偽了:並不是拋棄一切基礎設定的“黑死殘”,便是“深度”,而”深度“也不應該是任何的概念,必須與人物塑造的完成度息息相關。

扎克以超人之死開頭,直接指向了“單純依靠神力不足以拯救世界”的信息,給出了對“完全依靠神的絕對正確與絕對力量之下的反烏托邦社會形態”的否定。人類社會對於神級英雄的反饋,他們的膜拜與質疑,是扎克以“全宇宙第一部”《鋼鐵之軀》的人神共體內容為基礎,上升後的第二層主題。這也與扎克的偶像諾蘭對《蝙蝠俠》三部曲的操作類似,讓英雄與社會形成高度的聯繫互動——第一部的接受自我身份,第二部的堅定人性本善後的行為意義牢固,變為第三部中由“個體拯救社會”到“個體精神感染社會”的羣體英雄意識崛起,完成了對英雄之於社會意義的討論。
在此前的《BVS》中,藉助超人和蝙蝠俠的對決,扎克已經在鋪設這個主題,並在結尾通過瑪莎,建立了蝙蝠俠與超人基於人類感情的連接,讓蝙蝠俠看到超人的人性一面,而超人也展現出了人神意識兼容狀態下為世界提供己之所能的徵兆----作為克拉克挽救了愛人露易絲,而後作為超人使用神力(壓制了讓他的神之力量削弱的氪石,體現出他神力屬性的爆發),作為救世主而自我犧牲。但是,這樣的結尾,並沒有解答扎克的終極問題。他體現出了超人的人神合一,也展示了人神合一而後面對世界的理想化狀態:神的絕對力量與絕對正確,與人類自由選擇提供的可能性混合。但是,超人最終還是靠着神性的一面拯救了世界,而作為人類的蝙蝠俠則顯得無能為力。神絕對統治引導出的絕對正確社會,顯然成為了一種限定性極強的存在---神需要犧牲自己才能完成保護,這一方面體現出了人類在面對社會時的無力,但在另一方面也一併體現出了神之絕對統治的同樣無力。以社會掌控者而言,人類是弱小的,但神的“絕對力量”也只是消耗品一般,不夠強大。
扎克施耐德的DC電影宇宙,如果以三部曲而觀,有着自己的主題遞進性。第一部的《超人鋼鐵之軀》裏,主人公在克拉克與超人的雙重身份之中糾結,並最終堅定自我,確信了人類身份下克拉克之自我的真實存在,從而讓扎克實現了人性與神性的統一主題。第二部的《BVS》裏,扎克開始提出社會理想形態的主題層級,讓克拉克面對人性的複雜而產生混亂, 另一方面,也讓社會處在了對超人神權的頂禮膜拜中,加入美國政府的存在,表達社會對待神權的另一面態度,布魯斯更代表了秉持自由意志反對神權、建立人權社會的人類,與超人對抗。而人權社會的不完美,也在蝙蝠俠一度誤入的暴力欲與萊克斯竊取神力的膨脹心之中,體現無疑。最後,扎克用瑪莎再次堅定了超人的人性,而後用超人之死展現出神權社會的侷限性---無論人類還是神,都無法在社會引導中保持延續性,在真正的巨大力量面前顯得非常弱小。而第三部的《正義聯盟》,則是最終的答案。

在神性的自我犧牲下,世界得到了拯救,但這顯然無法成為長久的常規性狀態。《BVS》的結尾,扎克承接此前超人作品中對於個體人神雙性統一的表達,將佐德與克拉克之戰中有所指示的社會理想形態之論,擴大到了超人和蝙蝠俠之戰的明確形式上。克拉克是人神共體的,但在社會統治角度看,在《BVS》超人對蝙蝠俠這一“神與人的二元對立”架構下,超人在毀滅日之戰中的救世作用遠遠大於蝙蝠俠,神性的力量終究還是壓倒了人性的發揮。在結尾,人類完全無力,只能在敵人的攻擊面前像蝙蝠俠一樣“糟糕了”,然後閉目待斃。同時,扎克又弱化了完全神權的力量,讓超人必須靠犧牲才能拯救世界。神留下的人類,去面對自己相對於神的無力。
單純的神力有巨大的侷限性,理想的世界、合理的答案,還沒有浮出水面。這正是《正義聯盟》需要解決的。扎克在開頭部分藉助超人之死,展現了蝙蝠俠和露易絲等人類在此時的動搖表情。面對毀滅日無能為力的蝙蝠俠,意識到人類的侷限,而產生對神的依賴,但神又隕落了,讓人類產生了自己應該如何領導社會的困惑。由此,電影重申了《BVS》的階段性主題,而後引出了《正義聯盟》的新主題。在以章節劃分的影片主體中,扎克施耐德動用層層線索,完整到有些繁瑣地推進着對於主題的探討表達。
第一幕的名字,是“別指望了,蝙蝠俠”。這句話是布魯斯在第一次尋求海王入夥時得到的回覆。布魯斯組建正義聯盟的行為,與《BVS》結尾和《正義聯盟》開頭部分,構成了緊密的銜接。他先是作為人類反抗神權,但在毀滅日之戰中無所作為,意識到了自己作為人類的無能,因此想要依賴神的力量,偏向到了神權社會一邊,且略顯極端---目睹了超人“個體神”的力量侷限,就轉而尋求對“眾神”的組建。而神的力量,在神奇女俠出場部分中也得到了體現:大橋上掛着超人的標誌,體現着人類羣體與布魯斯相同的心境;而後銀行搶劫,劫匪向警察致意的肆無忌憚,與警方“不要開槍,裏面有孩子”的無能為力形成對比,劫匪的仰拍鏡頭與警察的俯拍鏡頭形成對比,在相對力量關係上強化了人類在力量與危機前的侷限。女俠舞動真言套索的登場,對罪犯拷問的一組正反打,則變成了女俠的仰拍與罪犯的俯拍,慢鏡頭下女俠擋住子彈的英武,強化了神之力量的偉大。
然而,在這場戲中,我們已經可以看到一絲鋪墊了----女俠拯救了人質,但如果沒有罪犯突然放下手槍、轉用機關槍的偶然決定,女俠終究趕不及。神力也有侷限,就在於此。至於出路,也經由女俠對女孩説的那句話得到暗示,“你可以成為任何人”---人類對於自己命運的自由選擇,人類自身對於社會的把控權利,是不能在自身的弱小與神力的強大之前丟失殆盡的。自由選擇權利的提出,自由意志的強調,與人類社會對超人神體的不同態度的刻畫一起,構成了電影從單純的“人性神性”層面上升,將主題引導到“人權社會與神權社會”方向的明確指引。顯然,這種衝突,與英雄自我認知上的人神糾結,有所區分。
因此,布魯斯依靠神力集合、對人類力量感到失望的想法,勢必是失敗的----他聚集女俠、海王、方盒力量的鋼骨、宙域統治者綠燈俠,依然在荒原狼和達克賽德面前不是對手。在第一次拉攏海王的段落中,扎克用兩個細節暗示了布魯斯此舉的內在心理---酒館中的人類,雖然説着“別小看我們”,但依然拿走了布魯斯的錢;隨後,面對跳入大海的海王,一個女孩唱起了聖歌,並對海王留下的衣服待若聖物,暗合着布魯斯的心境。人類的陰暗面與不完美,構成了人類對於社會引領中的侷限性,因此人類膜拜着完美的神力。然而,只有神力也終究無法達到理想化的社會狀態,就像海王拒絕了布魯斯的要求,排斥了他對自己的依賴一樣----別指望了,蝙蝠俠。
這樣的表達,在第二幕中繼續得到加強。標題“英雄時代”,形成了一種反諷式的效果。這一幕的開場,是破敗的宇航員海報到窗外荒原狼召喚大軍的移動鏡頭。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表達---人類衝上宇宙與宇宙軍團降臨地球,是一組對等的關係,而破爛與浩大的現狀對比,則成為了人類在絕對力量面前的弱小。在這樣的弱小下,人類才想要依賴神力,迎接“英雄時代”。然而,這樣的“英雄時代”,事實上早已淪落:緊接着這段開場的,便是亞馬遜人不敵荒原狼之後,向人類世界發出求援火炬信號的段落。人類想要依賴神的力量,就像布魯斯那樣“聚集眾神”,或者像第二幕中的鋼骨之父一樣,開發等同於神之力的母盒和氪星飛船,甚至像“極端化的鋼骨之父”萊克斯那樣,先試圖控制超人,再借用氪星之力製造毀滅日。然而,神戰的結果證明了:人類才是需要被依賴的那一方。
人類的過於被動,在他們面對火炬的無反應中得到了暗示。在神廟之前,鏡頭的對焦從外圍百無聊賴的人類警察切換到女俠,而後女俠---而不是人類----點燃了火炬。作為人類世界回應神界請援的,卻依然是一個神級的存在。人類在做的,只是用各種各樣的方式依賴神力。這樣的結果,鋪墊到了鋼骨之父接受調查的部分:研究母盒力量的他,在面對荒原狼手下畫像時,只能回以懵逼。扎克用一個對他身處走廊的拉遠鏡頭,配合以眾人的死寂和色調的昏暗,渲染出了他作為人類的無力絕望感。
在這一段引導的線索中,有一個非常有趣的部分:荒原狼被扎克賦予了主題表達者的身份,而不是單純的反派。在他首次闡述自我內心的時候,他稱“應該剝奪人類的自由意志”,這直接指向了主題,對應着女俠的那句“你可以做任何人”,也對應着當前人類放棄自我、依賴神權的狀態。而荒原狼自己,也放棄了自己對“更高神”達克賽德的反抗(“你本可以反抗的”),跪倒在他的力量之下,丟掉了自己的自由意志。

這樣一來,達克賽德和荒原狼的組合,無疑成為了一種力量更高的“神權社會體系”。它能夠壓制同樣仰賴神力的人類版神權社會,但會在人權與神權合一的完美社會形態中敗北。這種相對勝負關係的階梯狀分佈,便構成了扎克的主題呈現過程。事實上,在第二段的末尾,扎克已經給出了理想狀態的呈現----在遠古之戰的閃回中,眾神聚集,但其中也有人類大軍的存在,集結人、神的多方之力,才最終戰勝了達克賽德的大軍,這也正是三個方盒分別給予了人類、亞特蘭蒂斯、亞馬遜的原因:扛起世界責任的羣體中,必須有人類的力量存在。
“英雄時代”,並不是神的時代,而是神與人類共稱英雄的時代。這便引出了下一個章節:“摯愛的母親,摯愛的兒子”——指代失去兒子的瑪莎,將被全世界當作神明的超人,視作人類克拉克的老母親。這也是電影中,布魯斯---以及此前稍縱即逝的人性戴安娜---以外的超級英雄們,第一次以人類的形象出現。承接“英雄時代”最終給出的信息,第三幕開始展現英雄們人性的一面。第一幕中,布魯斯將亞瑟單純地作為亞特蘭蒂斯之神進行招募,而在一組“警告牌”與“無視警告入海的海王”對比鏡頭中,亞瑟也確實只是非人類的神明存在,因此布魯斯的招募必然失敗,而到了第三幕,超級英雄開始展現出人性,成為我們熟悉的“人神共體”,而布魯斯與之建立在人性情感交流上的招募,便會逐漸成型。
在這一幕中,扎克讓維克多、巴里艾倫、亞瑟正式登場,進入正義聯盟組建的重要環節。而在推動劇情前進的同時,扎克對初次登場的新人物進行基本背景的介紹,也藉助這個部分,讓他們的人神共體性得到了初步的展現。在鋼骨的部分中,維克多發現了自己“改變世界”的力量,手中握着從上古到當代的所有知識。而他所做的,卻不是推動世界發展,而是利用力量,給了老人一筆獎金,人性一面得到了展示。而鋼骨接受改造之前,進行橄欖球比賽時奮鬥揮灑的特寫慢鏡頭閃回,在意識世界中迴歸人類少年軀體的樣子,在現實世界中的機器人形態,在畫面中連續切換,特別是後兩者的畫面銜接時、鋼骨與維克多高度一致的動作,讓鋼骨/維克多的兩面性躍然而出。而在閃電俠和海王的部分裏,扎克則從二人的愛情萌動心理切入,大量地展現了閃電俠少年的嬌羞與話癆,海王從荒原狼手中救下媚拉時的深情對視。甚至無需基礎介紹的女俠,也表現出了更多的女人一面---與布魯斯不經意間碰手後的迅速收回,隱約帶出一些愛情的影子,在阿爾弗雷德的教導下笨拙地嘗試泡茶。

這一系列的人神共體表達,以蝙蝠俠接到閃電俠時的廣告牌、女俠會面鋼骨時的台詞得到落地----“你並不孤獨”。在這一段中,英雄們都展現出了自己的人性,而塑造的“人神共體中的孤獨感”,正是他們在人性一面的細膩情感,才讓自己倍感痛苦。作為非純粹人類,鋼骨在街頭忍受着路人的驚詫眼光,閃電俠的話癆中隱藏着他對於人類交流的極度渴望,海王在救人後被注視着離開酒吧,女俠也如自己所説--“我也曾經放棄過”---地,離開人類社會一百年(扎克施耐德版本的原有設定,後被華納刪除)。但是,他們的人性心理,無疑不能承受這樣的孤獨感,於是”聚集起來“,便成為了合理的出路。
基於人性、而非神性的組隊,互相將彼此從人神共體的孤獨感中解救出來,才是布魯斯和戴安娜組建正義聯盟的成功之路。在第三幕中,布魯斯/戴安娜和閃電俠/鋼骨的交流,對比之前的布魯斯對海王,明顯地更加擁有了人性的温度。正義聯盟從單純的“對抗荒原狼和達克賽德”的淺層意義升級,成為了主題中“理想社會”的一種縮影----半人半神的存在,聚集起來,將人性與神性進行結合。而引導出這一切的,恰恰是純人類的布魯斯:面對閃電俠“你的超能力?”的疑問,布魯斯“我有錢”的回答,明白地強調了他作為非神的純粹屬性。作為推動者的單純人類,彰顯了面對社會危機時,人類力量的存在感,暗示着人類在這個理想社會中的地位。
扎克想要在一部電影的容量中,加入大量的新人物、新線索,像往常一樣,以量的堆積代替質的不足,通過超多線的思路去共同托起自己的表意主題。但相比以往,他相對地考慮了劇情推進與主題表達的並行,沒有將二者完全分離,而是將新人物介紹與人神共體表現相結合,將正義聯盟“從失敗到成功”的過程,當作“人類從依賴神性到人神結合的社會形態變化”的隱晦象徵,甚至將荒原狼這個反派角色,從單純的“作惡--捱揍”工具人,變成了主題表達的反向側面,“放棄人類自由選擇權後的神權社會信徒,敗於人神結合的理想組合”。而達克賽德想要征服的,也正是刻在地球上關乎於“自由意志”的反生命方程式。
在一定程度上,這還是提升了扎克一向較弱的劇情推進節奏問題,展現出了相對而言更好的敍事效率。並且,扎克也嘗試着對棘手的“蝙蝠俠的存在感”問題進行合理化處置----他代表純粹的人類,與反派小兵的苦戰,符合他的較弱戰鬥力,但也體現出人類“不依靠神力,自己把握命運”(對應“自由選擇權”)在危機中的存在感。在戰鬥中的較弱表現從單純的“弱雞尷尬”升級成了主題表現的一部分,豐富了布魯斯的人物呈現。
其後,在高潮段落戰鬥中,布魯斯強調“無論如何都要執行我的戰術”的自信佈局,以及隨後在戰鬥中藉助戰機把握與敵方武器的活躍,始終給到的“蝙蝠俠搶佔敵方炮台並遠程火力掩護”的鏡頭,反覆強化着蝙蝠俠作為純粹人類在大戰中的作用。純粹人類角色的核心級活躍,形成了對社會形態中人類力量的完美映射。而在結尾,扎克也再次借旁觀者火星獵人之口強調了這一點——“沒有你,就沒有這個聯盟”,由旁觀的客體存在認證了人類的作用。
在第三幕中,正義聯盟結成之後的首戰,正是這樣一種表達典型----在這樣一個首次突出英雄人性的段落中,英雄們表現出人神共體特徵,以人性交互而實現結盟,首次出戰以維克多對父親即將被殺害時的人性親情爆發為開端,女俠單挑荒原狼時”我不屬於任何人“的宣示更是帶出了“人類女性的女權精神”。而核心人物蝙蝠俠奮戰一個小兵的過程,以及隨後使用人類科技蝙蝠戰機的過程,全部被完整呈現。這雖然讓蝙蝠俠在其他英雄的表現映襯下顯得過於弱小,但也彰顯着人類“靠自己”的精神,從而讓它有了主題表達上的作用,合情合理且產生價值。
作為後續,隨着首戰荒原狼時正義聯盟接戰不利,無法限制荒原狼的破壞,也引發了後續的變化----正義聯盟成員,以唯一純人類布魯斯為代表,對自己能力的又一次動搖和對神權的又一次傾斜,將劇情導向對超人的召喚。在拿到母盒後的新章節,“國王和馬“,直觀地比喻出了此時正義聯盟成員心中,自己與克拉克的地位區分:國王超人,與作為他手下的自己。而在會議上布魯斯“上次激發母盒沒有引來荒原狼,是因為他們怕超人”“紅色披風會把公牛擋回去”,也表現出了他在感受到荒原狼強大的無力感中,將一切交給超人的被動依賴心理。
然而,正如扎克已然一次次強調的那樣,這樣的行為註定失敗,完全依賴於神權不足以解決任何事情。復活之時鋼骨看到的眾神隕落與超人霸權的幻象,無疑指向了“聯盟眾人將超人作為耶穌一樣復活並救世”的不切實際。黑化超人的出現,強烈地説明了這一點---對於出現於人世,並獨力完成世界救贖的“救世主”,其存在本身便是不可指望的荒謬。在這裏,一個很有趣的暗喻是——開頭超人犧牲自我,拯救世界,而後重生,形成了對耶穌的高度對應,但復活後的超人,在喚醒人性之前的所作所為,顯然與聖經啓示錄中再次降臨的耶穌並無相似。純粹的神性,是不會讓他成為“耶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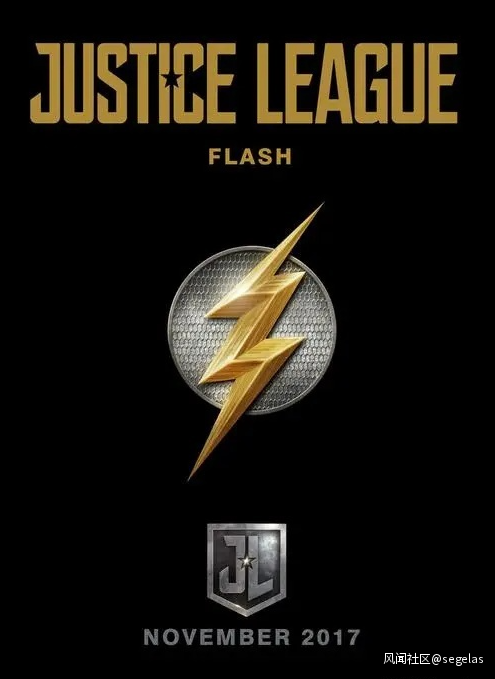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超人剛剛復活時的段落。扎克先是用一個警察掏出手槍的特寫細節,鋪墊了自由意志人類對於絕對神權出現的危機感,而後讓超人自己砸毀了代表英雄屬性的雕像,親手破壞了人類心中“拯救了自己,全民依賴”的人間之神。女俠呼喚“凱艾爾”的喚醒失敗,與露易絲呼喚“克拉克”的喚醒成功,也形成了對比。蝙蝠俠直面超人,屢次呼喚卻不停失敗,扎克對他此時的多個特寫,也試圖努力地傳達着蝙蝠俠此時受到的打擊----在認知中最強之神超人身上的失敗,讓他終於徹底意識到了絕對神權的不可依賴。
甚至早在黑化超人出現之前,扎克就藉助火星獵人的出場暗示了這一點。火星獵人先是變身瑪莎,作為超人人性一面的情感連接者,確認了人類露易絲對人類克拉克的思念之情,又變身國防部長,作為將超人視作神級戰力的角色投入工作。以原作設定中與地球牽絆較少---至少在電影發生時,未加入正義聯盟的狀態----更接近於“旁觀者”的立場,火星獵人明白,單純的克拉克或單純的超人,都不足以解決麻煩,他既需要推動超人的復活、神權的迴歸,也需要露易絲去激發克拉克的一面。正義聯盟會議中,紅披風超人的投影與露易絲和瑪莎“全世界都是S標誌,但他們不認識克拉克”的部分銜接,構成了強烈的對比,讓正義聯盟與露易絲看待超人雙重性的不同側重點,得到了揭示。火星獵人需要在大戰中混入人性的力量,説出了“世界也需要你,露易絲”。
火星獵人的想法,與超人復活後的細節形成了交互。被呼喚卡艾爾無效,被呼喚克拉克有效,穿上人類克拉克的衣服,則與開篇時“神性”狀態下被女孩頌揚歌唱的海王形成對比,加上超人飛上天空後的再次君臨、身穿人類衣服走進氪星飛船,表達出了“人性大於神性,二性共體”的社會統治系統。而進一步説,超人選擇黑色而不是紅色作為新戰袍,更是一種對神性之完美的有意打破——紅色是他帶給世界希望的顏色,是完全神性的代表,而黑色才是他作為氪星子民家鄉的制服,是他作為非神一面的象徵,且色調較暗,也是他人性一面存在缺陷的證明。
相對於絕對的神權領導,在高潮和結尾的部分,扎克頗為直觀地表達了正義聯盟---即社會---的理想運行形態。不同於喬斯韋登版本中“超人解決一切”的劇情,扎克強化了其他成員的作用,並加重了成員內心人性情感的驅動力----超人碾壓了荒原狼,但卻不能阻止母盒合體,必須要靠閃電俠自我鼓勵後的超越光速,而鋼骨在分開母盒前的一瞬間,也看到了作為人類的自己與家人。對陣荒原狼的勝利,是正義聯盟的集體,人性與神力共同作用的戰果。而在結尾,扎克用尾章的標題“重新為父”,並給出一段超級英雄們各顯人性的畫面,再次強調了人性的存在感。
必須承認的是,扎克在《正義聯盟》中做出了很多頗有價值的設計思路。他選擇了新人物中人神共體身份更易於表現,劇情立體性較好的鋼骨,增加戲份,讓鋼骨説出大戰前的“靠我們自己能搞定”,在分開母盒前看到人類時的自己,完全輔助了主題表現。母盒的宇宙神級力量構建了鋼骨,給予他操縱世界的學識力量,這讓他的神性超越了閃電俠,維克多則擁有比海王更豐富的人類成長背景,在人情維繫的小陣容裏無從發揮。鋼骨對自己身份的糾結,對人類社會的若即若離,對父親的複雜情感,都是很好的主題載體。在電影結尾,鋼骨面對父親墳墓,還原了父親留言的錄音筆,脱下遮掩的衣物,以鋼骨之姿直面對父親的情感,正是他同時接受了自己作為人與神混合的表現。
更重要的是,扎克處理了蝙蝠俠的作用,既讓他在作戰中有所貢獻,又在主題上成為了彰顯人類力量的關鍵象徵。在扎克的結尾中,或許會讓蝙蝠俠體現出更多的人類存在感,代表人類在達克賽德戰中發揮作用(自我犧牲),給出人性與神性---或許指向平民與精英----共同引導社會發展的最終主題,從而讓力量者神明自身屬性上的人神合一,與統治社會模式中的人神合一,實現對應。
在結尾中,布魯斯做了一個噩夢,預示了扎克計劃中的下一步方向。與布魯斯對談的小丑,無視了布魯斯殺死自己的威脅,稱自己就是另一個他。從“露易絲死的真可惜”的台詞來看,小丑用露易絲的生命誘發了布魯斯和克拉克的黑化,“你要想辦法把這裏變回失去她之前的樣子”則暗示了克拉克在失去露易絲後的爆發和毀滅,造成了眾人所處的廢土。而在更早一點的高潮段落中,扎克也已經用“更大的黑暗”標題,用達克賽德踩碎荒原狼頭骨那隻腳的特寫,用達克賽德軍團和正義聯盟的對視,鋪設了這個方向----正義聯盟,即將面臨更大的外力壓迫,從而暴露出更極端環境下的更黑暗心理。結尾中同樣出現的“面對強大神力壓制下人性極端化”代表萊克斯盧瑟,以及“反超級英雄”喪鐘,指明瞭“黑暗”的實質。
在這裏,布魯斯聲稱自己在逼迫下也會殺人,克拉克則已然成為了暴君超人,這樣的變化無疑代表了他們人性一面的缺陷——對感情的沉溺,讓他們軟弱,易於走向極端與黑化。而在扎克自述中後續的“布魯斯奪愛克拉克,和露易絲生下小孩”情節,也正是這一方向上的有力推動:他與露易絲的愛情是由人性不可抑制的愛情而生,哪怕違背了奪友所愛的道德與分裂聯盟的理智,而克拉克的黑化也將受自己愛情的丟失影響而更進一步。圍繞愛情這一人心中感性一面的典型,“人間之神”正義化身的克拉克黑化,“最強大腦”理應最理性的布魯斯做下衝動之事,再因為露易絲的死亡而更加深化。小丑在這裏説,他是布魯斯的另一個自己,正是點題之處。而後續“克拉克接受了小孩,取名布魯斯,紀念布魯斯犧牲”的情節,則明確地指向了人性的再放光芒——布魯斯以犧牲而對自我本性的拯救,克拉克基於人類善念而對孩子的接納。

在《正義聯盟》中,人性與神性合一而構成了超級英雄,人權與神權合一則形成了理想的社會形態。然而,人性的軟弱卻是一直存在的。從《bvs》開始,布魯斯在面對超人帶來的統治恐懼時,對抗之心就演變成了深度的暴力,更不用提萊克斯——正義聯盟結尾再次讓他出場,預示着後續作品中“人性之惡”的存在地位——這等人。人權提供了人類在自由選擇意志下的力量,但也帶來了墮落的隱患---由克拉克與布魯斯的個體體現,由“正義聯盟”這一社會縮影由統一到分裂的走向體現的,更由世界走向可能的超人王朝的前途體現。
人性的固有缺陷在社會中的處理方式,人性與神性在個體與社會中的缺陷克服、互補融合,將成為系列未來的探討重點。這很難,以扎克向來“架子很大,內容乾癟,高度概念化”的表達而言也難言樂觀,但無疑也很有趣。但是,作為唯一人類,布魯斯必然承擔消極人性的表達主體,並在形象上“荒腔走板”——他必將崛起,克服人性的陰暗一面,揭示主題,但也必然為了主題的呈現,而不得不得到許多黑化、歪曲、脱離主宇宙正統形象的劇情和設定。扎克對布魯斯無疑是愛不釋手的,將主題呈現工作都交給了他。但是,他想將電影拍成藝術片,讓布魯斯成為藝術片中那些邊緣人主角一樣的存在,然而dceu卻顯然不是藝術片,布魯斯韋恩——至少主宇宙裏的布魯斯韋恩——也不是那些邊緣人。
由於扎克本人執念頗深,樹立成DC宇宙創作根基的“純人性蝙蝠俠”象徵意義,他鏡頭下的布魯斯幾乎必然會越走越歪,一次又一次地成為“人性/人類”代言人---或是深度的暴力,或是“我們必須召喚超人”依賴神權的軟弱,或是超人死去後的絕望,甚至是扎克原本構想中後續“綠了超人”的“人類情感糾葛大戲”。唯一純粹人類的布魯斯,將成為他主題表達的最佳載體而一次次脱離角色塑造目的本身地濫用。對於以主宇宙為主體的正統系列來説,這樣的布魯斯,顯得過於荒誕了。並且,由於過度脱離原作,以及不佳的人物演進,這種蝙蝠俠,也必定只能停留在“概念”的層面上。

必須指出的是,即使在本作裏,扎克依然沒有解決一個本質性的缺陷:線索和人物的平面單一化,情緒氛圍表達的慢鏡頭---已經有所控制但仍然不少---過多。這兩點的並存,讓《正義聯盟》的主題表達、人物“深度”,彷彿一場動靜巨大的虛張聲勢。它更像是一種原地打轉的重複,在正義聯盟首戰前後、蝙蝠俠等人的兩次“人類信心動搖”,便可看到這一點。
條條大路通羅馬一樣的主題呈現,但其中相當多的非絕對主線和非核心人物,都陷入了碎片化狀態,呈現層面極其單一,欠缺發展延續性,甚至“個線有頭有尾”的基本完整度。例如,海王的人性一面只體現在他的愛情瞬間與粗獷性格,閃電俠則只能用羞澀的萌動與無限的話癆來撐起“巴里艾倫”,女俠與蝙蝠俠的感情線索只是隱晦一提,荒原狼的主題表達性也沒有基於其內心層面的更豐富呈現。此外,布魯斯對於正義聯盟的組建中,從第一次對海王強調他的神力到後續招募閃電俠時和他的玩笑,印證了他的內心從依賴神力到人性共鳴尋求的變化,但這其中的轉變過程,以及聯盟全體對於挫折下依賴超人的內心,都在屏幕上基本欠奉,只能靠着閃電俠“他是我的偶像”或蝙蝠俠“紅披風會趕走他們”“我們需要超人”之類的膚淺台詞來表現。
相對靠近主線劇情的環節都已經如此,更不用提那些走馬燈一樣出場的“龍套”了---火星獵人,綠燈俠,喪鐘,小丑,等等等等。扎克的版本里,明星,人物,線索,你方唱罷我登場,每一個局部似乎都指向了同一個主題,不可謂不規整統一,但每一個局部卻又都淺嘗輒止。扎克手下的事件與角色,以蝙蝠俠為典型代表,行為本身都顯得過於功利化,完全停留在了“作為主題表現側面”的水準上,缺少在心理上的更多合理性表現,行為機械,指向明確,但角色自身難以完整成立。
一旦心理合理性缺席,也就不利於觀眾理解人物行為,只能通過扎克在其他方面的手段----對“社會看待超級英雄的態度”的強調,“布魯斯復活超人時創造了黑色超人”的波折設置,“荒原狼的直白台詞”“反生命方程式代表的自由意志”“女俠嘴裏唸叨的自由選擇權”等明顯指向主題的內容,以及布魯斯説出的一堆堆直白到淺薄的台詞----來推導扎克的主題意圖,從而理解他藉助角色的表達。而更合適的辦法,顯然是建立角色內心的細膩性和完整性,讓觀眾先行理解人物情感,而後自然而然地通過人物行為的成與敗,接觸到作者的立意。

最典型的,莫過於火星獵人拜訪露易絲的一段。如果僅從劇情上看,瑪莎與露易絲建立起的克拉克存在感,二人對於人類克拉克的懷念之情,完全被瑪莎變成火星獵人的設計徹底打破了。觀眾可以理解瑪莎對克拉克的感情,但顯然難以理解“變成瑪莎”的火星獵人的動機,皆因扎克“火星獵人先確認克拉克與人類的人性羈絆,再推動神性超人復活”的構思。這實在是過於概念化的抽象了。對於主題表達來説,更直接易懂的方式,顯然是“瑪莎與露易絲交流”引出克拉克的人性一面,而後再由畫面的銜接,如接入布魯斯屏幕上飛行的超人、宛如耶穌復活一般的超人復活儀式,切換到神性的一面。然而,扎克卻放棄了這樣感情更飽滿流暢、易於共感的方式,而是採取了一種更為概念化和抽象化的象徵手法。
這樣的非感情的符號化、隱喻化、象徵化,是扎克一貫的問題。比起劇情層面人物心理情緒的流暢推進和自然變化,扎克不太在乎人物行為在基礎敍事上的合理性和自然性,將精力放在了更復雜更“高深”的表現方式上,這讓他的電影充斥了太多的標誌物,人物劇情呈現極度“主題表達功能化”的同時,敍事體系的運轉也顯得晦澀而又機械。其他的典型例子,還有扎克對鋼骨的使用:他準確地意識到了鋼骨維克多在聯盟中更凸顯的人性,將之設為主題表達的劇情重要載體,也讓他在大戰中充分地表現了人性親情對內心的支撐,然而,當鋼骨失去父親,處於表現內心情緒和參戰動機之人性化的最佳節點時,扎克卻完全沒有給鋼骨任何的戲份資源,前腳失去了父親,後腳馬上就開始了大決戰。
於是,扎克版本中的絕大部分人物和線索,在失去了自身完成度的情況下,就變成了某種意義上的工具人---雖然試圖努力地做出弧光,但卻只是只鱗片抓,整體呈現上依然是一個線頭到另一個線頭的集成,一個又一個於主題表達指向上絕對功利化的磚塊堆積。例如綠燈俠的出場,火星獵人的出場,都顯得過於倉促,只單純地成為了主題表達中“只有神力的無力”“神力與人力的結合”等主題表達的工具人,彷彿只是出現---完成主題呈現需要的片段,被打敗或認同人類----消失,個人角色的弧光完整度欠缺,過於碎片化。
而在情緒表達上,也有一些極其刻意、過度的部分,同樣淪為了表述主題概念的單純工具。如海王下水時女人的聖歌,鋼骨之父面對荒原狼手下時的茫然失落。而慢鏡頭無疑是其中之最:鋼骨橄欖球比賽中的奮鬥、怒吼體現出的人性情感,英雄們在戰鬥中的英武身姿體現出的神性,人類世界中瓢潑大雨落下與狼狽路人的慢鏡頭,甚至對主要角色宛如個人崇拜一般,對各種動作的慢鏡頭。並且,雖然已經有所控制,但扎克終究還是讓慢鏡頭引導出的情緒氛圍渲染遍佈了作品,神性、人性、神權社會中神的姿態、人類對神的信仰、人類失去信仰之神後的絕望、人類的崛起,都藉由慢鏡頭而得以呈現。
但問題是,這等頻繁的情緒表達,很多是並不必要的,只會過於囉嗦與重複,尤其是在劇情線索較為單一和停滯,缺少深度挖掘與演進發展的狀態下----人物的心理狀態,事件的進展階段,都沒有變化,而高度同質化的情緒,卻在一遍一遍地反覆強調。即使是核心人物布魯斯,他對待超級英雄的態度變化,對待超人的心理變化,也缺少了直觀的表現,就像“一次次呼喚超人甦醒失敗時的臉部特寫”的表意,因為缺少前因後果的細緻鋪設表現而顯得難以進入,需要用各種其他角度上的“符號”寓意來輔助理解。扎克總是這樣,努力地傳達人物情緒,通過情緒展現人物內心,但卻沒有提供內心的邏輯和動機的變化。這讓他的情緒往往流於表面,難以讓觀眾很自然直觀地接觸到他想借助人物傳遞出來的東西。

扎克施耐德在影像上的靈敏感覺,對於畫面構圖與背景音樂的藝術審美,支撐起了他電影中的腔調優點。這種腔調也勢必吸引一大批文藝向的青年,對其中的每一幀情緒頂禮膜拜,對扎克巨大----忽略其冗長地---的結構和信息量推崇備至。與此同時,這種“深沉”的氛圍、“黑暗”的質感,結合人物的“黑死殘”,也會讓很多投入度極高的觀眾,感受到一種所謂的“深度”。
然而,“深度”並不是單純的概念,它需要給人以説服力,提供推進更加完整的表達與塑造。而即使是“扎克自由出手”後“集大成之作”的本片,它的概念化、紙片化,外強中乾,相比前作而言,也依然只有一定的量變,而沒有本質的飛昇。
黑死殘不是深度,糾結也不是深度,在概念之下真地挖掘出“深度”的東西才有深度。
如果真的挖掘出來了,那麼即使不是黑死殘和糾結,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