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鄉的雲兒啊_風聞
秦朔朋友圈-秦朔朋友圈官方账号-2022-03-25 14:43

劉子 | 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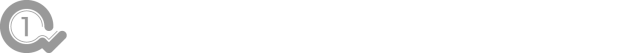
父親的散文詩
父親還是選擇了回家。
今年春節,上海疫情,我們不能返鄉過年,便叫父親趕來上海跟我們團聚。在上海的半個月,除了做飯,小孫女也不願跟他玩,他一個人出門抽煙,沿着門口的古浪路走很遠,往東或西。
我們希望他留在上海一起生活,還給他聯繫了家門口一所小學的勤雜工作,工資雖然不太高,但一天只需要工作到下午兩點,週末雙休、寒暑假照樣放假,算是自在。60歲的父親,其實已經很難找到工作,他們這代人,已經完全被社會淘汰。因此,這算是份不錯的工作。
只是他頭也不回地拒絕了。他聯繫了老家一個朋友,準備跟他去做房屋防水的活。他説,家裏還有你奶奶和外婆兩個老人。其實,我知道,根本的原因還在於,就算哪天我在上海混好了,這裏也不會是他的家。
元宵剛過,他就扛起行囊,坐上了還鄉的火車。他坐的是半夜12點上海南站的綠皮車,睡一覺,第二天上午就能到家。我把他送到古浪路地鐵站,他説我會坐地鐵了,下次來上海,就不用你到火車站接了。説罷揮揮手。我看着電梯載着他一點點下沉,直至消失不見。
讓我欣慰的是,他沒有去做防水。縣裏劇團的老朋友還惦記着他,鄉村文化振興政策下,劇團有不少下鄉的指標戲,團里人手不夠,把他叫了去,負責做一頓中飯,忙不過來時上台頂一頂。工資只有2000塊,但他很開心。
父親年輕時曾是地方劇團的骨幹,80年代初,政府退出基層文化事業,劇團解散。他在他爹的號召下回鄉務農,兼職村小民辦老師。他懂音律,擅二胡,在那文化貧瘠的鄉下,也曾是高山流水般的存在,只是後來漸被生活淹沒。
零幾年的時候,他從打工地深圳回鄉,和一幫年輕時的團友一起,重新操辦起他們的採茶戲戲團,一度風生水起,在縣裏連續幾年的文藝匯演上都引發轟動。我家鄉的親人去看了,都覺得很自豪。
 |
|
民間戲曲是傳統價值觀的重要載體。圖/李耀
只是,文藝在基層缺乏生存基礎,一個十幾個人的戲團很難持續運營,政府原本承諾的補助不見蹤影,指標戲也都劃給了縣文工團、劇團,那個鄉下老年戲團艱難地扛了沒三年即告解散,讓我們所有人都覺得遺憾。
好在“體制”還記得他,終於把他喚了回去。他很知足,每天的視頻電話裏也多了許多笑聲。他回到了自己的故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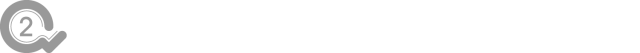
“回鄉種地吧”
疫情再度席捲而來,把許多人的工作、生活衝得七零八落。
從年前到現在,深圳一直身處困境,朋友前幾天打來電話,説公司隔離了一半人,外地的業務也一直沒辦法開展,他的公司已經快扛不下去。我們互相安慰。結果不兩天,深圳宣佈封城,全員居家辦公。
上海也疫情擴散,號召大家不要聚集。我愛人公司查出來有人感染,全體居家辦公。其中不少密接和次密接被拉去隔離,據説,家屬都給120打電話,讓救護車不要停在自家樓下,免得抬不起頭,“你們停得遠一點,我們把他/她送過去”……
杭州的朋友也打來電話,年後到現在,一單業務沒進,原本談好的政府業務還全部取消,也不知道還能支撐多久。我們相互鼓勵。臨了,他説,不如回江西老家種地吧。
我們一陣哈哈。聊起鄉下,心情才好了一些,與春光一道爛漫開來。

長久以來,習慣高處着手的各種經濟學家、專家只告訴我們城市化聚集的好處,從來沒有告訴我們它們的壞處。疫情代表自然界和社會規律,再次向我們提了次醒——有聚有散才是良性的社會規則。
**然而多年來,我們只知應該聚、如何聚,漸漸忽略如何“散”。**譬如談及鄉村,言必稱應該聚集到城市,已然忘記,龐大而臃腫的北上廣深常常不堪重負、身陷危機,廣闊而分散的鄉下,也會有它們的好處。
譬如,已經大到令人髮指的北京、上海,即便再聚集,面積再擴張一倍,GDP再增長一倍,對生活在其間的人們來説,又有何意義?又譬如那些遙遠的鄉下,人們從來不為疫情煩惱太久。
再譬如金融市場,聚集帶來效應,也孕育風險,一旦風吹草動,總是恐慌逃生、踩踏。人們集腋成裘,好不容易積累起來的財富突然崩塌,過往的努力就真的成了一堆容易消散的數字……
經濟不是人生的唯一目的,生活才是。對普羅大眾來説,生活的本質也不是一堆數字,而是各種感受。
好的生活,不只在強光下的此處,也可以在被我們忘卻了的他處。不沉迷於“聚集”。讓想聚的聚,讓願散的散。

|圖/王記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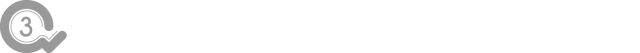
知識分子的哀歌
最近另一件大事是俄烏戰爭,我寫過一篇《從俄烏論戰這面鏡子照見自己》,本意是反對一些知識分子、媒體人缺乏專業,喋喋不休地爭論、站隊,不如多“照見一下自己”。
其實無意批評,我想,那些“XX智庫”“XX論壇”羣中,那些挺烏反俄、評論得頭頭是道,那些有頭有臉、許多還身在西方的知識分子,吵得最兇的是你,或許,最迷茫的也是你。
塞繆爾·亨廷頓在《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中分析,在西方的前殖民地和日本、中國這樣的獨立國家,“‘第一個推行現代化’的人或‘獨立後’的第一代人,常常是在外國(西方)的大學裏接受用西方廣為傳播的語言進行的教育……部分是由於他們第一次出國時是易受影響的青少年,因而他們從根本上吸收了西方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相比之下,為數眾多的第二代人大多數在國內由第一代人創立的大學裏接受教育,授課越來越多地使用當地語言而不是殖民語言……這些大學的畢業生不滿於早些時候受過西方訓練的那一代人的控制,因而經常“易受排外主義運動的鼓動”,他們被羅納德·多爾稱為“第二代本土化現象”。
從以往的日本,到中東伊斯蘭,到蘇聯解體後的俄羅斯,或者改革開放後的中國,莫不如是。第一代西方化精英,難免面臨民眾和第二代本土化精英的質疑,要麼徹底移民西方,要麼在迴歸路上陷入困惑、糾結,這是全球性的社會規律。亨廷頓繼續分析,“人們並不只靠理性活着。只有在界定了自我之後,他們在追求自身利益時才能理性地籌劃和行動……在飛速變革的時期,已確立的認同消失了,必須重新界定自我,確立新的認同”。
亨廷頓就將俄羅斯歸為“文明無所適從”的國家之列。地處亞歐結合部的俄羅斯,自古就在西方現代化和東正教、斯拉夫傳統之間搖擺,他們經歷過彼得大帝以來數百年的全盤西化,又經歷蘇聯時期與西方的全面對抗,然後是戈爾巴喬夫導向西方導致的蘇聯解體,此後是葉利欽試圖融入西方社會不得而導致的社會大分歧,直至普京後選擇迴歸其斯拉夫、歐亞文明……這個龐然大物,既讓西方人害怕,又是西方文明體系邊緣遊蕩的倔強的“孤兒”。
同理,烏克蘭人民在百年糾葛後,選擇告別俄羅斯迴歸基督教西方文明。我們尊重他們的選擇,反對戰爭,但也要看到,迴歸,通常是多麼巨大的代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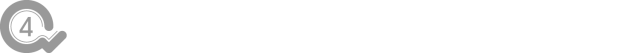
《故鄉的雲》
經濟不可能一直高速發展,也不是所有人都能一直往前走。當社會遇見挫折,何處安放失落者的身心?
“我曾經豪情萬丈,歸來卻空空的行囊”,當一個人歷經世事卻行囊空空,能張開懷抱擁抱他的,只有故鄉。
願他歸去時,故鄉仍安好。

作者:劉子,民間觀察派,獨立思考者。專欄作者,撰稿人,鄉村振興&縣域經濟學者。
參考書籍:塞繆爾·亨廷頓,《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