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名媛到集中營難民,這個被老外當巨星的中國女人,不應該被遺忘_風聞
最华人-最华人官方账号-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最华人2022-03-26 20:42
· 世界華人週刊出品 ·
作者:牧龍閒人

一位曾在上世紀登上世界各地報紙,
卻很少被中國人知曉的傳奇女性。
最近,B站上的一條視頻火了。
視頻開頭是一段老舊的黑白紀錄片,記錄着1945年4月,納粹德國戰敗前夕,一批難民被從拉文斯布呂克婦女集中營裏解救出來。
那是二戰期間最臭名昭著的“女性地獄”,曾關押過13.3萬名婦女、兒童和青年,其中近5萬人被迫害致死。
難民們重獲自由,露出了久違的笑容。
但就在鏡頭一晃而過的瞬間,畫面中出現了一箇中國女性的面孔。

她站在一眾金髮碧眼的歐洲人中,顯得是那樣格格不入。
一箇中國人,怎麼會出現在德國納粹集中營?
更讓人驚訝的是,就在所有人因獲救而高興的時候,這位中國女性,淡漠地看了眼鏡頭,嘴角微微牽動,勾出了一絲不屑的冷笑。

眼神中彷彿帶着一種穿越時間的魔力,以至於在70多年後的人們看來,仍能被其中的冷靜和孤傲所觸動。
很難想象,這樣的表情竟出自於一個剛剛經受了長期囚禁的難民。
她的身份也引起了人們的猜測,在經過網友的深挖之後,最終,一個早已淹沒在漫漫歷史長河中的名字,浮現而出。
黃訥亭。
一位曾在上世紀登上世界各地報紙,卻很少被中國人知曉的傳奇女性。

與青年毛澤東的一面之緣
1902年,黃訥亭出生在西班牙首都馬德里。
父親黃履和,浙江餘姚人,曾是清政府駐西班牙外交官,母親布魯塔是比利時貴族。
清政府垮台後,黃履和奉調回國,在北洋政府外交部任職,最高做到禮賓司司長。
用現在的話來講,黃訥亭是妥妥的高幹子弟。

● 兒時的黃訥亭和父親、母親
在1980年的第5期《讀書》雜誌上,甚至記載着23歲時的毛澤東,曾到黃訥亭家拜訪她的父親。
“有一天,一個青年學生到我家來訪問……這個學生是來指責我父親的錯誤的……但他很快就明白,我父親不僅不是他前來要加以責問的官員,而且我父親根本不贊成這樣的措施。於是他們的談話就活躍起來……
“這個青年在談話中還向我父親承認,目前他還沒有辦法在各省實現一項重大的改革。他説,他的許多同伴已經到法國去,例如周恩來、陳毅……但是他自己在國內有更重要的工作要做。
“‘好好注意這個年輕人,’青年走後,父親説,‘要記着他,他將來也許前程遠大。’在告辭的時候,我知道了青年的名字叫毛澤東,那時候他23歲。”
而那年的黃訥亭,剛滿14歲。

作為一個出身名門的少女,黃訥亭自幼接受了非常良好的教育,在上流社會的薰陶中長大。
她在法國教會創辦的聖心學校讀書,上學之餘,還在家中接受私塾教育,結交者非富即貴,不乏林語堂、胡適等文人豪客。
除了漢語,她精通法語、西班牙語、意大利語和英語,並通過函授,拿到了芝加哥漢密爾頓學院的法律學位。

在那個風起雲湧的年代,中西方文化激烈碰撞,這個受過最新式教育、見過無數風雲人物的混血兒,成了北京社交圈一道十分搶眼的風景。
但她絕不是傳統審美中的“大家閨秀”。
長相清俊,喜歡穿男裝,經常穿着男裝出席宴會;
擅長擊劍、騎馬、網球、冰球、賽艇、拳擊等各種在當時被貼上“男性標籤”的運動;
更積極投身社會活動,敢於站在集會上高舉着拳頭大聲演講,呼籲改革……

在舊社會婦女纏足的大背景下,黃訥亭的所作所為,對大眾而言是匪夷所思的,甚至讓一些遺老遺少們覺得“離經叛道”。
可黃訥亭從不屑於他們的目光,以自己前衞的思維方式和行事作風,努力將那個對女性充滿着束縛和禁錮的時代,遠遠拋於身後。

● 黃訥亭曾出現在世界各地報紙
美國藝術家野口勇對黃訥亭讚不絕口,稱她“年輕有為、英俊瀟灑”,覺得她看起來像一位“美麗的海盜”。
Le Temps(《時報》)則形容黃訥亭為“一個才華橫溢的天才”。
西班牙Estampa雜誌,更是將黃訥亭身着男裝的陽剛照,放在了雜誌的封面,在標題上註明:“中國的聖女貞德”。

這位魅力十足的東方女性,無形中影響着世界範圍內的人們對中國、尤其是中國女性的看法,將中國女性的精神風貌,大大方方地展示給了全世界。

我不是軍隊的“花瓶”
1921年,19歲的黃訥亭身着男裝參加舞會,以一支阿拉貢霍塔舞(一種西班牙傳統舞蹈),獲得了奉軍高層的賞識,被授予空軍上校軍銜。
憑藉一支舞蹈成為上校,聽起來有些不可思議,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她不俗的背景和出身。
但一個不能忽略的前提,人家不是空架子,是真有這個名氣和能力,支撐她在當時的軍政界站穩腳跟。

● 黃訥亭軍裝照
穿上軍裝後,黃訥亭不甘做軍隊中的“花瓶”。
為了成為一名合格的軍人,她去軍校,以頑強的意志和出色的成績,完成了所有課程。
之後,又前往巴黎,在布爾歇機場受訓,學會了開飛機。
她以果決膽大出名,在當時的民國空軍中,就連男性飛行員都很少有人敢像她那樣進行雜耍飛行。
見聞廣博,膽識過人,精通多國語言,極擅社交……黃訥亭無疑是上天眷顧的寵兒,也註定有着更廣闊的天地。
1926年,24歲的黃訥亭開始擔任北洋政府總理潘馥的機要秘書,把守着北洋政府重要的經濟職位,並負責與歐洲新聞界的關係。
第二年,她被派遣到美國俄勒岡州,從事外交工作。
但不久後,國內風雲突變,北洋政府倒台,南京國民政府完成了形式上的“統一全國”。
黃訥亭像一隻飛在天邊的風箏,突然斷了線。
她只好回國,成了少帥張學良麾下的一名中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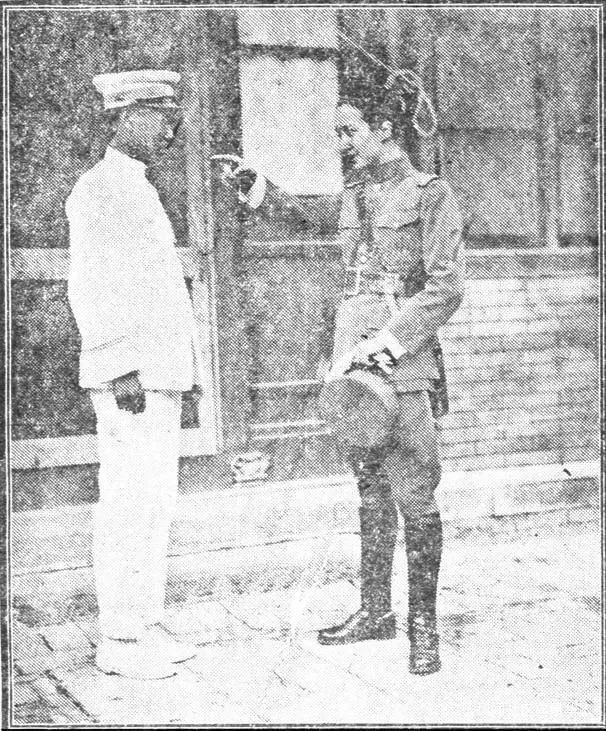
然而,國民黨統治下的民國,似乎並不能成為黃訥亭從軍報國的舞台。
1929年,中東路事件爆發,以張學良為首的東北軍,與蘇聯軍隊之間爆發了一場激烈的戰爭。
黃訥亭明確表示,希望自己能夠上前線戰鬥。
但她還未得到批准,這場戰爭便以慘敗告終。
連續的失意,讓黃訥亭有些心灰意冷,興許是疲倦了政場上的爾虞我詐,她最終移居巴黎,開始了一段波西米亞式的生活。

有悖於傳統的“同性戀人”
波西米亞式生活,是一種非傳統的生活方式,多存在於藝術家、作家之間,不受傳統思想的束縛,也不對傳統抱有任何幻想。
1933年,31歲的黃訥亭隻身來到巴黎,結識了57歲的美國女作家娜塔莉·克利福德·巴尼。
巴尼是文藝界的社交紅人,也是公開的女同性戀,她舉辦的沙龍一位難求,匯聚着來自世界各地的名流達人。

● 娜塔莉·克利福德·巴尼
黃訥亭起初是巴尼的司機和私人助理,後來,兩人漸漸發展成了情人關係。
面對周圍人異樣的目光,黃訥亭不以為意,她坦言:“我見到巴尼之際就明白會發生什麼事情。”
在巴尼的引薦下,黃訥亭經常參加各式各樣的沙龍,這些或精緻典雅、或富麗堂皇社交活動,對黃訥亭而言簡直是如魚得水。
她有着迷人的東方面孔,身材修長,氣質高貴,能夠輕鬆駕馭中式旗袍,並且非常善於展示自己,“當她穿着中式服裝表演劍舞時,無人不為她傾倒”。

黃訥亭很快融入了巴黎藝術界,名聲大噪,巴尼對她的愛慕也與日俱增。
作家Helene Nera曾對黃訥亭的魅力這樣描述道:
“她的華人身份和她受到的偏愛,讓她遭到了來自巴尼眾多愛慕者和情人的致命嫉妒,現場廝殺的激烈程度和後宮眾妃爭寵的情形別無二致。”
英國記者則對黃訥亭如此評價:時尚典範,令人難忘。
但他們絕不曾想到,黃訥亭社交名媛的面具之下,藏着的是另一重鮮為人知的絕密身份。

納粹集中營裏的險死還生
上世紀三四十年代,二戰期間,黃訥亭參加了一系列的反納粹運動,是法國反抗運動對納粹進行間諜活動的秘密特工。
1944年5月,黃訥亭不幸身份暴露,被納粹德國逮捕,隨後送往有着“女性地獄”之稱的拉文斯布呂克集中營。

● 拉文斯布呂克集中營
這裏關押的對象多為女性,據以色列猶太大屠殺紀念館的數據,該集中營關押過的13.3萬人中,有近5萬人死於槍擊、毒氣、苦役、酷刑或者醫學實驗,慘烈程度令人髮指。
即使處境如此惡劣,黃訥亭依然沒有喪失自己的風度。
一位一同被關押的猶太女性,在回憶對黃訥亭的印象時説道:
“她是一個獨特的女人,受過良好教育,活潑且個性堅強。”
1945年,蘇聯軍隊將要攻佔德國柏林的消息傳到了集中營,女人們看到了一絲希望。
但她們並不確定自己能夠活到那一天。
於是,她們找來一塊紅布,親手繡上自己的名字,證明她們曾經來過。
黃訥亭在紅布上繡上了“黃China”。

幸運的是,不久後,“白色巴士”營救行動開啓。
所謂“白色巴士”,是一項由中立國瑞典和丹麥政府組織的人道主義營救行動,通過秘密協商,設法將納粹集中營裏的部分“囚犯”安全轉移。
而為了避免沿途誤判,所有轉移“囚犯”的巴士都被塗滿醒目的白色油漆,刷上紅十字會標識。

● “白色巴士”行動
黃訥亭被列入了救援名單,而一些無門無路的“囚犯”,則被排除在名單之外。
黃訥亭不忍心讓一位9歲的女孩留在集中營,便找到被俘的英國間諜瑪麗·林德爾,通過層層關係,將女孩和她的母親一併加入到了救援名單中。
1945年4月,黃訥亭成功獲救,於是便有了紀錄片開頭,她面對鏡頭時那一抹令人難以捉摸的冷笑。
或許是不甘,或許是自嘲,抑或是在黑暗動盪的時局下,不自覺流露出的一種人如螻蟻、無力迴天的心灰意冷。
她本來應該去拯救別人,結果反過來,自己卻成了被拯救的對象。
這對一個一生要強的人來説,是多麼大的諷刺。

跨越時空的“重生”
重獲自由後,黃訥亭離開歐洲,移居南美洲委內瑞拉,和女友奈莉開始了嶄新的生活。
她們在委內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共同生活了20年。

● 黃訥亭和奈莉
奈莉在大使館工作,黃訥亭則因着法律專業的背景,在一家銀行擔任秘書。
工作之餘,黃訥亭仍然喜歡在家中開派對,她時而以男裝示人,時而換上中國旗袍,她的家也成了朋友們聚會的熱門場所。
60年代末,黃訥亭患重病,因過量服藥而突發中風,身體狀況急劇惡化。
她和奈莉前往比利時,在奈莉的故鄉布魯塞爾定居。
1972年,黃訥亭病重離世,長眠於布魯塞爾,享年70歲。
近半個世紀後,一部名為Every Face Has a Name(每張臉都有一個名字)的紀錄片在瑞典上映,片中出現了那個在納粹集中營裏被黃訥亭救下的9歲女孩。

● 9歲時的艾琳·克勞茲·費恩曼
她叫艾琳·克勞茲·費恩曼,如今已年過古稀,面對鏡頭,她動情地回憶着當年關於黃訥亭的一幕:
“戰爭快結束那會兒,集中營裏的狀況變得非常糟。那些人不斷用喇叭催促我們轉移到另一個叫貝爾根·貝爾森的集中營。很多人都去了。但是Nadine Hwang(黃訥亭的英文名)跟我媽媽説,別去。
“她從德國人那裏聽説有些塗滿了白色油漆的巴士就快來了,那些車會直接把名單裏的人帶出集中營,送到瑞典,然後就自由了。她設法把我們母女倆的名字弄進了那份名單。
“臨走前,我媽媽承諾,如果艾琳將來生下女兒,會取名為‘Nadine’,以紀念這份恩情。”

● 如今的艾琳·克勞茲·費恩曼
仿如生命的延續與重生,Nadine的名字在遙遙跨越半個世紀後,又一次出現在了人們的面前,帶給人們無限的悵惘與感動。
在那個20世紀最黑暗的時代,黃訥亭為國家奔波奮戰,為自己優雅而活,打破束縛與桎梏,為更多的人爭取到了苦難盡頭的一絲光亮。

前半生波瀾壯闊,後半生迴歸平凡,拼湊成了這位民國女性充滿着無限魅力、血肉鮮活的傳奇一生。
《世界華人週刊》致力於從世界發現中國,提供有廣度的知識,有温度的立場和有深度的思想。轉載請聯繫微信公眾號世界華人週刊(ID:wcweekly)授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