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澤克 | 連線大腦裏的黑格爾_風聞
保马-保马官方账号-2022-03-29 11:16
❖
保馬今日推送齊澤克的新書《連線大腦裏的黑格爾》導論部分。該書由朱羽老師翻譯。
作為一個黑格爾主義者,齊澤克認為如果説在某種意義上20世紀屬於馬克思而非德勒茲,那麼21世紀將成為黑格爾的世紀。成為一個黑格爾派意味着將黑格爾的話當作起點而非終點,用黑格爾的思想來理解我們今天的世界。齊澤克指出,黑格爾從來不是一位批判性的思想家:他的基本立場是和解。——和解不是一個長期的目標,和解是一種事實。正是和解,使我們直面現實化了的理想那一出人意料的苦澀真理。他假定黑格爾勾勒的不自洽總體性,正是展開思考的終極立足點,進而聯繫到當下的連線大腦,問題就成了:假若連線大腦之類的東西強勢登場,由我們的主體性來表達的人類精神該何去何從?齊澤克指出,連線大腦的出現是一個事件,針對我們的主體性將如何受它影響,我們只能進行推測。在某種極端新穎的東西出現之時,我們必須同樣懷有直接介入每一次重要轉向的決心:在這些轉折點上,如果想要有效地掌握新現象,我們必須再次下定決心去思考。而《連線大腦裏的黑格爾》既是一種哲學反思,也是一系列關於迂迴現象的隨筆。
《連線大腦裏的黑格爾》中文版將由西北大學出版社“精神譯叢”出版。感謝朱羽老師授權發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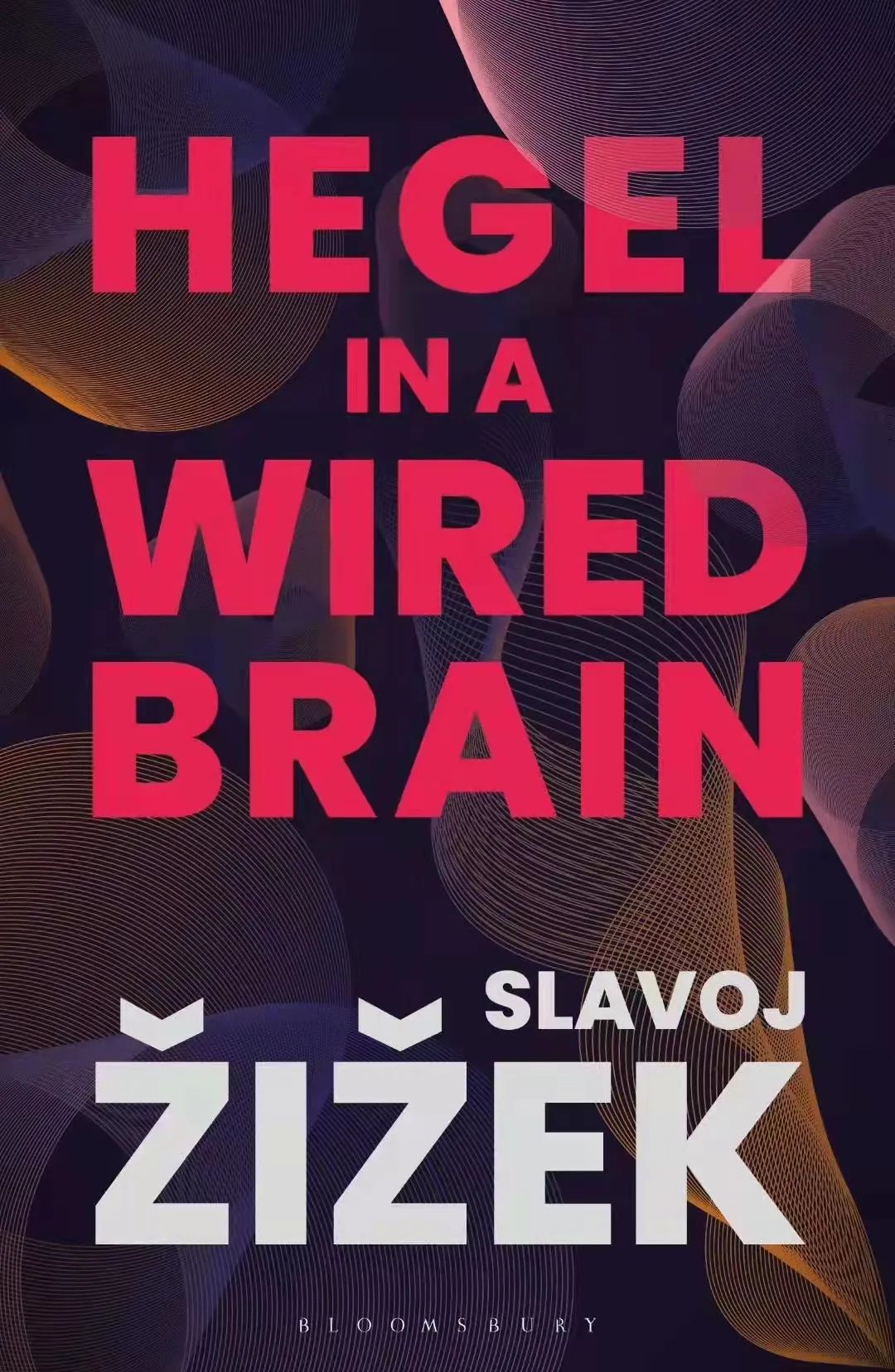
《連線大腦裏的黑格爾》 斯拉沃熱·齊澤克
《連線大腦裏的黑格爾》 導論
文 | 斯拉沃熱·齊澤克 譯 | 朱羽
“也許有一天,我們將迎來黑格爾的世紀”
2020年,我們迎來了黑格爾誕辰250週年這一值得慶賀的日子。可黑格爾不是已經成了歷史上的老古董了嗎?他的思想還能對我們説些什麼呢?“也許有一天,我們將迎來德勒茲的世紀”[1],幾十年前(1970),米歇爾·福柯評論德勒茲的書時寫下了這樣的句子。本書提出的假設則是,如果説在某種意義上20世紀屬於馬克思而非德勒茲,那麼21世紀將成為黑格爾的世紀。這一主張顯然有點瘋狂。在這個量子物理學、進化生物學、認知科學和數字技術宇宙裏,在這個全球資本主義和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2]世界中,黑格爾不是早已出局了嗎?不過,我們首先想説的並不是,黑格爾以某種方式看到了上述所有這一切,或對之做出了預言。——不,他根本沒有做到,而且他知道自己無法做到。黑格爾所謂的“絕對知識”[3],意思並不是黑格爾“知曉一切”。確切地説,它表示哲學意識到了無法逾越的界限。想一想黑格爾的《法哲學原理》吧,他在“序言”裏特別駁斥了“教導世界應該怎樣”:
無論如何哲學總是來得太遲。哲學作為有關世界的思想,要直到現實結束其形成過程並完成其自身之後,才會出現。……當哲學把它的灰色繪成灰色的時候,這一生活形態就變老了。對灰色繪成灰色,不能使生活形態變得年青,而只能作為認識的對象。密納發的貓頭鷹要等到黃昏到來,才會起飛。
羅伯特·皮平指出了此種主張顯而易見的內涵(雖然黑格爾很少把它勾描清楚):“密納發的貓頭鷹在黃昏起飛”同樣適用於從黑格爾自己的法哲學中發展出來的國家觀念。事實就是,黑格爾能夠發展出這一概念,便意味着黑格爾的讀者們通常所理解的模範理性國家的規範性描述,已經置身黃昏之中。這解釋了為何黑格爾的思想支持對於未來的徹底開放:在黑格爾那裏沒有終末論(eschatology)[1],也沒有我們這個時代將要抵達的未來形象——無論是光明還是黑暗。[2]但出於同樣理由,或許更加顯而易見的是,對於一個思考者來説,想要透過某人的思想透鏡來閲讀我們的當下,黑格爾可能是最糟糕的選項。——沒錯,他可以完全向未來開放。可是,不也正是因為如此,他才無法説清楚未來是什麼樣嗎?
我們在這裏的賭注恰恰是,站在這一“顯而易見”的俗論的對立面。恰恰因為黑格爾的思想完全“過時了”,它才賜予了我們獨特的透鏡,幫助我們去感知這個時代的願景與險情。在今天成為一個黑格爾派,並不意味着去構造一種新的理想(關於充分承認、理性國家、科學認知等等),然後去分析為啥我們還沒達到理想狀態,以及如何抵達這個狀態。成為一個黑格爾派,就得像一個真正的後黑格爾派那樣行動:別把黑格爾的話當作結論,而是當作起點,並問這樣一個問題:從這個起點出發,當下萬物的狀態將會如何呈現?進一步説,倘若黑格爾能讓我們更好地(恰切地)領會那些顯然是黑格爾離開我們之後才誕生的現象——那些“黑格爾根本無法想象”的東西,那會怎麼樣呢?
# 黑格爾的方式…… #
然而,我在這裏指的是哪個黑格爾呢?我自己站在哪個位置上説話呢?[1]將之簡化到極致,我的哲學立場可以由以下三人組來界定:斯賓諾莎、康德、黑格爾。斯賓諾莎處在實在本體論(realist ontology)的塔尖:實體性的實在是存在的,我們可以憑藉自己的理性揭去幻象的面紗,認識實體。康德的先驗轉向(“先驗”亦可譯作“超越論的”)在此處引入了一種極致的裂隙:我們永遠無法掌握事物自在之道,我們的理性束縛於現象領域。如果嘗試去超越現象,直抵存在整體,我們的心靈必然會陷入二律背反,無法自洽。黑格爾提出的則是這樣一種設定,現象之外並沒有自在的實在。這並不意味着所有存在無非是現象間的相互作用。而是説,現象世界被標上了一道不可能性之槓(the bar of impossibility)[2]。越出這條槓,啥都不存在,沒有另一個世界,沒有實定性的實在。因此,我們並沒有迴歸康德之前的實在論。毋寧説,在康德看來彰顯知識之限度的東西——即抵達物自體的不可能性,刻入了物自體本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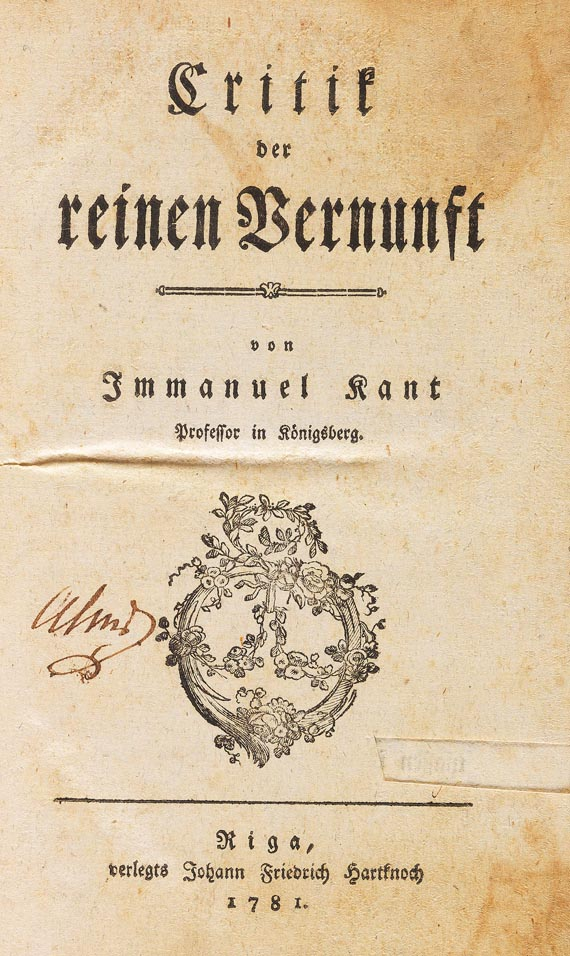
康德 《純粹理性批判》
但是,我們可以再問一次,黑格爾還能扮演這種角色嗎?即我們的思考所無法逾越的邊際線?同傳統形而上學宇宙之間真正的決裂,難道沒有在隨後發生嗎?而正是這場決裂界定了我們思想的座標。這場決裂最無風險的跡象是一種直覺。當我們閲讀某些經典形而上學文本時,這種直覺就會壓垮我們。——這個跡象告訴我們,今天確實無法再像那些文本所指示的那樣來思考了。……當我們讀到黑格爾關於絕對理念等等的思辨性論述時,難道不也是這一直覺壓垮了我們嗎?造成這場決裂的候選人有好幾個,他們使黑格爾不再成為我們的同代人。謝林、克爾凱郭爾和馬克思的後黑格爾轉向是始作俑者,然而這一轉向可以簡單地用德國觀念論主題的內在倒轉來解釋。就最近十幾年主導性的哲學議題而言,保羅·利文斯頓為此種斷裂提供了更具説服力的新案例。他在《邏輯的政治》[3]一書中將斷裂放置在“康托爾”、“哥德爾”這些名字所代表的新空間裏。自然,“康托爾”代表集合論以及自我關聯的程序(空集、集合的集合),這種理論迫使我們承認無限的無限性;而“哥德爾”指的是他所提出的兩項不完備定理,用極其簡化的方式來説,這兩種定理演示了一種公理系統。此一系統無法證明自身的自洽性,原因在於它必然會產生出既不能被證明也無法被證否的命題。[4]
藉助這場決裂,我們進入了一個新宇宙。這個宇宙逼迫我們拋棄關於(所有)實在的自洽觀念。[5](甚至馬克思主義——至少其主導形態,也依然可看作是歸屬於舊宇宙的思維方式:它闡述了關於社會總體相當自洽的觀點。)不過,新宇宙同“生命哲學”的非理性主義毫無關係,後者第一個代表人物是叔本華。此種非理性主義認為,我們的理性頭腦只不過是稀薄的表層,實在的真正根基是非理性驅力。新宇宙的意思則是,我們依舊身處理性王國之中,但這一王國從內部被剝奪了自洽性:理性內在的不自洽,並非表明存在着一種能夠逃脱理性掌控的更深層的實在;而是説,在某種意義上無法自洽的正是“物自體”。因此,我們會發現自己身處這樣一個宇宙之中,不自洽在此並不是認識遭遇混亂的標誌,也並非表明我們錯失了“物自體”——因為從定義來看,物自體不可能是不自洽的。恰恰相反,它標誌着我們已然觸到了實在界/真實(the real)。[6]
當然,所有這些不自洽性的根基正是諸多悖論,如自我關聯,一個集合成為自身的元素之一,一個集合包含一個作為其子集的空集——空集成了它在其他子集當中的替身。黑格爾-拉康視角將這些悖論視為主體性在場的跡象:主體只會在類屬與種的不平衡關係中出現。從根本上講,主體性的空無就是以種的身份來呈現的空集;在此,正如黑格爾可能會説的那樣,類屬在其對立性的規定中遇到了自己。可是,同一個特徵如何既是主體性的標誌,又同時成為我們觸及實在界的標誌呢?難道我們不是恰好在消除了主觀立場,擺脱了主觀立場來感知事物“如其所是”時,才接觸到實在界嗎?黑格爾和拉康帶給我們的教益卻截然相反:關於“客觀實在”的每一種設想,已然是(先驗的)主體性的建構產物。只有看到主體性指引出的實在界中的那道切口(the cut-in-the-real of subjectivity),我們才能觸及實在界(或真實”)。[7]
主體性的形而上學憑藉反思性概念[8]來處理這些悖論,而反思性正是自我意識的基本特徵,是我們關涉自身的心靈能力。這種心靈能力不僅能夠意識到對象,也能同時意識到自己,意識到自我與對象如何建立關係。反思性的基本姿態表現為回撤一步,把自身在場納入到我們正在觀察、分析的圖景或情境之中。——只有以此種方式才能把握到完整的圖景。舉個例子,偵探小説裏的調查人員分析犯罪場景時,就不得不把自己的存在、自己的目光納入其中。有時,罪行確實就是為他安排的,是為了吸引他的注意,使他捲入到事件之中。(在有些電影裏,調查謀殺案的探員會發現他直接就是罪行的受話人。兇手犯下罪行,為的是警告他。)與之類似,在某部佩裏·梅森探案集裏,梅森全程見證了警方審問一對夫婦,他們被懷疑犯下兇案;可他無法理解,為何那位丈夫特別願意將謀殺那天兩人做了些什麼全講出來。但後來他明白了,丈夫那事無鉅細的報告的真正受話人是他妻子。也就是説,他利用了兩人在一起的機會(兩人本被分開關押),把虛假的不在場證明告訴了她,提示兩人應該一起維持這個謊言。……我們還可以想象這樣一個故事。嫌疑犯把自己犯下的事説給警察聽,其實是在暗中實行恐嚇。——他就是有意説給某個在場的警探聽的。所有這些案例共享的是這樣一種事實:要理解某一陳述,就得確認它的受話人。這就是為什麼一位偵探需要另一個人,如同福爾摩斯身邊的華生或波洛身邊的黑斯廷斯。華生和黑斯廷斯代表了佔據常識一面的大他者[9],他們的目光是罪犯實施犯罪時的目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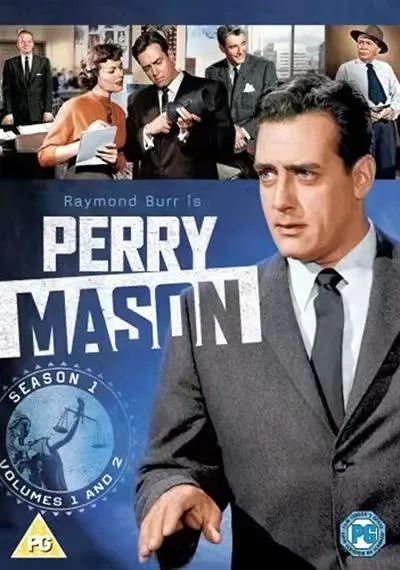
《佩裏·梅森探案集》
藉由康托爾/哥德爾所造成的斷裂而變得易於察覺的,正是從屬於主體性的自我指涉悖論全貌:一旦我們將自己的立場納入到全部圖景之中,就無法再回歸自洽的世界觀了。因此,“康托爾/哥德爾斷裂”使自洽的總體性不再可能。我們不得不在總體性和自洽性之間做出選擇;我們無法同時擁有兩者。而此種選擇最終實現在20世紀的兩種方向當中。利文斯頓對之進行了命名,一種是類屬方向(這是巴迪烏的立場,他放棄總體性,選擇了自洽性)。一種是悖論-批判方向(選擇總體性,放棄自洽性——利文斯頓把維特根斯坦、海德格爾、列維-斯特勞斯、福柯、德勒茲、德里達、阿甘本和拉康都放在裏面,當然這並不讓人特別信服)。[10]在這點上,我注意到利文斯頓整幢大廈的第一個奇怪之處,一種令人驚詫的不平衡:雖然悖論-批判和類屬表現為處理新宇宙的兩種方式(這個宇宙使自洽總體性不再可能);然而,一面是各不相同的思想家所構成的多樣性,另一面就只有巴迪烏孤家寡人一個。這種不平衡性的涵義很明顯:它展示出利文斯頓一書真正的主題:為了回應巴迪烏類屬的方法,如何給出一種合適的批判-悖論式的回應。利文斯頓懷着極大的敬意來對付巴迪烏。他完全意識到,比起那些悖論-批判方式主要代表們的立場,在巴迪烏那裏,類屬立場的邏輯與政治基礎得到了遠比前者精微而準確的闡述。巴迪烏是如此重要,正在於他以極其明晰的方式就此主題——即利文斯頓書的標題“邏輯的政治”——展開了詳盡的闡發,即他闡明瞭自洽性、總體性和自我指涉悖論這些哲學-邏輯主題深刻的政治涵義。這些悖論不正位於每一種權力構造的核心處嗎?這些權力構造不正是以不正當的方式強加於人,然後再回溯性地正當化自身的權力施行嗎?
我非常欣賞利文斯頓的方法,可在許多方面卻不敢苟同。首先,對我來説,在康托爾/哥德爾斷裂出現之前的思想世界裏,基本的二元性並不表達為本體-神論(ontotheological)與準則論(criteriological,利文斯頓也稱之為“建構論”),毋寧説呈現為(實在論的、普遍本體論意義上的)本體論與先驗論。[11]——舉兩個特別典型的名字,即斯賓諾莎與康德之間的對立。其次,黑格爾已經展現了同這個舊世界的真正決裂。依照黑格爾的標準,黑格爾之後的思想發展其實是倒退的。利文斯頓應對黑格爾時的立場清晰可辨:他承認黑格爾的辯證法是不自洽總體性的典範案例,與此同時卻堅持認為,黑格爾思想中的不自洽性,最終“揚棄”在了更大的自我演化的理性總體當中;因此,對抗和矛盾就簡化為從屬於“一”的環節。雖然這是個幾乎不證自明的看法,但我們應該質疑它。黑格爾的方式與悖論-批判立場不同,原因不在於他思想中的所有對抗與矛盾都“揚棄”在了辯證總體性的“一”之中。當然,兩者之間的差別極其微妙。
為了解釋這一差別,讓我們取徑拉康,迂迴一下。對一個拉康派來説特別明顯的是,利文斯頓所謂類屬與悖論-批判二元性,完全符合“性化公式(formulas of sexuation)”裏男性一面與女性一面所構成的二元性。巴迪烏的類屬立場顯然是“男性的”:我們掌握了普遍的存在秩序[12](巴迪烏的書詳細地描述了存在論結構),以及真理-事件這一例外(它只能偶然發生)[13]。存在的秩序是自洽的、連續的,它服從嚴格的存在論規則,不允許任何自我指涉悖論存在。這個宇宙沒有任何預先設立的統一體,它只是由不可化約的“多”構成。這是一個擁有眾多世界與眾多語言的宇宙。針對生命是一種循環運動、最終萬物歸於塵土這一傳統智慧[14],巴迪烏給出了一種偉大的教益:這種實在的封閉圓環,這種出生、腐爛的循環,並沒有窮盡所有;奇蹟會一次次發生,生命的循環往復會被突然爆發的事件打斷,傳統形而上學與神學稱後者為永恆,或一治一亂的瞬間(stasis)[15]——從stasis的雙重意義上説,既是生命運動的凝固,又是騷動、不安,對於萬物規則性運行的抵制。想一想墜入愛河吧:它嚴重擾亂了我習以為常的生活,一切都固着於愛人身上,我的生活彷彿凍結了起來。……同存在的普遍秩序及其事件性例外的邏輯形成對照的是,悖論-批判方式將焦點放在了存在秩序自身內在的不自洽與騷動上。存在沒有例外——不是因為存在秩序全體就是如此,用思辨的話來説,是因為悖論-批判分析展示了這一秩序如何已然是它自身的例外。[16]——恰恰需要通過不斷違背秩序自身的規則來維持這一秩序。雖然巴迪烏用精準的術語描述出存在秩序之中(在場與再現之間)的空無與缺口如何使事件成為可能,但他卻將事件定義為一種奇蹟性的闖入。事件擾亂了存在的連續性,它不是存在的一部分。[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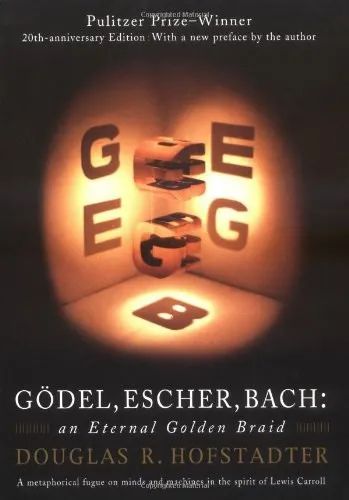
《哥德爾、艾舍爾、巴赫———集異璧之大成》 侯世達
然而,從悖論-批判立場來看,存在的秩序在其構成上就是毀於內部。侵擾起於內部。用弗洛伊德的話説,巴迪烏始終將人類存在的秩序指認為倖存者尋求快樂,就此而言,巴迪烏忽視了弗洛伊德所謂“死亡驅力”的維度,即“存在”的核心處有着一種引發混亂的力量。由此,我們從“男性”邏輯轉到了“女性”邏輯:不再是普遍的存在秩序遭受事件性例外的侵擾,而是存在自身烙印上了一種基本的不可能性:非-全(not-all)。
巴迪烏為了自己普遍而自洽的數學存在論不得不付出代價,對於這一點,利文斯頓明察秋毫。巴迪烏不得不將多與空無設定為實在的基礎構成要素。“不可化約之多”(multitudes of multitudes)起自空無,而非經由“一”的自我差異化而來。在康托爾-哥德爾的宇宙中,只有在最基礎的層面上排除“一”,我們才能夠獲得一種自洽的普遍性。——“一”只能在第二次出現(第一次只有“多”),它是“數”這一操作的結果。正是這種操作從“多”中構造出了世界。在這個層面,我們也擁有了諸種世界不可化約的雜多性。——諸種身體、諸種世界、諸種語言,都是“多”,不可能被總括進某個“一”。唯一真的普遍性,唯一能夠推行“一”的普遍性,——“一”穿越了身體和語言(以及“世界”)的雜多性。——就是事件的普遍性。就政治而言,存在層面上只有龐雜的身體和語言,或是龐雜的“世界”(文化)。所以説,我們在此所能得到的,就是某種自由主義多元文化主義,它寬容不可簡化的差異;而任何一種想要推行普遍方案來一統文化的嘗試——比如共產主義,一定是壓抑性的,以暴力的方式強加於人。[18]與巴迪烏的類屬方式形成對照的是,悖論-批判方式並不接受“多”蓋過“一”這一存在論上的優先性:對抗和不自恰當然破壞、挫敗、阻礙了每一種“一”,但是,這裏從一開始就呈現出一種不可能性,它為雜多性打開了空間。涉及語言時,《聖經》裏的巴別塔寓言是完全正確的。語言的雜多性預設了單一語言的失敗。這就是黑格爾提出“具體的普遍性”的意旨所在:把失敗串聯在一起。歷史上出現了眾多國家形式,原因正在於國家本身就是一個不自洽的/對抗性的概念。
換種説法,具體的普遍性的基本運動,就是將普遍性的例外轉化為一個為此種普遍性奠定基礎的要素。讓我們來舉一個或許會讓人感到吃驚的例子:猶太人和以色列國。法國猶太裔哲學家阿蘭·芬基爾克勞(Alain Finkielkraut)寫道:“猶太人,今天已經選擇了紮根之路。”[19]我們很容易就能在這種論斷中辨識出海德格爾的迴響。海德格爾在接受《明鏡》週刊採訪時(1966年9月23日),堅稱所有偉大的、本質性事物的出現,只能從擁有家園開始,只能紮根於傳統。這裏的反諷之處在於一種詭異的努力:為了正當化猶太復國主義,卻調動起反猶的老調子。反猶主義因為猶太人沒有根基而斥責他們;猶太復國主義卻彷彿是為了挽回這種失敗,想以一種遲到的方式把“根”帶給猶太人。……難怪許多保守的反猶分子野蠻地支持以色列國擴張。但猶太人今天碰到的麻煩是,他們現在想要紮根的地方數千年來都不屬於他們,那是其他民族定居之處。這裏的解決之道並不是把猶太人羣體重新規整為另一個紮下根來的國家,而是將視角倒轉過來:要是作為例外的猶太人恰恰是普遍性的真正代表呢?也即是説,如果沒有根基恰恰是生而為人的原初狀態,如果我們的根僅僅是一種次生現象——無非是為了遮掩我們構成性的無根狀態,那又該怎麼辦?
然而,比起利文斯頓所描述的悖論-批判立場,黑格爾要走得更遠:對後者來説,自我同一之“一”並非總是不自洽的、破裂的、對抗性的,等等。同一性本身就堅定地主張徹底(自我)差異:説某物與自身同一,意思是它區別於自身所有的特殊屬性,即它無法還原為這些屬性。“這朵玫瑰花是玫瑰花”,意味着一朵玫瑰花不只是它所有屬性的總和。——存在着某種“我不知道是什麼”的東西(je ne sais quoi)使它成為一朵玫瑰。這是“玫瑰裏更似玫瑰的東西”。正如此例所示,我們在這裏碰到了拉康稱為“對象小a”(objet petit a)的東西[20]。這是處於對象所有屬性之下的神秘X,卻使此對象成為其所是——維持了它獨特的身份。更準確地説,這“更多一點”的東西在崇高和愚蠢(或粗鄙,有時甚至是淫穢)之間來回搖擺:説“法律就是法律”,意味着就算它有失公正又十分武斷,乃至於成為腐化行為的工具,它卻依然是值得尊敬的法律。所以説,同一性無法再減縮的結構(就是它總能自我同一,而原因正如黑格爾所説——它是一種“映現”範疇[21])即1-1-a,意思是一個事物與它的所有特定屬性相比照,總有對象a這種難以捉摸的剩餘物存在,靠它來維持對象的同一性。
最終,正是“同一性”問題,將我們引向了黑格爾與悖論-批判方式之間的微妙差異。黑格爾並沒有讓不自洽和對抗臣服於某種更高的統一體,恰恰相反,對他來説,同一性,“一”的統一體,具有自我差別化的形式。同一性無非就是將差異引入自我關聯的極致狀態。與其説裂縫和不自洽性不停地對“一”的統一體造成威脅,毋寧説,“一”的統一體就是裂縫本身。這句話的意思是,黑格爾筆下的總體性是悖論式的,不自洽的,但並不是“批判性的”。——如果我們是在抵抗權力中心的意義上來界定“批判”的話。總體性並沒有陷入這樣一種永恆的鬥爭。——這場鬥爭號稱要破壞、取代權力中心,尋求能夠侵擾並拆解權力大廈的裂縫,尋找那些“無法確定的”剩餘。或者,用黑格爾討論思辨同一性的措辭來説,權力自己就是越界的;正是通過違背自己所奠基的原則,它為自己奠定了基礎。悖論-批判方式提出構成我們身份(同一性)的正是不自洽性,它的批判立場使之投身於一場克服這些不自洽性的行動。雖説如此,這個目標卻無法實現,永遠會被錯失或推延。這就是為什麼悖論-批判方式會將自身視為一種永無盡頭的過程。德里達這位悖論-批判方式的終極思想家,就喜歡把解構説成是對於正義的無限追求。在政治上,他喜歡談論的就是“將來到來的民主”(民主永遠不會是已然就位的東西)。
與此種立場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黑格爾從來不是一位批判性的思想家:他的基本立場是和解。——和解不是一個長期的目標,和解是一種事實。正是和解,使我們直面現實化了的理想那一出人意料的苦澀真理。如果黑格爾有他的箴言,就會是這樣:在事物出錯的地方找到真理!黑格爾傳遞的信息並不是“信任的精神”(布蘭頓論黑格爾《精神現象學》新書的標題[22]),而是不信與懷疑的精神——他的假設是任何一種宏大的人類工程都會出差錯,但我們也只能以此種方式來抵達真理。法國大革命想要普遍自由,卻在恐怖中達到巔峯狀態。共產主義想要解放全世界,卻催生出斯大林主義的恐怖一面。……因此,黑格爾帶給我們的教益類似於,奧威爾《1984》裏的“老大哥”那句著名口號的翻新:“自由即奴役。”當我們想要直接強力推行自由時,結果就是奴役。所以説,無論黑格爾什麼樣,他肯定不會是這樣一位思想家:樹立一個只能無限接近的完美理想。海因裏希·海涅(海涅在黑格爾最後的歲月裏做過他的學生)宣揚過這樣一個段子,他有次告訴黑格爾,自己不同意“凡是現實的東西都是合乎理性的”[23],黑格爾謹慎地環視一週後,輕聲告訴他的學生:“或許我應該這樣説:凡是現實的都應該合乎理性。”即使這個段子是真的(就算不是海涅純粹的捏造),也無礙於它在哲學的意義上成為一則謊言:黑格爾試圖對學生掩蓋自己思想裏的痛苦真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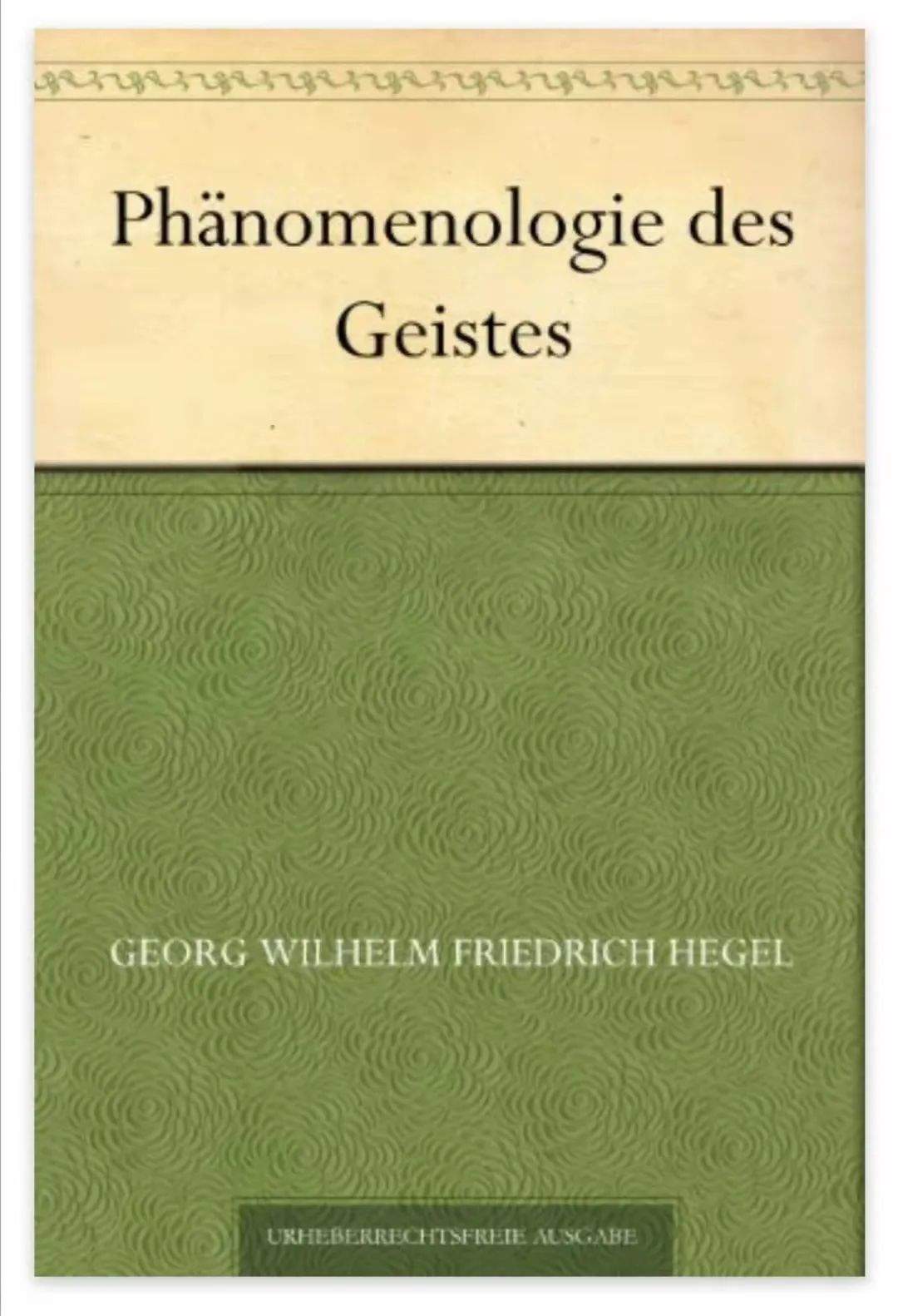
《精神現象學》黑格爾著
放棄批判立場並不意味着拒絕改變社會,這只是表明要為改變付出更多。讓我們就以接收移民這樁棘手事為例吧。Iuventa號船長皮婭·克倫普(Pia Klemp)在地中海搭救了眾多難民,卻拒絕接收巴黎市府授予她的韋爾梅伊大獎章(Grand Vermeil medal)。她用一句口號解釋了自己的舉動:“為所有人辦妥身份文件並提供住處!我們要的是移動和居住的自由!”[24]如果這意味着——長話短説吧——每一個體都有遷居到他或她所選擇的國家的權利,同時,這個國家有責任安置他們,那麼我們在這裏就碰到了嚴格黑格爾意義上的抽象設想。這個設想忽視了社會總體性的複雜語境。問題不可能在這個層面上得到解決,唯一真實的解決方法,是去改變不斷製造出移民的全球經濟體系。因此,我們的任務是從直接的批判撤一步回來,轉而去分析所批判現象內在的對抗狀態。這同時也是將我們的焦點對準以下癥結:自己的批判立場究竟是怎麼樣參與了它所批判的現象的。
因此,關於改變世界的努力,黑格爾賜予我們的教益既絕望又樂觀:所有努力從來無法實現目標,然而經由一次次失敗,一種新的存在形式就會出現。是的,查韋斯在委內瑞拉失敗了,左翼聯盟(Syriza)在希臘失敗了,中國共產主義沒法成為我們的理想,但是所有這些進程都在為精神隱秘的生成添磚加瓦。而精神將帶來無法預言的新景象……或是恐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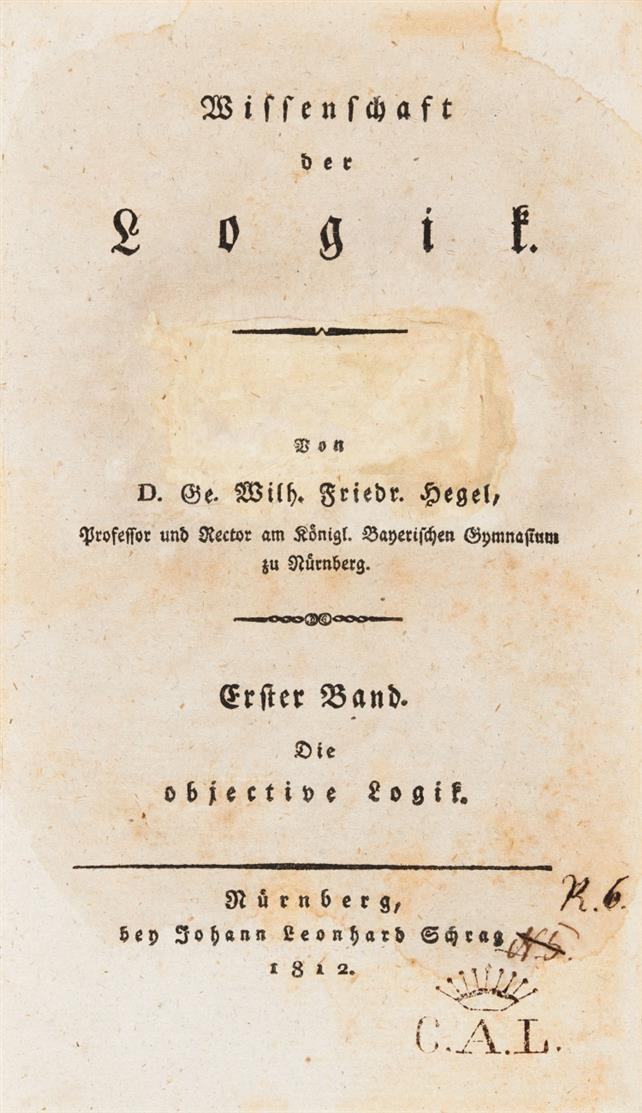
黑格爾《邏輯學》
# ……應對連線大腦 #
上述討論將我們帶往本書主題。我們假定,黑格爾勾勒的不自洽總體性,正是展開思考的終極立足點。重複一下上文引用過的黑格爾之言:哲學只是把“灰色繪成灰色”,哲學只能在某個時代抵達終點的時候把握到它的概念真理。我們在應用這些話的時候,無需畏手畏腳。黑格爾的思想在今天已經再次成為一種終極形式,但這一次具有了康托爾-哥德爾宇宙的形態。這個事實也説明某種新的歷史形式漸露端倪,對它造成了威脅。因此,我們可以把上述假定再往前推一步:連線大腦(把我們的大腦同數字機器直接連接起來,流行説法管它叫“神經連接”)是這種威脅的主要表現。所以問題就變成了:假若連線大腦之類的東西強勢登場,由我們的主體性來表達的人類精神該何去何從?或許,能夠躲避數字空間的並不是複雜的思維,而是事物最基本的自我同一性,即簡單的“A就是A”——它只是在象徵空間裏才會有效運作。
因而可以説,本作不是一項黑格爾研究。但我想要實踐一下黑格爾的方式。這種嘗試成立的前提是,只有當黑格爾的方式還能起效時——即“這個時代在黑格爾眼裏是啥樣”這個問題,依舊有意義且具生產性時,黑格爾身為思想家才是“活着”的。而要問黑格爾方式到底有沒有生產性,比起連線大腦這個卓爾不羣的後黑格爾現象(黑格爾根本無法想象,顯然屬於另一個時代),我們還能想象出更加苛刻的測試嗎?
履踐黑格爾的方式,要做的可不少。首先,本書會對連線大腦觀念及其意識形態推論,以及奇點(Singularity)觀念展開哲學分析。我並不會涉入技術、經濟、政治、性以及藝術這些龐雜無邊的經驗領域。也就是説,本書並不給出關於具體現象的分析,比如連線大腦會為醫藥技術、市場、計算機算法帶來什麼。同時它也不會去理睬某些具體議題,比如連線大腦對於跨性別問題意義何在。我只將焦點放在唯一一個核心問題上:連線大腦現象究竟如何影響“自我經驗”這種自由人類個體獨具的東西?它又是如何波及我們身為自由個體真正的地位的?這個問題也將逼迫我們去澄清“生而為人”這一觀念本身:如果我們確實會走進後人類時期,這個事實將如何使我們以一種新的方式來感知生而為人的本質?一般來説,只有在某種現象真正的存在遇到威脅之時,我們才能把握到它的本質維度。同理,只有當某人意外亡故時,他或她精神上的分量才能被我們體會到。我的目光一刻都不願意離開這個核心問題,這一點大家很容易就能看出來:幾乎在本書的每一章裏,你都能看到這個問題的強迫性重複,彷彿我正在拼命去破解一個無解的謎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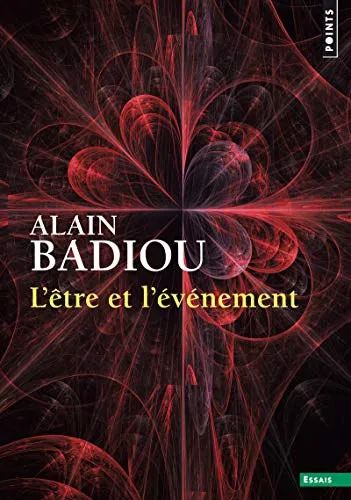
阿蘭·巴迪烏 《存在與事件》
其次,黑格爾的方式意味着,事先去定義連線大腦和奇點觀念是沒有意義的,因為本書的真正任務就是一步一步去闡述它們。我們這裏所能做的,就是以一種純粹形式的方式來為之劃界。“連線大腦”指的是把我們的精神進程與數字機器直接連接起來。此種連接能夠讓我僅僅起一個念頭,就直接發動現實中的某件事。比如,我想着要開空調,電腦就能解碼我的念頭,然後啓動空調。與此同時,它也能使數字機器控制我的思維。而“奇點”指的是這樣一種理念:通過直接向他人分享我的思想和體驗(讀取我精神進程的機器能夠將它們傳輸到另一個頭腦裏),一個全盤共享的精神經驗領域將會出現。這就彷彿是一種新的神性形式在發揮作用。——我的思想將直接融入宇宙自身的全局性思維。
你也應該注意到,我們將擱置連線大腦技術可行性的問題。(譬如它是否會像那些後人主義的支持者所設想的那樣實現呢?)在巨量報道中,讓我們僅舉AlterEgo一例。它是“一款麻省理工學院媒體實驗室開發的可攜帶設備,能夠識別沉默語言(捕捉下頜和麪部神經肌肉信號),完成輸入輸出。這個設備可以戴在頭上,並貼近頸部與下頜。它能夠讀取你大腦語言中樞的脈衝,然後在電腦上把它翻譯出來,而且全程默音。”[1]開發這套系統的阿爾納夫·卡普爾(Arnav Kapur)指出:“並不只是它能夠讀取你的思想,你得有意識地決定去使用它。”:
當你在心裏對自己説話的時候,這個小小的頭戴裝置能夠憑藉強大的感受器,去追蹤大腦傳送給內部語言機制——比如舌頭和喉部——的信號。想象一下你問了自己一個問題,但實際上沒把這個詞説出聲來。即便你的嘴唇和麪部一動不動,你的內部語言系統還是在履行它的工作,形塑出了那句話。內部語言所涉及的肌肉(如舌頭)發生了符合你想説的那個詞的振動。就算它極其細微乃至難以追蹤,也能被這種設備捕捉到。[2]
因此,到目前為止一切尚可接受。這一設備並沒有讀取我的頭腦,只是讀取了我意圖説話時產生的內部語言肌肉信號。在這個層面,扯謊依舊可能:我只需簡單地想着去説一些不真實的東西,我的言説肌肉就會相應地運動起來,機器就會“讀取”我這一欺騙性的言説意圖,把它當作事實。……然而,我們也很容易就能想象,進一步的發展會使機器追蹤到我的思想線索,而這無需我同意,乃至我根本意識不到。——這顯然帶來了惡託邦(dystopia)式的前景。
可是,我們真的活在一個惡託邦的時代嗎?還是説,我們只是活在一個充斥着惡託邦幻想的時代?連線大腦這一理念本身,以及它關於集體共享私密經驗的設想,難道不是一種幻想嗎?難道不是對某些趨勢做出了幻想性推論?而實際上這些趨勢不可能像所設想的那樣實現?有一件事是確定的:我們不應低估集體共享經驗所帶來的影響,它極其令人不安。任何事物都會被它改變。近期發生在韓國首爾的一場辯論,完美地概括出了對之抱有懷疑的觀點。一位年長的紳士(名字我記不起來了)提出了一個精彩的悖論:不僅奇點不會像人們預言的那樣糟糕(我們人類將留住自己的精神性,雖然這種精神特徵會變得模稜兩可,會產生不信之信,指涉缺席者[3]),而是它根本不可能發生。我同意奇點不可能如那些鼓吹者預料的那樣發生,然而我們應該堅持,某種不可預料的新事物的確會出現。彼得·斯洛特戴克[4]把雷伊·庫茲韋爾看作新的施洗者約翰——一種新的後人形態的開路先鋒。這是正確的。庫茲韋爾完全把握住了連線大腦的激進含義。關於實在的整個設想以及我們在現實中的地位,都將產生鉅變,他對此看得極為清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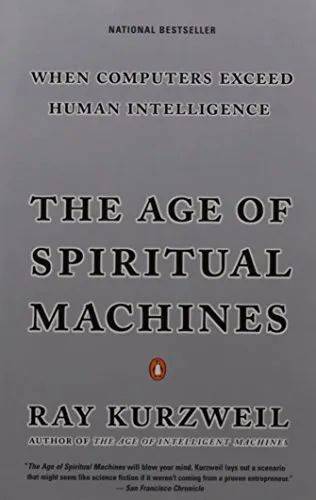
庫茲韋爾 《靈魂機器的時代》
不止是連線大腦理念,庫茲韋爾關於奇點的觀念一樣依賴人工智能前景:他的預言是,由於數字機器的能力呈指數式增長,我們很快就能和那些全面展示出自我覺知(self-awareness)跡象的機器打上交道了。它們遠超人類智能。我們可別把這種“後人”立場,和那種用技術全面操控自然的實用主義現代信念搞混了。我們在今天見證的東西,恰好是對之的辯證倒轉,且具有典範意義:如今的“後人”科學不再強調支配,而訴諸令人震驚(偶然、非計劃)的湧現。讓-皮埃爾·杜普伊偵測到了此種奇特的反轉。植根於人類技術的傳統笛卡爾式人類中心主義的傲慢被顛了個個兒。這一反轉顯然可以在今天的機器人、基因、納米等技術領域以及人造生命與人工智能研究中識別出來:
我們怎樣去解釋,搞科學成了一種“有風險”的活動?對於某些頂級科學家來説,科學成了如今殘存的人性的主要威脅?有些哲學家對於這個問題的回應是,錯在笛卡爾之夢——“成為自然的主宰和所有者”,我們迫切需要去“支配那種支配”。我覺得他們懂個屁。他們根本沒看到技術呈現在我們面前的樣子:技術“融合”了所有學科,為的是不去支配。未來的工程師不是因為疏忽或無知,成了巫師的學徒,而是選擇成為他的學徒。他會“贈予”自己複雜的制度和組織,他會嘗試去學習這些制度和組織能夠做些什麼,他的方式是去探究它們的功能屬性——一種自下而上、從細部到全體的方式。他會成為一位探索者,一位實驗者,但絕不會是一位執行者。成功的標準與其説是讓自己達成的業績符合既定任務清單,毋寧説是在何種程度上他的創造會給自己帶來驚異之感。[5]
這種想要達成自我排除的詭異傾向,不正有着弗洛伊德所謂死驅力的形式嘛?——一種令人意想不到的形式!這種人類自我超越的推動器,正是在進化生物學、神經學和認知腦科學領域中產生且依然在推進的科學進展。有一種詭異的羞恥感維持着這些探究:我們的生物侷限性,我們的必死性,我們如此愚蠢的生養後代的方式,都成了我們的恥辱。京特·安德斯稱其為“普羅米修斯之恥”[6],從根子上來講它是這樣一種簡單的羞恥:“我們是被生出來的,而不是被造出來的。”尼采那個看法——我們都是些“末人”,無非是為自己的滅絕和新的超人的到來做了鋪墊。——因而被賦予了一種科學-技術癖好。……不過,由於主題限制,我在書裏會略過人工智能話題。雖説人工智能和連線大腦顯然相互關聯,但兩者之間還是有着顯著的差別:人工智能可以超越我們人類,但並不會使我們捲入共享經驗的空間。也就是説,人工智能會讓我們悲催的大腦依舊以迄今為止熟知的方式來運作,卻不加干涉。
因而我們假定,儘管公共媒體的報道存在簡化與誇張,這個領域中確實有某種東西正在蠢蠢欲動。我則會把自己限制在追問連線大腦和奇點的哲學含義與哲學後果上。這就是為什麼奇點想象是值得來講一講的:儘管其中“新紀元”(New Age)矇昧主義[7]氣味濃厚,又混合着對於技術的天真看法,我們還是應該搬用喜劇演員格魯喬·馬克斯的話:“他們聲稱要呈現某些真正新穎的東西,他們的做法好像是在呈現真正新穎的東西,但別讓他們把你騙了(你別認為他們是在做戲)!——他們的確指向了真正新穎的東西!它正在出現!”在這個“連線大腦”和“奇點”剛剛起步的階段,圍繞融入奇點(共享思想和體驗的空間)究竟是如何組織起來的,我們進行了如下推測與思索:主體與/或機器究竟如何來決定連接或(斷開連接)?連接範圍究竟如何來劃定?——我能獲得多少關於機器的知識?我究竟以何種方式來共享經驗?同誰來共享經驗?始終應該牢記的是,這些同時也是極為重要的政治問題。[8]
因此,問題的要點不在於批判馬斯克、庫茲韋爾以及其他連線大腦支持者的觀念,説他們關於人類心靈與語言的看法天真且原始。他們當然把常識性的自我觀與粗糙的自然主義一鍋燴了。關鍵問題是,這些流俗而粗鄙的觀念將現身為數字機器,後者能掃描並處理我們的大腦。那樣的話,這些觀念就成為現實了。即使馬斯克等人談到連線大腦會如何威脅我們的人性,他們也只是用一種極其狹隘且誤導性的方式來把握這個遭受威脅的維度——我們生而為人的本質。所以説,或許真正對我們生而為人造成威脅的,是這種狹隘且誤導性的生而為人的觀念。馬斯克、庫茲韋爾和其他一些人也描述過何者將受到連線大腦的威脅,可他們首先會自發地將此種“生而為人”的觀念作為討論前提。因此,當我們討論“後-人類”(post-humanity)時,應該格外留意自己是怎樣來理解人性的。或許,展望“後-人類”,恰恰可以使我們獲得何謂生而為人的洞見。[9]
由此,我們的研究方案必然是三個方面相互交織:理論、經驗和體制。我們會一直往復考察這三個方面:(1)探究連線大腦的結構,追問其可能的理論含義。(2)把大腦連接起來,對於個人來説究竟意味着什麼;連線大腦怎樣改造(自我)經驗。(3)最後不能不問,連線大腦的社會-政治制度性含義究竟是什麼。它會催生出何種新的權力關係?維護連線大腦的龐大數字網絡是如何組織起來的?又會受到何種約束?軍事機構正以意料之中的方式回應此種威脅:“徵召:軍事‘倫理學家’。技術:數據挖掘、機器學習、殺手機器人。必須具備:冷靜的頭腦、道德準則,不會對將軍、科學家,乃至總統説不。五角大樓正在尋找適合者為涉入人工智能這潭道德上的渾水來掌舵,後者已被列入21世紀戰場名單。”[10]與之脈絡不同的倫理委員會所能給出虛偽解決也只是:限制科學的“濫用”。
一位消息靈通的觀察者不禁會注意到,任何一種意識形態同樣由這三方面構成。就以宗教為例:宗教是(1)一種由神學闡明的信仰體系,包含了對於實在終極本性之類“大”問題的答案;(2)關涉神聖向度之私密體驗的複雜網絡;(3)一種意識形態機器,一系列制度和物質實踐(儀式等等)。其實精神分析也是這樣,它是一種理論,(當然不僅僅)涉及人類心理與臨牀實踐,以及(我們不可忘記這一點)“組織起來的羣體”,一種能夠催生認同的診療體制。[11]回到奇點上來,它由以下三方面組成:首先提供了一套關於人性的解釋,也闡發瞭如何從人過渡到後人,甚至表達為一種新的神學向度;其次,奇點向我們許諾了一種新的主體經驗——融入集體心靈空間;然而,最後——這個方面經常被人忽視,奇點也暗示着一種龐大的機器網絡,後者終究嵌入在支配性的社會關係當中。我們會簡單地受到機器控制嗎?是否一部分人會出售同機器之間的特權性聯結?粗暴而直接地説吧,奇點這一(事件性的)崛起將如何影響資本主義?如何影響社會權力形式?
因此,我們應該讓連線大腦觀念在三個不同的層面上接受批判性分析。首先,(但這溢出了本書的範圍),應該追問其技術可行性:我們真能造出那種機器嗎?它們可以與神經流直接產生互動?(神經流為我們的自我意識提供了物質基礎。)其次,即便我們以某種方式成功地連接了大腦,就真能直接共享其他人的經驗嗎?遇到外部主義(externalist)的觀點[12]怎麼辦呢?對於此種見解來説,富有意義的經驗並不是頭腦裏的內部形象,而是“在大腦之外”。經驗產生於大腦、身體活動與複雜現實之間的相互作用。這是一個相當繁複的過程,而我們也只能在外部實在當中發生互動。照此定義來説,聚焦於孤零零的大腦必將錯失目標。再次,即便憑藉某種手段可以達成經驗共享,我們的主體性會在融入共有空間之後存留下來嗎?預先透露一下我們最後的分析結果:能夠躲開奇點籠罩的,並不是我們活生生的體驗,而是我們的無意識。不過,此種無意識恰恰關聯於笛卡爾式主體的自主性。
# 並置 #
最後告誡一聲:黑格爾的方式會盯着基本概念,但並不涉及體系性的概念分析。後者往往會忽略特殊的內容。如果你仔細研讀黑格爾,馬上就能意識到,黑格爾實際上是以並置的方式來推進論述的,即常常猛地從一處特殊內容跳躍到另一處。因而這本書同樣也是對連線大腦這一主題展開並置式呈現。並置(希臘語寫作παράταξις,指“把一物放置在另一物旁邊的行為”)是一種文學技巧,它喜好短小、簡單的語句,愛用並列連詞而非從屬連詞。在詩歌並置中,兩個意象或片段——往往是毫無相似之處的意象或片段——在缺乏清晰聯繫的情況下並列在一起。這會給讀者留出空間,並置的句法會給出暗示,讓他們自己來推出聯繫。……所以説,指責這本書既無關於黑格爾,也沒好好討論連線大腦,在某種意義上命中了目標。——它命中了目標,但卻錯失了要點。這個要點恰恰身處並置模式之中,圍繞着兩個並置的節點來回遊走。這樣一種分析步驟對於黑格爾的體系方法來説會不會太陌生了?當然不會!難道還有比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更具並置特徵的作品嗎?
本書的隱秘模型是我所喜歡的作品——E.L.多克特羅[1]的《詩人的生活:一部中篇與六部短篇》:先是六篇完全無關的短篇小説(互相之間僅有些許隱秘的呼應),接着是一部中篇小説,寫一位紐約作家。讀者會從中發現,上面六部短篇是這位作家想象性自傳的片段。我這本書本可以採用這樣一個副標題:“一篇論文和七篇隨筆”。七篇隨筆討論七個不同的主題(神經連接、神學中的墮落問題、蘇聯早期社會主義建設的死結、新型數字警察國家……),然後跟着一篇更具實質意義的研究論文,它涉及前述所有主題,嘗試對連線大腦的前景展開哲學意義上的説明。
我們將從生活本身的數字化談起,討論這一現象的政治含義:一種新型警察國家是否正在逼近?從一般意義上的數字化和數字控制出發,我們會轉向更加具體的連線大腦方案。我會用一些開放性的提問來對那種簡單、天真的描述進行補充。連線大腦究竟如何影響我們的權力關係這個問題,將帶領我們回到蘇聯的生物-宇宙論。此種關於共產主義的設想——即共產主義是一種共享的經驗空間,預示了奇點的靈知式觀念[2]。安德烈·普拉東諾夫[3]清楚地看到了這種靈知式共產主義觀念的限度。這樣,我們就轉向了一種批判性分析。關於奇點的通俗神智學解讀(“新紀元”運動)——即認為奇點最終是精神與物質重新合一,正是此種分析的批判對象。鑑於奇點許諾去解決基督教所謂的“墮落”,我們將探究墮落、自由和知識限度之間的聯繫。我們的目標是澄清黑格爾的“揚棄”(Aufhebung)概念與奇點所帶來的“消除”(人之有限性在奇點中被消除)之間的差異。接下來,無意識的自我反思結構將得到詳盡闡發。我意在勾勒出那種可以避開奇點掌控的象徵世界的輪廓。緊隨其後的是一種文學幻想。連線大腦不斷擴張,相應的主體性模式也會出現;這種文學幻想就嘗試對之展開想象:倘若貝克特筆下“無法稱呼的人”所藴含的笛卡爾沉思恰恰可以給我們指明出路呢?那篇結論性的論文則假定,奇點如事件一般出現,它顯然是天啓式的。但奇點會是哪種天啓?新的天國會不會隨之來臨?還是説無法到來?十分清楚的是,後-人類轉向標誌着我們所知曉的歷史的終結。——但是,究竟什麼與之一塊終結了?又是什麼隨之誕生了?

安德列·普拉東諾夫
讀者不應在此尋求詳實的預言:本書給出的是一種哲學反思。連線大腦的出現是一個事件,針對我們的主體性將如何受它影響,我們只能進行推測。此外,我們甚至察覺不到自己的大腦被連接,由此一種新的自由與權力形式將會出現。説起來也簡單,這種自由與權力就存在於這樣一個時刻:我們能夠脱離奇點(或與之斷開聯繫)。全盤性的數字控制,我們甚至難以察覺。這種前景殘忍地把一個基本的哲學問題拋在我們面前:是否贏得自由的唯一機會,就是脱離奇點空間?是否存在一種生而為人的向度,就算我們完全融入奇點,這一向度還是能讓我們基本擺脱它?
所以在某種意義上,本書也是一系列關於迂迴現象的隨筆。這些現象從一開始就像鬼魂一樣糾纏着哲學:為何比起直接抓住事物,一種迂迴接近事物的方式能帶給我們更多東西?這個悖論在眾多層面上生效。比如,為什麼我們只能通過謊言和騙人的幻覺來接近真相?也就是説,為啥忽視了環繞着真相的謊言之網,我們就會錯失真相?温斯頓·丘吉爾曾寫下這樣一句話:真相是如此珍貴,以至於要用一層厚厚的謊言防護牆來保護它。在這一點上他是正確的。又比如,為什麼一部具有藝術水準的小説比起紀錄性的描述更能抓住一個時代的本質?比起事無鉅細的歷史著作,為什麼我們能從莎士比亞的戲劇那裏學到關於伊麗莎白時代更多的東西?最後不得不提的是,為什麼對一個情慾對象單刀直入所能帶來的快感,遠沒有采取種種複雜的手段推遲與對象相逢、繞着它打轉來得多?兩位思想家深諳此種迂迴的悖論,且言之甚詳:黑格爾和拉康。黑格爾辯證法的基本假定就是:通往真理的道路是真理自身的一個環節。真理最終無非是為一連串錯誤做出體系性的闡明。拉康引入剩餘-享樂概念正是為了解釋:為何推遲獲得快感乃至禁止獲得快感,卻生產了這一行為自身的快感。今天,隨着數字技術的爆炸性發展,迂迴的問題不斷加劇,乃至達到了極致狀態。數字化使我們最私密的體驗變得不再直接:情色製品正在成為我們日常情慾活動的一部分。我們越發只能通過數字媒體來接近實在;數字媒體不僅能夠忠實地呈現實在,而且可以強化實在。然而,認知科學和技術的新趨勢打開了一種前景,即繞開語言以及其他交流媒介,直接進入他人的思想和體驗。這又將給生而為人帶來何種影響?
所以,再説一次,這並不是一本關於黑格爾的書。這本書關乎一個當代版的黑格爾如何來直面對於他的世界來説全然陌生的東西——連線大腦現象。這本書也關乎黑格爾自己提出的無限判斷[4]“精神的存在是一塊骨頭”[5],當然本書所涉及的是它的當代版本——我們的頭腦是一個數字機器。黑格爾説,邏輯真正的開端是“決定”去思考——思考什麼都可以;去做點什麼,即便它不具有實定性行動的意義。海德格爾派可能會直接將這種主張視為某種證據——黑格爾依然沒有越出“願的形而上學”(the metaphysics of Willing)[6]視域。我們可以不接受這種讀法,然而,只要“決心”表明一種主體性維度,事實就依然沒有改變。——但如今是以極為複雜的方式發揮作用,不再僅僅是“我們必須去思考思維本身。”“決心”在黑格爾那裏的地位,無法用心理學或非理性的方式來把握(即外在於邏輯的非理性剩餘物),而是具有嚴格的邏輯意義,內在於邏輯學構造。在某種極端新穎的東西出現之時,我們必須同樣懷有直接介入每一次重要轉向的決心:在這些轉折點上,如果想要有效地掌握新現象,我們必須再次下定決心去思考。而展望神經連接,肯定就是這樣一個時刻。
註釋:
向上滑動閲覽
[1] 在接下來的這個部分裏,我會概述一下自己處理黑格爾的方式,這是從我近期一系列書裏全面發展出來的看法,尤其是《性與受挫的絕對》(Sex and the Failed Absolute)(London: Bloomsbury Press, 2019)。
[2] “槓”(bar)這一術語顯然具有拉康精神分析的特徵,可參考迪倫·埃文斯:《拉康精神分析介紹性辭典》,李新雨譯,重慶: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2021年,第31頁。台譯本《拉岡精神分析辭彙》(劉紀蕙等譯,台北:巨流圖書公司2009年)則將“bar”譯作“隔離線”。——譯註
[3] 參看Paul Livingston, The Politics of Logic:Badiou, Wittgenstein and the Consequences of Formalism(New York: Routledge, 2012).
[4]簡單來説,哥德爾兩項不完備定理即:第一定理——任意一個包含一階謂詞邏輯與初等數論的形式系統(皮亞諾算術的形式系統),都存在一個命題,它在此係統中既不能被證明為真,也不能被證明為否;第二定理——對於一個包含皮亞諾算術的形式系統,該系統的一致性或自洽性不能在系統內部證明。而嚴格來説,證否(disprove)不同於證偽(falsification)。可證偽指的是實證的、而不是邏輯的概念。證偽是理論言説與實際經驗之間的比較,而無關乎理論本身的邏輯結構。因此,在此處,disprove更應譯為“證否”。——譯註
[5] 自洽性或一致性(consistency)指的是:一個系統不會同時推出一個命題和它的否定。——譯註
[6] 此處“實在界”(李新雨譯法)或“真實”(劉紀蕙譯法)顯然需放在拉康精神分析的“象徵-想象-實在”構造中加以理解,但因為齊澤克這本書幾乎無處不在對“實在界”的意義加以發揮,故本處不作特別解釋。關於拉康的“實在界”的基本意涵,可參考迪倫·埃文斯:《拉康精神分析介紹性辭典》,李新雨譯,第309-311頁。——譯註
[7] 這裏涉及拉康的象徵界與實在界之關係:“儘管象徵界是一系列被稱為能指的業已分化的離散元素的集合,然而實在界,就其本身而言,是未經分化的,‘實在界是絕對沒有裂隙的’。正是象徵界在意指過程中引入了‘實在界的一道切口’:‘正是詞語的世界創造了事物的世界——這些事物在形成過程中的此時此地原本是混亂不堪的。’”迪倫·埃文斯:《拉康精神分析介紹性辭典》,第310頁。關於此段最後一句拉康原話的翻譯,另一譯本稍有不同:“是詞語的世界創造了事物的世界——事物原本是隨時隨地地混融於所有發生過程的此時此刻之中。”(《拉岡精神分析辭彙》,第267頁。)——譯註
[8] “反思性”(reflexivity)在當代學術界譯多譯作“反身性”、“自反性”乃至“反射性”。實際上齊澤克使這一經典的德國觀念論術語與當代“邏輯的政治”產生了積極的關聯。為了凸顯齊澤克所強調的觀念論傳統,因此我主要將它譯作“反思性”,這樣亦可使“無意識”(精神分析)與“反思性”(觀念論)產生一種辯證的語義張力。當然,需要説明的是,“reflexivity”基本意義是“自我指涉”,其語用學意義則包含“反思性”、“自反性”與“詮釋學循環”。關於這一概念的簡要辨析,可參考肖瑛:《“反身性”多元內涵的哲學發生及其內在張力》,《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2004年第3期。——譯註
[9] 齊澤克關於“佔據常識一面的大他者”的分析,與德國理論家普法勒(Robert Pfaller)所謂“無主的幻覺”或“他人的幻覺”之間形成了富有意味的共振關係。在後者看來,在面具儀式或劇院裏往往會有這樣一種幻覺,我們並不是這些場景的承受者,但為了使我們獲得滿足,它必須要有一個承擔者——後者完全處在幻覺之中。這種既不是你也不是我的“天真看客”,勾勒出一個“無知”或僅僅從“常識”出發的大他者的位置。普法勒此説又在很大程度上得自法國精神分析學者馬羅尼(Octave Mannoni)。可參看Robert Pfaller, On The Pleasure Principle In Culture:Illusion without Owners(London: Verso, 2014).——譯註
[10]在利文斯頓看來,巴迪烏的類屬方向考慮到了自我指涉悖論,而且從自我指涉出發創造出多之無限性的原理,並描摹出柯恩所謂力迫之技(technique of forcing)的轉型性後果。這樣一來,巴迪烏也就使類屬方向反駁了任何想要批判性地訴諸語言結構或語言本性的做法,他將後者一律歸入建構主義方向。利文斯頓則指出了另一方向,即充分認識這些悖論而且並不拒絕在語言內部展開反思。此即“悖論-批判方向”,它會在可思、可説的邊界上,追蹤自我指涉悖論所造成的動盪的意義。簡言之,利文斯頓認為,類屬方向堅持真理溢出語言,而悖論-批判方向則堅持語言可以捕獲真理。參看Paul Livingston, The Politics of Logic:Badiou, Wittgenstein and the Consequences of Formalism, pp.56-57.——譯註
[11] 參看利文斯頓的論述:1、本體-神論方向指的是:通過指涉一種特權性存在、一種“超級實存”來建立存在的總體性。總體性由此被構想為恰切安置諸存在的一種特定秩序。總體性隱晦地受到某一典範存在的規約,被設想為超越了事物秩序,難以言説。2、準則或建構論方向則早已潛伏在唯名論傳統以及康德以後的批判思維之中,並在20世紀的語言學轉向那裏得到了充分的方法論表現。這種方向所理解的總體性,可以通過廓清語言的結構與邊界而得到表述。參看Paul Livingston, The Politics of Logic, p.54. ——譯註
[12] 在巴迪烏看來,存在論/本體論是數學的而非哲學的。存在論研究純粹多(pure multiple)的呈現(presentation),其中不摻雜半點被象徵秩序結構化的“多”的經驗。巴迪烏關於真理的表述如下:真理是忠貞進程的無限的肯定性總體。對於任何一種“百科全書”或“知識”規定來説,它包含了至少一個避免了“百科全書”規定的探究。這樣一種進程就可以被稱為類屬程序(generic procedure)。一種不可分辨的“包含”(inclusion)就是真理,它除了“屬於”(belonging)之外,沒有其他“屬性”。這個部分是無名的。除了來自呈現(presentation),除了由那些可以再次被標記的毫無共同之處的“項”組成之外,除了屬於這個情境之外,這個部分沒有任何其他標記。嚴格説,這個部分就是自身作為存在而存在。但是就這樣一種“屬性”——存在(“多”而非“一”)——而言,這個部分為情境中所有的項共有,它與任何一個彙集了項的部分並存。因此,不可分辨的部分由定義來説,簡單地佔有了任何一種部分的“屬性”。——譯註
[13] “事件”是巴迪烏哲學的核心概念。簡單來説,在存在論意義上,“事件”是一種悖論性的存在。一方面,為了確認事件是否呈現在“情境”(指有確定規定的集合)中,首先事件得作為情境的一個元素得到呈現;但另一方面,只有解釋性的介入(命名),才能宣佈事件呈現於情境之中:事件是作為非存在的存在到來,作為不可預見的可見到來。事件即堅持情境內在的不自洽性與過剩性。——譯註
[14] 認為萬物終將破毀的立場,並沒有什麼反左翼的地方。——甚至可以説,所有真誠的左派都會同意這一立場。在搖滾樂領域,英國託派分子樂隊“家庭”創作的《織工的回答》堪稱這種立場的終極表達。這首歌以單曲的形式於1989年面世。它從“織工”(命運、死亡)的立場出發,描繪出關於主體生命的看法。在這裏,就算是快樂的家庭生活也終將歸於孤獨與絕望。如果我們比較一下《織工的回答》與他們下一張專輯《即便如此》(1970)裏的主打歌《好消息壞消息》,那麼這個樂隊的真正天才之處就會一目瞭然了。《好消息壞消息》吸收了《織工的回答》的第一旋律主旨,但是將這一主旨分割成更短小的部分,從而歌詞就以一種絕望的方式質問了既存政治秩序,諸如“為啥改變規則/上頭的人説/對着底層/他們正抬着頭看。”這種將旋律線切短的方式,呈現出了干擾、爆發,使得智慧的充分表達(生活終是一場空)變得不再可能。當然,這絕非表明家庭樂隊的歌曲只給苦澀與狂怒留了地盤:他們那首最使人震動的《沒有一頭驢子是傻子》就非常精彩地描摹出男孩和他那頭懶散的驢子愉快共處。因此,這三首歌給出了一個自洽的三元組合:日常的快樂諸瞬間;將這些特殊的快樂瞬間普遍化為生活的根本毀滅;最後,是對毀滅與壓迫展開絕望的抵抗。
[15] “一治一亂”(stasis)這個譯法得到了姚雲帆研究的啓發,關於stasis的思想譜系亦可參考姚的研究。參看姚雲帆:《神聖人與神聖家族:阿甘本政治哲學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161-171頁。——譯註
[16] 正文加粗部分為齊澤克原文強調語句,本書一律以加粗標出。——譯註
[17] 我們可以在這裏指出,利文斯頓在描述巴迪烏理論構造的同時也製造出了一個悖論:在利文斯頓看來,雖然巴迪烏選擇了自洽性而非總體性,但他的想法並不是説,宇宙就是一團不能自洽的混亂之物,僅有邏輯自洽的空間從中誕生:而是説,我們將“存在”視為“全有”(在這個意義上就是總體性)。就此而言,總體性是自洽的(正如巴迪烏的存在論指出了這一點),不自洽性只能產生於極其罕見的事件性例外。
[18] 齊澤克在此並沒有具體展開巴迪烏關於“共產主義”(其實此處主要指“現實社會主義”)的看法,因此有必要略作説明。巴迪烏的相關反思可以在他的《世紀》一書中找到。在他看來,“對於真實的激情”是20世紀的核心主題,其中包括斯大林的革命實踐及其恐怖的“大清洗”。巴迪烏所謂的“真實”取源於拉康的“實在界”(the Real),而非實證主義意義上的“實在”。而用馬克思主義的語彙來説,“真”即是所謂歷史真理或社會現實的本質。求“真”與克服資本主義、開創“新”世界的衝動相關。在巴迪烏看來,這一激情所帶來的“淨化”衝動企圖使真實和外觀相同一。擺脱這一“壞的無限性”的方式則是將真實把握為“裂隙”本身。參見Alain Baidou, The Century, trans.by Alberto Toscano (Cambridge: Polity, 2007).——譯註
[19] 《世界報》2015年1月29日。
[20] “objet petit a”在中文語境中有多種翻譯,如“客體小a”,“小對形”、“對象小a”等。此處採用“對象小a”的譯法,主要根據齊澤克自己的説明:“齊澤克從德國唯心主義哲學視域對這個詞進行了解釋,認為對象和客體是完全不一樣的:客體是主體沉思的東西,而對象則是動態的,主體要和它鬥爭,在費希特意義上講就是自我和非我的關係;在拉康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