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應對“疫情倦怠”?一個來自人類學者的建議_風聞
上弦继国岩胜-2022-03-30 11:15
轉自公眾號信睿FM,作者張慧、黃劍波。

©Unsplash user Hello I’m Nick
[ 編者按 ]
2022年的春天,我們仍然處於新冠疫情的長期影響之下。隨着深圳、上海等城市先後進入大範圍檢測和封控的緊急狀態之中,最初的那種焦慮和恐懼仍舊普遍,與此同時,還有一種無以名狀的疲倦感,在新日常中瀰漫開來。
我們或許可以稱之為“倦怠”。作為一個近兩年十分流行的詞彙,倦怠既是一種個人感受,也是醫學描述中的“突發應激能力”被掏空之後的狀態,更是一個社會結構性的癥結。倦怠的背後,是對秩序和確定性的期待,以及優績主義的陷阱。
除了學會與風險和不確定性共處,我們應如何以一種更積極的姿態應對?今天的文章由兩位人類學者張慧和黃劍波共同撰寫,講述新冠疫情時期的倦怠,並呼籲一種有“痛感”的關係。在此分享給大家,以期帶來些許思考和慰藉。
文 / 張慧(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
黃劍波(華東師範大學社會發展學院人類學研究所)
焦慮是否一定是一個時代病症或現代性問題,我們難以確定,但是我們大概可以確定我們確實生活在一個焦慮的時代,一個焦慮無所不在、全面覆蓋、深度滲透的時代。這是我們的日常生活經驗。
焦慮是否一定是一箇中國特色問題或發展階段問題,我們也難以確定,但生活於當下中國的我們大概也可以確定這是一個全民焦慮的時代:幾乎每個個體都能感受到不同程度和類型的焦慮。而社會學家和人類學家更為關注的顯然是社會性的焦慮和結構性的焦慮,尤其是其具體的生成機制和文化邏輯。確實,焦慮的生成和強化有着其具體的社會性和文化性,觀念性和處境性。
一年多來,因為新冠疫情,我們被籠罩在一種全方位的焦慮和全新的不確定性之下,習以為常的生活模式似乎也很難回到從前,比如不戴口罩出門。在一個習慣了每天都有to do list(待辦事項),年終要盤點總結,去到每一個餐廳、景點、國家都要打卡的時代,這種無法做(長遠)計劃、無法預知未來半年、一年甚至更久的生活無疑給習慣了全球化與流動性(無論是貨物、人員還是信息)的我們帶來了對不確定性的新體驗。
我們對新冠疫情暴發初期的緊張、焦慮都不陌生,無論是不停地刷手機、看新聞,還是對身處其中的風險的切實恐懼;我們對發生如此大規模疫情蔓延的無助和恐慌也並不陌生,無論是搶口罩、無數次地洗手,還是需要就醫的等待及信息不對稱帶來的“病急亂投醫”;憤怒和悲傷也不少見,正如美國人類學家羅納託·羅薩爾多(Renato Rosaldo)所描述的,悲痛之中隱藏的難以名狀的憤怒甚至足以使菲律賓的伊隆戈人去砍下敵人的頭顱……[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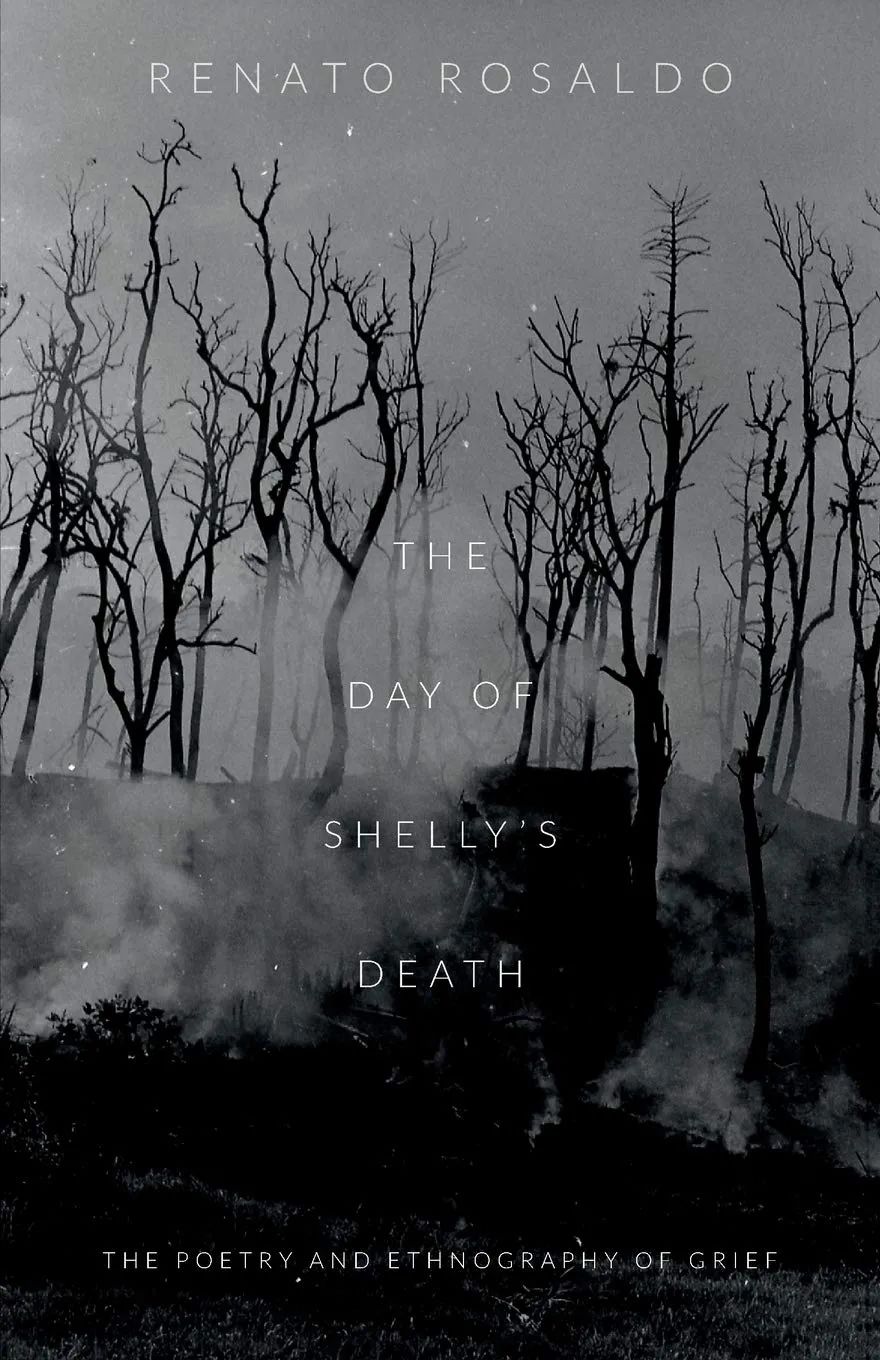
The Day of Shelly’s Death
Renato Rosaldo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3
無以名狀的“倦怠”
在一個長期的疫情狀況下,應激機制並沒有一個結束、恢復、重建的過程,所以突發應激能力被掏空之後的狀態就變成了荷利所描述的一種“焦慮似的抑鬱加上趕不走的倦怠”的複雜混合體。
除了這些可以被“命名”的情感,似乎還有許多無以名狀之物,説不清的“累”“提不起精神”“無所適從”及“效率低下”。科學記者塔拉·荷利(Tara Haelle)在一篇題為 Your “Surge Capacity” Is Depleted —— It’s Why You Feel Awful(《你的“突發應激能力”已經耗盡——這是你感覺糟糕的原因》) 的文章裏提到了一個醫學詞彙——Surge Capacity(突發應激能力)。其指代一系列心理和身體的應激系統在人類面對極端壓力(比如自然災害等極端狀況)下的短期生存機制——但自然災害往往在短時間內發生,即使災後重建非常漫長。
而這次疫情不一樣,這場“災害”到底什麼時候能結束還是未知數。荷利的文章指出,這種短期的應激能力在幫人類度過災難之後就會被耗空,需要時間才能恢復,讓人類有可能面對下一次的災難。但在一個長期的疫情狀況下,應激機制並沒有一個結束、恢復、重建的過程,所以突發應激能力被掏空之後的狀態就變成了荷利所描述的一種“焦慮似的抑鬱加上趕不走的倦怠”(anxiety-tainted depression mixed with ennui that I can’t kick)[2]的複雜混合體。
在全球不同地區都經歷了或多或少、或長或短、或緊或松的隔離、禁足、封城的背景下,澳大利亞天主教大學的喬納森·澤克博士(Jonathan L. Zecher)在Acedia: the Lost Name for the Emotion We’re All Feeling Right Now(《倦怠:我們目前感受到的那種失去的情感的名字》)一文中提出了一個用來描述古希臘人的情感的詞彙——Acedia(倦怠)——來描述當下的狀況。
Acedia的古希臘文原義是指一種無痛無感的遲鈍狀態,是對任何事物的漠然,是根本上的不在乎。在公元5世紀記述了這一感覺的神學家約翰·卡西安(John Cassian)如此描述這種感覺:“像是經歷了長途旅行或是持續很久的齋戒之後,身體的無精打采,以及疲憊的飢餓感……下一秒他開始左顧右盼,然後抱怨沒有人來看他。他不斷進出房間,不斷向上看,好像覺得太陽落得實在是太慢……”[3]
在當時,人們認為Acedia不會影響城市人或是生活在羣體之中的修士,只有那些獨自修行的人才會因為空間和社會的隔離而產生這種感覺。按照澤克的説法,很多政府對疫情的應對在很大程度上覆制了獨自修行的修士的狀況:社會隔離限制了社會交往,封城導致了活動空間的限制,在家工作或失去工作使我們日常工作和生活的界限被打破,或完全改變了此前建立的生活秩序和節奏。

Hieronymus Wierix的作品Acedia,16世紀晚期
被“懸置”的時間
在不能出門、不能聚會、不能旅行的時間裏,時間感被重構,我們也生活在一種不能確定未來日期的“懸置”之中。
14天的集中隔離、7天的居家隔離,封城第XX天……疫情自發生開始也引入了一套新的時間敍事。這套時間敍事有其流行病學依據,但也切實地改變了我們習以為常的日常生活安排。在不能出門、不能聚會、不能旅行的時間裏,時間感被重構,我們也生活在一種不能確定未來日期的“懸置”之中。
在人類學研究中,時間本就是一個相對之物:中國的農曆是一個以耕種為中心的農業時間表,“三十而立,四十不惑”是古人對人生歷程的期待……在人類學中,時間的另一個重要面向是針對暫時性(temporality)的研究。
正如一個關於“暫時性”的民族誌研究中所提到的,“無聊、等待、無事可做、線上活動以及不作為,是人類學探討時間的重要維度。因為恰恰是在這些時刻,時間流動的規律性被打破”[4]。當習慣的時間安排和時間感受到限制和挑戰,我們對既有生活的理解也不得不相應被打破和重建。

《世界上最糟糕的人》
“不確定”和“失序”
對秩序的預期可以是航班按時起飛、快遞當天送達、商場正常營業……這種秩序可以是個人設定的、習以為常的,也可以是社會文化所安排的、約定俗成的,當然也可以是更為宏大的全球政治經濟結構的產物。
無論是個人層面上感知到的焦慮,還是社會結構意義上的焦慮,都有着某種對於失序或出位的強烈感知和反應。而這正好表明人類對於“應當如此”的嚮往,對秩序或在位的想象。對秩序的預期可以是航班按時起飛、快遞當天送達、商場正常營業……這種秩序可以是個人設定的、習以為常的,也可以是社會文化所安排的、約定俗成的,當然也可以是更為宏大的全球政治經濟結構的產物。
與失序對應的是關於“不確定”的研究,無論是針對doubts(某種信仰或信任崩塌所導致的懷疑),還是uncertainty(人類所認知的、定義的或試圖控制的不確定),都在試圖發現和理解當某種秩序被破壞之後人類的社會文化應對策略。
正如學者常常論證的,在風險中存在客觀和主觀的區分。客觀的風險可以是真實的威脅,而主觀的風險則更多地基於文化的觀念、信仰,甚至針對這種風險的知識和認知也是可以協商和改變的。基於這一本質,所謂的失序和不確定可以既不完全是客觀的,也不完全是主觀的,而是在一個被認為有價值的東西受到威脅的情況下出現的。
這種“不確定”與人們如何確認、感知、理解和控制風險的一系列觀念有關。比如,我們的時間焦慮可能與“與時俱進”“只爭朝夕”的文化觀念有關;我們常常提到的住房焦慮、教育焦慮,也許恰恰是因為住房和教育承載着我們認同的核心的內在價值體系——比如對家的依賴、“望子成龍”裏隱含的對向上流動的期待……
當在追求這些核心價值時,人們面臨巨大的經濟壓力和挑戰,與此相關的焦慮也就不可避免了。
“秩序”與對生活的“掌控”
唯一確定的是不確定,與不安全共處是唯一的安全感。這也許是新冠疫情給我們上的重要一課。
讓人無處可逃的疫情使我們重新反思生活中的那些“確定”,並遭遇了更多的新的“不確定”。荷利在《你的“突發應激能力”已經耗盡——這是你感覺糟糕的原因》一文中提到,生活在“新常態”之中的應對方法之一就是:接受不完美、降低對自己的要求。以前兩週能做完的工作,現在花一個月才完成也沒什麼;當你什麼都不想做的時候,就給自己放兩天假。
事實上,這種焦慮和倦怠在成就高、成績好的人身上表現得更為明顯,也更難克服。而在時間的“懸置”之中,我們也可以重新思考,哪些價值是對我們最為重要的,哪些又是可以被捨棄的?
顯然,人類面對和應對不確定時的身體和心理反應既是個人的,也是社會文化的。如何重建自身的“秩序”,如何重建社會對於“確定性”的需要,是我們需要共同面對的問題。正如那句著名的引文所説**,**Uncertainty is the only certainty there is, and knowing how to live with insecurity is the only security(唯一確定的是不確定,與不安全共處是唯一的安全感)。這也許是新冠疫情給我們上的重要一課。

《世界上最糟糕的人》
回到合宜的位置:在關愛中活下去
或許更為重要的是,在指代深度關係的同時,“關愛”還是一個動詞。甚至可以説,如果沒有具體的行動或動作,所謂關愛的合宜關係是根本不存在的。
不過,在新常態的情境下接受不完美,降低預期,並不意味着“放棄治療”“認命”“投降”。事實上,這些描述雖然都是鬥爭式的語言,但指向的是戰敗之後的沮喪和絕望。長久以來,我們已經習慣了這種“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的思考方式。
如前文所述,焦慮指向的除了恐懼和憤怒,還有可能是倦怠、失去活力。倦怠的根本在於無望,這是在“空虛混沌”狀態下無法逃避的處境——“淵面黑暗”之際,還有什麼可期待的呢?擺脱這種混沌或失序的出路,或許正在於修復和重建各種合宜的關係:天與人、地與人、人與人及人與自我的關係。
換言之,回到合宜的位置,在彼此的關愛中勇敢地活下去——儘管我們面臨的是“血淋淋的現實”。我們需要找回“痛感”,找回對人、事、物及世界的真切的關懷和在乎。畢竟,有痛感,有在乎,表明還有盼望,有活力,生命仍然在運轉之中。
我們無須完全同意人類學家閻雲翔對於中國社會正在全面且快速個體化的判斷,但他所描繪的一些現象至少讓我們心有慼慼。我們大概可以説,正是孤零零的個體在一個強大的、充滿了危險或風險的外部社會中的這一意象,日益強化了作為個體的人的恐懼和無時不在的焦慮感。
問題在於,這並不僅限於自我關係的糾結,我們的經驗現實似乎是,每個人都成為別人的威脅,每個人都不在其當在的位置上或關係中。作為羣體的人似乎也在以彼此為敵,生活在一個充滿敵意的競爭性的族羣關係、地區關係或國際關係中。
文明的衝突不僅是一種學術觀點,在一些地方和人羣內部更是一種立場和主張。進而言之,作為類別的人似乎同樣也在與天地爭鬥,結果則是整個自然界似乎也在做出反抗,從食物,到土壤,再到空氣、氣候、宇宙……在當下,這也是一種“新型”病毒。
我們或許還可以從古希伯來人那裏找到一些可資借鑑的思想資源。例如,“愛裏沒有懼怕”這句看似雞湯的話語在當下仍有直接的意義。不過,這裏的“沒有”不是有和無的意義上的“沒有”,而是指“懼怕”可以被安置、面對和轉換。更重要的是,在這個表達中,愛不僅僅是一種情感性甚至情緒性的東西,而是一種持久的、有深度的、恰當的關係。
換言之,在(愛的)關係中就有可能面對恐懼,面對無以名狀的焦慮甚至倦怠。進一步,若處在(正確的或合宜的)秩序中,或許就可以免於過度的焦慮。個體的人之間如是,羣體的人之間如是,作為類別的人與其生活的世界也如是。
人類學家和哲學家摩爾(Annamarie Mol)在The Logic of Care(《關愛的邏輯》)一書中也有類似的表達。儘管摩爾批評的主要是現代西方醫學及現代西方社會的個體主義哲學和人際關係,希望在過度強調個體自主的“選擇的邏輯”的這個時代,重新去尋找一種更健康、持久和深刻的“關愛的邏輯”,呼籲一種關係性的人類生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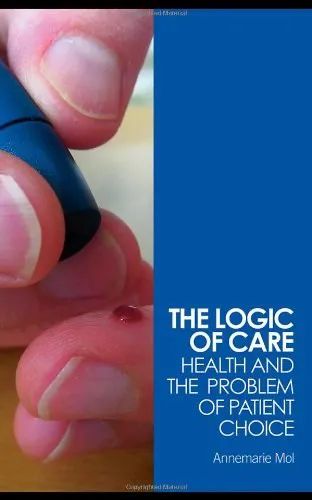
The Logic of Care
Annamarie Mol|Routledge 2008
或許更為重要的是,在指代深度關係的同時,“關愛”還是一個動詞。甚至可以説,如果沒有具體的行動或動作,所謂關愛的合宜關係是根本不存在的。只有當你真正投入了對某人或事物的關愛的行動,對其精心地照料(care for),才能説明你真的在乎(care about)。
而這種照料和在乎正是對那種無以名狀的倦怠(Acedia)的回應和可能出路,是存着盼望的帶有活力的行動,儘管這一過程可能非常艱難,常常伴隨着眼淚與汗水。顯然,不同於倦怠所描繪的那種根本上的冷漠,這是一種有痛感的關係:你痛,我也痛,因為我在乎你。
註釋
[1] ROSALDO R. The Day of Shelly’s Death: The Poetry and Ethnography of Grief[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4.
[2] HAELLE T. Your “Surge Capacity” Is Depleted- It’s Why You Feel Awful[Z/OL][2020-8-17]https://elemental.medium.com/your-surge-capacity-is-depleted-it-s-why-you-feel-awful-de285d542f4c.
[3] ZECHER L J. Acedia: the lost name for the emotion we’re all feeling right now.[Z/OL][2020-8-27]https://theconversation.com/acedia-the-lost-name-for-the-emotion-were-all-feeling-right-now-144058.
[4] DALSGARDL A. et al (ed.) Ethnographies of Youth and Temporality: Time Objectified[M].Temple University Press, 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