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喜劇的作用也就到這兒了,只不過是在這十幾分鍾內給大家制造一個幻覺_風聞
观察者网用户_239515-2022-04-08 14:03
來源:一席
六獸,單口喜劇演員/喜劇編劇。
我希望至少在我的作品裏,每一個人物都是值得被拯救、被原諒的。我覺得既然喜劇講的是我們的故事,那如果他們值得被原諒,至少我們也值得被原諒。
(本演講推薦大家觀看視頻!)
迎着屁股向前闖
2022.3.12 杭州
大家好,我叫六獸。我是一個胖子。我是單立人喜劇旗下的一個單口喜劇演員,也就是人們經常説的脱口秀演員。
有一些朋友認識我,可能是因為去年有一個綜藝,叫作「一年一度喜劇大賽」,我在裏邊擔任了一名編劇。
編的東西是什麼呢?我們管它叫作Sketch。然後接下來的那個問題一定是,Sketch是什麼?
我們想了很多辦法去解釋,把它翻譯成了素描喜劇或者是美式小品,但是我都不是很滿意。我覺得直接把Sketch當作小品理解就行,那我其實就是“寫小品的”。
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什麼呢?我想稍微賣一個關子,先給大家講一個故事。
01 穿制服的小偷
這個故事發生在30年前。北京的街頭,一個寒冬的夜晚,來了兩個小偷,一個老手,一個新手。
老手要進屋去偷東西,需要新手小弟在大街上給他放風。但是那個時候的北京夜晚非常寂寥,沒有什麼人,一個人杵在大街上半天不動,肯定會引起懷疑,所以老小偷拿出了一身衣服,讓小弟穿上。
那是一身警服,是他們剛剛從勞改農場逃出來的時候順手從人家辦公室裏邊順出來的。新手小偷穿上也不是很合身,但是勉強能矇混過關了。
這個時候街上來了一名真的警察,他看到有個同事在街邊杵着,自然要上去攀談一番,於是他們兩個就聊起來了。聊着聊着,走過來了一個路人,向警察問路。
警察幫助了路人,路人向警察表示感謝。這其實是很正常的一個狀態,但是新手小偷心裏邊卻悄悄地起了一些變化。他問警察説,只要我們幫助別人,就能收到感謝,對嗎?警察非常詫異地説,當然了,肯定是這樣的。
於是當警察走開的時候,這個小偷也開始嘗試幫助其他人。隨着收到的感謝越來越多,他心裏邊也越來越亢奮,亢奮到最後他在這個空無一人的街道上開始指揮交通。這個亢奮變成了一種社會責任感,當這個社會責任感達到頂峯的時候,他就相信了自己真的是一個警察。
所以當老大行竊成功,走到他身邊的時候,他一個箭步就把老大按在地上説,我抓住了一個小偷。
這是一個非常魔幻的時刻。我知道咱們觀眾席裏邊肯定有些人已經想起來了,這是30年前陳佩斯、朱時茂還有魏積安先生的一個小品,叫《警察與小偷》。

▲ 從左至右分別是:朱時茂、陳佩斯、魏積安
當然如果你想起來的話,你也別藏着,那你年紀基本上和我差不多了,已經是個中年人了。
我今天其實就是想從這個小品説起,聊聊Sketch的兩種人物狀態。
我們在寫Sketch的時候,管陳佩斯老師演的“新手小偷”這種角色叫作怪人,顧名思義就是怪異的人,是思考邏輯或者是行為舉止跟大家不一樣的人。跟他對應的就是朱時茂老師的“警察”角色,我們叫直人,就是所謂的普通人或者是正常人。
怪人和直人放在一起就是一個最基本的喜劇搭檔,小品裏面經常會看到。其實這種搭配在很多其他藝術形式裏都有,比如有一段傳統相聲叫《黃鶴樓》,

▲ 相聲《黃鶴樓》代表版本:馬三立&趙佩茹
(圖片來自網絡)
裏面的逗哏演的就是一個假裝自己是京劇大師的菜鳥戲迷,一個典型的怪人。再比如在日本漫才裏邊,也有裝傻役和吐槽役這兩種角色。
我接觸過很多編劇和演員,他們有一部分人在接觸到這個理論以後自己消化了一下,就直接管這個怪人叫傻子。我自己的理解是有一點點不同意的。
比方説剛才的小品中,我們能説新手小偷是一個字面意義上的傻子或者是白痴嗎?我覺得不是。他的行為邏輯基本上是正常的,只不過在那個時刻,他相信了自己是一個正直的人,相信了自己是一個警察。
當他夢醒的那一刻,有一句台詞讓我記了很久,他説:“我是小偷,我怎麼會是小偷呢?”

▲ 小品《警察與小偷》片段
這句話傳到我耳朵裏邊其實是另外一個意思,聽起來就像是,我這20年白過了,我選錯了路。
這個時候他的老大魏積安先生在旁邊説了一句台詞,那句台詞就格外地扎人心。他説,你以為你是個什麼東西。
我當時7歲,看到這裏的時候,我心裏邊想的是,喜劇的內核是悲劇。
這真是一個好作品,我非常喜歡。所以我不覺得他是一個真正的傻子,他只不過是在那一刻呈現出了一個怪人的狀態。
02 看升旗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過這樣的時刻,就是在生活中突然有一瞬間意識到,我現在想的事情,或者是我正在做的事情,好像和所謂的普通人不太一樣。你們有沒有?
我每天都在經歷這樣的事情。我給你們舉個例子。
還是在我7歲左右的時候,我跟父母一塊去北京旅遊,我們決定去看一場升旗。但是我們起晚了,倒也不是特別晚,旗還沒升起來。但是當我們到天安門的時候,前面已經牙牙差差地累積了十幾排的人。
那個年代看升旗沒有現在秩序這麼好,大家都需要往前擠。我媽可能覺得我們都已經付出這麼大代價到這來了,可不能只聽一個升旗就回去,所以她就計劃讓我從前面這十幾排屁股中間鑽過去,開始玩命往前推我。
我不知道發生了什麼,當時就本能地抗拒,拼命往後躲,於是我們兩個人就開始對抗,她越往前推我就越躲,我越躲她就越往前推。
過了大概兩分鐘,她才突然意識到為什麼推不動我,並不是前面的人牆太過堅固,而是因為我在跟她對抗。那個時候她給我下了一個評語,“不出攏”。這是我們老家的話,用普通話翻譯過來叫“沒出息”。

這個評語在我身上扛了大概有二十多年。所以在過去二十多年裏,從某方面來講在我媽眼裏,我就是一個怪人,這個怪人的性質叫作“沒出息”。
但是現在我想我可以跟我媽解釋一下,當時我為什麼做出那樣的決定。
首先,我不覺得迎着屁股往前闖這件事比看升旗更簡單。第二,我7歲左右的時候,身體開始發胖,我意識到了我跟身邊的小朋友是不一樣的,於是開始有意識地脱離集體生活,不參加集體活動,也不參加什麼運動。
順便説一下,我那個時候最擅長的一門運動叫原地不動。我真的很擅長這個運動,可以一個週末什麼事也不幹,就往我家客廳沙發上一坐,腦子裏胡思亂想,一坐就是一整天。也就是説一直到現在為止,我對人羣都是抱有恐懼的。
所以你們知道我為什麼是個脱口秀演員了嗎?我就是想離人羣稍微遠一點,人羣最少的地方就是這兒了。

我覺得當時我如果跟她説了這些話,她可能就不覺得我是一個怪人了,但是我沒説。
反過來説,時間差不多過去了30年, 現在把這個故事放到網上,大家可能反而會覺得我媽是一個怪人——你是一個媽媽,你為什麼強迫你的孩子做不願意做的事情?為什麼面前有上百個陌生的人,你會覺得你可以把你的孩子推到這些人羣中,而不覺得他會不知所措?
這個問題我也困惑了很久。但是當我長大以後,我把這個問題想明白了。我的媽媽是上個世紀60年代生人,她生活在一個物質非常匱乏的年代。
那個時候物質匱乏大概到什麼地步呢?我媽跟我爸談戀愛的時候,她第一次去我爸家做客,我奶奶給她做了一大鍋燉菜,多到什麼地步呢?是用洗臉盆裝的。
她把這個盆放到桌上,然後招呼我媽過來吃,我媽就一個手拿着筷子,一個手拿着碗,剛要走到那桌菜跟前,突然覺得身後有十幾道寒光在看着她。她扭頭一看,是我爸爸的七個兄弟姐妹。那些人跟她一樣,一手拿筷子一手拿碗,“嗷”地一聲,跟野狼一樣,就把那桌菜給圍了。
大概兩分鐘過後,他們散開了,就是在電影裏邊經常看到的那種橋段,只剩下一個空的洗臉盆在桌上轉,所以那頓飯我媽什麼也沒吃上。我奶奶就非常生氣,當然那是後話。
我媽就是生活在那麼一個年代。在那個年代出生的人,無論想爭取什麼,或者想保護自己手上應該有的東西,他們都要靠自己想辦法去努力、去爭取,沒有人能替代他們。
我家後來養過二十年的奶牛,最多的時候有七十多頭。我的姥爺跟我説,你媽在開這個奶牛場之前,一頭牛都沒見過。但是她在養這些牛的時候,餵牛和擠奶基本上都是她自己弄的,甚至有的時候還要給奶牛接生,給奶牛做手術。
所以你們大概知道我媽是一個什麼樣的性格了吧?如果她設定了一個目標叫看升旗,她絕對不會覺得面前的屁股是什麼問題。所以想明白這些以後,好像我媽也沒那麼怪了。
我記得海明威有一個冰山理論,是説觀眾能看到的部分其實只是水面以上很小很小的部分,在它下邊可能是一個非常龐大的山脈,否則的話冰山就會漂走。

▲ 圖片來自網絡
那水面之下的部分,需要演出來嗎?肯定不用,這部分是我們要放在自己心裏邊的。
其實生活裏也一樣,我覺得這個地方用竇文濤老師的一句話來形容非常合適,他説你想一下,如果我們有能力走到一個人內心足夠深的地方,這世界上還有正常人嗎?
我覺得沒有。所以我們每個人都可以是怪人,我們每個人都會有那樣的想法,只不過是需要一些條件和原因來觸發,把他激發成怪人的那個狀態。
如果你明白了這一點的話,只要你願意,你也可以成為一個喜劇編劇。因為説實話,喜劇裏邊這種經典的怪人角色實在是太多了。比如説剛才小品裏邊那個以為自己是警察的小偷,再比如需要在一個月內花光十個億的屌絲,

還有為了驗證自己的孩子孝順不孝順,而給自己辦了一個假葬禮的農村老太太,

還有我最喜歡的,這位帶着一個屍體旅行的農民。

這些全都是怪人角色。
03 密室裏的最後一課
我們去年在那個節目裏面也創造了一些怪人角色,有一些也受到了大家的喜歡。比如説作品《這個殺手不大冷》裏面,我們創作了一個聽到音樂就停不下來的殺手。

▲ 「一年一度喜劇大賽」作品《這個殺手不大冷》
還有大家看到的作品《最後一課》中,一個要在密室逃脱裏面給他的學生指導表演的老師。

▲ 「一年一度喜劇大賽」作品《最後一課》
還有作品《台下十年功》裏,穿越回二十年前想勸自己改行的京劇演員。

▲ 「一年一度喜劇大賽」作品《台下十年功》
這些都是挺有趣的怪人角色,也收到了很多人的好評。
也會有一些人覺得在這些人身上看到了自己。我覺得他們能有這樣的感受,是因為我們做對了一步工作,就是我們在找到了一個足夠好笑的怪人角色以後,多問了一句為什麼——
他為什麼會變成這個樣子?
他為什麼會在這個時刻被激發出來?
······
也就是我們開始嘗試找冰山下的那部分了。但是這個真的增加了好多好多的工作量。
我們要找到一個符合大家共鳴的、符合邏輯的、符合人物性格的原因,真的好難。比如説在我們的作品《最後一課》裏塑造的這個老師,張弛。

▲ 演員張弛扮演的老師
這個小品講的是戲劇學院的一個表演老師,在玩密室逃脱的時候,突然發現這個密室裏的NPC,也就是臨時工演員,在演喪屍的這個人是他前幾年教過的最好的學生。
然後他做了一個決定,他決定在這個密室裏當着大家的面調整他的表演。這個時候演喪屍的演員蔣龍自然就非常尷尬,這個喜劇的衝突就產生了——老師越熱情,蔣龍就越尷尬。

▲ 演員蔣龍扮演的密室NPC演員
這個時候就出現問題了。演老師的這個演員叫張弛,他是一個非常棒的演員,他當時問了我一個問題。
他説,如果是我在密室裏邊看到這個學生,我第一選擇可能是繞開他,假裝看不見,如果劇情要求我必須跟他去搭話的話,我也會鼓勵他,你挺好的,你可以的,然後就走了。但是要我上去當眾調他的表演,這種事我幹不出來。
我聽到了一句演員們經常説的話,“我過不去”。
於是我們就一起去尋找這個角色的狀態,我們看了很多心理方面的書籍,也找了很多相關的故事。最終張弛找到的老師的這個狀態是什麼呢?
其實他兜裏邊裝的那個東西很簡單,那就是他是一個老師,他是一個非常負責任非常喜歡這個學生的老師。
那又怎麼樣呢?他當下能給他的學生一個電影邀約嗎?給不了。他能給他介紹一個其他的行業,讓他去做,讓他賺大錢嗎?也給不了。他能直接給他五百萬嗎?也給不了。他只是一個老師。
而下一次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會見,他能做到的最好的事情也就是在此時此刻,再給他上最後一堂表演課。
準備到這裏,張弛就知道該怎麼演了,也就有了大家最後看到的這個狀態,非常可愛的一個老師。

▲ 全程都很好笑,推薦大家去愛奇藝看完整版!
這個老師也收到了很多觀眾的好評,他們説在這個老師身上看到了自己,看到了自己以前的老師和同學,想到了很多東西。
我覺得很棒,但是我覺得喜劇的作用也就到這兒了,它只不過是在這十幾分鍾之內給大家制造一個幻覺,能讓你想起來自己心裏邊本來就有的一些東西,能讓那個火苗往上再燒個十幾分鍾,也就是這個意思了。
04 剩下的253個人
在講這個問題的時候,我相信有一些觀眾心裏邊可能有一個疑問,就是剛才舉的那些例子裏邊,《落葉歸根》不是個喜劇。
是的,怪人不只是存在於喜劇裏,怪人可以存在於任何的藝術形式裏。因為藝術其實就是在講述生活對我們造成的改變,所以在各種文藝作品裏面,怪人的出現就成了一個非常有趣的把手。
那為什麼喜劇裏面的怪人會好笑呢?這個我想就牽扯到了另一個問題。我的朋友賈行家曾經問過我這個問題,當時他問我的時候我真的無地自容。他問我的問題是,
喜劇是什麼?
嚇死我了,喜劇是什麼?我的天哪,在我的印象裏能回答這個問題的人基本上已經死了幾百年了,我就是一個寫小品的,我怎麼能回答這麼龐大的問題呢。但是我又很雞賊,我又不想輸,所以我就給他講了一個故事。
日本有一個民間故事,叫作《忠臣藏》。它大概講的是日本古代的一個城主被屈含冤,被天皇壓在皇城裏邊。他城裏邊的那些家臣中,有47個武士決定組成一支敢死隊衝到皇城,把主人給救出來。

▲ 圖片來自網絡
最後他們成功了,不光把主人救出來了,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改善了當時武士階級在社會中的待遇。這是一個非常熱血的故事,它被改編成了很多種藝術形式,描述的都是這47個人的故事。
但是在日本有一種藝術形式叫落語,基本上可以理解成是日本的單口相聲。唯獨在落語裏邊,這個故事是從另外一個角度展開的。
在落語裏,當主人出事的時候,城裏一共有多少個人呢?有300個人。也就是説當這47個武士決定要去營救主人的時候,還有253個人不知道在幹嗎。
落語裏講這253個人在幹嗎呢?他們跑了。所以一個德高望重的日本落語大師立川談志跟我們説,喜劇講的就是這253個人的故事。
一聽就很合理是吧?我們都能想象那個畫面了,47個武士在圓桌前説,“我們要起義!我們要抗爭!”

然後旁邊200多個人説,“算了吧,好死不如賴活着。”

“多混一天是一天,跑吧,沒事的。”
這種話我們在生活裏其實每天都在碰到:當我面對一大桌美食的時候,旁邊的人會跟我説,你要減肥。我説算了吧,吃飽了才有力氣,明天再減。我們喜劇演員經常會碰到的一種情況就是互相鼓勵,“今天場子冷,不是你的原因,都是觀眾的原因。”
我想落語裏邊説的是這253個人的故事,其實也是在講我們的故事,我們就是這253個人。
立川談志後來還補了一句話,他説所謂喜劇就是對我們人性裏愚蠢、懦弱、懶惰這些不好的特性的一種肯定。我想這個應該不是什麼讚揚或者讚美,而是想告訴大家,每一個人身上都有這些特質。
如果你能想明白這一點,你就能理解我的一個小執拗,就是在我的作品裏,我不想出現那種十惡不赦的臉譜化的壞人。我希望至少在我的作品裏,每一個人物都是值得被拯救、被原諒的。
因為我覺得既然喜劇講的是我們的故事,那如果他們值得被原諒,至少我們也值得被原諒。
05 喜頭可以悲尾嗎
其實這些年小品在輿論環境裏邊有一個槽點,叫喜頭悲尾。説的是一些小品可能在結尾的時候要刻意地上一下價值,或者是煽一下情,希望能以一個濃烈的情感作為結束。
去年我們也收到過類似的評價,有觀眾在評論裏説,“我就是來樂呵樂呵的,你逗我就完了,為什麼非得來這麼一下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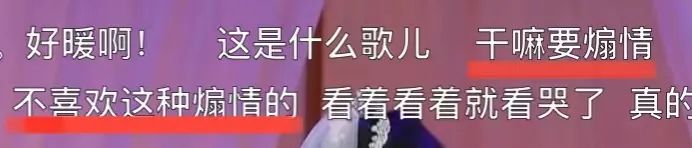
我當時心裏想的是,我也不是非得來這麼一下子,只不過我前面都已經把情感堆到那個地步了,我是真誠的,我到這兒不來這麼一下子,它不對呀。
我能保證我正在描述的情緒是真實存在的,演員、編劇、導演在堆疊的這些東西,都是我們每個人心裏邊本來就有的東西,哪怕是流眼淚也是真誠的眼淚,那為什麼不可以呢?
我們有一個作品叫《走花路》,講的是一個父親在自己女兒的婚禮上,由於慌張、恐懼這些感情而大鬧一場的故事。可能有人會説這都説爛了或者這不真實,但是其實真實情況下只會更煽情。

▲ 「一年一度喜劇大賽」作品《走花路》
我們在找原型的時候看到過一個視頻,那個視頻非常非常地打動我。那是一個婚禮的真實錄像:舞台上一對新人正在舉行婚禮,舞台下邊是一張飯桌,是父母坐的主桌,兩個父親坐在一起。
男孩的父親看上去非常開心,拿着酒杯觥籌交錯,四處應酬;女孩的父親則低頭吃肉,生怕別人過來跟他聊天,他就一口一口往嘴裏扒那個肉,就感覺好像下一秒鐘,他那個鼻涕、眼淚就會噴出來一樣。
我看得非常感動,我也感受到了那個情緒。它可能打動不了所有人,可能只有當你有了那個經歷才能理解那種情緒。但是在那一瞬間我就感覺無論如何,這個本子也得做下來,並且它在最後一定會有高濃度的感情的升温。
但是到排練的時候,我們發現演員對那個高濃度的情緒有一點點牴觸,其實不如説叫害怕,他們有點害怕那個感情,所以演起來就很彆扭。
於是在排練的時候,表演指導劉天池老師就衝到舞台下邊,她衝着台上的女主角喊,史策,你可以害怕煽情,但是你不能害怕感情。
於是女主角史策在真正演出的時候呈現出了一個非常漂亮的狀態,在她扭頭的瞬間,有一滴眼淚從她的眼眶裏噴湧而出,但是非常剋制。

▲ 演員史策
一個絕美落淚。好漂亮,是吧?
我們對這個結果非常非常地滿意,她表達出了我們想表達的東西,呈現出來的也非常地完美。但是這個作品卻收到了剛才説到的那種評價,我當時真的好氣憤。
我想跟他説,你可能沒經歷過,所以你不知道這種感情,但不代表它就是錯的,不代表我不應該做。
但是我沒有發出去,因為我突然意識到了,對於他們來説,我也是個怪人。
他們在説這句話的時候,他們想表達的是,你是一個喜劇編劇,你為什麼最後要用一個悲劇來結尾,要用眼淚來結尾?而我沒有告訴他們後面這些原因。
反過來對於我來説,他們也是怪人,因為我從來不知道他們到底是誰。有沒有可能他們在白天干了一天的工作,然後晚上非常地疲憊,就是想看一個直截了當的喜劇呢?當然有可能。
有沒有可能他正在備考,壓力特別大需要放鬆一下呢?當然有可能。
有沒有可能他就是那個吃肉的父親本人,他不想看到自己的那個情緒呢?當然有可能。
想到這的時候,我那個信息沒有發出去。我當時想的是,你看,我們從來沒有真的理解過對方。
這就是我對喜劇的一些小感悟。我是六獸,我會繼續在喜劇裏邊尋找自己。
謝謝大家。
策劃丨Holiday
剪輯丨F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