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世間》:好故事的能量_風聞
秦朔朋友圈-秦朔朋友圈官方账号-2022-04-12 16:55

過蟈 | 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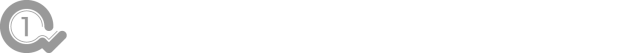
好故事的能量
《人世間》的導演是李路,他上一部大火的電視劇是《人民的名義》。
這部劇看得我幾乎每一集都要哭,想下筆寫寫,卻又千言萬語不知怎麼説。文學界有一種職業叫“評論家”,能評論得頭頭是道的故事,往往不是一流的。對真正的好故事,人們是不會説很多話的,只會看一遍再看一遍,或者就着其中某些橋段看好幾遍。
原著小説《人世間》曾獲得2018年茅盾文學獎,作家梁曉聲以自己的東北家庭記憶寫出了115萬字。故事從1969年開始講起,生活在東北吉春“光字片”的周家五口人面臨離別,父親是八級技術工要前往重慶支援“大三線”,大兒子周秉義要去兵團報到,二女兒周蓉為愛遠走貴州,留下小兒子周秉昆和母親在家留守。
一家五口分散天南海北,也就過年有時回到光字片團聚,一家人各自跌宕的悲喜都在時代的大開大閤中展開。
作為一個沒怎麼離開過江南地區的80後,東北是遙遠的,年代是遙遠的,在東北五十年的全景描繪下,既有全面恢弘的大廠改革,也有底層普通人的生活日常。這些普通人,近在眼前,他們有時代的弄潮兒,更多的是被時代傷害了的小人物。我買來了原著卻不敢打開——因為據説小説更加壓抑沉重,電視劇已經把故事的調性色彩調得温暖明亮了許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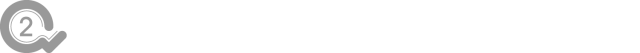
好故事來自於哪裏?
一個好故事,核心在於有魅力的人物。尤其是要搬上影視劇,角色的魅力更加重要。張愛玲、魯迅的小説為什麼很難演?**因為他們筆下的人物往往是被時代、社會壓榨掉了僅存的生命力,只能在充滿蛛網的命運角落裏暗自嘆息。**這樣的人物是很難上舞台的,只能在文字中細細體會。
在當下流量加持、爽劇甜寵盛行的一眾影視劇中,題材追求熱點話題感十足,場景道具日臻精美,情節也更密集緊湊,但人物卻越來越乾癟,性格的發展毫無邏輯可循。這樣的影視劇離“好故事”太遠了。
編劇中有一個概念,叫做“人物的弧光”——每一個故事都在展現人物一段成長曆程,他從懦弱變得勇敢,從自私變得無私,反過來也是一樣的,成長的變化就是人物的弧光。
《人世間》的人物塑造是我近年來看到的最好的一次,沒有一個人是臉譜化的,也沒有一個人是反派。尤其是周家三兄妹,分別代表了上、中、下三個階層的人物形象。
其中對主角周秉昆的命運講述最為豐滿,這個人物也傳遞了故事本身的價值觀——温暖的平凡。
周秉昆是家中最普通的留守者,沒有哥哥姐姐北大的光環,心裏有點小自卑,總想證明點什麼給父母看看。他膽子不大,卻對愛情勇敢執着;他為人熱心仗義,把朋友的事兒當自己的事兒;他歷經苦難是個“倒黴蛋”,每當生活好不容易有點起色,又馬上迎來了下一重危機。
在故事的結尾,他也沒有像流行爽劇那樣,迎來自己的成功逆襲。但這才是最接近生活的真相和底色,沒有逆風翻盤,沒有世俗的成功。每個人都是默默地和自己的日子相守。他靠着愛、真誠、良知和本色,一次次在粗暴的危機面前貼身肉搏。他代表了底層的小人物,傷痕累累,甚至一無所有,卻活得坦坦蕩蕩!這個人物是我最喜歡的。
劇中的哥哥周秉義、姐姐周蓉也都充滿魅力。很多人不喜歡周蓉,尤其是80後90後,説她很自私。但梁曉聲卻説,周蓉是他這部作品中最喜歡的人物了。作者和觀眾為什麼會產生這樣的偏差?
在我看來,周蓉是那個時代的“另類先鋒”。她50年代出生,那個年代的人大多像鄭娟一樣忍辱負重,文化程度比較低,習慣自我犧牲的。但周蓉卻是一個自我意識相當強烈的人,她敢愛敢恨,十九歲為了愛情從東北遠走西南,對自己所愛的,義無反顧。她不懂人情世故,沒幫她分到房子,就能把禮物要回來。這種“任性”“自我”,在那個時代具有超越的魅力。
但在今日80後90後獨生子女身上卻不少見了,對時代的超越消失了,“個性”成為了“共性”, “自我”也被理解成了“自私”。所以,在年輕觀眾那裏,忍辱負重的鄭娟,收穫大家一片喜愛;活出自我的周蓉卻成了被罵最慘的那一個。
大時代,小人物,大東北,小家庭。且不説上述主演,裏面每個配角也十分鮮活。真是應了那句行話:“沒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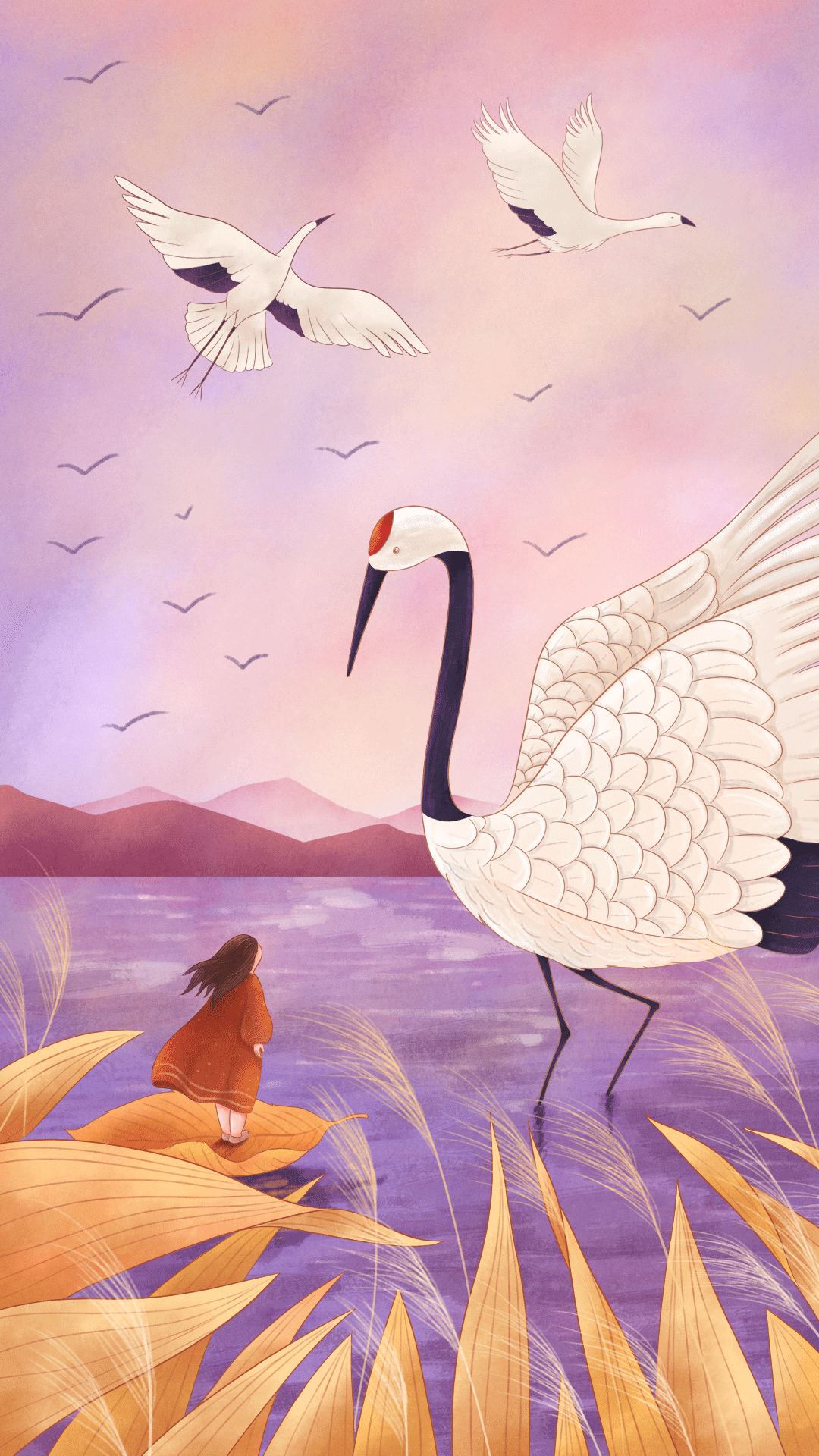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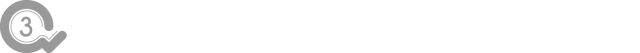
好故事的稀缺性
好故事是稀缺的,它會給人一種向善的能量。曾經,我們的好故事非常多。就像《我愛我家》《貧嘴張大民的幸福生活》《父母愛情》都是其中的經典。它們多是平民的視角,講述老百姓自己的生活,嬉笑怒罵、喜怒哀樂,引起我們極大的共鳴。
但現在的故事呢?人均中產、身居大平層、出入豪車、全身名牌、霸總豪門,卻掩蓋不了時代精神的疲弱。用編劇毛尖的話説:“影視劇就是全中國最封建的地方,按地位,財產分配顏值,按顏值分配道德和未來。”
她還説,“大錢勝小錢,有錢勝沒錢,正出壓庶出,正室壓側室。耍弄心機做壞事的,往往都是那些從底層爬上來的角色。”國產劇已經在消滅“窮人”、消滅“普通人”,偶爾來幾個“窮人”也是來壞富人們事兒的。
反之,能產生共情的好故事,擁有一種普世的情感。《人世間》從人人都想脱離的“光字片”開始,從最傳統的“家文化”擴大到了熟人社會的法則。這份共情源於兩點——一是關於國人對“住”的痛點,二是來自於熟人社會的温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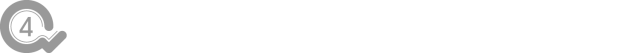
好故事的愛與痛
國人的居住痛點
《人世間》裏對“住”的問題,有着來自不同階層的描繪。省級幹部大院裏,是省長敞亮的洋樓別墅,知識分子蝸居在“筒子樓”裏,為了分得兩室一廳要打點送禮;最難的是“光字片”裏的老老少少、男男女女,他們一直在為居住發愁,一張炕睡全家人,每個人都想逃離“光字片”。
雖然周家在炕上的絮絮叨叨,温馨瑣碎感人,但更多的是像國慶家那樣,為了住房不停爭吵的。
可“住”何止是當年東北“光字片”的困境?十幾年前上海火爆的《蝸居》到最近上演的《心居》,都在講述人們在上海努力生存、奮鬥買房的故事。時至今日,《心居》已經沒有了《蝸居》對現實的批判精神,也沒有《人世間》對苦難的尊重、温情,只有市井裏弄、中產階級們的計較猜疑,人物懸浮、時代精神已經開始墜落蒼白。
“住”的痛點,何止是在劇中,正是長期以來人們居住條件的惡劣,才導致我們變成今日最愛買房子的民族。在很多人的早年,身體和生命並沒有被很好地照顧、尊重過。
二十年前,蘇州的古城區也有大片棚户區,廚房衞生間都是自己搭建的“違章建築”。在當年為保存蘇州古城的特有風貌,數十萬居民一直生活在老城區內,日常生活還離不開“三桶一爐”(馬桶、浴桶、吊桶和煤爐)。每天清晨,居民們在路旁“聲形俱備”地洗刷着上萬只馬桶,成為當時古城內一條苦澀的“風景線”。在當時能讓老百姓扔掉“馬桶”都是一件了不起的工程啊。蘇州從1985年開始就陸陸續續在消滅“馬桶”一直到2010年左右,總共消滅馬桶十萬餘隻。這樣的情形,上海也是一樣的。上海的住房問題要比蘇州更加嚴重。
因為住房難,那個年代裏人們的生活方式是比較壓抑扭曲的,有些人一到晚上會少喝水,因為怕晚上上廁所太麻煩;有些學生寧可跑到馬路邊路燈下寫作業,因為家裏的樓板薄,總是傳來鄰居打麻將的聲音。在逼仄的空間下,人們習慣性地壓縮自己的需求。文明,是一種意識也是一種生活,這是在温飽富裕以後,人們才會去思考、去追求擁有的,就像抽水馬桶並非與生俱來。
熟人社會的温情
住的問題固然壓榨了我們的生存空間,“熟人社會”卻得以構建,展示出它的温情。劇中的“光字片”依託熟人社會的法則,從獨立的小家延伸到“鄰居”“發小”“朋友”這樣的小圈子社會,只是“熟人社會”的生活方式在城市化的洪流下逐漸瓦解了。
八九十年代江南地區也有不少類似的棚户區。寒山寺邊曾經有一大片低矮平房,我有個同學就曾經住在那裏,打個羽毛球都會飛到寺廟裏。隨後大叫一聲,寺廟裏的小和尚就會把羽毛球扔出來。平頭百姓、佛門僧侶一牆之隔,釋俗混居,和睦相處,想想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
不僅寒山寺,蘇州除了幾大名園外,很多不知名的小園林都住着十幾户甚至幾十户人家。電線密密麻麻、太湖石假山上曬被子、亭台裏堆雜物,誰家大人有事外出了,孩子就自然上鄰居家蹭飯。
“熟人社會”還有一種代表,就是“以廠為家”的文化。那時的一座座國企大廠配備有自己的託兒所、學校、書店、電影院乃至醫院。一座大廠就是一個小社會,一座小城市。人們的流動性比較低,集體的歸屬感很強烈。和今天上班就是工號、工牌的企業文化完全不同。
一邊是住房的緊張,一邊是熟人社會的温情,在物質稀缺、居住惡劣的年代裏,人與人之間聯繫也更加緊密,更注重幫襯扶持。
“熟人社會”作為80後的我多少有一點經歷。它有不好的方面,比如不夠自由、缺乏機會,扼制人們的創造力。但它也有好的方面——温情與歸屬感,人與人之間的情誼、理解和守望相助。在天災人禍面前個人、小家庭抵抗風險的能力其實是很低的。有一個強大的熟人社會,能夠更加高效、團結地抵禦風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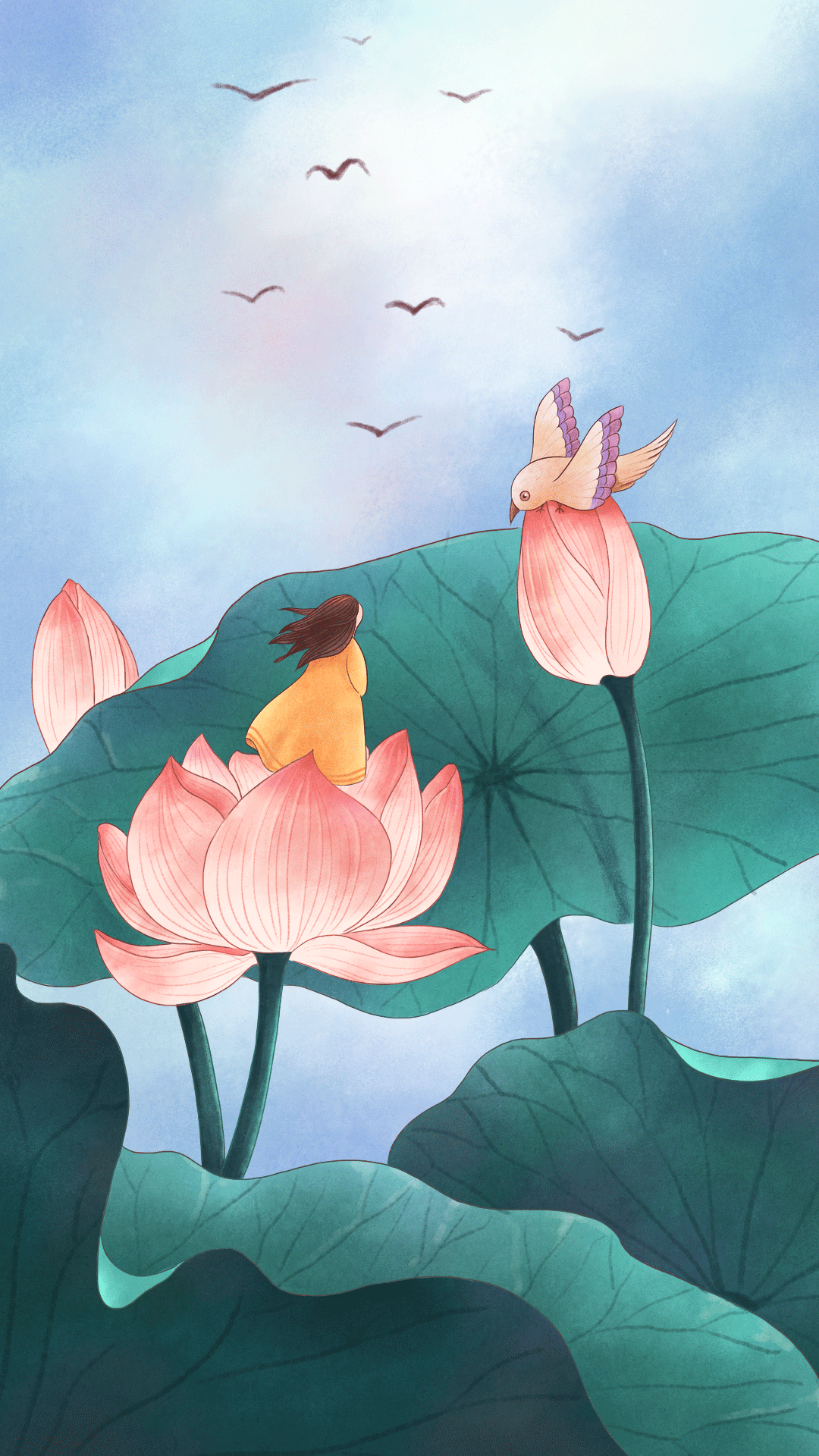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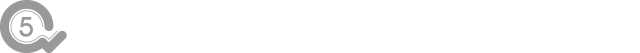
文學從“無用”到“大用”
近些年《人世間》《大江大河》《山海情》這些電視劇都收穫了很好的收視率和口碑。這些電視劇都是從文學作品改編而來的,我們一直對現實主義題材十分重視。這些劇都很熱,但原著好像又沒那麼暢銷。
我曾經和“讀客文化”的創始人華總聊天,我有個問題——“經典文學有沒有迴歸到我們的生活中?”
問這個問題是因為當時莫言的《生死疲勞》一個月的印刷量達到48萬冊,雄踞各大暢銷書排行榜前列。但華總認為《生死疲勞》的成功,是源於銷售網絡的成功,並不代表閲讀風向的轉變。
此後我也和一些出版人聊過,大家的共識是文學類圖書還是比較難賣的。經典文學作品還擁有固定的粉絲羣,通俗文學只能等待影視化的改編。
文學書籍難賣不奇怪,因為文學是一項最“無用”的專業了。它沒有實際的功能,只是在創造一個個幻想的帝國、精神的花園。它甚至談不上是一項“專業”。但時至今日,在貧富差距日益拉大、階層認知形成撕裂的當下,文學或許是“讓我們成為我們”的良方。
就像俄烏戰爭、新冠疫情等等天災人禍前,多的是矛盾爭論、站隊拉架甚至冷嘲熱諷。媒體流量在加重撕扯、消費災害,好的文學則尊重差距、敬畏苦難。
《人類簡史》裏寫道:“人類幾乎從出生到死亡都被種種虛構的故事和概念圍繞,讓他們以特定的方式思考,以特定的標準行事。無論是現代國家、中世紀的教堂、古老的城市,或者古老的部落,任何大規模人類合作的根基,都在於某種只存在於集體想象中的虛構故事。”
就像《人世間》傳遞着時代的共情,江南人一樣能尊重理解東北生活。是好的故事,好的文學,喚醒我們心底的良知情愫,打破偏見,彌合撕裂,消除人與人的隔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