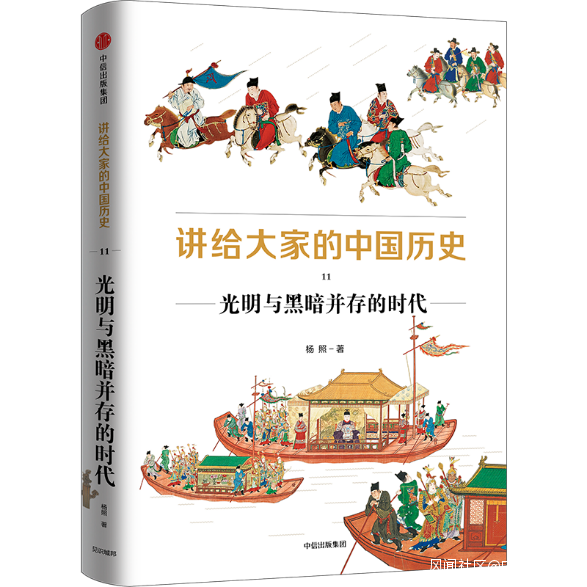明朝人是怎麼通過衣服來炫富的_風聞
中信读书会-中信读书会-2022-04-21 11:23
明朝人是怎麼通過衣服來炫富的
文:楊照
來源:《講給大家的中國歷史11:光明與黑暗並存的時代》
整個明朝,史料上不斷出現討論“逾制”的問題,到了晚明,更提升為對於奢侈現象的種種形容與批判。“逾制”與奢侈,是這種虛榮滿足必然帶來的現象,其影響層面非常廣,對於明朝人如何穿、如何吃,乃至如何蓋房子、如何行動,都有着關鍵的作用。一言以蔽之,強大的炫耀、表演性的消費行為,成為近世後期的主要生活因素。
京劇中有一齣戲叫《鳳還巢》,那是很有名的丑角戲。戲中兩個角色,程雪雁和朱千歲,都是由丑角扮演的。戲中有一段,朱千歲應邀去程浦老先生的家裏。他帶着兩個家丁,一進去,先説:“來呀,脱去我的路衣,換上我的壽衣,好與老先生拜壽。”家丁幫他換了,他才向程老先生説了祝壽的話,被請到裏面吃酒,朱千歲又説:“來呀!脱去我的壽衣,換上我的便服,好與老先生飲酒。”又説了幾句話,朱千歲起身:“老先生,天不早啦,我跟您告辭啦。來呀!換上我的路衣,也好趕路。”
另外一段,兩個家丁幫他換衣,換好了他一看,勃然大怒:“怎麼還是我來的時候穿的那件兒呀?”家丁説:“就是那件兒!”朱千歲就罵:“別的衣裳你沒帶來?”“我的衣裳有的是,怎不多帶出兩件來?沒用的東西,下回記住了!”
這兩段強調了朱千歲的誇張奢侈,而在劇情的設計上,換衣過程中程夫人誤將朱千歲認為是穆居易,因而決定將程雪雁嫁給他,這是其中一對陰差陽錯配對的來由。而程夫人如何做出這決定?就是看他的衣着,被他頻頻換衣服這件事打動了,認定這樣的人值得嫁。
再回頭看《鳳還巢》開場戲,程浦、朱千歲兩人到郊外踏青,書生穆居易也在。但因為身上衣服太寒磣了,不敢去和程浦相認,是朱千歲叫了他,過來後問起,才發現他是程浦老友的兒子。
戲的發展就架構在衣服上,故事明白標舉了是以明朝為背景,主角名叫朱千歲,這顯然是明朝的皇族子弟。這樣的聯結不是偶然,這出戏中顯現了明朝的社會現象—對於外在衣裝的重視,以衣服來決定人的地位、身份,甚至以衣服來判斷人的價值。
**01“**衣着逾制”與衣着顏色、圖紋等禁令
明代最突出的社會現象之一,是“衣着逾制”。首先這“制”源於朱元璋的統治信念,他希望在國家體制中給每個人一個固定的位子,大家都乖乖地待在各自社會空間的原地上,安靜過着如同“小國寡民……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的生活。所以他的統治一直管到人民的生活細節,有很多相關的“制”。
據《明史·輿服志三》記載,1458年有一道禁令,規定人民穿衣服不得使用幾種顏色。第一是“薑黃”,那是淺黃色;還有“柳黃”,柳葉剛冒出來的顏色,接近黃綠色。最大的禁忌當然是皇帝用的“明黃”,即鮮黃色。另外“玄黃紫”也不能用。
此外還規定衣服上不能有哪些花紋。蟒、龍不能用,飛魚、鬥牛、大鵬、獅子不能用。四寶相花,四個圖案連續盤在一起的,不能用。大雲紋,即大塊雲狀圖案,也不能用。
這道禁令告訴我們,到這個時候,明朝的服飾已經改變了。當初朱元璋的理想是用衣服顯示社會身份,你是什麼樣的人就穿表現你身份的那種衣服。而且不管什麼身份穿的,基本上都以功能為主要考量,儘量簡樸。但這樣的原則沒能維持很久,到15世紀中葉已經瀕臨瓦解了,才會在英宗時又頒佈這道禁令。
使得朱元璋的信念實行不下去的一股力量,正來自其信念內部的弔詭。衣服要清楚顯現身份,別人可以從你的衣服上立即看出你是什麼社會階級的人,這種規定反而提供了強大的“衣着逾制”誘因。只要換穿上不一樣的衣服,在別人眼中的地位就改變了,那麼方便就可以提升地位的方法,幹嗎不用啊?
到必須以禁令明白標舉哪幾種顏色、哪幾種花紋不準用,表示連“明黃”和“蟒龍紋”這種明確和皇家有關的服制元素,都有人敢亂用了。
不過1458年的禁令,主要處理的還是衣裝上的社會標記問題,然而也差不多在這時候,另外一方面的發展變得愈來愈嚴重、愈來愈誇張,那就是在衣服上奢侈浪費,產生了許多和原有皇族、官職象徵無關的新奢靡表現方式。
從1370年代開始,朝廷就多次發出對“衣着逾制”的警告,最後一次的相關禁令,出現在1541年。這次的禁令則是特別針對“雲巾”“雲履”。這裏的“雲”指的不是一個世紀前的“大雲紋”了,而是一種特別的材質。“雲”指的是“雲縑”,這道禁令管的,不是外表花紋,而是某些最為貴重的特殊材質。
“雲縑”是一種絲織品,織得特別鬆軟,感覺上比一般的絲還要更輕。這當然牽涉到高度複雜的織工技術,可以做出特殊的皺紋,會有波浪的效果。這麼貴重的布料,卻有人用來做“雲巾”“雲履”,那明顯是誇示。
這時期最貴重的衣服材質除了“雲縑”之外,還有“吳綢”,即蘇州的絲綢;“宋錦”,這是帶繡花的衣料;“駝褐”,駱駝毛織成的,是最好的毛料。
禁止用“雲巾”“雲履”,那就不是在管“逾制”了,而是針對奢侈風氣。將這種大家都看得出來很貴重的材質用在做佩巾,甚至做鞋上,這明顯的用意與效果就是炫富。到這時候,炫富的情況已經超越“逾制”了,想要自我標榜、得到社會地位的人,不再是去穿不屬於其身份的衣服,因為這種做法太普遍了,大家都這麼做,以至於身份和衣着相連的“制”已經喪失意義了。所以要凸顯身份就要穿別人穿不起的衣服,或者像《鳳還巢》戲中朱千歲那樣,以別人無法負擔的方式來穿衣服。
02****從馬尾裙到蘇樣,衣裝的“創起為奇”
明憲宗成化年間,1470年代,在北京出現了“馬尾裙”的流行風潮。“馬尾裙”以馬尾毛織成,這種裙子材質較硬,就像撐開的傘,據説是從朝鮮傳進來的。一時之間很多人都穿,連大學士都有人跟着趕流行。
因為是新鮮的外來樣式,所以身份高的人穿、身份低的人也穿;有錢人穿,沒錢人也穿。大學士萬安還每天都穿,本來是冬天的服裝,萬安卻連夏天都不願換下來。大家都要穿,馬匹當然就倒黴了,當時北京附近到處都是尾巴光禿禿、毛被剃光拔光了的馬。
1458年下的服色禁令,由一位叫周洪謨的大臣負責監管,但到馬尾裙流行時,就連周洪謨身上都穿了兩層“馬尾裙”,形成了莫大的諷刺。周洪謨正代表了歷史的變化,一個曾經主管糾察“衣着逾制”的官員,自己抵擋不了誘惑,公開將流行的新服飾穿在身上。“衣着逾制”這個觀念本身落伍了,新時代的穿着風格不再是去模仿有錢有地位的人穿什麼,而是創造、趨附新的流行。穿着一眼看去就不一樣,因而會讓人羨慕的衣裝,成為風氣。
“衣着逾制”的觀念被拋棄了,衣裝外表的問題變得更加嚴重。衣服變得和錢、和財富緊密聯結,甚至説穿什麼衣服主要就是為了彰顯財富都不為過。新興的服飾風氣是“始以創起為奇,後以過前為麗”,好衣服的定義是新發明的,之前沒有人穿過的,而且是在某個點上,即某些方面明顯超越以前大家看過、穿習慣了的。
16世紀開始,明代服裝的特色便是追求變化。例如簡單的“方巾”,朱元璋開國時訂定了“四方平定巾”作為讀書人的身份表徵。第一等社會地位的人戴帽子,其次就是讀書人戴“方巾”。但到了這時候,“方巾”又分“漢巾”“晉巾”“唐巾”,還有“諸葛巾”“純陽巾”“東坡巾”等等。因為和讀書人有關,所以命名上就標舉歷史來源,宣稱是不同朝代留下來的,或是和名人、道教扯上關係。但真正的意義是形狀、花色都不一樣,可以有所選擇,尤其會傾向於選擇和別人不一樣的。
晚明張岱的作品中就記錄了紡織業中心蘇州不斷推出新的布樣,浙江人看到了便急着模仿、追趕。而一旦浙江人穿了,蘇州人就嫌棄不要了,再換不同的新樣式。張岱諷刺浙江人如此愚蠢,一直被蘇州人牽着鼻子走。張岱的態度很明顯表示了,不是要浙江人不要變了,而是應該自己去變、去創新,不要一直跟在蘇州後面學人家的。
明代晚期的史料中,常常出現一句慣用語“一時之妍”,多半用來描述服裝。這是之前沒有的語詞,主要用來凸顯之前的流行。“一時之妍”,表示當時大家都覺得漂亮,人人趨之若鶩,然而那“一時”過去了,現在回頭看,奇怪,有什麼好看的啊?彼一時此一時,時間不同,流行改變了,美或不美的看法也跟着變了。此一時如果還穿着彼一時流行的衣服,那麼非但不會被認為漂亮,甚至還會被恥笑。
依照張岱的回憶,他年輕時蘇州流行風潮的“賞味期”大致10年左右,每10年就會有一波大變化。等到他進入中年,變化的速度加快為每兩三年就換一次了。顯然明代後期的服裝,符合我們今天所説的fashion性質,那就是流行,有着明確、強悍的流行遞換操作,也有全社會介入、參與的趕流行,生怕跟不上流行的集體心態。
蘇州是流行的中心。有流行的發動者,也有流行的跟隨者。而特別的是,士人因為仍然在社會上擁有醒目的示範作用,可以説積極參與了流行的發動與決定。
浙江人李樂留下了以下有趣的詩句:“昨日到城郭,歸來淚滿襟。遍身女衣者,盡是讀書人。”進城一趟,回來哭了,因為在城裏一看,外表上是女性的,穿女裝的,竟然都是士人!
為什麼説士人穿女裝?因為明代男裝、女裝有不同的顏色。男裝本來主要是青色,如果不是以青色為底,而是比較明亮、鮮豔的,傳統上被認為是小孩和女人才適合穿的。到了明朝後期,城裏街道上,沒錢沒身份的人才穿青衣。其他稍有財資稍有辦法的人,都放棄青衣換穿更鮮明的顏色(“盡為婦人紅紫之服”),從傳統保守的眼光看去,就像是男人在衣裝上都變身為女性了!
歸有光對於明朝中葉的風氣有一番整理,得到的結論是:世俗奢侈的習慣是從士人身上開始的,然後感染到城市,城市流行了,再往外擴展到城郊。
為什麼從士人開始?因為士人和商人之間的距離不斷縮減,使得士人的文化帶有愈來愈強烈的商業性質。商人有奢侈炫富的動機,那是使得他們得以增加社會能見度,藉此提高社會地位與社會正當性的手段。而商人在社會地位改變上的主要目標,也就是追趕上士人。
商人的行為給了士人一種集體壓力,刺激催生了一種集體自覺,即必須維持和商人間的一定距離,在外表上和商人維持可以辨識的區隔。在近世社會中,沒有了封閉、固定的身份制,不能去規定誰是豪族、誰是寒門,於是外在的表徵很容易模仿,也必然會招惹來模仿。尤其商人有特別動機,又有充分資源去模仿士人的穿着外貌以自抬身價。如此就逼得士人必須不斷“創起為奇”,放棄已經被其他人模仿,失去階級標示意義的服裝,改換出新的一套來。
士人仍然握有訂定社會品位的優先權力,但商人有可以不斷變換追摹的資源與能力。於是一個換、一個學,構成了明代的服裝流行動力。這種條件下,出現了特別的讀書商人,將他們的士人本事拿到市場上去換得金錢。唐寅的畫、文徵明的字,在當時都帶有商品的性質,但又有高於商品的地位。他們的畫和字不再是單純在文人間相贈流傳,而是特別賣給有錢人,作為有錢人的品位象徵。
這些參與市場的士人就有了新的自覺,必須維持自己品位上的領先地位,他們一方面代表文人,一方面積極和商人周旋,併為商人提供有品位的商品與品位指導,和以前的文人很不一樣了。
明末出現一種特殊的衣着服飾,稱為“蘇樣”,“蘇”指的是蘇州。蘇州既有錢,又是紡織業中心,而且聚居了大量的文人,是文人文化的制高點。“蘇樣”最特別之處,在於表面上沒有絢麗的色彩,也沒有繁華的紋飾,講究的是極其細膩的布料織法,以及巧手精工的剪裁。這是進一步為了擺脱模仿而產生的低調奢華風格。
“蘇樣”不只是出現在衣服上,甚至可以説是明末文人精神與生活意趣的總體風格。由外而內,要創造一種沒有那麼多表面可以抄襲模仿的元素,卻內藴涵藏必須有一定文化程度才能看得出來,要更高的文化修持才能參與的藝術化生活。
03****社會性衣裝的展示場,舉國若狂的炫耀熱
近世後期在商業領域創造了大量財富,卻除了消費之外沒有太多其他出路,消費便因而有了愈來愈高的社會標誌功能。社會標誌需要在公共空間展現,這進一步在近世後期提升了公共空間的重要性。
明代最特別的就是“社會性衣裝”格外發達。出門在外穿的衣服,和家裏穿的愈來愈不一樣。
如果你出門要去的地方,人家不會憑藉你的衣着估計、評價你是什麼人,你有幾分斤兩,那麼你不會花那麼多時間、力氣去準備衣服,不會那麼在意自己穿了什麼。
另外,一個星期出門一次,和每天都要出門相比,對於衣裝的講究當然不同。前一種狀況,不需要特別準備什麼,後一種就必須有好幾套輪流穿的衣服,必須考慮不能每次出門都穿同一套。
接下來,不同的公共空間有其各自的特性,要求不同的穿衣服方式。去衙門裏辦事和去勾欄看戲,穿不一樣的衣服;乃至於要到衙門所在一帶的地方,和到勾欄所在一帶地方,都會需要換上不同的衣服。
明代出現了愈來愈多作為展示場,讓人去展示身份的空間。其中很重要的,是有了讓女性可以公開參與的空間。歷史上,上元節為什麼那麼重要?因為唐朝長安城內每天晚上里門、坊門都要關閉,完全沒有活動,唯一的例外是上元節三天不閉門,夜晚公共空間裏擠滿了看燈的仕女們,蔚為稀有的奇觀。
明代之後,這種仕女如雲的場合變多了,產生了新的奇觀。據範濂《雲間據目鈔》的記錄,在松江的迎神賽會上,各鎮都租了兩三百匹馬,在路上大遊行。馬上坐着扮裝的戲中人物,他們有的穿着“鮮明蟒衣靴革”,完全不顧什麼“衣着逾制”了,而且“幞頭紗帽滿綴金珠翠花”,首飾華麗。
若是狀元遊街,身上戴着三條“珠鞭”,價值超過“百金”;旁邊圍了妓女三四十人,扮成《寡婦徵西》《昭君出塞》等劇中角色。還有花車上“彩亭旗鼓兵器,種種精奇,不能悉述”。為了不受天氣影響掃興,還將街道橋樑都用布幔遮起來,如此當然吸引了“郡中士庶,爭挈家往觀”。那種熱鬧情況,是“遊船馬船,擁塞河道。正所謂舉國若狂也”。遊行輪流在各鎮進行,每一鎮四五天,每天都需要很高的開銷。
描述完了這樣的奇觀,範濂更補上背景與後續:“日費千金,且當歷年饑饉。而爭舉孟浪不經,皆予所不解也。壬辰,按院甘公嚴革,識者快之。”這可不是什麼豐年,甚至不是一般承平時節,而是經歷了一段饑荒,卻都無法阻止松江地區如此瘋狂地花費炫耀。因為情況太誇張了,後來甚至驚動了按察使正式立案調查懲處,有識之士才感到安心欣慰。
晚明李日華《味水軒日記》中記載浙江秀水神會,情況也很類似:“秀水濮院鎮醵金為神會,結綴羅綺,攢簇珠翠,為抬閣數十座,閣上率用民間娟秀幼稚裝扮故事人物,備極巧麗,迎於市中。遠近士女走集,一國若狂。”最醒目的是各式各樣服裝,以及服裝上掛滿的珠翠飾物,花車上有漂亮女性扮演故事人物。所製造出的效果,兩位作者不約而同地皆用“一國若狂”來形容。
那就是羣眾的集體狂熱,顯然這種廟會很接近歐洲中世紀的“嘉年華狂歡”,以財富炫耀式消費為人民提供一種暫時擺脱現實、進入狂喜狀態的刺激。
本文整理自《講給大家的中國歷史》 2022.3 中信出版集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