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正|新文科的實踐導向與平民性_風聞
探索与争鸣-《探索与争鸣》杂志官方账号-2022-04-24 21:55
王正|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哲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副編審
本文刊於《探索與爭鳴》2022年第3期
非經註明,文中圖片均來自網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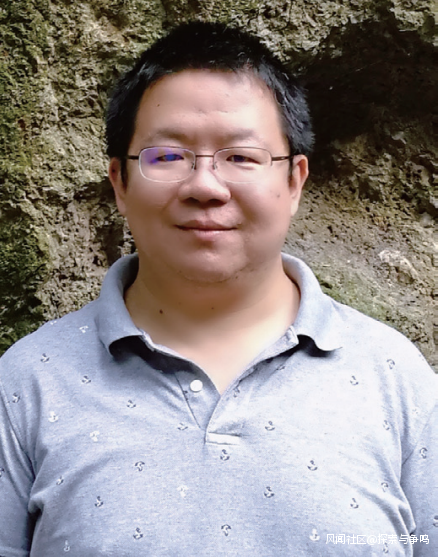
王正副編審
近年來,新文科的建設成為一大學術熱點。然而細繹諸種關於新文科建設的討論,可以發現兩個根本問題:一是相關討論過於圍繞新技術的發展而展開,如很多對跨界性文科發展的言説,事實上有將文科技術化、智能化之嫌;二是很多討論雖然試圖超越啓蒙話語等西式表達,但仍舊在問題意識、思維邏輯上被現代性的西方思想所框限,無法真正構建中國自己的哲學社會科學體系。當然,新文科建設中之所以出現這兩個問題是有原因的:新技術是當前時代面臨的重要問題,且事關人類未來,不由不令學者普遍關注;西方話語體系乃是整個現代學術體系建立的源頭,學者們的話語乃至思維方式大多建基於其上,因此很難短期內克服之。
但是,如果我們的新文科建設不能擺脱被新技術所引領的現有態勢,而建構起自身的在先性、前導性、指引性,則文科不僅將無以為新,且只能日益成為技術的附庸與後置的詮釋者;如果我們的新文科始終只能在西方話語體系下進行言説與表達,則我們將根本無法面對與理解中國本身,也就無法構建自身的哲學社會科學體系,更無法為世界學術思想的發展貢獻中國資源。
一
文科在很多國家和地區近年來都呈現萎縮的態勢,我們的新文科建設能否克服這一頹勢是值得思考的。另外,當我們進行新文科建設和中國哲學社會科學體系建設的時候,我們如何恰當對待西方的思想資源,又如何真正形成自身的話語體系,這兩者之間的張力是極難拿捏的。而筆者通過近年在山東壽光等地的調研發現:我們的新文科建設不能遠離實踐導向,新文科的實踐不僅是技術的,更應是生活的;新文科建設的關鍵點在於人文精神的重構或者形成新的人文精神,而這種人文精神不能僅是象牙塔式的,更需要是平民式的。
既往對新文科實踐導向的討論,過於強調高、新、精、尖的面向,卻忽視了日常生活中的實踐問題。人們總是容易被新奇的東西所吸引,卻常忽視身邊最普遍存在的問題。然而孔子提醒我們,“近取譬”乃是成就德行、學問的重要方法。筆者曾嘗試通過閲讀相關論著來理解“壽光模式”這一縣域發展的成功案例,於是發現當學者們運用各種經濟理論、社會理論來探討“壽光模式”的時候,總是將技術發展、科技更新換代作為第一位的要素。當然,科技進步在壽光縣域經濟的成功發展中乃是重要因素,但是這一解釋模式有兩個核心問題無法解説:一是令壽光農業發展起來的蔬菜大棚種植技術並非源於壽光,而是源於東北,但東北未能成為這項新技術的最大受益地;二是壽光的蔬菜種植技術早就已經向全國推廣,但是其他地方未能形成“壽光模式”的發展樣態。

山東省壽光市現代農業高新技術試驗示範基地
對這兩個問題的解釋,是一般的經濟學、社會學理論無法給出的,而在筆者看來,關於這兩個問題的答案正在於常被人們忽略的自身生活於其中而不自覺的文化因素:壽光自古屬於齊地,齊文化的開放性使得此地對技術有開放、容納的心態,如寫作了《齊民要術》的賈思勰正是壽光人,壽光本地一直有接納、學習、創新科技的文化土壤;山東稱齊魯大地,質樸的魯文化對山東人也影響很大,當然這種影響的負面性常被人戲謔為“含魯量”,但這種文化的正面影響不可低估,它潛移默化地影響着壽光人在生活中認真踏實、在工作上勤勉肯幹,而這種勤奮的態度與開放的心態之結合,正是“壽光模式”形成的重要原因。然而在目前對“壽光模式”的研究中,文化影響這種日常性因素的作用常常不被考慮在內,這其實是研究上的一個重大缺失。可見,新文科的實踐導向不能僅關注新技術方面的問題,因為技術發展並不是人的生活的全部。人本身及其生活的豐富性,才應當是新文科之所以為新的關鍵所在。而這種新,既應當超越西方啓蒙話語的人類中心主義,又需要擺脱現代性、後現代性造成的人日益成為機器或技術性之人的陷阱,從而能為活生生的生活中的人給出價值觀念、意義詮釋、信仰構建。否則如果新文科的實踐面向只針對新技術而言的話,則我們既會讓新文科死於新技術之下,也會無法面對同樣宏大和重要的問題:對中國之所以為中國、中國之新發展給出全面的解釋,進而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體系。
二
正是在實踐導向的視野下,新文科的內核——新人文主義的建設,不能僅僅是象牙塔式的,而必須兼顧平民的生活。新文科的建設之所以被普遍關注,在於人們意識到淵源於啓蒙運動的近幾百年的文科建設出現了問題。這一問題的最重要表象就是在歐美日等國家和地區出現的人文學科的日漸萎縮,這和過去幾百年間人文學科的繁榮發展和多學科並進產生了鮮明對比。
這種情況的出現,一方面是新技術的迅猛發展既不斷佔領原本屬於人文學科的領域,又使得人文學科只能成為新技術的後置詮釋者;另一方面是經歷了現代建構和後現代解構後,人文學科似乎已經失去了創新的能力,它既不能引領世俗時代,又不能解答時代之問。由此,一些學者發出了“文科之死”的哀嘆。但人文學科真的就必然走向沒落麼?其實這正是人文學科的學者本身失去了創造力的體現。所謂“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人文學科的當代衰落當然受新技術興起、研究範式框限等外在因素的影響,但更多應當由人文學者自身來承擔責任。
當代人文學者似乎在為自己構築三個牢不可破的鐵籠。一是現代性話語體系和學術體系的鐵籠。我們已經完全習慣於以啓蒙運動以來的各種話語體系和思考模式來進行研究,以至於當我們嘗試擺脱的時候,竟然根本無法用其他話語來進行表達。二是理性、科學性的思維方式的鐵籠。理性的權威乃是現代文科建立的基礎,所有現代文科的繁榮都與對理性的崇尚密不可分;而理性研究的追求則是為文科建立如科學技術般的確定性——人文學科的科學性,這同樣是現代文科蓬勃發展的重要原因。但是當理性、科學性的思維發展到極致的時候,則和人文學科的初衷形成了背反——它不再關注活生生的人本身,而是將人窄化為純粹理性、客觀科學性的存在。三是人文學科的象牙塔化鐵籠。儘管在當今社會,民眾的識字率和受教育程度日益提高,但是一方面,數百年人文學科發展的積累已經使得其研究變得十分精緻和細化,普通人很難進入其前沿研究中,似乎只能接受普及性的成果;另一方面,新媒體技術的更新換代與自媒體前所未有的巨大傳播力,已經使得普通民眾幾乎不再借助一手的經典文獻去理解人文學科的古典力量與現代價值,而只能藉助二手甚至三四手的傳播媒介來獲得關於人文學科的碎片化的認知。這既使得民眾對象牙塔中的人文學科有很強的疏離感,也使得人文學科學者本身日漸遠離民眾,無法從鮮活的生活中感受到人文學科到底意義何在,以及可能的未來何在。
這三重鐵籠會使得當代人文學者既失去了思維和話語上創新的能力,又無從與鮮活的現實建立起真正的勾連,這也使得新文科的建設其實面臨巨大的困難。而要想解決這一困難,需要人文學者在根本上進行一場思想變革,即從啓蒙運動以來的人文主義走向一種新的人文主義。這種新的人文主義首先是以啓蒙反思為基礎的,它對工具理性、科學主義等有着強烈的警惕,從而努力走出人類中心主義,以更好地面對當下和未來的人類生活;其次,新人文主義努力超越西方話語體系和思維模式,以開放的心態面對各種文化、文明資源,嘗試形成一種“第二軸心時代”式的多元現代性的文明;最後卻是最重要的,新人文主義不滿現代人文主義對人的狹窄化理解,而努力從更豐富的視角(如天、地、羣、己及身、心、靈、神)來理解活生生的人。杜維明、湯一介、查爾斯·泰勒(Charles Taylor)、雷蒙·潘尼卡(Raymond Panikkar)、埃沃特·考辛斯(Ewert Cousins)等中外學者在這方面貢獻了很多有意義的思考。

正如現代人文學科的勃興與啓蒙運動以來的人文主義息息相關,新文科的建設也迫切需要新人文主義的興起,只有以更新了的人文主義為內核,我們所期待的新文科建設才能真正完成。這種新人文主義如前所述,其最根本的內容是對活生生的人的理解,這提示我們,新人文主義不能遺忘無數普通民眾,它只有能夠面對並理解普通民眾的鮮活生活,才可能真正呈現出新的意義與價值。
三
當我們的視角由象牙塔轉向普通民眾後,我們可以發現新文科建設的豐富空間。其實,普通民眾對文科知識及其背後的觀念、意識、價值的需要是超乎學界目前所提供的知識供給的。賀麟曾指出,“哲學的知識或思想,不是空疏虛幻的玄想,不是太平盛世的點綴,不是博取科第的工具,不是個人智巧的賣弄,而是應付並調整個人以及民族生活上、文化上、精神上的危機和矛盾的利器”。從事人文科學研究,離不開現實的生活與當下的實踐。哲學研究的日益專業化、碎片化導致了一些堅硬壁壘的產生,如中國哲學研究中似乎存有一種 “太哲學”了的傾向,即過於疏離現實實踐與當下問題,這將導致我們的研究成為喪失了問題意識的無本之木、無源之水,最終流於空洞虛幻。據筆者在壽光及周邊縣域進行的鄉村文化尤其是鄉村儒學建設情況的調研發現,無論是住在縣域中心的人們,還是居住在縣域邊緣的人們,他們都對文化有很深的需求,而且這種需求不僅是面向文化的知識,更是面向知識背後所凝聚的文化意識、生活方式、價值體系等。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各種鄉村文化,尤其是鄉村儒學建設在壽光及周邊縣域正在逐步展開,人們在追求美好生活時有了心靈上的方向感與安定感。
這提示人文學科學者,新文科的建設及新人文精神的構建之重要方向在於要能為民眾的生活賦予人文意義與提供建設性的良好生活形式,否則將無以生成自身的學科價值與普遍化意義。應當説,這種人文學科與人文精神的平民化轉向,一方面是對近代以來世俗化傾向的恰當接受與延續,另一方面又努力改變世俗即庸俗的傾向。即新文科的平民化既肯定普通民眾對人文學科的追求與對新人文精神的接納,又努力從普通民眾的鮮活生活中探索人之所以為人的各種豐富性,以及平凡生活中所藴含的超越日常與當下的面向未來與永恆的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