項目停錄、演出泡湯,上海文娛人經歷了一個“魔幻”春天_風聞
娱刺儿-娱刺儿官方账号-娱刺儿是刺猬公社旗下文娱报道账号2022-04-25 08: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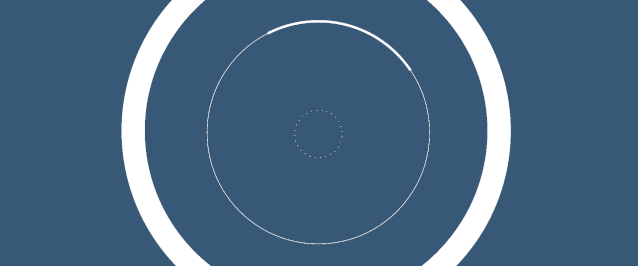
直三 丸子 怡晴 | 文 Tim | 編輯
4月,是上海春暖花開的季節。
往年,在這個票房最好的黃金週期,戲劇製作人佟孜會緊鑼密鼓地準備五月“靜安戲劇谷”戲劇節中,參演劇目的前期宣傳;綜藝導演小小會往返於繁華的外灘和郊區的錄影棚,開始緊鑼密鼓地錄製;劇集製片人張景會輾轉於全國各地,見客户、看場地、盯拍攝進度;紀錄片導演靳導會加快拍攝進度,儘早讓片子上線;而影院經理李成梁會忙着給五一檔影片排片。
而這一切,在2022年都按下了暫停鍵。
自從上海多地區進入疫情封控以來,線下演出已經全面停止,很多外地來的演員至今仍被困在酒店;綜藝、劇集、紀錄片拍攝也全面中斷,上線日期被無限推遲;而影院更是幾乎顆粒無收。
在這個春天,上海的文娛從業者們在未知的前景中困惑、掙扎、迷茫。但他們仍沒有放棄,即使內心只剩下一絲希望的火苗,他們仍在努力地保持熱愛。

拿什麼拯救你,線下演出?
在受到疫情衝擊的文娛產業中,首當其衝的便是線下演出。
2021年下半年,為了在戲劇土壤更好的上海施展拳腳,戲劇製作人佟孜向公司申請,來到上海做市場開拓,提升上海站巡演的票房以及維護媒介關係。
2022年大年初七,佟孜便開始籌備3月份巡演的大戲。排練了半個月後,2月24日,排練廳的大廈突然出了一例確診,而劇組一位演員恰好和確診病例搭乘了同一部電梯,需要集中隔離。這位演員,也因此失去了演出機會。
佟孜記得,這件事成了演員的心病,他總是和自己賭氣説:“為什麼就是那個時間我出現在那架電梯上,我為什麼不能早一點或者晚一點下樓?”

圖源:上海大劇院微信公眾號截圖
此時,普陀已經開始浮現出零星病例。但基於普陀離排練廳很遠,上海之前的精準防控也很到位,佟孜並沒有把這件事放在心上,劇團依舊在正常排練。
直到3月9日,劇組裏又一位演員成了密接,導致整個劇組在酒店接受了48小時的健康監測。禍不單行,幾天之後,佟孜所住的小區由於出現密接突然被封,而她也收到了3月上海站演出取消的消息。
好不容易捱到小區核酸全陰解封,佟孜第一時間給劇組發消息,説自己終於可以出來一起排練了。結果,劇組告訴她,就在她被封的這段時間,劇組緊急做了一個決定——去上海周邊的另外一座城市排練。
聽到這個消息,佟孜非常震驚。“因為當時上海的情況還沒有那麼緊急,我在想發生什麼事你們這麼着急要撤。現在想來他們的決定很正確,如果他們待到現在,就會被困在酒店裏,根本無法排練。”
演出取消、排練取消,佟孜在上海的工作也徹底陷入了停滯。她把所有的希望,寄託在4月份另外一場戲能正常推進上。
為了緩和心情,佟孜打算出去散散心。看到上海4月飛西安的機票只要99塊錢,她滿心歡喜地聯繫了朋友準備去玩。朋友還特地安慰她:“按過去的情況來看,線下演出頂多需要一週就會開始恢復了。”
結果3月底,佟孜等來的是4月演出取消的通知,這意味着整個4月份,佟孜將沒有任何工作可以推進。“如果沒有疫情,春季黃金週期內,我們三、四、五月會分別安排一部劇目在上海巡演,這也是今年Q1和Q2的工作重點。但因為疫情,三個項目全延期了。”
3月27日,佟孜打算下樓買東西,鄰居突然告訴她,小區大門又封了,因為小區內出現了一例陽性。從這天開始,佟孜正式開始了她的長期居家隔離生活,而這一隔就是近30天。

圖源:佟孜提供
居家隔離期間,佟孜出不了門,戲劇籌備和排練也無法同步進行。每天除了搶菜之外,讓她更苦悶的,是整個上海戲劇行業失去了3-5月這個往年票房最好的黃金週期。經歷過這樣一次重創之後,行業到底如何恢復?
根據中國演出行業協會綜合調研票務平台、劇場、演出經紀機構,從2月中旬至3月中旬,演出取消或延期的場次超過4000場,3月下旬還將有約80%的項目停演或延期。據測算,預計至3月底,全國取消或延期的場次約9000場,佔一季度專業劇場、新空間演出總場次的30%。預計一季度演出場次較2021年同期降低25%以上,票房收入降低35%以上。
“2018、2019年國內戲劇市場發展得非常好,出現了很多好戲,很多國際大導演也會來國內演出,也出現了很多好觀眾。但正當我們滿懷期待的時候,2020年突然開始疫情爆發,此後再也沒有外國劇團來到國內,國內從業者也不能去國外戲劇節選戲,無論是對觀眾還是從業者來説,都是極大的損失。”
2月的時候,佟孜還看到很多劇團在招新人,但到目前為止,幾乎所有劇團都停止了招聘。她很擔心,本就造血能力不強的戲劇行業,是否又會迎來新的一輪規模縮減?
在線下演出極其不穩定的狀態下,佟孜身邊已經有朋友考慮從戲劇圈轉行,去大公司做公關經理。但佟孜依舊不想在這個階段離開戲劇行業,她依然享受在小劇場排劇、演出的狀態,享受每天為了一出好戲拼盡全力的過程。
令她欣慰的是,很多戲劇人和她一樣沒有放棄。
佟孜所在的編劇羣裏,很多編劇開始自發組織起了線上劇本朗讀會。很多平時被瑣碎工作連軸轉的編劇,開始利用這段時間閉關修煉;還有的朋友試圖嘗試做live cinema,在線上直播表演戲劇;上海國際舞蹈中心、上海話劇藝術中心、上海大劇院都把過去的一些精彩演出在網絡上進行直播,上海話劇藝術中心官微播放的契訶夫經典話劇《萬尼亞舅舅》觀看次數達44.6萬;
**“我知道大幕終會拉起、場燈終會開啓,現在要做的無非是等待,在等待中創作。”**佟孜説。

綜藝錄製,無限期推遲
因為做的都是平台A、B級,體量不大的項目,小小調侃,自己是一家駐紮在江浙滬地區、“臀部”綜藝製作公司的編導。
2012年,謝滌葵導演的《爸爸去哪兒》一炮而紅,小小心中對綜藝的熱愛也因此種下。
上大學時,她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廣播電視編導專業。2020年,大三的小小便進入這家綜藝公司實習,最終成功留用。由於公司規模較小,兩年下來,小小几乎做遍了執行導演、編劇、Follow PD等各個工種。
由於入行時疫情已經蔓延,小小一入行便知道了很多新“規則”,比如所有涉及到出國的項目都是不可能推進的;去全國各地錄製的時候,第一道流程同樣是查錄製地點的疫情情況和防控措施。
“那時候一直很恐慌。好像我們去哪,一離開那裏疫情就爆發了,有一種‘跑毒’的感覺。”

小小疫情前拍攝的上海
圖源:小小提供
2021年11月,小小的項目被安排在長沙錄製。結果錄製當天,長沙出了確診病例,行程卡也帶上了星。藝人臨上飛機前知道了這個消息,本來想下機,但已經無法回頭,還是硬着頭皮去了。
錄製結束後,小小進行了為期7天的居家隔離。這是她第一次因為錄節目被隔離,而這卻只是個開始。
2022年1月末,小小去上海為今年的新節目做錄前準備,結果恰逢上海小規模疫情爆發,回家隔離了7天。節目組有一位從北京過去的執行導演,因為行程卡帶星無法返京,愣是帶着團隊去其他城市旅遊了十四天把星摘掉,才回到北京。
3月中旬,節目正在上海錄製。休息期間,因為沒帶夠衣服,小小去上海逛了一家商場,沒想到這家商場第二天就被封了。但當時的她並沒有在意,還和朋友保證:“不會有事的。”
結果錄製結束三天後,小小當時在上海住的社區就被封了。再一次慶幸“跑毒”成功的同時,她眼看着上海的封控範圍一步步擴大,最後到了所有錄製不得不全面停止的地步。
因為要回收道具,道具老師往往要比節目組晚走兩天。節目組離開上海之後,道具老師卻被封控在上海酒店,至今無法回家。前兩天,道具老師發了一條朋友圈,上面寫道:“這是我好久好久以來吃到的正常的一餐”,照片上是一盒盒飯。
“比如説道具、攝像這樣的工種,他們按天算錢。像他這樣沒辦法工作,肯定是什麼工資都拿不到。對於公司來講,要承擔他隔離期間的費用,相當於這個節目的一單白乾,甚至會虧損。”
由於後續錄製暫停,節目原定上線計劃也被無限推遲。上海平台方的工作人員被封控,審片也無法推進。
而對節目影響最大的,是贊助商。
小小透露,現在節目至少要比原計劃晚上線一個月,但贊助商尤其是手機、服裝、化妝品等品牌,如果要推出新品,在綜藝節目的投放是講究時效性的。如果沒有在預期的月份播出,贊助商很有可能撤資。如果大體量的贊助商撤資,整個節目可能都會流產,這對公司來講將會是一個不小的打擊。

小小之前在上海發佈的朋友圈
圖源:小小提供
由於錄製遙遙無期,小小現在只能做一些節目籌備和研發工作,強度比之前少了一大半。但這也意味着,今年的年終獎要大打折扣。
利用這段清閒而又焦慮的時期,小小思考了很多。她覺得,即使公司的抗風險能力可以讓自己再安然無恙的呆三年,但如果疫情一直持續下去,公司會變成什麼樣子?整個綜藝行業會變成什麼樣子?而自己到底要不要繼續做綜藝?
為了緩解焦慮,小小去做了一些面試,拿到了老師和短視頻編導的兩份offer,薪水也比現在的工作有所提高。
但在接收到offer的那一瞬間,小小發現內心沒有任何對新工作的興奮和憧憬。這和兩年前入職綜藝公司的心境,是完全不同的。
她意識到,自己好像真的很愛很愛綜藝。即使薪資不高,經常加班,但是就這份工作帶給自己的情緒價值而言,確實是其他崗位無法比擬的。
這次面試的經歷,更讓她想明白了很多道理。
“雖然準備了這麼久的節目如果觀眾看不到,我會很傷心,但我從來不覺得我的努力白費。因為我付出了,我獲得了成就感,也讓周圍的人認可了我,這就夠了。無論環境如何變化,我就盡100%的努力做好節目,如果結果不好,我也不會後悔。”
同時她也看到,上海很多的綜藝製作人都在開線上研討會。有一家公司的節目正值籌備期,即使全員居家辦公,團隊也經常在線上開會開到凌晨,精心地去打磨選址、選角、台本等每一個細節。
她相信,或許上海解封之後,綜藝行業會迎來一個新的大爆發。

把自己寫進劇本的製片人
與製片人張景取得聯繫的前一天,他剛剛離開上海四葉草方艙。
從3月中旬到4月中旬,近一個月的時間裏,住在上海的張景經歷了封閉在家、發現自己是密接被隔離、入住方艙、回家做核酸搶菜的全過程。而他工作最大的變化,便是學會在輾轉多地、紛繁嘈雜的環境中,依然能夠穩中前進,繼續把工作推進下去。
張景目前正在做一部古裝IP劇的前期開發,主要任務是每天和編劇溝通改編方向,聽一聽平台的意見。
只要有一個電腦和手機,無論在怎樣的環境下,張景都要繼續工作。因為前期開發時間一旦耽擱,接下來的籌備、拍攝、後期等工作也要推遲,整個項目的週期不僅變大,資金回籠的時間也會變晚。
以往這個時候,張景會和同事們在公司開會,或者出差見客户。但同事們紛紛居家隔離之後,張景的項目討論會被迫搬到了線上。
為了能夠讓工作順利展開,且保證效率,張景的團隊經常會前一天敲定第二天開會的時間,但也會有無法預料的事情出現,比如做核酸。“有時候我們正在開會,團隊的同事就會被通知做核酸,大家只能停下手中的工作,等對方做完核酸繼續工作。”
語音上的溝通經常有延遲,他們無法看見對方的表情,更準確地接受到對方的信息,也會使得效率變低。
“以前和團隊面對面溝通,話説一遍大家就能明白。但當會議搬到了線上,我闡述完對項目的見解後,同事還會反覆確認‘你説的是這個意思嗎?’”
生活總是具有挑戰性。4月初,從家搬到酒店隔離的張景,好不容易花費近兩週的時間適應了酒店的生活,到了4月11日晚上十一點,抗原檢測為陽性的張景又被通知要搬往方艙。
張景對那晚的記憶十分深刻。在漆黑的夜晚中,他站在大巴車上等了一個小時,後被告知方艙已滿,他又在車上站了近五小時(往返時長)回到酒店,此時已經凌晨四點。折騰到4月12日下午,張景才正式順利住進方艙,此時的他早已經身心俱疲。
而工作難度也隨之增大。
張景所在的方艙位於青浦的國家會展中心——四葉草方艙。無論是空間還是條件,已經算不錯。但問題是,方艙體量大,張景所在的區域以大通鋪的模式,容納了幾乎三千人。他們的牀鋪就像電視劇中職場劇的格子間工位一般,小隔間挨着小隔間,每個小隔間擱置兩張牀鋪,二十四小時不熄燈,幾乎沒有個人空間可言。
張景工作時經常需要閲讀,梳理工作,有時候還會自己上手寫一些東西。但在方艙的一週裏,四周有人和家人、朋友打電話,有人不斷抱怨起居環境,還有做核酸的事情穿插進來。與此同時,他還要照顧同行的女兒,自己很難找到一個完整的時間段專注工作。
張景經常需要等到10點之後,大家基本都睡了,才能拿出電腦工作,“每天大概工作兩三個小時。”張景説到這裏,不免感嘆自己的睡眠質量比較好,才能保持一定的身體能量,“隔壁牀鋪的阿姨,在這種光亮下很難入睡。”

張景家窗外的風景
圖源:張景提供
一個月的封閉生活,張景還能掌控。但如果疫情持續下去,整個影視行業發展就會受到較大的影響。
在籌備劇集的過程中,團隊通常需要實地堪景、協調演員的拍戲時間。但如果不知道上海疫情何時截止,這些工作只能擱置在一邊,而等是唯一的答案,“我手裏也有一些中視頻的項目,不能拍就只能擱淺,沒有辦法。”
如果有劇組正在上海拍攝,無法按時拍攝是小,一旦影響演員的排期,那麼即便後期有時間拍攝,演員時間的協調也會成為一大難事,是劇組有錢也無法解決的問題。對於主要跑上海劇組的底層羣演來講,停工更加意味着失去了收入來源。
到了後期階段,團隊還要和後期進行一幀一幀敲定畫面。受疫情影響,這些工作只能在線上進行,然而幾十集的畫面容量很大,網絡傳輸文件便需要幾個小時,“時間成本也是一種消耗。”
項目推遲或停擺的每一天,都意味着燒錢。
張景的製片朋友告訴他,有一個劇組被困到了上海的酒店裏待命,“住宿費和一日三餐的費用,整個劇組加起來,一天也要消耗十幾萬了。”張景説,按照一般情況,如果劇組有事停工一天,工作人員的工資是照發不誤的,但遇到疫情的特殊情況,劇組可能也會做出工資方面的調整。
在不可抗力面前,所有人都束手無策,他們能做的,就是儘量把手頭工作做好,在混亂中求穩。
團隊計劃手頭IP的開發期為一年,前期工作中,編劇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張景團隊中的編劇王恆,也被隔離在上海家中。往常這個時候,王恆的孩子都會去上學,自己在白天可以擁有大段的時間進行創作,如今小孩和自己一起隔離在家中,時不時地會跑過來找他,從而擾亂創作思緒。王恆沒辦法,也只能選擇深夜進行創作。
方艙隔離的過程中,張景很關注編劇的創作狀態,偶爾也會打電話給他,“我隔一段時間會了解他的工作進展,有問題及時溝通,因為編劇如果狀態不好,整個項目就沒有辦法按時完成了。”
儘管困難重重,但影視人們並沒有躺平。
張景從業十餘年,影視行業裏的大風大浪他已經見怪不怪,即便親歷上海疫情,他仍然對未來充滿希望,“行業走在低谷之處,不用焦慮也不用迷茫,大家只要堅持做自己熱愛的內容,低谷之後,就是走上坡路了。”
張景做過一些現實題材的項目,他想,如果公司有機會做一個關於疫情的項目,自己一定是故事中最有發言權的人。

紀錄片人,首先要活下去
“首先要活下去。”這是紀錄片導演靳導現在最想跟同行們説的話。
從大學到現在,靳導從事紀錄片創作已經五年。但畢業於傳媒學校的他告訴娛刺兒,身邊很少有同學進入紀錄片領域,因為紀錄片屬於影視產業中的“邊緣行業”。
“我們行業裏一直有這樣一句話:‘想發財就不要做紀錄片。’因為掙錢真的太少了。”
靳導苦笑説,自己每年只能拍一兩部紀錄片,收入僅可支撐他的日常開銷,做紀錄片導演也幾乎是他全部的收入來源。
然而,從2022年4月1號至今,靳導被隔離在上海浦西的家中已經近一個月,一沒工作,二沒收入。最重要的是,之前已經在進行的紀錄片項目被中斷,未來如何發展還不得而知。
按正常計劃,他目前參與執導的紀錄片項目本該3月15號就在平台上線,但3月份上海疫情已經非常嚴重,劇組的拍攝、交片時間一再被拖延,節目到現在為止也沒能播出。
“我們前期已經準備了小半年,制定了非常詳細的排期表,疫情影響的雖然只是其中一個環節,但就像‘多米諾骨牌’,後續一連串的工作都被推遲了。”

圖源:靳導提供
目前,靳導所參與的紀錄片項目播出形式為周播,無法接續拍攝導致節目上線遙遙無期。如果因為封控而導致節目遲遲無法交片,中間空出的數月時間裏,靳導和他的劇組成員就會沒有任何收入,因為只有節目上線後才能拿到尾款。而公司也會因為空有成本支出而沒有收入,面臨不小的虧損。
靳導向娛刺兒透露,此次上海停擺,一些小的影視公司甚至會因為資金鍊中斷而倒閉,“我一個開後期公司的朋友現在就遲遲收不到尾款,但公司還要保障房租、水電、職員工資等硬性支出,後期公司設備更新升級等也是一筆不菲的開銷,現在公司運轉都成很大問題。”
上海疫情形勢發展,完全超出了靳導與其團隊的預期。靳導每天悶在家中,對未來的不確定性時刻困擾着他。
一是收入的不確定性。舊的項目沒有完成,也不清楚什麼時候能接到新的項目;另一方面,紀錄片行業本身就是小眾行業,疫情影響下導致整個影視行業持續萎靡,紀錄片行業也更難以注入新的資本,從業者也會因為“吃不上飯”而漸漸流失。
靳導擔心**,紀錄片行業會因此而停滯,甚至是倒退。**
基於這種苦悶與未知,靳導的心情也逐漸由前期的樂觀逐漸變得焦慮。“我也只能通過做點‘可控’的事情讓自己暫時抽離出來,比如最近我刷完了七十六集的老版《三國演義》,不過這也只能暫時緩解這種‘心焦’的狀態。”靳導笑着説道。
但在焦慮的同時,出於自身職業敏感性,靳導突然開始好奇同在隔離中的其他人,是怎麼度過這段迷茫而苦悶的生活的。
於是,靳導向周圍人徵集了一些他們居家隔離的視頻。
在這些影像中他發現,其實大家都在努力用樂觀的方式,來對抗內心所有的不安與焦慮。視頻雖短,卻温暖而有力量。
在靳導收到的視頻中,有人記錄了自家窗外棲上枝頭的鳥,是如何一步步給自己築巢,甚至孵蛋的場景。他看完之後特別感慨,平常大家忙於生計,卻忽視了窗外的一草一木。如今靜態的人類看着動態的自然界,不同的視角之下也會有不同的感受。
“這也是我熱愛紀錄片的原因吧,打動人的總是最真實的。”靳導對娛刺兒説道。

圖源:新浪微博@護鳥熱線
在影視寒冬之下,靳導的不少朋友都選擇離開了影視圈。甚至有人直接轉行做起了電商。但在靳導眼裏,不論他們是真的放棄了理想,還是想“曲線救國”,這些都無可厚非,畢竟“活着”才是最重要的。
儘管靳導現在仍然很迷茫,但他仍選擇會為理想而堅持着。**“一個國家沒有紀錄片,就像沒有相冊。而我願意成為這個相冊的製作者。”**靳導對娛刺兒説道。

影院人的煎熬與堅持
而相比於紀錄片導演靳導的“堅持”,上海一家影院經理李成梁則用“熬着”這個詞來形容他的現狀。
根據貓眼專業版數據,截至2022年4月24號,影院營業率仍不足50%,全國一半以上的影院都在關停狀態,這其中當然包括李成梁的影院。
除2020年之外,往常的4月中下旬開始,各大片方就會帶着物料、搶票費等陸續來拜訪李成梁的影院。而現在,李成梁已經居家隔離了一個月,他的影院從3月9號就已被通知關停。
“其實普陀的影院在3月9號之前就停業快一週了。3月份重量級的進口片都在下旬上映,所以算下來整個上海的影院從3月份到現在,幾乎顆粒無收。”李成梁用“一夜之間,大廈將傾”這句話來形容上海影院被關停這件事。
**從2020年疫情爆發開始,李成梁坦言這幾年他的影院根本沒有掙到錢。**一方面是由於現在院線影片的質量、數量逐年走低,無法拉動觀眾;另一方面,像“幽靈”一樣的疫情神出鬼沒、揮之不去。
2020年復工之後,影院的限座率從30%逐漸上升到70%;疫情之前,片方還“求”着影院給排片,而現在影院卻陷入被動狀態,甚至一度出現片方要求影院交保證金電影才能上映的情況。影院與片方之間的關係,也因為整個電影行業的頹靡變得緊張起來。“2020年復工到現在,每個月都像噩夢一般。”李成梁形容道。
與2020年相比,李成梁坦言,2022年影院停擺對行業的打擊更大。
李成梁的影院共500個座位,同體量的影院在五一檔大約有20萬元的票房入賬。2022年失去“五一檔”,也意味着這些收入將“打水漂”。而另一方面,2020年停業期間,李成梁的員工還能每週去影院給放映機通通電,防止主板虧電損壞。但今年上海疫情爆發後,防疫政策更加嚴格,所有員工都隔離在家,影院也只能空關着。
“放映設備是我們影院的‘心臟’,如果影院持續關停,復工之後放映設備一定會出現大問題,一塊主板好幾萬呢。”李成梁無奈説道。

李成梁的影院
圖源:李成梁提供
一方面面臨虧損,另一方面“影院何時能復工”也一直縈繞在李成梁的心頭。
李成梁告訴娛刺兒,以2020年為借鑑,影院是各個社交場所中復工最晚的,甚至KTV都比影院復工早。此次上海影院停業,李成梁估計少説會停工四個月,更悲觀一點可能國慶節才能復工。
然而,等影院復工之後,李成梁又將面臨與物業就房租進行“談判”的棘手情況。2020年,物業給李成梁的影院減免了三個月的租金,共56萬元。而今年能減免多少,他也不得而知。
2022年3月31號,上海市國資委發佈了《上海市國有企業減免小微企業和個體工商户房屋租金實施細則》,其中提出將對小微企業減免六個月的房租。
“雖然有利好的政策,但我們還是得跟物業協商的。況且人家物業也不好過,人家憑啥就願意給你減免呢。”李成梁苦笑道。
李成梁管理影院已經十四年有餘,但他坦言,行業要想回到2019年的水平,絕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實現的事情。
從2020年疫情爆發到現在的兩年多來,影院中上游的電影公司、營銷宣發等公司都遭遇重創。影片數量減少、中游宣發疲軟,而影院處於影視行業食物鏈最底端,自然難以分到一杯羹。
十四年前,李成梁剛入職時,他的老闆告訴他影院行業“五年一輪迴”,但他依然懷抱着熱愛來到這個行業。如今十四年過去,李成梁形容影院經理這份職業,對他來説已是一個無法回頭的選擇。
“一些人退出,一些人也會因為‘熱愛’而留下。影院人未來充滿困境,但也充滿變數和機遇。疫情之下影院行業會被刷新、規範,能堅持留下的影院人,也會慢慢成為這個行業‘中流砥柱’吧。”
李成梁説,即使最後他沒能堅持下去、放棄了,也會找機會重新回到行業中來,只為他熱愛的“電影”。

後記
在籌備選題期間,娛刺兒曾在朋友圈發問:“是否有上海的朋友項目被迫中斷或者延期的?”而大多數朋友給娛刺兒的回覆是:“你要問誰沒有嘛?”
但慶幸的是,儘管經歷了一個有些魔幻的春天,他們對生活和創作的熱情絲毫未減。
有人停下了忙碌的腳步後,開始記錄起自己的父母、鄰居、以及志願者們的故事,並準備寫成劇本或小説;有人開始堅持讀書打卡、直播,或是蹲守在劉耕宏直播間跳操減肥;還有人已經從只吃外賣的人變成了“大廚”,成為小紅書做飯博主。
在行業的鼎盛時期,這些文娛行業者們滿腔熱血,奔赴熱愛;而在行業的低谷時期,這些文娛從業者們不輕言放棄,也從未後悔熱愛。他們感性、脆弱,但又積極、堅定。
生活如戲,他們仍在努力“活到”最後一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