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校留學歸來,她去劇組跑龍套_風聞
InsGirl-InsGirl官方账号-都市新女性的时尚生活美学2022-04-29 15:18
來源:InsGir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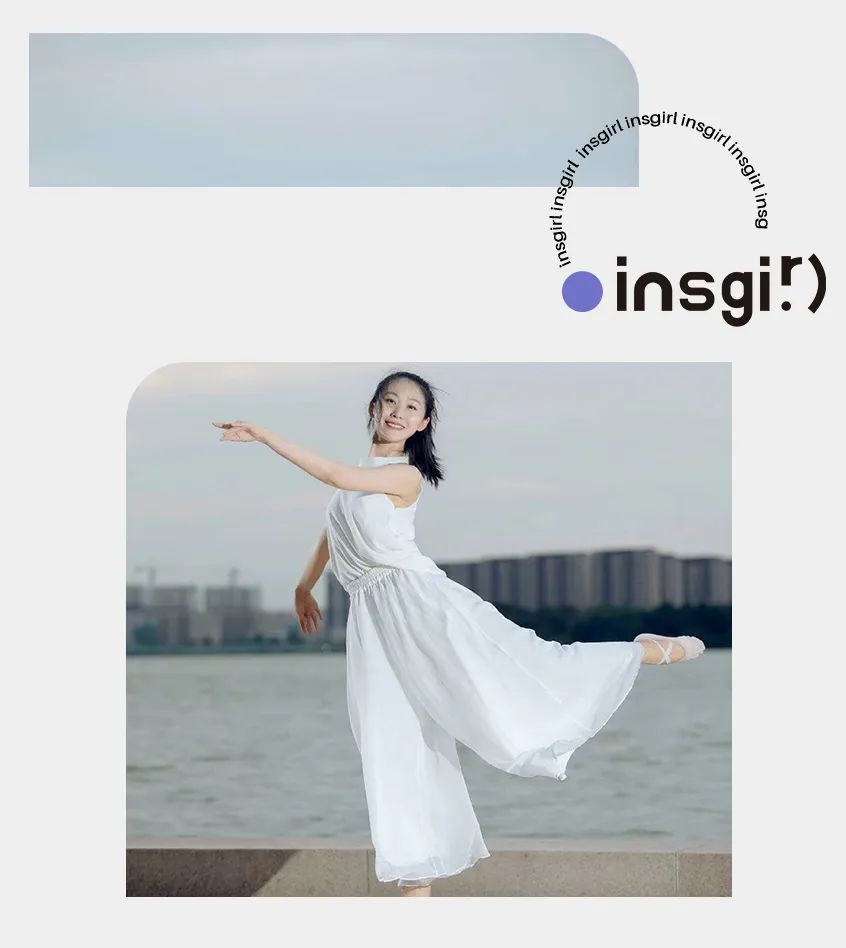
每部電影裏都應該有一個主角。
無堅不摧,閃閃發光,在芸芸眾生的哭喊聲中把握世界的興衰變幻。
這個設定本身無恙,但可怕的是,主角的位子永遠不乏有人蜂擁而來。
卻始終沒有人,甘願成為芸芸眾生。
編輯|弼馬
憑一己之力改變世界,是很多人藏在內心深處的宏圖壯志。
這個目標彷佛象徵着人類智商和能力的最高體現,換句話説,人們更偏向於把它歸結於人生的意義。
人們本能地抗拒平凡,恐懼平庸。
因為在某種意義上,這些詞語代表着失敗、退縮和妥協。
在邵逸凡收到賓夕法尼亞大學錄取通知書的那一刻,她更加堅定自己就是那個要改變世界的人。
來人間一趟,她絕不僅僅只是為了看看太陽。
二十三年前,哈佛女孩劉亦婷的故事爆火。
一夜之間被學生和家長奉為聖典,以幾乎人手一本的傳播度霸佔着女孩們的夢想。
還在小學的邵逸凡也不例外,反覆讀了幾遍之後,她當機立斷許下一個“樸素”的願望:上哈佛。
並且她堅信這個目標對她而言,並非不可攀登。
小時候的邵逸凡,一直活在一種優越感中。
別的孩子還在圍着及格線打轉的時候,她已經以每次考試成績第一,並且連續跳級的勢頭一路小跑了起來。
家裏條件不錯,她從小想學什麼就可以去學。
母親每個週日都會蹬着自行車帶她去各種興趣班,學習唱歌、跳舞、彈琴、各種才藝。

二年級的時候,母親給她買了台電腦,每天讓她守着電腦上的多媒體軟件學兩個小時英語,她的英語水平,可以説是贏在了起跑線上。
高中的時候,邵逸凡一直是全校文科第二。
但高考那天卻發揮失常,從第一志願落到了第三志願,最終以比本地同學高差不多100分的成績進入了天津師大英語專業。
大學畢業以後,憑着優秀的英語底子,她成為了新東方部門最受歡迎的老師之一。
在別的老師都生源慘淡的淡季,她的課依舊有着很高的上座率,這讓她的自信心不斷地膨脹。
2010年,《杜拉拉昇職記》爆火,大家都開始憧憬那種高大上的白領生活。
那個時候,有位諮詢公司的老闆告訴她,你和諮詢公司之間,就差一個名牌大學的招牌。
就這一句話,在邵逸凡心裏掀起了軒然大波。
她很快就準備好了申請材料,投了賓大和哥大。當然,還有小時候的夢想,哈佛。
母親不理解,你這是成心不想出去?你不留個保底?
她胸有成竹回幾個字,賓大是保底。
很快,她就如願以償收到了賓大的offer,甚至還有當年的獎學金。
父母高興壞了,勸她趕快辭職辦手續。
邵逸凡卻還執意要等着哈佛,直等到截止時間的前一天才給了回饋。
那時候的她沒意識到,她一直把自己往一座山的頂峯上推,能登頂絕對不肯低半步。
但她沒想到的是,這也許是自己作為一個要改變世界的人,最後能擁有的驕傲。
如果説人生所有痛苦的本質都是出於對自己無能的憤怒,那麼也許更痛苦的就是從無所不能的神壇上墜入一無是處的煉獄。
邵逸凡怎麼也沒想到,那個人人心之嚮往的地方,會變成自己的地獄。
她是以託福聽力和閲讀雙滿分的成績進入賓大的,但是第一節課的時候,她卻非常惶恐地發現自己根本聽不懂老師和同學在説什麼。
因為選擇了教育學專業的社會學方向,課堂上經常會有偏社會政策和現象方面的探討。課程對閲讀和寫作的要求都很高,那些晦澀生僻的單詞,讓她覺得自己武功全失。

她引以為傲的英語成績,在這裏連基本的交流和聽課都保證不了。
她這才注意到,13個學生裏,只有兩個非英語母語的中國學生,另外一箇中國學生,從中學時期開始就在美國讀書了。
一開始,她把自己的落後歸於自己並非英語母語學生,但後來她發現,學校裏甚至有一些上外畢業的中國學生,GRE寫作能拿到差0.5分滿分的狀態。
但這還不是最難的,選課的時候邵逸凡選了一門會計課。
母親是大學的高數老師,本以為算是大環境帶來的優勢,沒想到她的認知又一次欺騙了自己。
在賓大,她周圍的學生都是一些來自哈佛大學數學系、中山大學數學系的學生。她醒悟過來自己的選擇有多愚蠢之後,漫長的痛苦開始了。
一次小測結束之後,周圍的同學都在抱怨,怎麼還錯了一兩道,沒拿到滿分,邵逸凡的卷子上卻赫然寫着1分。
後面的每次會計課都是噩夢,她最大的剋制是讓自己不要在課堂上就哭出來。
然而在賓大,最累的不僅僅是高強度的學習本身,而是不能讓別人看出來自己很累。
因為那樣,會顯得自己很弱。
就像經常被提起的那句雞湯“你只有用盡全力,才能看起來毫不費力。”在她看來,賓大的每一個學生都無時無刻不在奉行這句話。
不讓別人發覺自己在用盡全力追趕,不在別人面前暴露軟弱,這是大家心照不宣的默契。
你永遠不知道一個表面談笑風生的人背後會經歷什麼。
而這種談笑風聲的狀態,和邵逸凡拿着1分卷子哭哭啼啼找老師講錯題的場景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像是無意間打破了某種遊戲規則。
但邵逸凡已經顧不上體面,她只在乎自己還能不能畢業。
所幸,在刷了很多份卷子之後,她憑着肌肉記憶低飛通過了會計課的分數線。
第二年,有新生學弟和學妹向她打聽,這課難不難通過?
她心想,自己這樣的水平都通過了,應該不算難吧。就很誠懇地回答,不難。
接着他們又問了一個讓人窒息的問題:那你拿到A+了嗎?
她怔住,原來在賓大,拿到A+才算通過。
自己是什麼時候把通過的標準降到這麼低的,她不太記得了。
只是有時候想起之前偶爾拿不到班級第一就要哭鼻子的經歷,彷佛上輩子了。
二十多年基礎教育和大環境造成的差距,有着讓人絕望的距離。

邵逸凡比以前的任何時候都要清醒,自己無法在短時間內追趕任何人,那是一條不能靠努力拉近的鴻溝。
老師給別人論文的評語,是大篇幅的溢美之詞之後,再針對內容展開的學術討論。
到了自己這裏,就剩下貧瘠又儘量顧全顏面的一句話,“你能不能多寫一點?”
她這才意識到,原來自己一直以為的山頂,對別人而言只是院子的一個土堆而已。
有天,母親提出想要去賓大看望她,她算了算準備簽證和機票的時間,把見面時間定在了幾個月後。
第二天的時候,她被約好了一起吃飯的同學晃了約,理由是:我媽突然過來了,下次再約吧。
她抱着一絲僥倖問一句,你媽從哪裏過來啊?對方回,北京啊。
那種漫不經心的語氣,讓她的問題很突兀又多餘地僵在那裏。
邵逸凡在這個時候不合時宜地想起,小時候的自己曾經是學校裏為數不多有電腦的家庭。
接觸到演戲,是一個巧合也是必然。
畢業回國後,她拿到了行業內名列前茅的戰略諮詢公司的offer,但是因為程序問題,推遲2個月才入職。
這2個月裏,她看了很多影視劇來消遣。當時喜歡胡歌,就追完了他所有的劇。
胡歌在上海演《如夢之夢》,黃牛票一萬多,她也一咬牙買了去看了。
2017年休年假的時候,邵逸凡突發奇想去嘗試配音,第一次去就面到了一個女一號的配音。
那天好多好多的女孩兒,但偏偏就選中了她,那種“天選之子”的使命感又死灰復燃,她覺得自己又可以了,會在百忙之中擠時間去做做臨時演員。
諮詢公司的本職工作,用她自己的話説,要麼你能熬夜,要麼你聰明,但這兩個自己好像都不沾邊。再加上因偶然的機會加入了《非誠勿擾》的錄製,她的生活像一個快要被榨乾的橙子。
2018年的某天,邵逸凡認真告訴老闆,我要辭職去學舞蹈,我還要去演戲。
老闆也認真回覆,想要跳槽去別的公司,能不能編出一個像樣點的理由。
但她果真認認真真跳了三個月的舞蹈,接着翻出了那些羣頭的微信,走上了臨演的路子。

但做臨時演員的日子,也沒有想象中好過。
劇組人多,等級森嚴。只是最簡單的吃飯問題,就恨不得劃出三六九等。
大明星吃飯在房車裏,導演們在室內或者棚子下面,重要點的演員有個桌子,劇務和工作人員也能上桌。
像她們這種被稱作“跑龍套”的演員,隨便找個地方蹲着就湊合一頓。
不管有多少戲份,必須去的最早走得最晚,被劇務呼來喝去什麼的也是家常便飯。
有時候新來的羣演,不太懂規矩,端了飯坐在桌子前吃。
很快就會有人來攆,你羣頭是誰?誰讓你坐着吃飯的?
這樣的環境,讓她早都習慣了放低姿態。
每次別的臨演抱怨不公的時候,她都會以一種自嘲的口吻説,擺正自己的位置,我們只是跑龍套的,別太把自己當回事。
有一次,她接了一個500塊的前景,其中還需要一個稍微漂亮點兒的女生做最前排的演員。
邵逸凡和很多女生一起在地鐵門口站一排,像青菜一樣給人選。
羣頭指指點點地挑着,有個男生指着她,“我覺得這個不錯。”這時他旁邊一個女生特別大聲地説,“你什麼眼光?還是我來挑吧!”
邵逸凡沒説什麼,也沒賭氣走,像是習慣了,又像是沒什麼可反駁的。

那天,她們一羣人熙熙攘攘跟着去了以後才發現,那場是演妓女,配的服裝也非常暴露。
但已經這時候了,走是肯定不能走,也不敢走。
用她自己的話説,走了一是沒錢,二是行業會覺得你矯情,以後就不找你了。
穿着妓女的衣服站在那裏,副導演手上一隻激光筆,換一場戲就換幾個女孩上去。綠色的光點兒在她們身上掃來掃去,像挑什麼貨物。
你來你來,你站起來,你不行,旁邊這個,你過來吧。
有時候,她覺得身體裏面的那個邵逸凡好像不復存在了。現在的邵逸凡,早已經成了平凡的不能再平凡的人了。
什麼時候開始的,她不大記得了。
也許是賓大抱着1分試卷找老師哭的時候,也許是在客户面前困得睜不開眼的時候,也許是自己穿着妓女的衣服被激光筆指着的時候。
那種與生俱來的優越感被按在粗糙的木板上,粗暴地來回拉扯,一層層打磨出一個光滑的弧度。
從賓大回國的這些年,邵逸凡常常會牴觸那些和挫折有絲縷關聯的回憶,她覺得這是自己體內的自我保護機制在本能地發揮效應。
沒戲拍的時候,邵逸凡會去學芭蕾,大汗淋漓跳芭蕾的時候,那些封鎖的記憶會跑回來一些。

她想起,在賓大的最後半年,她組織了一個合唱團,每天和來自五湖四海的朋友們一起排練。
畢業的時候,有人特意找到她,“凡姐,你不知道這個合唱團帶給我多少慰藉和快樂。”
她也想起,自己在諮詢公司的時候,曾經組織了轟動行業內部的音樂會,那天晚上收穫的掌聲,比自己考上賓大時候還要多。
她還想起,有天演完戲,劇務喊她別走,當她以為要扣工資的時候,大導演向她走過來,認真地説,“我以前怎麼沒發現你,你演得特別自然特別好。”
這些片段像電影一樣從腦子閃過去,她的眼淚和汗水也混着湧出來。
我會跳舞。
我還會演戲。
我其實英語很好。
我讀了很好的學校。
我還可以帶給別人快樂。

以前的邵逸凡,總覺得自己在一條河裏,好像不拼命撲騰就會沉下去。
現在,她好像站在了山上,看着山下河裏的自己,有時候甚至會想,就算沉下去,又能怎樣呢。
我的確就是一個特別普通的女孩。
如今,邵逸凡還是會遇到那種經過層層篩選,好不容易選到手的角色,進組前兩天被告知換人了。
但對於這種事情,她已經可以做到波瀾不驚了。
別太把自己當回事,是她現在經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
她認為人類的大多數痛苦都是來源於此。
最近因為疫情封控,她連續三次被換掉。
這讓她想起去年的時候,自己曾經頂掉過好幾個被封控的演員的戲。
現在回頭想想,並不是那個演員太差了,自己太厲害了,而是整個大環境造就的。
有時候,她會覺得自己像顆樹。
長成什麼品種不是自己能決定的,長在什麼位置也不是自己能決定的。
如果前面沒有樓,也許就可以長得茂盛一點兒,如果前面有樓,也許就會拐個彎兒。但起碼,她健康平穩地活了下來。
她開始覺得,自己來人間一趟,的確不僅僅只是為了看看太陽。
她還有很多事情可以去做,但唯獨不是一個救世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