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等到城市病了才想起鄉村_風聞
秦朔朋友圈-秦朔朋友圈官方账号-2022-05-05 15:53

劉子 | 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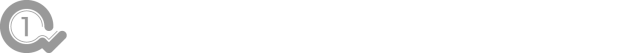
城市病了嗎?
我想從曾經工作過的房地產説起。2015年,我在某新一線城市郊區做一個剛需住宅盤,為了首次開盤順利去化,價格定在7000元左右,還算合理。
這個階段,目標客户主要是外地人,他們或做點小生意,或開大貨車,或在附近工廠打工,多半在此地呆了多年。他們來到售樓處,拘謹地喝着水,問到價格,大多搖着頭表示有點貴,爽快下定的總是少數——我們心裏有底,這個定價合理,挑貨的才是買貨的。
首開果然火爆,之後,領導倒不着急了,我們都有點詫異。事實證明,還是領導知道的多,半年後,當地開始推行大規模棚改,每平米補償8000元左右,項目銷售迎來第二次爆發!我們和周邊競品心照不宣,同時提價到8500左右——什麼是好的銷售策略?永遠不是滿足客户(輕易滿足就是“賤賣”,要被老闆罵),而是讓主力客户踮踮腳(差太遠客户又會放棄)。
我們的主力客羣變成了拆遷户,他們急需房子住,都揣着錢來到售樓處。他們一面抱怨補償不夠還得貸款,一面看着身邊的房子在“暴漲”,只得無可奈何地付款。
第一批外地人客户知道了,憂心忡忡地趕來,這回他們得從開始的踮腳,到需要起跳了。但多數人寄望政府調控,掏錢的還是少數。
拆遷户消化後,又面臨一段客源短缺的時期。當然,我們有的是辦法,“小步快跑”,控制出貨量,一點一點小漲價,通過製造緊缺、還要繼續漲價的氛圍逼定猶豫客户。
終於,我們等到第三波高潮!果然,地方政府比我們急,棚改完成後,地方需要新的刺激點,“為進一步引進人才”,市政府宣佈大幅放寬落户條件,只要購房90㎡就可以。由於户籍與教育捆綁,以往許多被學歷、社保等條件卡住的外地人們“轟”地炸了,為了留在本地,為了給孩子一個平等的教育,什麼都不管了,不要説“六個錢包”,首付貸什麼的,能上的都上了。隨着全城樓盤一片漲,我們的項目迅速漲到一萬多。
還是第一批來看房的外地人,等了兩年,在前赴後繼的政府調控中,他們越來越失望,又越來越無奈。那幾年,製造業困難,電商衝擊下小生意難做,他們的收入估計還縮水了。凡是能貸款蹦躂上的,都嘆息着交了錢,實在付不起的,就一邊咒罵着,一邊準備退回老家。
好在購買的客户並沒有吃虧。2018年初,城市房價對標上海、杭州,瘋了一樣的繼續“補漲”,我們項目短短幾個月再次翻倍,被賣到2萬多!
三年翻了三倍,買了的慶幸,沒買的腸子都悔青了。眼見價格猛漲,想買的都殺紅了眼,那些為了留在城市想盡各種辦法籌到錢的人,那些以普通家庭為代表的瘋狂的小投機者,咬着牙入了最後的局,站在了最高處……
多少年後,人們寫經濟史,都應該重點分析一下2018年。清華大學鞠建東教授也指出,2018年是中國經濟從工業化時代到知識化時代的大轉折的一年,外部,美國發起貿易戰遏制中國經濟升級,內部,“世界工廠”的“規模紅利”,其長期累積的“產能過剩”“勞動力過剩”“核心技術依賴進口”等問題不斷暴露,製造業和許多傳統行業的巔峯都停留在了那一年。
那座以製造、外貿為基礎的城市,無疑大多數人都身處“傳統”,經濟狀況每況愈下,那些咬着牙、殺紅眼站到了最高處的家庭,欲哭無淚。近兩年再去問,據説不少人陸陸續續斷供了……
房子還是那些房子,人也還是那些人。變的是什麼?除了越來越“漂亮”的城市,還有人們從心底發出來的嘆息。
後來,這樣的嘆息越來越多,並逐漸從小老百姓擴展至中產,化作一個大多數人都不得不面對的字眼——“內卷”。
我時常想,如果就“停”在2015年(當然,不是主張倒退),從地方政府到開發商到人民,都不要那麼急功近利,房價7000多元/平,或者跟着GDP以每年6%-7%地合理增長(到今天11000元/平左右),那個城市郊區,以及那座城市的人們會不會好一些?
如果那些外地人,老家農村也有還馬馬虎虎的教育,他們就可以選擇帶着幾十萬、近百萬的錢回鄉,蓋個小別墅、買輛小車,再在老家打個工、做點小生意,順便拉動一點地方經濟發展,那或許就是共同富裕了。那樣,總要比辛辛苦苦白乾很多年、揹負很多債務、乃至最終落個一場空,要好得多吧。
沒有如果。那座光鮮亮麗的城市,這個從上往下看一片繁華的時代,虧欠人們太多。城市化、房地產、商業邏輯、市場經濟、經濟刺激,怎麼看都是對的,但“刺激”的成本,最終都要落到老百姓頭上,而“刺激”的成果,雖然看上去大眾共享,但實際上,隨圈子不同、階層不同而差距懸殊。
“城市,讓生活更美好”,今天怕是要打上個問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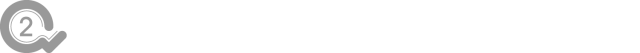
城市病了嗎?今天的答案更是顯然的。
內卷之下,三年疫情又席捲而來。一面是擴散的風險、對老年羣體潛在的巨大沖擊,一面是債務負擔加劇與實際收入停滯乃至倒退,人們的生活苦不堪言。
長期以來,房地產旗手、“大國大城”式的經濟學家和社會精英們,只講聚集、規模化、城市化、經濟刺激的好處,不講它們帶來的內卷、城市病和社會風險——畢竟,他們不用擠公交地鐵,內卷也不會捲到他們頭上。
但這場疫情,卻是公平的,縱你是資本巨鱷,也得早起搶菜,縱你是學者教授,也得隔離難受。
他們看不到,以城市化、工業化、大分工、自由競爭為導向的現代經濟和思想,有其根本弊病——就是把世間萬物,包括人,物化、標價、推向競爭,然後在競爭中推動發展,在優勝劣汰、資源聚集中加速分化、對立。
好的一面,確實發展了,壞的一面,確實分化和對立了。
譬如,城與鄉的對立。試問,城與鄉為何要競爭?需知千百年來,雖然城市要優越一些,但城鄉相互依存,談不上、也不需要競爭和對立。緣何今天,雙方非得就勞動力、土地、民間資本(儲蓄)乃至社會輿論展開競爭——這“競爭”還是單向的,因為鄉村根本毫無招架之力。
譬如,人與人的零和博弈。千百年來,我們的文化講求各得其所、心安理得。緣何今天非得只有“競爭”這一條道?而所謂競爭,無非是誰能以更低的成本搶佔更多資源誰就能勝利,誰先耗盡相應資源誰就敗下陣來。到最後,“優勝者”為守住成果憂心忡忡、疲於奔命,“劣汰者”則為失敗憤懣不已、躁動難平,最終人人不安,這“現代化”的意義又何在?
譬如,人與自然的對立。千百年來,人類雖然需要向自然獲取生存條件,但總體還是自然循環、有限度的。但現代工業化以來,卻成了生態災難。無需舉太多例子,且看人類被偷走的這兩年多時光,帶給了大自然多麼久違的喘息自由。
據統計,疫情期間,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超過6%,大西洋海岸海水清潔度評級直接從差晉升到良,印度恆河氧氣含量增加了80%,動物們開始以我們幾十年都沒有見過的規模繁衍生息,印度人民甚至驚訝地看到了,在霧霾後隱藏了30年的遙遠的喜馬拉雅山。人類的禁足反倒成全了世界的清澈與安靜,人類的疫情災難,卻成了自然界的太平盛世!
|《地球改變之年》
眼中只見發展而不見“人”,終將困於發展!
眼中只見“大國大城”,而不見生活在城市中的“人”,最終也將困於城市!譬如這兩年大量失業、高不成低不就的房地產人,譬如深陷內卷的億萬城市中產,譬如疫情下無可逃遁的城市人……
大家還能去向何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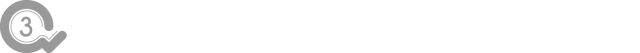
最近,身處上海的我,就成為老家親人、鄰里關心的對象。他們每天打來電話,擔心我們買不到菜,擔心我們會餓死,擔心我們憋出病來,又都説要給我們寄食品和物資。遙遠的老家鄉下,雖然附近縣也有無症狀,地方政府一片緊張,但人們並不需要發愁,米在缸裏,菜在地裏,蛋在雞窩,又沒有負債,該怎麼過還怎麼過。
今年來上海過年的父親,也半開玩笑地説,幸虧他過完年就回去了,不然,現在真的要一大家子人坐在大上海的小房子裏大眼瞪小眼了。
他們問起怎麼買菜,當得知我花180元團購了9斤水果,200元買了一些肉和菜,還有浦東一個朋友花200塊買了2斤肉,都驚訝得説不出話。200元錢,別説疫情期間,就連平時也買不了多少東西,但在鄉下,它依然稱得上“購買力”。
末了,父親沉默許久,説,我去查查車,要不我帶着東西來上海吧……
這些年,我始終對生活了15年的上海有一些隔閡,比如,多年來,我始終只有寥寥一兩個上海本地人朋友。疫情期間,我跟“外地人”朋友聊起來,大家紛紛苦笑,“要不,我們還是準備回老家吧”。
**田園將蕪胡不歸?實際上,綜合房貸(租)、教育、交通、養車、物價等綜合因素,上海中產月收入兩萬,跟內地省城一萬多,縣城五六千,農村三千,生活水平其實並無本質差別,但背後的質量、實際“獲得感”差別卻挺大……**便要問,這辛辛苦苦、謹小慎微、忍辱負重的生活,意義又在哪裏?
自古以來,大疫止於鄉野。大多數疫情,都在城市爆發,甚至引發動亂。而鄉村,由於其分散性和生態性,往往問題要小得多——即便有問題,也更容易阻隔、控制。譬如,2003年的SARS就止步於鄉村,今天的新冠,6億農民也少有感染者,所以温鐵軍教授説,“世界上最低成本的防疫,就是在鄉村”。
當然,城市之病,何止疫情。那麼,我們再擴大一點,更多的城市病,又何嘗不需要鄉村?
只是多年來,我們習慣站在城市化、規模化的視角,將鄉村視作“髒亂差”、落後的包袱。彷彿鄉村是個毒瘤,切掉它,或者讓它自生自滅就好,這樣我們就可以騰出手來全力搞“經濟建設”。
這個思想,主導了中國近四十年“建設”,從八九十年代政府甩包袱、退出鄉村公共服務,到分税制改革後地方政府公司化對鄉村的疏遠,從房地產、工業園對鄉村土地的大肆侵佔,到前些年大量的合村並居、撤併鄉村中小學……
的確,我們的經濟發展了,但“切掉”鄉村後,我們的社會、你的生活,真的更好了嗎?
也許,我們是時候換一種眼光了,比如——鄉村,非但不是“包袱”,其實,她也可以是一種解放。

作者:民間觀察派,獨立思考者。專欄作者,撰稿人,鄉村振興&縣域經濟學者。個人公號:劉子的自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