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蘇州,悲欣交集_風聞
秦朔朋友圈-秦朔朋友圈官方账号-2022-05-06 14:46

過蟈 | 文
半個多月前,網上説,蘇州人民在囤積物資中等待封控。
這句話沒錯,至少我囤了一家四口一個月的雞蛋、土豆、洋葱和胡蘿蔔。蘋果、橙子、梨也夠吃半個月的。結果是,沒有封城,菜場照開,超市營業,外賣暢通,其價格也和疫情前差不多。
本輪疫情,影響最大的自然是上海,但蘇州的承壓也十分巨大。蘇州的尷尬在於,上海不好,它就不會好。上海好了,它也可能有問題。
蘇州從2月14日開始就沒停歇過。“214停課”,整頓一個月好不容易要開學了,“314”又繼續停課,“414”火車站軌道交通停運。
説實話,此前我對蘇州的“抗疫”政策是有點小牴觸的。因為工作在杭州,週五到蘇州後,要從高鐵站被“閉環”交接到社區,然後居家隔離三天後才能再去杭州。可杭州當時明明沒有“星”,無奈之下,只能跟公司請假,在家裏等待疫情過去。
在家的這段時間,我看着蘇州打起這場抗“疫”的硬仗,我身邊的親戚、朋友、鄰居、同學,或多或少都參與到這場戰“疫”裏,心情就變得很不一樣。每個人都很難,但總有更難的人。不管大局還是個人,疫情面前沒有一個人是“局外人”,所有人都置身事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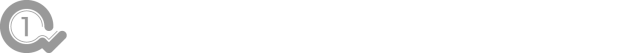
“百強崑山”
蘇州的抗“疫”裏,最嚴峻的戰場大概是在崑山。
我有一家崑山的親戚,平日我們之間的聯絡只靠微信。直到這次崑山連續多日的“靜默”,才知疫情的艱鉅。她和先生都是一線的醫護工作者。
崑山作為一個縣級市,卻有209萬常住人口,比浙江衢州、麗水等地級市僅少了十來萬。作為縣級市的崑山,醫療資源本來就不足,還抽調了一些醫護支援上海。雖然也有其他省內城市醫護來崑山支援,但現在各地都自顧不暇了,幫助也是杯水車薪。
我親戚家兩口子,從2月14日那天蘇州發現疫情開始,到現在幾乎沒有休息過一天,每天睡眠不足四五個小時。兩個人幾乎不回家,都在隔離點生活、工作。上幼兒園的孩子只能由老人帶着。
親戚所在的花橋隔離點,收容了很多流浪漢和經濟水平比較低的羣體。有些隔離點是要收費的,他們這個隔離點住宿三餐全部免費。有很多人是從上海“逃離”而來:游泳過來,徒步過來,騎自行車過來,鑽後備箱過來,他們拼足了力氣在“逃離”上海,情況五花八門,一開始大家談起只當是笑話,但看到越來越嚴峻的形勢後,也不敢説誰笑話誰了。
只是到了崑山又怎麼樣?也一樣是“疫區”啊!
4月上旬,PCB板廠台光電子、南電、欣興電子,面板廠友達,板卡廠微星等諸多崑山廠區都已暫時停工。
崑山是全球電子設計和製造業重鎮,上海和崑山之間有大量日常通勤的人員。上海集成電路產業收入超過全國四分之一,聚集了全國近40%的集成電路產業人才,從業人員達20多萬。崑山則聚集了大量面板、PCB(印刷電路板)企業,大量終端的廠商都在崑山採購零部件。
我有個同學是經營電子設備的小老闆,在蘇州木瀆有一家十幾人的小工廠,他的上游在崑山,下游在無錫。崑山“封”了,蘇州和無錫間的物流也斷了。政府雖然支持開工,但他根本無工可開,每天心急如焚,從沒想到這麼近的幾處地方竟有無法聯通的一天。好在崑山目前已打好了這場攻堅戰,物流逐漸恢復,復工在望,他也安心了不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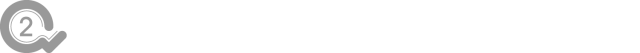
“白髮姑蘇”
崑山是蘇州的“硬仗”,姑蘇區的“抗疫”充滿人文温情。
姑蘇區不久前有一片封控的小區,由政府統一發放三餐物資,媒體便有了話題“造勢”。有些小區的供應是不錯的,有麥當勞的早餐,有蘇州當地有名的“雅都大包”。惹來網上不少羨慕。但是比起媒體喧譁的“抗疫”畫風,更有一些悄無聲息的變化,這樣的變化可能更加可貴。
比如社區做核酸,核酸的頻率幾乎一兩天一次。我們小區有1500多户,常住3000多人,在姑蘇區算大的小區。之前測核酸,是按樓棟測,每個樓棟1個小時。只要一棟樓慢了大家都會慢,很容易積壓排長隊。現在測核酸只給一個時間段,5-6個小時內,隨時下來隨時能做。
令人驚奇的是,沒有安排反而不排隊,隊伍很空。看到人多就晚點來;看見人少就直接測。跟市場經濟一樣,每個人都能做出合理、理性的選擇。
社區工作者也很納悶,以前要千叮嚀萬囑咐,居民還挺有怨氣;現在就給個時間,大家倒都很配合。
我問了身邊的社區工作人員,她説現在的社區工作還是很細膩的。每個社區有多少黨員、機關幹部,社區手上都有名單,這份名單能夠保證,如果哪天社區工作人員因疫情被封在家裏,這些人員能挺身而出,及時地進行小區自治管理。
她的話讓我想起了諜戰片裏的地下黨名單,不明覺厲。但能有這份名單,得是對居民有多麼深入的瞭解啊。也不能光知道黨員幹部,還得知道誰家是空巢獨居老人,誰家裏有大病重病,誰家裏有困難,不説家家户户,一個社區三四千號人,七七八八的情況都得知道。
再比如醫院通道,期間我去了姑蘇區兩家醫院,就醫的大部分是老年人。雖然形式不同,但兩家醫院都設置了電子化和人工化兩條通路,一條是針對普通人,一條是針對不會弄手機的老年人。兩條通道都有人查驗、病患排隊配合,一切井然有序。
就我的觀察,蘇州的基層工作做得挺好的,這大概和城市特性有關。我分析如下:
**首先,這和蘇州人口的均勻分佈有關。**蘇州並不是一座真正的“大城市”。它雖然總人口有1200多萬和杭州人口數量差不多,但分佈卻極為不同。
杭州是進入了“無縣”時代,縣級市被合併的很多。杭州縣級市如桐廬、建德等多在山區,人口稀少。1200萬人口多集中在幾大城區裏。
蘇州市和所轄的幾大縣市,人口各佔一半。崑山人口209萬、常熟167萬、張家港143萬、就太倉人少一點,也有83萬。吳江撤縣並區有154萬人口,但自成一個體系。所以很多外地人士所理解的“蘇州市”,大概也就500多萬人口,且各個區的人口都比較平均,更有利於治理。
**其次,蘇州並不是推崇金錢和效率至上的城市,生活成本低,且有大量和“體制”相關的崗位。**以姑蘇區為例,很多人在企業上班也就每個月四五千塊,工作壓力還不小。很多人更青睞於“體制”,安安穩穩。很多高素質的年輕人也樂意到社區工作,學歷幾乎都在大專以上,本科以上更佔一半!
比如我們社區的副主任就是85後211碩士畢業,樂於溝通、能力很強。這種現象在大城市就很少見了,大城市生活壓力大、高薪的崗位也多,年輕人更願意去企業上班,基層工作少有人願意幹。
**第三、蘇州“市民化”的程度比較高,尤其在姑蘇區,重視“熟人社會”的關係網絡,****有利於社區工作者對居民家庭情況有深度的瞭解。**這在上海、杭州這樣的大城市是非常難的。
我在杭州的小區住了五六年,鄰里間幾乎不認識,只在業主羣裏偶爾聊聊,更不要説串門什麼了。但我在蘇州生活的小區,鄰里關係就很親近,會去對方家裏做客。逛超市多買了食物,也會和鄰里們一起分享。
大城市是“生人社會”,居民更有隱私意識,講私密性。但在重視“熟人社會”的蘇州,人們的信賴度更高一點,基層工作也更好展開。物業和社區的配合度非常重要,因為居民不一定認識社區工作人員,但一定認識物業,並且物業比社區更瞭解業主情況。我們社區的很多工作其實也是由物業共同承擔。
**第四、蘇州是“大政府”,行政干預一直比較強。**舉個例子,在姑蘇區找共享單車很難,車輛也少,根本達不到“共享”的目的,但管理上是沒有亂停亂放的現象。杭州是“小政府”,有些企業代管了一些城市行政管理的服務。杭州的數字化治理比蘇州好,不是傳統人盯人的方式,而是把外地行程帶星的人員,全部黃碼處理,然後根據不同情況實行不同隔離政策。
人類有史以來成為主要生活在城市中的物種——預計2050年,全球70%的人口生活在城市。城市化、高鐵、互聯網、工業化養殖等遍佈的今天,某種隱秘的威脅也正暗地潛伏。
這次的疫情暴露了諸多“大城市病”。任何管理都不會是沒有範圍、邊界的。到底有沒有一個合理的人口規模,既有利於經濟又有利於生活?
我生活的蘇州市姑蘇區GDP墊底,老齡人口密集,曾有數據統計,姑蘇區的老齡化程度已達31.1%,每3個人中就有1位老人,屬於深度老齡化。在這個區裏,隨處可見白髮蒼蒼、慢悠悠行走的老年人,公交車也開得慢慢悠悠,成為了“白髮蘇州”的另一番意境。很多“中產”抱怨房價不漲,甚至選擇主動“逃離”。
因為老年人眾多,各社區都開設有“老年食堂”,一直為轄區內的老人們提供午餐。現在食堂服務依舊,沒有被疫情打斷。由堂食改為了上門送餐和自提午餐。老年人多、社區工作繁瑣,但還是有很多熱心的市民保持着這座古城的温度。新聞報道有一個社區志願者,她看見防疫人員太累了,幾近暈倒在地,就主動讓出了自己家,新換了牀褥被單,從此讓家成為防疫人員的休息站。
蘇州近期還出台了政策,在疫情防控的特殊時期,針對居住在蘇州的上海人,可以在蘇州刷上海醫保卡就醫。
這座城市的温暖和善意,承擔了蘇州的根本,保護了最年邁衰弱的人們,幫助鄰近的城市,它沒有很高的政治地位,也不是誰的後花園。它只是秉承兩千多年的文明,做該做的事,不聲不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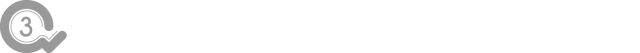
“高三的蘇州”
疫情中有幾個羣體很難,一是孤寡的老年人,二是斷了生意的小老闆,三是因為疫情失業的人們,四是高三的學生。
B站上有一則視頻叫《目送》,是在我們蘇州人的教育“聖地”——蘇州中學拍的。我看得幾近淚目——這些高三的學生提着行李、被褥,和父母擁抱告別,一個個走進學校。
不止蘇州中學,全市高三的師生、教職員工都進入了全封閉住校的狀態,一起吃住生活在學校裏。這屆高三學生太不容易了,高一開始,高中就三年疫情佔三年,有多少被耽擱的青春和學業。但老師也很難,共同住校的有臨近退休的老教師、也有普通的教職員工,有些老師家中孩子無人照看也帶着孩子一起住進了學校。老師不僅教學,週末還得化身“髮型師”“廚師”。
高考也是一場戰役,和個人命運休慼相關。不知若干年後,這些學生會如何回憶這段歲月。看到那些教室燈火通明,在如此嚴峻的形勢下共同奔赴前程,我竟感到一絲蒼涼和悲壯。蘇州近年來的高考成績本來就難和無錫、蘇北相比,如此“疫”來,雪上加霜。
**蘇州中學可以追溯到北宋景祐二年范仲淹創建的蘇州府學,在全國都享有“千年府學”的美譽。**哪怕在抗日戰爭期間,蘇州中學也先後遷校到上海租界、常州、宜興等地進行異地辦學。在炮火聲中,也堅持辦學,給學子們帶來希望。
我在視頻下方讀到一段評論:“范仲淹創下的府學就在蘇中門前,範公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理想抱負和胸襟膽魄,啓蒙了無數青年,一定影響着這一批背影。聽風聲雨聲讀書聲之外,如今的家事國事天下事也需重點關心。”
明清時期蘇州一直盛產狀元,近年來的高考卻不如人意。但這座城市擁有綿延千年的人文之光。有這樣的光芒,城市就不會老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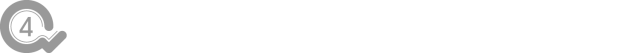
疫情三年,悲欣交集
弘一大師圓寂前曾提筆寫下四個字:“悲欣交集”。
當弘一法師還是李叔同的時候,早些年馳名上海灘,是一名翩翩公子。隨後留洋日本,學習西洋文明,繪畫、音樂、文學、戲劇全都悉心研究,回國後在杭州師範學校上課,隨後學習道家,最後剃度出家。他積極地入世,默默地潛懷,逝世前用“悲欣交集”概括自己的一生。
這四個字,我也用來形容疫情三年。以後,也不知還要多少年。一百多年前,弘一法師也同樣生活在“百年之大變局”的拐點上,人生如寄客,在激流中飄蕩,處處是被時代裹挾的無奈。長亭外,古道邊,芳草碧連天。
但他始終認認真真地做自己,認認真真地活着,是李叔同的時候做好李叔同,是弘一法師的時候做好弘一法師。據説,他給自己起過非常多的名字,每一個名字,都是他的一段際遇,認真對待。
大大方方地悲,熱熱烈烈地喜,用不同的經歷填補生命的空白。可能我們無法改變時代,但積極地參與過、存在過,悲欣交集、有血有肉地活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