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新:從“魚+羊=鮮”説開去_風聞
虎落平阳-2022-05-11 16:28
【按語】《讀寫》雜誌曾以“字”為主題詞,有讀者朋友看到“海峽語文網”徵稿啓事後問該如何寫,其實“文無定法,端在揣摩”,如何寫,誰都説得清,誰都説不清,筆者幾十年前曾在《杭州日報》“西湖”副刊刊發一篇名為《從“魚+羊=鮮”説開去》的雜文,似與“字”主題有關,為“拋磚引玉”,今仍以此題重作一文,匆匆之間有失慎重,見笑於讀者諸君。

從“魚+羊=鮮”説開去
金新

中國漢字的奇妙之處,恐怕在於巧妙的表意功能。比如,泱泱水中“魚”與茫茫原上“羊”一相加,竟創造出一個人皆會意的“鮮”字。不明底細的老外,可能還以為這是文字遊戲。殊不知,此乃祖先嘔心瀝血的結晶。


筆者並非美食行家,一個偶然的機會與文友合編一部關於飲食文化的電視劇《南宋菜與八卦樓》,有幸品嚐了一道具有食療性質的南宋名菜“鱉蒸羊”。“鱉”,為魚中之珍,屬江南滋陰大補菜,可腥味甚濃。“羊”,系肉中之貴,王安石《字説》解釋“美”時稱“從羊從大,大羊為美”,古代從皇宮到民間均以品羊肉為美事,但羶味頗烈。奇怪的是,只要將羊肉塞入鱉肚一起蒸制,馬上就腥去羶除,恰如“鮮”字的形象再現。


“鮮”字的誕生啓發我們,萬事萬物之間組合的重要與必要。
想到“東學西漸”,諸如,絲綢的西傳、造紙術的西傳、印刷術的西傳、磁學的西傳、冶金術的西傳、造船術的西傳、橋樑術的西傳、中醫學的西傳、兵法的西傳、茶道的西傳、農業術的西傳、園林術的西傳……東方文明為西方送去新鮮“血液”。

想到“西學東漸”,諸如,哲學的東傳(《辨學啓蒙》《穆勒名學》等),數學的東傳(《幾何原本》《數理精藴》等),地理學、地質學的東傳(《萬國全圖》《地學淺釋》等),生物學的東傳(《獅子説》《天演論》等),應用科學及技術的東傳(《遠西奇器圖説》《泰西水法》等)……西方文明為東方送來新鮮“活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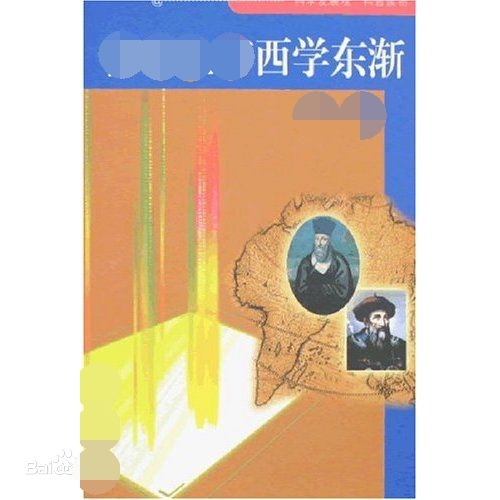
其實,東西融合互補而保持各自獨立個性,是人類社會的巧奪天工。
曾記得,在我國民歌向何處去的十字路口,出現了一種“混合”歌曲,它彙集中國民歌和西方搖滾樂為一體,在保持“信天游”婉轉動聽等本質屬性的同時,汲取了搖滾樂的高節奏,從而將漢語音律的長短平仄韻味美的優勢發展到最大限度,使聆聽者莫不嘆為“聞”止。


曾記得,1919年1月15日,中國人欣喜若狂地迎來了兩位陌生的客人德先生和賽先生。這兩位來自西洋的先生為中國的啓蒙運動、新文明理想帶來了黎明的曙光,熱血青年高舉“民主”和“科學”兩大旗幟,向封建禮教以及封建專制思想猛烈開火,現在北大校園裏還有當時歷史背景下的產物“德莫克拉西”和“賽因斯”的雕塑。

當然,“萬事萬物之間組合的重要與必要”之前提在於“有機”。
所謂“有機”,就是 事物的各部分互相關聯協調而不可分,就像一個生物體那樣。這從華夏文字瑰寶之“合體字”之造字可見一斑。
段玉裁《説文解字注》有道:“析言之,獨體為文,合體為字,統言之,則文字可互稱。”獨體者是以筆畫為直接單位構成的漢字。合體者是由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單個字組成的漢字,從其分合間可窺極妙之意趣,而“鮮”僅屬數以萬計之大家庭之一員,諸如:“休”字,取“人依樹而息”之意;“尖”字,上“小”下“大”為“尖”;伐”字,表示以“戈”伐“人”;“取”字,從“又”從“耳”,表示捉取一個人……

“有機”是一種境界。
王國維《人間詞話》有言:“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必經過三種之境界。‘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眾裏尋他千百度,回頭驀見,那人正在燈火闌珊處’,此第三境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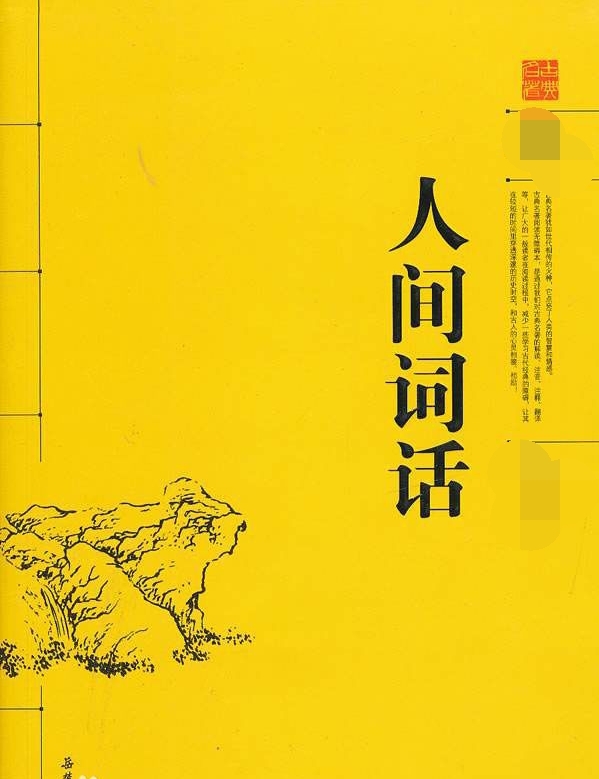
遠離“有機”而無“境界”的“組合”不啻“烏合”。
史載:唐人王昌齡一次夜航於海,途徑一常沉舟滅頂處突然風興浪作,大驚失色之餘急令僕人以隨帶備食之小魚祭龍王,須臾風平浪靜,“靜影沉璧”中一大魚躍於甲板,嗜美食之詩人欣喜若狂,命庖廚立馬趁鮮烹飪,下人剖開魚腹,見方才所拋之小魚居然在焉,異之,“七絕聖手”王少伯遂將此菜名之為“懷胎鮮魚”,嗣後菜名不脛而走,成天下庖廚競相烹製之名菜。
古之名菜大多是文化名人“紙上談兵”的產物。古代的庖廚少有文化積澱者,清乾隆年間名廚、袁枚家的掌勺大廚師王小余繫個例。其不光烹飪手藝高超,燒的菜餚香味散發“聞其臭香,十步以外無不頤逐逐然”;而且有豐富的理論經驗,袁枚的《隨園食單》有許多方面得益於王小余的經驗總結、真知灼見。王小余死後,袁枚專門寫了一篇《廚者王小余傳》紀念這位優秀廚師。王小余是中國唯一一位死後有傳的古代名廚。唯因“唯一”,是故餘者往往只有“依葫蘆畫瓢”的份。換言之,在飲食文化領域,常常文人出“理論”,庖廚出“實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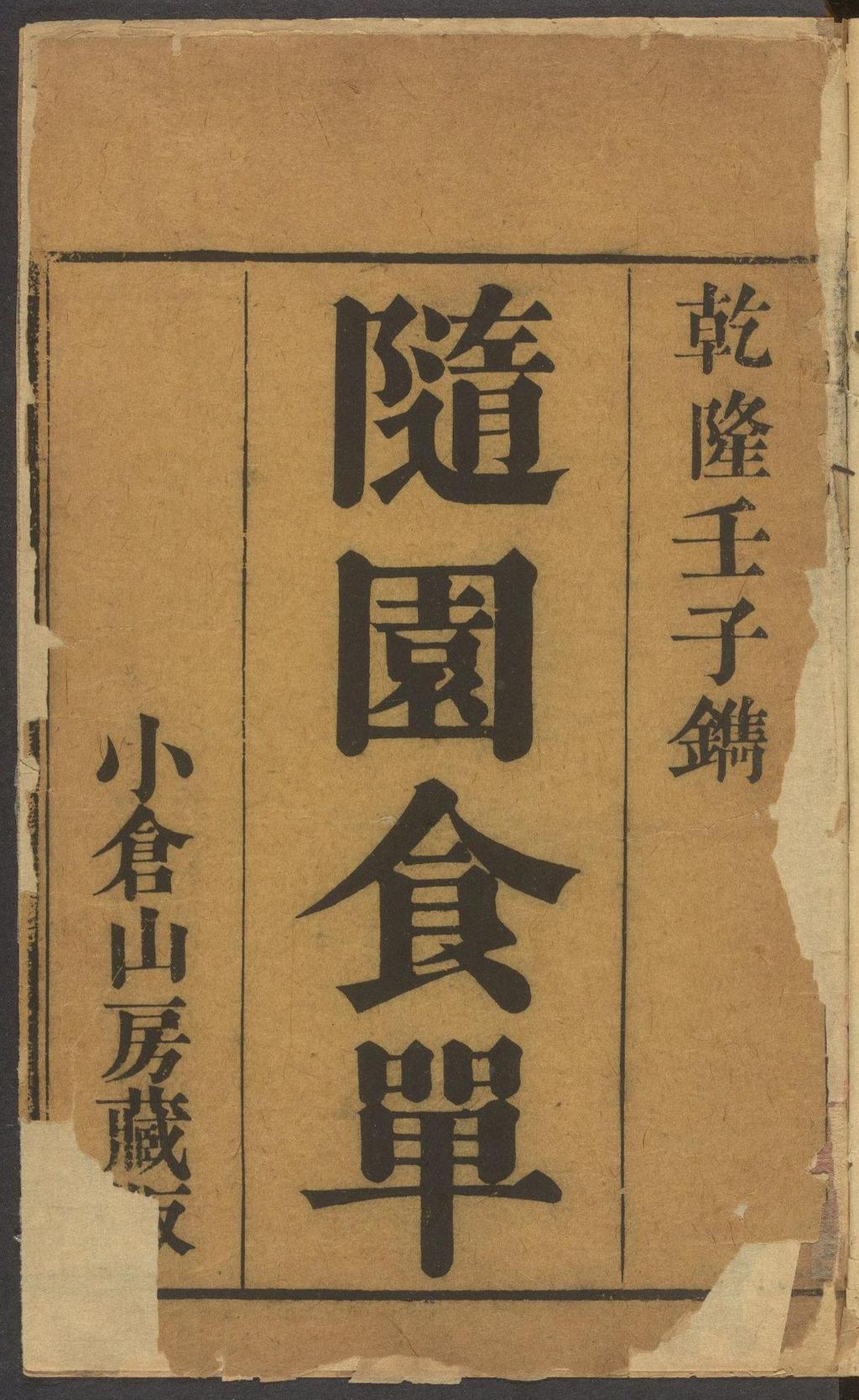
遺憾的是,飲食是一種文化,烹飪是一門科學,真正上得了門面的好菜而如“鱉蒸羊”者,其配料應該是大有講究的,絕不會有類“懷胎鮮魚”那“拉郎配”樣的偶然甚或“荒唐”之“鮮”。
任何事物,一旦上升至“文化”、“科學”甚至“政治”之“境界”且“理論”與“實踐”結合,必然有相通之處。
老子《道德經》有云:“治大國若烹小鮮。”睿智的李耳用了一個經典的比喻,讓人切切實實感覺到統治國家的君主與烹飪菜餚的庖廚亦十分神似:“小鮮”肉嫩不斷翻身“烹”而煎烤容易爛而弗“鮮”,“大國”輿情複雜不斷“治”而折騰容易亂而不穩。

哲人的偉大在於能夠預測未來。
君不見,近一個世紀過去了,作為民主的德先生眼下卻正面臨着一場前無古人的政治考量——或激進論、或漸進論,或災難論、或模式論……不一而足也?此與其説是民主的信任危機,弗如講是文人的“烹小鮮”的悲哀!
“籠天地於形內,挫萬物於筆端”之際,一個“鮮”字給人的啓迪應該是無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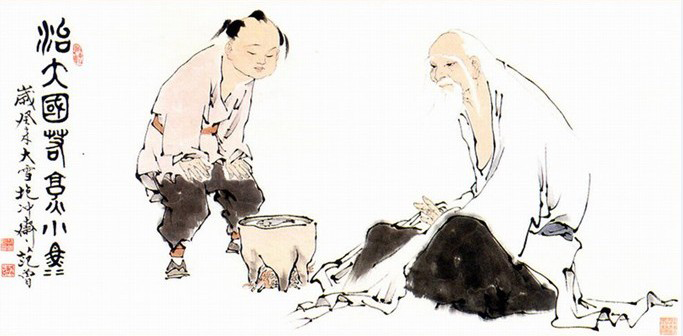
【附】當年《杭州日報》刊發的原文——
從“魚+羊=鮮”説開去
金新
中國漢字的奇妙之處,恐怕在於巧妙的表意功能。諸如泱泱水中“魚”與茫茫原上“羊”一相加,竟創造出一個人皆會意的“鮮”字。不明底細的老外,可能還以為這是偶然的文字遊戲。殊不知,這是我們祖先嘔心瀝血的結晶。
筆者並非美食行家,日前與文友合編一個關於飲食文化的電視劇,有機會品嚐一道具有食療性質的南宋名菜“鱉蒸羊”。“鱉”,為魚中之珍,屬江南滋陰大補菜,可腥味甚濃。“羊”,系肉中之貴,據説王安石《字説》解釋“美”時講:“從羊從大,大羊為美。”確實,古代從皇宮到民間均以品羊肉為美事,但羶味頗烈。奇怪的是庖廚無意間將鱉羊一起蒸煮,馬上腥去羶除,恰如“鮮”的形象再現。
“鮮”字誕生啓發我們,萬事萬物之間有機組合的重要與必要。像現實生活中“紅花綠葉”、“郎才女貌”這類也不勝枚舉。窈窕淑女穿着新穎得體的時裝,其貌更加嫵媚動人;陝北信天游配上節奏明快的搖滾樂,其音更加激越高亢;傳統中醫輔以現代科學儀器,其術更加高超卓越。
“近水樓台先得月,向陽花木易為春”,妻子有幸在某省級醫院供職,愚為“白衣天使”之夫,時時感悟到“鮮”字之類的“組合效應”。且不説桌上的豪華水瓶曾與金銀花露作伴,盤中的高級咖啡杯曾與感冒通為侶,櫥內的漂亮米箱曾與板藍根同心;連那裝飾櫃裏各具形態的各種點綴物,亦曾與各類中成藥喜結秦晉。
人到中年,親眼目睹午時茶的外包裝,從兒時土頭土腦不登大雅之堂的塑料袋,發展到今天的圓形、腰鼓形、橢圓形、竹節形的玻璃器皿,真是感慨萬千。俗話説:“人要衣裝,佛要金裝。”藥物儘管擔負着救死扶傷的人道主義重任,但作為商品,或者説一種特殊的商品,仍有美化外觀之必要。記得一位著名的經濟學家説過,商品的梅花程度,反映了一個國家的文明程度、管理水平、經濟態勢。可是面對這一堆惹人眼花繚亂的包裝,我心中總有絲絲疑慮。人非聖賢,尤其對於那些“隔三差五醫院跑,從小到老藥裏泡,有病沒病不重要,反正公家掏腰包”的人來講,一旦“魚與熊掌不可得兼”,到底如何取捨?藥品耶?器皿耶?治病耶?擺設耶?叫人難以猜度。
日前夜讀閒書,瞥見一則遺聞軼事。明朝醫藥家李時珍在撰寫《本草綱目》之際,亟需收錄一種名曰“巴豆”的中草藥。本着對後人負責的態度的,他親自服藥試驗,不料發現一個奇怪的現象:少服能治癒腹瀉,立竿見影;多服會引起腹瀉,難止難息。絕然相背的“巴豆現象”,似乎又給我們一點啓示,萬事萬物之間是有所制約的,其貴在恰倒好處。倩女刻意妝扮容顏,不免“東施效顰”;民樂過於西化音律,不免張冠李戴;中醫完全依賴器械,不免生存危機。同理,藥物過於求裝飾,不免本末倒置。
如今社會上“包裝”一詞很是盛行,可那絕不應該是圖浮華表面的代名詞。如果不將內裏的質地烘托出來,喪失的便是本真。小到藥品,大到社會,莫不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