罵這麼久,才知道冤枉它了......_風聞
影探-影探官方账号-美日韩剧资深鉴赏员,电影专业老司机2022-05-14 14:17
作者| 甜茶
來源| 影探
保質期最長的是什麼?
如有候選,斗膽提名國產劇。
國劇不差,國劇牛逼。
這話説出來,估計要惹人發笑。
但。
如果,把主語換成“國產老劇”呢?
別不信。
今天咱就聊國產老劇,不拘泥於類型,不限制於內容。
回望,對視。
你將發現,不管過去多久,老劇不老。
>>>>兩性儘可言
百無禁忌,口無遮攔。
國產老劇多少帶點“狂”。
比如《暖春》,拍得感人,看得催淚。
劇裏卻有段,香草媽侃了香草爹一句,蹦出來仨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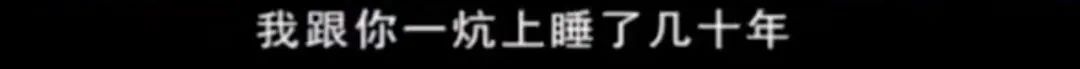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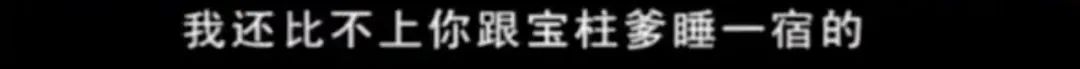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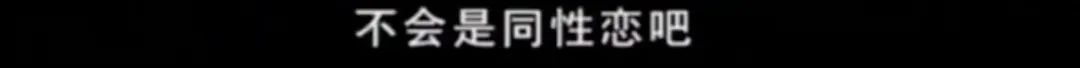
嚯,這是可以説的嗎
再如《武則天》,1995版。
講的是權力、情慾、心計。
武媚娘入感業寺,被尼姑覬覦,尼姑語言赤裸,動作大膽。
她告訴武媚娘,男人靠不住,青燈古佛,不如你我好作伴。

2000年,《大明宮詞》。
早就寫過,合歡那一跪。
男僕愛上皇子,跪叩的是皇權,臣服的是自己。
愛是合謀是忤逆,是我既出此言,便不懼天理。
嗯,央視首播,也是勇。

螻蟻託千斤,兩性儘可言。
搖擺、反擊、打壓、共存,透視女性與男性間的攻伐。
《情深深雨濛濛》,陸振華被九姨太雪琴氣成土撥鼠。
雪琴控訴:
“你有多少小老婆,我為什麼要為你守身如玉,我又不需要貞節牌坊……”


你既然玩女人,那我就找男人。
不用道德拷問苛求自己,快活!
但。
女性最困頓的地方,在於對男權的反抗,是對男權的模仿。
所謂大女主,常是女肖男。
怎麼辦?
辯。
1992年,《編輯部的故事》,某集講“妻管嚴”。
李冬寶和餘德利倆男人説婦女能頂半邊天,總不能把另半邊天也搶了吧。
話裏話外:平權可不是特權哦。
戈玲説,這事兒上我保持中立。
牛大姐“喲”一聲,臊戈玲一臉:

瞧,今天輿論場上的話術,都是老劇講剩的。
兩性話題,燙手,要麼雞賊圓滑,要麼諂媚逢迎,犀利者得有被罵的覺悟。
2004年,《中國式離婚》,遭到社會道德批判。
陳道明和蔣雯麗演夫妻,最窒息的婚姻莫過於此。
妻子逼丈夫飛黃騰達,丈夫飛黃騰達又怕他偷吃。
人一有罅隙,便成深淵。
跟蹤、控制、設套,過着過着人的心理就變態了……
你丟了我,我也丟了自個兒。

婚姻被血淋淋提溜到觀眾跟前。
看完就沒了那種世俗的慾望。
被噴三觀不正也好、被質疑厭女也罷,編劇王海鴒説她的創作初衷不過四個字:
一吐而快。
這幾年,我愈發明白這四個字意義重大,它代表個人的創作意志與能言的自由。
巨浪中,書寫是一塊浮木。
>>>> 巨浪可浮游
什麼是書寫?
《我愛我家》有一集,圓圓寫作文。
她寫父母總愛吵架,得分並不高。
爺爺説她沒分清主旋律和陰暗面。
她另寫一篇,開篇是誇爺爺從不嘮叨,父母從不吵架,叔叔從不遊手好閒……語氣肯定確定以及一定。
當事人聽着彆扭。
陰陽怪氣是不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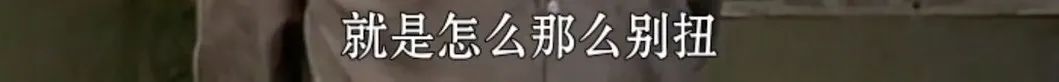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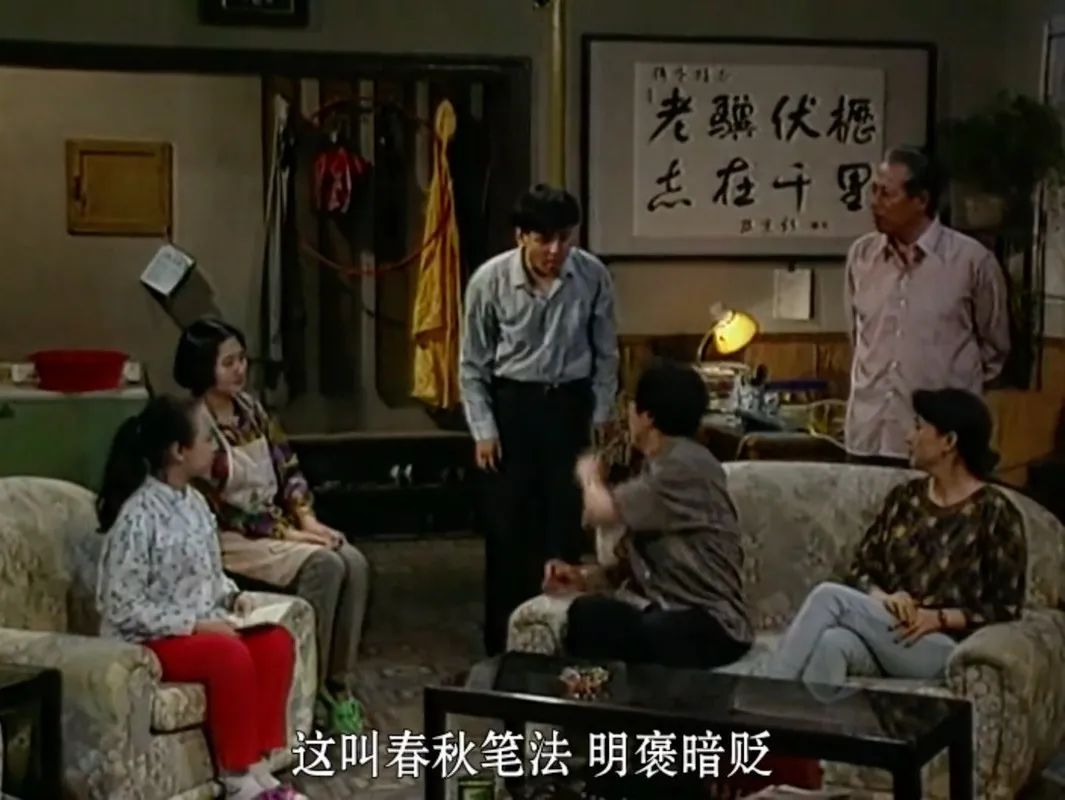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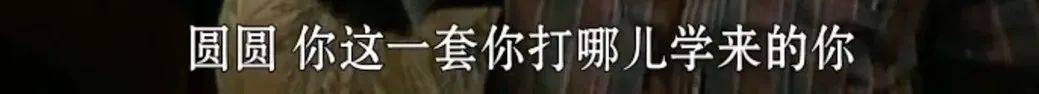
接着往下念。
具體到個人,我家裏有全世界最好的爺爺,關心世界風雲,胸懷寬廣;全世界最好的爸爸,任勞任怨,為國貢獻;全世界最好的媽媽,兼顧家庭與事業,無微不至……
每個人都點頭:
很生動,很貼切,很正確,很感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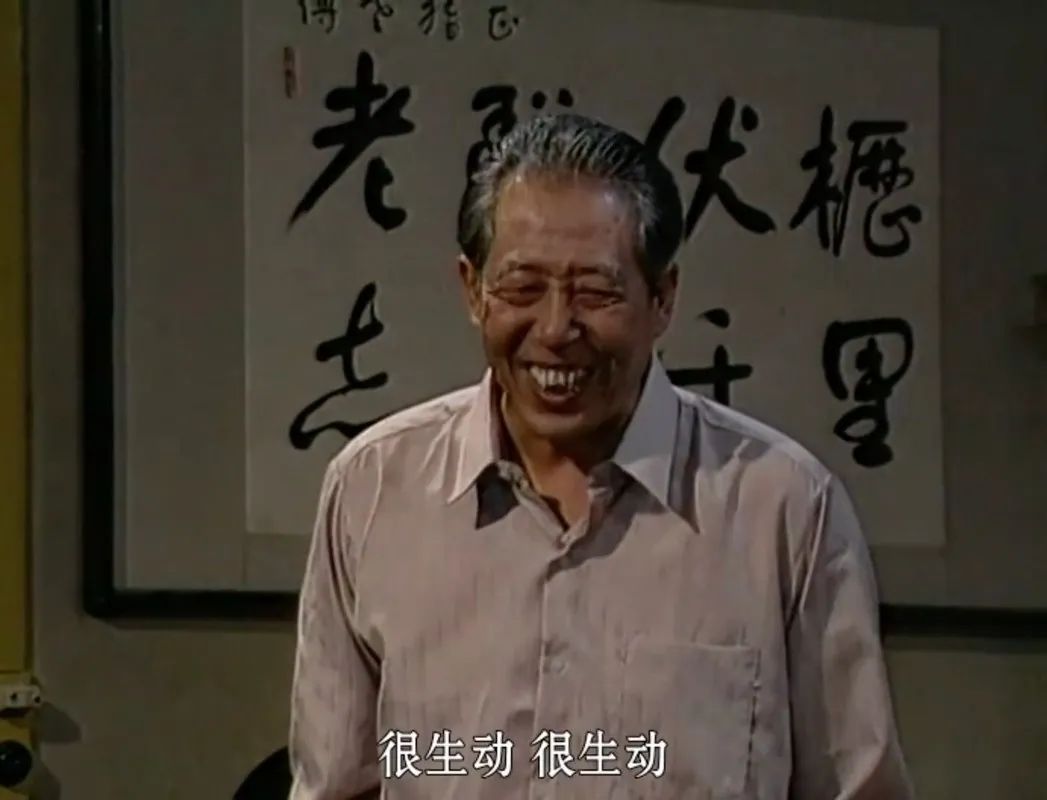



這叫敍述與創作自覺的培養。
如今這樣的“陰陽怪氣”怕是看不到了。

2008年,《天道》是書寫的叛逆者。
**“那種企圖説些什麼的狂妄野心”,**有人如此評價道。
它是如此怪誕離奇的存在。
依託於商戰,講殺富濟貧,講道玄佛法,講民族文化。
王志文演男主,一個冷眼觀世的修行者。
他否定傳統:
“還債報恩,讓每個人直不起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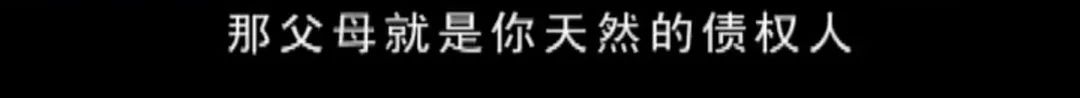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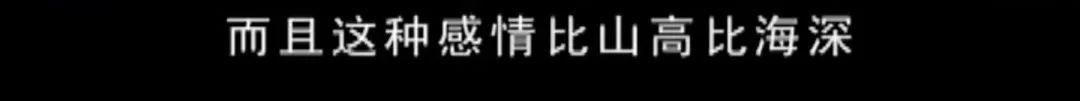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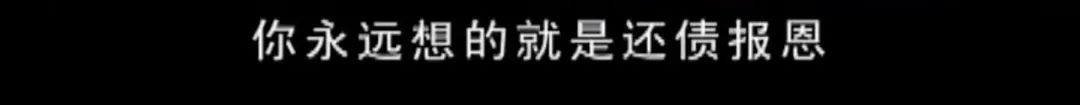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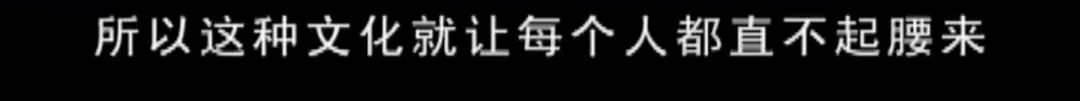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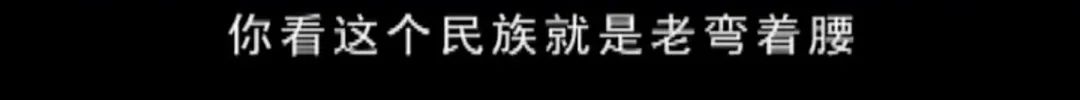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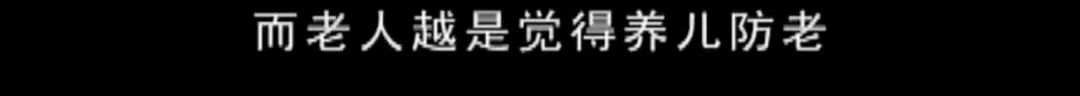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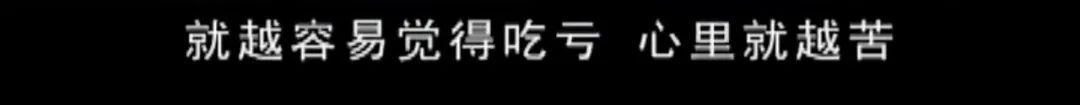
他懷疑道德:
“一個民族最強調道德的時候,正是這個民族道德最淪喪的時候。”
他認為文化屬性塑造個體與民族命運。
強勢文化是遵循事物規律,弱勢文化則依賴強者的道德破格獲取。
我反覆咂摸,而知其味。
知無不言,言則必有物。
有些台詞,現在看來,簡直直白到令人心驚膽戰。
不屑於正確,不求於追捧。
這是老劇的清高,老劇的骨氣。

老劇中的叛逆者很多。
以《外鄉人》《生存之民工》《山城棒棒軍》為代表的“職場”劇,以《中國刑偵1號案》《征服》《命案十三宗》為代表的黑色犯罪劇……評分皆在9以上。
那種表達欲的噴發,那種對現實的體察。
那種直愣愣的勇氣,那種赤條條的敍述。
令人歎服。
甚至姜文主演了一部劇,名為《北京人在紐約》。
近乎咬牙切齒地迎上了異國他鄉的耳光。
放在今天,都算得上敏感。

好的劇,書寫一種時代心態。
側面是狂躁的。
正面是温順的。
>>>>人生多悵惘
一些平和無害的劇,亦有千鈞之力。
書寫的是小確幸、小幽默、小傷感。
《武林外傳》裏,郭芙蓉説她要的很簡單:
一日三餐,輕食低卡,奶茶火鍋,薯片零食,穿有普拉達,化妝要有辣妹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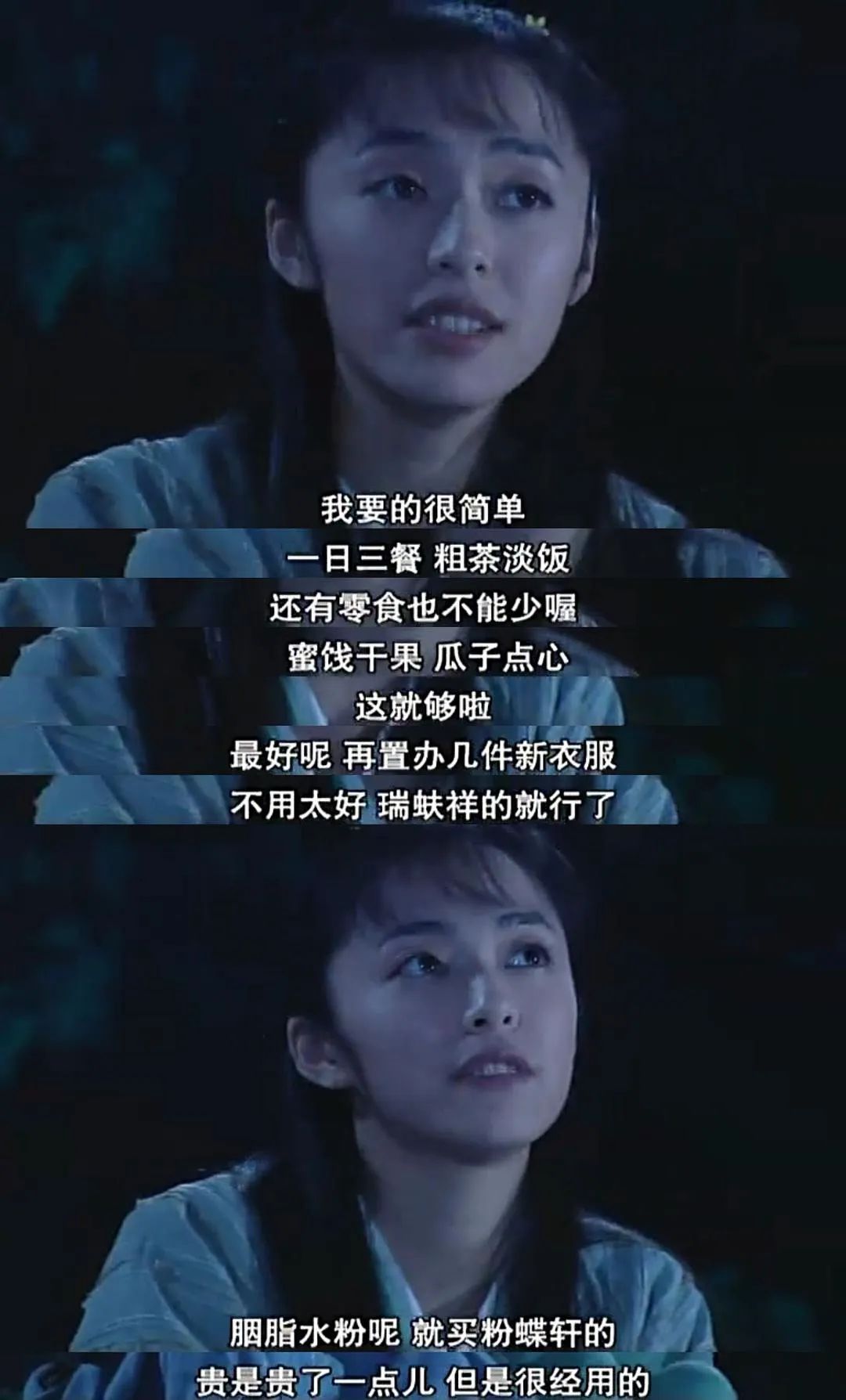
温飽下,有餘力且心甘情願地落入消費主義的陷阱。
有地兒賺,有地兒花。
足矣。
卻難。
堂堂盜聖,通天的本事,闖過皇宮,去過御膳房偷過粥。
心願卻如你我:

“只要給夠加班費,當牛做馬無所謂”,這是老白的原話。
“我出來打工,我不惦記錢我惦記什麼?”
就是就是!

呂輕侯三歲識千字,五歲背唐詩,七歲熟讀四書五經,八歲時精通詩詞歌賦。
二十五歲?
窮得連飯都吃不飽。
一樣一樣。

佟湘玉萬里出嫁成寡婦,郭芙蓉遠征江湖當雜役,白展堂心驚膽戰,呂輕侯空有學識,李大嘴痴心不得“惠蘭惠蘭惠蘭……”
《武林外傳》有種閒庭信步式地調侃。
調侃狗遭世界烏煙瘴氣世事不如人願。
《武林外傳》也有一點即化地傷感。
佳節久從愁裏過,壯心偶傍醉中來。
“就讓我做一個堂堂正正的廢物吧。”

活着到底有勁沒勁?
張大民説:
“我覺得活着挺來勁的啊,甭説別的,光這一天三頓飯就特別來勁,早上弄碗小米粥,來倆油餅,切點細鹹菜絲兒,中午來碗炸醬麪,拍幾瓣蒜擱裏頭一拌,再弄點醋… …”
出自《貧嘴張大民的幸福生活》。

張大民12歲,父親被爆炸的鍋爐燙死,底下是年幼的弟弟妹妹。
等熬到個個成人,母親得了老年痴呆,小妹得了白血病,沒了,小妹夫因公殉職,沒了,大妹兩口子天天互毆,弟弟性格懦弱……
一大家子擠十幾平房子。

兩對夫妻睡上下鋪,辦事都得悠着點。
張大民媳婦兒懷了,為了生孩子,違規擴建一間屋。
有棵樹不能砍,便穿屋而長,劈開雙人牀。
好傢伙,還能磨襠,真的給整樂了。

孩子生下來,取名叫張樹。
一種苦澀的幽默……
我想起今年五四青年節,莫言寫給年輕朋友的一封信,叫《不被大風吹倒》。
是個隱喻。
信裏寫道:
我驚問爺爺:“那是什麼?”
爺爺淡淡地説:“風,使勁拉車吧,孩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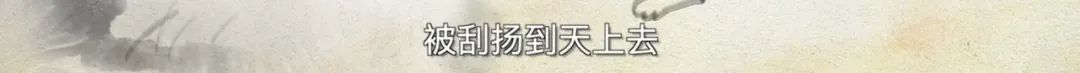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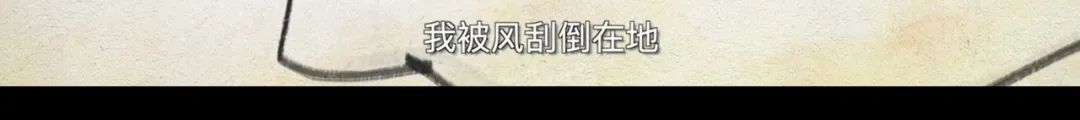
2000年,《貧嘴張大民的幸福生活》播出,收視率攀至70%。
是新千年伊始,一種集體情緒共鳴。
放在今天,這樣的收視率已不可能。
我們擁有更多劇,擁有更多信息源,與生活疊加出更分裂的異見。
感動與憤怒間有隔音壁。
共情成為太難發生的事。

我仍能記起,暑假要上輔導班,下午快上課了,我窩沙發上邊看《武林外傳》,邊掐着表準備衝刺。
《武林外傳》第八十集,字幕寫“前八十回,完”。
但沒有等來後八十回。
最後一集,凌騰雲問他們怎麼認識的。
佟湘玉説:“那是一個很長很長的故事,從哪兒開始講起呢……”
大家咧着嘴笑,眼裏都是淚,説“再見再見”。
鏡頭最後定格在那塊牌匾——同福客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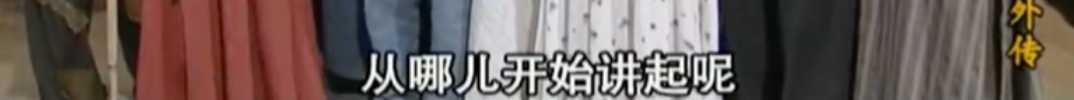
片頭曲的詞是:
“嘿,兄弟,我們好久不見,你在哪裏;嘿,朋友,如果真的是你,請打招呼…….”
過盡千帆皆不是,你我曾是有緣人。
我們身體的某一部分,是由看過的老劇塑造組成。
寫出《我愛我家》的編劇粱左,痴迷《紅樓夢》。
某集,小晴表妹説:
“雖然今天我們是初次見面,但好像很早就認識了,好像故友重逢的樣子誒”。
如賈寶玉初見林黛玉:
“這個妹妹,我見過。”


翻出老劇,再講老劇。
每一次,像久別重逢。
你啊,我見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