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繆的藥方"_風聞
秦朔朋友圈-秦朔朋友圈官方账号-2022-05-14 12:07

水姐 | 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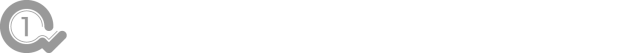
最近的世事,有強烈畫面感的是:活魚進不了小區,送貨小哥一條條在門口徒手摔死;封控樓棟開封,舉行剪彩儀式,放《拉德斯基進行曲》;年近60歲男子拖着癌症死去的妻子的骨灰徒步7小時走到高鐵站……
我想起加繆的“怪誕身體書寫”,用病態、扭曲、異常,與周圍環境格格不入的身體,充當“荒誕感”展開敍事的手段。
對哦,沒有哪一年像今年一樣“身不由己”。近幾年,卷、躺、潤、跳,其實都是對身體的敍事。身體似乎就是生活本身了——
先是機會少了,所以捲起來;
不願意卷的,就躺平,或者潤(逃);
逃離不掉的就在房產證除去公攤面積裏像劉畊宏那樣跳着發泄情緒;
我們這些年,都沉浸在身體的掙扎中了,其實都是內心掙扎的呈現,身體果然是最誠實的。
跟多年創業的閨蜜聊,她也在裁員調整,縮減各種業務,也拓展新的思路。她説,小企業主們,大多都在賣房賣車,扛着。對,你看,扛也是個形象的身體畫面,像推着巨石的西西弗斯。
卷、躺、潤、跳、扛之外,還有什麼可能性啊?其實,人們一直都在找尋,從來不曾放棄探索,有這股意志在日常中堅持,便是幸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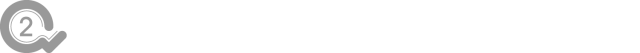
加繆(1913-1960),阿爾及利亞人。上個世紀法國最著名的文學家之一,諾貝爾文學獎最年輕的得主之一。47歲的時候因車禍去世。他曾説,車禍是最荒誕的死法。
他説,“對於人的命運,我是悲觀的;但對於人,我則是樂觀主義者。”意識也是可以平衡的。
他的小説《局外人》《鼠疫》《墮落》等,包含哀傷深沉、荒誕反抗;而他的散文《西西弗神話》《反抗者》《婚禮集》《夏》,則和善温情,意氣風發。人本身也要具有開放性,容納不同的見解、氣質,甚至是包容完全相反的東西。
他善於塑造悲劇英雄,這種命運的反抗者。比如在《鼠疫》中,鼠疫其實象徵着人類無盡的痛苦和死亡的恐怖,這是人註定的命運。面對不可改變的困厄,有的人可能會自暴自棄、屈膝服輸、隨波逐流、虛度一生;而有些人則選擇對抗無法選擇也不能逃避的命運,那種自始至終的不屈,將會贏得與命運之神平等對視的力量,自豪地度過任何壓迫性的、艱難的、逼仄的片刻時光。
**真誠地面對自己,做好自己該做的事情,積蓄自己日復一日的力量和鬥志,是加繆給我們的藥方。**永遠記住,低落的時候,是整理和積累最好的時刻。你終於知道自己需要什麼了,你要把自己還給自己了。當人們要面對同一種災難環境壓力的時候,人們也會緊密結合在一起抵抗鼠疫,彼此安慰,相互取暖,前赴後繼,這種患難中的真情,也尤其可貴。
“必須要做的,就是該認清的事情要認清,然後驅除無用的疑慮,採取適當的措施。……日常工作才是可靠的,而其他一切都不過是繫於毫髮之上,一個難以察覺的動作就能斷送掉它們。不能糾纏在這些上面。要緊的是把本位工作做好。”——《鼠疫》
柳鳴九説:加繆的“荒誕-反抗”的哲理體系成為在法國二十世紀精神領域與薩特的“存在-自我選擇”,馬爾羅的“人的狀況-超越”哲理交相輝映的三大靈光。
**所以,加繆的藥方,恐怕就是不斷克服自己的侷限性和悲觀,始終審視和保留自己的樂觀。**他的信仰,是對人類的熱愛,他的原則永遠是尋求心靈上的力量。任何困難下,懷疑下,絕望下,依然熱愛。沒有絕望過,不會真的懂生活,愛生活。
他筆下的人物,都不信神,信自己的行動。死亡的不可撤銷性,反而賜予他們更多的自由和行動力。上帝的不過問,反而使得他們更加熱愛塵世。
“塵世啊,在這神靈逃離了的偉大廟宇裏,我所有的偶像都是隻有泥塑的雙腳。”面對人與世界的荒謬,唯一的得救之路只可能在塵世之中。怎麼辦呢?忍受不斷的磨難,憑的是深切關愛。要始終相信,人內心裏值得讚賞的東西總歸比應該唾棄的東西多。
他17歲患重病,22歲經歷痛苦的離別,失去了《阿爾及爾共和黨人報》被流放到巴黎。1942年出版了《局外人》,29歲的他成了名人。加繆出生成長於北非,是阿爾及利亞人,也是法國人。北非,總是有明媚的陽光、温暖的海水,所以他始終保留着他的暖。《局外人》裏的主角,默爾索拒絕為自己做任何辯護,懷着熱愛走向斷頭台。他的理念是,人生在世,永遠不該演戲作假。《鼠疫》裏的裏厄,始終在日復一日地治病救人。荒誕總是令人喪,但暖色,也是不會丟的,大概他相信,人類會自我康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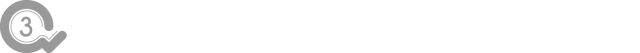
《鼠疫》發表於1947年,出版當年就獲得法國“批評家大獎”。小説的梗概是:
裏厄是一位好醫生,也是一個好丈夫、好兒子。不過妻子患了重病,被送去了外地療養院。不久,奧蘭城(阿爾及利亞的第二大城市)裏出現了大量鼠羣死亡的現象,裏厄發現每天都有人死於相同的疾病。在他的堅持下,政府承認鼠疫襲城,宣佈全城戒嚴封控。來奧蘭旅行的塔魯和小公務員格朗主動投入戰鬥。但兩人都染上了鼠疫。就在快抗疫成功之時,塔魯失去了生命。來奧蘭採訪的記者朗貝爾和帕納魯神父,在漫長的過程中,逐漸意識到自身的侷限,後來也全力抗疫。裏厄的妻子在療養院死了,他還留在奧蘭救生命。最終在全城人的努力下,鼠疫被制服了,生活恢復常態。但其實,只有裏厄知道,鼠疫並沒有消失,它只是躲起來了。
裏厄會説,習慣於絕望,比絕望本身還要糟糕。既意識到生存的慾望,又意識到死亡的命運,這兩者,都可以存在於同一顆人心。現在的傳播方式,讓我們觀點鮮明、犀利、潑辣、矚目,注意力才直接代表了利益,但其實寬容對立,彌合針鋒相對,防止進一步撕裂,才有更高的福祉。
“沒有對生活絕望,就不會真的愛生活。”
“真正的救贖,並不是廝殺後的勝利,而是能在苦難之中找到生的力量和心的安寧。”
裏厄是孤獨的,親人間的那種相互關心和依靠他是擁有的,但他內心的孤獨處境是改變不了的。外地來的旅人塔魯,跟他一起在抗疫過程中,經歷了很多事情,大家心意相通,相互安慰。最經典的場景是兩人一起去大海里游泳。不過最後,塔魯死了,裏厄重歸孤寂。塔魯注射血清後依舊感染瘟疫而死,且“鼠疫桿菌永遠不死不滅……也許有朝一日,人們又遭厄運。”所以,你知道嗎?人類當一次兩次英雄根本就不夠,各種疫情還是會發生,各種魔幻還是會發生,重要的是,人人都有一顆彼此拯救、幫助的心,喚出人們這樣一顆克服世界中兇惡勢力的不斷嘗試的心。
加繆喜歡塑造小人物悲劇英雄。大人物悲劇英雄,往往會建立豐功偉業後,最後抵不住命運捉弄和毀滅性力量而消亡。而小人物悲劇英雄,則是以自己的微薄力量和微弱之軀,默默與不可挽回的命運進行抗爭,明知不可為而為之,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雅斯貝爾斯曾説,悲劇有兩個層面,一個是所有人的生命、活動、功業和功勳最終都註定要遭逢毀滅,意識到了這件事本身就是悲劇;二是現實世界四分五裂,連真理也是如此。人們用“真理”反對“真理”,用“正確”反對“正確”,並且為捍衞他自己的正當主張,不僅必須反對非正義,而且還反對其他真理的正義主張。
你堅持你的,我堅持我的,我們必然是孤獨者,但我們至少應該抱有善念和柔軟,去緩解一些衝突。**文明的下級目錄是價值觀,價值觀在工作和生活中是各種各樣的“執行標準”。**其實很多時候,人與人之間的衝突是堅持的“標準”的衝突。你覺得這樣行,我覺得這樣不行,在市場上是價格的差異,在非市場上是對規則掌握、理解和認知的差異。
其實,人就是囚禁在一種狀態和規則中的。“人們從早到晚地工作,而後卻把業餘生活的時間浪費在賭牌、上咖啡館和閒聊上,這種情況,看來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直到有一天,不明原因的疫情來襲,人類突然被拋入到一個極端處境內,加繆想要“用另一種囚禁生活來描繪某一種囚禁生活,用虛構的故事來陳述其事”。
“鼠疫”具有三層意藴:即表層的,字面意義上的;象徵的,時代意義上的;寓意的,絕對意義上的,瘟疫就是對現代人生存狀況和精神世界的陌生化書寫。
身體被限制後,物理和精神上的雙重隔離,使奧蘭居民對孤獨痛苦的生存現狀有了切實的體會,逐漸開始反思之前的生活,意識到了咖啡、閒談、禮拜活動掩蓋下的一片荒蕪。
是啊,你到底需要什麼?你到底擁有什麼?其實想這些問題是很痛苦的。人和組織都不會主動變好,除非不得不變好。一個人能在鼠疫和生活的賭博中所贏得的全部東西,就是知識、記憶、反思和覺醒,未來還是要靠行動,靠自己的行動。
薩特生前跟加繆決斷,在他去世後,卻盛讚他:在本世紀頂住了歷史潮流,獨自繼承着源遠流長的警世文學。他懷着頑強、嚴格、純潔、肅穆、熱情的人道主義,向當今時代的種種粗俗醜陋發起勝負未卜的宣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