閆宏秀|數據時代的道德責任解析: 從信任到結構_風聞
探索与争鸣-《探索与争鸣》杂志官方账号-2022-05-17 22:00
閆宏秀|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與科學文化研究院教授
本文原載《探索與爭鳴》2022年第4期
非經註明,文中圖片來源於網絡
數據是一種新型的生產要素,以數據為紐帶的“東數西算”工程為數字中國的建設注入了強勁的動力,基於數據的數字化轉型已成為全球發展的一個重要趨勢,基於數據的人類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構建被視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基於數據的社會形態構想正在成為人類社會發展的一種未來樣態。就我國而言,近年來,旨在有效激活數據要素潛能、充分發揮數據作為新生產要素關鍵作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數據安全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信息保護法》以及來自不同省市、不同行業的相關政策法規相繼出台。一系列政策法規的出台一方面説明了數據所具有的重大戰略意義,另一方面也反映出關於數據要素的理論研究亟需加強。如關於數據的本質、倫理問題、經濟價值、法律地位、治理等的研究就是當今社會的熱點與難點,而責任問題則伴隨人類社會的數據化與數據的日益智能化成為備受關注的焦點。
特別是當人類基於數據科學與數據技術進行認知以及作出判斷與決策等時,分佈式數據的聚合及其與人類的融合所帶來的後果是否可歸因或可追責到數據,**數據是否有承擔道德責任的義務,數據承擔着何種責任又是如何來承擔的,諸如此類的問題也相伴而至,併成為了技術倫理學研究的新論域。**如同漢斯·約納斯(Hans Jonas)在20世紀80年代針對當時的技術發展而展開對責任的反思一樣,面對數據科學與數據技術在當今社會中所產生的重要效用,我們同樣也需要對道德責任予以進一步的反思。

對數據的“信任”與道德責任的“轉移**”**
數據科學與數據技術因其對人類的生活方式、生產方式、思維模式與未來等的全範圍塑型而引發了諸多討論。維克托·邁爾-舍恩伯格(Viktor Mayer-Schönberger)、伊恩·艾瑞斯(Ian Ayres)、尤瓦爾·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等在論著中展開了關於數據的多種解讀。其中,**數據主義(dataism)將宇宙視為 “由數據流組成,任何現象或實體的價值就在於對數據處理的貢獻”。**這種觀點一方面充分彰顯了數據科學與數據技術在人類社會中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則將世界萬物的價值囊括在數據之中。
(一)世界的數據化與人類對數據的信任緣起
毫無疑問,人類正在通過數據科學與數據技術將人類社會中的諸多事物與事務予以表徵。這種表徵既包含人類對世界萬物認知的數據化,也涉及人類自身生理、心理等的數據化。基於數據的人工智能、物聯網、身聯網、數字經濟、數字人文、數字政府等將人類社會的方方面面與數據緊密地關聯在一起。從本體論的維度來看,世界被視為是由數據構成的,即萬物皆數據的觀念湧現出來;從認識論的維度來看,數據已經成為人類表徵與認識世界以及自我的一種重要方式,在當下,數據自然界和數據自我被視為與傳統意義上的自然界和自我並存的現象;從價值論與倫理學的維度來看,關於數據時代的人類自我評判與認知、關於人類文明的重新界定等打開了關於人與數據的關係、關於人的價值以及數據價值的深度反思,數據正義、數據偏見、數據挖掘、深度學習、數據所有權、許可權、隱私權等的倫理意藴解析成為倫理學的研究對象,數據倫理學作為一個學科分支也正在悄然興起。
事實上,**上述所描繪的人與數據的緊密關聯所呈現出的種種現象不僅僅在於人類對數據的依賴,更多的在於人類對數據的信任。**伴隨海量數據的湧現,以及數據科學與數據技術對數據處理能力的不斷提升,通過對現實世界的模擬而構建虛擬世界的數字孿生技術(digital twin)已經超出了產品的設計和運維,延伸到了非物理對象和流程的分析與監控,信數據得永生、數字文明、數據權利、數據力等觀念進入人類的視野之中。從這些觀念中,可發現人類對數據的不同程度的信任。如,“信數據得永生”這一論斷體現出了對數據的完全或絕對信任。進一步説,依據此論斷,還可推演出若不信任數據,則意味着失敗與錯誤。因此,信數據意味着通向成功與正確,人類也應該且有義務信任數據。若不履行該義務,則就應承擔相應的責任。此時的責任主要指向由不信任數據而帶來後果的追責、問責或曰指責。
與此相映成趣的是,由於信任數據而帶來的後果也面臨着責任的問題。如替代性制裁的懲罰性罪犯管理量表(Correctional Offender Management Profiling for Alternative Sanctions,簡稱COMPAS),因其依據數據智能所作出的預測與現實不吻合而遭受質疑,但這種質疑並非是對COMPAS的完全否定,而是旨在提醒人類注意數據主義所帶來的危害,呼籲人類應當以更負責任的方式來對待數據,警示人類不應當無條件地信任數據科學與數據技術。此時的更負責任既涉及後思性的道德責任,即追責、問責或指責,也包含作為前瞻性的道德責任,即作為義務與美德的道德責任。

**因此,無論是數據主義對數據的完全信任,還是對由於信任數據而帶來後果的追問,都伴隨着道德責任的出場。**雖然道德責任在上述兩種情境中出場的方式並非完全相同,但無論是哪種方式,都是由對數據的信任而引發的。就對數據的信任而言,包括人類究竟該不該信任數據、應該信任什麼樣的數據,以何種方式信任,這種信任的底線在何處等問題。對這些問題進行破解的一條有效途徑是追溯對數據產生信任的源頭。
(二)道德責任問題的出場:信任過程中的“委託”
對數據的信任源自人類依賴數據科學與數據技術來處理原本由人類所完成的任務。事實上,反觀人類藉助數據完成任務的過程,在某種意義上就是人類將自身的部分行為或部分能力委託給數據。這種委託旨在將任務進行委託,而非將人類自身進行委託。但也正是在這種委託過程中,人類將自身的責任也“隨着機器在普通人的生活和工作中的普及,通過機器使行為和責任脱鈎日益成為普遍現象。越來越多的人將失敗的責任轉嫁到機器身上”。上述責任的轉嫁意味着機器在某種程度上被視為一種道德責任主體。
與此同時,數據科學與數據技術呈現出了某種能動性與某種技術自由的特徵,而能動性與自由意志是判斷是否應當負道德責任的兩個基本依據。那麼,機器被視為道德責任主體的原因何在?這種責任轉嫁成立的理由又何在呢?若這種責任轉嫁是成立的,機器與人又分別應該承擔什麼樣的道德責任?
特別是在數據科學與數據技術完成任務的能力在某些方面表現出了超越人類的跡象,其在完成任務的過程中出現了超乎預期的結果或後果時,此時關於數據信任的追問就走向了關於道德責任的追問,更確切地説是人類是否可以將道德責任轉移到數據科學與數據技術?數據科學與數據技術能否承擔責任,承擔何種責任以及對誰負責?在數據已經成為人類社會的一個基本要素的當下,無論是基於人類自願式的主動性數據信任,還是基於人類對技術的長期高度依賴而形成的被動性的或者強迫性的數據信任,事實上對數據信任的探究,都是對人類道德責任轉移的審視。只有當數據具有成為道德責任主體的資質時,人類的道德責任才有轉移的可能。於是,數據時代的道德責任主體界定成為人類不得不面對的問題,而關於此問題的解答可以從數據自身的特質與成為道德責任主體的條件兩方面着手。
數據智能化與道德責任主體
數據科學與數據技術發展的核心重在預測與決策功能,而預測與決策功能能夠得以實現的主要基礎是數據智能化。近年來,數據智能(data intelligence)被視為數據科學與數據技術發展的未來所在,其旨在“從數據中提煉、發掘、獲取有揭示性和可操作性的信息,從而為人們在基於數據制定決策或執行任務時提供有效的智能支持”,並“朝着更自動、更智能、更可靠、更普適、更高效的方向繼續發展”。
(一)數據智能化及其對道德責任主體界定方式的新挑戰
在數據智能化的過程中,數據在與人類的互動中不斷地趨向自主,並逐漸呈現出成為具有自學能力的智能體的趨勢,完成着原本需要人的智能才能完成的任務。如,就人類的決策而言,無處不在並日趨智能的數據使得人類作出決策的這一行為被置於數據背景之中,數據可助推、導引甚或規約人類決策。在當下,從數據在決策中所發揮的效力來看,數據力是構成人類決策力的一個核心要素,但更值得人類關注的是“數據智能應用的終極目標是利用一系列智能算法和信息處理技術實現海量數據條件下的人類深度洞察和決策智能化,最終走向普適性的人機智能融合”。
**在數據時代,預測與決策通常不僅僅是由人類獨立作出的,而是在人類與數據科學和數據技術的交互中形成的。**在數據智能所追求的人機智能融合中,或許人類可以如願以償地保持對機器智能的有效控制,即人類的預測與決策僅僅是基於數據智能,而非高度依賴或受制於數據。但這僅僅是一種可能,且這種可能也頗受質疑。退一步説,假設這種可能就是人類的未來,但我們同樣不能忽視數據智能所藴含的技術能動性與某種技術自由度。基於此,需要對“一個人只能在他行為——派生性的——的後果邊界上承擔責任,因為它是真正自我行動的後果,也即在控制力下自我意圖的結果”作出新的解讀。

智能主體、擬主體、準主體等詞彙的出現一方面體現了學術界對新興科學技術所藴含的巨大力量作出的新詮釋,另一方面對現有的道德責任主體界定方式提出了新挑戰。如關於“某人對某事負道德責任是因為他對某物負責任是適當的,還是因為某人對某事負道德責任所以他對某物負責任”的爭議等。“如果一個實體能對其行動承受道德責任,並具有道德層面的責任,它需要至少滿足如下兩個標準:意向性(intentionality,即形成意向的能力)和實現其意向的自由(freedom)。”在彼得·保羅·維貝克(Peter-Paul Verbeek)這裏,意向性即擁有意向,其意指能動性。那麼,依據上述標準,基於數據智能的數據科學與數據技術是否可以被視為道德責任主體呢?
(二)基於能動性的道德責任主體與數據
首先,從能動性的維度來看,所謂承擔責任就意味着責任主體擁有完成某事的能力,即責任主體與能力或曰能動性相關。“當我們説某個人是一個道德責任的行為主體時,一般就意味着他有足夠的能力對某事負責。”數據智能之所以被稱為數據智能的一個重要原因就在於其擁有預測與決策的能力。
數據分析是數據智能的核心所在,是在人類的需求與其自身的功能共同聚合下進行的,其結果是人類作出預測與決策的必要環節。如,在日常生活中,智能軟件基於用户自身的習慣、喜好、體能特徵、所處環境等數據參數的分析可為用户提供決策選項,可對用户的行為進行預測,進而導引用户的未來行為。在這個過程中,數據的能動性與某種技術自由度不斷呈現。這表現為智能軟件在數據智能的驅動下,既可以滿足人類的需求,也可以導引人類的需求;既可以呈現與分析人類已有的行為軌跡,也可以預設甚或創設人類未來的行為軌跡。特別是數據智能的導引、預設甚或創設能力,將技術的能動性與自由進一步放大。由谷歌所研發的自動機器學習(Auto ML)就旨在將數據的處理、特徵的選取等任務無需人工干預而進行自動化。易言之,智能閉環式的自動機器學習將替代機器學習專家的技能,並擁有完成數據分析任務的能力,技術所具有的能動性可將人類置於該系統之外。
**當這種能動性帶來了人類從未預料或期望的結果時,雖然是數據的這種能動性促成了該結果的發生,雖然人類是處於技術迴路之外且被動接受結果,但是這不足以將數據界定為道德責任主體。是否可以將數據界定為道德責任主體還需要輔助其他的判據。**因為按照傳統的理論框架,道德責任是人特有的一種品質,“人與其他生物的一個重要區別是僅有人能夠對其所為負道德責任”, “儘管人和非人都可能對某一事件負有因果責任,但只有人才能有道德責任”。
(三)基於自由意志的道德責任主體與數據
從自由意志的維度來看,“ 存在責任的唯一真正的形式,它和自身自由行動有關”。當某主體擁有自由意志且其行動是在自由的而非強迫的情景中進行時,才能探討與其相關的責任問題,例如,何為責任主體等。
2018年11月,微軟亞洲研究院在其所發佈的《數據智能的現在與未來》一文列舉了“數據智能技術的未來熱點”,指出“智能代理 (intelligent agent) 技術與數據分析技術的融合是一個重要的方向”,“且這樣的智能體還具有一定的學習能力,能夠通過與人類分析師的對話交流積累特定領域的知識”。這種具有學習能力和擁有與人類進行溝通能力的智能體或許在特定場景中具有自由運作的能力,具有產生出乎人類意料結果的自由能力,但這種自由不能完全等同於自由意志。
毫無疑問,數據科學與數據技術對人類社會的影響使得人類將數據作為自身的一個智能陪伴,數據自然界的出現為人類造設了一個新的存在境遇,數據畫像成為人類自我的又一種表徵方式。但是這些跡象可以説明數據智能可以擁有某種形式的自主性和某種技術自由度,但這並不足以説明其擁有自由意志,能被視為等同於人的自由行動者。

(四)基於可歸因性的道德責任主體與數據
從可歸因性的維度來看,當所產生的結果與道德責任主體有因果性時,道德責任主體才涉及相關的責任。承擔道德責任意味着要追問促使這個結果的原因,即責任的可歸因性。而責任的可歸因性是 “基於行動是我們的能動性表達的這一觀點。我們對我們的行動負道德責任是在僅當我們的行動顯示了我們是作為道德行動者的時候,即當作為我們的目的、承諾或價值表徵的行動確實是由我們引起的時候”。
當數據智能調節人類的決策與預測時,數據科學與數據技術和人類一樣都是參與者,只是參與的程度有所不同。因此,在對此情境中的預測與決策所產生的結果進行道德責任歸因時,該如何對數據的功能進行解析呢?之所以能被歸因是因為主體的能動性及該結果與主體之間的因果性關聯,而數據智能確實藴含着某種能動性,且調節着人類的預測與決策。這種調節可以視為數據與道德責任存在相關性的理由,但關於道德責任是否可歸因到數據科學與數據技術則有待進一步的商榷。
能動性與自由意志一直被哲學界視為考察責任主體的兩個基本要點,即是否具有能動性與是否具有意志是具有責任的必要條件。因此,數據智能化並不意味着數據科學與數據技術可被視為道德責任的主體,即其並不擁有主動承擔責任的資格,但是在被追責的意義上,應將其納入其中,因為數據智能所具有的能動性確實是導致結果產生的一個原因。
基於數據科學與數據技術的分佈式道德責任
對道德責任主體的考察有助於道德責任的釐清。當將數據視為對道德責任進行審度的一個元素時,數據科學與數據技術自身的特質也必須予以考察。數據科學與數據技術可將分佈在不同時間、不同地點與不同主體的數據、分佈在不同領域與不同區域的專家們,以及數據意義上的相關利益羣體彙集起來,形成一個由分佈式的行動者構成的數據之網。
(一)數據科學與數據技術的分佈式特徵所引發的分佈式道德責任
從技術層面來看,數據既是分佈式的散落,也是全球化與網絡化的聚合;既是個體性的獨立呈現,也是集體性的彙集表徵。如在日常生活中,由諸多用户所提供的網絡點評、道路信息等數據雖然是個體性的、分佈式的,但是由這種大量分佈式的數據聚合所帶來的效應確實遠遠超乎其在單個個體層面的效用,並創建出新的效用。其中,與數據的這種分佈式特徵相伴隨的是分佈式道德(distributed morality,DM)和分佈式道德責任(distributed moral responsibility,DMR)。
分佈式道德僅僅指“在一個多代理系統中,道德中立的或者至少是道德上可以忽略的代理間的交互行為能產生的道德行動。在這裏,代理可以是人、人工的,或者是雜合體”;**分佈式道德責任則是基於分佈式道德基礎之上的,旨在對分佈式行動的道德責任進行釐清。**例如,將某人存留在不同區域的分佈式數據痕跡進行綜合之後,不僅可以勾勒出其行動軌跡、行為模式、偏好,更可以衍生出關於其的數據畫像,並可藉助該數據畫像對其進行行為預判。顯然,該數據畫像是由不同代理的交互行動聚合而形成的,且其用途及其結果也並非是原始數據採集者或提供者所能有效預期的。面對不同用途所帶來的迥異結果,將產生相應的責任問題。數據提供者是上述數據畫像中的一個代理,但就單個代理而言,其無法對其被綜合化之後的用途作出有效判斷。那麼,該如何審視這種由分佈式代理聚合而來的結果的道德責任呢?
(二)道德責任多手問題與分佈式道德責任
湯普遜(Dennis F. Thompson)在其關於公共部門的道德責任論述中指出,政府的決策和政策是源自不同的部門,因此存在難以辨別誰應當對政治結果負道德責任的情況,於是他提出了多手問題(the problem of many hands)。此時的道德責任針對的是人以及由人組成的機構。對上述數據畫像所帶來結果的道德責任追問,與湯普遜所言的多手問題有着共同之處,即結果都是由多元代理以及多代理之間的交互或曰互動形成的,但也有不同之處,即數據科學與數據技術的多元代理除了數據的提供者、使用者等之外的人的因素,還涉及數據智能、機器學習等技術邏輯的因素,以及人與技術之間的交互。
關於此,勞倫斯·馬格尼尼(Lorenzo Magnani)和艾曼紐·巴頓(Emanuele Bardone)將分佈式道德視為倫理知識外化在技術物中的結果,認為:“雖然從道德的視角來看,許多外部事物是惰性的,但是其可被轉換為道德調節者(moral mediator)。因此,並非所有的道德工具都是內在於頭腦之中。事實上,在作為道德裝置發揮作用的外部客體和結構中,也有一些道德工具,如互聯網就是一種道德調節者。”當今,關於算法中立的質疑、關於算法霸權的揭示、關於數據權力的闡述等一方面顯示了對技術作為道德調節者的某種認同,另一方面則説明了對結果進行道德責任釐清的複雜性。

因此,關於數據科學與數據技術所帶來結果的道德責任毫無疑問也是一個多手問題。如同湯普遜對多手問題分析的那樣,“我們很難鑑定是誰應當對所有的一切負責”,但是“對個人責任的追尋,能為人類能動性在好的政府和壞的政府中的作用解讀提供最好的基礎”。依據此邏輯可發現,就對由數據多代理所帶來結果的道德責任探究而言,對各個代理的分佈式道德責任探討或許有助於對結果的解讀,但是這並不足以對其進行解析。因為“如果將分佈式道德責任的詮釋徹底還原為(某些)人、個體和負道德責任的行為總和時,那麼分佈式道德責任的分配,無論是讚賞和獎勵或譴責和懲罰,從概念的角度而言,是沒有問題的,但從實際操作上則是非常困難的”。
(三)分佈式道德責任在數據時代的有效性與侷限性
在數據智能化的背景下,雖然數據的透明性和可解釋性有助於對道德責任的歸因,但是這並不意味着在數據的運作及其與人的交互過程中不會形成更新的模糊性與不可解釋性。例如,一種新的、未曾預期的結果在各代理之間的交互中出現,然而關於這個結果的歸因卻並不能被簡單還原到某個或某幾個代理,或某個具體的環節。因為即使數據生產者或提供者清楚何種數據被採集與被輸入,且數據使用者或平台按照約定使用上述數據,但是最終呈現出的數據樣態及數據所產生的效用並非如各方所願。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過程中,信息疫情的出現就是由科學技術的分佈式特徵與多元主體匯聚所產生的爆發效應帶來的。目前,對於信息疫情的防控已經成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一個核心任務。在此情境中,若囿於還原式的分佈式道德責任,將可能出現基於交互的隱匿性、基於交互過程中的隔閡或交互錯誤而造成諸如無責任主體、責任主體泛化,或者諸如安德烈亞斯·馬蒂亞斯(Andreas Matthias)所言的“責任鴻溝”等困境。**因此,對數據時代道德責任的合理解析與數據相關倫理問題的有效應對必須走出分佈式道德責任。**恰如尤金·施洛斯貝格爾(Eugene Schlossberger)所言,“不能將道德責任侷限於行動和選擇”,而且關於道德責任的解析不應是“一個因果概念。重要的不是如傳統觀念所要求的,我們導致某事以正確的方式發生的原因,而是特性,那種我們通過實例所表達的或者適合我們世界觀的特性”。
易言之,分佈式道德責任雖然有效地呈現了數據科學與數據技術的分佈式特徵,但是其尚未能有效詮釋數據科學與數據技術的全球化與網絡化特徵,因為數據科學與數據技術的在線性、生成性及其與人的交互等又使得分佈式的多元個體責任與網絡式的集體責任之間的轉換更為深度與及時。反觀對分佈式道德的界定可發現,道德行動可以是源自道德中立或道德上可以忽略的代理之間的交互行為。進一步來説,對道德責任考察需要將各個代理在系統中的交互行為納入。因此,依據此邏輯,道德責任至少可以推演到代理所在的系統之中。這種推演因其包含數據科學與數據技術自身的邏輯演繹、人與數據之間的交互等,所以並非是重現基於以人為單位的集體責任,而是一種多元代理的結構式道德責任出場。
探尋分佈式道德責任有限性的破解
在《“十四五”國家信息化規劃》《全球數字治理白皮書》《數據治理標準化白皮書》《歐盟數據治理法案》等對數據治理模式所展開的探尋中,責任共擔、責任分擔一直是非常重要的議題。2020年11月世界互聯網大會組委會發布的《攜手構建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行動倡議》中所提出的“責任共同體”㉖顯示出了分佈式道德責任在當下的有限性。人類對數據信任的道德責任轉移、數據科學與數據技術的分佈式特徵是分佈式道德責任產生的兩大主要原因。而上述兩大主要原因恰恰為分佈式道德責任的破解提供了最佳的突破口。
(一)弗洛裏迪的破解方式
弗洛裏迪基於設計的視角,提出瞭解決之道,即“制定一個機制,在默認情況下,把對整個因果關係網絡造成的所有責任後向傳播給它的每一個代理”。該解決之道是基於如下兩點建立起來的:一是基於視角的轉換,即從以代理(agent)為導向的倫理學走向以受事(patient)為導向的倫理學,從關注個體發展、社會福利和終極救贖,轉向了對受影響體系的福祉和終極繁榮的關注;二是基於對無意向性的倫理是何以可能的論證,將道德責任與代理意向性之間的關聯進行了某種剝離。
就數據科學與數據技術而言,上述解決之道一方面呈現出了各個代理之間的交互性,以及由這種交互性所帶來的生成性等對人類的影響,如數據智能的生成性、人與數據之間的交互性等所產生的結果並非可以簡單地還原到某個代理的意向性;另一方面用後向傳播的方式來界定道德責任主體,避開了分佈式道德責任因其分散性而造成無道德責任主體的僵局。即不能因數據科學與數據技術的多代理分佈而使道德責任消解,應當通過嚴格的後向傳播來進行破解。因此,該解決之道有效地回應了技術、意向性與道德責任之間的關聯性問題,恰如漢森(F. Allan Hanson)對延展能動性道德責任的考察一樣:“對於一個行動來説,如果道德責任在於承擔責任的主體,且如果主體包括人和非人的話,那麼道德責任也可以如斯。”
與此同時,一個不容忽視的現象是:數據科學與數據技術的分佈式道德責任恰恰是在一個由多代理構成的結構式系統之中產生的。因此,必須重視關於這個系統的整體考察。如果説,分佈式道德責任是基於向後看的後向傳播而展開對道德責任的探究,那麼對其產生語境的考察則應是從向前看的視角展開對道德責任的探究。弗洛裏迪通過轉向關注受影響體系的福祉和終極繁榮來樹立道德責任產生語境的倫理目標,但又該如何看待產生語境的道德責任呢?當向前看的視角與向後看的視角共同指向分佈式的道德責任時,需要從廣義的視角將上述二者置於某個系統中進行有效的統攝。易言之,對於分佈式道德責任的審視應有效涵蓋分佈式道德責任,但又不能囿於其簡單彙集,這樣才有可能破解分佈式道德責任的侷限性。
(二)基於系統視角的分佈式道德責任破解
同樣地,數據科學與數據技術的道德責任是散落在基於多元代理集成的系統之中,也正是在這個系統中,多元代理可以構成一種結構式意圖。這種意圖因其並非是單個代理意圖的靜態拼圖,故不可也不應被直接還原,但是它確實存在。
以數據治理為例,其至少包含兩方面:其一,將數據作為被治理的對象而展開的對數據的治理,即對技術的治理;其二,將數據科學與數據技術作為治理工具而展開的治理數據化,即基於技術的治理。但無論是前者還是後者,從技術生命週期的意義上來看,在數據收集、分類、典藏、交易等的過程中,道德責任已經滲透在所有環節之中;從該行為所涉及的羣體來看,數據的生產者、使用者、擁有者以及數據挖掘工具的設計者與開發者等都可視為道德責任的主體。進一步而言,基於技術生命週期的以單個過程為模塊的數據治理和將所涉及羣體進行細化的數據治理為將問題在某個環節進行最大限度的阻斷提供了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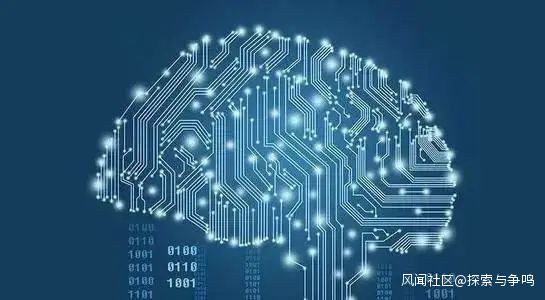
**與此同時,更需要注意的是,數據作為一種新型生產要素,正在以基礎性架構的方式深植到人類社會之中。**毫無疑問,分段、分層式的碎片化治理模式與數據科學和數據技術的分佈式特徵相契合,但是數據效能的釋放恰恰在於流通與匯聚,缺乏頂層邏輯的碎片化治理必將以隱匿的方式帶來災難性後果,特別是由單個獨立的善意或非惡行為悄然匯聚的惡。即,雖然就每個參與者、每個環節而言都沒有惡的輸入,但是最終輸出的恰恰是惡的結果。針對上述現狀,亟需一種結構式道德責任出場來彌補碎片化的治理模式。那麼,何謂結構式道德責任呢?
(三)結構式道德責任的定位
首先,結構式道德責任的定位是分佈式道德責任的一種補充,其功能是通過對分佈式道德責任產生語境的解析,將基於多元代理交互的道德責任從一個整體性的視角予以呈現,以一種動態結構式的模式進入數據科學與數據技術的道德責任探究之中,進而避免數據治理的碎片化。
其次,結構式道德責任作為一種底層架構,為分佈式道德責任的後向傳播閾值設定提供理論依據。弗洛裏迪從結果輸出的角度,以後向傳播的方式進行道德責任的分配。例如,當輸出的結果是惡的時候,將責任通過後向傳播分配到每一個代理。從理論上來説,通過這種方式,可對每個參與者、每個環節都沒有惡的輸入但是最終輸出的恰恰是惡的結果的情況進行嚴格意義上的追責。然而,循環式的無限後向傳播可能會導致該過程中的某個代理不願承擔技術創新風險,進而阻礙技術發展的現象。因此,需要為其設定一個合理的閾值,確保在保留追責邊界的情景下保護技術創新。
最後,結構式道德責任是依託於一個宏觀的倫理主旨,且該主旨滲透在分佈式道德責任之中。針對數字技術的發展,貝爾納·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認為:“一個系統性愚昧的時代”已經開始,“普遍性麻木狀態似乎已經伴隨着系統性愚昧、功能性愚昧而出現了。”反觀數據時代的日常生活,信息繭房的出現與斯蒂格勒所言的“系統性愚昧”之間有着某種同構性,對數據的高度依賴與斯蒂格勒所言的“功能性愚昧”之間有着某種相似性,深度沉溺於數字技術及其產品現象的出現,事實上就是一種斯蒂格勒所言的“普遍性麻木狀態”的悄然而至。**對於系統性的、普遍性問題的應對,需要有一種更為本源意義上的系統性綱要,即以宏觀的倫理主旨作為頂層邏輯為人類行動提供指南。就宏觀的倫理主旨而言,人類社會基本的倫理準則是其底線,科技為善、構善、至善是其主線。**在數據活動與數據生產的所有環節中,以保持該條主線一直在線的方式,規範數據科學與數據技術的發展,避免出現斯蒂格勒所言的數字化困境,為構建良好的數字生態環境提供實踐智慧。
綜上,分佈式道德責任與結構式道德責任分別從兩個不同的維度回應了由數據科學與數據技術的不同特徵所引發的道德責任問題,但這兩者並非是以二元的割裂模式來應對數據時代的道德責任,而是以一種有效的融合來共同構築良好的數字生態環境,共同助推數據要素潛能的激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