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湧進約友軟件,陌生人的鼾聲陪伴到天明_風聞
普通路人Y-2022-05-19 14:42
【文章來自極晝工作室,作者 魏榮歡】
失落的「魚」
“扛不扛咬?”一個語音聊天羣裏,四川口音的年輕女聲問,她一説話,灰髮上長犄角的卡通頭像就跟着亮。東北腔的男聲率先回應,“必須扛啊!”另一個男聲略顯青澀,“我練過一年半自由搏擊。”聊天羣的目的是「蹲CP」,十幾種聲音正在互相提問了解彼此。
一個蘇北口音的女聲引起了關注,聲線經過57年和世界的撞擊已變得粗糲——“什麼是CP?”馬上有人發現了她的真實身份,“60後老太”就寫在備註裏。有人告訴她,CP就是固聊,固聊就是網絡對象,她更困惑了:網絡還有對象?三句話之後,年輕人的耐心用完了,讓她自己去百度搜索,“阿姨你出去吧”,“阿姨你去跳廣場舞吧”。
女聲退出,又進了交友平台上的另一間聊天室,這次大家主動迎接了她,“來了一條魚”。她以為説的是自己網名帶個“魚”字,但越聽越不對,這裏的“魚”似乎是別的意思。
屏幕後面,徐州市區一棟住宅樓裏,於淑琴在搜索框裏輸入“海王”和“養魚”,試圖破譯。今年五一假期第三天,兒子一家出去旅遊了,她沒跟着。早上六點多醒來,從冰箱裏拿一小盒酸奶,就着麪包當早餐。中午熬小米粥,晚飯燙點青菜掛麪,和昨天、前天、大前天都一樣。
飯後回到次卧,倚在牀頭看手機。丈夫病逝後她有時寄住在兒子家,除了吃飯基本待在自己房間,緊閉着門,晚上有時候八點就睡着了,有時到凌晨三點也不困。
這樣的日子自2020年底丈夫離世就開始了。葬禮過後,她沒再在兒子面前掉過眼淚,不願讓他擔心。誰都知道丈夫寵她,每天早上起牀會先倒一杯水放在牀頭,喊她喝甲狀腺的藥,出門回來手裏拎着早點。丈夫不吃豬肉,但顧慮她的口味總會定期買豬蹄回來。
於淑琴不會做飯,都是丈夫做,最拿手的是炒雞。即便當天有應酬,也會先回家做好飯才走。如果哪天打開冰箱發現被塞滿吃食,説明丈夫馬上要出差了。他的朋友們調侃:“你這是找了個老婆還是找了個女兒?”
於淑琴退休前是美術教師,跟丈夫是介紹認識的,她起初對學歷不高的男士沒動心,直到有次被雨困在單位,丈夫送來一把黑色折傘。現在想起來,求婚也很不浪漫,他只説,單位給結了婚的分房,要不要去登記?
婚後三十餘年,於淑琴對丈夫沒少耍性子,自己也知道算不上“賢妻良母”,甚至過於矯情了。有次感冒家裏沒人,她心裏委屈,便打電話給正跟同學聚會的丈夫,邊打邊哭。後來據同學回憶,丈夫接到電話,丟下一句老婆有事就跑了。同學得知她沒什麼事,忍不住怨於淑琴,“嫂子,你以後可不能這麼對他。”
她一直有寫日記的習慣,但丈夫走後再沒寫過。“你不開心就去XXX(某交友平台)呀”,手機裏彈出的廣告語打動了於淑琴。那大概是一年前的晚上,也是倚在牀頭,手機屏幕的亮光在她的眼袋上投下陰影,如果不是網絡,她與這個年輕人的交友世界大概永遠不會交匯。
下載軟件的第十天,她學會了卡通自拍,還發了一條「瞬間」——類似日記的功能收容了她的思念與悲傷。那天從深夜到清晨,她連發了九條,早上5點48分的時候,“想哭”。

●資料圖,源自視覺中國。
接下來的一年,對丈夫的思念似乎從未減弱。他的辦公桌即將被拉走,她“心堵得厲害”,五位陌生網友在下面留言安慰。到了節日她寫,“人如空殼,心在流浪”。上個月丈夫生日,她又寫,“無助的時候除了你,也許沒有人會無條件包容我的壞脾氣了!”
另一些瞬間被她打上了“自我救贖”的標籤。剝好一碗蒜,換好水龍頭,在完成這些從沒做過的家務事後,她鼓勵自己能幹,也會分享清晨的日出和盛開的石榴花。然而情緒總會在一些時刻墜入低谷,也許是有人送來了燒雞,或是走到丈夫舊時的辦公樓前,有時僅僅是城市起了濃霧,於淑琴一腳踢翻水杯,“真無能,想哭”。
這些她從不敢跟兒子説。兒子總加班,且因為陪丈夫治病在職碩士答辯已經延期了一年,於淑琴想,“不能拖後腿”。內心的情感被她藏在虛擬ID後面,釋放在與現實隔絕的網絡空間。
在聊天室裏串得多了,於淑琴知道了更多新詞。“養魚,網絡用語中指養備胎的意思……備胎有一大羣,養魚塘的主人會被稱為海王。”進入「魚」羣那天,於淑琴分享了自己在網上查到的釋義。每次學到新詞,她都記錄在平台上,“凡爾賽文學”“怎麼可以吃兔兔”的梗都在其中。
如果光憑打字速度,很難發覺這是一個將近六十歲的人。於淑琴年輕時就愛趕時髦,剛有相機的時候就學攝影,自己沖印照片,也第一時間買來電腦,現在用手機也是兩個大拇指同時打字,“新鮮的東西就想去嘗試”。
不過在另一些方面,她仍透着老式的做派。起網名是和起真名一樣慎重的事,於淑琴説,“魚”是自嘲忘性大,飛起來又是鯤鵬,包括現實與理想多層含義。
作為家裏第三代教師,説教的習慣也被她帶到了網絡世界。在一個本地羣裏,看到有年輕人用方言罵人,她忍不住打斷,“你們是否知道徐州的兩漢文化?不知道應該覺得慚愧,年輕人應該把時間用來學習而不是在這浪費。”
也看不慣有家庭的人還在網上「蹲CP」,對方説她落伍,她無法接受,還因為收到已婚男士發來“親親”表情差點舉報對方。最不能接受的一次,一個二十多歲小夥子説,“阿姨我不想奮鬥了想躺平”,她聽出對方想被包養的意思,回覆他,“老阿姨也不想奮鬥了”。
夕陽之約
在匿名世界放肆了近一個月,一條懷念鐘鼓樓老街巷的分享貼打破了於淑琴的次元壁。去年5月底,一個男人跑來跟於淑琴私聊,説自己也是街上的老住户,小時候上學的院子裏有一口井,還有不少共同認識的人。
自那天起,老鄰居每天都來問候於淑琴,知道她喜歡花草,就拍一些小院裏種的花和景觀樹發過去,介紹説,“這片地和院子都買下來了。”他邀請於淑琴到大兒子開的燒烤店吃飯,去的時候一定要提他的名字。也講這些年生意的起落,跟第二任妻子的感情也隨之變差,正處於分居狀態。於淑琴回覆他,“你們做生意的真亂。”
她反覆叮囑老鄰居不許跟別人説上網的事,不然就不理他了,“你是窺探了別人的隱私,要再告訴別人……做生意的人要講誠信的。”
雖然怕在現實中被暴露,偶遇老鄰居還是給於淑琴帶來過慰藉。有次她説喜歡吃榴蓮,老鄰居當晚就送到於家附近,兩人在公園附近的十字路口見了面。
於淑琴回憶,自己穿着短褲拖鞋,手裏提着要送給對方小女兒的派克筆和油畫棒。老鄰居穿一件帶領的短袖衫,五官裏透着生意人的精明——明明騎電動車來的,他卻要跟於淑琴説,開車不方便。於淑琴笑笑,心裏看不上他,“雖説後來掙了錢,但從小就不愛學習,像我們家庭的話,對看書學習都是比較看重的,不像他們根本(就是)玩。”
母親和奶奶都是教師,於淑琴從小在重點校讀書,但她身體不好,經常上半天課歇半天,初中畢業就沒再讀,進了師專。到小學任教後,她不大理周圍的同事,覺得她們整天家長裏短,“像街頭大媽”。於淑琴喜歡看偵探小説,讀席慕容,畫人魚公主和白雪公主,也喜歡畫宇宙星空,自己加一點想象和創作。
沒有走出家鄉始終是她的遺憾。婚後,於淑琴並沒有放棄自考大學的夢想,但兒子出生後顧不過來了。
她覺得文憑很重要,曾經放棄過互生情愫的男同學,就是因為對方文憑更高,覺得自己配不上。後來在教案比賽獲獎,也努力發表論文,但升到一定級別還是被文憑困住了,她鼓勵小三歲的弟弟到廣州工作,“我走不出去,就希望他走出去。”
年近六十,於淑琴不再畫畫,不過仍喜歡穿粉色的兔子睡衣,在陽台種上球蘭和君子蘭。和老鄰居聊了兩個月,對方問她以後怎麼打算,於淑琴説自己過蠻好的。“我知道你看不上我,如果你要是動找(老伴)這個念頭,可不可以最先考慮我。”留下這一句,老鄰居就消失了。
在交友平台上,於淑琴發現像自己一樣把這裏當樹洞的只是少數,更多人交往目的直接明確,不只是老鄰居。
在聊天室裏,聽説離異阿姨和20歲的小夥聊成CP,飛奔到他的城市,於淑琴不信,直到看到了兩人合照。53歲的上海小老闆和妻子分牀十年,明確想找性伴侶,30歲的男士只對年長阿姨有感覺。還有人故意説些激怒別人的話,換到另一間聊天室後口氣全變了,後來於淑琴才知道這在平台上叫「角色扮演」,為了博取關注和流量,“都是靈魂空虛者。”
真正嚴肅追求婚姻的人不多。於淑琴所在平台大大小小的社交羣組裏,只限60後的就有三十多個,大都標着“單身”、“離異”、“真誠徵婚”等關鍵詞。但於淑琴加過幾個,聊天稀稀落落,只在新人加入或天氣突變的時候才會熱鬧幾分鐘。
其中一個叫“60後夕陽紅”的有96個人,算是最活躍的。羣主陳強生曾把真摯的徵婚貼置頂——1969年出生,內蒙人,早年離家四處做生意偶然留在了海南。他曾勸説前妻來跟自己團聚,但前妻不願意,離婚後他已經單身五年。陳強生還附上自己的半身照,皮膚黝黑,笑容燦爛。
如今老家的父母都已離世,陳強生想踏實找個聊得來的伴侶度過餘生。“不和年輕的聊”,是他設定的門檻,他覺得無法溝通。羣裏其實有不少是年輕人,《新週刊》的記者曾見過一個90後來這個羣求助:父母分別有出軌的傾向,自己應該怎麼辦?叔叔阿姨回應他:“這不是你應該考慮的事。”
更多年輕人是被系統推薦入羣的,也懶得退出了。曾有一個00後入羣,另一位稍早入羣的跳出來跟他搭話,倆人很快私聊去了。年輕人越來越多,也最活躍,每當有新人入羣,搶先回應的總是他們,這讓新入羣的中老年人很困擾。
只有陳強生會很興奮地迎接他們,“太好了,有同齡人”。在羣簡介中,他這樣寫道:60後出生在物質匱乏年代,愛情觀純正,一切以集體為榮,沒有私心。
曾有個系統配對的山東女孩到海南旅遊,他問了一句住哪,女孩直接發來地址,問“要過來嗎?”陳強生沒去,“我們這個年代的人面對現在的社會是很尷尬的,現在的人都不相信愛情,只要結果不注重過程。”徵婚帖掛了一年,沒有一個人衝着徵婚來找他,他悄悄刪除了。
孤獨的重量
跟兒子住了半年,於淑琴決定獨自搬回老房子,畢竟不是自己的家。打開房門,一股黴味撲面而來,牆上的瓷磚不知何時掉落了一塊,在地上碎成幾瓣。她連發了幾條圖文,拍下屋內牆皮掉落和瓷磚破裂的照片,配文“屋外景色依舊,屋內突變不堪”。藍白色傢俱還是結婚那年打的,刻着三十多年來的回憶。
丈夫離開後,煤氣灶打不着火,急得她在交友軟件上求助,按網友指導更換了電池。水龍頭爆了,過濾珠子散落一水池,她情緒崩潰,“全完了”。早上五點母親打電話叫她陪去醫院,丈夫在世時買的期房交付後因為電梯問題陷入維權,這些事情過去男人全部搞定,她發帖感慨,“單身女人真不易”。
跟兒子住的時候,兒子有時不放心會敲門問,她趕緊清一清哭濁的嗓子,説睡下了。實在難受得厲害,她就藉口飯後遛彎,到樓下給丈夫過去的酒友打電話。
“你們都有伴,我沒伴了。”於淑琴有怨氣,丈夫家有癌症家族史,如果不是他們老拉着喝酒,説不定他不會走這麼早。於淑琴認為,喝酒是夫妻間幾乎唯一的矛盾,有時一覺醒來不見人,她會直接衝到樓上掀翻朋友家的桌子——丈夫常和朋友喝酒打牌到凌晨,有時約酒的電話打進來,她會氣得把電話座機摔在地上。
“他朋友都説我kou(三聲),徐州話母老虎的意思。”於淑琴説。前陣子兒子兒媳吵架説了重話,往事湧得她眼底一熱,跟兒媳説:“不要這樣,以後會後悔的。”
不過,近幾個月她的傷心貼頻次少了,開始分享好吃的米線、花壇裏的花,用過期中藥製成藥包泡腳。最近她學會了自發豆芽,記錄下整個過程。在幾張逛手工藝集市的照片下,她鼓勵自己要學會一個人自在逍遙。
然而上個月整理丈夫遺物,於淑琴好不容易找回一點秩序的生活又塌了。她把每年送他的領帶鋪成一排,捨不得收起來,恍惚間覺得他只是出差未歸。那天夜裏,於淑琴失眠了。
晚上10點,她闖進一個夜班出租車司機開的聊天室,跟陌生網友反覆講那段傷痛經歷。她耿耿於懷丈夫生命的最後,醫院走程序造成時間耽擱,一説到他發燒打寒顫引起血管破裂就忍不住抽泣。那天她很幸運,出租司機和一位女網友輪流開導她,給她講笑話,分享自己的旅行見聞轉移注意力,直到她睡着。
這個聊天室原本是司機師傅想有人陪聊,晚上開車不犯困創建的,漸漸發展成了失眠者們的“陪睡”房間。於淑琴剛進去的時候,有個自稱喜歡滑雪、潛水,經常出國談業務生意做得不錯的男士,疫情後壓力越來越大,半個月不出門也不跟別人不説話,正在裏面嘮叨發泄。大家聊着困了就睡,也不掛斷,彼此的鼾聲互相伴着直到天明。
第二天於淑琴醒來,房間已經關閉。那次之後,不知道是不是改了名,她找不到那個失眠之夜闖進的房間了,包括那兩個陪她一整夜的好心人。她曾經在其他聊天室打聽他們,但再沒找到。

●資料圖,源自視覺中國。
在交友平台上,很多聊天室都不固定,房間名常換,同一個頭像的人一天能遇到好幾個,想要記住一個人很難。每天系統會配對新人,一打招呼,聊天就開始了,因此大部分的關係都是“日拋”,再也不見。於淑琴關注列表裏有200多人,她認得出的只有四五個。
另一位60後孔雲飛來這個平台三年了,已婚,只是想找一個異性知己。遇到過聊得不錯的,可過兩天就找不到了,失望地卸載了軟件,但沒過多久又裝回來。
他是東北人,在當地開了家書店,順帶做點設計和打印生意。2017年小女兒出生,家裏的開銷一下子緊張起來,偏偏岳父捲入一起土地糾紛案件,書店生意顧不上打理,收入減少了很多。疫情之後書店又無法營業,他找了一份送外賣的工作,常常送到夜裏兩三點。
糖尿病也是在那時候加重的,忙起來忘了吃藥直到頭暈才想起來。妻子嫌他不夠努力,常在外人面前説他。孔雲飛對這點頗為反感,也吵過幾回。“指責,壓抑,控制對方,吵架,製造困難,這樣的家庭就像掉進了地獄”,孔雲飛在他的「瞬間」裏寫道。他問網友“Have you ever be longly?”
孔雲飛喜歡英文,儘管lonely寫成了longly,但Queen是他最喜歡的樂隊。提到年輕時的舊時光,孔雲飛的聲音總會比平時亮一些。那時事情排得很密,下了班要運動、約會,週末去攝影、郊遊,總覺得時間不夠用。他建了一個百人騎行羣,閒時會組織騎上一百多公里到水庫玩。羣裏公認最漂亮的女孩跟他約會過,也曾有兩個女孩同時追求他——這是他念念不忘的事。
現在他還保持着每天騎行的習慣,但每天早上騎十公里就回來了,“累,就想趕緊回來”。和妻子除了生活瑣事和孩子,不談其他。他帶女兒在商場買衣服帶了一件送給妻子,妻子不高興,“我有衣服穿”。聽到好聽的英文歌,他只能跟女兒分享,妻子不懂。他曾跟自己的妹妹訴苦,妹妹嫌他絮叨:“家家都那樣,孩子都那麼大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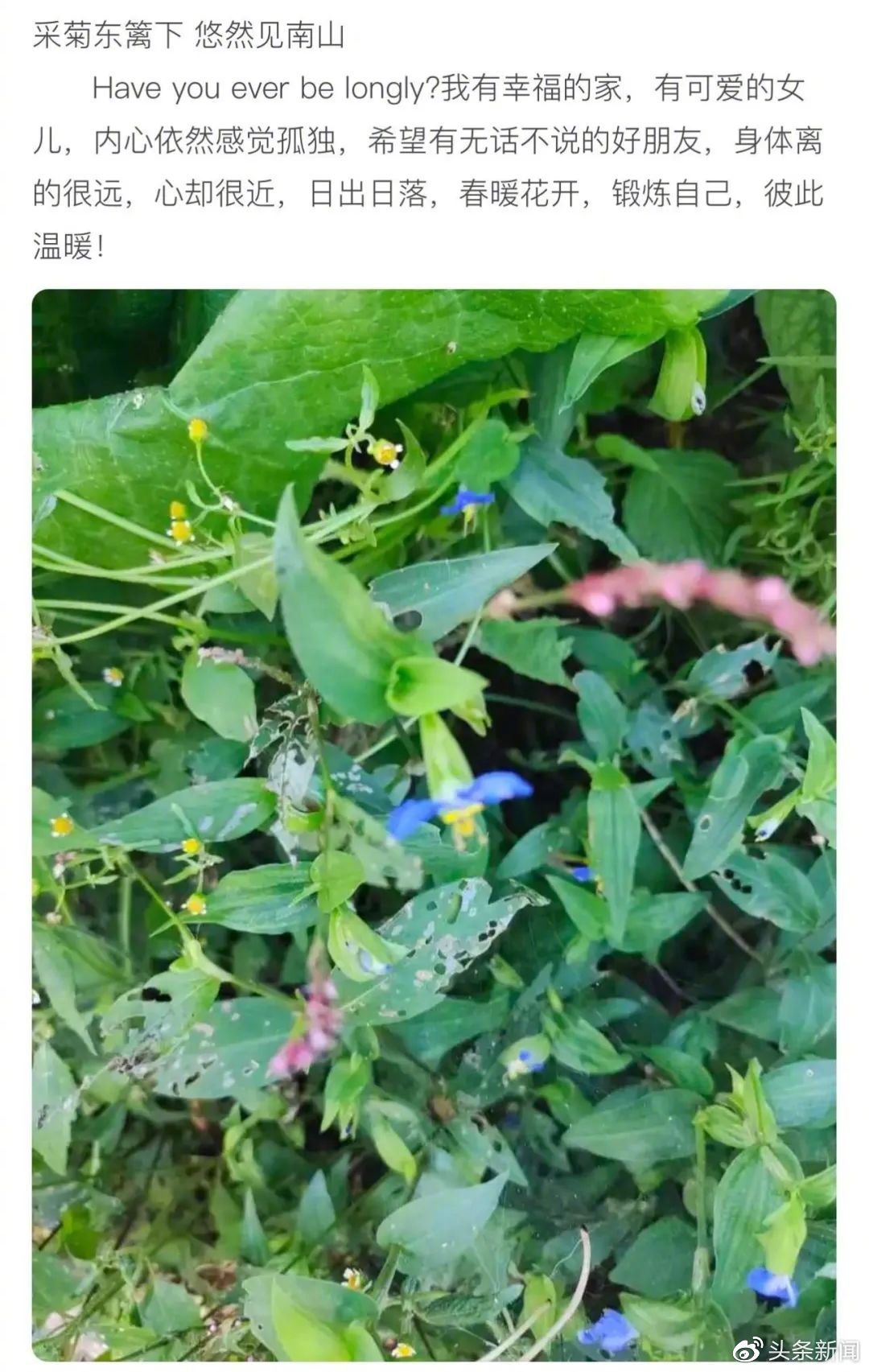
●孔雲飛的分享貼。
像泥鰍一樣滑走了
上個月,孔雲飛遇見一位自稱在合肥的女網友,難得覺得興奮。那是他上大學的地方,回鄉多年,身份證的開頭還是合肥的“340”。初戀也發生在那裏,同系的一個女生,“講話很軟,她走過的地方都是神聖的。”
女網友讓他回憶起了昨日世界,孔雲飛問她住在合肥哪裏,説自己非常喜歡那裏的桂花樹。對方坦白,自己其實是江西的,他頓時沒了興致,卸載了軟件。
過去三年,交友平台上時不時會突然冒出來個人,問孔雲飛記不記得自己,他對着名字看了半天沒有印象,這令他煩躁。他懷念曾經的QQ羣,約會過的女網友多年後還能保持聯繫,聽到對方説在醫院,他立馬問是不是母親又犯病了。“網友間建立的默契在這裏完全找不到。”孔雲飛説。
陌生女人讓他推薦美劇,説不知道在哪能看,他也沒耐心教了,潦草結束了對話。印象裏,聊過最長的網友也不過倆小時,生氣的時候就會把軟件刪掉。
但平淡的現實生活又令他泄氣。孔雲飛想起年輕時盼着冰箱裏有喝不完的啤酒,每天工作順暢,總想着以後能實現。他忽然發現,那時過的就是盼望中的生活,但不自知,“人生不能總往後盼。”
今年五一假期,妻子因為書店入賬都進了他户頭而不滿,他已經失去了吵架的衝動,沉默了一會,把新進賬的一筆錢轉到妻子卡里。也就在那兩天,他把交友軟件又裝回來了。
獨自住回老房子一年後,於淑琴覺得孤獨,還是想找一個搭夥過日子的人,“但可能性很小”。她很挑剔,如果再婚,月工資不能比她低,要喜歡旅行,“我喜歡旅行,這個人也要喜歡,還要乾乾淨淨利利索索的。”
“這(交友軟件)上的人是絕對不會考慮的。”這一點她很肯定,上週還下載了一個專門相親的軟件,但和上面的人好像聊不到一起。
她還是無法不去回憶丈夫。在網頁聊天室裏聽人唱歌,她嫌唱得不好,磨丈夫唱一首,網友都説像原唱鬱鈞劍。他的微信也是於淑琴弄的,她把個性簽名改為“老婆第一”,騙他沒辦法修改。別人問起,丈夫認真解釋,“這個是沒法修改的。”
這些屬於她的珍貴時光永遠消逝了。現在於淑琴很少再去聊天室,之前跑進去絮絮叨叨,甚至説到整個房間的人趕她走,網友告訴她,都是來解壓的,她這樣反而弄得都不開心。年輕人直接問於淑琴,“你上這個目的是啥?得説實話”。她在「瞬間」裏發飆回擊:“本人雖然喪偶單身,但並不需要自賤的性伴侶!”
但她懷念起曾經遇見過的一個網友,用心撫慰了她半個月。他介紹自己是68年的,一家小企業主,有房有別墅,離異帶着女兒生活。為了讓她相信,還發了幾張和女兒的合照。照片裏的男人在於淑琴看來結實帥氣,聊天也特別紳士,叫她“姐姐”,沒有半點曖昧,對她的訴苦也從來不煩。
只是他從來沒發過語音只打文字,並稱因為工作只有晚上八九點有空。聊了兩週,男人介紹她下載一款軟件可以投資賺錢,於淑琴説不會。之後,男人再沒出現,“像泥鰍一樣滑走了”。
其實於淑琴已經發現了,她看過殺豬盤的文章,男人是騙她投資。只是那種被人傾聽的温情真的很好,而且“和這種人聊天反而更安全”。某一瞬間,久違的關懷又回來了,儘管她知道那只是來自一個騙子的忍耐。
(為保護隱私,文中人物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