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素平|為什麼説“受教育權”是基本人權_風聞
探索与争鸣-《探索与争鸣》杂志官方账号-2022-05-20 21:47
申素平|中國人民大學特聘教授,教育學院副院長
本文原載《清華大學教育研究》2020年第6期,原標題為《重申受教育人權:意義、內涵與國家義務》,感謝作者授權推送
非經註明,文中圖片均來自網絡
編者按
5月18日晚,天津市招考院出台《關於調整天津市2022年春季高考考試時間及防疫要求的通知》,其中第一版本第7條規定:“若為新冠肺炎陽性感染者及其密切接觸者、密接的密接,或為天津健康碼‘紅碼’,或處於集中隔離、居家隔離狀態,或處於天津市封控區內,不得參加考試。”引發社會輿論質疑,後該條“不得參加考試”的表述被緊急調整為“不得在常規考點參加考試”。但輿論對於該規定的爭議仍在持續發酵,爭議的焦點在於,緊急狀態下因公共利益的需要是否可以限制、剝奪公民作為基本人權的考試權(受教育權)?本公眾號推出本組文章,供讀者思考。
教育不是特權而是人權。作為人權,受教育權具有基礎性、普遍性和優先性**。**它意味着,每一個人,無論是兒童、青少年、成人還是老年人,都有權利接受優質的教育。它意味着,國家有義務在法律和政治承諾的基礎上,努力使所有人的受教育人權成為現實。受教育權既是國際人權法上的基本權利,也是我國教育立法保護的核心權利,是一個連接國際法與國內法、人權法與教育法的重要範疇。受教育人權還是一個不斷發展的概念,從二戰之後的“國際人權憲章”到21世紀的《殘疾人權利公約》,其內涵始終在變化發展。2019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和受教育權倡議組織發佈了最新的《受教育人權手冊》,重申受教育人權的意義和內涵,為各國保護和促進受教育人權提供指引。由此,本文擬從國際人權法和教育法的視角,基於現有法律文本和解釋,系統分析受教育權作為國際人權的規範依據、規範內涵及對國家的義務要求,以期為我國全面履行國際公約義務、完善教育法律制度、保障公民受教育權提供有益的參考。

一、受教育權作為國際人權的規範基礎
**人權(human rights),是指人之為人而應享有的權利。促進和保護人權在二戰之後成為國際社會的重要目標。**1945年成立的聯合國,在憲章第一條中明確指出,其核心目標之一是“不分種族、性別、語言或宗教,增進並激勵對於全體人類之人權及基本自由之尊重。”國際社會關於促進、保護和監督人權的主要依據是由《世界人權宣言》《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等國際文件組成的國際人權公約體系。這三部文件共同組成了“國際人權憲章”,它們分別從不同的側面確認了受教育權是一項重要的國際人權。
1948年聯合國大會頒佈的《世界人權宣言》是第一個較為全面地規定人權和基本自由的普遍性國際文件。二戰後國際社會普遍認為,納粹德國大力鼓吹“種族優越論”“擴充生存空間論”為法西斯戰爭鋪路,與其將教育視為國家工具,漠視公民的尊嚴和自由息息相關,“為使人類不致迫不得已鋌而走險對暴政和壓迫進行反叛,有必要使人權受法治的保護”,因此在制定人權宣言時,特別在第26條規定了受教育權。由此,受教育權作為一種基本權利得到國際社會確認,尤其是教育領域的非歧視原則和平等原則被普遍接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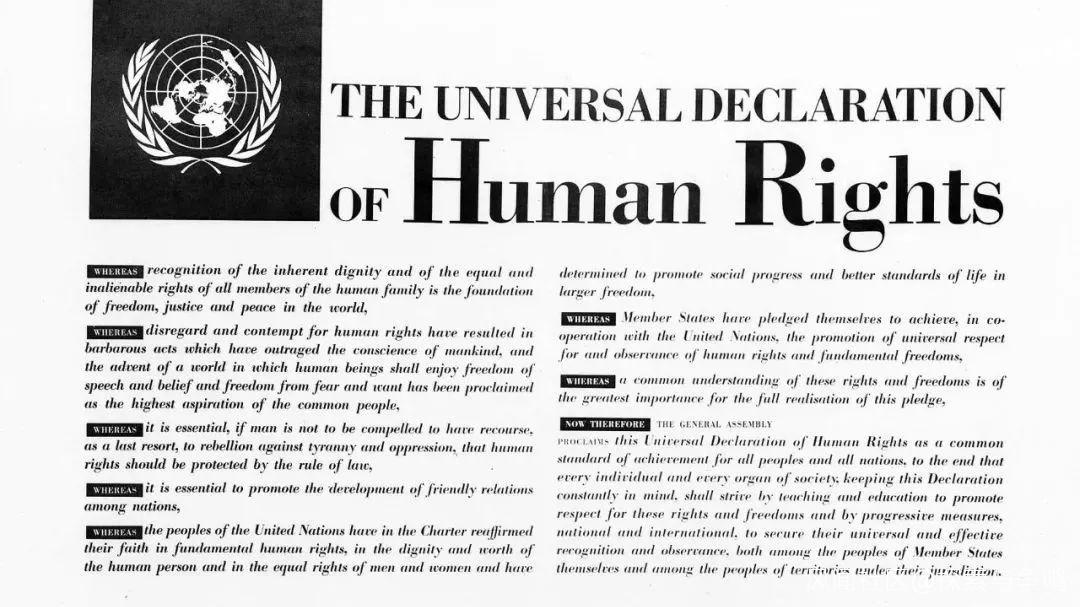
儘管《世界人權宣言》在國際社會上產生了深遠影響,但在法律性質上,它並非具有法律拘束力的國際公約。故此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決定製定具有法律約束力與執行力的國際人權公約,也就是在1966年第21屆聯合國大會上通過的《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與《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兩項基本人權公約”)。《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主要是規定公民權與政治權,故而並未對公民的受教育權作出正面規定,但仍在第18條第4款規定“尊重父母和(如適用時)法定監護人保證他們的孩子能按照他們自己的信仰接受宗教和道德教育的自由”,從宗教與信仰自由的側面保護了父母教育權與兒童受教育權。《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則有兩條專門針對教育的條款。該公約在第13條莊嚴宣告:“本公約締約各國承認,人人有受教育的權利。它們同意,教育應鼓勵人的個性和尊嚴的充分發展,加強對人權和基本自由的尊重,並應使所有的人能有效地參加自由社會,促進各民族之間和各種族、人種或宗教團體之間的瞭解、容忍和友誼,促進聯合國維護和平的各項活動。”在確認人人享有受教育權並規定教育的根本目的與宗旨之後,第13條第2款緊接着詳細列舉規定了從初等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具體權利內容。
除了上述國際人權憲章的主要規定,後來出台的其他人權文件也陸續對受教育權作出確認並提供更具有針對性的實施框架,如《兒童權利公約》《取締教育歧視公約》《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殘疾人權利公約》等,所有這些國際公約使得受教育權被牢固地確立在國際人權體系的目錄之中。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2019年的最新數據,受教育人權目前已經整體或部分地被至少48部有法律拘束力的國際人權文件所確認,其中28部是地區性的,另有23部不具法律拘束力的軟法性質的國際人權文件也對其進行了規定。這其中就包括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頒佈的各種以“宣言”“建議”等形式命名的國際文件。
二、受教育人權的性質
作為一項權利,受教育權存在性質定位的問題。按照國際法通常採用的“人權代際理論”。**第一代人權指個人的政治權利與自由,一般被稱為“消極權利”,是強調國家不予侵犯的自由權。**它以限制政府對人民行為的干涉為追求,先於其他兩者出現,產生在自由放任資本主義的全盛時期。第二代人權以生存權為本位,是“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也即“積極權利”,是強調國家積極作為使個人受益的權利。**第二代人權的主要目的在於通過國家干預和規制為全體人民謀求經濟與社會福利。**根據其權利各自的特性,其實現要求有賦權標準、資源的分配和政治控制機制,要求政府採取積極行動給予劣勢地位的個體以福利。第三代人權是“連帶權利”,以發展權為本位,包括和平權、環境權、發展權以及民族自決權等,故又稱集體人權。
將一種權利在三代人權之中進行歸位對於確定權利持有者的法律訴求和國家的相應義務是有用的。受教育權作為一項國際人權,從其產生背景來看,具有明顯的第二代人權的特徵,強調國家提供教育機會和條件,指向國家的積極保障。但其也關涉公民的個體尊嚴與自由,對公民行使政治權利有着至關重要的影響,因此也具有第一代人權的特徵。這一特點可從國際人權文件的規範內容得以佐證。現有規範受教育人權的國際文件中,《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13條第1、2款,《兒童權利公約》第28條第1款,《取締教育歧視公約》第4條a項等人權公約將受教育權定位於第二代人權,要求國家在現有的資源條件下發展和維持一套學校系統。而《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8條第4款、《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13條第3款,以及如《歐洲人權公約第一議定書》第2條等地區性的人權公約中,受教育權則被視為第一代人權,要求政府尊重父母的權利和自由,以確保學校教育教學與父母的宗教和道德信仰相一致,保護父母權利免受政府的干預。因此,只有從第一代人權的自由屬性和第二代人權的社會屬性雙重角度理解受教育人權的內涵,才能不至偏頗,而這一理解也正和現代憲法對受教育權的雙重屬性的性質定位相一致。
三、受教育人權的規範內容
受教育權具有綜合的人權屬性,內容龐雜,規範來源多樣且新舊疊加。有的國際人權文件具有法律拘束力,有的僅有道義或政治上的影響,其規定並不屬於法律規範的內容。並且由於目標和定位的不同,不同國際人權文件對受教育權的規定各有側重。需要根據相關文本系統地進行梳理、辨析和解釋,才能對受教育人權的規範內容做出準確描述。
筆者此前將受教育權的國際標準框架界定為五個維度和五個層次,其中**五個維度包括教育的目的、教育的受益權、教育的自由權、不歧視與制度保障;五個層次包括初等教育、中等教育、職業技術教育、高等教育與基礎教育。**在五個維度中,受益權維度是唯一與締約國的國力聯繫在一起的可變動因素,不僅在五個層次中的內涵差異較為突出,而且在同一權利中的內容也在不斷發展。除了有新的國際公約締結而促成變化之外,其與國際法的性質也有密切關係。國際法上受教育權的內容雖然具有法律確定性,但由於各國財政能力和社會情況差異較大,難以進行統一要求,故而其僅對教育目的、教育自由、不歧視等不與國家財政能力掛鈎的內容做出了立即實現的要求,而對於需要國家財政投入的受益權內容,公約則只規定了免費初等教育,其餘的內容均賦予締約國較大的自由裁量權以逐步漸進實現,因而其內容也就具有了可發展性。近些年來,聯合國有關機構通過制定新的“一般評論”或專門報告對既有的人權公約和文件進行解釋,從而為傳統條款注入新的內涵。受教育人權的內涵不斷拓展,其邊界開始向早期教育和終身學習延伸,其重心也愈益從獲得教育機會向獲得優質教育過渡和發展。
1.初等教育權
根據《世界全民教育宣言》的觀點,初等教育是“除家庭教育外對兒童進行基礎教育的主要傳授系統。初等教育必須普及以確保所有兒童的基本學習需要得到滿足,並考慮社區的文化、需要和機會。”根據國際公約的規定,初等教育必須具備兩個特徵:第一為義務性;第二是免費且可獲得性。
2.中等教育權
中等教育在不同國家及不同歷史時期的內涵雖不一樣,但至少包括完成基本教育併為人的終身學習及人格發展鞏固基礎。根據國際公約的規定,中等教育應當有彈性的課程及多樣的提供方式以應對不同社會及文化背景學生的多種需求,為此需要國家提供與中等學校體系並行的可替代性的教育項目。其次,中等教育必須以一切適當方法,特別是要通過逐步引入免費教育的手段,令所有人可獲得或可進入。主要公約均使用了“普遍設立”和“對一切人開放”的概念,表示中等教育不是以學生表現出來的成績或能力為前提,而是對所有人在同等的基礎上普遍提供。“一切適當方法”則強調國家應在不同社會及文化條件下采取多樣及創新的機制與方法來提供中等教育。“逐漸做到免費”則意味着,國家儘管必須優先提供免費初等教育,但同樣也有義務採取切實步驟努力實現免費中等教育。
3.技術及職業教育權
技術及職業教育是所有教育層次的內在組成部分,但在中等教育階段具有特別的重要性。因此,公約使用了與高等教育一樣的概念來描述技術和職業教育權的內涵,即“以一切適當方法普遍設立”“對一切人開放”“特別要逐漸做到免費”。但聯合國《技術與職業教育公約》也明確指出“技術與職業教育包括教育過程所涉及的所有形式和層次”,其內容不僅應當從受教育權的角度分析,而且應當包括勞動權。
4.高等教育權
國際公約關於高等教育的規定與中等教育有很多相似之處,如應以多樣的形式提供,逐步做到免費等;但也存在明顯的區別,即高等教育不能夠普遍獲得,僅能根據能力平等獲得。而能力必須通過對個體的專業知識、技能和經驗的評估加以確定。
5.基本/基礎教育權
基本教育(basic education)與基礎教育(fundamental education)在國際公約中的含義基本相同。“基本教育”系《世界全民教育宣言》所使用的概念,“基礎教育”乃《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所使用。其含義是指為那些沒有接受或完成初等教育以及所有未滿足基本學習需要的人所提供的教育,權利主體包括了兒童、青年人、成人和老年人,因而構成了成人教育和終身教育的內在組成部分。
6.最新發展
近些年來,隨着經濟社會和教育發展,受教育人權的內涵不斷得到豐富,其外延開始向早期教育和終身學習延伸。在國際人權公約中,早期教育並不是一項明確的權利,但各國在這方面的實踐卻大大超前,從而有力推進了國際社會的認識。聯合國兒童權利委員會指出,“高質量的教育課程對幼兒成功地過渡到小學、教育的進程和長遠的社會適應方面具有產生積極影響的可能性”。並將《兒童權利公約》第6條第二款和第29條第1款a項所保障的兒童受教育的權利解釋為“從出生開始,並與兒童的最大發展密切相關”。這在一定程度上增強了早期教育的法律基礎。
終身學習是另一個受到關注的領域,特別是其中的成人教育部分。按照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定義,終身學習是建立在學習與生活的融合之中,涵蓋各個年齡段的人們(兒童、青年、成年人和老年人,無論男孩或女孩,男人或女人)的學習活動,在所有的生活環境(家庭、學校、社區、工作場所等),並通過多種方式(正規的、非正規的和非正式的)來共同滿足廣泛的學習需要和要求。因為內涵過於寬泛,因而它也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受教育權的組成部分。但聯合國受教育權問題特別報告員最近指出,終身學習是代表學習和教育過程的連續性的一個概念,始於出生並貫穿人的一生,因而也可體現在受教育權中。這一點無疑也是重要的進步。

而對於受教育權的實質內涵,國際人權法越來越多地從獲得教育機會向獲得優質教育過渡,認為受教育權意味着權利持有人有權接受優質教育——因為享有接受劣質教育的權利沒有多大意義。聯合國受教育權特別報告員在2012年提交人權理事會的專題報告中強調,國家對受教育權的義務必須以接受優質教育的權利來理解。不過,國際人權文件只是從教育的可接受性角度提出了教育質量的要求,並未對優質教育的內涵進行規範定義,也未規定所有國家都要執行的普遍質量標準,因此關於優質教育的構成因素並不清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指出:“優質教育是一個動態的概念,會隨着時間以及社會、經濟和環境的背景而變化和發展。”因此,關於“什麼是優質教育”顯然有一定程度的主觀性,在不同的國家、在不同的條件下它可能意味着不同的事物,這也就意味着國際人權法對優質教育權的全部規範(標準)內容缺乏精確性,需要由各國決定。
四、受教育人權的國家義務
**受教育人權的義務主體主要是國家,實現公民的受教育人權主要是國家的責任。**研究國家對受教育權的義務內容,是落實受教育人權的重要理論基礎。傳統上,根據人權性質的不同,國家義務可以分為消極義務與積極義務。對於第一代人權即公民與政治權利,國家承擔消極義務,自身不能採取損害它們的行動。而對於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等第二代人權,國家承擔積極義務,必須積極提供相應的資源,才能保證權利的充分實現。由於受教育人權同時具有第一代人權和第二代人權的綜合性質,因此國家既對之承擔積極的義務,同時也負有不予侵犯的義務。
隨着人權理論的發展,由於逐漸認識到任何權利都可能同時要求國家的積極義務與消極義務,人權學界逐漸發展出了更為綜合的國家義務分類。其中,美國政治哲學家亨利·蘇(Henry Shue)最早在其著作《基本權利》中提出,國家承擔的人權義務可分為:“避免剝奪”的義務、“保護不被剝奪”的義務和“幫助被剝奪者”的義務。這一分類經過眾多學者特別是挪威人權專家阿斯布佐恩·艾德(Asbjorn Eide)的發展,演變成為尊重、保護和實現的義務,並被國際社會普遍接受。根據這種分類,國家對受教育權的義務分為三個層次:第一層次是“尊重的義務”,它禁止國家違反受教育權,不得非法干涉或限制受教育權的行使;第二層次是“保護的義務”,它要求國家在不違反之外,還要採取措施阻止第三人對個體受教育權的侵犯;第三層次是“實現的義務”,它要求國家根據經濟發展水平和財政能力,進一步發揮積極作用促進公民切實享有和實現受教育權。
可以看出,上述三個層次的義務是一種不斷遞進的關係,其中,“尊重的義務”基本上不需耗費國家資源,而“保護的義務”及至“實現的義務”則需國家逐步發揮更為積極的作用並投入更多的資源。這一分類包含一種從“消極”逐步向“積極”過渡的義務譜系,在公民與政治權利和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之間架設了橋樑,更為符合受教育權所具有的綜合性質。目前,這一分類標準已被廣泛引入對受教育權的分析,不僅聯合國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委員會在關於受教育權的一般評論中運用了此種分類,而且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也運用該分類來闡釋國家對受教育權的義務。
為了更有針對性地從教育的特徵對國家義務進行分類,聯合國有關機構在對包含受教育權保護條款的主要國際公約對比的基礎上,提出了受教育權的國家“4A”義務。根據該理論,任何一個國家所提供的教育,都應當體現出可獲得性(Availability)、可進入性(Accessibility)、可接受性(Acceptability)和可適應性(Adaptability)四個方面的基本特徵。在此基礎上,國家在教育的可獲得性、可進入性、可接受性和可適應性四個方面承擔責任,簡稱為國家的“4A”義務。經過二十年的發展,國家的“4A”義務框架逐步完善、內容日益充實,已成為當今分析受教育權國家義務的權威理論。
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等國際機構的最新闡述,國家的“4A”義務主要包含如下四方面內容。在可獲得性方面,國家必須建立、發展和管理一套教育體系,確保學校數量充足且安全達標,以保障教育機會的“可獲得性”。在可進入性方面,國家應秉持教育的“非歧視”原則,保證每一個人特別是邊緣化羣體不受歧視地接受教育,同時實現教育的“身體的可進入性”和“經濟的可進入性”。前者指學校應設置在適齡兒童安全可達的範圍內;後者指義務教育必須免費且其他教育逐步實現免費。在可接受性方面,國家應在公立和私立學校中提供優質教育,尊重多元文化並重視教育的文化關聯性,確保兒童是權利享有者並免受任何形式的暴力。在可適應性方面,國家應確保教育滿足每個學生個體的獨特需求,教育要主動適應才能各異、需求多樣、處境多元的兒童,要順應不斷變化的社會需求,還要順應當地的情況和需求。
五、結語:促進人權公約受教育權規定在中國的實施
目前,中國已經簽署了《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兒童權利公約》等人權公約,並且批准了其中兩部。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按照國際公約在中國適用的慣例,國際公約不直接作為中國法院審理案件的法律依據,而是通過立法程序轉化為國內法律後予以適用。因而,教育立法在轉化國際公約相關要求上承擔着重要的責任。在此方面,中國“已形成以《教育法》為核心,包括《義務教育法》《職業教育法》《民辦教育促進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規組成的法律體系,並已實現全面普及九年義務教育”。但毋庸諱言,我國對受教育權的保障距離國際公約的要求仍有一定距離。為更好地履行國際條約義務,也為全面貫徹實施我國憲法“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的條款,應進一步完善教育及相關立法落實受教育人權。
**首先,從受教育權的性質和內容來看,立法應進一步強調國家的積極義務,根據國力為公民享有和實現受教育權提供充足而適當的物質條件保障,建構合理的受教育權給付義務體系。**一方面,在已初步建立起法律保障體系的義務教育、職業教育、高等教育、民辦教育等階段和領域,應朝“不斷使之趨向免費”的方向,繼續完善教育資助和津貼等制度、組織和程序設計。另一方面,在學前教育、終身教育等受教育人權的新興發展領域着重填補立法空白,增強國家的給付義務功能。同時,不能忽視受教育人權對國家的消極義務要求,對受教育權的限制應堅持法律保留原則、比例原則、正當程序原則與利益平衡原則。
**其次,從尊重、保護、實現的義務來看,立法應進一步強化非歧視原則與教育平等的價值,加強國家的保護義務,特別是加強受教育權受到侵害時的司法保護,增強受教育權的可訴性。**一方面要暢通行政訴訟渠道,落實公民對免費義務教育、就近入學、教育選擇自由和機會平等這些屬於國家“最低核心義務”的給付請求權,為受教育權的行政侵權提供更為完善的司法保障。一方面還要暢通民事訴訟機制,為“冒名頂替”這類平等主體之間的受教育權糾紛以及輟學等涉及父母侵權的受教育權案件提供可行的全面法律救濟。

**最後,受教育人權是一個不斷發展的概念,國家在教育的可獲得性、可進入性、可接受性和可適應性四個方面承擔的義務具有長期性,貫穿受教育權開始階段的“學習機會權”、過程階段的“學習條件權”和結束階段的“學習成功權”。**從形式到實質、從機會到質量,從達到最低標準到提供優質教育,受教育人權的內涵發展要求教育立法不斷根據經濟社會條件和財政能力將其適時確認和法律化,這是一個歷久而彌新的長期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