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麗雲、鄧瑋|當“百度患者”遭遇“麥當勞式醫生”,醫患交往困境怎樣破局?_風聞
探索与争鸣-《探索与争鸣》杂志官方账号-2022-05-22 23:01
編者按
改善醫患關係長期是社會關注的課題。本文從一個個案分析出發,指出當前的醫患互動與健康日常中,出現了麥當勞化的“標準醫生”與網絡自診化的“百度病患”的對壘,即技術的“分割效應”使得臨牀實踐標準化下的醫生與多元信息裹挾下的病患之間不斷產生矛盾與衝突。醫患關係既被醫療制度正式地構建,也被包括醫學在內的現代技術深刻地形塑。在網絡等現代性技術迅猛發展的時代,醫療工作者怎樣才能回應社會公眾的健康確定性期待?未來可能需要訴諸醫生積極闡釋者角色的轉向、病患醫學知識信念的重塑,以及醫患主體性迴歸的“闡釋-交往醫患關係模式”,以扭轉“機-人”式醫患互動,緩解醫患“交往困境”,構建和諧醫患關係。
當“百度患者”遭遇“麥當勞式醫生”,醫患交往困境怎樣破局?
董麗雲|廈門理工學院外語學院教授
鄧瑋|集美大學法學院教授
本文原載《探索與爭鳴》2022年第4期,原標題為《標準醫生、百度病患與闡釋-交往性醫療圖景——技術語境下的醫患關係個案研究》
非經註明,文中圖片均來自網絡
技術語境中的醫患關係
緩解醫患矛盾、構建和諧醫患關係是建設健康中國的題中之義。但近幾十年來醫患關係日趨緊張,醫患糾紛與衝突事件呈現爆發式增長態勢。通過對2021年6月30日中國司法大數據服務網上數據庫的檢索,2009年至2019年10年間,全國醫療損害責任糾紛與醫療合同服務糾紛案件數量共計111511件。其中2009年為67件,2019年則為24090件,增長幅度驚人。各種傷醫甚至殺醫事件不斷見諸報端,一些醫院通過入院安檢、警察駐守、穿戴防護設備等措施來“保衞”醫生,輿論驚呼醫患關係由“魚水關係”轉變為“水火關係”。在公眾對醫患關係表達不解與不滿的同時,學界對醫患關係也進行了深入的討論與反思。
視角一為市場説,認為醫療行政市場化引致了供方激勵扭曲,依靠醫療服務創收來進行醫院的發展建設與日常運作;加之醫生受醫院考核機制的影響,存在對病患實行過度診療、增加護理等情況,出現醫院與醫生的逐利敗德行為。醫患關係被制度化為市場交易關係,是醫患關係惡化、醫療矛盾產生的根源。視角二為社會控制説,認為醫患關係出現衝突的根源在於醫學與社會之間的“醫療政治”。醫生由於職業聲望承擔了社會秩序中的控制角色,而病患則由於疾病“不可欲”和社會“健康資格化”的原因扮演了對醫生強烈情感依賴的角色。由於文化背景、疼痛態度、對醫生依賴程度等因素的差異,醫患關係呈現出不同的社會控制模式。基於兩者角色期待形成醫生主導的權力差異關係,為“規訓”與“抵抗”之間形塑了衝突結構。視角三為溝通説,重點從就診的微觀活動入手,探究因醫患溝通導致的醫患關係困境。未能清晰説明處方關鍵信息,醫生態度冷淡、醫療呈現問題的方式與無關問題的限制,以及病患帶着未解決問題的離開等醫患溝通,會影響病患就診滿意度,甚至惡化二者關係。
市場説、社會控制説以及溝通説等論點深刻地分析了醫患矛盾的生成機制,但細讀可以發現這些理論敍事均有一個共同而含蓄的指向:醫患關係問題化的根源主要在醫方。誠然,在醫患關係格局中,醫方天然處於優勢與主導地位;但若是把問題全歸結為醫方,則過於簡單化了醫患關係,上述三種傳統視角不可避免地片面解釋了醫患關係的特徵與演變。
技術是區別於市場、控制及溝通的第四種邏輯,醫學技術發展及其組織技術對醫患關係具有重要的影響。“技術改變世界”,在現代社會中技術深刻“嵌入”政治、經濟、文化及社會網絡中;然而,技術卻常因為發揮作用時的“自我隱蔽”而被忽視。波斯曼甚至認為人類社會已跨越“技術使用”階段、“技術統治”階段進入“技術壟斷”階段。在這個技術壟斷階段,技術全面侵入社會日常、顛覆傳統文化、植入意識形態。如在社會成員關係上,技術通過組織形式、文化觀念以及角色再分配嵌入、統治甚至“壟斷”社會成員之間的聯結關係。與傳統社會相比,現代社會醫患關係所處語境已發生明顯技術變遷。醫學技術高速發展,機器學習、大數據和人工智能技術不僅極大提升了醫學影像技術分析能力和醫療健康服務效率,而且推動了醫療信息的傳播與獲取,顯著增加了公眾對醫學知識的可及性。忽視現代醫學技術與信息技術等對醫患關係的“溢出效應”,將導致對醫患關係深層機理缺乏認識與把握,也難以對醫患關係持續惡化狀況作出更加具有穿透力的解釋。由此,醫患關係研究不僅要從傳統的市場、社會與互動維度進行討論,還須關注技術的影響,在一個更加開放的技術語境中加以反思。
綜上,本文將醫患關係納入新的理論框架——技術語境中進行審視,在一個個案——Z姐與K主任醫生的日常診療互動及健康日常中,呈現醫患各自的角色演繹與博弈,進而揭示醫患關係重塑的技術根源,並順應技術發展趨勢展望未來的可行圖景。
醫院“麥當勞化”:標準醫生與百度病患的對壘
以Z姐為例,其看似事業有成、家庭幸福,但自述體弱多病,因職場壓力與家務勞動導致常年遭受頸椎、腰椎、腸胃、頭疼、睡眠等問題的困擾,常自嘲“不在醫院,就在去醫院的路上”。比如,近段時間Z姐就因胸悶多次前往K主任醫生處就診。K主任是一家市屬三甲醫院心內科主任醫生,多年來發表論文、主持課題,獲獎頗多,有中華醫學XX專業委員會委員等一系列學術頭銜,同時擔任碩士生導師,在該醫院算是中堅骨幹。我們在Z姐診療過程中的病史採集、診斷問詢、治療與自療三個主要階段中,一方面可以看到K主任的臨牀實踐是如何踐行標準化審查機制從而引發病患不滿的;另一方面也可以發現病患迷失在互聯網醫療健康信息中,從而與K醫生標準化臨牀實踐發生對抗的深層機制。
(一)病史採集:故事的分離與肉身的疏離
在傳統醫學時代,由於沒有掌握疾病的固定特徵、病程與發病機制,疾病被認為是特殊的、變化的,疾病故事被認為同疾病發生與變化的軌跡具有互滲性關係,因而顯得異常重要。例如神靈醫學時代,脆弱的醫學與巫術糾纏不清,病患需向巫醫講述疾病故事,才能藉助巫醫得到神靈的“啓示”,這一互動過程除了能驅鬼祛病,還能獲得確信的安慰。中世紀期間的臨牀主要以醫生直接觀察為主,根植於生活世界的疾病故事是醫生診斷的重要依據,由此病患聲音得到了充分傾聽與尊重。同樣,中國傳統醫學疾病觀認為,疾病是病患生命格局的偏離並以症狀的方式表現出來,醫生需要了解病患的疾病故事以調解病患的生命態度與生活處境。
現代醫學發展使得醫患疾病的認知產生了分殊。病患主訴疾病故事更願意從自身特殊經驗出發建構性地理解疾病,而醫生的科學疾病觀則遵守標準化的解釋程序,並盡其所能將疾病故事驅逐出去。如解剖學將身體看作一台精密儀器,醫生治療疾病就像工人修理機器一樣,疾病故事自然無足輕重。在生物醫學訓練與實踐中,疾病被還原為細胞、分子等基本物質的故障,疾病故事更是退化萎縮。隨着“互聯網+醫療技術”的應用,疾病故事的價值進一步喪失。以電子病歷的使用為例,在過去的幾十年中,如果説疾病故事價值尚存的證據在於,醫生至少還會對疾病故事進行個性化的編碼,在破舊的病歷本上書寫着讓人費解而難辨的文字。近年來取而代之的電子病歷卻是“模板化”修剪疾病故事,留下極為簡短、非人格化、去社會、去情緒的軀體記錄。在此,趨近界定疾病分類的意向性淹沒了疾病病患的獨特性需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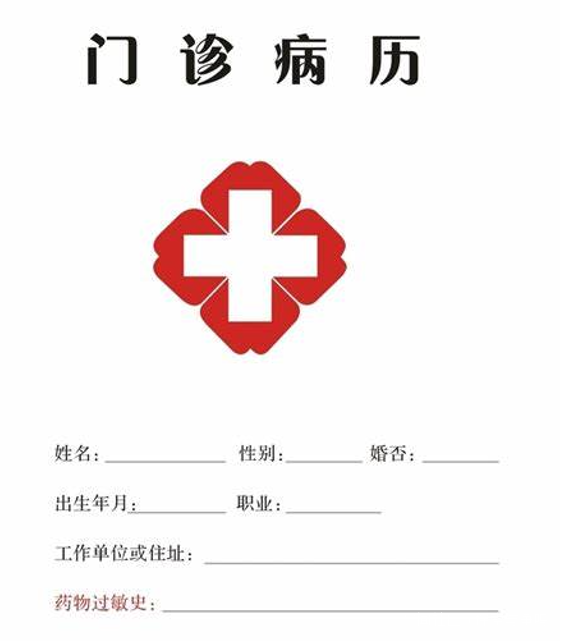
為了讓K主任瞭解整個病情的前因後果,Z姐準備了一個詳細的、有條理的敍述,希望醫生能找出病因並進行診斷。她把要陳述的要點記在備忘錄上演練了數遍,包括哪些症狀、哪些可能的原因、曾經做過哪些相關的檢查、諮詢還需要做哪些相關的檢查。然而,面對Z姐辛苦準備的疾病故事,K主任頭也不抬地在系統電子病歷上的初步診斷欄寫下了關鍵詞“胸悶”。而在主訴欄,生動的疾病故事也被化繁為簡:“間斷胸悶30年,發病7天。”K主任對着電腦用最精煉的文字對病歷進行刪除、改寫和增加的操作,以求病史書寫方式規範化。
在Z姐眼裏,醫生在電子病歷的撰寫過程中對“冗長”的疾病故事不僅是忽略,甚至是排斥的。在Z姐就診於K主任的診室,筆者記錄了當時Z姐自述產後進行過心臟的檢查,結果顯示心臟不存在器質性問題,因此胸悶被認為與“二胎後遺症”並無關係。儘管如此,Z姐經百度搜索,仍將“胸悶”的症狀鏈接上“二胎後遺症”這個疾病故事。在這個過程中,Z姐與K主任的互動並不愉悦。“我講了那麼久,病歷上的‘主訴’欄只寫了一行,而‘初步診斷’欄也只寫‘胸悶’兩個字……那個K主任冷冷的,我説什麼都不搭理。當我問她心臟不舒服與高齡二胎有沒有關係,她只懟了我一句‘百度查的吧’”。
無論是醫生的“冷漠”抑或是大聲呵斥,都是排斥這樣“私有”疾病故事的具體體現。電子病歷去個性化的書寫方式,體現了麥當勞化式系統通過標準化與電子化來實現高效目標的特徵。**標準化不僅是一種高效生產機制,同時也是一種嚴肅的信息控制機制與“注意力分配”機制,有助於組織、篩選和排除信息,禁止不必要的信息進入,只允許數量有限的客觀的非個性化的信息准入。**在這點上K主任坦言一是系統有現成標準模板,二是對自己科研也沒有多少幫助,但主要是因為就診量過大,每個病患平均只有5分鐘的診斷時間,不允許過多地聽取患者傾訴以及對病症的細節描述,即使是他想這樣做但看到門口還有一堆候診患者時又止住了。可見,標準化具有可計算、可預測和高控制等特點,而且一切標準化環節都只為迅速完成一筆又一筆“交易”,醫患情感交互被排斥在程序之外。
與病史採集過程同時進行的是物理檢查。在此過程中,醫生不僅表現出對疾病故事的驅逐,也表現出對病患身體在空間上的疏離。Z姐曾向筆者抱怨K主任通過手搓消毒液和洗手表現出對病患身體的物理空間疏離,以及醫生主動與病患身體在社交空間保持疏離:“醫生其實也很怕病人,那個K主任吧,她要用聽診器給我聽診,我就自然往前靠了一步,她就嚇得往後挪了一步,我立馬就意識到離她太近,自覺地往後挪了挪。那個K主任説了句不要這麼近,坐遠點。我就嚇了一跳。”醫生對病患身體的疏遠並非源於醫生對病患的厭惡情緒,而是一種去個體化的職業化的表徵。醫療檢查尤其是私密性檢查通常需要醫護陪診在場,也包括穿白大褂、戴手套、保持社交距離、去個性化的醫學術語表述來標識職業化行動的界限,以避免醫療檢查中的不確定性,但這種職業化的形式卻極易被病患誤讀為關係的疏離。
隨着醫學技術的發展,醫療的組織管理技術也在不斷調整,使就診、檢驗及手術等程序不斷適合醫學技術的特點而非根據患者及人性的需求進行設計,並趨向標準化或者説麥當勞化。喬治·瑞澤爾形容現代社會中不僅企業,甚至教育、衞生、保健等公共服務行業都普遍奉行麥當勞似的高效率、可計算性、可預測性和全面控制的理性化原則。在麥當勞化的現代醫院裏,排隊、掛號、就診、取處方、取藥,基本都以“流程為中心”的技術要求而非以“患者為中心”的人文關懷展開。疾病、保健、生育乃至死亡都制定了規範化與標準化的作業程序。在這個過程中,從醫生到護士,再到就診者,都像是這個系統中的某一個程序,而不是一個有必要發生互動的個體。在組織管理上,醫生被視為流水線上的工人,圍繞着掛號診察量、處方量、看檢查報告量、開入院通知量、開展醫療服務項目量等KPI指標進行作業與流轉,並嚴格按照標準化的作業程序,普遍採用“審訊式”而非“會話式”的診療話語模式,在實現大規模作業的同時最大程度地規避風險與責任。
(二)醫療診斷:技術檢查與百度經驗的分野
現代醫學要求疾病的診斷必須遵照標準方案與順序。從本質上説,診斷是一個從特殊納入一般的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環,通過診斷可以對個體的疾病實體進行標記、定義和預斷。在Z姐的初診中,K主任遵守了標準化的診斷步驟:首先進行了血壓檢查;在排除血壓問題之後,K主任利用聽診器進一步輔助檢查,仍未能確診;於是,K主任問Z姐是否要做進一步的24小時心電圖檢查,Z姐同意且問是否還要做更先進的檢查,K主任認為沒有必要,但還是會考慮本人的要求。隨後檢查報告顯示“ST下移”,K主任基於以下考慮作出“自主神經功能紊亂”的診斷:在Z姐的主訴中,已進行過多次心臟彩超檢查,冠脈狹窄的器質性問題已經排除;鑑於年齡因素,排除了ST下移的兩種原因之一的心肌缺血,從而診斷指向了另一種可能——自主神經功能紊亂。
對於醫生僅藉助量血壓與聽診器進行物理檢查而沒有進一步做24小時心電圖的檢查,Z姐深表不解,她一邊在手機裏翻找着百度截圖,一邊自言自語,“我網上查了,只要心臟不舒服,一般直接進行24小時心電圖啊”!而K主任也顯示出了對聽診器醫學診斷的“不自信”。聽診器曾經在破解人體密碼的歷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義,正是由於聽診器的使用,醫患交流經由醫療器械而發生,醫生能聽懂身體發出的更加客觀的聲音。隨着病理學、放射學與影像學的出現,數字化、可視化的技術檢查取代了聽診器成為更標準、更科學的證據。相比之下,聽診器有主觀判斷的成分,提供不了精確的診斷依據,只能作為輔助檢查,為此需要更為精確的24小時心電圖來幫助診斷。至於更加複雜的檢查,K主任認為暫時沒有必要,患者的要求是焦慮的表現。

由於服藥三天,胸悶症狀沒有明顯緩解,Z姐不敢大意,畢竟心臟問題是個定時炸彈,手機裏幾乎每天都有職場精英猝死的新聞。於是Z姐再次就診,而在就診前,Z姐與微信網友交流、查閲“胸悶”相關信息之後,陷入更大的迷茫之中。通過百度百科,Z姐查閲得知“自主神經功能紊亂是一種功能性紊亂,多由心理、社會因素誘發,表現為胸悶、頭痛、失眠等”。但在瀏覽各種與胸悶相關的網頁信息時,Z姐越來越發現自己與“心肌缺血”這一心臟的器質性問題症狀更為相似,但需要進一步做冠狀動脈CT檢查才能確診。於是,Z姐搜索並加入了一個自主神經功能紊亂病患的微信羣,和羣裏的病友交流後發現自己的症狀與心肌缺血癥特別吻合,其中一位網友也建議Z姐做冠狀動脈CT進一步檢查。然而,在39健康網“問醫生”的在線互動中,Z姐獲知冠狀動脈CT檢查屬於有風險的侵入式檢查。也因此,當Z姐詢問是否需要做冠狀動脈CT檢查時,K主任不由分説地拒絕了。對患者不斷提到網絡搜索疾病信息的情況,K主任也表示出“不屑”,批評網絡信息魚龍混雜且每個人的症狀不一,不可對號入座,現在的患者不斷提出一些“奇葩”問題,動不動往疑難雜症上靠,還是應通過線下就診方式解決問題。
在此,Z姐源於網絡搜索而來的個性化診斷在臨牀診斷中遭到醫生的標準化壓制。根據現代醫學的診斷指南,心血管疾病診斷順序為物理診斷(如使用聽診器、血壓計)、基本的技術檢查(如心電圖、超聲心電圖)、無創傷性檢查(如24小時動態心電圖檢查);當以上檢查仍無法確診時,才是冠狀動脈CT這類成本高且有創傷的檢查。可見,當Z姐能通過動態心電圖確診時,再做侵入性的冠狀動脈CT檢查確實屬於過度檢查,這不僅加重病患經濟負擔、浪費醫療資源,而且將導致不必要的身體傷害。但對此,Z姐感到十分焦慮沮喪:“醫生怎麼都不聽聽病人的想法和意見?不聽就算了,但必須告訴我們為什麼要做這些檢查、不做那些檢查,嚴不嚴重……動態心電圖檢查的醫生也不肯説什麼,只讓我給K醫生看。這樣看病還不如在家找‘尋*問藥’和‘怡*健康’線上諮詢醫生,態度好又耐心,平均每次諮詢80元,解答非常詳細。”
在身體檢查的數字化時代呈現明顯的“技術分割效應”,醫生既享受技術發展帶來的紅利,也面對技術帶來的對醫生專業與權威的挑戰。當現代醫學的發展將病患等同於尿液、血液、圖像、體温曲線等時,醫生只能將物理與輔助檢查都推給更為精準的“聲光電磁”技術,這既是為了獲得更準確的指標,同時也是回應民眾對科學的期待。其消極後果是,醫生漸漸失去對疾病診斷過程的控制,自主性與價值也隨之退隱,成為病患發泄不滿、怨恨甚至使用暴力指向的主體。而民眾則間接獲得了對健康疾病定義與治療的新的話語能力,在線上線下醫療競爭市場環境下有了更多選擇,對醫生的“規訓”也不再簡單服從。
醫療技術的進步也使得醫生與患者的關係距離愈發疏遠,越來越多儀器代替人工判斷與治療,診所式的個性化藥物也被大批量的認證化工廠藥品所取代。**醫療技術越是先進,越是將患者物化與對象化,患者越是難以和醫生建立更深的聯繫,醫生除了對儀器指標與軀體化症狀感興趣外,對患者的其他“感覺”或“故事”往往採取排斥壓制的策略。**凱博文認為這種排斥有可能是因為擔心故事會使他們糾纏不清,可能遮蓋疾病的跡象從而使診斷更困難,或者干擾針對疾病的治療計劃的實施。同時,醫療知識與技術的分化日益精細,科室與專業也不斷地細分,傳統醫患之間的相對固定性被割裂,本就微弱的關係被一再分解。
(三)學習型病患:自療對治療的沉默抵抗
與臨牀實踐的任何一個階段一樣,治療方案有着高度的專業性,是由有着共同研究目標的醫學共同體成員遵循着共同的研究規範,經過充分交流和臨牀試驗得出的共同體成員一致認可的結果。然而,隨着互聯網技術日益深入大眾生活世界,出現了越來越多搜索醫療信息的“學習型病患”,以自療方式沉默抵抗醫生的醫療方案。市場也通常利用健康大數據與“症狀全舉、對號入座”的策略,誘導個體“患者化”與“自診化”來製造健康危機從中漁利。
海量的網絡養生信息固然滿足了大眾的健康養生與疾病知識補課的需求,但同時也挑戰了臨牀醫學診療的權威性。由於“非常病”與“經常病”,更由於信息技術下健康、養生信息獲取的便捷性極大提升,Z姐成為一個有“經驗”、有“素養”的學習型病患。Z姐每天清晨5點準時醒來,在瑜伽墊上完成5分鐘腹式呼吸之後,接着擴胸運動100次,敲打膽經一遍;按摩心包經和檀中穴各100下;最後貓式舒緩腰背5分鐘……Z姐幾乎每天都會根據狀況對身體進行不同的調試與修復。
因信“是藥三分毒”,Z姐有食療情結。身體略有不適,她首選食療與身體按摩進行自然調節。一旦就醫,Z姐會很謹慎,選擇醫療技術最好的醫院。就診前,會在預約網站查看醫生擅長的領域、職稱、畢業院校以及網上口碑。對於藥品,Z姐每次都要上網查閲用藥説明與副作用,如果傷肝傷腎,她會選擇不吃或減半。對K主任開的谷維素和“博*”兩種藥品,Z姐認為維生素純屬心理安慰,因為網上資料顯示“沒有確切的生物醫學證據證明其有效性”。為此,Z姐並沒有打算服用谷維素。況且,她在微信裏還看到一位山東男子因盲目服用複合維生素而致肝衰竭的事例。回家後,Z姐立即百度查詢“博*”。她很震驚醫生為何要開這種價格又貴、副作用又大的藥品,因為在“春*醫生”裏看到有評論説,這種藥不能長時間服用,否則記憶力減退。Z姐減半服用了3天的“博*”,症狀似乎也沒大的緩解,又害怕副作用,於是就停藥了。令Z姐倍感疑惑的是,百度百科顯示自主神經功能紊亂的發病多半為心理與社會因素,説明藥品治療是沒有必要的,主要靠情緒調節,於是質疑醫生為何還要開藥?最終,Z姐還是聽取了“自主神經功能紊亂”微信羣網友們的自療建議,例如放鬆心情,積極運動;早上艾灸檀中穴半小時;並早中晚拍打檀中穴、按摩心包經各100下。
對於K主任開的中成藥“逍*丸”,Z姐也疑慮重重。事實上,Z姐自小對中藥一直信任有加,認為中藥安全且副作用少。Z姐早就知道,“逍*丸”主要用於疏肝化淤,但她胃寒脾虛,應儘量少服用去肝火的中藥,擔心非但不能治癒自主神經功能紊亂,脾胃反而更加虛弱。當K姐提及這一顧慮,K主任淡淡地回答:“吃段時間看看。”於是,Z姐提議能否換成多位網友建議服用的“開*順氣丸”。可K主任不耐煩地説“沒用”。無奈,她回家後又上網查閲了自主神經功能紊亂的中醫治療文獻,根據症狀下載了一個藥方,並去藥店抓了三副中藥來看看是否對症。
在Z姐的自我治療過程中,各種形式的健康、疾病與養生信息向她湧來,如對記憶力有損傷的博*、被建議服用開*順氣丸、養生拍打、艾灸、疏肝解鬱的藥方……Z姐在多種信息圍獵中不知所措,根本來不及去了解這些信息的源頭。細究起來,病患從網絡上獲取信息的途徑無不令人擔憂——沒有資質的網站、各式各樣的沒有控制組與隨機化的小型觀察,要麼是刊發於不為人知的刊物上的文章,要麼是微信網友的建議,要麼是販賣疾病焦慮的廣告等。在這種情境下,Z姐和眾多病患一樣,迷失在混雜的健康養生信息中,陷入不確定性和喪失掌控力,引發焦慮與困擾,併產生了一系列未遵醫囑的行為。
斯波特認為,現代社會中由於病患自我付費模式的採用,以及對醫學技術進步的期待,權益意識也在不斷強化,傳統意義上的醫患關係在21世紀已經不復存在。隨着信息技術的深入,健康、疾病與養生信息的渠道和總量急劇增加,健康疾病信息的可及性與互動性不斷增強。信息環境的複雜化又使這種主體性變得更加脆弱,大量互聯網健康信息良莠不分,在內容上缺乏信度和效度的檢驗,即便是來自權威機構與專家傳播的信息,也極有可能因為脱離專業知識的語境與缺乏系統的臨牀訓練而被誤讀;並且,許多信息經過大數據用户識別後被選擇性地投餵給大眾,並不斷通過淺薄化與聳人聽聞的標題博取關注。患者互聯網使用時間越長,越不信任醫生。而K主任對這種學習型病患的態度是,“醫生最不喜歡的就是當老師、律師、記者和公務員這些職業的病人,最喜歡問問題,對醫生的話不太信任,喜歡網上查”。當麥當勞化的標準醫生與迷失於網絡信息的百度病患兩者之間不同的慣習被置於同一場域時,新的控制策略與抗爭行動就會被不斷地生產出來。

技術語境下醫患關係演化的邏輯
在Z姐的健康日常與不愉悦的就診故事中,歷經病史採集、技術檢查以及治療過程,隱約可見技術語境下醫患診療實踐中的控制與抗爭。而醫患關係演化的底層邏輯可能在於,技術語境下醫生作為健康疾病立法者的退場與患者健康確定性期待的強化,共同導致了二者由“神-人”向“機-人”關係的轉變。
(一)健康立法者轉向被動闡釋者
鮑曼在討論現代社會中的知識分子角色時,用“立法者”向“闡釋者”轉變來説明其變化。這一概念也非常適用於比喻傳統醫學模式向現代醫學模式轉變中醫生角色的變化。在傳統社會里,醫學知識在信仰等級層次上曾經佔據一種特權性的地位。醫生出現在個體生命變化的關鍵性時刻,減緩身體的痛苦,甚至使用抽象的科學知識語言去解釋個人心靈中的各種困惑,指導人們的生活應該如何進行,告知社會應該如何進行健康管理,從而獲得了極具權威性的作為“立法者”的知識分子認同。在傳統醫學模式下,醫患關係表現為“父權式”關係,患者體驗的表達與醫生的治療解釋間並不存在明顯的分歧。醫生根據患者的生活故事給予解讀,患者相信自身的體驗在醫生那裏得到了理解與確認,因而服從醫生的治療及對生活的指導。
生物醫學的興起對醫者既是“賦權”的過程,亦是“剝權”的過程。技術發展賦予了醫學儀器以壟斷性地位,使得疾病定義逐漸從醫生的話語轉移到儀器檢查測量獲得的指標上,醫生成為各種數據與圖像的被動“闡釋者”,機械而又簡單地解讀其中的個別信息,並略過許多對病症無關緊要而患者想深入瞭解的指標。技術與專業科室的分化使醫生愈發侷限在狹窄的專業領域,失去了對患者健康及整個社會生活進行指導的能力。同時,麥當勞化技術語境下的醫生面臨着更為沉重的工作困境,日常工作中不得不在應對大量患者的同時完成各類考核指標,無瑕顧及患者的感受與故事。

同時,與醫生的知識分子立法者的角色匹配的是傳統私人化醫療場所模式,在時間與任務分配上具備高度的自主性。而在工業化醫院體制中,醫生受到科層制體系化的人員管理,不再具備自主性,除了完成診療任務外,往往還需要完成教學、社會服務及科研工作。為了在“職稱錦標賽”以及各種考核評比中勝出,許多醫生只能忙於撰寫許多隻有醫學共同體成員才能理解的醫學成果,難以與病患、大眾積極互動。作為知識分子立法者的公共意涵不斷消退,**醫生只能習慣於以一種“被動闡釋者”的角色面對迷失又疑慮重重的病患,表現為懶於回應、冷淡、嘲諷甚至大聲斥責等消極應對方式。**令人憂慮的是,在技術語境下這樣“剛性”的臨牀實踐,隨着醫學技術的精深化可能將變得更加突出。
(二)技術確定性轉向健康確定性
人類社會在科學和理性的幫助下實現了巨大的進步,也衍生出科學至上論與技術確定性的傾向,特別是醫療技術進步使社會公眾對戰勝疾病及延長壽命抱有極大的樂觀與極高的期待。如抗生素、激素的問世,X線、B超、CT、核磁、內鏡等各種實驗室檢測儀器的應用,機器人手術、3D打印技術等先進技術的發明,使醫學在疾病面前似乎取得全面勝利,人類對生命長度的期待達到空前水平。同時,公眾對疾病與非健康狀態的容忍度也急劇下降,人人都追求一種確定性的健康,通過對健康的籌劃以對抗生命消失的確定性。因為當失去健康時,疾病的身體就像破損的工具一樣,阻擋着我們用情感、行動、思想獲得對世界的理解。
除去先天體弱以及對長壽與福祿期盼的中國傳統文化底色,恐懼疾病會導致生活失序也是Z姐勤於健康管理的重要原因。她時常感嘆:“與老公的關係為戰略合作伙伴關係,單位和家庭是兩個戰場;怕生病,更怕沒有時間生病。”隨着社會醫學化進程的推進以及健康成為社會“治理術”的主要內容之一,對健康確定性的追求愈加篤定。**健康成為檢驗社會成員是否合格的一項技術,意味着社會成員必須在激烈的現代社會競爭中成為一個優質的零件,滿足社會機器對一個零件的要求。**各類錄用體檢如公務員體檢、婚檢以及私人日常體檢等“健康資格化”過程,都是健康治理術的重要表徵。
醫學技術的進步使人類的平均壽命大幅提高,也使公眾對健康確定性的追求有了具體目標,疾病需要徹底“根治”、人至少要活到平均壽命才“夠本”,是許多民眾的健康追求。對健康確定性的渴望,使得健康永恆的慾望假象被再一次釋放,養生與“治未病”因此成為一種大眾文化——健康是1,其他是0。互聯網信息技術的發展為像Z姐這樣的病患緩解健康危機提供了最便捷、最豐富的渠道。可想而知,當大眾竭力利用形形色色的方式進行健康管理以趨近於完美的健康狀態時,一方面,以市場主義為主導力量的養生大眾文化增加了大眾醫療信息的可及性,從而減少了醫患間的信息不對稱並在一定程度上瓦解了傳統的醫生父權制;另一方面,市場主義帶來的碎片化生活方式與規範意識的喪失而引發專注與反省能力的減弱,加劇了大眾迷茫與身體焦慮,使其不可避免地走向粗俗甚至反智,質疑醫生的權威與合法性,由此滋生了將焦慮外化轉向衝突的可能性。
(三)神-人關係轉向機-人關係
在形塑標準醫生與百度病患的技術語境中,由於臨牀實踐的被動闡釋與健康確定性的轉向,醫患二者主體性不同程度地喪失與迷失,迫使其關係的實質發生了歷史性的變化。
在古代的神靈醫學模式與中世紀自然哲學醫學模式中,疾病的診療依賴於疾病故事的講述-傾聽這一雙向溝通的過程,醫患二者的主體性得到了充分彰顯。在這個階段醫生具有非常崇高的地位,如中國傳統醫生曾被尊稱為聖人、賢人、大夫,而西方古代醫者則大量由薩滿巫醫、僧侶、神父、教士擔任。醫者往往因利用魔法與通靈等技巧而被賦予了神的地位,這兩個時期的醫患關係實質可以理解為“神-人”關係。
進入現代工業社會之後,醫患由“神-人”關係逐漸向“人-人”關係轉變。由於科學技術的進步,醫學逐漸從其他學科中分化出來,成為一門專門的科學技術。與教師、工程師類似,醫生羣體也逐漸專業化,必須經過學院化的正規訓練與資格考試,才能從事醫療工作。而受教育機會的增加,也使得這一羣體數量得以持續擴大,有效地支持了工業化與城市化的進程。雖然專業醫學知識的複雜性使醫生掌握瞭解釋疾病的話語權,病患只能作為醫療被動的“接受者”。但經過教育的“袪魅”,醫生成為一種普通的職業,這一時期的醫患關係可喻為“人-人”關係。
而21世紀的現代醫學、工業技術的發展及信息革命推動了醫患關係實質性的變更,誘使醫患關係轉碼為“機-人”式互動。從研究身體結構與功能的解剖醫學,到醫學細胞分子生物學,在疾病的認知上都越來越精細化、分子化與儀器化,醫生的個人化、經驗化及主觀化判斷的價值趨向下降。與此同時,隨着人工智能化醫療時代的到來,醫生的觀察力、思考力、決斷力等主體性漸趨消失。醫生的診療以大數據、影像技術與遠程醫療等為特徵與依據,任何判斷都不敢與這個系統相左, 也不敢超越這個系統。所謂醫患關係中的“醫”,很多時候只能被重新定義為“醫療儀器”而已。而在以“自由與選擇”為主題詞的信息技術語境下,病患投身於搜索引擎帶來的信息迷宮,混淆了與專業知識的邊界,進而掩蓋了現代社會精英與大眾的“文化非同步性”。“久病成醫”,病患不再是簡單的接受者,而成為醫療知識的“抓取者”“分享者”甚至“生產者”,驅使傳統醫患模式產生深刻轉變。
結論與展望:訴諸闡釋-交往性醫療圖景
**醫患關係不僅是技術共同體,也應是社會共同體。**面對技術對社會系統的壟斷,哈貝馬斯提出訴諸“交往行動”,生活世界可以用來質疑和修正社會系統。或許,置於多重技術語境中的醫患關係重塑與再造的關鍵同樣在於,通過積極的闡釋-交往醫療模式來召回醫患主體性,達成共識性的醫患關係。
就塑造積極的醫學知識闡釋者而言,闡釋-交往醫患關係模式中的醫生既非要重新成為健康與疾病的立法者,也非只做生物數據的消極被動闡釋者,而應成為積極的闡釋者。闡釋行動並非為了免責或是走程序,而是以教育大眾與病患為闡釋行動的目標,旨在實現由“醫生最懂”向“醫患都懂”醫學主導模式的轉變。因此,作為積極的醫學知識闡釋者,醫生的教育職責在於向病患闡釋“帶回家”的知識。將醫學研究的發現與術語轉化為大眾與病患容易接受的二級健康知識,確保醫患理解一致,也包括向病患闡釋“不帶回家”的關切。為了讓病患不要帶着“未述的擔憂”離開醫院,產生額外的心理負擔,闡釋病患的體驗、偏好、價值觀念、生活影響等與疾病關係的真偽非常必要。當然,這也包括闡釋時使用非言語行為,如微笑、認同回應、眼神交流、開放的身體姿態等。無疑,以教育大眾為目的的闡釋活動,不僅對創設醫患互動的理想交談情境具有基礎性的價值,而且預設了“醫學專家-大眾”的界線,意味着從醫學知識到醫學信息的過渡必須是一個由醫學專家主導的過程,更是一個有目標、有策略、喚回醫生主體性的行動過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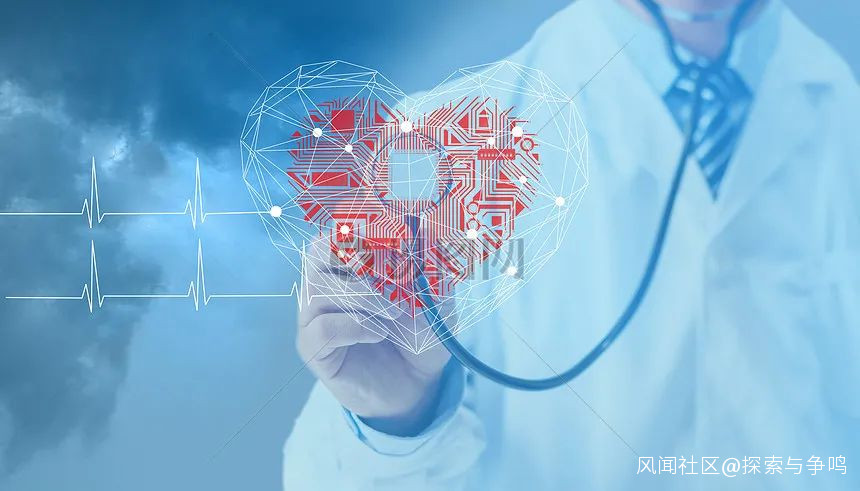
同時,“闡釋-交往”醫患關係模式以塑造有醫學知識信仰的大眾與病患為目標,通過交往行動實現醫療模式從“人的病”向“病的人”的重心轉移。在醫患的闡釋交往行動中同時考慮到病患知識與主體性關照:病患聲音不僅被充分地回應與尊重,而且還生成了醫患知識共識,大眾與病患獲得確定的專業醫學知識與素養以及對健康確定性的客觀把握;更為久遠的是,在此過程中,通過將醫學知識的真與對醫學知識的信仰緊密地關聯起來,重新習得“尊重真理”的社會心態,從而病患的主體性得以在理性的軌道上,有序運行這或許也是解決現代社會個體精神危機的有效路徑,畢竟專業知識理想王國的消亡是極其危險的,專業知識仍是人類賴以仰望的星空。
類似於“闡釋-交往”的醫患關係模式運用於改善醫患關係的努力已經有一定的實踐支撐。例如,美國已實施對病患進行病情介紹、問題解惑、措施解釋、治療建議等的“知情同意”原則和專門開設醫患溝通中心。20世紀初,歐美發達國家如英國、美國、瑞典以及我國港台地區已經將醫務社工引入到改善醫患關係的工作中去。以英國為例,醫務社工的工作主要包括協助醫患溝通、講解醫療常識以輔導病患、收集病患背景資料、幫助病人尋求醫療救助等。我國大陸地區亦於2000年左右,在上海等大城市重啓了中斷數十年的醫務社會工作。
為此,未來的實踐方向需要考慮設立醫患溝通中心或專業諮詢崗位,進一步發揮醫務社工在緩解醫患矛盾中的作用;運用App、公眾號等新媒體方式推動積極闡釋性交往等,用“趨技術化”來替代簡單的“去技術化”,以此形塑新型技術生態下的醫患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