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政治學理論是弘揚民主的嗎?不對,它在一開始是反民主的!_風聞
观视频工作室-观视频工作室官方账号-理性观世界,自信看中国!2022-05-24 14:02
大家好,我是青年up主傅正。
因為疫情防控需要,我被封控在家。這迫使我不得不做出一個非常重要的決定,忍痛採用錄音的方式跟大家分享內容,所以在這幾期節目裏,大家就看不到我機智的小眼神了。
在開始本期節目之前,我先澄清一個小小誤區。我講到美國新保守主義者相信當今世界是一個被文化多元主義敗壞的世界,迫切需要復興美國傳統,以拯救正在走向墮落的西方文明。大家可能第一反應就是MAGA:

事實上,新保守主義跟MAGA不是一個陣營的,非但不是一個陣營,還非常的對立。請大家注意,保守主義跟馬克思主義不一樣。馬克思主義是有一套非常完整的理論體系,儘管西方馬克思主義流派繁多,今天還有新馬克思主義、後馬克思主義,但無論它們怎麼變,都要圍繞馬克思、恩格斯、列寧這些經典作家的作品展開理論闡釋。
但保守主義不一樣,從定義上説,只要堅持或復興本民族或宗教的正統價值,都可以算保守主義。問題是什麼才算本民族、本宗教的正統價值?這個沒有標準答案的。尤其像美國這種文化拼盤國家,到底哪些才是正統的美國精神?這個爭議就大了去了。
新保守主義與MAGA有一個共同點:都鼓吹單邊主義。它們共同的思想基礎,就是美國不屬於歐洲文明,它跟歐洲文明有很大的差別,所以美國也不應該按照歐洲人的方式去做事。
但雙方的共同點也就僅止於此了。就好比説,美國第3任總統托馬斯·傑弗遜和第7任總統安德魯·傑克遜都宣稱美國不同於歐洲,都強調美國要堅持自己的本土特點。但這兩個人的精神氣質相差十萬八千里。傑弗遜是美國知識精英的代表,而傑克遜卻是美國尚武民風的體現。
MAGA跟新保守主義的差別比這個還要大。新保守主義是一種強硬的世界主義主張,強調美國的使命就是要輸出民主價值觀。但MAGA卻是美國民間孤立主義傳統的體現,你俄羅斯跟烏克蘭打成什麼樣,關我什麼事?我不care。我美國沒有義務幫你們擺平這些爛事的,你們要我美國保護你們是吧?給錢。所以你看川普有事沒事就喜歡把伊拉克戰爭的事情拎出來噴一通,反正只要我川普在台上,絕對不會讓美國去趟這趟渾水。
我不久前曾看到有朋友微信羣聊時,講到俄烏戰爭對於美國主流輿論的刺激比較大,新保守主義有捲土重來的架勢。這個我沒有求證過,不知道符不符合事實。不過大家不要怕,我們治不了新保守主義,懂王能治。什麼保守主義都幹不過懂王。
2008年民主黨人奧巴馬贏得總統大選,之後共和黨就出現了建制派和茶黨的分裂。懂王作為第三方勢力強勢登場,這是之前誰都沒有想到的。懂王的登場,讓美國的傳統保守派勢力更加稀碎,我看到有人説分裂為四派,還有説分裂為五派。但現在看來,無論哪一派都不是懂王的對手,誰要是得不到懂王的祝福,誰州議會選舉就成問題。
總之,大家想一想就能明白,一個傳説中什麼都懂的男人,最遭什麼樣的人厭惡?肯定是知識精英對不對,在美國最反川普的就是那些有專業技術職稱的人。新保守主義者都是文化人,比如羅伯特·卡根是一名歷史學家,他有好幾本書早就被翻譯過來了,大家有興趣可以找來看一下。比如大衞·弗魯姆是小布什總統的主要筆桿子,小布什很多演講,包括2002年罵朝鮮、伊朗和伊拉克是邪惡軸心的國情諮文演講就是弗魯姆草擬的。這些人最恨懂王了,哦,你什麼都懂,還要我們幹嘛?
好多他們罵川普的文章都有翻譯。網上一搜就能搜出好多。比方説2016年3月份,川普還在參加共和黨初選的時候,羅伯特·卡根就罵他是共和黨內的“怪獸”,“他現在強大到足以毀滅共和黨”:

去年1月6號國會山事件爆發,大衞·弗魯姆馬上就寫文章,“今晚必須除掉懂王”:

去年10月份,小布什政府的國務卿,也是共和黨內的温和派鮑威爾去世。懂王不按套路出牌,不尊重“人死為大”的基本原則,公開挖苦鮑威爾:

然後威廉·克里斯托爾立馬就噴回去了:

其實早在2020年5、6月份弗洛伊德事情期間,威廉·克里斯托爾就沒少在發推特號召人們起來推翻懂王。
當然,這些共和黨建制派在懂王面前確實戰五渣,得不到懂王的祝福,選民不認啊怎麼辦。於是羅伯特·卡根就十分驚恐地寫道,完了,懂王要殺回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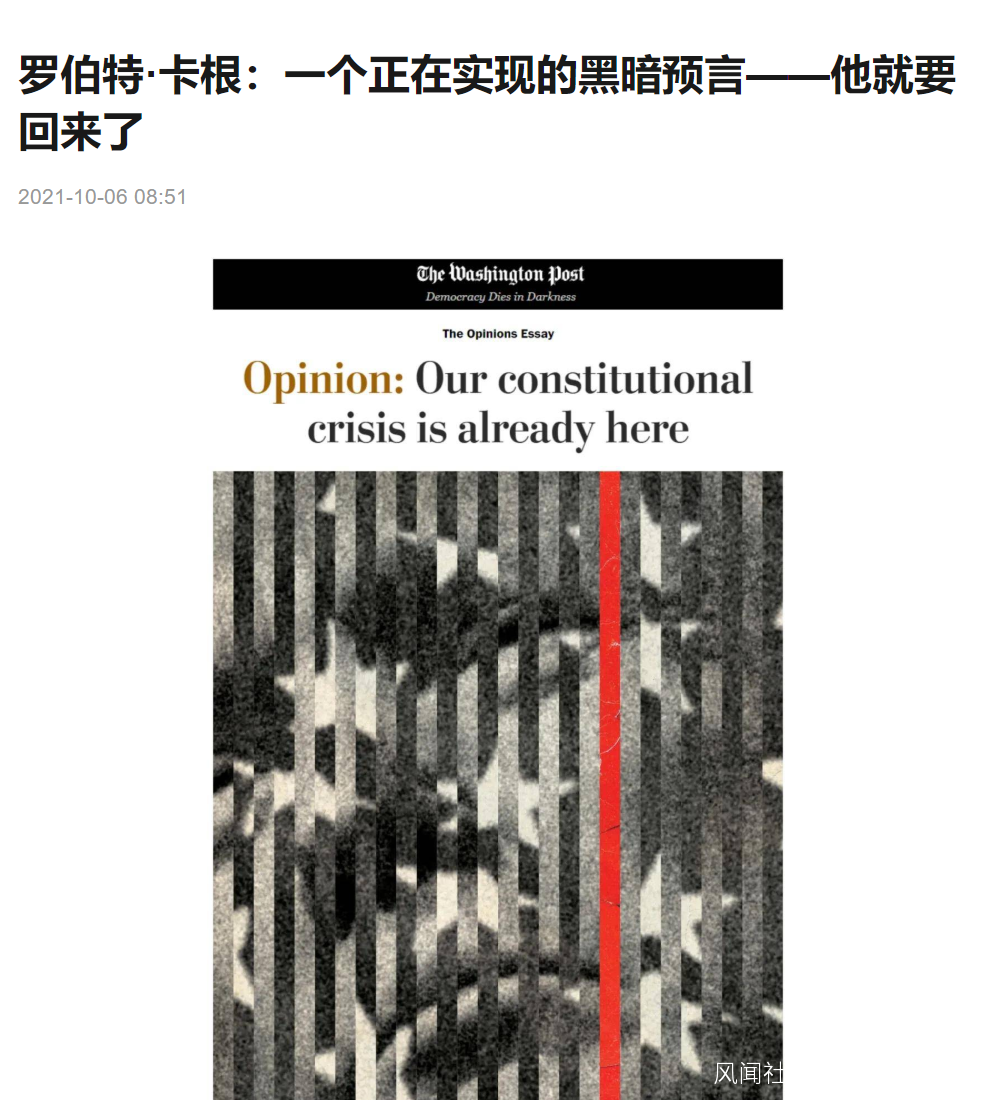
卡根説懂王再度崛起,很可能讓美國陷入自南北戰爭以來最大的政治危機和憲法危機,共和黨內的理智派正在遭受系統的清算:

這些評論基本上反映了新保守主義者跟懂王那種水火不容、勢不兩立的關係。
所以懂王不僅掀起了一股強大的民粹派保守主義浪潮,更讓美國右派分裂得一塌糊塗。
在今天的西方,“自由民主”與其説是一個政治學術語,倒不如説是一個神學術語或宗教術語。它是完全不能反對,甚至不能有一絲一毫質疑的。無論什麼阿貓阿狗,無論他做什麼偷雞摸狗的事情,都必須高舉“民主”的旗號,才有合法性。
不僅西方國家對外干涉,搞“顏色革命”,要喊着“促進民主”或“保衞民主”的口號,抨擊那些自己不喜歡的政權是“反民主政權”“威權主義政權”,甚至“極權主義政權”。就連西方政客內部互毆,也必須打着“捍衞民主”的旗號,抨擊政敵“違背民主原則”。
不僅西方國家對外干涉,搞“顏色革命”,要喊着“促進民主”或“保衞民主”的口號,抨擊那些自己不喜歡的政權是“反民主政權”“威權主義政權”,甚至“極權主義政權”。就連西方政客內部互毆,也必須打着“捍衞民主”的旗號,抨擊政敵“違背民主原則”。
2020年美國弗洛伊德事件就是典型的例子。民主黨和部分共和黨建制派就攻擊特朗普總統“玷污了美國的民主精神”,各種“民主”基金會和NGO紛紛砸錢,用來反對川普。這民主一上頭,真是,連自己人都鏟。
大家回顧一下前年的弗洛伊德事件,不就是美國人拿搞顏色革命的套路搞懂王嗎?
我要是美國黑人,我肯定投票給川普。道理很簡單啊,川普在台上,這些建制派精英還會站在我們黑人這邊,為我們搖旗吶喊,擱着拜登上台了,我死在臭水溝裏都沒人管。要換了奧巴馬時代,弗洛伊德事件算個什麼嘛。然而美國黑人就沒搞明白這個基本道理。
言歸正傳,民主與民主化幾乎已經成為了打着政治科學旗號的當代新神。以至於今天美國政治科學基本只研究怎麼民主化。然而諷刺的是,民主其實不是西方政治的傳統精神。一百多年前,民主在西方政治精英眼裏還不是什麼好東西。
1965年,加拿大左翼知識分子克勞福德·麥克弗森(Crawford Macpherson),這個人的代表作《佔有性個人主義的政治理論》被翻譯過來了,大家感興趣可以找來讀一讀。麥克弗森在一本題為《民主的現實世界》的書的開篇,就説了這樣一番話:
民主曾經是一個壞詞。每個人都知道,民主的原初意義是人民的統治,或政府依據人民的大多數意志統治,這是一件壞事情——對於個人自由和對於文明生活的一切優雅來説都是致命的。從上古時代到近一百年前,幾乎任何有教養的人都持有這樣的立場。然而,在五十年內,民主變成了一個好東西。
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中,民主從一個壞東西變成一個好東西,這個過程從19世紀後期開始,到20世紀中期才基本完成。甚至直到半個多世紀以前,主要還是蘇聯、中國這些社會主義國家在對外宣傳民主,而不是美國。美國當時還在扶持蔣介石、吳庭豔、朴正熙、佛朗哥、薩拉查、皮諾切特等軍事獨裁政權。直到1977年,民主黨人吉米·卡特出任美國總統以後,美國才綁定了人權外交的政策,把輸出民主價值觀作為重要的外交目標。
那麼我們就要問了,西方意義上的民主政治是怎麼產生的?“民主”在西方語境中是怎麼從一個壞東西變成一個好東西的?
我們這次先看第一講,“古希臘人的民主觀”。請大家帶上這三個問題觀看視頻:
第一,雅典的民主政治需要哪些現實條件?
第二,民主與共和這兩個東西有什麼區別?
第二,三權分立學説的原型是什麼?
西方人喜歡把民主政治的源頭追溯到古希臘,尤其雅典政制,被認為是古代民主實踐的高峯,但事情真的是這樣嗎?
一、古希臘城邦世界
古代希臘文明與今天希臘的地理疆域並不完全重合,除了今天希臘的大部分地區以外,還包括塞浦路斯、土耳其東部和意大利南部,但不包括色雷斯地區。

跟古代中華文明不一樣,古希臘文明從來就沒有形成過大一統王朝,它是一羣城邦的鬆散集合。各個城邦之間語言有別、風俗有異、神廟祭祀的主神也各不相同,政治制度也有差異。古希臘史學家修昔底德就指出:
荷馬雖出生在特洛伊戰爭以後很久,但是他從來沒有在任何地方用“希臘人”來稱呼全體軍隊。……他甚至沒有使用“異族人”一詞,大概是由於希臘人那時還沒有一個獨特的名稱,以和世界上其他民族區別開來。
應當説,古希臘之所以能成為一個文明整體,很大程度上還要感謝東邊的波斯人。波斯人的入侵讓希臘各個意識到,我們相對於波斯還是同一個文明。希波戰爭不僅大體確定了希臘文明的範圍,還樹立了歐洲與亞洲的分別。
舉個例子,“專制”(autocracy,αὐτοκρατία)這個詞最初就是亞里士多德用來形容以波斯為代表的亞洲文明。用他的話説:“因為野蠻民族比希臘民族為富於奴性;亞洲蠻族又比歐洲蠻族為富於奴性,所以他們常常忍受專制統治而不起來叛亂。”
這番話到了18世紀啓蒙運動時期,被孟德斯鳩等人扒出來,用來抨擊亞洲專制主義,對於近代歐洲人的文明意識和文明等級論產生了不小的影響。比如20世紀的著名英國軍事學家約翰·富頓(John Fuller,1878-1966)就把公元前490年的馬拉松戰役稱為“歐洲出生時的啼哭”。
但請大家千萬注意,在亞里士多德的語境中,“專制”的反義詞並不是民主,“專制”與“獨裁”也不能劃上等號。專制指偶然、任意的統治,而不是依據自然秩序的理性統治。古希臘人滿足於城邦生活,他們理解不了波斯這種大帝國。這種幅員遼闊的大帝國是沒有辦法推行那種只適應於城邦的公民政治的。
“政治”(Politics)這個詞的古希臘詞源“Polis”就是城邦。亞里士多德有句名言:“人天生就是政治的動物”,也可以翻譯為“人天生就是城邦的動物”。在他看來,波斯帝國不是城邦政治,波斯人就不是真正意義上的人,只是奴隸而已。
需要補充的是,古希臘世界也有帝國。他們的“帝國”跟我們理解的完全不是一回事。它不是指大一統的中央集權王朝,而是指軍事同盟集團。比如雅典領導的提洛同盟,斯巴達領導的伯羅奔尼撒同盟,都是古希臘意義上的帝國。今天也有很多西方學者在這個意義上,把北約稱為“帝國”。
一言以蔽之,在近代西方人眼裏,西方文明與東方文明、歐洲文明與亞洲文明的絕大差異,起源於古希臘文明與波斯文明的分野。古希臘產生的很多核心政治術語一直沿用到今天,成為今天西方政客、媒體最喜歡標榜的東西。但今天西方人嘴裏的這些政治術語,又跟古希臘人的本意相去不可以道里計。比如“自由”(liberty)一詞,在古希臘人那裏指的是城邦的獨立,是指城邦不受外邦人奴役,而不是個人權利或私人空間不受公共權力的侵犯。古希臘人講的自由不是個人自由,而是“城邦的自由”。
總之,城邦構成了古希臘人對於政治的基本理解。所謂的雅典民主政治只能建立在城邦這個基礎之上。
二、民主與獨裁
公正地説,儘管亞里士多德把波斯人稱為野蠻人,但波斯帝國的文明程度其實遠遠高於古希臘。古希臘的民主政治實際上帶有濃厚的部落血緣習性。按照亞里士多德的記載,某個人當選雅典的行政長官以後,需要接受資格審查,通常會被問以下問題:
您的父親是誰,他屬於那一個村社,您父親的父親是誰,您的母親是誰,她的父親是誰,他屬於哪一村社?而後問他是否有祖上崇拜的阿波羅和家庭崇拜的宙斯,以及這些神廟在哪裏;而後問他是否有家族墳墓以及這些墳墓何在;而後問他待他的父母好不好,他納税了沒有,他已服了兵役沒有。
這些問題的實質就是在確認當選人是不是與城邦有確鑿的血緣關係,是不是真正的本邦人。一個人的公民身份是跟他的血緣關係緊密綁定的。這反映出古希臘人的城邦民主實際上體現了比較原始的或比較初級的社會組織結構。
今天的中青年人已經有很少有這種感受了,有傳統農村生活經歷的老人家就能理解,是不是“本村人”不是依據於你是不是生活在本村,而是依據你本村宗族的人,“本村”不是個地理概念,而是個宗族概念。只有列入宗族譜系的人,才有資格參與本村的大小事務。雅典人的公民身份大體上就是如此。
隨着社會生產的發展,雅典城邦的貧富分化日益加劇,有條件從事公民事務的人越來越少,大多數人不得不忙於生計。根據西方學者的説法,公元前5至公元前4世紀,雅典大概有25萬人口,只有不到1000人算是富人,能夠有充足的時間和經歷參與城邦公共事務。
在這個狀況下,雅典出現了尖鋭的階級對立,一邊是所謂的“無賴”“窮人”“下等人”“平民”或“暴民”,另一邊是“有權有勢的人”“優秀的人”“幸運的人”“品德高尚的人”或“貴族”。
因此,民主派與貴族派的鬥爭,構成了雅典政治的重要內容,也構成了雅典民主制改革的基本背景。
公元前594年,雅典人邀請梭倫擔任執政官,這就是著名的“梭倫改革”。公元前509年,克里斯提尼又進行了新一輪的民主改革。梭倫改革的內容、克里斯提尼改革的內容,百度百科上就能搜得出來,我就不重複了。請大家注意兩點:
第一,梭倫改革、克里斯提尼改革的核心要義,就是站在平民一邊,打擊富人或貴族。
第二,也是更重要的一點。平民與貴族的矛盾往往表現為執政官與貴族的矛盾。往往越強悍的執政官,越有領袖氣質的執政官,越熱衷於擴大公民大會的權力,打壓貴族的權力。一邊是執政官聯合平民,另一邊是貴族寡頭,雙方的衝突構成了雅典政制的常態。
我再説得直白一點,所謂的民主制恰恰需要依靠執政官的獨裁或專政(獨裁和專政實際上是一個詞)。雅典越民主的時候,往往就是執政官越獨裁的時候。所以“民主”的反義詞最初根本不是獨裁。
類似的現象一直延續下來,後來文藝復興和啓蒙運動時代的許多思想家都傾向於認為,真正的君主制反而更加接近於民主制,它是與貴族制對立的。馬基雅維利在名著《君主論》的“獻詞”中講過這樣一段話:
正如那些繪風景畫的人們,為了考察山巒和高地的性質便廁身於平原,而為了考察平原便高踞山頂一樣,同理,深深地認識人民的性質的人應該是君主,而深深地認識君主的性質的人應屬於人民。
20世紀傑出的意大利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前意大利共產黨領導人安東尼奧·葛蘭西就發展了馬基雅維利這個觀點,他指出真正的“現代君主”不是某一個人,而是無產階級政黨。無產階級政黨只有在與貴族寡頭的持續鬥爭中,才能真正代表人民,也只有爭取人民,才能戰勝貴族寡頭。
三、雅典民主的巔峯與衰落
雅典民主制的頂峯是伯里克利獨裁時期。按照亞里士多德的披露:
伯里克利所施行的政策,多數是由俄厄的達摩尼得斯建議的,他後來因此而被陶片放逐。此人向伯里克利建議説,既然他不能在其私人財源上佔居上風,就應該取之於民,用之於民。伯里克利採納了他的建議,制定了向陪審員發放津貼的辦法。
為什麼要向陪審員發放津貼?因為這樣才能使窮人有能力參加陪審工作,讓平民牢牢掌握陪審法庭。亞里士多德的信息道出了雅典民主的實質:伯里克利不能在財產上競爭過貴族,就只能拉攏平民對抗貴族。它再一次證明了,所謂的古典民主政治,其前提是執政官能夠運用他的獨裁權力壓倒貴族寡頭。
正是在伯里克利的強力領導下,雅典走向了輝煌的巔峯,讓雅典有能力去挑戰斯巴達的霸權地位。
公元前431年,伯羅奔尼撒戰爭爆發,交戰雙方是雅典領導的提洛聯盟和斯巴達領導的伯羅奔尼撒聯盟。
在戰爭開始後不久,伯里克利就發表了一場《陣亡將士國葬禮上的演説》,動員雅典人為榮譽而戰,為保衞雅典帝國而戰。這場演説對雅典的民主政治極盡吹捧之能事,把雅典的政治體制説成是“其他城邦模仿的範例”,因為這種體制是最民主、最公平的。
比方説伯里克利就講了:
(我們的)城邦是由大多數人而不是由極少數人加以管理的。……法律在解決私人爭端的時候,為所有的人都提供了平等的公正;在公共生活中,優先承擔公職所考慮的是一個人的才能,而不是他的社會地位,他屬於哪個階級;任何人,只要他對城邦有所貢獻,絕對不會因為貧窮而湮沒無聞的。
伯里克利又宣稱,雅典人是最幸福的,他們有最好的物資供應和精神財富:
我們安排了種種娛樂活動,以使人們從勞作中得到精神的回覆。……我們的城邦如此偉大,它把全世界的產品都帶到我們的港口,因此,對雅典人而言,享受其他地方的產品,就如同享受本地的奢侈品一樣。
再比方説,伯里克利宣稱雅典是最開放、最包容的,這根植於雅典人的民主精神:
我們的城市對全世界是開放的,我們從未通過排外條例,以防止外人有機會探訪或觀察,儘管敵人的耳目時而從我們的自由開放中撈取好處。我們所依賴的主要不是制度和政策,而是我們公民的民族精神。
反正,伯里克利總結道:
一言以蔽之,我們的城邦是全希臘的學校。我認為世界上沒有人像雅典人這樣,在個人生活的許多方面如此獨立自主,温文爾雅而又多才多藝。
怎麼樣?這個味道是不是很熟悉。今天美國總統的演講也沒有從根本上超出這些內容吧?
好景不長,戰爭爆發的第二年,雅典城爆發了大瘟疫。伯里克利的統治聲望急劇下降,他本人也因感染瘟疫而去世。此後雅典和斯巴達雙方打打停停,一直持續到公元前404年,雅典戰敗。
在斯巴達人的扶持下,雅典建立了三十僭主制。這個三十僭主制僅僅維持了大半年,民主派發動了反叛。
就在這個關鍵的時刻,斯巴達人果然地拋棄了他們扶持的三十僭主,轉過頭來就跟民主派簽訂條約了。還是得益於斯巴達人的庇護,民主派再次獲勝,雅典又一次進入了民主政治。
只不過這個時期的雅典民主與伯里克利時期的輝煌判若雲泥。它不再有一個強有力的領導人,相反,各方勢力粉墨登場。比如有一些所謂的詩人,他們把各種小道消息編成段子,到處傳播,到處造謠。再比如有一些所謂的智者,他們四處開班講學,兜售修辭學和雄辯術,靠教人怎麼煽動民意來謀生。這好像確實挺像我們今天某一類人的。
所有這些都使得雅典政制走向了衰敗,但它反而促使雅典產生了真正意義上的哲學和政治學理論。
請大家注意,這種混亂不堪的雅典民主政治是西方政治學產生的基本背景。西方政治學在一開始就不是歌頌民主制度,恰恰相反,它產生於對民主政治的反思。這大概就是所謂的“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
我們最後做一個總結:
第一,在西方傳統的政治語境中,民主制就是指多數人的統治,或者説平民的統治,跟什麼代議制或者憲政,沒有一毛錢關係。與之相應,少數人的統治是貴族制,一個人的統治是君主制。
第二,古希臘城邦“小國寡民”的狀態,是其公民政治的基本前提。所謂的共和制最初就是指城邦的公民政治。共和制不等於民主制,它既有可能是一個人的統治,也有可能是少數人的統治,還有可能是大多數人的統治。
第三,雅典的民主政治產生於一種比較原始的社會結構。公民身份是高度依賴於血緣關係的。隨着社會發展,雅典等古希臘城邦出現了嚴重的貧富分化與階級對立。這種階級對立表現為貴族制與民主制之間相互交替。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點,無論是梭倫、克里斯提尼,還是伯里克利,他們的民主改革都是建立在執政官獨裁統治的前提之上。往往是越民主,越獨裁。所以民主最初的反義詞不是獨裁。民主與專政本身就具有親緣性。
第五,伯羅奔尼撒戰爭的失敗,使得雅典走向了一個敗壞的民主制。各路詩人或者智者粉墨登場,煽動民意,他們時而慫恿羣眾焚燒5G基站,時而慫恿羣眾注射消毒液……
不好意思,我真的沒有影射某些國家。反正大家設想一下,你要是一名科學家,看到這些景象,會怎麼想?想到這裏你就能夠理解柏拉圖的政治觀點了。
下一講我簡要地談談古希臘哲學家是怎麼看待民主政治的?他們的理論對後人有哪些影響?
謝謝大家的一鍵三連,我們下集再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