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你不忘少年樣,也無懼那白髮蒼蒼_風聞
秦朔朋友圈-秦朔朋友圈官方账号-2022-06-05 08:45

何志毅 | 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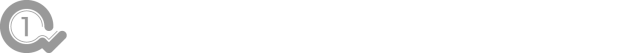
最近幾天,先在車上聽到家人播放的電視劇《人世間》主題歌。此歌,一聽就覺得好聽,然後越聽越好聽。我把詞曲打印出來,把歌詞抄一遍,再把歌一遍一遍地聽。這樣聽歌曲在我人生中只有三次,前面兩次,一次是聽《草帽歌》,一次是聽《心中的太陽》,都是30多年前的情景了。
這歌,首先是詞寫得好,我開始以為是梁曉聲寫的,結果不是,是唐恬寫的。還真是術有專攻,寫小説歸寫小説的,寫歌詞歸寫歌詞的。
查了一下唐恬,女性,1983年生,早年成名,2012年被診斷患癌症,今年39歲。我第一次聽説這個名字,她能夠寫出這麼好的歌詞,好像歷經了滄桑,閲盡了情感,跨越了時空,洞察了人生。據説,她的人生願望是比父母活得久一點。
作曲是錢雷。他受雷佳之邀,與她共同看了60分鐘樣片後,泣不成聲,決定要寫曲子。他是吉林人,片子也勾起了許多東北的兒時回憶。儘管他覺得這曲子很難寫,卻是幾分鐘就寫完了。“當時有個旋律在心中流淌,我就邊唱邊寫,心裏想到什麼就寫什麼”。
令我意外的是,此歌是先有的曲子後填的詞,因為他和唐恬有過多次合作,相互有默契。我猜這個作品是互動出來的,先有曲後有詞,再互動修改磨合,不知道多少回合,不可能是完全地照譜填詞。現在聽到的作品已是渾然天成、天衣無縫之感,似乎天生就是這樣的。
那旋律、那節奏、那斷句,那氣口、那輕重、那調性、那高低起伏、那漸強漸弱……,就連前奏的鋼琴聲飄出的“咪西哆來咪”都好像就天生是這樣,非它莫屬。也許真是我愛屋及烏了。錢雷也是80後,1982年出生的。
再説演唱者雷佳。一查才知她名滿天下,還是中國第一位“民族聲樂表演藝術研究博士”。根據我的常識,聲樂和器樂表演沒有博士學位啊。誰唱得好、器樂演奏得好,誰就該是博士嗎?什麼標準?怎麼衡量?
因此音樂學科的博士都是做理論研究的,也許現在改了?但話説回來,雷佳這首歌唱得實在好,如果説博士裏唱得最好的,好像也非她莫屬了。很難想象有其他人可以唱得更好,很難想象還會有其他唱法的版本。
這首歌曲的音域跨度是兩個八度加半度,雷佳處理得絲絲相扣、爐火純青。看着譜子自己哼哼,絕對想不出這歌能唱到這種程度。據説這不是雷佳的一貫風格,但絕對體現了她的藝術水平。真聲、假聲、高音、低音、呼吸換氣,如泣如訴、或柔或強,淺唱高亢,拿捏得都恰到好處,扣人心絃。雷佳是1979年出生的,也相當於80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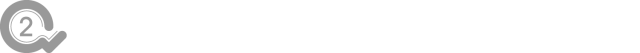
這詞、曲、唱家三人的合作令人拍案叫絕。我聽歌曲之前對此三人都毫無所知,在潛意識裏,我以為他們都可能是梁曉聲的同代人,實際差了一代人。
由此我感慨,這一代人確實很優秀,絕不亞於上一代人。以此為例,詞、曲、歌都不亞於上一代人。其實延伸到其他領域裏也當如此,例如航天、航空領域等等。因此我們應感到欣慰。
前幾年,在看德國電影《我們的父輩》時,我曾經感嘆,該電影的編劇、導演、演員俱佳,他們是德國的第三代人,把二戰時期他們的父輩(廣義)的方方面面演繹得淋漓盡致。
要知道以德國人的身份描述二戰是一件很困難的事,儘管是在戰後八十年的現在。那使我感覺這一代德國人確有人才,由此可以推理不僅在文藝方面。
而《人世間》主題曲給我的感覺亦是如此,他們不到40歲,不到不惑之年,卻似乎早已不惑了。
一代勝過一代,是歷史規律,除了極少數天才人物和特殊時期之外。我想向所有的80後説,人世間是我們的,也是你們的,但歸根結底是你們的。
繼續譜啊,繼續寫呀,繼續幹喲,繼續歌唱吧!
祝你不忘少年樣,也無懼那白髮蒼蒼。我們啊,像種子一樣,一生向陽。在這片土壤,隨萬物生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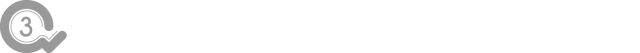
前天是端午節,每年我們都在此時紀念一個因為解決不了問題就解決自己的屈原。我們為什麼紀念他呢,因為他是寫了《楚辭》的大文豪?因為天問沒有答案?因為九歌沒有迴響?因為他找不着了生的意義則勿寧死?反正他衣袂飄飄縱身一跳,成為永恆。是啊,也是永遠的少年樣了。
他是楚人,他把楚當作國,後人不能要求他把統一後的秦當作國,當作未來中國分久必合的大國之基。我們看重的是他的文人氣節和愛國情懷。既然解決不了國破的問題就解決自己吧。這種解決是一種解脱,是一種昇華,是一種抗爭,是一種悽美。2000多年之後,我們還用全國人民放假一天來紀念他。
他潛移默化地影響了一代一代的中國人。於近代我們有王國維等,在我們的時代,有老舍,傅雷,鄧拓,翦伯贊,嚴鳳英,上官雲珠,榮國團,吳晗,範長江,聞捷,熊十力,顧聖嬰,……等等,這個名單很長。
但是解決不了問題就非要解決自己嗎?除了解決自己之外還有什麼其他辦法嗎?我想至少還有三種辦法。
第一種,解決其它小問題。例如陳寅恪解決了柳如是的問題。他用了8年時間,為十七世紀的“秦淮八豔”之首柳如是寫了82.3萬字的《柳如是別傳》,他雙目失明,還持之以恆完成了這個三部頭的大著作。
第二種,忍辱負重,以待時來運轉。在《趙氏孤兒》中有個經典問題,生難還是死難?公孫杵臼認為死易生難。於是他選擇了死,把更難的事情留給了程嬰。季羨林先生在特殊時期中也準備死,因為安眠藥還沒有存夠,他就被抓去批鬥、掛牌、遊街,回家後想想最壞也就不過如此,於是豁然開朗,不準備死了。而後,迎來了柳暗花明的大好年華。
第三種,培養能夠解決問題的人。楊昌濟先生是個典型,他一介書生卻培養了許多雄才大略、文治武功的解決問題高手。他曾對當時的教育部長章士釗説,君不救國則已,要救國,則必須倚重毛澤東、蔡和森。當時的毛澤東等人都是二十多歲的初出茅廬之輩,這是何等的英明自信。
屈原已經成為中華民族文人氣節和愛國情懷的符號。我們要繼承的是他那種高潔的氣節和深沉的情懷。但我更倡導用這種氣節和情懷去解決問題,而不是解決自己。
有屈原一個人解決自己就夠了,我相信他並不希望別人都學習他解決不了問題而解決自己,而是用解決自己去激勵別人解決問題。這就是我們世世代代紀念屈原的意義。我們需要白髮蒼蒼仍有解決問題的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