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峯|“教材事件”之後:專家系統怎樣重建民眾信任?_風聞
探索与争鸣-《探索与争鸣》杂志官方账号-2022-06-15 07:56
羅峯|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助理研究員
本文系“探索與爭鳴”微信公眾號專欄專稿
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編輯部立場
非經註明,文中圖片來源於網絡
一、專家系統失靈偶然與必然
5月底以來,中國教育部下屬的人民教育出版社(人教社)出版的小學數學教材插圖事件在我國互聯網輿論場中持續發酵(以下簡稱教材事件)。而對於該事件的關注也逐漸脱離了教材插圖本身,發展成為全民尋找“有毒教材(讀物)”的風潮。相關討論也從審美的爭議逐步上升到西方文化的滲透,甚至更為嚴重的指控。僅就教材事件本身來看,其實充滿了令各方都為之詫異的偶然性。普通民眾(尤其是家長們)詫異於如此不符合大眾審美的怪異形象及其背後隱藏的不良內容,能夠堂而皇之的成為中國孩子們的必讀教材;一線教師們詫異於在2014年就已經有人專門提出異議的同時,這份教材還能挺立至今。而令包括筆者在內的學術圈人員詫異的則是,出版社的制度和流程為何失靈?

人教版數學教材插圖
**事實上,筆者認為,這種令人詫異的偶然性背後,卻反映出專家系統(在本文中表現為專業的教材出版團隊)固有缺陷的某種必然性。**20世紀末,吉登斯在《現代性的後果》中,專門論述了現代社會中兩種脱域機制。由技術成就和專業隊伍所組成的體系——專家系統正是其一。民眾依託對於專家系統的信任來面對諸多現代社會中不可避免而又無法理解的專業情景,專家系統從中獲得基於信任的符號權力,而民眾則獲得在對抗現代社會中免於焦慮的安全感。但是,專家系統的固有缺陷也使之面臨着無時無刻的脆弱性。首先,專家系統中某些個體不可避免地存在知識的侷限性。民眾對於專家系統的信任,並不針對某個個人或組織,但是卻必須建立於某些具象化的個人或組織之上的。而現代社會的分工細化,使得任何專家脱離了自己的領域都等同於普通人。其次,專家系統的建立,即信任建立與維繫,無法脱離交匯口這一樣一個非專業性個人或團體與抽象體系的代理人之間的連接點,而這恰好是專家系統的薄弱環節。因為,交匯口為民眾與專家提供了廣泛的接觸機會,並讓他們能夠捕捉到專家在面對具體議題之時的無能為力,從而失去對專家個體,乃至整體專家系統的信任。恰如吉登斯所言:如果一個人發現所僱來的“專家”根本就不能正確地安裝中央空調,他也許就會決定在學習了有關基本技能後自己去安裝它。
本次事件中的交匯口就是教材。畢竟,再沒有什麼能比教材更能定義知識了。而它所觸及的議題——青少年教育,既重要到被國家乃至每一箇中國家長所在意,又廣泛到民眾能夠普遍接觸並提出自己的見解。從網絡上的輿論來看,民眾對於事件中專家系統的不信任,已經超出了對其專業知識與技能的不認可,更產生了對特定專業人士品行方面可靠性的指控(例如對涉事專家們的指控:脱離羣眾、知識結構侷限以及缺乏紅線意識等等),甚至是對專家系統內部知識生產機制有效性的質疑。這種局面,並不是相關部門道歉、整改與徹查就足以解決的。更需要籍此對社會科學研究界的專家系統進行一次系統性反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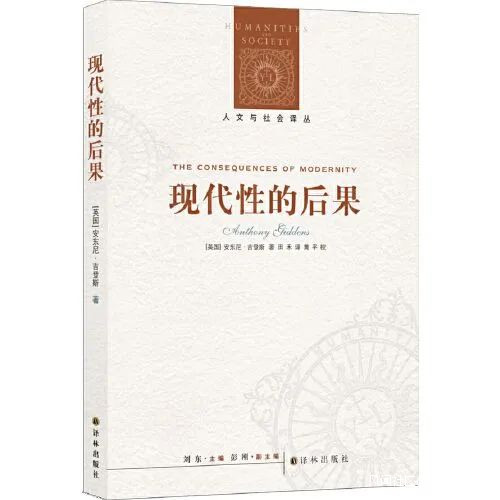
二、共享知識的分野
在現代的教育體系中,“第一原則”,即知識在原則上是不容質疑的被普遍遵從。這一點在傳統中國文化中“尊師重教”的價值觀下得到加持。因此,很多時候,在教育過程中,專業主體(學校、教師,當然也包括教材)與家長這樣的非專業主體之間產生分歧之時,非專業主體總是天然地傾向於聽從專業主體的意見。雖然,很多時候,對於自己專業知識不可辯駁的認識,是被專業主體用來建立相對於非專業民眾優越感的工具。而且,專業人士從書本中得來的知識,並不一定比一個歷經現實的民眾更加深刻。可惜的是,並不是所有知識(包括但不限於社會科學)都能夠長期保持這樣的優勢,甚至可以説,只要是和社會、民眾產生重度關聯的科學,都不具備這種特質。尤其是在大眾審美(例如教輔材料的插畫)這樣無法脱離社會意識土壤的領域。更遑論專業體系內部也有無數的小羣體,以及更加爭鋒相對的知識分歧(例如在教材事件中的一線教師與教材編纂專家們)。
如果將教材生產所涉及的專家系統予以整合,無疑是布迪厄筆下文化生產場域的經典類型。在這之中,教材審核團隊授予並認可了編纂者參與教輔材料插畫繪製的合法性地位,而這份賦予合法性地位的權力則來自於教育行政體系的下放。教育行政體系的權力下放,是基於對專家系統內部自我認可的信任,卻有意無意地忽視了專家系統自我認可的背後,複雜的個體關係。當然,事後來看,這種個體關係確實體現出了教輔材料插畫繪製專家們所擁有的外人無法比擬的“藝術家的稀缺性”(具體參見呂旻、呂敬人、吳勇、鄭文娟之間的關係)。然而,如果不是民眾與專家系統之間,在教材這個知識之上所擁有的分歧過於激烈,進而使得矛盾暴露於眾的話,這份稀缺性原本可以被很好地隱藏。
在論及媒體全球化擴張的影響之時,很多人都會天然的認為,這會導致社會大眾都去接受無比豐富卻又趨同的信息。正如《現代性的後果》一書中説的那樣,十九世紀晚期,報紙的閲讀者,就好像都在“同時關心着發生在智利的革命、東非的叢林戰爭、中國北方的屠殺和發生在俄國的饑荒”。事實可能並非完全如此。**趨同的信息並不足以使所有人都共享一套趨同的認知。因為,民眾認知的建立,並不侷限於接收到來自媒體的信息,更立足於自己所處的社會地位與社會遭遇之上。**例如,在同樣閲讀那份報紙中有關中國北方的報道(從上下文推斷,很可能是1891年的金丹道事件)之時,滿清統治者看到的是發生在自己統治核心地段(內蒙古)的不穩定;中國革命者看到的是滿清政權對於漢族的民族與階級雙重激烈壓迫;宗教同情人士則可能會攻擊清政府在對於宗教的包容程度。因此,社會羣體之間的割裂,對同樣的信息乃至知識,持有截然不同甚至相互對立的認知的情況並不罕見。而在教材事件中,無論插畫繪製團隊及其支持者們,如何用獲得專家系統認可的專業性以及審美多樣化等作為理由,都無法顛倒民眾心中保護兒童(尤其是自己的孩子)的樸素情感、對於民族國家的基本認同、以及對於類氏三體綜合徵患兒那詭異面目的天然“厭惡感”。
三、媒體?不,媒介的勝利
回首這次教材事件的發酵可以發現,很多關鍵節點都是民眾之中的專業人士所推動的。這之中,既有最早就向教育部門進行郵件投訴的一線教育工作者,也有發掘插圖細節乃至幕後人物關係的不知名網友。這無疑與民眾僅能作為專業媒介的傳播受眾的既有印象大相徑庭。與之相對的,諸多媒體的專業從業者(無論是傳統媒體還是互聯網新媒體),更多時候都只是在扮演一個信息整合者的角色,而非原本自我期許的事件挖掘者。所以,本次事件更可視作一次現代媒介的勝利,只不過這個勝利的主體並非專業媒體人,而是與民眾相結合的媒介本身。
事實上,布迪厄已經非常詳細的論述了,**在知識的生產與傳播場域中,都不可避免的隱藏着權力爭奪的主線邏輯。**而在知識生產的學術專家系統和知識傳播的媒介專家系統看來,這份權力爭奪的對象都是國家或者資本,並且以保持相對於他們的獨立性為榮。而民眾則天然應該是屈居於他們之下的知識施與者,畢竟,自己才擁有無可辯駁的知識優越性。然而,這種優越性導致了上述專家系統在不懈努力試圖從國家或者資本手中奪取有形權力的同時,更加試圖將這份獨享知識的符號權力更加長久且牢固地攥在自己手中。
可惜的是,現代社會的複雜與多變,使得這種知識壟斷的企圖被一次次打破。這其中的原因,既有現代社會飛速的知識迭代導致了知識價值的速朽;也有專業知識高度分化導致了全能知識分子的出現成為不可能;更有知識傳播的便捷帶來了全民知識素養的提升;**更重要的是,知識出現了一種新的發展形式:“回濾”過程。非專業人士能夠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不斷地以這樣和那樣的形式,對各種專業知識進行再佔有和再使用,進而完成新的專業知識的再生產與再傳播。**這一切都進一步降低了專家系統中,每一個個體專家存在價值。從樂觀的角度來看,這恰好印證了專家們所一直強調的,民眾啓蒙(雖然其啓蒙是整個社會發展的結果,而非某個專家的實現。因為至此,民眾已然具備了在特定議題(尤其是那些與自己的價值體系以及生活閲歷深度關聯的議題)與專家體系進行討論的能力。而這份能力在與現代媒介相結合之後,又深刻改變了知識場域中的權力邏輯,因為出現了一個能夠爆發出令所有人都為之炫目能量的新玩家。
四、學術共同體的信任重建
至此,專家系統可能開始面臨前所未有的獨立性與專業性的雙重存在性危機,向上有來自國家與資本等維度的有形權力之約束,向下則有無數完成啓蒙並在特定議題中專業性不下於己的民眾的符號權力之爭奪。這也意味着,包括但不限於社會科學專家們組成的學術共同體們亟待信任的重建。正如《現代性的後果》中一直強調的那樣,信任是對抗存在性焦慮的基礎。而這份焦慮也並非為非專業人士所獨有,甚至對於專家而言更為重要。畢竟信任關係的失去乃至對立,對於民眾而言,只是生活中面對某些專業場景之時的偶爾焦慮,而對於以此為生的專家們來説,更可能意味着存在價值的喪失。
因此,學術共同體的信任重建,既需要面向民眾,也無法脱離民眾的參與。這種參與,一種是教材事件中所體現出的這樣,在事後進行監督和糾正。另一種,也更為有效的則是在事前和事中就直接參與到專業知識的生產與傳播之中。正如被國內專家們所推崇的“民主國家”,總是有些使公民捲入政府程序的過程。將這一過程嫁接於某些領域專業知識的生產之中,無疑正是知識民主化的應有的題中之義。而民眾的深度參與,不僅有助於生產出更加符合現實需求的知識,更重要的是,可能發展出一種學術共同體建構的新形式。對此,我們有理由抱以樂觀。因為在歷史上,中國的民眾已經多次證明了自己經過啓蒙和組織之後的力量,並將在未來繼續證明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