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後,嘉湖“第二次握手”_風聞
秦朔朋友圈-秦朔朋友圈官方账号-2022-07-12 08:18

· 這是第4597篇原創首發文章 字數 3k+ ·
· 土哥涅夫 | 文·
對於生活在錢塘江北岸的浙江人來説,杭嘉湖、杭嘉湖,似乎是個脱口而出的並列稱呼。因為它既是一塊完整的地理單元,也是區別於江對面“上八府”的文化存在。
其中,杭州作為省會,是天然的帶頭大哥。而嘉湖兩地,早在15年前杭州都市圈剛啓動時,便已作為重要的核心成員參與進來。杭海、杭德等城際軌交的陸續建成或規劃,浙大海寧國際校區、浙工大莫干山校區、浙傳桐鄉校區等高校的佈局,更是説明了這種水乳交融的連接。
然而,最近公佈的浙江省第十五次黨代會報告,卻出人意料地打破了上述固有格局。在這場註定將影響未來很長一段時間浙江區域版圖的大洗牌裏,嘉興湖州被單拎出來,形成新的城市組團,並被賦予了“共建國家城鄉融合發展試驗區”的使命。
杭嘉湖要分道揚鑣了嗎?其背後究竟發生了什麼,又意味着什麼?難道一切的一切,都只能用那句老話才解釋得清: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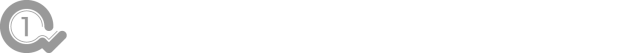
中國人喜歡説“自古以來如何如何”,要是照此標準,那麼杭嘉湖“自古以來”還真不是一夥的。直到今天,除了海寧以外的嘉興地區,基本都是親滬勝於親杭的。
這是因為,上海地區(古稱華亭縣、松江府)是元朝至元十四年(1277年)從嘉興分出去的。而嘉興在後唐同光二年(924年)吳越國王錢鏐設立開元府前,則長期隸屬於蘇州。
所以,滬蘇嘉才是真正的一家。
至今,蘇滬嘉小片仍是吳語最重要的方言單元。尤其是滬嘉兩地。別看近世上海話深受蘇州、寧波的影響——最明顯的例子就是上海話中“我”的兩種叫法,“阿拉”來自寧波話,“我伲”來自蘇州話,但就整體相似度來説,嘉興城裏話跟上海城裏話最為接近,甚至超過上海一些郊區方言(如崇明)。
因此,過去,一些嘉興人跑杭州辦事,常常被誤認為是從上海來的。
至於湖州,其作為州郡的歷史,更是遠久過杭州。當吳興郡(湖州)已經與吳郡(蘇州)、會稽郡(紹興)三足鼎立,並稱為“三吳”之時,地處三郡交界處的杭州,還只是個藏在靈隱山中的小縣(錢塘縣)。雖然隸屬於蘇州,其實是片三不管的狹長地帶,經濟水平遠不及同樣屬於蘇州的嘉興、華亭等望縣。
正是因為不重要,錢鏐的老大董昌在佔領浙東後,才會移鎮越州,而將杭州讓給錢鏐。
真正使杭嘉湖形成共同體意識的,是明太祖洪武皇帝。要不是這老兄在江淮之間任性地畫了個圈,把江南大量州府劃為直隸,從而打破了唐宋以來兩浙地區以錢塘江為界,東西各八府的格局,形成了後來“上八府、下三府”的不對稱新局面,杭嘉湖或許也不會那麼抱團。等到了清朝,隨着杭嘉湖道的設立,三地終於真正意義上成了一家人。
進入民國後,杭嘉湖又同屬於錢塘道,直至1927年道制被廢,杭州作為省會,成立省轄的杭州市。到1949年新政權成立時,浙江總共只有杭甬温三個省轄市,這也奠定了他們仨的地位。而嘉興湖州兩地則被合併為嘉興地區,地委先在嘉興,後遷湖州,直到1983年分家,兩者同處一地領導下,時間長達34年。
難怪至今,兩地“邊界”上仍有不少糾纏不清。其中最有名的莫過於烏鎮。今天的烏鎮,歷史上以市河為界,分為烏青二鎮。河西的烏鎮,屬湖州府烏程縣;河東的青鎮,則屬嘉興府桐鄉縣,直到1950年才合二為一。也因為此,對於像茅盾等文化名人,在當時究竟應該算嘉興人,還是湖州人,兩地網民多年來一直拌嘴不斷。
好在中華智慧博大精深,一句“打是情、罵是愛”便將齟齬化解於無形。況且分家近40年後,如今浙江的區域經濟格局,早已不允許嘉湖內鬥。隨着温台、金義等的相繼崛起,嘉湖再不抱團,真的快沒一席之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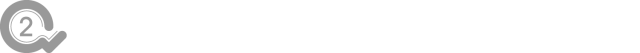
83年分家時,嘉興得海,湖州得山。不過總體來看,這兩個地方的市民性裏,既沒有海洋族羣的闖勁,也缺乏山區人民的堅韌。
得益於杭嘉湖平原的豐饒地利,在魚米之鄉、絲綢之府浸淫了千百年的嘉湖人,早已養成了安耽白坦的性格,習慣了小富即安的生活,對於在市場大潮中縱橫搏殺的興趣不大。
以至於那麼多年過去了,嘉湖地區真正能報的上名字的大公司和企業家屈指可數、寥落晨星,反倒是上八府那些“地無三尺平”的窮地方,一個個靠着“雞毛換糖”、手工作坊實現了逆襲。
這種“逆水行舟,不進則退”的城市競爭狀況,最直觀地反映在年復一年的經濟報表上。1978年改革開放之初,嘉興GDP13.29億,在浙江省內僅次於杭州、寧波,甚至還領先温州;而湖州8.88億的GDP,也相當於金華的九成。
但隨着上八府鄉鎮企業、民營經濟的蓬勃崛起,到了1990年,嘉興GDP開始被紹興超過,1991年又被温台趕上,1995年更是落到金華後頭。最低谷時,嘉興GDP排名屈居全省第七。雖然在世紀之交反超了金華,但是與第五名台州的纏鬥,卻持續了整整20年,直到2019年才分出勝負。
而比嘉興更慘的,要數湖州。由於既不在滬杭甬、滬寧這兩條幹線通道上,又被太湖隔開了蘇錫常,湖州過去堪稱長三角的交通死角。受到區位的拖累,很長一段時間內,湖州的發展始終不盡如人意。省內排名“萬年老八”不説,GDP總量一度只有金華的60%都不到。
所以當1994年湖州日報刊出《為了太湖不再傾斜》一文,立馬引發全市上下的大討論。而關於“湖州與同處太湖流域的蘇錫常,發展差距為何越拉越大”的反思,更是持續至今。期間,湖州也不是沒做過各種嘗試與努力,比如2013年時就曾想將長興撤縣設區,在太湖南岸一線打造統一的城區框架,可惜最終功敗垂成。
而與此同時,周邊城市卻一個個相繼崛起,這也使得近些年湖州的地位愈發尷尬、落寞。GDP在江浙滬排名靠後不説,甚至都被蕪湖、滁州等安徽城市趕上或反超了。
如此局面,對於湖州來説,光靠內部整合、自己單打獨鬥,要想在強手如雲的長三角殺出一條血路,已經很難了。求助外援甚至抱大腿,可能是唯一的辦法。只是,在大多數人的預想中,這條大腿要麼是上海,要麼是杭州,萬萬沒料到,最後牽手的竟然是嘉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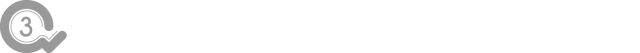
嘉湖的這次聯手,目標是“共建國家城鄉融合發展試驗區”,而這正是兩地的拿手好戲。
長期以來,嘉興湖州在網上被戲稱為“種田嘉”“養魚湖”,搞得好像兩個落後大農村似的,但其實,這裏恰恰是全國城鄉發展差距最小的地區。特別是嘉興,其農民收入曾連續多年排名全國第一。2021年,嘉興城鄉居民收入比為1.6:1,遠低於全國平均的2.5:1。
除了農村發達,嘉興城市發展這幾年同樣風生水起,否則也沒有底氣喊出“打造長三角城市羣重要中心城市”的口號。而這一切,都得拜長三角一體化所賜。
作為中國面積最大、人口最多的城市羣,如果從1982年12月全國人大提出“編制以上海為中心的長江三角洲經濟區規劃”算起,長三角城際合作到今天已經走過整整40年了。但直到2019年上升為國家戰略,長三角一體化的進程才真正開始加速。而地處江浙滬交匯處的嘉興,也是從那時候開始,迎來了城運的風口。
當時距離我離開西塘,僅僅過去半年。在此之前,我在那裏幹了三年多的文旅。因為覺得跟烏鎮的差距越拉越大,所以公司開發的內部房也沒買,就拍屁股走人了。結果前腳剛走,長三角一體化戰略便橫空出世,西塘連同周邊姚莊、黎裏、金澤等鄉鎮,被劃為一體化示範區的先行啓動區。而我們開發的那片區域,定位也變成世界級科創綠谷,瞬間鳥槍換炮,房價也跟着翻番。
不只是西塘,也不只是西塘所在的嘉善縣,整個嘉興都因為一體化而彷彿打了雞血,再加上去年“第一個百年”的契機,嘉興的城市建設迎來了一次蜕變。高架建起來了,南湖湖濱亮起來了,寸土寸金的市中心崛起了以子城、天主教堂為核心的大片遺址廣場……曾經的“縣城嘉”,終於有了點大城市的模樣。
如果説城建蜕變為嘉興長了面子,那麼產業經濟的快速發展則夯實了其裏子。自從2019年GDP超過台州後,嘉興勢頭不減,迅速逼近紹興。“十四五”規劃甚至喊出“2025年破萬億”,要知道,温州的目標也只是破萬億。
而比GDP數據更亮眼的,是嘉興近年來的人口情況。根據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嘉興人口達到540萬,超過了紹興、常州等競爭對手。十年增加了89萬,排名全省第四,大幅領先温台等人口體量更大的城市。特別是一體化戰略出台後的這幾年,嘉興每年的人口增量都僅次於杭甬,不僅領先省內其他城市,甚至能力壓南京、蘇州等大城市一頭。
雖然現在談論嘉興能否趕超温州,上位“浙江第三城”還為時尚早,但可以肯定的是,隨着通蘇嘉甬、滬乍杭等高鐵十字網絡的建成,嘉興作為浙江新一極的地位將逐漸凸顯。
與此同時,一旁的湖州也藉着長三角一體化的東風,拿下了直通上海的滬蘇湖鐵路。加之商合杭、杭寧高鐵的相繼建成,曾經的交通死角,正在變成浙北通向安徽、江蘇乃至中部地區的又一個樞紐節點。
或許正是看到了這種變化,所以浙江方面才會將嘉湖單拎出來,形成新的城市組團。事實上,早在去年浙江謀劃毗鄰地區先行一體化時,便已有此苗頭。
作為推進長三角一體化的分拆步驟,當時浙江確定了杭嘉、杭紹、甬紹、甬舟、嘉湖等五大重點區域一體化合作先行區。其他幾個都是圍繞杭甬兩大核心城市展開的,唯獨嘉湖一體化先行區合作雙方均為普通地級市。而這一次,嘉湖組團甚至被排在了金麗衢前面。要知道金義都市區可是浙江四大都市區之一,這就更能説明問題了。
當然,考慮到除了嘉湖,杭嘉、杭湖(主要是餘杭與德清)之間也在推進一體化,所以説,杭嘉湖分道揚鑣是不準確的。它們只是兩兩組團,這樣,彼此的融合反而更加緊密,浙江的經濟重心,也將隨之進一步北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