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減政策實行一年後,孩子們真正減負了嗎?_風聞
精神状态不太好-2022-07-13 14:44
雙減政策出台已經一年了,這一年裏,孩子們真的減負了嗎?
貌似不是這樣的。甚至反倒是家長們花的錢更多了。
看到公眾號“每日人物”裏一些孩子媽媽們以及很多網友説的故事。
雙減後,政策要求學科類培訓不得佔用休息日,機構們紛紛把上課時間從週六日挪到了週中。一時間,全民“夜校”的時代開始了。學而思、新東方等各大機構周邊路段的擁堵景象也換了時間。

在學校上一天課,放學後上培訓班,回家後還要寫作業,最苦的還是孩子。因為第二天週末能緩衝,週五晚上也就成為最搶手的“黃金時段”。一名家長説,培訓機構App換班功能一上線,家長們搶紅了眼,她最終還是沒搶到,只能報名週三班。
家長們不僅有超高的“時間管理能力”,還要想辦法攛掇起小班課和名師一對一。
雙減之後,補課班隱藏到地下,“如果沒有信得過的熟人搭線,一律沒戲”。
宋美玉和老公都是內向的人,認識的人不多,突然就沒了門路,託關係打聽了好幾回,仍然一無所獲。211大學畢業的夫妻倆只能自己出馬,中午15分鐘間隙給孩子補英語聽力,晚上寫完作業,再讓老公補數學。
家長們有着共同的體會,到了此時,錢已經是次要的,只要能插班拼課,多少錢都不吝嗇。深圳家長鄒悦有個上初二的兒子,成績一直很好。暑假前,她想聯繫補課老師,沒想到不管收費是980元還是380元,老師們一律把假期課排得滿滿當當,原先一起補課的6個孩子,家長們兩兩一組,早就組團完畢,21天學費就要上萬元,不接受加人。
關鍵時刻,還是同班的一個學生家長接納她入夥。他們聯繫到學校裏一個剛剛退休的老教師,做的就是培優,只收尖子生。鄒悦感嘆:“能分享詳細的課外班或老師信息,那就算是過命的交情了。”
老師在自己老伴工作的大學裏找了間空教室,囑咐他們,別結伴來,不能穿校服,有人問起就説是家長在這裏上班。在學校裏,不能討論補課提到的題,也不能把講義帶去。後來,補課地點換到老師家裏,5個人坐在餐桌上,拉個大白板講課。
上小課後,花銷自然更多。鄒悦算了一下,5個人的數學課就算大課了,一節課250元,一對一的物理課700元,上個三四門,一個月就要上萬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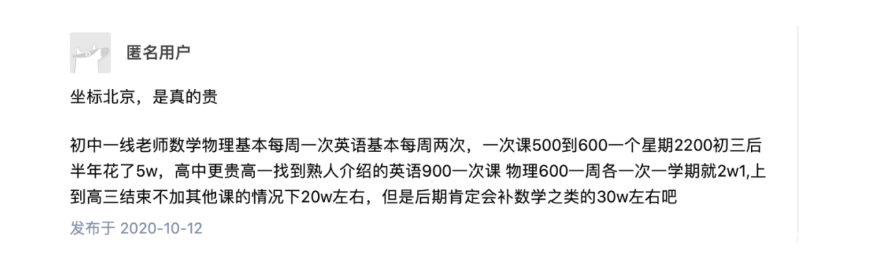
一位家長也分享過自己的賬本,只能拼小課後,一週一個孩子的補習班要4000元,一個月就是小兩萬元。
都説女人和小孩的羊毛好薅,但最好薅的羊毛,一定是家長,尤其是雙減後的媽媽,“只要你説有用,能提供好思路和方法,媽媽都願意去試一試”。
雙減後,學科班卷在隱秘的角落,興趣班正大光明地席捲而來。孩子上小學後,廣州家長蔣怡的課外班花銷每年20萬元,大頭全在興趣班。即使雙減後,減至16萬元,也多是減在語數外上。
她和老公都是“小鎮做題家”,上學時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學習上,沒培養出什麼拿得出手的興趣愛好,“既找不到好老師,學費家裏也負擔不起”。現在,他們做了家長,素質教育也流行起來,他們想為孩子找一門能夠終身獲益的特長。
從女兒一歲多開始,能報的班,他們都報了。游泳體操芭蕾舞,擊劍輪滑空手道,鋼琴滑板創意畫,他們打算“遍地撒網,重點捕撈”。

更多的家長則把興趣特長當成“升學新路”,甚至有了一條鄙視鏈,越冷門、越燒錢,越站在金字塔尖。
大家都説,運動類中,足球、籃球、跆拳道已經不時興了,受追捧的變成了棒球、馬術、擊劍和高爾夫。棋類中,會下圍棋的代表聰明,下國際象棋的更像是高人一等。家長圈子裏早就流行過一句話,愛馬仕包、香奈兒包,都貴不過孩子的書包。杭州家長楊慧深有同感,8歲兒子的書包裏放的是幾千元的馬術行頭,每週末去馬場上課,45分鐘就要400元,後續的馬術考級、參加比賽更是一兩萬的花銷。
在北京,一節滑雪課,1小時300元,再加上滑雪板、滑雪服、頭盔等裝備,租一天也要200元,一個寒假至少花費1萬元。
體育加入中考之後,體育培訓班更是成了薅羊毛的香餑餑。金欣給兒子報了一個名叫“少兒體適能”的補習班,前期把各個器械摸個遍,培養孩子的體育興趣,後期直接對標小學期末考和中考項目,比如跳繩、籃球、足球和男生1000米、女生800米。
現在,金欣把這門課排得更多了,“平均每週要上兩次”。
這樣的故事還有很多,一位家長曾因為小學期末考試加入跳繩項目,給孩子報了一個2000多元的跳繩班,結果班還沒上,孩子就學會了,只能找到補習班,無奈表示能不能把錢退了。還有的補習班教練,用電動車拴着孩子練跑步,只為達到800米跑在3分30秒之內的標準。
雙減以來,體育、藝術類培訓機構新增3.3萬餘家,較前一年同期增長99%。每一個新培訓班,都直指家長們的錢包。

如今,很多家長的覺悟都上升到這個高度:要教好孩子,先要教好自己。
補習班不能旁聽,媽媽們就聚集在空閒的教室、走廊過道里,以及樓下的休息區裏。孩子上大課,媽媽們上自習。她們在做練習冊、聽網課、記筆記。金欣也是其中一員,她買了考教資的網課和習題,不考證,只為了學習“如何更好地給孩子講題”。
金欣的兒子生日月份小,比班級裏大一點的孩子小了8個月,刷題時,她常常給兒子刷8個月之前學習的知識點,買了市面上十多本不同的練習冊,把不會的相同題型彙總一起做,哪怕是過年回老家也不放過。
80、90後的家長們,是比拼成績的一代,現在做了家長,他們仍然在比——看誰能把孩子教得更好。金欣常常覺得自己會把責任攬得很大,“我更怕的是,是不是自己沒做到最好,把孩子耽誤了”。
金欣的擔憂主要來自於中考分流。在廈門,“只有45%的孩子能有高中上,剩下的就要被分流到職高”的傳説,如同緊箍咒一樣紮在頭上,令他們頭皮發麻。
面對這一考驗,大多數家長都難以輕鬆。鄒悦同樣也是如此,身處深圳的她,知道想上個好高中有多難。“想要考上深圳四大,不走體藝和指標生,最起碼要擊敗98.9%的考生。”
為了教好自己,媽媽們不僅考教資、考幼師,還能再過英語關,重學化學和物理。有一天,金欣的小兒子從幼兒園放學回家,告訴她,園長説有一門課,教的是如何輔導孩子,問她要不要去聽聽。金欣一聽了然,這門“家長課”瞄準的是現在很火的“家庭教育師”,一般培訓班的費用是四五千元。
她聽過試聽課,跟一些講座和心理學的書上講得差不多,只不過“把書上寫的做成視頻了,配上動畫和案例”。
為家長定製的課程還有很多。比如,高途開設家庭教育板塊,關注親子關係和專注力。一個智慧父母研習班,每次課時長為2小時,61課節售價為3880元。新東方也推出會員制度,充值399元一年會員後,可以聽專家講座、直播和付費課程,其中有主題是“大咖助力志願填報&孩子厭學難題”。
長春家長阿芳也相信“親媽先行”的道理。大兒子剛上初一,她剛打贏小升初的勝仗,卻不敢有絲毫懈怠,立馬備戰3年後的中考。她買了245本初中教輔書,準備在兒子之前,把所有書都翻上一遍。書的側面被她貼滿了索引便利貼,標記好知識點,兒子想翻的時候,一下子就能找到。她稱自己“就是個親媽版‘搜索引擎’”。
上小學二年級的小兒子,她也抓得緊,光是資料就從二年級囤到了初中。囤個“資料庫”並不簡單,她養成了一閒下來就逛書店教輔區的習慣,花在習題冊上的錢“少説也有兩三千元了”。

她還跟其他媽媽學習,入手打印機,自制單詞小吊卡、生字表、拼音聽寫表和學習計劃表。每天放學回家路上,她把晚上要用的資料用手機上傳好,到家直接就能用。買A4紙雖然花不了多少錢,但用得多了也是一筆花費。阿芳時不時把公司用過的單面紙帶回家,利用另一面打印。
阿芳很多次告訴兒子,多跟班級裏學習好的孩子一起玩,跟人家學學,但兒子根本不聽。為了獲得更多新消息,她只能自己出馬,跟成績好的學生家長搞好關係,組小班課的時候就能“帶她一起”。
光靠學費不好薅錢,許多補課機構挖空心思想出了新招數。
有一天,金欣看到兒子吉他班的家長羣有新消息,打開一看,是要家長們眾籌投資,一起開個吉他店,需要200多萬元,攤下來一股3萬元。
金欣一下就想明白了,前段時間,聲樂和美術班有了全市藝術類培訓的指導價格,一節課從200元變成了60元,培訓班不賺錢了,才想出這樣一個招。雖然眾籌的錢跟這些年的補課費相比不算多,但金欣還是不敢貿然投資。事實上,着急讓孩子上課的家長佔大多數,願意投資的佔了七八成,錢很快就湊齊了。
這並不稀奇,很多興趣班都變身成為研學基地,不僅靠家長們眾籌投資,還要他們找地點、託關係、搭人脈,組織孩子們去參觀遊覽。金欣明白,這是“借雞生蛋”,“家長想要孩子有班可上,就會出錢出力,想盡辦法(把研學基地)維持下去”。
這看上去不理性,實際上卻包裹着家長們的心思。他們深諳升學的門道:有時能考高分還不夠,還要有研學任務、藝術特長、交流項目和義工等種種額外標準。為了給孩子鋪更多的路,他們既要能上手求門路,又要花錢買服務。
貼近生活和大自然,也是花錢購買的服務之一。蔣怡給女兒報了一門“博物户外課”,也是為了趕研學的熱潮。她花錢陪女兒徒步、划龍舟、舞獅,還學過製作弓箭和風箏,觀察昆蟲和植物,以及使用創可貼和碘酒。
儘管蔣怡明白這些都是“花拳繡腿”,也學不到什麼,甚至“更多是做給家長看的”,但她還是願意投入這些,讓孩子有機會出去看看,而不是坐在家中。
一些不想刻意雞娃的家長,為了讓孩子學得更輕鬆、愉悦,也要額外花錢買單。
俗話説的好,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雙減政策沒有讓這些孩子真正地減到負,反倒是讓家長更焦慮了,畢竟升學率那個明晃晃的數字是真真切切擺在家長眼前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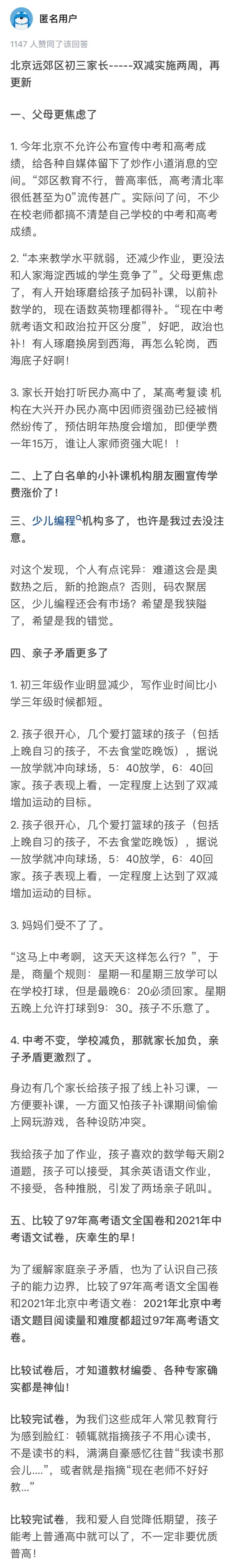
政策倡導舉報教育機構和補課班,但這似乎並不能解決問題的根本。因為通常這些舉報也是家長們的比拼環節。而一批的教育機構和補課班關門的同時,將會又有新的一批在崛起,是家長們大量的需求在造就這個補習班市場,甚至在擴大。
如果只是看到市面上的補課班數量減少以及學校的課業負擔減輕,這又何嘗不是一種自欺欺人?
如何打消家長們對孩子補習的需求,真正減緩升學的壓力,應該才是孩子們能真正減負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