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琳 | 考上劍橋後,她的生活卻開始充滿困惑_風聞
我从新疆来-我从新疆来官方账号-从人物到文化、不断探索异域风光,诉说不一样的故事。2022-07-18 11:30
拋下 · 極簡
最近幾年,邵琳一直在嘗試着拋棄一些東西。
她曾經在自己的公眾號上對她過去的十年做了一個總結:從劍橋大學碩士畢業,涉獵金融、服裝、古董、珠寶、騎馬,掌握英語、法語、西班牙語……十年時間,她幾乎活出了令絕大部分人羨慕的成功女性模樣。

如果將過去的這十年分成兩部分,在前半部分,她是一位精英女性,令大部分人仰而卻步,而在後半部分,她擁有的卻是另外一個完全相反的劇本。
她真的如自己説的那般,拋下一切,來到新疆,騎馬看世界。
離開繁華的都市後,邵琳的生活節奏可快可慢,她習慣於高效地完成工作,進而空出更多專屬於自己的時間,沉浸在一天的閲讀或寫作中,亦或是去公園長椅上靜靜地躺着,什麼都不幹,感受陽光的沐浴。
一年裏,邵琳大概有七個月會待在新疆騎馬。山裏的夜晚沒有燈紅酒綠的繁華和車水馬龍的喧囂,常常會有一大堆朋友在騎馬結束後聚一起,喝酒吃肉唱歌,這些都讓她感到快意。

如果不是有這種所有人都湊在一起放鬆的機會,邵琳很少去社交,在她看來,和一羣不相干的人吃飯,那是浪費時間。
邵琳幾乎和所有人都是保持一種極低的聯繫頻率,和朋友分開後,她很少對她們説自己的新鮮事,也從來不會去噓寒問暖,只不過她會一直惦記着對方,即便兩人五年沒見了,再見面時的感覺還是和沒分開那時一樣。
在她的身上,你可以看到對於極致簡單的追求。
她是個特別珍視時間的人,只願意將時間花在她認為有意義、能夠讓她開心的事情上。
在邵琳家裏,你見不着電視,她不喜歡看電視,因為邵琳覺得看電視就是浪費她的人生,電視無法帶給她任何愉悦感。
“因為看電視是一個被動接收信息的一個過程,人是有惰性的,能躺着就不坐着,能坐着就不站着。
我們在跟他人交流或者看書卻是一個抽象的過程,需要大腦的工作來建立連接,就像是長跑那樣,需要不斷地鍛鍊,很長時間不跑,身體自然也就不行了。”

最近邵琳又給自己買了一個類似於電子書般的新手機,“它幾乎可以滿足我的日常需求,還保護眼睛,但它又巨難用,反應和電子書一般慢,還會出現重影,用起來很不爽。”
她使用手機的頻率很低,把從前遇到大事小事就發朋友圈的習慣戒了,刷視頻的習慣也戒了,對於所有的電子產品都可以做到近乎隔絕的狀態。
一天下來,她發現自己並沒有因為這樣而錯失什麼重大的事情。
這是騎馬看世界給她帶來的改變。
待在營地的日子基本是沒信號的。第一次到新疆無人區騎馬時,恰逢邵琳在國內做珠寶生意的那段時間,習慣了將手機24小時開機保持聯繫,一旦失去信號,對她而言“簡直是毀滅性打擊”。
在野外的前兩天,這種狀態給她帶來了極大的焦慮感。但到了第三天,她想通了,反正也沒信號了。
一個人坐在馬背上,沒有人打擾,反而感覺到從未有過的心靜。
一開始去野外騎馬,邵琳帶的東西還挺多的,若是計劃要騎行一個星期,她要帶一個28寸的箱子,再後來攜帶的東西越來越少,現在大概一個雙肩包就夠了,裝有為了預防極端天氣而備用的一條換洗褲子、一兩件穿在外套裏面的上衣、夠換洗的內衣。
她發現,很多一開始覺得必須攜帶的東西,後來其實都用不着,反而增加了負擔。

這些年,她越來越習慣於給自己的東西精簡化。
剛辭職從英國回來那會兒,因為頻繁搬家,她把儲藏室的東西全部清理出來,這才意識到自己的東西無比的多,還有好多是從來沒有用過的。
後來每隔一兩個月,她就會整理一次家裏的櫃子,把所有不要的雜物一箱一箱的捐出去,一直扔扔扔,家裏的空間開始變得無比大。
搬到大理後,她的房子裏,沒有沙發,沒有電視,沒有衣櫥,沒有牀,更不用説雜物,就連食物慾都是極低的,從來不煎炒炸,吃最天然的味道。
有時候,邵琳的媽媽到這個家裏小住一些時日,總崩潰地嫌棄:“這日子怎麼過!”
但束縛的東西好像一直也沒有拋棄完。
不久前,邵琳在公眾號上寫下自己和丈夫張大聖之間吃醋的日常。
這件私密的小事若是放在以前,她是絕對不會將它寫成文章併發布給讀者看的。
她覺得自己總是活在別人的眼光裏,“我會擔心,別人會怎麼想我呀,會不會笑話我呀,跟我的人設這麼不符,七大姑八大姨看見了,會不會嚼舌根,會不會數落我呀?”
最近,她想通了,“關她們什麼事?”努力讓自己的情緒變得簡單化。

她從小就是典型的討好型人格,能自己解決的事情絕對不麻煩別人,讓她乾的事情絕不拒絕,她覺得自己的這種性格直白點説就是好面子。
小時候,聽多了長輩對小孩教育期待和要求,她就想到去好學校上學,因為成績是評價一個小孩的標杆。
如今到了大眾面前,與面子相對應的則是維護人設。
她看過讀者在文章末尾給她的留言:“你活成了我想要的樣子!”看多了別人給她的讚美,她忽然間覺得自己好像不接地氣了,“像是一個飄在天上的人,活成了一個仙氣飄飄的修道之人的狀態,但那不是真實的自己,只是自己選擇給他們看的樣子。”
而在這個故事的後面,她選擇突破自己的舒適圈,強制性給自己解綁,在公眾號上寫下自己的“小女孩心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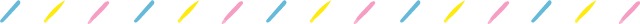
“我再不自由發揮,再不林黛玉附體,芝麻大點事我都會第一時間直説:‘剛才誰來電話你為什麼要出去接?你朋友圈下面留言的這個人是誰,為什麼經常看到他留言?’
每次他都呵呵笑着有圖有真相人證物證俱全地給我看到一點疑點都沒有,找茬都找不了。他不知道的是,每次我半嗔半笑半真半假地盤問完,都默默心裏給他加一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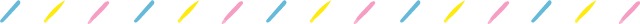
拋下不需要的人設後,邵琳似乎變得接地氣了些,“過回正常人的生活,喘氣都舒暢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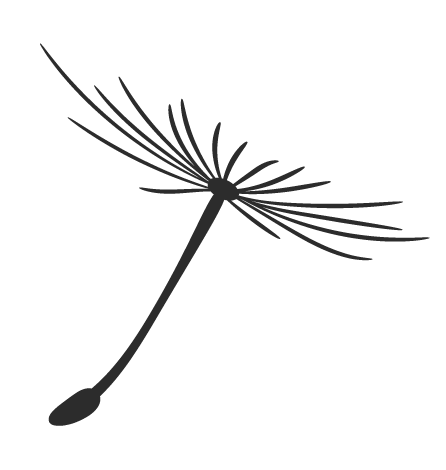
雲端的困擾
每次和我説起過去的成績,她都帶着一絲淡淡的惋惜。
讀博後,她常常會陷入迷茫。
她想在讀博期間繼續本科時做過的課題,跟着當時的導師研究癌症、治病救人。
真正進入實驗室,卻發現現實和自己的理想有很大的偏差。
科研是一份非常艱苦的工作,實驗操作對結果要求非常精準,不允許出現任何的差錯,所以在實驗室的時候,不可以和別人説話,以免打擾到其他人。
每天進入實驗室後,她第一件事情就是戴上耳機,開始實驗。
她在實驗室待了三個月,幾乎沒有和他人進行交流,甚至還不知道實驗室其他人的名字。
她覺得自己是需要和人溝通的,做一個完全與人類隔絕的工作,違背自己的天性。

她和導師聊過自己的想法,想成為科學家,奔着自己想做的課題去研究。
但現實是,想要研究一個課題,需要先申請並獲批課題,獲取研究資金方可以開始,而在這之後,實驗室老闆的預期、想法、分工等等又會進一步決定她最後的工作任務。
這就是導師告訴她當時研究中心的現實狀況,最後的研究內容完全可能和科研者的初衷相離。
那個時候,她才意識到,自己恐怕並不適合這項工作。
讀博三個月後,她向學校提交了退學申請。
幾年後,邵琳當年的研究項目在團隊的努力下終於取得了一個重要的進展,研究成果被髮表在頂級的刊物上。
看到這個消息,邵琳幾乎能想象到導師在實驗室恨不得跳起來,一邊還喊着“太好了!”的模樣,但那時候她的內心卻毫無波動。
“我沒有產生一個科學家見到成果應該有的心情,就感覺這個實驗做出來了,可以交工了,然後接着開始下一個就好,並沒有應該有的喜悦,可能是因為我本就不太適合(這個工作)。”
她進一步確定了自己退學的選擇沒有錯。

邵琳形容自己是一個目的性特別強的人,甚至於過去的整個人生都是帶有目的性的。
她明白父母對於自己的教育期望,於是總習慣於用聽話懂事和好成績換得別人的認同與接納,而劍橋則是這場自我競賽裏最大的執念。
在她只有十二三歲時,她就和別人説起要上劍橋的想法,所有人聽了都只是一笑而過,覺得是痴人説夢,“我就覺得這個學校很好,既然在那別人可以上,我為什麼不能上?”
她不覺得這是一種好強,只是從小就懂得給自己樹立了一個目標,那個時候的她特別清楚自己想要幹什麼。
她是一個非常典型的目標型驅動選手,一旦確定自己目標就會以最快的速度去實現,甚至於有很多天馬行空的想法。
十幾歲時候莫名其妙想要去北極科考,18歲時英國皇家科考隊招募隊員,她就去考了;17歲想學潛水,18歲她便拿下了潛水證書。

邵琳想出的主意很大膽,父母拿她沒辦法,最後給女兒要上劍橋的想法設置了測試:
“既然你説可以照顧好自己,那就自己去辦簽證,申請學校,如果你可以辦成這些事情,就證明你在國外自己一個人生活應該也是沒問題的,我們便同意讓你走。”
結果她按着流程一步步摸索,自己申請學校、考試、準備材料,真的做到了。
邵琳在國內讀完高一後,父母履行了承諾,她開始一個人的英國生活。
邵琳在英國時所上的這所高中,每年只有一兩個學生能考上牛津、劍橋大學,除了學習能力外,學生的邏輯思維能力和社會實踐經歷也是這類頂尖高校招生時考察的重點。
她仔細研究過申請劍橋大學的要求,並從中學時開始考鋼琴、潛水、科考、馬術等各類證書。

邵琳的生物學得很好,初中畢業後,她在全自學的情況下,用了不到兩個月的時間把高中生物知識掌握,又用了大概四個月的時間將大學生物課程學完,然後跑去參加全國競賽,為她申請劍橋增添了一筆籌碼。
後來選擇專業的時候,她覺得自己既然擅長生物,那就去學醫吧,至少她能保證是做自己擅長的事。
定下這個目標後,她又跑去社區當義工,到醫院做實習生。
在大部分的時間裏,她幾乎都在做和學習無關的事,她對自己有“一種不切實際的自信”,幾乎只是在考前看一下,便可以將自己的成績保持在前列的水平。
最後,她真的就成為那年學校唯一一個成功被劍橋大學錄取的學生,而另一個學習成績明顯比她好,但沒有實踐經歷的同學卻連面試的機會都沒有。
因為暈血,她沒有選擇臨牀醫學專業,改學遺傳學,這是唯一與她的預想不同之處。
進入劍橋,這樣的不同開始增多。
她曾經對這所學校充滿了幻想,認為劍橋應該是一所閃閃發光的大學,這裏的學生更是神仙般的天才。
到了劍橋,邵琳平均一天兩節課,每節課的老師會佈置需要30小時才可以看完的資料,並要求學生在此基礎上提出自己的新想法。她通常會選擇性地完成自己可以解決的一小部分任務,剩下的她覺得自己確實無能為力了。
她不是那種一味地扎進學習世界的學生,將自己的大學過得非常豐富多彩。
劍橋有許多世界級的社團,她選擇了華人樂器社團、國標舞蹈社、馬術社團,這些都是她從小便接觸過的業餘活動,相比於前兩個,馬術是她為了申請劍橋而“強迫”自己培養出的“愛好”,她對馬術談不上喜歡,不過因為曾經學過,所以還是將它挑選出來,作為大學生活的主要內容。

她承認,自己做不到像極少部分人那樣,天天在外面玩,考試仍然可以比第二名高出一大截。
第一個前半學期,她抱着僥倖心理,和大家一起玩,考前隨便看看就去考了,結果那次模考才40分。
自那時候起,她開始意識到自己其實挺普通的,在劍橋上學的也只不過是一羣成績比較好的普通學生而已,而真正的頂尖水平其實只存在於一小部分人身上,現實和理想從那時候開始產生更多的不同。
直至讀博後,她又進一步深刻地研究自己。
“突然一種非常明確的目標就沒有了,在那之前,我只需要知道自己要上什麼學校,一個很簡單的目標就可以了,上個好學校永遠不會錯。但到了那個好學校後,再往後走的那些人生路就很複雜了,怎麼判定好的人生?”
邵琳覺得上大學之後,自己就屬於走一步看一步的狀態了。
她告訴我“判斷這個職業是否適合自己”的技巧,只需要看看自己上司的上司,他的人生狀態是不是自己十年之後想要擁有的樣子。
退學離開實驗室後,邵琳沒有特別想做的事情,她在大學期間一直在倫敦投資銀行實習,因為投行的工資特別高,所以她便轉去了投行上班。
在投行總部,周圍都是這個集團最頂層的人,只有她工作足夠出色,才有可能抵達他們的位置。

可是她認真觀察分析過這羣人,也是天天開會,討論如何從客户身上賺錢,實現集團利益最大化,然後做出戰略部署。
包括她在內的大部分同事,都並不喜歡自己做的工作,她甚至覺得不如之前自己夢想的醫生的工作內容有趣,就算拼勁全力做得更優秀,但最後的結果也仍和自己的三觀相悖。
2014年底,她辭職了,離開了金融行業,也離開了英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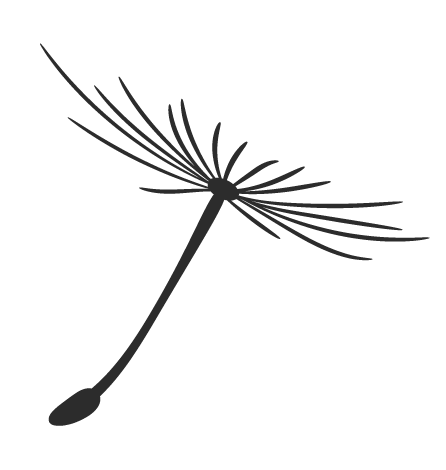
理性的瘋狂
邵琳的祖籍在山東,她循着地圖,在上面尋找一個不如倫敦嘈雜卻又不失現代氣息的城市,最後頭腦一熱就去了青島。
她像一個流浪者,抓住這個難得的機會,去尋找自己到底想幹什麼。

最初,邵琳設想的是到世界各國旅居,在每一個國家住上幾年,不再像之前走馬觀花式的打卡,而是靜下心來融入到當地的生活,她希望以此來影響和改變自己。
可回國後,她一直沒離開中國,而是選擇了兩三年換一個城市。
因為對珠寶有了解,所以她選擇了從事珠寶行業,整日飛往全球各地參加珠寶展覽。
2016年,一次偶然的機會,她在青島騎馬,聽到同行的人説在新疆騎馬的感覺很好,她便一個人去體驗了一番。
從前帶着“功利”的心思學習騎馬,她並未感受到騎馬的快樂,只不過自己騎得還行,結果待在新疆的一個星期讓自己上癮了。
邵琳在新疆大山深處騎馬時所見到的少數民族,大多都保持着非常質樸、原汁原味的民族風味。
這和她一直經歷的都市生活有很大的差別,也不同於商業氣息濃厚的景區帶來的體驗,她覺得在牧區的生活離自己的生活很遠卻又無比真實,令她震撼。
她還喜歡那的風景,雪山花海,坐在馬背上,放空自己,貼近自然,讓她感到前所未有的放鬆。

回到青島後,她發現自己已經完全不適應以前的生活了,滿心都在惦記着去野外騎馬,一到天氣稍微變冷,就開始計劃着該去滑雪了。
後來她搬到大理,從那時候起,她就基本上一半時間在大理,一半時間待在新疆,並漸漸離開珠寶行業,開啓了騎馬旅行的事業。
每年的四月到十月,是她出門騎馬的日子,她幾乎走過新疆的每一條可以騎馬的路線。
開始的時候,她一個人獨自去招募牧民合作,根據經驗設計出路線,又自己當領隊接待遊客。
團隊的人越來越多後,她還是會抓住所有可能的機會跟着隊伍騎馬出發,一年下來,在牧區待上三到四個月,她很享受在野外工作的時光。
她給自己取的筆名是“野丫頭”,認識的人大多也叫這個名字。
她覺得自己當真很“野”,很少會糾結計較一些小事。
小時候,跟她玩得好的朋友大部分都是男生,她像他們一樣,特別喜歡爬沙堆,很少顧慮衣服會不會髒,會不會受傷,會不會被曬到。
16歲初中畢業後,她不想再父母陪着出門,沒考慮太多就一個人去雲南旅行,現在回想起來,還是覺得很刺激。

她一直是瘋狂的,對於愛情也是如此。
她很早就在英國完成了自己的人生大事,擁有兩個可愛的寶寶,直到回國後,她第二次遇到屬於自己的愛情。
她用“非主流”來形容自己和張大聖,兩個在出身、學歷、職業背景等方面都天差地別的人。
在他們相遇之前,張大聖的童年、青年和成年時期,幾乎所有在乎的人和在乎的記憶都只在昆明,他做夢都沒想到“下半生居然要跟個(從外面來的)講普通話的人在一起”。
可兩人不顧眾人的勸阻走到了一起。
邵琳覺得,她和張大聖兩個人在一起就像小孩一樣,“特別幼稚,特別高調,特別不現實、不接地氣”。
經常説走就走,開車去看山、看水,然後就在車上睡一晚上。他們探討的大部分都是哲學問題,談人生、談理想、談各類亂七八糟的,一聊起來可以持續好幾個小時,等結束後她也記不得説了些什麼。
但兩人從來沒有討論過家庭的財務規劃,她不知道張大聖有些什麼,張大聖也一樣。

她也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好媽媽。
她認為,自己和孩子間是相對獨立的關係,給孩子提供的愛完全出於自願的原則,她很少將心思完全放在孩子身上,甚至反對父母與孩子間相互過度付出。
有時候孩子耍賴皮對邵琳説:“那你為什麼不給我買這個?”她説:“我憑什麼給你買?”
孩子們的主意總是特別多。
雲南的冬天挺冷,小男孩喜歡穿短袖出門,她只告訴孩子:“你出去有可能冷,你要不要帶衣服,你不帶你會凍着。”
可即便兒子真不帶着她也不會勉強,“孩子到了七八歲就已經可以選擇自己吃什麼、穿什麼,冷不冷自己知道,他又不會凍死,而且他的身體真的特別好,從來不生病。”
這種做法被她的爸媽或者街邊的阿姨們見了,嫌棄説:“她是個後媽吧,這麼對自己的孩子?”

但邵琳有自己的限度,她對於一切的思考都很理性。
她是在傳統教育下成長起來的“精品”,但如今她自己卻並不認同傳統的教育理念,每次都點到為止,尊重孩子的想法,讓他們想明白屬於自己的人生。
這也是她自己所惋惜的,直到現在,她還是沒有想明白自己未來要做什麼,好像沒有特別想做的事。
劍橋帶給她思考問題的底層邏輯,“學校讓我學會了如何腳踏實地地去思考,我希望自己擁有精彩而不留遺憾的人生,所以從來沒有過舉棋不定,後悔自己曾經的選擇。
”還帶給她人生的底氣,“有了劍橋這張免死金牌,無論我做什麼事情,也不會有人覺得我是不思進取,因為讀很多的書、見更大的世面、擁有很好的工作這些我都曾經擁有過。”
邵琳也不是一味地追求“詩和遠方”,從投行辭職前,她有過兩年的深思熟慮,“首先我得有經濟保障,我非常明確地知道我不可能保持當時的消費水平,只要我把當時為了面子而消費的奢侈品去了,我就沒有經濟壓力了,有足夠的底氣去追求我想要的自由,後面做的一切就全都隨心而來了。”

所以她才會不斷地拋棄自己過去的人設,她所指的“人設”包含她身上的標籤,以及她在做什麼,“如果給自己限定了,我一定要做這個的話,那我的人生就受限了。所以説我就儘量不會承諾我這一輩子做這一件事情,這是一個人不應該背的枷鎖,我很清楚自己不想做的事情就可以了。”
在2015、2016年之前,每年邵琳都會給自己設立至少三個目標,要學什麼東西,要達成什麼心願,她基本上都會完成。
但那之後,她想清楚了這個問題,不再給自己設立目標,“我覺得我現在的生活沒有什麼重點,也沒有要求自己一輩子就做‘騎馬看世界’這份工作了,每年都只是希望這一年好好過去,每一天不能白過了,只要是不違心的快樂狀態那就算過好了。”

如今,和邵琳同期畢業的同學、之前一起共事的同事,都已經做到很高的位置、擁有高於普通人幾倍的薪水,成為世俗評論裏的人生贏家。
但邵琳覺得自己賺大了,她説:“因為活得很勇敢,夠快樂。”
-END-
主 編:阿布德吾力
副 主 編:劉美儀、艾孜則
版 塊:疆來人物、疆來電台
版 主:許露琪、米合熱阿依
作 者:黃毓婕
校 對:努爾扎代木
主 播:祖麗哈婭提
排 版:希日爾帕
圖片來源:邵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