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家| 主流紀錄片能做作者表達?從首枚氫彈到貴陽臭酸,她這麼總結_風聞
第一导演-第一导演官方账号-导演社群2022-07-22 08:16
採訪、撰文/法蘭西膠片
**《尋味貴陽》**第三集的最後10分鐘,有點令我驚訝。
因為劇中人物在系列片大結局的時刻,突然不做貴陽菜了,他們反而做起了江蘇菜、廣東菜甚至北方菜。
這當然不是腳本事故,但也絕非一個“叛逆”的創意那麼簡單。
當你意識到,這是在拍新舊交替的貴陽,在拍一位老人,她在自己的百歲壽宴上迎來八個五湖四海的兒女,並孤獨地與她們告別,你就知道,雖然菜品在線,但這已遠遠超出美食紀錄欄目的表達框架。
我喜歡在庸常中突然給你來點破格的東西,這裏面是藏着一個作者的。
作者名叫劉清予,從事紀錄片導演工作十餘年,曾供職於中央電視台**《探索·發現》**欄目,後又和騰訊、搜狐等網絡平台合作,期間參與了十餘部紀錄片創作。

劉清予
她曾目睹中國探險神器,從青島到南海,再穿過印度尼西亞島嶼,在深海“水之道”探索海底生物。
她也曾採訪幾十餘位僅存的科研專家,拼出50多年前,中國第一顆“人造太陽”的背後秘聞(《第一顆氫彈》)。
她甚至曾翻遍一個縣市的所有歷史文檔,就為了找到,這個地方真正為老百姓開天闢地的英雄,而當地人,卻對此一無所知。
後來又與陳曉卿共事,創作了2020年播出的**《尋味東莞》,以及剛剛播出的《尋味貴陽》**。
“説到底,紀錄片到最後都是關於人的故事。一旦到了人的層面,很多東西就可以解釋了。採訪一個人,是這個行業給了你一個合法權,讓你在一個短暫的時間內,去了解一個人的一生。”
回到《尋味貴陽》,這樣一個選題,對她的職業生涯來説,又多了一份意義。
因為她就在這裏土生土長,一個三線家庭的女兒的生長印記再次顯現,她這一次,不單單是回到故鄉,還要書寫以暖寫悲的歷史情感,為美食紀錄欄目注入“地久天長”的口吻。
“歷史的塵埃放在每個人身上是一座山。你再往後走30年、50年、100年,你再回來看現在,我們一樣是在大的歷史洪流當中,同樣無法跳出時代賦予的印記。”

《尋味貴陽》工作照,劉清予(右一)
技術總會疲憊,安定使人觸底。
就在兩年前,在劉清予中央民族大學文學系(新聞)畢業九年的時刻,她重新回到校園,考上了北京大學的藝術學院藝術碩士(電影),她想重新用電影的審美潤一潤紀錄片的心得。
“我這樣的導演,行活兒,是有困境的。如果你一直陷在行活兒裏,今後呢?”
她早就過了戾氣爆棚的歲數,工作久了你就發現,反叛之後,並不一定能建立更先進的話語權。最艱難的作者表達,需要在主流中調動大智慧,而很多人並不相信這一點。
當下,我們正經歷一個巨浪動盪時刻,很多人不好過,很多人不問過,但誰也經受不起“時代一粒灰”式的得過且過。
雖然劉清予自認還沒邁進職業電影導演的門檻,但**第一導演(ID:diyidy)**採訪劉清予,打心眼裏是把她劃入貴州新影人的序列,她可能沒有今年攜商業短片去戛納競賽的那位貴州新生代導演的標杆效應,但她十幾年的紀錄片經驗複述出來,也基本就是一個行業的全部操守了。
本篇採訪近8000字,乾貨居多,多認識一個新導演,她其實是個老手。

劉清予(中)
01
記憶
紀錄片最基本的本性
我從小在貴陽長大,家裏經歷三線建設,是廠礦子弟,所以我看王小帥的片子特有感覺,**《地久天長》**裏的人際環境和我家裏一樣。
但我發現,這裏並不是一個顯著的地方。
當年考察大學生羣體,有人問我,貴陽?在哪,在廣西嗎?甚至有同學以為我平時騎馬……
從上大學離開貴陽,到工作兩三年,大概七年時間裏,我每年回家,這發現家裏拆掉一個標誌性建築,改建成現代化的大樓。
這種感受對我來説很強烈,因為我是不記路的,只記得那些標誌性老建築,它們讓我在這個城市裏能找到定位。
我現在有時候真不知道自己在哪。

加上很多其它原因,包括從2008年貴州開始修高速,導致這裏的生態改變了,或消失了。
但這兩年也有很多貴州電影人出來,我還在想,是不是路通了的原因?
這很矛盾。
所以這次參與導演《尋味貴陽》,我是自告奮勇地想做第三集——《城記》,作者空間最大的一集,因為相比前兩集《山語》和《水韻》,《城記》更抽象,我想在故事的最後,加入一個緬懷三線的故事。

《尋味貴陽·城記》
一開始不知道這個故事要從何去找,從何下手,它畢竟是美食紀錄片。
我爸爸是河南人,我媽媽是湖北人,我從小吃的就是融合的菜式,調研過程大概四、五個月,找不到這種與菜式相匹配的極致的人物。
結果你猜怎麼着?最好玩的是,繞了一大圈,繞回自己家了!現在故事裏這位百歲老太太和她的八個高齡子女,就是我鄰居,住在我成長的小區裏,那最小的小兒子,就是我爸的同學!小兒子的女兒和我又是小學同學!我們原來就這麼近!
她們家起初也有些疑慮,我就讓我爸去做思想工作,天天約那個老同學出來散步,老同學再跟他的姊妹幾個做工作,就這麼勸成功了。
02
周旋
從片場的“套近乎”到後期的情感征服
在拍攝之前,我和他們家人彼此並沒有那麼熟,但我們相處得很愉快,我都喊她們“姨”“叔”,她們跟你距離越近,在鏡頭前就越放鬆。
這次我還認真地挑了一下攝影師,找了一位很温和,喜歡社交的攝影師,最終80%的鏡頭都是一台機器完成的。

《尋味貴陽》工作照,右一為劉清予
説起實操原理,一般這種紀實性強的內容,我們先躲在角落,拍一些鏡頭,不相關的人都藏進卧室,就我,攝影師,還有一個攝助,就三個人,讓她們不太關注到我們,然後慢慢地參與進去。
像片中那個炸餃子,有一部分餃子皮都是我們擀我們包的,時不時幫她們一起幹幹活。
你會發現鏡頭裏有我穿幫的鏡頭,因為我隨時要看監視器,我會觀察到這個情境可以了,就趕快躲開鏡頭,跟攝影師有一個配合,絕對不會大聲指揮,去打斷這家人的氣場。
她們也會覺得奇怪,明明是拍做菜的,卻拍了那麼多一家人的事,但好象這個疑問對他們來説也不重要。
重頭戲,八名子女做各自的地方菜,我是跟他們八個都溝通了一下,給了兩個要求,一是做你們的地方菜,另一個是,從中間挑你最擅長的做。他們基本上都會做飯,那我們就把相對不太會做的,以及和貴陽菜太相似的刪掉,畢竟這菜還是要上鏡的,它還要保留一定的視覺呈現力。

雖然她們的故事只有十分鐘,但我們的拍攝週期還是很緊,就那幾天,必須拍完。但是對她們來説,就那幾天在老家貴陽,她們是要犧牲很多陪伴家人的時間來配合我們的拍攝,她們對拍攝到底有多累這件事是沒有預期的,你再提醒她也沒有預期,拿捏也是個度,講得太嚇人人家就不拍了,不講吧,她真拍到一半也不拍了,更麻煩。
這場家宴的意義,對於生活在貴陽、經歷過三線的人,很容易感受,但沒有這層經驗,就需要一定的文化感知。

所以這一段最初在團隊內審的時候就有其他的導演產生過質疑,為什麼《尋味貴陽》在大結局的時刻,會出現一個東北菜,一個江蘇菜,可就是沒貴陽菜?什麼意思?
我也沒有去力排眾議,因為陳曉卿老師在這個質疑的點上一直沒有把它擴大化,我相信陳老師是喜歡這個故事的。
當然了,在最後告別的幾分鐘,陳老師也表達過他的看法,他覺得人生如飄零,飯還怎麼吃。
我很理解他的疑問,畢竟節目有自身的定位,但對我個人來説,《尋味貴陽》已不僅僅是一個作品。它就是我家鄉的一部分,承載着,也塑造着我的人生觀——**人生是充滿遺憾的,充滿這種不可控的東西。**這個認知是我的一部分,很難從作品中分割出去。
本來已經被拿掉,可能因為最後這個故事把大家都打動了,那八位兒女與貴陽百歲老人離別的段落,又給拿上去了。當然,最後剪掉了一些可能更傷感的鏡頭。
我的判斷就是,在這個結尾,這場戲,一定要落得住!後來陳老師還發了一個朋友圈,説這場戲在配旁白的時候,工作台有人哭出了聲。

所以我相信陳老師其實是喜歡我這個路子的。另外也是,作為三集片子的結尾,對觀眾、對劇組、甚至對故事裏的人物來説都是一種結束。所以最後這個位置,就用了告別。
其實幕後還有一件事,這位百歲老太太,正好在拍攝前不小心摔過一次,變得不是特別精神,時而清醒時而糊塗,**在拍攝這場告別戲的時候,老太太一下就清醒了!所以她才會問女兒,“你幾時回來?”我想,這告別可能也是人生的必修課吧。**而且,她用的是“幾時”,這是一個70年前的詞彙了,那句話非常真實。

這一集播放了之後,老太太在小區裏可出了名,大家都在那説她的故事,都在説這個片子,她們應該是很高興的。
當然我心裏還有一個遺憾,就是給老太太祝壽的時候,他們辦了一個很大的壽宴,兒女中有人是文工團的,比較能歌善舞,就給老太太彈手風琴,跳交際舞,唱歌什麼的,形成一個家族的儀式感。
那段拍得太好了,阿姨手風琴拿起來就是一段《友誼地久天長》,在那個超現實的時空裏,她們都不是老人,她們每個人都和當年一樣年輕。
這是一個以暖寫悲的氛圍,是我對時間的一個認知,它第一層是最直接的,就是歲月的流逝,回不去的青春,和回不去的故鄉與童年的記憶,而第二層是這種大的時代環境帶來的人的聚散離合,這個感覺,就交給了告別那一場戲。
只是家宴的素材確實太長,我放上去好幾回,理智告訴我,還是得拿下來。紀錄片就是這樣總是充滿遺憾,有些是因為你沒拍到,有些是因為你拍得很好,但不合適。
太可惜,單獨為此做一個新的紀錄片都沒問題。

導演劉清予和袁愛芳老人合影
我特別喜歡方方的一句話,歷史的塵埃放在每個人身上是一座山。
我們現在所説的,北漂或南下,看似是我們自己的選擇,就像我當年高考去北京,我根本沒有意識到這時你就要離開家鄉了。
現在想想,可能只是因為,我們現在還沒有完全跳脱這個時代。
你再往後走30年、50年、100年,你再回來看現在,我們一樣是在大的歷史洪流當中。
因為我們身處其中,所以對它的認知、態度總難避免盲人摸象的片面。
真的放在歷史的時間線上,我們都身處在無法全身而退的時代。

袁愛芳老人一家
03
職業
有限創作的魅力:妥協/接納不確定性/生命自有的力量
做紀錄片耗時很長,要考驗耐力,拍**《深潛》,就是蛟龍號,之後又拍了《第一顆氫彈》、《尋味東莞》**,一個個項目非常漫長,動輒一年兩年,最長一個片子拍了差不多五六年。

劉清予和《深潛》的總導演廖燁合影
但一邊拍你就得一邊想,這個片子,到底要往哪講?
有時候你就是在賭你追的人物對不對,當然,拍一段時間,你就知道哪幾個環節是最重要的,也容易出現信息量,你就可以去跟。問題在於,你能不能有判斷力,抓得住,還能引導表達。
我前幾年做軍工類題材,知識門檻很高。還有些領域至今仍是涉密項目。有一天,睡到半夜,我就驚醒了,立刻去看我的資料U盤還在不在。
**紀錄片有一個最大魅力,就是在有限的空間做創作。**這個有限可能是題材,可能是拍攝對象,可能是拍攝環境等等,這就帶來了它的失控感。
這很有趣,就是你永遠沒有辦法按照你的想法去做這個片子,你的創作的成形,是你和你的拍攝對象共同創作出來的,你想得太多,反而會限制你的應變能力。
像我當時做《第一顆氫彈》,它講的是中國1967年做的第一顆氫彈的故事。時間比較久了,那些最熟悉項目的人,基本上都走得差不多了,我們只能採訪中層或基層的從業者,他們各自只知道自己領域的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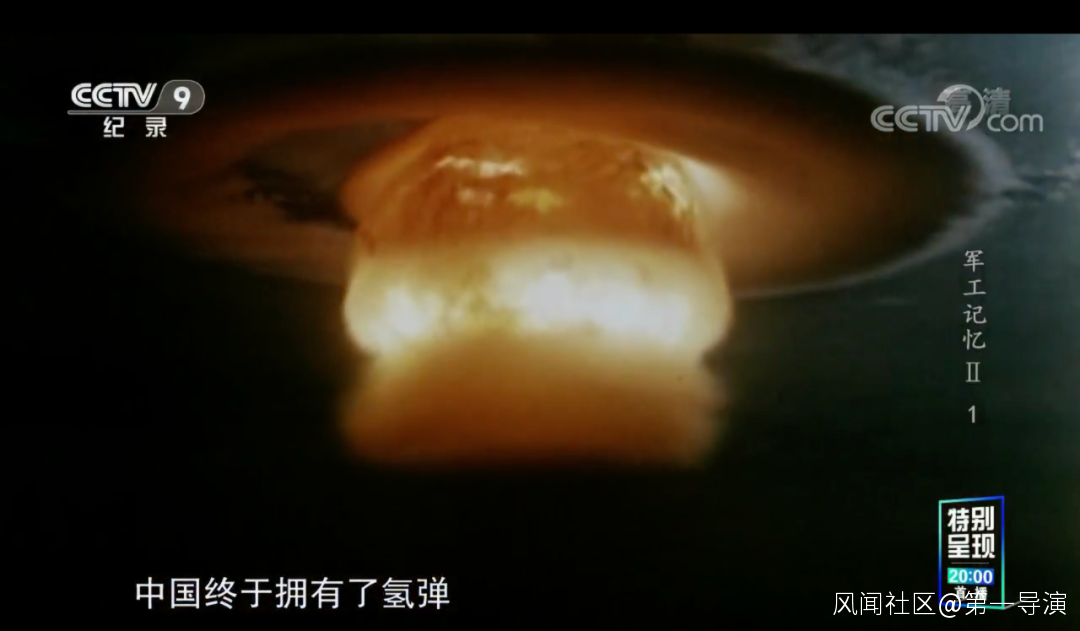

《第一顆氫彈》
所以《氫彈》製作過程中,我們總共採了四五十個人!要把這麼多人拼圖一樣拼在一起,而我就是那個拼圖的人。

劉清予和張興鈐院士合影
説到底,紀錄片到最後都是關於人的故事。一旦到了人的層面,很多東西就可以解釋了。採訪一個人,是這個行業給了你一個合法權,讓你在一個短暫的時間內,去了解一個人的一生。
當然總會遇到令你無奈的事,我經常遇到,還摔過甲方電話。
但是現在想,難免有點幼稚,人家也不容易,也有他的立場和決策。
我記得那是一個系列紀錄片,其中有一個關於地方名人的故事,要我在整個歷史長河中選一個人,作為這一期的主角。
那個地方就沒什麼名人,都不適合做當地形象的主角。在我持續的調研中,通過查閲他們當地所有的縣誌,一手的文件,包括以前的書信,我意外地找到了一個人,是一名博士,也是當地歷史上唯一一個博士縣長!
我估計他抗戰時西遷到這來當的縣長,在解放的時候已經沒有了政治工作的記錄。然而,直到一百年後的今天,當地的教育、經濟都受惠於他那七年的政策!都是在他的基礎上生長出來的。
這個人是個英雄,但他最後只留下來一張照片和一份簡歷。我就去調查和他有千絲萬縷聯繫的人的後代,還去採訪當時的縣誌專家,那個老專家60多歲,一開始他從來沒有從這個角度想過這個博士縣長的重要性,後來聊着聊着,竟然哭起來,説,“我們太對不起這個縣長了”。
原來當年浙大西遷,所有西部地區都困難,問了一大圈都不肯收學校,直到問到這位博士縣長,他收了。
他當時做的最牛的事,是手繪了一張縣地圖,上面標註這每一家農户的數字,這數字不是指每家住着幾口人,而是指這家農户能為浙大接收幾個人住宿。
浙大搬來之後,沒有那麼多學生、教師宿舍,他就把學生和教師分散在每個農户家,就告訴你,雖然我們縣城小,但這家住五個,那家住兩個,我都能給你裝下。
這個題材我報了,上級批了,我也做完了,但最後,還是沒了後續,因為大家擔心這個人一問誰也不認識,沒名氣。
有時候覺得無奈,並不是因為你做的努力白費了,其實是在於,追求真實其實是很多維的問題,有時候並沒有那麼容易。

04
入行
只需見證一次奇觀
高中時因為看**《霸王別姬》**,足足抑鬱了一個禮拜,在心裏揮之不去,電影原來能走到人性的邊界。
學的雖然是理科,但高考報專業第一就是新聞,第二是法律,第三才是數學。現在倒是有點後悔了,呵呵。
當時我的大學老師,他一邊教課一邊在電視台做**《走進非洲》**,這節目在那會兒挺火的,我就跟着他學做獨立紀錄片。
我一直特別喜歡社會類話題,和新聞相比,紀錄片有個特別好的點,就是它可以用更長的時間去觀察一件事,能更深入地看到社會下層的問題。因為這個原因,我開始對紀錄片感興趣。

劉清予(右)
還有一件事,一下子把我帶進去了,我本來就很想做人類學紀錄片,正好在2010年那會兒,就是我大三大四的時候,學校來了一個國家級的少數民族傳統體育項目,由體育學院和我們學院一起操作,有人寫書,有人拍紀錄片,我當時就是負責紀錄片的部分。
這個事完全落在我身上了,團隊裏有三五個人,光拍就拍了三個月,持續了一年的時間。
它是在貴州的東南地帶,有個苗族的寨子,叫施洞鎮楊家寨。他們有一個獨木龍舟節,這是這個體育項目中最重點的一個。
那個寨子是純正的苗寨,從貴陽開車,上高速,走國道,再走省道,最後走盤山公路,一圈一圈繞,大概要開七、八個小時。當時帶隊老師是北京人,自己也開車,結果開完一趟就不敢開了,另找了司機,有時候盤山路會來一個180度拐彎,萬一趕夜路,就很不安全。

貴州省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楊家寨
調研的時候,大家都住寨子裏的木頭房子,等於在農民家住了三個月,然後從做龍舟,到最後比賽,目睹了全過程,這是一場奇觀。
獨木龍舟節的起點,就從找做龍舟的那棵樹開始。大家跟着族裏最健壯最有經驗的男性,揹着行囊,背點肉,背點米,揹着鍋,就上山了,特別野生。
進了山,砍木頭,堆成三角形,塑料布一蒙,就是睡覺的小賬篷。再砍倒一些小樹,留着下山時有用。
找到適合龍舟那顆樹之後,不能立刻就砍掉,他們要祭樹神,拜山神。等龍舟找到,之前上山砍的小樹就當輪子,墊在大木頭底下,像《陸上行舟》一樣,就這麼慢慢運下來。滾到基本快到山地了,有路了,再用吊車運到大路上。


獨木龍舟節
回到寨子裏,大家都出來放炮,全寨子100號人都聚在廣場上,一起吃飯,有酒就會唱山歌。
原來他們從六、七十年代之後就沒有再做新的舟了,就為這根龍舟,前後花了七天時間,這個過程本身就是前所未見的生命力,人和自然界的最原始的關係。
因為拍攝,我跟鄉親們關係很好,特別是做祭祀的“鬼師”,老爺子當時都92歲了,腿還有點問題,拄着枴杖,大家攙扶着上了山。他的兒子、孫子都不願意再幹這個工作,周圍的寨子也沒有這種人了,但是他們一遇喪葬嫁娶,還是要找他做法事。
我當時就在這個紀錄片里加了一條人物線進去,講鬼師和他的孫子,他的孫子當時比我小几歲,做的是打苗族銀飾的生意,已經有點城鎮化了。老爺子的方言很重,基本上跟他聊天只能聽懂50%,一吃飯就老敬我酒,我的酒量就那時候練出來的。
這也就成了我的傷心之地。
離別的那天,不知為什麼,我不敢告訴那個老鬼師。
車就停在稻田邊的小路上,我們悄悄地走了。

劉清予和苗族古歌傳承人合影
另一頭的遠方,就是村子,從村子到小路是一條田埂路。當車馬上要啓動時,鄉親們知道了,全都跑來和我們道別。
我當時已經上了車,遠遠看見村子的那頭,來了一輛摩托車,是那個孫子,載着他“鬼師”外公,遠遠地從村那頭開過來。
老爺子提了一袋東西,是他們家自己種的李子,還給我裝了一些零食,他可能覺得,現在的年輕人喜歡吃零食。
我當時哭得稀里嘩啦,泣不成聲。
車一開動,老爺子也哭了,他們就在後面唱起山歌。人變得越來越小,歌聲慢慢散在山裏。
回到北京,那一週特別抑鬱,藏在家裏,不説話。
後來我發現,自己每次做完一個片子都會陷入一段時間的抑鬱。就好像是一段人生結束了。

劉清予
05
前行
重回課堂,調動智慧,珍惜表達
我做紀錄片導演已經十幾年了,在2020年的時候,我決定考研,讀了北大的電影研究生。
為什麼回爐?就是覺得創作遇到了瓶頸。
我這樣的導演,行活兒,是有困境的。如果你一直陷在行活兒裏,今後呢?
重新學電影就能帶動我一個思維空間,電影的敍事思維,分鏡技巧,哪怕是迴歸到經典文本,都可以給我流程化的紀錄片創作模式重開一扇窗,回到電影,是吸一會純氧。

劉清予(前排左一)北大學習照片
做紀錄片當然也可以反哺電影,你對現場的敏感度,對人物性的觀察力,也是精準調度的一部分,它甚至就是一種明確的電影風格,未來,我希望能把紀錄片的這些優勢和經驗能夠有機的放到電影導演的工作中。
無論是電影還是紀錄片,我都想借助這種視聽語言去做自我表達。
只是在今天這樣的商品環境裏,有很多事情是沒有辦法做改變的。

劉清予(右一)
首先你得生存下來。生存下來的前提是,你得對得起別人給你的酬勞,對得起觀眾,這兩個是要一同去做的。
在這個圈子創作,首先要珍惜自己的話語權,如果你被邊緣化了,談什麼作者表達。
另一方面,你也並不能保證自己當下的態度和判斷就一定是客觀的,只能説儘可能讓你的作品能夠經得住歷史的考驗。
同樣一個東西,同樣都是主旋律,如果你有更好的認知,有更好的技術,有更多的智慧,我覺得這個選題放在你身上,肯定會做得更有價值,並且它能夠最廣大地得到呈現。
就比方説,我們的國家此時此刻的階段,讓我特別想沉下來,去做像鄉村建設這樣話題的紀錄片,我想打破公眾的刻板印象。
我在貴州的很多貧困村做過調查,跟着當地的駐村書記深入到鄉村生活後,我突然發現,我才是活在象牙塔裏的人。
我們現在看到農村的信息是高度不對等的,那裏人的生活經驗在互聯網上,在這個信息媒體中被共享得太少了。
這裏還有其它更深層次的問題,中國的發展層級跨度太大了,北京月薪一兩萬很難活,但在當地,年入6500就是脱貧。不同的人需要解決的生存困境完全不一樣。
當這個差距大到這個程度的時候,如果信息不夠流通,雙方是無法對話的,爭議只能更大。假如雙方突然有一天碰面了,才發現,我的天啊,很多我們以為理所應當的認知是完全割裂的。
在這一層現實上,我告誡我自己,要繼續做一個合格的影像創作者,珍惜我能夠拿到的這個表達空間。
它不僅僅是你堅守客觀的正義,我們更需要大智慧,去完全實現它。這是未來每一個從事影視創作的人的必修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