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批評 | 洪子誠:“有神”與“無神”之間,隔着廣大的空間_風聞
文艺批评-文艺批评官方账号-2022-08-08 09:15
編者按
本文是洪子誠老師為新版《契訶夫手記》(賈植芳譯,上海文藝出版社)作的序言。契訶夫這位俄國作家曾給予賈植芳先生坎坷的生命歷程以啓示和支持的力量,讓他“像一個人那樣活了過來”。《手記》是契訶夫1892到去世當年日常生活中觀察、閲讀、思考的片斷記錄,以及1896到1904 的日記,另外還有一些附錄文字。對契訶夫和俄國文學的研究者來説,《手記》自然是重要的材料,於一般讀者而言,這也是一部值得一讀的智慧、幽默的雜記隨筆集。洪子誠老師認為,契訶夫生性謙遜,對生活,對藝術有他的獨特追求,有他的堅持的理想和思想原則,對許多作家、讀者來説,和契訶夫相遇不一定就一見鍾情,可一旦邂逅並繼續交往,他的那些樸素、節制、幽默、憂鬱,也對未來滿懷朦朧想象的文字,很可能就難以忘懷。契訶夫能夠將豐富多彩的生活全部容納在自己的有限篇幅之中而達到史詩式的雄偉,他書寫“小人物”,日常生活中的人、普通人,沒有明確的派別立場和意識形態歸屬,“關注的是人物的虛假和真實”。因此,洪子誠老師寫到:“契訶夫在‘有神’與‘無神’,愛與恨,觀念與行動、真實與美,犀利的揭發與體諒的同情……之間的‘平衡’,從根本上説不是導向無原則的中庸、冷漠,而是尊重事物的複雜和多樣,並最終為常識,為弱者,為普通人爭取到存在的價值和尊嚴”。
本文原刊於“讀書”雜誌2022年第8期,發表時有所修改,文藝批評公號推送的是原稿,感謝洪子誠老師和《讀書》雜誌授權轉載!

洪子誠
“有神”與“無神”之間,
隔着廣大的空間
新版《契訶夫手記》序言
《契訶夫手記》(下面簡稱《手記》)是契訶夫的書,也是賈植芳先生的書。這樣説不僅因為賈先生是《契訶夫手記》 的譯者,還因為這本書和譯者情感、生命之間的聯繫。1953年譯本由文化工作社初版後的第三年,賈植芳就因胡風事件而遭受牢獄之災。二十多年後冤案平反,他偶然從圖書館看到這個譯本,“就像在街頭碰到久已失散的親人一樣,我的眼睛裏湧出了一個老年人的淚花”。原先賈植芳翻譯這本書的初衷,是基於對這位俄國作家的喜愛,對他在人生道路上給予的啓示;經歷了二十多年坎坷的生命歷程,他更意識到這種啓示、支持的力量:就如賈植芳説的,讓他“像一個人那樣活了過來”(《新版題記》)。

契訶夫
《手記》包括1892到去世當年契訶夫日常生活中觀察、閲讀、思考的片斷記錄,其中有一些成為他後來作品情節、人物的依據。另外的部分,是他1896到1904 的日記。80年代《手記》新版增加了江禮暘翻譯的《補遺》。書中還附錄了契訶夫妻子奧爾加·克宜碧爾(也譯為奧爾加·克尼碧爾)談契訶夫臨終情景的文字,和他的弟弟寫的《契訶夫和他的作品中的題材》。《契訶夫年譜》是賈植芳在50年代初編寫的,留存有那個時期思潮的痕跡;而《我的三個朋友》一文講述的則是這個譯著出版和再版的經過。對契訶夫和俄國文學的研究者來説,《手記》自然是重要的材料,於一般讀者而言,既可以藉此瞭解這位作家的思想藝術,它也是一部值得一讀的智慧、幽默的雜記隨筆集。
契訶夫對生活,對藝術有他的獨特追求,有他的堅持的理想和思想原則,但正如不少同時代人和後來評論者説的那樣,他是生性謙遜的人。在寫出《草原》《命名日》這樣的作品之後,他給柴可夫斯基的信中,在以托爾斯泰為首的單中將自己列在第98位。托馬斯·曼説,直到生命的結束,他也從來不曾擺過文學大家的架子,更不用説那種哲人的或托爾斯泰式的先知的派頭了;“多年來西方,甚至俄國對契訶夫評價不足,在我看來是跟他對待自己的那種極端冷靜、批判而懷疑的表現以及他不滿意自己的勞動的那種態度,簡單説吧,是跟他的謙遜分不開的”。伊利亞·愛倫堡也有相似的評述,説契訶夫不斷矯正自己的缺點,但“他無需與驕傲作鬥爭”,“他逃避榮光”(《重讀契訶夫》,童道明譯)。1900年,他離世前四年,在和布寧的一次談話中,有點憂傷地預測他的作品還會給人讀七年。他幾乎沒有寫過專門的文學問題文章,也沒有撰文談論過自己的創作。我們現在看到的《契訶夫論文學》(汝龍中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收錄的主要是他寫給親人和朋友的書信,以及同時代人回憶的言談片斷。《手記》中記錄了這樣的細節,在朋友家聚會,突然有人面色莊重舉杯向他致敬,“在我們這個理想變得黯然無光的時代……你播送了智慧,不朽的事業啊”。聽到這些恭維的話,契訶夫當時的反應是,“我覺得我本來是蓋着什麼東西的,現在卻被揭去了,被人用手槍瞄準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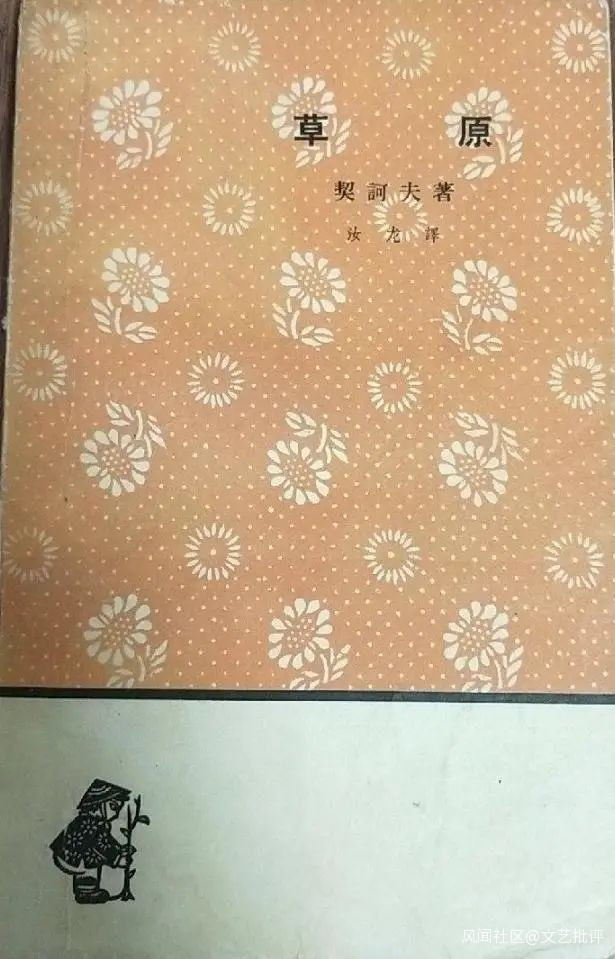
《草原》
[俄]契訶夫 著
汝龍 譯
人民文學出版社19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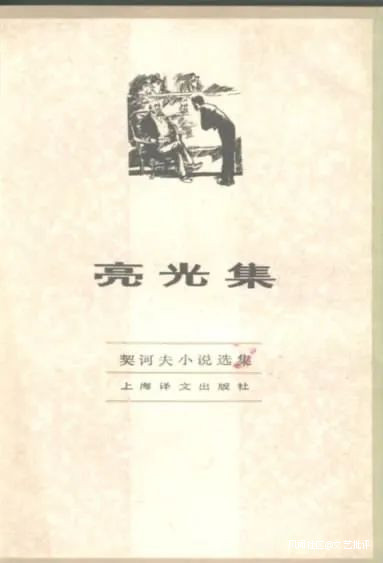
《亮光集》
[俄]契訶夫 著
汝龍 譯,
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 1982-8

《重讀契訶夫》
[蘇] 伊利亞·愛倫堡 著
童道明 譯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1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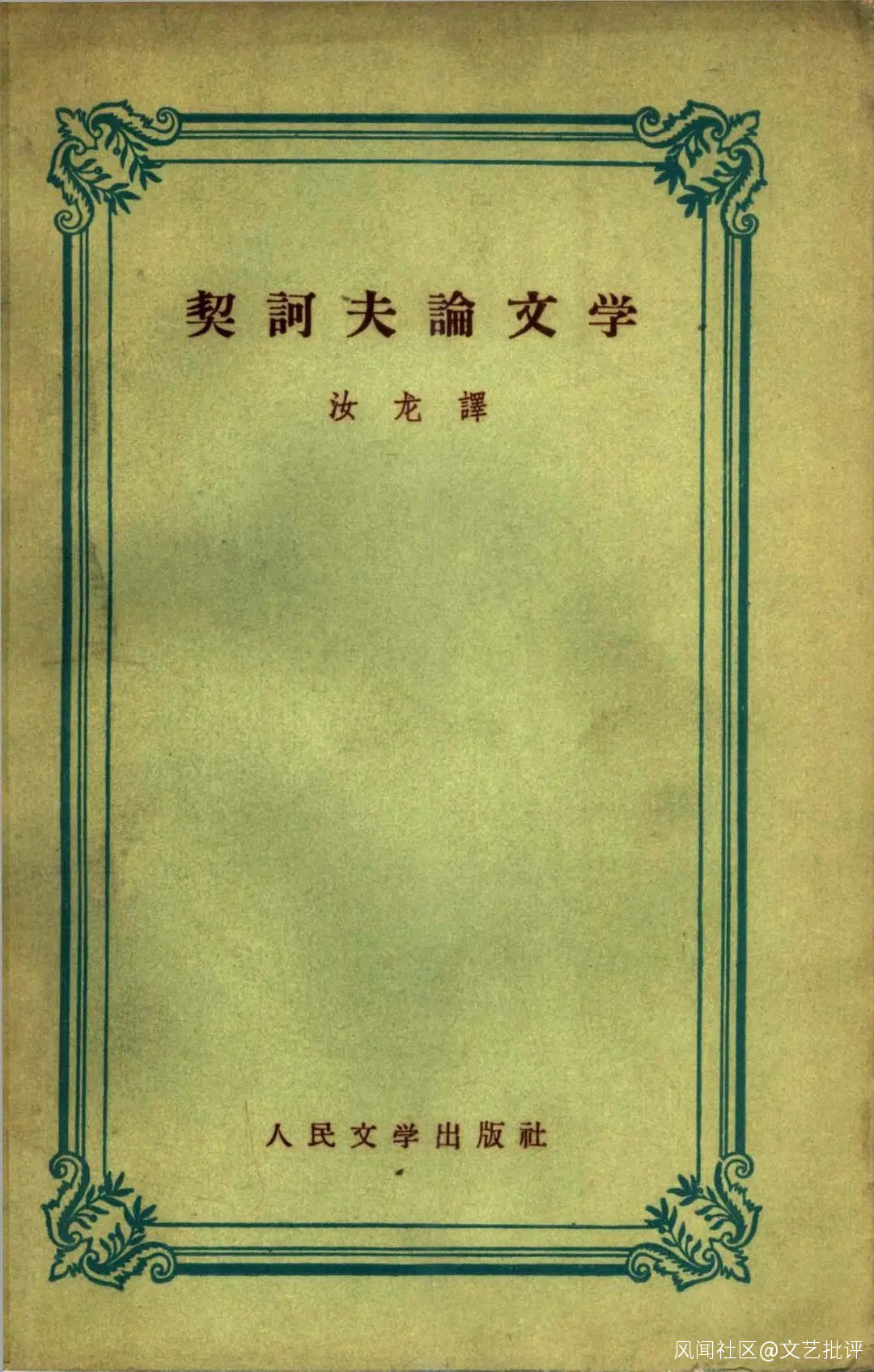
《契訶夫論文學》[俄]契訶夫 著
汝龍 譯
人民文學出版社
1958-9
契訶夫在德國的巴登威勒去世,那是1904年7月。比他小15歲,剛開始文學寫作的托馬斯·曼談回憶説,他極力思索,也無法記起這位作家逝世的消息給他留下什麼印象。雖然德國報刊登載了這個消息,也有許多人寫了關於契訶夫的文章,可是“幾乎不曾引起我的震驚”,也絕對沒有意識到俄國和世界文學界遭遇到很大損失。托馬斯·曼的這個感覺是有代表性的。契訶夫不是那種能引起震撼效果的作家,他不曾寫出“史詩”般的宏篇巨構,在寫作上沒有表現出如托爾斯泰、巴爾扎克那樣的“英雄式”的堅韌氣概。但是正如托馬斯·曼説的,雖説他的全部作品是對於史詩式豐碑偉業的放棄,“卻無所減色地包括了無邊無際廣闊巨大的俄國,抓住了它遠古以來的本然面目和革命以前社會條件之下毫無歡樂的反常狀態”——對於他的價值,他的“能夠將豐富多彩的生活全部容納在自己的有限篇幅之中而達到史詩式的雄偉”,人們是逐漸認識到的(《論契訶夫》,紀琨譯)。確實,對許多作家、讀者來説,和契訶夫相遇不一定就一見鍾情,可一旦邂逅並繼續交往,他的那些樸素、節制、幽默、憂鬱,也對未來滿懷朦朧想象的文字,很可能就難以忘懷。
賈植芳説契訶夫讓他“像一個人那樣活了過來”,“像一個人”的“人”沒有前置詞和後綴,就是日常生活中的人,普通的人。契訶夫作品的人物圖譜中,基本上也是一些“小人物”,用當代一個奇怪的概念來説就是“中間人物”。我們從裏面找不到搏擊風浪的英雄,其實也可以説沒有典型的壞蛋、惡棍。他刻畫了19世紀末俄國社會中下階層的各色人物:地主、商人,鄉村教師、醫生,農民、大學生、畫家、演員、小官吏、妓女… …其中,知識分子佔有重要地位,也傾注作家很多的複雜情感。他筆下的知識分子,大多是有道德理想、有莊嚴感,不倦想象、追求着有價值生活目標,並自認為對人類懷有責任的人。但同時,他們又是軟弱,缺乏行動力,生活在烏托邦夢幻煙霧裏,什麼大事都做不成的人。《手記》中有這麼一條,“伊凡雖然能夠談一套戀愛哲學,但不會戀愛。”——賈植芳先生加了一個很好的註釋,指出了這裏的雙關義:“契訶夫之兄名伊凡。伊凡泛指俄國普通人,這裏有‘俄國伊凡’之説。”

契訶夫筆下的小人物
這樣的人物自然難以鼓動起讀者的鬥爭熱情,契訶夫也不會有這樣的打算——從《手記》中知道,他質疑將人類歷史看成戰鬥的連續,將鬥爭當作人生主要東西的看法。那麼,這些“灰色”人物有什麼存在的價值?作為藝術形象他們的意義何在?或許可以用曾是契訶夫同胞的納博科夫的話作答:
//
……契訶夫暗示説,能夠產生出這種特殊類型人物來的國家是幸運的。他們錯過時機,他們逃避行動,他們為設計他們無法建成的理想世界而徹夜不寐;然而,世間確實存在這樣一種人,他們充滿着如此豐富的熱情、強烈的自我剋制、純潔的心靈和崇高的道德,他們曾經存活過,也許在今天冷酷而污濁的俄羅斯的某個地方,他們仍然存在,僅僅這麼一件事實就是整個世界將會有好事情出現的預兆——因為,美妙的自然法則之所以絕妙,也許正在於最軟弱的人得以倖存。(《論契訶夫》,薛鴻時譯)
契訶夫在寫作上嚴格面對現實生活;他努力拓展生活的疆域,但從不寫他不熟悉、未曾深入體認的事物。他説,《手記》中説,哈姆雷特不該為夢見的鬼魂奔忙,“闖入生活本身的鬼魂更可怕”。他的作品——小説、戲劇,也包括這本《手記》,給我們許多啓示、感動我們,犀利的觀察和評述推動着我們的思考。當然,我們也會有疑惑,也會與他磋商,甚至暗地裏發生爭議。譬如:對人性的理解(“邪惡——這是人生來就揹着的包袱”;愛、友情並不可靠,而仇恨“更容易將人團結在一起”);對女性品格更多的苛求;對自然科學、科技發展推動人類進步的理想化想象……但是,我們沒有料到的是,這個熱切追求理想生活和人的高度精神境界,不斷揭露虛偽、庸俗、欺詐、暴力的作家,在世和死後,卻會受到冷漠、無傾向性、無思想性的責難,以至在他死後50多年,愛倫堡在《重讀契訶夫》中,還要用很多篇幅來為他辯護。
造成這個狀況的原因,一是契訶夫很少在他的作品中發表政治見解,在俄國當時的政治派別和意識形態紛爭中,從未明確表示他的派別立場和意識形態歸屬。另一方面,則是他看待生活、看待人的方式。對於責難他曾有這樣的回應 :“我不是自由主義者,不是保守主義者,不是漸進論者,不是僧侶,不是冷漠主義者……我憎惡一切形式的虛偽和暴力”;“當然,我的小説中平衡正負關係的努力是可疑的。但要知道,我並不是在平衡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這些對我並不重要,我關注的是人物的虛假和真實。”

“契訶夫花園”中的契訶夫雕像
“平衡”這個詞,也可以用分配、調適來替代,可以理解為慎重處理對立物關係。別爾嘉耶夫在《俄羅斯思想》中説過,俄羅斯精神結構中具有兩極化的對立傾向,一切事物均按照正統和異端來進行評價;俄羅斯人不是懷疑主義者,不大瞭解相對的東西。契訶夫對這一特性也有深切瞭解,他警惕、抵抗着這種極端性。《手記》中寫道:“在‘有神’與‘無神’之間,隔着廣大的空間。……俄羅斯人都知道這兩個極端之中的一個,但對於這中間卻毫無興趣。”契訶夫在“有神”與“無神”,愛與恨,觀念與行動、真實與美,犀利的揭發與體諒的同情……之間的“平衡”,從根本上説不是導向無原則的中庸、冷漠,而是尊重事物的複雜和多樣,並最終為常識,為弱者,為普通人爭取到存在的價值和尊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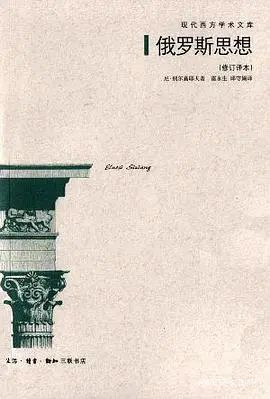
《俄羅斯思想》
尼·別爾嘉耶夫 著,雷永生 / 邱守娟 譯,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4-3
在“可疑”的平衡正負關係的努力中,藝術家的社會責任和藝術創造的自由,是其中重要的一項;契訶夫的處理方式,也提供了後來討論這一無解問題的絕佳“案例”。“案例”這個詞,來自愛爾蘭詩人希尼,他寫有《尼祿、契訶夫的白蘭地和一根敲擊棒的有趣案例》(The Interesting Case of Nero, Chekhov’s Cognac and a Knocker 吳潛誠譯,《希尼詩文集》中馬永波譯為《尼祿、契訶夫的白蘭地與來訪者》)。這裏牽涉到契訶夫一生中的一個重要事件:1890年30歲時的薩哈林島之行。這期間,契訶夫已經確立了他的藝術家的社會地位,他執意長途跋涉去考察囚禁各種罪犯的“罪惡之島”的決定讓莫斯科的朋友吃驚。契訶夫認為,作為一個幫人解除病痛的醫生,有權在世上佔有一定位置,但是在許多人得不到自由,遭受苦難、折磨的情況下,從事修辭寫作和藝術演練,豈不是對生命的冒犯、褻瀆?他需要有所證明,他決定進入這個“罪惡之島”,與囚犯一起生活,寫出類乎見證之書的考察報告。臨出發時,朋友送他一瓶昂貴白蘭地,在六個星期的舟車勞頓中一直珍藏。待到達薩哈林島的那一天晚上,才開瓶暢飲這琥珀色的醇香的酒。希尼將這看作是象徵意義的一刻:白蘭地不僅是朋友的禮物,也是契訶夫的藝術:他對周圍的苦難毫不退縮,他有了回應而獲得心安,獲得了作為一個藝術家的內心的平靜。

契訶夫遠行薩哈林島
之前與家人合影

1890年契訶夫在薩哈林島
這裏涉及嚴肅、真誠的藝術家經常面臨的藝術與真實、與生命,歌唱與苦難的緊張關係。如同希尼説的,詩歌、藝術無論怎麼有所擔當,總有一種自由的,不受束縛的因素,總有欣悦、逃遁的性質。因此,藝術家在抉擇上,在契訶夫所説的“平衡”上的工作並不容易,這種調適和平衡也無法一勞永逸。契訶夫的薩哈林島之行,是以親身深入苦難之境的行動來介入,也以撰寫類乎“見證”的,波蘭詩人Z·赫伯特的“敲擊棒”式的文字(赫伯特寫有題為《敲擊棒》(A Knocker)的詩:“我的想象/是一塊木板/我唯一的樂器/是木棍”),以面對實實在在的苦難和生命,來試圖減緩、解除詩歌、藝術與現實之間的緊張衝突。
我第一次讀契訶夫作品是1954年,那年開始上高中,從《文藝學習》讀到他的《寶貝兒》,也從這個雜誌的封面見到他那標準的大鬍子、帶夾鼻眼鏡的畫像。當時並不覺得《寶貝兒》有多好,還認為他是個六七十歲的老頭。後來才知道他死時只有44歲,這樣的年齡,在我們這裏還算是青年作家。原先以為只有藝術家會短命(莫扎特、舒伯特、梵高……),一直的疑問是,這樣的成熟、睿智、節制、美麗的文字,怎麼會出自30餘歲人的筆下。契訶夫無疑屬於那種將真理、正義放置在首位的作家。但是,他的藝術實踐也提出了這樣的問題:在藝術、文本的內部,是否也可以取得一種歌唱和生命緊張關係的平衡?而純粹的,並不傳達救贖訊息的美本身,是否也是增加世界良善的“救贖”的力量?回答應該是肯定的。事實上,無論是契訶夫,還是希尼,都是將藝術、歌唱與現實政治的衝突,看作是特定歷史情境中的邂逅;契訶夫也明確將他的“贖罪”行為看作是個人的選擇。他們無意將這些普遍化,無意將踐行自己理念的行為扭曲為一種準則,而讓其他人都處於“道德的陰影”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