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心內外:衝突、炎症和戰爭_風聞
来者建强-仁者见智2022-08-16 16:10
感染,是人體最常見的致病過程。從感冒、肺炎,到鼠疫、天花,大多數急性發作的症狀均可稱為炎症。拉丁文的病名中,凡是帶“-itis”這個後綴的都是炎症,例如colitis(結腸炎),hepatitis(肝炎)等。
在傳染病這個大領域裏,現代正規醫學通過抗生素的發現和疫苗接種對抗感染取得了巨大成功。如果説過去大部分人都死於傳染病,那麼今天在醫療條件優越的地區和國家,這已不成為一個問題。但並不是説,我們感染得少了,而僅僅是我們已經掌握了消滅傳染的利器。
“利器”一説多少會讓人覺得有“好戰”之嫌,這恰恰提醒了我們,炎症的過程實際上正是發生在“身體內的戰爭”:身體的防禦系統正在攻擊和消滅敵對的病原體的危險勢力,如病毒、細菌、毒素。這種鬥爭可以清晰地投射在我們所能體驗到的那些症狀裏,如發燒、疼痛、紅腫。
炎症,通過中文象形的構造可以讓人更加一目瞭然地抓到它的靈魂,“火上加火”之症,而“火”是可以引爆炸藥的常見物。炎症在現代英文中叫做“inflammation”,字面的本意也是“着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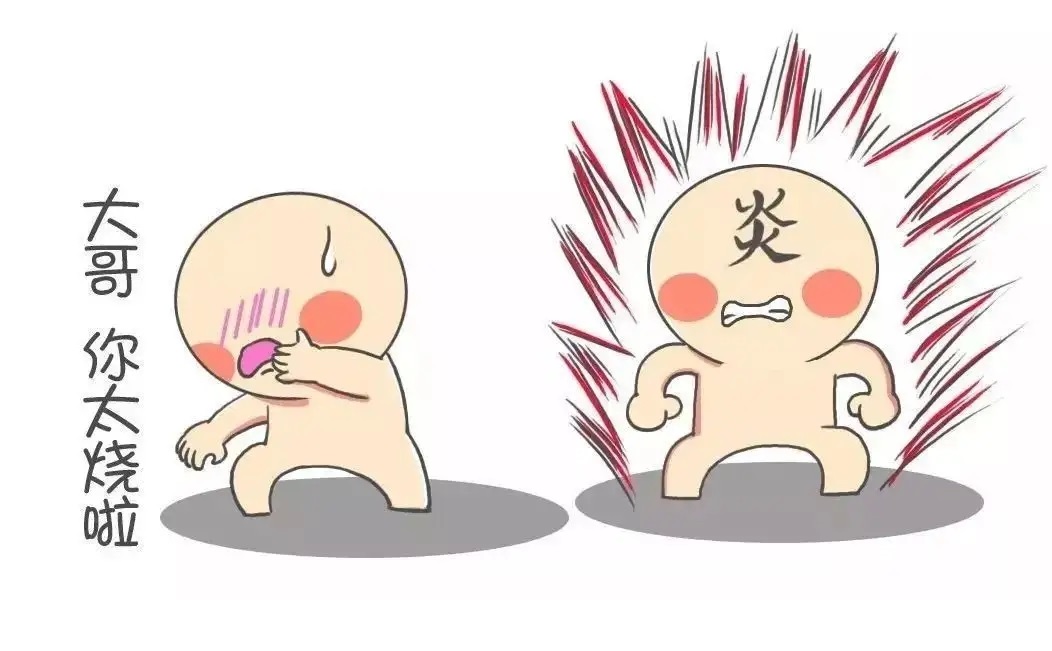
以上這兩則語言學的補充證據可以很好地用來強化把炎症比作戰爭的恰當之處,例如:一場懸而未決的衝突變成了熊熊大火,點燃導火線,火把被扔進了房子,歐洲的東部變成了一片火海,等等。這麼多引爆物一般遲早會引起那個地區早已陳年積聚物的爆炸。
這種現象我們不僅能在戰爭中看到,也可以在我們的身體裏看到,如果有什麼小膿皰或大膿皰要發泄的話。所以,人也會“炸”。當然,會炸的絕不是什麼膿腫,而是指一種情緒感覺的變化,一種內心衝突壓抑的釋放。
每一種感染都是物質化的衝突。如果身體能夠戰勝入侵的病原體,人就克服了感染;如果病原體勝利了,人恐怕就要面臨命懸一線的危險。在心靈中得以避免的交鋒也會以炎症形式在身體層面上強行取得它的合理性。
炎症與戰爭之間雖然並無因果關係,但是兩者內部結構是一樣的,兩者要實現的原則也一樣,只不過顯示的層面不同罷了。所以,從衝突,到炎症,再到戰爭,大致可以找到七個進展層面的對應關係。
第一,病原體入侵帶來刺激反應。
病毒、細菌或毒素的侵入,其真實的意義並不是為了驗證病原體的存在,而是要表明人的身體自己放它們進來的。醫學把這稱為免疫狀況不佳。不像那些殺菌熱衷者所信奉的那樣,傳染是因為有病原體存在,其實是因為與傳染共同生活的能力出現了異常狀況!
這種説法完全可以移植到意識層面,在此,需要我們認清的重要問題,不是人是否生活在一個無菌的——即無問題和衝突的世界裏,而是人是否有能力與衝突打交道。免疫力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受心理控制的,這一點已為當今科學所認可。

反過來的説法可以被用來形容對自身炎症問題的觀察。例如,誰不願意向一個使他不安的衝突開放他的意識,誰就必須向病原體開放他的身體。病原體沾附在身體的某些抵抗力弱的地方——正規醫學稱之為先天的或遺傳的不足之處。
缺少類比思維(或同理心)的人在這個地方往往會捲入一個不可調解的理論衝突之中。正規醫學把某些器官對炎症缺乏抵抗力的原因僅僅説成是先天的器官虛弱,彷彿不可能再有其他的解釋。然而,心身醫學早已注意到,某些問題與某些器官相關,這種思路自然與正規醫學所説的抵抗力弱的闡述大相徑庭。
繼續來觀察炎症的進展,先不去管具體的發病部位,病原體侵入身體,在心理層面上與這一過程相對應的是產生了一個問題的挑戰。一個我們迄今為止尚未真正對待過的衝動突破了我們意識邊界的防禦線,使我們感到不安。它點燃了對立性的對立大火,於是我們就經歷了對立性,即衝突。
炎症是物質層面的衝突,我們不應該犯這樣的錯誤,即表面化地看待傳染病,從而得出“我根本沒有衝突”的結論。正是這種無視衝突的態度導致了生病。弄清衝突所需的努力,是需要一份能揭露虛偽的真誠,但這大多會給心靈帶來不適,就像感染給身體帶來不適一樣。而我們總是習慣於避免這種不適,但病毒根本不會顧及這些。
如果我們的心理抵抗力發揮良好,那麼衝動就不會到達我們的上意識,我們不會受到挑戰的影響,卻必須體驗這種挑戰的發展。當前,海峽兩岸有如此例。
在戰爭這個層面上,與刺激相對應的即是敵人強行闖入。這樣的攻擊當然會把全部的軍政注意力引到進犯者頭上——所有的人都變得格外積極主動,盡其全力來對待這個問題,調集軍隊,進行動員,尋找同盟軍。簡而言之,人們的注意力都集中到這個攪局的策源地上來了。在身體層面上,醫學把這一過程叫做滲出階段。
第二,滲出階段,即病原體附着以後就形成了一個炎症灶。組織液從四面八方朝這裏流來,組織腫脹起來,形成較大的內壓。
在心理衝突層面,這個階層壓力可能增大得更明顯。我們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新問題上,我們已不能再考慮其他事情了,新問題日夜折磨着我們,我們無心再談及別的話題,思想不停地圍着新問題轉圈。就這樣,我們的全部精神力量都花在了衝突上面,但是又不允許被人拿來到處去講。
看來,是我們在扶植問題,使它膨脹起來,直到它像一座不可逾越的大山聳立在我們面前,聳立在波詭雲譎的平面上。衝突動員了我們的全部精力去對付它。

第三,防禦性反應。身體在病原體(抗原)基礎上製造了特定的抗體——在血和骨髓中製造。淋巴細胞和粒性白細胞在病原體四周築起一道長城,即所謂的粒細胞牆。
然後,巨噬細胞開始吞食病原體。於是,身體層面上的戰爭如火如荼:敵人受到包圍和打擊。如果衝突不能在局部解決(有限戰爭),那麼接下來就會發生總動員。要求全體參戰,並全心全意為戰爭服務。在身體中的這個情形叫做發燒,即一場表面平靜而內裏翻江倒海的炎症風暴。
第四,發燒,就是病原體被防禦力量擊垮了,其間釋放出來的毒素導致發燒症狀。
發燒時,我們全身通過升温來對付局部的炎症。體温每升高1攝氏度,代謝效率翻了一番。由此可見,發燒對付防禦的強化作用是多麼大,或者説代價也很大。因而,有民諺説:“發燒有利於健康”。這正好説明了發燒是體温與生病過程的速度關係。所以,我們可以放心地把一切退燒措施控制在不發生生命危險的極限值,不要一碰到體温升高就立刻如臨大敵地進行人為降温。
在心理層面上,衝突發展到這一階段就把我們的全部活力和精力都吸引了過去。在身體發燒和心理激動之間有着十分令人矚目的相似性,以至於我們常自詡“我們是發燒友”、“為某某激情燃燒”。我們在激動時會感到渾身發燙,心跳加快,臉紅、脖子粗,不論是因為愛情還是憤怒,機制都是一樣的。
我們會興奮地出汗,緊張到顫抖。所有這一切聽起來不怎麼動聽,但卻有利於健康。因為不僅僅是發燒對健康有利,處理衝突對健康可能益處更大。可是,人們卻千方百計把發燒和衝突儘可能消滅在萌芽狀態,而且還為採取種種壓制手段而感到驕傲。

第五,緩解(或是解決)。
假定身體抵抗獲勝,趕跑了異物,吸收了其中一部分,結果是抗體和病原體都發生了衰變,生成了黃色的膿。病原體失去了鋒芒,改變了形式,離開了身體。另一方面,身體也起了變化,現在它掌握了病原體的信息,具有了所謂的“特異性免疫”。同時,全部防禦力量都受到了鍛鍊和加強,也就是説加強了“非特異性免疫”。
從軍事上來説,這相當於在雙方都受到損失以後,一方取得了勝利。然而,勝利的一方經過交戰變得更強大了,因為它已經適應了敵人,瞭解了敵人,將來能對它做出專門的反應。
從這一點來説,面對病毒流行遲遲做不到放手的人,多半是一個身心都不夠強大的人。放不下的舉動很容易被敵人看穿,從而自我暴露了虛弱的底子。
第六,死亡。這種情況的發生是病原體獲勝了,這是人不願看到的結果,但也是人的一種片面看法。
這就像足球比賽,就看你是站在哪一邊。勝利就是勝利,戰爭也常以一方的勝利而告終。勝利的歡呼聲同樣都是響徹天空,區別僅僅在於是哪一方的歡呼聲罷了。
第七,慢性化。
如果衝突雙方中沒有一方能如願以償地解決衝突,那麼就會在病原體和防禦力量之間達成妥協:病原體雖未獲勝(致人於死地),卻依然獲得了在人體內的“居留權”。這種情況我們就稱之為慢性化。
其症狀特點是:淋巴細胞和粒性白細胞數量持續過高,血沉略有提高並伴有低燒。沒有消除的衝突在體內形成一個病灶,日夜不停地消耗着集體本已欠缺的精力,最後很有可能產生更可怕的疾病——癌症。
於是,病人總是無精打采,疲憊不堪,對生活提不起興趣,甚至麻木不仁。他既不病倒,也好不起來,這不是真正的戰爭,更不是真正的和平,而是一種妥協的後遺症——屈辱。
正如世界上所有的妥協一樣,它也是不可靠的。妥協是怯懦即“不冷不熱的人”的最佳收穫,這些人始終害怕自己行為的後果,害怕承擔由此而產生的責任。因此,妥協算不上是一種解決辦法,因為它既不是兩個極端絕對平衡,也沒有力量使兩個極統一。妥協意味着持續不和,繼而是誰也別想好的蕭條。

從軍事上講,妥協是陣地戰,它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使得其他領域如經濟、民生、文化等被大大削弱甚至會癱瘓。
在心理範圍,慢性化的對應物是持續衝突。人們陷於衝突的泥潭,沒有勇氣和力量來做出決定。(2022年的大型音樂勵志類節目《中國好聲音》特別邀請馬來西亞華語女歌手梁靜茹擔當導師,用意似乎就在梁的那首歌曲——勇氣——當下最稀缺、昂貴的資源。)
每一種決定都要付出犧牲——同一時間只能兩者求其一,而這種必要的犧牲也會使人膽戰心驚。許多人就死守在衝突雙方中間,重複塗抹略有涼意的消毒水,而沒有能力去幫助這個極或那個極去獲得勝利。他們始終在權衡哪種決定對、哪種決定錯,其實根本不懂得,抽象意義上的對和錯是不存在的,也是毫無意義的。
每一個乾淨利落的決定都有解放作用。而慢性化的持續衝突卻只會不斷自我消耗,直至讓人灰心喪氣。如果決心向衝突的一個極挺進,很快就會感到我們的精力得到了解放。身體在感染後會變得更強壯,同樣,心靈在衝突中也會變得更堅強,因為它通過處理問題學到了東西,通過在對立的兩極之間進行抉擇而擴大了自己的領域。
我們每一次衝突都會取得收益,這就是信息,信息與特異性免疫相似,能使人以後採用平安的辦法來處理同樣的問題。此外,我們所經歷的每一次衝突也教會我們更妥善更勇敢地去對待以後的衝突,這種能力就相當於身體的非特異性免疫。
正如在身體層面上每一種解決方式尤其會給戰敗一方帶來犧牲一樣,在心理層面上的每一個決定會帶來巨大的犧牲:例如某些一貫的觀念和意見,某些愛——不能捨的生活態度和習慣——只好化作一包膿水。
舊事物的死亡是新事物誕生的前提,正如較大的炎症病灶會在身體裏留下疤痕,有時候也在心靈上留下傷痕,這就是我們對過去生活中重大事件的回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