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CM2022訪倪憶:關乎取捨_風聞
返朴-返朴官方账号-关注返朴(ID:fanpu2019),阅读更多!2022-08-20 10: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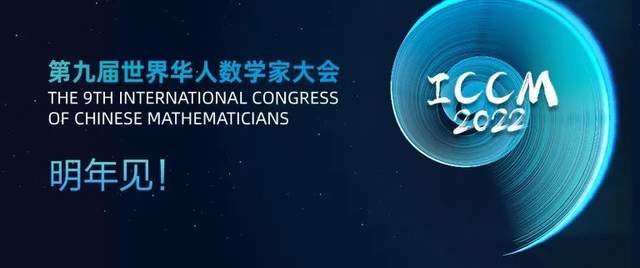
提起倪憶,眾數學同仁恐怕都不陌生,公眾號“普林小虎隊”、“返樸”時常刊發、轉載他撰寫的科普文章,引經據典,風趣幽默,發文量頗為可觀。2022年菲爾茲獎公佈前後,一系列預測、分析文章,令人叫絕。倪憶描述自己的生活:“平時除了研究數學和教書帶學生,喜歡追蹤科研熱點新聞,喜歡帶娃鍛鍊身體。”
特別感謝倪憶老師以文字回覆了我們的問題。全文刊發,以饗讀者。
被採訪者 | 倪憶
編輯 | 牛芸

Q:您的主要研究領域是三維拓撲與紐結理論,特別是Heegaard Floer同調論及其應用(three-dimensional topology and knot theory, specifically Heegaard Floer homology and its applications)可否對這一領域做一個簡單介紹?這一領域目前的熱點研究問題是什麼?和其他數學分支的關係?可否介紹您正在從事的工作、最新成果以及創新點?
倪憶:我的研究領域是低維拓撲。這是拓撲學的一個分支,主要研究低維(二、三、四維)流形的拓撲學。在拓撲學發展的早期,大家主要研究一般空間的性質。上世紀五六十年代,Milnor、Smale等的工作使得對(單連通)高維流形拓撲的研究蓬勃發展。到了七八十年代,Thurston、Donaldson等從別的領域引進了新的思想,讓低維拓撲學跟許多其他數學分支聯繫起來,產生了異常豐富的內容。從此低維拓撲成為數學的一個主流分支。
我的具體研究方向是Heegaard Floer同調論,這是Ozsváth和Szabó在2000年創立的一個理論,用辛幾何方法對三維流形、紐結、以及光滑四維流形定義了新的不變量。從歷史發展看,這一理論跟八十年代的Donaldson理論一脈相承,但具體表現形式已經天差地遠了。Heegaard Floer同調從技術上説,比以前用規範場論定義的不變量簡單許多,但又可以用來解決低維拓撲裏的一大批問題。所以過去二十年裏,其研究非常興盛,進展極其迅速。Heegaard Floer同調本身的發展受到了辛幾何、切觸幾何、規範場論、葉狀結構、量子代數等領域的影響。另一方面,Heegaard Floer同調也極大地促進了這些領域的研究。
當前Heegaard Floer同調研究的一大主題是在各種意義上把這一不變量推廣到別的形式,例如等變形式、曲線形式、同倫形式等等。另一方面,人們對於Heegaard Floer同調中究竟包含着什麼樣的幾何與拓撲信息也非常感興趣。有一個“L-空間猜想”,就是將Heegaard Floer同調裏的L-空間與緊繃的葉狀結構以及基本羣的可排序性聯繫起來。
我原計劃在ICCM上報告的題目是 “紐結Floer同調的次高項”。紐結就是三維空間中的繩圈。Heegaard Floer同調有一個對於紐結的版本,稱為“紐結Floer同調”。Heegaard Floer同調裏最深刻的結果之一就是發現了紐結Floer同調的最高項裏藴含着豐富的拓撲信息。近年來,我們發現,紐結Floer同調的次高項同樣也有着大量的拓撲/幾何信息。我講的內容有三點:次高項是否非零,不動點個數的估計,右傾自同胚的判定準則。其中,次高項非零是一個猜想,但此前支持它的證據很少,我們的工作表明這個猜想很有可能是正確的。不動點個數的估計涉及到紐結Floer同調與辛同胚的Floer同調之間的關係。以前大家對這一關係有所猜測,但未能證明。我們使用了一個技巧,把紐結Floer同調化為一個閉流形的Heegaard Floer同調,然後就可以利用一些已知的結果來得到我們需要的關係了。右傾自同胚的判定準則是一個出乎意料的結果,我和我的合作者們對於能夠證明這樣強的判別準則也感到非常吃驚。這些結果在Dehn手術、切觸幾何等領域都有應用。
Q:從黃岡中學一路走來,您也曾經獲得國際奧賽金牌。您在基礎教育和高等教育階段,是如何完成從參賽到科研的轉變的?
倪憶:我上大學以後就基本脱離了數學競賽,從頭開始進行高等數學的學習。最初也曾迷茫過,不知道自己是否有能力從事數學研究。直到後來做了一些工作,才產生了信心,繼續在這條道路上走下去。我最早的科研工作是在北大讀碩士的時候做的,當時王詩宬老師給我一篇他寫的論文,叫我把其中的定理推廣到另一種情況。這其實並不難,基本上只需要模仿他原來的證明,在一些細節上作少許修改。後來我讀博進入Heegaard Floer同調這一領域,做的第一個工作是把Ozsváth和Szabó關於紐結的一個重要結果推廣到鏈環。這個證明也是模仿原來的證明,但在一些細節上用到了我從Gabai論文中學到的葉狀結構方面的知識。對於初學者來説,只要有一定基礎,模仿並推廣前輩數學家的工作應該是一個很好的入門手段。這一過程中,能夠對原來的證明理解得更透徹,並學習一些相關的必要知識,積累信心。我同輩的數學家中,很多人都有類似的經歷。
Q:您師從美國院士David Gabai教授, 跟隨大師學習的過程是怎樣的?David Gabai院士對您的影響有哪些?
倪憶:普林斯頓數學系的傳統是導師不太管學生,放任學生去尋找合適的問題。跟我同一個辦公室的某人,有時一個學期都沒機會與導師單獨會面。相比之下,Gabai算是比較隨和。我經常不預約就去敲他辦公室的門,總能找到他。現在想起來,我這種做法挺不禮貌的。
我的研究課題跟Gabai的相差甚遠,所以當時從他那裏學習的不多。儘管如此,我往往能從與他的談話中得到啓示。他給大家的印象,並不是反應非常快的一個人。問他問題,他經常要想很長時間才回答。但他思考問題特別深入,每每一語中的。我博士論文中有一個關鍵的步驟就是在他建議下,使用他早年一篇著名論文中的方法才得以完成的。
Gabai的研究涉及到低維拓撲的好幾個不同領域,非常博大精深。他做的數學我懂的還不到十分之一,但對於我的科研已經非常有用。他1980年獲得博士學位,從那時至今一直活躍在學術前沿,不斷有第一流的工作面世。他自己不做Heegaard Floer同調,但他的工作對這一理論影響非常大。Heegaard Floer同調裏一些最深刻的定理都建立在他早年工作的基礎之上。我這次報告中提到的右傾自同胚,其定義的靈感來源也是Gabai早年的工作。
Gabai的一大特點是非常專注。他的導師Thurston剛出道時研究葉狀結構,僅僅兩三年時間就像推土機一樣推平了葉狀結構裏的一大批公開問題,以至於業界專家普遍認為葉狀結構是一個已經沒有前途的領域。Gabai跟隨Thurston時,Thurston已經轉去做雙曲幾何,Thurston的學生也都在做雙曲幾何,只有Gabai在做被認為是已經死掉的葉狀結構。為了不被做雙曲幾何的同學影響,Gabai每天只在晚上來系裏工作,白天都在宿舍睡覺。就這樣,他發展出一套自己獨特的研究葉狀結構的方法,做出了一鳴驚人的工作。他的這種專注力是我望塵莫及的,但我還是努力地在研究過程中儘量向他看齊。
Q:經常可以在網上看到您撰寫的科普類文章,數學史文章,這是您的愛好之一麼?您還是加州理工學院少兒科普組織Caltech CPA STEM的一員,可以講講為小孩子做科普是什麼樣子的麼?
倪憶:我在小學和初中的時候讀過一些數學科普和數學史的書籍,從中受益良多,對數學的興趣就是從那時產生的。所以,我自己有時也會寫一些這方面的文章。大學時是在bbs上寫,現在就是在微信公眾號裏寫,受眾更廣。如今自己對數學的理解當然比大學時更深刻了,再看大學時寫的一些東西就會覺得很幼稚,貽笑大方。
Caltech CPA STEM是加州理工學院部分有小孩的教職員工自發組織的活動,輪流給同年齡段的小孩講課。疫情前每週一次,疫情後至今還沒有恢復活動。我當初講的時候,面對的是幼兒園的小朋友。聽眾知識結構比較單純,連加減法都沒有學過。所以只要給他們講一些圖形的知識,再佈置一些任務讓他們自己動手去做。這樣的講座相對來説比較容易準備。如果聽眾的知識背景複雜,會更難講一些。
Q:授課、科研、科普寫作,看起來您的生活節奏也非常快,您是如何平衡的呢?
倪憶:對我來説,取捨比較容易。我的主業是授課與科研,當然優先要把這些做好。有時我在科研上沒有什麼進展,並且因為疫情宅家比較無聊,寫寫科普文章也算是一種調劑。有時科研上的想法比較多,有很多問題可以做,就自然會把科普的事情放一放。
Q:您如何看待華人數學家的發展?
倪憶:最近十幾年來,湧現出來了很多非常優秀的青年華人數學家,遍佈數學的各個分支。其中雖然還沒有出現像陳省身先生和丘成桐先生這樣的大師,但青年華人數學家作為一個整體在國際數學界業已產生了非常大的影響。
現在這個時代就是中國數學的黃金時代。希望華人數學家大會作為華人數學界最有影響的交流平台,能夠團結最廣大的華人學者,在華人數學史上寫下新的篇章。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微信公眾號“清華大學丘成桐數學科學中心”。
特 別 提 示
1. 進入『返樸』微信公眾號底部菜單“精品專欄“,可查閲不同主題系列科普文章。
2. 『返樸』提供按月檢索文章功能。關注公眾號,回覆四位數組成的年份+月份,如“1903”,可獲取2019年3月的文章索引,以此類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