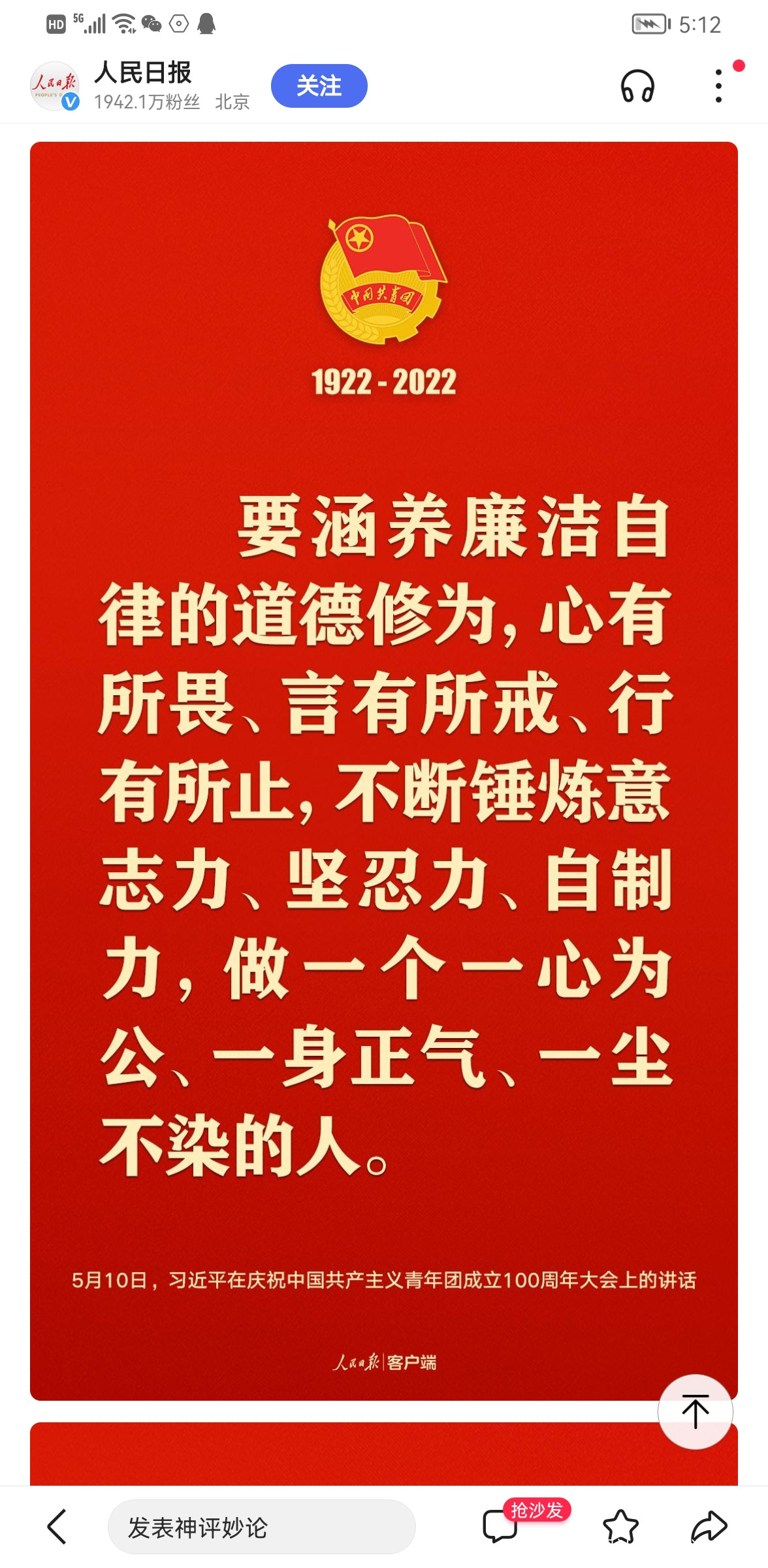我們必須作出的抉擇——也談司馬南事件_風聞
驱逐舰051-人民主体的历史和政治哲学。2022-08-24 21:37
一
看到司馬南承認在美國買房投資的微博,我很鄙視那些以此大做文章説他“反美是工作,赴美是生活”的人,也完全相信司馬南老師不但是愛國的,而且堅持着社會主義的方向和勞動人民的立場。
然而,正因為這樣相信,我又不由得再一次感到:
很多人、很多事,總比我們想像得或我們願意相信的要複雜得多。
司馬南只是在美購房,並沒有移民,但熱愛祖國、熱愛社會主義而又移民出國、移民出國而又熱愛祖國、熱愛社會主義的人,我卻是認識一些的。
曾有人攻擊蘇聯作家肖洛霍夫的《靜靜的頓河》一書塑造了一個內戰期間在紅白兩軍間不斷搖擺的格里高力作為主人公,作家回答:
“我們都知道,那時候,不是一個、不是幾個,也不是幾百個格里高力曾經動搖過。”
我還在報紙上讀過紅八軍團軍團長、八路軍115師參謀長周昆的情況。他從秋收起義直到參予指揮平型關大戰,表現一直堅定勇敢。然而,1938年3月,他到臨汾領到國民黨發給八路軍的6萬元軍費,卻拿走其中的3萬元潛逃,從此再無蹤跡。
劇作家黃紀蘇認為:這個世界上有一種野心勃勃、生氣勃勃的人,對自己認為有意思的事,就會激情澎湃、熱火朝天地一干到底。革命年代,他們幹革命義無反顧死不旋踵;市場經濟時代,他們追求金錢同樣如醉如狂毫無顧忌。
司馬南、移民的愛國者、格里高力、周昆,以及黃紀蘇談到的這種曹操式的以個人意志把正面反面都做到極致的人,當然是不同類型甚至截然相反的人物,但隱然又有着草蛇灰線般的聯繫。
方誌敏同志曾經寫道:
“清貧、潔白、樸素的生活,正是我們革命者能夠戰勝許多困難的地方。”
毛主席在談到共產黨人應該永葆革命本色而不講究物質享受時説:
“沒有條件講究的時候不講究,這一條好做到。經濟發展了,有條件講究仍然約束自己不講究,這一條難做到。共產黨就是要做難做的事。”
他還將那些做不到這一點的人比喻成屈服於不拿槍的敵人的人,在糖衣炮彈面前打敗仗的人。
這些説法,有人曾將其類比於王陽明的“第一等事是要做聖賢”、“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自然也是有道理的,但我認為毛主席這樣的表述有着更為深刻明確的內涵:
1.階級指向更明確:王陽明的“山中賊”是指農民起義軍,“心中賊”卻是指他這樣的封建衞道士個人自己的貪慾對封建綱常的違背等等,二者並不一致——並不是農民起義軍這個“山中賊”導致你心中有“賊”的。而毛主席所説的“拿槍的敵人”、“不拿槍的敵人”與“糖衣炮彈”之間,則有着直接的聯繫:都是剝削階級以及剝削階級的思想觀念、生活方式對我們的影響,那些“糖衣炮彈”確實是剝削階級向着我們打過來的。
正因為這樣,也就有了第二層:
2.教育效果更動人:王陽明只説了個難易對比,而並未也不可能説出破兩個“賊”的內在聯繫,而毛主席揭示了這個聯繫(當然毛主席的階級立場、敵我判斷與王陽明的截然相反),那麼他就更有理由對他的教育對象提出要求:
同樣一個敵人還沒有被徹底打倒消滅,過去在有硝煙的戰場上,如果屈服於拿着槍武裝到牙齒的他們,是可恥的,今天如果在沒有硝煙的戰場上屈服於已經沒有真槍實彈而是射出糖衣炮彈的他們,不是更無能、更可恥嗎?而且在糖彈面前吃敗仗,會讓我們過去在有硝煙的戰場上打的勝仗變得毫無意義,甚至變成失敗的前奏。因此你要當英雄,要保持過去的英雄榮譽,就要和這個敵人繼續戰鬥下去,從勝利走向勝利,直到這個世界上再也不存在剝削,也不存在產生剝削的任何土壤。
毛主席的這個政治修辭是耐人尋味的。
他總是讓他的戰友們不要忘記戰爭年代的很多經驗和傳統;他喜歡用戰爭和軍事術語來分析與形容和平年代的各項工作。
有人認為這只是他留戀過去的軍事共產主義生活;
有人甚至認為這是為了故意製造敵人,製造緊張空氣,加強個人權威,限制個人自由,反對獨立思考。
而我認為,真正的原因在於毛主席深深懂得他的很多戰友更接近柏拉圖筆下的“武士”型的人物:
他們對敵鬥爭很英勇,重視榮譽,對國家也很忠誠,但對革命事業的理性認識不夠,不能像“哲學王(就這個詞的正面意義説)”那樣深刻把握住人類前途命運的本質,在“工作更偉大更艱苦”的和平年代,容易失去方向乃至“死於安樂”。
那麼對這樣一羣人,必須讓他們至少要感到(如果一時還不能理解到)現在的工作仍然是對敵鬥爭的繼續,仍然是他們要打的“仗”,我們仍然是在以另一種戰略戰術在和那些狡猾了十倍而且喬裝改扮了的敵人較量,這才能激發他們的捍衞榮譽的動力,讓他們感到這樣的仗打不好,自己就和自己過去所鄙視的膽小鬼、逃兵、降敵的叛徒沒有區別,就是自己抹黑乃至毀滅自己英勇無敵的形象。
換言之,毛主席是在用軍人自己的經驗、軍人最容易接受的語言,來增進這些戎馬半生的戰友對“不忘初心、永遠奮鬥、改造到老、革命到底”的認同感,先激發他們本有的榮譽感和戰鬥欲,再讓他們在實踐中去思考和昇華。
“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我們每個具體的人總是複雜的、有差異的:軍人有軍人的情況,司馬南有司馬南的情況。
但我們不得不對自己提出高標準、嚴要求。
建國初期,有的將軍向毛主席抱怨:
“資本家吃飯五個碗,我們部隊吃飯只有酸菜。這個太苦了,要改善。”
毛主席回答:
“這是好事。你資本家五個碗,我解放軍吃酸菜。這個酸菜裏頭就出政治,就出模範,解放軍得人心就在這個酸菜上。”
大家一定要懂得,毛主席這話不是説部隊生活不要改善——相反,毛主席非常關心戰士們的生活,哪怕在最艱苦的戰爭年代他也是想盡辦法讓戰士吃飽穿暖,逢年過節還想着讓戰士們吃點兒好的,打打牙祭——而是高度警惕和強烈反對那位將軍流露出的一種思想苗頭:
“我們部隊要跟資本家比生活水平,像資本家那樣過日子,才舒服、才體面,不然就是遭罪,就是沒面子……”
這些話還説不上是什麼腐敗,但在毛主席看來,讓我們的指戰員不去管勞動人民過的什麼日子,而是盯着資本家比吃比穿,這就是思想上沾了灰塵,這就是在敵人的糖衣炮彈面前要打敗仗的先兆。
目前狀況比建國初期複雜得多,各種誘惑也多得多,所以我們每個人學習和實踐馬克思主義,都要問自己:
這個主義現在就是要求我們即使有條件,也不能去做一些很多人可以放心大膽去做,做了之後還有很多人眼紅心熱豔羨不已的事情,那麼我願意付出這個代價嗎?
如果不願意,我們就容易在糖彈面前吃敗仗——你的知名度越高,這個敗仗的影響力也就越大。
我認為司馬南是個很優秀的馬克思主義宣傳戰士,戰鬥力強於很多研究馬克思主義的教授,尤其是那些專門到《資本論》裏尋章摘句為資本塗脂抹粉的“著名馬克思主義學者”,與司馬南同志更是相去不可以道里記。
有缺點的戰士終究是戰士,但缺點還是需要戰士們防微杜漸,因為它不但關乎個人修養的完善,往往也關係到正在進行的戰鬥(比如對國資流失問題的追究)的順利進行。
而戰士沒有別的選擇,只能去做難做到的事情。
二
上文在我空間發表後,有位網友評論説:
“根據個人較長時間間斷性觀察,認為司馬南算不得有缺點馬主義戰士,更像公園老大爺和民粹(截圖無法發出)。”
我將文章轉到朋友圈後,一位同樣屬於馬克思主義陣營的網友還對司馬南作出了更嚴厲的批判。
自己的文字能引來大家這樣嚴肅認真的回應,真是何幸如之。也正因如此,我感覺有必要進一步闡述一下我對有關問題的看法,以供探討,這才對得起大家的賜教。
這位同學説的 “公園老大爺和民粹”,因為“截圖無法發出”,我不知道究竟是指什麼,只知道這類詞經常被我在今天講蘇州和服事件的説説中提到的那些“精英”們用來指稱那些對祖國尤其對毛主席有着強烈摯愛的普通羣眾。這些羣眾大多學歷不太高(微博上有人嘲笑道“司馬南的支持者學歷不超過初中”)、不太會説話,無財無勢,無刀無筆,有的年紀還比較大,而“精英”們就抓住這些,對他們極盡嘲弄羞辱之能事。然而,這些羣眾正是社會主義事業所要依賴的基本力量。誠然,我們不難從“公園老大爺和民粹”身上找到各種各樣的缺點(這些缺點,大半都與三四十年來的歷史原因造成的人民羣眾中的思想混亂有關),可是如果我們因為他們受到以“上層”、“精英”自居的人的嘲笑,就想與這些“土”、“憨”、“窮”的人劃清界線,也學着去高高在上地“內涵”他們,那除了説明我們自己不知不覺中在向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繳械投降並且當上了幫閒幫兇,還能有什麼別的解釋呢?
任何進步的事業,包括社會主義的事業,是由現實的社會人而不是宗教裏才存在的那類聖徒在推動的。某微信羣裏曾有一位學者説現在要警惕“極左”分子詆譭改革開放,我回應説:
“我擁護並高度評價改革開放,還因此被一些紅色網友當作修正主義罵過。但我完全理解他們。我知道這些人真心擁護黨和社會主義,他們完全理解社會主義需要自我完善,需要改革,也完全承認改革開放以來的巨大成就。但是,有很多經歷讓他們在一定程度上對我們的一些具體改革措施是否堅持了社會主義方向產生了疑慮。他們看到並且指出了很多影響到他們作為普通勞動人民的切身利益和社會地位的問題,這些問題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完全可以解決但一直沒有很好地解決,因此我們不能説他們的這些疑慮沒有一點根據。與其要求這些羣眾想問題、談看法都像領導、專家一樣滴水不漏,恰到好處,不如認真思考一下怎樣回應他們的關切,更好地解決他們所提出的問題。鄧小平同志早就説過,對有這些疑慮的人,我們只能拿成百上千的事實來回復他們,讓他們看到改革開放確實姓社不姓資。另外,極“左”如果有,也是被極右逼出來的。在極右甚囂塵上,詆譭毛主席和其他革命先輩、英雄烈士,説得好像新中國還不如舊中國的時候,有些人在其位不謀其政,採取妥協退讓乃至姑息縱容的態度,而奮起反擊來捍衞黨和國家的反倒是這些無職無權的基層羣眾,所以他們當然會有想法,會反感、鄙視那些失察失責的人,會追問一個為什麼,甚至可能產生一種擴大化的激憤情緒。我們越是要把改革開放搞好,就越是要正視和關注這些意見。所以如果您真的擁護社會主義的改革開放,真的是為國家和人民利益考慮,那麼在批評您口中的極“左”之前,您要想想他們為什麼會這樣,最好也要自問一下在極右猖獗的時候,您又在做什麼。”
司馬南的節目,我的很多長輩都很愛看,認為自己的很多感受和想法都被他表達出來了。
而在我印象較深的一期裏,司馬南提到:
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國企改制職工下崗的大潮中,他在東北某市參加了一個飯局。席間那些暴發户們眉飛色舞地談論着某某大橋下如今成了那些為了生計被迫從事某種“職業”的下崗女工們招攬“生意”的地方,而那些姿色可人的女工昔日是如何有頭有臉,今天又是如何“風情萬種”……
司馬南當時大概礙於情面沒有多説什麼,但在那一期視頻上,他説他聽到這些是很不好受的,因為他感覺那些被蹂躪被編排的女工就像他的親人一樣,都是曾經那樣有尊嚴的意氣風發的勞動者,理應是這個社會的主人,實在不該受到這樣的羞辱與褻瀆。
2010年,司馬南在一篇文章中説:
“ 還記得嗎?當年幾千萬國企職工,上級開完動員會,每人拿幾萬塊錢(有的根本沒錢)抹着眼淚就回了家。現在回頭看,為國分憂,犧牲自己,成全改革的善念義舉,固然都是工人階級有覺悟、顧大局、聽話的標誌,但是,事情本身並沒有那麼簡單,後來,有人藉着改制大肆侵吞國有財產,有人急藉機渾水摸魚兼併重組,頃刻之間當上了百萬億萬富翁,而回到家的工人羣眾,很多人淪為城市低保一族,當了“光榮的弱勢羣體”,每逢年過節,就有社會各個方面的關懷送上門來。工人階級的主體地位,莫名,成了別人施捨的對象。這件事,過去很多年了,我沒搞清楚為什麼。”
現在從時間看,這正是他在美國買房的那一年。
可是,知道了他在美國買房,絲毫沒有影響我對司馬南所説的認同。
其一,我想,他在美國買房,了不起就是想賺錢吧,那又怎樣呢?我認識的不少心向馬列的朋友,特別是年輕人,都很想賺錢,賺大錢,很想盡早實現“財務自由”,因為在這個社會里,有了錢能幹的事情,或者至少有了錢你就有底氣不幹的事情,都比沒有錢的時候要多得多。可是在這個社會里,除非你有華為那樣的核心技術,或者像李子柒那樣天賦異稟,否則你用來“賺大錢”的那些手段,恐怕都難免會帶有金融資本主義的那種投機性乃至虛偽性,因為當代資本獵取利潤的操作邏輯就是這樣,能讓你那麼容易“站着把錢掙了”,它就不叫資本主義了,不然為什麼連李子柒那樣心靈手巧萬人喜愛幾乎毫無瑕疵的“網紅”都只好停更了呢?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在那天的説説裏要提醒他們不忘初心,防微杜漸,千萬不要為物所累——這是很難的,但必須做到,否則就會受挫折、打敗仗。但不管怎麼説,我決不是要大家都將“阿堵物”當作禁忌絕口不提,更不是説敵人攻擊我們做某事,我們就該視為畏途,縮手縮腳。
其二,更重要的是,我就是國企工人的子弟,司馬南説的那些事情,與我家長輩以及他們同事對我説起的,還有我自己耳聞目睹的,非常吻合。他的視頻下面常有自稱工人的網友點贊,感謝他替自己説出了心裏話,我想也是同樣的原因。而那些攻擊司馬南的人,除了拿“美國購房”、“收割流量”、“司馬粉月入不過三千,學歷不過初中”等説事以外,沒有一句話來直面司馬南談到的這些問題本身,沒有一條證據説他究竟哪兒講得不對。
其三,司馬南所説的這些不但沒有削弱反而大大增強了我對改革開放的信心。像他這樣的聲音能夠發出來並在廣闊的社會範圍內引起反響和探討,説明今天我們的黨和政府有自信和勇氣直面改革開放過程中出現的問題,而不是像某些人所慣常做的,一看到今天的問題,就把責任推給“文革”,推給前30年,推給毛主席,或者簡單歸咎於“西方影響”、“中國人素質差”。這種自信和勇氣,當然使我們更有理由相信偉大的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會朝着更健康、更有利於絕大多數人的方向發展。
我們還應該看到,被某些人稱為“民粹”的這種思想和聲音由一個或一羣司馬南這樣的人發出來,這有一定的偶然性;但這樣的思想和聲音一定會有人發出來,一定會強有力地迴響在21世紀的中國與世界,則是歷史的必然。這背後的邏輯,是進行了20世紀最偉大的社會革命的中國人民,在這個革命要在新的形勢下走向深入的時候,會有一個艱難痛苦的自我反思與批判的過程,這難免被敵人利用來渙散人心,製造混亂,以致於讓人民心中的主旋律一時間似乎被淹沒無聞,但現在它以一種哪怕不夠成熟完美的形式發了出來,標誌着它已經開始了聲勢浩大的再出發。
這個再出發當然也是開啓了一個探索和鬥爭的過程,幾乎每一件事都不是無可非議的,因為人民一定要在鬥爭中學會鬥爭,在千錘百煉中清除雜質。但我們和九十多年前寫作《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的毛主席一樣,首先面臨着一個判斷它“好得很”還是“糟得很”的根本抉擇。
我們必須作出這個抉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