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異化—馴服德先生_風聞
博文说史-重庆人文科技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2022-09-13 12:33
民主作為一種政體,已有2500年的歷史,在過去的2300年裏,整個西方知識精英視其為洪水猛獸。直到近100年,“民主”才被視作好東西。那麼一向被視作壞東西的民主是怎樣變成了一種值得稱頌的制度呢?被不少人奉為圭臬的代議制民主,是不是真的民主呢?要解決這個問題我們首先要追本溯源去看看民主的源頭。

一、古希臘民主的真相
民主起源於古希臘。民主一詞由兩個字組合而成,一個是demos,意思是公民,一個是cracy意思是統治,合起來就是公民的統治,準確地説,是由全體人民平等的、無差別地參與國家決策與管理,這是民主最原始的含義。
我們以最著名的雅典民主為例,去考察希臘人是如何實踐民主的。首先,要明確的是,無論過去還是現代,只有公民才是能夠行使民主權利的人,而公民從來不是簡單的數人頭,不是每一個自然人都是公民。在公元前6世紀到公元前4世紀的雅典,公民必須是年滿20歲,且父母雙方均為雅典人的男子。成年婦女、奴隸、外邦人皆不是公民,沒有任何權利。根據西方歷史學者的研究,雅典公民人數大致在3-6萬人之間,同時期雅典的總人口約在30-50萬之間,雅典公民只佔雅典人口的十分之一,可見雅典民主,也不是人人平等,一人一票。雅典民主之所以被人稱道,是因為其制度設計,充分保證了公民的政治權利。
雅典的政治體制,主要有三個機構;一是公民大會,是雅典的最高權力機關,與後來的議會不同,雅典公民大會並不存在選舉,而是由全體公民參加。為了保障國家大小事務(戰爭、條約、外交、財政、法律等)都是經過民主決策產生,雅典每年至少召開40次公民大會,每次間隔不超過10天,每次的會期長達5個小時,使每個與會公民儘可能充分地表達自己的意見。
公民大會休會期間,由每個部落採用抽籤的方式抽出50人,參加500人議事會(雅典有十個地域部落)。議事會內部進一步以部落為單位設置十組五十人團,每組在一年十分之一的時間裏,輪流執掌雅典政務,在當政期間再由抽籤選出一人擔任主席,其職責是全日待命以應付突發事件。在直接民主下,整個雅典所有行政、司法職務,除了十將軍等少數需要專門才能的官員,由公民大會選舉產生且能連任外,其他所有官員均通過抽籤的方式產生。與今天的選舉不同,抽籤不偏袒佔有資源優勢的人,是完全隨機的,每個人被選上的機會是均等的。

如果將雅典民主與代議制民主進行對比,就會發現今天代議制民主中的很多東西都是雅典民主中不存在的。第一,沒有選舉產生的政府,而是採用抽籤的方式,使得任何公民參與國家管理的機會是均等的。第二,雅典沒有代議制機構,而是實行公民直接參與,第三,雅典沒有政黨。從上面的介紹,我們看到,雖然,雅典民主具有很大的侷限性。但雅典公民做主的權利確實得到了充分保障。
作為一種制度,民主在希臘城邦時代結束之後就中斷了,至於羅馬共和國,則完全不是民主制度。羅馬共和國的正式名稱是“羅馬元老院和人民”,主要由元老院、執政官、民眾會議三層機構組成。元老院在整個政治組織中,處於核心地位,其成員由前執政官、貴族、大地主組成,制定政策和法律,監管國庫,可否決公民大會決議。羅馬的國家首腦為執政官常設兩人,任期一年,十年內不得連任,且無報酬,實際等於直接剝奪了貧苦百姓當選的資格。19世紀德國歷史學家奧多爾·戴森認為羅馬共和國開始是貴族制,後來變成了寡頭制。事實上,在過去100多年裏,大部分歐美學者都對羅馬共和國是民主政體的説法嗤之以鼻。

二、“民主”是個壞東西
今天世界上幾乎所有的政權都自稱是民主國家,這裏暗含着一個前提,民主是一種好制度。但在19世紀以前人們卻不這樣看。古希臘學者認為大眾是無知的,容易受人蠱惑、擺佈,最容易被別有用心的人利用,而政府治理是一種精妙的藝術與技能,一旦讓多數人蔘與影響決策,就會變成集體暴君。蘇格拉底表示修辭只會對無知的人產生作用,有可能讓他們改變主義,而對於那些真正的賢人,根本起不來什麼作用。他説“民眾沒有任何關於善的知識”,因此他拒絕“附和民主原則和民眾主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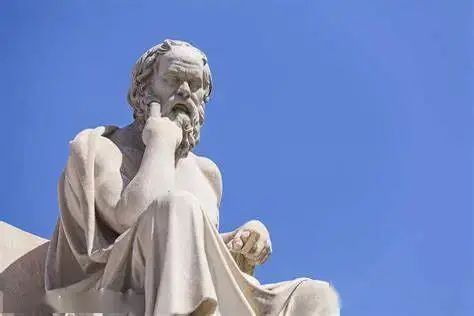
柏拉圖認為,一個理想社會應當由三種人組成;監護者、輔佐者、被統治者。其中監護者必須接受良好的教育,是最聰明,最有智慧的人。輔佐者掌握國家暴力機器,被統治者只需做好生產工作就可以了。為了證明他理論的合理性,他還説“在這個社會里,你們都是兄弟。但造物主創造你們的時候,他在那些有資格成為監護者中的人加入了金,在有資格成為輔佐者的人中加入了銀,而在農民和其他勞動者中加入了銅和鐵”。因此,柏拉圖認為民主是一種“無政府狀態的花哨的管理形式”。因為民主不允許分工。沒有分工,就沒有專業化,其後果是政治變成一種毫無效率的東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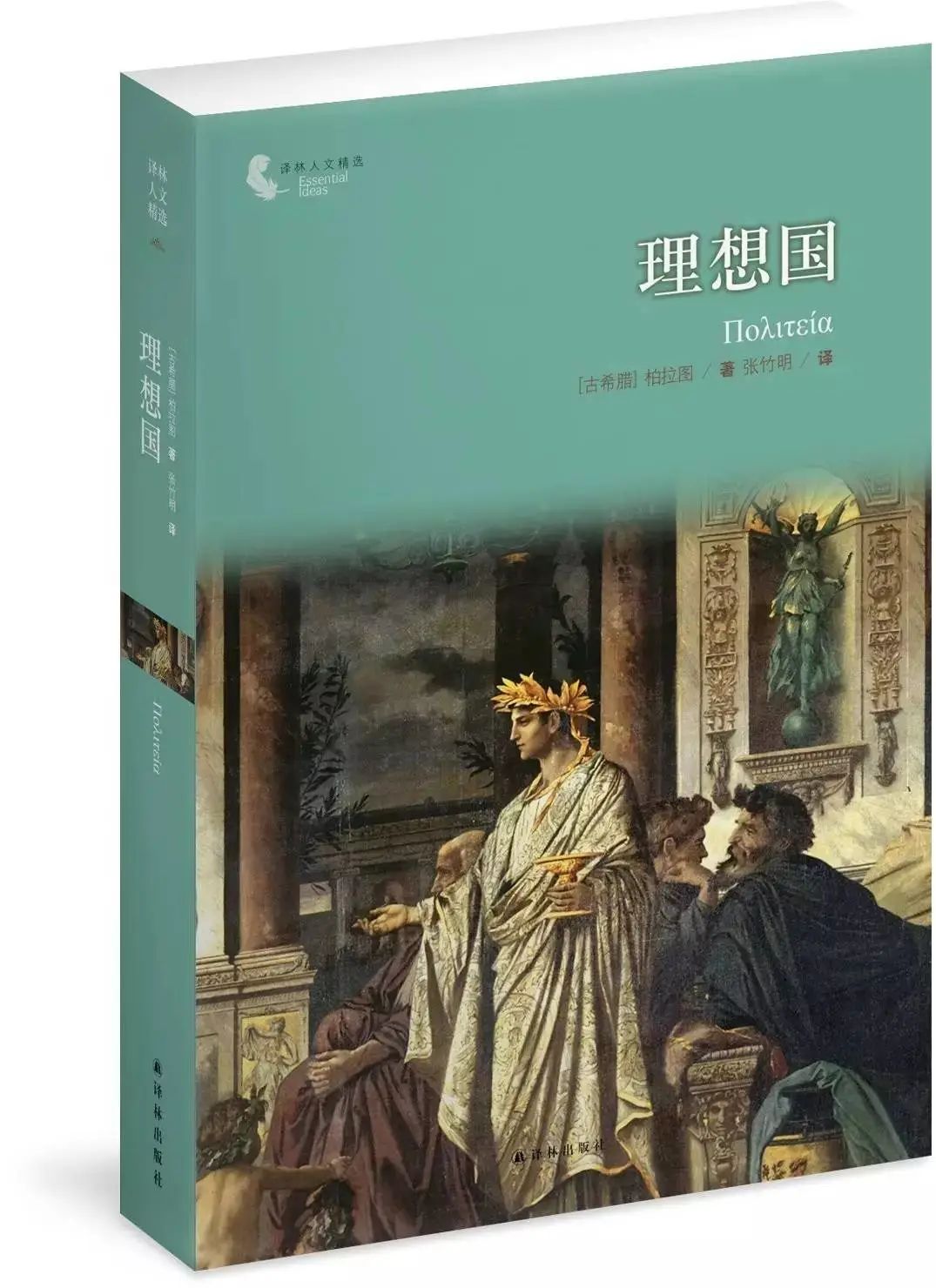
亞里士多德在他的《政治學》中這樣寫道“農民是最好的公民,因為沒有太多的財產,所以他們總是忙於生產,極少參加公民大會。同樣也由於他們缺少生活的必需品而不得不整天在田間勞作,他們也不貪圖別人的東西,他們在勞動中獲得更多的滿足,只要從參與政治生活中得不到更多的好處,他們就對參與公共事務和統治國家沒什麼興趣。他們中的大多數都只想賺錢而不是為了名和譽”言下之意很清楚,不參與政治的公民是好公民。
希臘城邦滅亡後,古代羅馬學者依舊對希臘的“民主”制度口誅筆伐,西塞羅認為,把地位不等的人置於同等的位置上,這種“平等實際上是最大的不平等”。人民是渾渾噩噩的,民主給他們過多的自由,必然會使他們變得盲目、任性、放縱、蔑視法律、不服從任何統治者。在他的心中理想的政體是“君主對臣民的父愛,貴族議政的智慧和人民對自由的渴望”於一體的混合政體。
西羅馬帝國滅亡以後,無所不在的上帝,代替了羅馬的法律、行政制度、官僚體系,古代希臘羅馬的人本主義蕩然無存。即使有人偶爾提起民主,其評價也是十分負面的。托馬斯·阿奎那説“不義的政治可以由許多人行使,那就叫做民主政治,當平民利用他們人數上的優勢來壓迫富人時,這種政治就是暴民統治。在這樣的情況下,整個下等社會就變成一種暴君。”換言之在阿奎那看來民主等於暴政。

冷戰結束以後,民主與自由經常一同提及,於是我們形成了這樣一個思維定式,從中世紀末期開始的文藝復興起到啓蒙運動,就是歐洲有識之士追求自由與民主的過程,然而這是我們的錯覺。從文藝復興到啓蒙運動,歐洲的思想家們確實在不斷推進人的解放和自由,但對於絕大多數思想家來説,民主等同於多數人的暴政。
西方現代政治學的奠基人,文藝復興時期的馬基亞弗利在《論李維》中表示“他既不信任權力不受約束的君主,也不信任行為不受約束的“人民”。在他看來,雅典的民主政體與波斯的君主政體都比不上羅馬共和政體。國家要長治久安,必須在君主、貴族、人民三種要素之間維持平衡,人民的所作所為必須受到君主貴族的引導和制約。
洛克十分重視個人自由和權利,但對民主並不感興趣。他在日記中寫道“由於大多數人沉迷於激情與迷信,人類的未來不能由多數人掌握,只能由開明者掌握”。孟德斯鳩認為“民主政體下,平等精神會走向極端。由此產生的一窩窩小暴君們與單一暴君一樣可怕。而且,很快自由就會消失,單一暴君就會出現,人民就會喪失一切。”所以他真正青睞的是當時英國有節制的,寬和的,君主政體,只不過需要立憲對君主權力進行制約。

伏爾泰主張人人自由,平等,不過他所理解的平等是有前提條件的。“每一個人在內心深處都有權認為自己與其他的人完全平等;但是並不能由此便説,一個紅衣主教的廚子應當命令他的主人給他做飯”。至於民主政體“只適用於非常小的國家,即便如此,它也會不斷出錯,因為它是由人構成的。相互傾軋在所難免,就好比女修道院來了一羣男教士”。至於狄德羅,他不僅憎恨專制君主與愚昧的教士,而且十分鄙視人民。“你們要當心民眾在推理和哲學方面的判斷,民眾的聲音在此時是惡意、愚蠢、無情、不理智和偏見的聲音……民眾是愚昧與遲鈍的。”
實際上在整個啓蒙時期,只有盧梭是個例外,他在《社會契約論》中提出了人民主權理論,要求將立法權還給人民,主張直接民主,但對於民主的前途他不抱希望,因為“多數人統治而少數人被統治,那是違反自然秩序的。”康德也認為,民主制度是不合理的,因為“它不是建立在從事物的永恆秩序中生發出來的理智和正義之上,而是多數人隨性而為的結果。”
實際上,整個十九世紀,除了馬克思主義者,整個西方政治學,幾乎沒有什麼人支持民主。法國政治思想史學者埃米爾·法蓋(1874-1916)對此十分感慨“幾乎所有19世紀的思想家都不是民主派。當我寫《十九世紀的政治思想家》一書時,這令我十分沮喪。我找不到一個民主派,儘管我很想找到這麼一位,以便能介紹他所闡述的民主學説”。
三、美國建國是民主神話?

長久以來,不少人把美國建國曆史描繪成了一幅民主的神話,殊不知,美國的建國先驅們嚴格踐行了歐洲大陸主流政治思想,他們制定憲法的目的就在於防範民主。
獨立戰爭剛結束時,美國發生了謝司起義,這直接引起了美國的精英階層的恐慌,他們把“所有的動盪都算在了民主的賬上,迫不及待地以法律和正義的名義熄滅民主之火”。在這個背景下1787年的制憲會議,變成了保守主義的聚會。隨便翻翻《美國制憲會議記錄》就會發現,這次會議是漢密爾頓、麥迪遜、莫里斯、梅森、格里、倫道夫等所謂美國“國父”對民主的聲討會。他們提到“民主”時,總是把這個詞與“動盪、愚蠢、過分、危險、罪惡、暴政”連在一起。最後通過39人簽署,2000人投票,美國建國先驅們把羅馬共和制度複製到了美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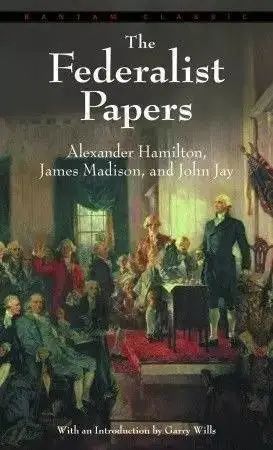
第四任總統麥迪遜直截了當地説“政府若採取民主的形式,與生俱來的就是麻煩和不方便,人民之所以譴責民主,原因就在這裏。”在今天的人看來“民主”與“共和”似乎是同義詞,但實際上二者有天壤之別,民主是人民參與治理國家,或者主權在民,而共和則是禁止最高權力的世襲制度。美國國父們所鍾愛的制度,正是西塞羅、馬基雅弗利、孟德斯鳩都主張的羅馬式的共和制度。是君主(以總統為代表)、貴族(參議院)和人民(眾議院)三者之間的平衡。這個構想理論的基礎是制止一個人、少數人、多數人壟斷行政、司法權力,所以這套制度既防範獨裁者也防範民主。
總之,美國國父們接受的是啓蒙時代的主流思想,對於民主是反感的,他們是不願意建立一個由眾議院(民意)主導的政體,而是希望用各種制度設計來削弱眾議院的權力。首先分割立法權,對此華盛頓有很形象的描述“我們將(來自眾議院)法案導入參議院的碟子裏冷一冷。”這是因為眾議院的議員是由民眾選舉產生,為了避免民眾對國家政策的影響,要讓參議院去制約民眾。事實上,在美國成立後的頭126年,參議院都不是民眾選舉出來的,而是各州的立法機構遴選出來的。目的在於“建立一個由具有社會地位、財富高貴人士組成的國會第二議院,與英國的上議院越相似越好”—約翰·迪金森。
其次,賦予總統“帝王般的權力”,國父們認為“舍此,不能保衞美國免遭外國的進攻;舍此,亦不能保證穩定地執行法律;不能保障財產以抵制聯合起來破壞正常司法的巧取與豪奪;不能保障自由以抵禦野心家、幫派、無政府狀態的暗箭與明搶”。這表明美國總統最重要的責任有三點:一是保衞國家安全,二是防止民眾侵犯有產者利益,三是防止出現獨裁者。
第三是建立具有貴族色彩,完全不受民意影響的最高法院“宣佈違反憲法明文規定的立法為無效之權”。至於這樣做的目的,麥迪遜説得很露骨“完全排除以整體身份存在的人民,以免它染指政府事務”。
四、馴化民主
由此可見,從古希臘到十九世紀上半葉,西方社會上層精英一直把民主看作洪水猛獸。洛克、伏爾泰、孟德斯鳩、康德這些我們耳熟能詳的賢者們,都不把民主看作是好東西。因為他們擔心,一旦允許大眾參與政治,窮人勢必會利用手中的權力要求剝奪富人的財產。為了保衞自己的財產不受侵犯,有產者竭盡全力阻止民主的出現。但是歷史的發展,不以少數精英的意志為轉移。
19世紀三十到四十年代,英國出現了以爭取男性普選權為主要訴求的憲章運動。1848-1849年間,法國、德意志、奧地利、意大利、匈牙利相繼爆發民眾廣泛參與的革命,雖然這些運動都以失敗告終,但他們大大震動了歐洲的精英階層,這使得一些人意識到民主潮流無法阻擋。

托克維爾發出這樣的感嘆“到處都在促進民主”,在他去世那一年(1859),穆勒判斷人民對於民主權力的訴求“並不是思想家們鼓吹的結果,而是由於幾大股社會羣體已變得勢不可擋”。於是,不少意識到民主潮流不可阻擋的西方社會精英,轉變思路,用在民主前面加入各種漂亮的修飾詞來閹割民主、馴化民主。今天,我們所看到的自由民主、憲政民主、代議民主、程序民主的説法都不是自然形成的語言,而是資產階級學者們刻意加上去的,每一個詞都是對民主的馴化。

1、通過“自由”和“憲政”限制民主權威的適用範圍
前文説過“自由”與“民主”是兩個不相關的概念,而且在很長的時間裏是相互對立的。古典自由主義者在反抗君權,神權和封建貴族體制方面的確不遺餘力,但他們的目的是為了爭取新興資產階級參與政治的權利,而不是真正的、普遍的政治參與。因此在資產階級革命席捲歐陸的很長時間內,選舉都是有產階級的特權。
18世紀中期,全英國700萬成年人中,僅有15萬人享有選舉權,佔成年人口的2.1%,1831年,英國有選舉權的人也只佔成年人的4.4%。法國大革命後《1791憲法》以財產和年齡將人民劃分為“積極公民”和“消極公民”前者的要求是年滿25歲以上的男性且繳税,婦女、家僕、無家可歸者、教士、不納税者為消極公民。如此全法2600萬人只有440萬人享有投票權,1795年法國修憲,提高投票權的門檻,選民數量下降到10萬人左右。早期資本主義國家之所以將選舉權縮小到如此狹窄的範圍之內,目的就在於阻止羣眾利用國家機器損害有產者的利益。
19世紀中期以後,伴隨着國際工運高超的到來,為了保衞自己的利益,他們決定必須給公共權力規定一個明確和固定的界限,不得越過雷池半步。同時劃分出一個不受政治權威干預的私人領域,強調個人權力的不可侵犯,用自由來規範民主,來限制民主的權威。其辦法是通過憲法來對國家權力進行限制,使得即使普通民眾擁有選舉權也無法損害有產階級的利益。可以説憲政是制服民主烈馬的繮繩,它用憲法的形式禁止公權力干涉個人權力,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財產權。亞當·斯密反覆強調,政府的主要任務是保衞富人,對抗窮人。因此,必須對私有產權進行整體上的保護,包括在憲法中特別列舉私人產權,在它周圍豎起一道警戒線,不允許任何人染指。
也許有人會説,憲政民主雖然限制了國家的權力範圍,但同時也阻止了社會力量對公民權益的侵犯。然而,事實是,資產階級在組織國家公權力染指自己經濟利益的同時,卻通過對司法的解讀與操作,讓國家機器為自己服務。如美國憲法第五條修正案規定“禁止在不給予合理補償的情況下,將私有財產充作公用”但現在美國法院對“公用”的解釋已經變得十分寬泛,連強行拆除一片社區,交由通用汽車公司使用也可算作“公用”了。可見,在自由和憲政的前提下,個人權力並不存在不可逾越的界限,只需要你有足夠的財富影響政府決策,所以“憲政民主”只能是“憲政財主”,保障自由也只能保障有產階級的財富自由。

2、通過“代議”和“選舉”偷換了民主的概念
今天,代議制,議會幾乎成了西式民主的標配。那麼議會、代議制真的是為民主設計出來的嗎?答案是代議制、議會都是中世紀的遺留物。“代表”和“議會”的概念大概有兩個來源一個是教會、一個是國王,教會選派代表主要是為了參加跨地區的宗教大會。至於議會,則是起源於君主或貴族為決定税收、戰爭、王位繼承等問題,召集的臨時會議,在會議中不同階層的代表不發生交集。實際上是國王和貴族的協商和諮詢機構。所以,議會設計的初衷並非為了代表人民,而是中世紀教皇、君主、貴族為維護統治而做出的發明。那麼,既然議會是中世紀的產物,我們實行直接民主是否可行呢?
從邏輯上講,直接民主必須要滿足五個條件,才能實現。第一個條件是公民的利益相差不大,這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是不存在的;第二個條件是公民在種族、語言、宗教等方面也要具有高度同質性,因此也無法在移民國家和多民族國家實現;第三個條件是公民總數不能太大,有的理論家認為六萬人是極限,這就基本否定了直接民主在現代社會的可行性;第四個條件是所有公民具有決定法律政策,表達自己利益、意願、偏好的能力,否則會被詭辯者牽着鼻子跑;第五個是政體必須是獨立自主的,必須在政治、經濟、軍事上獨立於外部勢力干涉,否則民眾無法自己做主,因此,無法在經濟、軍事的半殖民地實行。
可見,實現直接民主不現實,所以在民主的輸入端(民眾參與管理國家)今日是無法與古希臘相比的,所以現代民主更應看重輸出端(政府對於民眾訴求的回應)。然而,西方只是精英卻繼續在輸入端大做文章,將代議制和競爭性選舉與民主等同起來,徹底偷換民主的概念,並最終馴化了“民主”。

最早將代議制與民主聯繫在一起的是漢密爾頓,他在1777年首次使用了“代議民主”這個詞。麥迪遜認為,代議制民主是解決民眾多數暴政的利器,因為它通過一個從公民中挑選出來的機構,對公眾的看法加以提煉和補充,以這些人的智慧,使他們能最清楚地瞭解真正的國家利益之所在,他們的愛國心和正義感也使他們不大可能出於短期和狹隘的考慮而犧牲國家利益。在這種制度安排下,經過人民代表的表述,公眾的聲音會比由他們自己直接表達更符合公共利益。
在大西洋彼岸功利主義思想家邊沁認為代議制是“從目標和效果上能夠使最大多數人得到最大幸福的唯一政治形勢”。約翰·穆勒被認為是19世紀代議制民主的集大成者,他認為“一個政府的理想類型一定是代議制政府”。這是因為,控制政府和管理政府有極大的差別,政府的正當性通過民眾選舉的代表來實現。不過穆勒所認為的民眾,與我們所理解的似乎不是一個概念,他建議實行這樣一種選舉制度:越聰明的人,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應該分到更多的選票。因此,時至今日,我們在觀察西方選舉制度時,依然能夠見到通過設置各種門檻,巧妙的剝奪底層羣眾選舉權的現象。

比如,美國個別洲要求選民通過文化測驗才能投票。這些題目有多難呢?我們可以列舉一下:A什麼機構有權彈劾美國總統?B如果一個人被控叛國罪,但嫌疑人本人否認控罪,需要幾個證人檢控他,才能判他有罪?C請説出現任美國總檢察長的名字?試問沒有受過高等教育的美國藍領階層有幾個人能回答正確呢?此外,美國大多數州要求選民在選舉日的30天以前登記,錯過登記,或者表格填寫錯誤,則不準投票。結果是窮人文化水平有限往往登記表格出現錯誤,又因為登記日是工作時間,窮人不願請假扣工資錯過登記等等。這一切使得美國民眾參與選舉的比例在西方社會中非常之低。
很明顯與抽籤不同,由於代議制與選舉密不可分,而影響選舉結果的因素舉不勝舉,選舉制度的設計、選區的劃分、選舉人的資源(暴力、金錢、知名度、相貌、口才、演技)、競選策略(輿論控制、抹黑對手、造謠、苦肉計、離間計)等等。所以,選舉制度天然傾向於富人、名人、從而將窮人徹底排斥出政治決策層,將人民大眾的作用(通過選舉制度予以限制)侷限於幾年一次的選舉,從而使代議制民主帶上“貴族”、“寡頭”的色彩。
實際上,對於代議制的真相,早有人有了清醒的認識,比如無政府主義者蒲魯東就斷言代議制根本不是民主,19世紀末20時年代初意大利經濟學家帕累託、思想家馬斯卡、米歇爾提出了“寡頭統治的鐵律”認為民主也罷,專制也罷最終都是寡頭統治,政治最終不可避免的要有極少數的社會精英分子來操弄,人民當家作主是不可能的。但這種過於接近真相的認識顯然不利於資本主義的統治,資產階級需要的是將通過代議制和選舉馴化的、閹割的“民主”神聖化、教條化,成為大眾欣然接受的東西,如此統治才能穩固。最終,約瑟夫·熊彼特完成了這一過程,在其1942年出版的《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民主》一書中,熊彼特批判了“古典民主觀”並毫不諱言地聲稱“民主不是,也不能意味着任何明顯意義的‘人民的統治’,民主僅僅意味着人民有機會接受或拒絕將統治他們的人,但由於人民也可以用完全不民主的方式來決定誰做領導人,我們必須再加上另一個標準收窄我們對民主的定義,即候選人自由競爭人民的選票”。
這就徹底顛覆了民主的原意,民主不再是人民的統治,也不是政府要回應人民的訴求,而是意味着人民有機會去選擇統治他們的人,人民變成了選民,民主變成了選主,至於這個過程完成之後,人民在政治生活中變得無足輕重。在過去幾十年裏,經過熊彼特改造的民主定義被西方主流以及受西方主流影響的知識精英奉為圭臬,有沒有競爭性的選舉成為評判政體是否民主的唯一標準,至於人民是否能夠當家作主,政府是否回應了民眾訴求、被選舉者是否增進了社會公平正義,縮小了不平等,都無足輕重。
結論
綜上所述,今天西方社會所大聲呼喊的自由、憲政、代議制、選舉跟民主的本質沒有絲毫的關係。形象地説無論是古希臘的直接民主,還是科學社會主義所提倡的經濟和政治的雙重民主,對於資本主義社會來説都是一匹未經馴化的烈馬,於是他們用各種工具閹割、禁錮這匹烈馬,並將其包裝得十分精緻,變為資產階級所期望的那樣,成為其意識形態的工具和供權貴把玩的寵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