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地人不生了,長三角的最大隱憂_風聞
秦朔朋友圈-秦朔朋友圈官方账号-2022-09-20 08:07

· 這是第4714篇原創首發文章 字數 4k+ ·
· 土哥涅夫 | 文·
我大學剛畢業時,陰差陽錯回了老家的報社。別看只是一家地市級報紙,我們那批招的人中間,除了我一個本科生,其餘都是碩士。事後得知,我之所以被“特殊對待”,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我是本地人。
後來的事情發展,也驗證了領導的判斷。從見習期開始,就陸續有人或跳槽到省裏的媒體,或選擇考公考博。等到幾年後我離開時,我們同一批進來的人,七七八八已經走得差不多了,而且一多半去了外地。
可見,哪怕是地處長三角核心區的城市,真正能長久留住的,還是本地人。
這點從任澤平團隊最新的一份報告中,也得到了側面印證。他們發現,自2010年以來,隨着沿海地區產業轉型升級、中西部地區產業承接以及老一代農民工老化,人口呈現向中西部迴流的態勢。
特別是四川、重慶和湖北三地,常住人口分別從2000~2010年的年均減少19萬、17萬、23萬,變為2010~2020年的增長33萬、32萬、5萬,實現了歷史性地由負轉正。
與之相反,東部的人口增速則開始減緩。
外地人不來了,或者説來得少了,本地人口的數量、出生率和增長情況,便顯得愈發重要。也正因如此,當我看到最近浙江省統計局發佈的《人口“浙”十年》系列文章中,有關本地人口的數據,才會感到脊背一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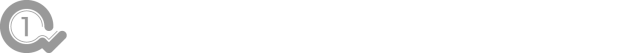
説起人口表現,浙江在全國各省市中,不説最優秀吧,那起碼也是“之一”。
過去十年,浙江人口增長了1014.07萬,增量僅次於廣東(2170.93萬人),高居全國第二。全省常住人口達到6456.76萬,一舉超過安徽和湖北,排名從全國第10位上升至第8位。
同時,跟廣東人口增長主要集中在珠三角,粵東的潮州、梅州、揭陽、汕尾、河源,及粵西的湛江等很多城市,均呈現人口淨流出的情況不同,浙江是沿海省份中唯一一個所有地市都實現人口正增長的省份。
即使放眼全國,有此佳績的省份也才浙江、貴州和西藏這區區3個。所不同的是,後兩者主要依靠本地人的高生育率,而浙江則仰賴外來人口源源不斷地輸入。
至於浙江本地人口的情況,就不容樂觀了。根據《人口“浙”十年》文章分析,至少存在如勞動年齡人口和育齡婦女比重下降、老齡化程度加深、生育水平處於超低區域等一系列的問題。
2020年,浙江全省15~49歲的育齡婦女人數為1553.22萬,佔全部女性人口的50.29%。這個比例較2010年時(60.44%)大幅降低了10.15個百分點。其中,20~29歲生育旺盛期年齡的婦女人數為387.96萬,佔全部女性人口的12.56%,比2010年時下降了4.84個百分點。
育齡婦女比例持續減少的同時,生育意願的下降,無疑更令人擔憂。
過去30年,浙江人口的總和生育率由1990年的1.40降到2010年的1.01,此後雖經單獨二孩、全面二孩、鼓勵三孩等政策的輪番刺激,也只小幅回升至2020年的1.04。不僅遠低於2.1的代際更替水平,甚至連1.5的國際警戒線都難望項背。
所謂總和生育率,是指平均每對夫婦生育的子女數。經常和它一起被提及的,還有另外兩個概念:生育率和人口出生率。
生育率,指的是某地在一定時期內 (通常為一年)出生活嬰數與同期平均育齡婦女(15~49歲)人數之比。
而人口出生率,是指在一個時期之內(通常為一年),出生人數與平均人口數之比。這裏説的“平均人口數”,是年初、年底人口的平均數,也可以用年中人口數代替。
跟總和生育率不同,生育率和人口出生率通常用千分數來表示。
在浙江,總和生育率最高的衢州(1.37),也僅剛剛超過全國平均線(1.3)。剩下的10座城市,集體不及格。
省會杭州的總和生育率,更是已跌至0.96,也就是每對杭州夫婦只生育不到1個孩子。這個數值快接近韓國了,而後者可是被稱為“或將成為世界上首個消失國家”的恐怖存在啊。
伴隨生育率的下降,浙江的人口出生率也比2010年時下降了3.14個千分點,降至2020年的7.13‰。與此同時,全省老齡化程度的不斷加劇,使得死亡率從5.54‰上升到5.84‰。這一降一升,浙江的人口自然增長率從六普時的4.73‰,被直接打到了只剩1.29‰。
受此影響,浙江户籍人口占常住人口的比例,從2010年時的87.23%,下降到了2020年的78.5%。這些户籍人口中間,還包括很多過去十年落户浙江的外來人口,真正“本地人”的比例恐怕更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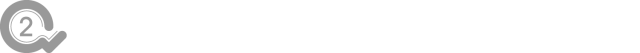
**事實上,這些問題並非浙江特有,同處長三角的江蘇、上海,情況更為嚴峻。**畢竟浙江好歹還有温州等宗族勢力強大、歷來抗拒計生的地區,而江蘇有的則是“比全國提前二十年進入老齡化”的計生紅旗縣如東。至於上海,人口總量停滯了都快有十年了。
體現到具體指標上,上海的總和生育率已經跌到0.74,比韓國還低。江蘇在這項指標上雖然與浙江齊平,都是1.04,但其人口出生率卻只有6.66‰。
儘管得益於長三角的地利優勢,過去十年,江浙滬常住人口增量少則上百萬,多則上千萬,但本地人不生了這點,還是在經濟、文化等方面,帶來了許多不容忽視的負面衝擊。
對此,可能有人要説了,你這是杞人憂天。粗魯一點的可能直接破口就罵了:你這是典型的地方本位主義,在搞地域歧視。發展經濟,有人、有勞動力就行了,哪裏還分什麼本地人外地人?
況且歷史地看,自打泰伯奔吳開始,江南一直是片南下北人和本地土著共存、互動的移民社會。永嘉、靖康年間的幾次大規模南渡,不僅沒有衝擊本地經濟,反而大大促進了江南的開發,助力其最終成為全國的經濟中心。
這話當然沒錯,但是要知道,隨着中國人口增長由正轉負,各地對於人口的爭奪重點,已經從增量轉入存量階段。長三角雖然吸引力巨大,但架不住人口迴流川渝鄂的趨勢,搶人難度越來越大。這點在上海、江蘇體現得尤其明顯。
過去五年,上海人口增長時正時負,總量才多了不到30萬。而江蘇的幾個頭部城市,南京、蘇州和無錫,人口年均增量也都在10萬以內,很多年份甚至不到5萬,只有成都、西安、鄭州等中西部核心城市的一個零頭。
而蘇中、蘇北的一些城市,人口直接負增長了。就連GDP破萬億、全國排名前20的南通,也存在户籍人口大於常住人口,也就是説人口外流的情況。
為什麼江蘇GDP始終追趕不上廣東,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廣東本地人“能生”,人口後勁足。2021年,廣東自然增長率高達4.52%,僅次於貴州(4.98%)、寧夏(5.53%)、西藏(8.7%),高居全國第四。而江浙滬分別為-1.1%、1%、-0.92%。
不要小瞧這幾個點的差距。
如果説,經濟數據是對過去發展的總結,它影響着今天的人口,那麼人口數據則關乎未來的經濟發展。特別是在全球貿易摩擦、產業外遷的大背景下,本地勞動力往往發揮着經濟穩定器的作用。這方面,珠三角確實略勝長三角一籌。
而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一方面是由於江南的宗族傳統,沒有閩粵那麼根深蒂固。特別像上海,計劃經濟時代人人都是體制內的職工,這也導致上海和東北一樣,計生政策執行得特別到位。
**另一方面,跟廣東人“早茶、夜宵、會生活”不同,江浙人被公認是“移動的賺錢機器”。**行走在浙江的城市,晚上十點一過,大街上就冷冷清清沒啥人氣了。要説這兒的人有什麼愛好,除了賺錢,就是買房。搞得浙江市縣的房價,比中西部很多省會都高,從而也將樓市的“避孕”作用發揮到了極值。
不過,相比對經濟的影響,本地人不生了,對江南文化的負面衝擊無疑更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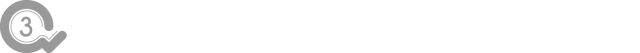
很多年前,上海就流傳過一句話:內環説英語,中環説國語,外環才講上海話。
這個説法可能有些誇張,但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本地人的日漸邊緣化,以及隨之而來的,吳語在江南的整體性式微。
這可不是我危言聳聽。根據對各地6~20歲青少年方言使用情況的統計,吳語區年輕人能夠熟練使用家鄉話的比例,是各大方言區裏最低的。其中,“外環才講本地話”的上海,已經是比例最高的城市了,達到22.4%。而上海話的兩大源頭,蘇州話和寧波話,在各自城市青少年中的掌握比例,分別已低至2.2%和4.6%,近乎消亡。
這和我們的日常感受是一致的。
從90後開始,能夠講一口流利家鄉方言的江南小囡,人數微乎其微了。受此影響,普通話已經取代吳語,成了長三角的通用語。人們見面後,通常會先用普通話交流,直到發現彼此是老鄉,才改説方言。這跟珠三角的情況正好反過來。
在廣東,粵語仍是主流用語,只有當交談對象聽不懂時,才會改講普通話。這是因為,廣州6~20歲青少年中,能熟練使用粵語的比例高達72%。
作為中國經濟的兩大火車頭,長珠三角本土方言的命運為何會如此天差地別?要知道,經濟、文化的興衰,常常是相伴而生的。大家看國外,無論是好萊塢的風靡,還是韓流的盛行,本質都是國家經濟硬實力的外化。
而在國內,晚晴民國時期的上海,不僅經濟上傲視東亞,本埠文化也是相當強勢,湧現了像《海上花列傳》等一批吳語小説,滑稽戲等吳語戲曲。1949年後,隨着大批上海豪商鉅富南遷香港,上海話一度成為香港上流圈子的通用語,這點從《花樣年華》等電影中都有體現。
六七十年代,隨着香港經濟的崛起,粵語文化進入興盛期。到80年代改革開放後,粵語音樂、電影大量輸入內地,一度成為流行文化的代名詞,很多其他方言區的人們都爭相模仿、學習粵語。
而現在,長三角論經濟已恢復到歷史高位,可以吳語為代表和根基的江南文化卻面臨危機。
這其中,既有吳語自身的原因,比如不像粵語那樣有廣府話作為標準發音,吳語是十里不同音,內部不同小片間交流都存在障礙,所以很容易在強勢普通話的衝擊下式微。但更關鍵的還在於本地人口的生育率過低,導致人口相對比例不斷下降,吳語的使用環境遭到破壞。
不要覺得語言就是個交流的工具,換一種使用也無妨。須知,語言的背後是文化,每一種方言的消亡必然伴隨相應地域文化的衰落。事實上,類似情況在江南歷史上曾不止一次發生過,最著名的莫過於古越文化的消失。
今天的江南有很多迥異於中原、難以用漢語解釋的地名,比如姑蘇、句容、餘姚、諸暨、上虞……它們都是先秦古越語稱呼的漢化遺存,可惜除了“餘”指的是鹽外,其他絕大多數字詞是什麼意思,我們已經搞不清楚了。唯一保留下來的一首越地詩歌《越人歌》,還是用古楚語翻譯記錄的,想想真是遺憾。
如果説古越語和越族文化的消亡,是文明幼年期族羣戰爭的不幸結果,那麼現在,吳語及其所代表的江南文化,在和平環境下的不斷式微,則是必須也完全可以避免的。相比經濟的一時起落,地域文化的存續,以及由此確保語言、文化的多樣性,無疑更加茲事體大。
在這個意義上,江南人不生了,並不只是個人口問題。希望這一長三角當前的最大隱憂,能引起全社會,而不僅僅是地方政府的共同關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