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知識分子,到底應該幹什麼?_風聞
新潮沉思录-新潮沉思录官方账号-2022-09-21 23:05
文 | acel rovsion
在前段時間玄奘寺供戰犯牌位的事件中,學者戴錦華幾年前的一個講座視頻在網絡上流傳開來,大意是説她在與日本和歐美左翼學者的交流過程中,這些學者普遍拒絕正視南京大屠殺的歷史性質,因為在他們的眼中,南京大屠殺和猶太人大屠殺是不可以相提並論的,因為猶太人大屠殺是一種“現代性悲劇”,是德國法西斯用現代化和技術化的手段來實現的,代表了現代性和工具理性中藴含的精神危機,需要深刻反思,而南京大屠殺就像古代慣常的戰爭屠殺,沒什麼值得討論的地方。(工具理性概念源於馬克思韋伯,簡單來説指追求通過工具和手段達致功效最大化,後成為以法蘭克福學派為代表的對現代性的批判理論中主要批判對象之一)

在我們看來,這當然充滿了一種西方中心式的傲慢和輕視。從現代史上來看,對於現代性是什麼,因技術進步和工具理性等等帶來的現代性精神危機該如何解決等問題的探討,始終貫穿着以歐陸哲學為代表的西方知識分子的話語體系構建中,又由於西方人文學術界在20世紀的絕對主導地位,他們的話語體系構建實際上又給所有後發國家定義了一整體套關於現代化與現代性的先驗概念,並深刻影響了以西方人文學科體系為導向的後發國家中知識分子的思維傾向,比如我國的知識分子,也由此導致我們的很多知識分子,在靠攏西方的過程中最終走向我們的反面。
我們必須先對西方知識分子中關於現代性與現代性危機的一些代表性看法有個概括性的認識,然後才能探討這種認識是不是能普適於所有後發國家,以及後發國家的知識分子們到底應該做什麼。
如同前面所説,整個二十世紀歐洲知識分子的精神危機核心來説是——我們歷史如何走到當下,而當下的現代性危機又來自於何種緣由。由於德國一直是歐陸哲學的源頭之地,且德國最終走向法西斯化,德國知識分子的爭論經歷着從戰前到戰後的深刻歷史轉折後,面臨着“什麼是德意志”以及“德意志可以是什麼”,這種從歷史意識延展到當代的共同敍事重新建構的新問題。德國的問題,就等同於了什麼是現代性與現代性危機從哪來的問題。
因此,各路歐洲知識分子就德國就提出了自己的質疑與想法。雅斯貝爾斯和鮑曼強調了工具理性與現代性社會機器的共謀,鮑曼側重於分析工具理性,“科學意識”和現代性機器對大屠殺的流程化甚至機制化(代表作《現代性與大屠殺》)。雅斯貝爾斯側重批判工具理性和現代性危機對歐洲自啓蒙時代以來歷史理性的敗壞,工具理性的過盛導致歷史理性的嚴重不足,形成了“反理性”,歐洲就此走入了一種荒誕的過分建構。這些人着眼於歐洲尤其是德國精神領域理性破碎的世界,以及對未來世界性哲學的想象。(雅斯貝爾斯,德國存在主義哲學家。齊格蒙特·鮑曼,英國社會學家)(未來世界性哲學,從黑格爾歷史哲學觀中衍伸出來的一種終極哲學想像,關於世界的最終社會形態的想像,如福山的歷史終結論)
而桑巴特和梅尼克恰恰相反,他們試圖去探討一種普遍理性和歷史意識的“誤用”。他們認為德國發展到第三帝國形態,是由於德國社會以歷史理性去思考的德意志民族國家未來,對改變魏瑪共和國命運的強烈需求,導致倒置和誤用了原本黑格爾歷史哲學的辯證模式——彷彿德國人的內在需求需要一個先知和一個宗教,一個終末之後的未來圖景,來包圍歌德時代到此的德意志文明遺產。在他們看來,德國精神危機和雅斯貝爾斯認為的理性不足恰恰相反,而是理性過度帶來的一種狂熱。(桑巴特,德國社會學家。弗里德里希·梅尼克,德國歷史學家)
洛維特等人卻去着眼於所謂歐洲虛無主義導致的現代性危機。特別是洛維特從尼采揭露了虛無主義的核心是對基督教價值的徒勞信仰,更核心的是對傳統歐洲歷史闡釋學的徒勞信仰。這種徒勞信仰面對新世紀的價值缺失和價值倒塌的無力,所以虛無主義意味着,歐洲人喪失了共在(Mitsein)感,或者説舊歐洲堅持的所謂世界性哲學圖景就此倒塌。(卡爾·洛維特,德國哲學家)
當然經濟學人和社會學人可能就更願意落腳於社會結構分析上來。德魯克把歐洲精神危機尤其是德國法西斯主義的本源歸因到二十世紀經濟危機對早期資本主義信仰的衝擊和懷疑。歐洲人經歷了早期資本主義對資本增殖的無監管、所謂自由企業利潤導向的交換關係,經濟增長導向的社會驅力,以及市場正義的道德神話構成的總體社會建構。而週期性經濟危機給了歐洲人當頭一棒,這使得歐洲特別是德國人的精神信仰產生了空缺,而二十世紀的新神學理論並不能填充這個空白,這使得對於社會一種機械理性的總體圖景,變成了歐洲人對早期資本主義的一種反叛。(彼得·德魯克,美國人,現代管理學之父)
而米哈伊·瓦伊達就乾脆直接歸因到小資產階級的羣眾運動特性上去,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驅使着他們與強力集團看似“反抗”的妥協和結盟;小資產階級的盲目性導致他們認同於一種脱離現實的超然主導力來解決現實的問題,讓渡自己的政治行動力;小資產階級的妥協性導致他們相當部分趨向於一種無意義的温和改革,並極度恐懼德國工人階級的革命思想,形成了一種自我以上“追求平等”,自我以下“秩序萬歲”的人間喜劇。體現為軟弱式互害、自欺式自利以及冷血式鄉愿。(米哈伊·瓦伊達,匈牙利布達佩斯學派代表人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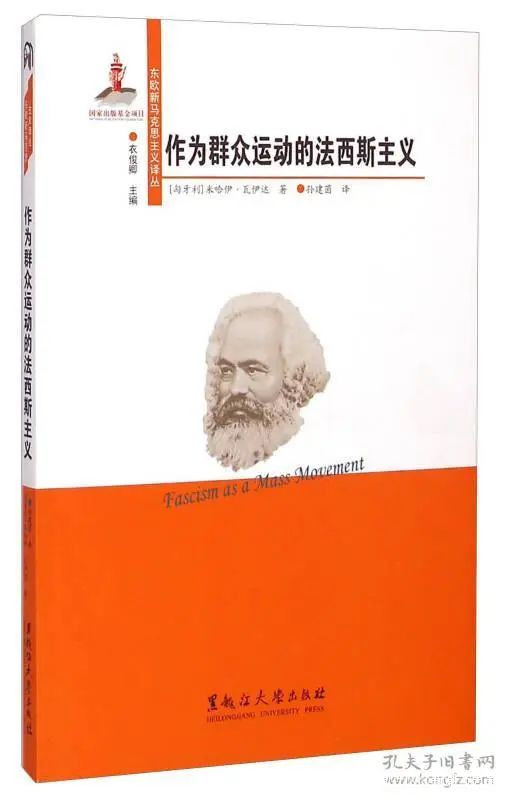
對於歐洲這些知識分子的總總思考,列維納斯有過一個概括,他將這些思考活動稱為一種歐洲精神的唯心主義——當然我個人可能更願意把它叫做現代性的”逃避主義“——以一種普遍性的靈感試圖去超過實存的現實性,引誘我們前往一種虛假的寧靜,而這之中又不可避免地包含一種悲劇性地絕望。
但是這其中也有崇尚新世紀樂觀的人,布魯門貝格提出了一種進步主義的“線性歷史觀”,把現代人的歷史語境看作一種關乎集體自我肯定和積極建構的社會進程,這種自我創造在歷史進程中不斷地重構和再造,始終前瞻性去引發了歷史進步的可能性條件。當然,這實際上是在歐洲人的立場上把基督教倫理迴歸到了意志的發展,把歷史哲學理解成按單一線性規律可以走向未來,而把歷史中的偶然危機看作一種歷史發展過程的不斷試錯,但錯誤本身並不能去質疑時代的正當性。(漢斯·布魯門貝格,德國哲學家)
所以整個德國轉型期間的思想政治本質就成了西方知識分子們基於歷史語境對於時代性的一個理解,以及對他們所處時代的歷史感的建構。如同“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和“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
但無論如何,通過我們剛才的總結可以發現,西方知識分子們關於現代性與現代危機的一切討論,本質上是建立在歐洲社會和學術歷史之上的,如啓蒙時代的理性主義,從康德到黑格爾的哲學傳統,基督信仰危機,早期資本主義史等等,這套人文學術體系無疑是基於歐洲的情況發展而來,但在西方主導整個現代化的過程中,反而成了所有致力於融入西方體系的後發國家知識分子必須靠攏的標準,最終使得後發國家相當多的知識分子變成了西方體系的附庸和傳聲統。
這就涉及到知識分子這一角色的功能問題。知識分子到底應該起到什麼作用?
**知識分子可以作為知識分子(功能)存在,但不能作為知識分子階級存在,**這使得知識分子本身應該在文藝、人文思想領域應該去盡一些責任。因為人文價值或者文藝印象在當下的語境中往往是被先賦或者給予的,當然其媒介可能是傳統的再造,文化工業的生產以及消費媒介的書寫,這形成了關於價值體系、人類行為原則、以及對當下世界的基本理解等方面的總體取向。
我們在歷史感生成的實踐過程中,通過構想過去的某種定義和限定,來導向對於當下和未來的解釋並賦予意義,而這種實踐互動歷經學術探討、文藝創作和集體儀式之後形成了制約當下實際生活的原則和動機,並形成闡釋過去和指導未來的框架,而這同時包含了反思和建構兩方面的工作。
目前是有一些學者在真正的進行反思與建構的工作的。比如我們之前文章介紹過的華人學者趙月枝,是由斯邁思一派開啓的政治經濟傳播學在當下的代表性學者。她批判了來自於歐美對於現代性社會的一種線性歷史觀理解。這種線性歷史觀伴隨着歐美數百年文化擴張中生產出一種對內對外的世界基礎理解,與文化帝國主義話語同構,把資本主義的固有發展階段和內化的文明等級觀摹寫給後發國家的思想話語生產中,並建立在後發國家的文化精英與新生“全球化”階級的文化在生產之中。

使得所謂的線性歷史觀構成的“現代化”話語變成一種實質性的依附話語,號召放棄文化身份和經濟自主去加入所謂世界性分工體系和世界性的價值規範,並通過媒介產品、消費文化輸出和價值規範等傳播策略構成了一個無處不在的跨文化網絡,彷彿成為了一種關於當下的世界性歷史意識。
洛維特也批判過這種線性歷史觀的問題,他結合海德格爾的論述,認為美國所謂現代世界的歷史形態(給世界輸出進步、民主和社會平等的擴張性價值規範)所包含的支柱——個人主義、自由主義、憲政與公共輿論並不能帶來所謂的“普遍歷史進步”,**也並非當下世界的唯一解釋。**這種反思本身需要對抗的是一種不容易發現的歷史虛無主義——即完全無視本國的歷史語境去移置、雜糅並替代一種既有的歷史意識成品。
可惜,斯邁思一派的政治經濟傳播學,在我國高校傳媒學科系統中並非主流,這點在沉思錄之前的文章中也説到過,不得不説是我國人文學科狀況的一個側面反映。
從建構工作來説,張旭東等學者重温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這篇講話的精神很大程度確立了文藝和思想路徑的歷史主義立場、羣眾取向和現實主義基調,探討的核心就是“文藝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關係”。
而張旭東等人提出了兩種理解,一個是“革命機器”,即文藝工作要求以政治實踐和政治站位作為第一性,服務於政治本體論的總體性要求,作為文藝鐵軍奮鬥在文藝戰線,從而釐清革命的文藝工作者在政治空間內部的功能、角色與定位。把創作和社會運動和總體政治發展相結合,把視角和人民羣眾相結合。這樣的文藝才是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歷史實踐的觀念性體現。
第二個是“普遍的啓蒙”,從羣眾的視角去談普及與提高,不僅是服務普及羣眾符合人民路線的文藝,還要深入學習羣眾的思想和需求,提煉總結並沿着無產階級前進的方向去提高,先做羣眾的學生,再做羣眾的先生,並最終羣眾結合在一起,成為羣眾主體創造力的一部分,真實反映和思考現實問題,最終實現解放的目標。
當然關於文藝理論的建構,只是我們亟需的思想建構的一小部分。客觀來説,當下知識分子羣體似乎也做了一些工作,**人文思想領域主要體現為兩大塊,包含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以及現代思想的本土性起源,**比如哲學領域丁耘做了《道體學引論》,陳來也做了《仁學本體論》,以“生生”為線索,丁耘把“虛”“一”統一的道體作為中國本土形而上學的本體論探討,而陳來用仁體作為本體來設立世界存在、生產和運動的內在根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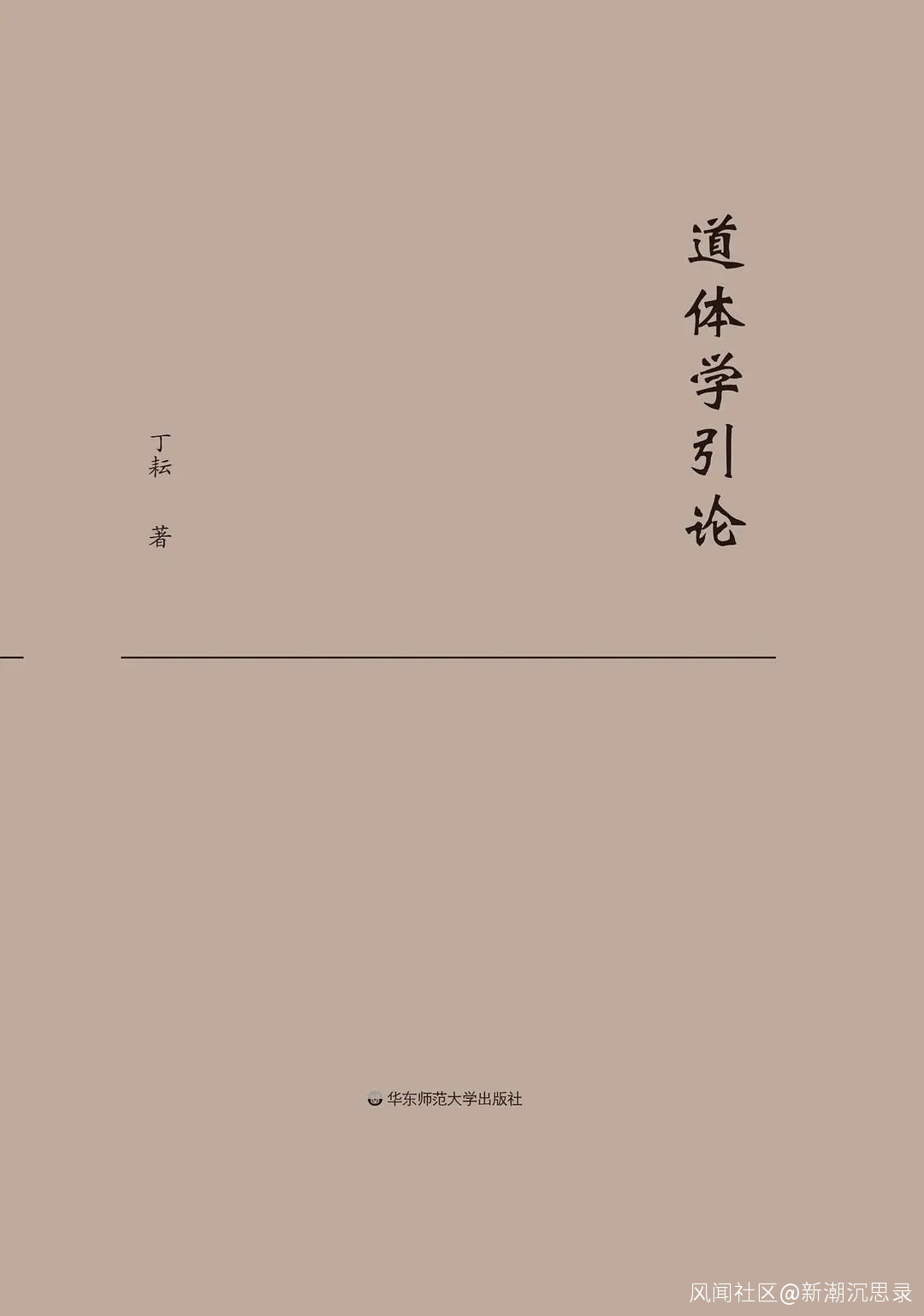
**但是整體來説,在建構中國話語、歷史意識、文化主體,以及新主體性位置的進程中,**中文知識分子們是否普遍性發揮了積極的反思和建構作用,參照我們文章的論述和當下的現實,我想大家自己都有評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