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隱入塵煙》現象中,尋找意識形態批評的邊界_風聞
新潮沉思录-新潮沉思录官方账号-2022-09-30 21:39
文 | 思蘆
電影《隱入塵煙》本來早在7月就登錄各大影院,但由於文藝片一貫慘淡的排片量而反響平平,直到後來才因在抖音等平台的口碑發酵而意外票房攀升、成功“出圈”。
儘管同時發酵的還有導演在宣傳中的一些爭議性言論,這些言論和片中略顯工具化、刻板化的女性形象共同體現出了導演性別觀的侷限。但整體上《隱入塵煙》在呈現農業勞動和農村邊緣人時的嚴肅與用心仍是多數觀眾能感受到的,它讓我們在大銀幕上久違地看見了那些不曾被看見的人,開始瞭解和關注貧困人羣的生存現狀,就社會意義而言,在當下電影市場中也稱得上難能可貴。

然而即使不談及戲外爭議,針對影片內容自身的批評仍然不絕於耳,就在最近還傳出了其在網絡平台遭遇全面下架的消息,正和紅極一時又旋即引發全網批判的b站視頻《回村三天,二舅治好了我的精神內耗》所受到的非議如出一轍,總結起來大概有以下兩個觀點:
誇大了農村的窮或農村人的壞,是通過醜化農村來醜化中國、迎合外國。
美化了苦難的意義,宣揚主人公的逆來順受,是一種麻痹大眾的洗腦術。
而作品支持者的觀點則與之正好相反:
是寫實而不是醜化,經典名著和他國獲獎影片無不旨在暴露現實。
被讚美的不是苦難,而是苦難中的人性光輝。
這是看似簡單的幾條觀點,但其實每種聲音背後所站立的人羣都並不是鐵板一塊,而是錯綜複雜、彼此交織的。
例如認為作品在醜化農村和農村人的,就既有反對國族間刻板印象的民族主義者,也有反對歧視人民大眾的共產主義者;認為作品是美化苦難的,既有基於個人-權力、民間-官方的二元對立語境而反感某種“官方洗腦”的自由派(後來官媒的熱情宣傳正好與此呼應),也有基於階級分析認為這是反映了小資產階級軟弱性的左派;而作品的支持者同樣既有站在他國立場樂見暴露本國弊病的所謂“殖人”“公知”,也有比起其他更優先關注如何為底層發聲的熱心人士,以及大多數單純是被人物故事感動的普通觀眾。

即使看似同一派別的人,關於“美化”還是“醜化”的看法也可能大相徑庭,對待同一作品能產生如此紛繁的評價,不得不説也是一件奇事。
那麼,究竟怎樣是美化?怎樣是醜化?
或者説,怎樣才能既不美化也不醜化,而達到真正的寫實呢?
其實,以上問題都是假問題,永遠不可能得到統一答案。
因為,無論美化還是醜化,都不是針對某種抽象的、絕對的“客觀現實”而言,而是針對不同立場而言的。我們每個人都只能依據自身經驗看到自己眼中的那部分“現實”,而不同身份/處境/立場的人所看到的“現實”本就是大不一樣的。
比如關於《隱入塵煙》中貴英不慎落水時卻沒有一個村民出手相救的情節,有網友説“這太假了,在我們村根本不可能”,也有人説,“這是真的,我們村就這樣死過一個人”。你無法指責誰在撒謊,或誰看到的不是“現實”,更無從比較誰的“現實”更“現實”。

實際上,與其説針鋒相對的人們是在爭辯“何為現實”的答案,不如説是在爭奪關於“何為現實”的定義權。
當我們説“醜化”的時候,其實在説這一事物應該更美。
當我們説“美化”的時候,其實在説這一事物應該更醜。
當我們説“不真實”的時候,其實在説它不是我觀念中應該有的“真實”。
就像一個革命者絕不會忍受電影將他的敵人描繪為“大善人”,因為於他而言這是對那些犧牲的戰友的侮辱與背叛;而一個聲稱崇尚“藝術自由”的人也可能不自覺地視任何革命英雄主義作品為“虛假宣傳”而一律給出差評,因為在他看來沒有這些“愚蠢”的革命者,世界會更美好一些。
魯迅曾將那些為中國譯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先行者稱為盜火的普羅米修斯,而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最重要的觀點之一就是——在階級社會里不存在無階級的藝術。正如蘇聯理論家盧那察爾斯基所説,“在我們還不是勝利者而是戰士的時候,我們將嚴正地並長時間地使階級藝術發展着。”

共產黨人不屑於隱瞞自己的觀點和意圖,關於藝術“功利性”的問題,毛澤東也曾做過一段精彩闡述。
“唯物主義者並不一般地反對功利主義,但是反對封建階級的、資產階級的、小資產階級的功利主義,反對那種口頭上反對功利主義、實際上抱着最自私最短視的功利主義的偽善者。世界上沒有什麼超功利主義,在階級社會里,不是這一階級的功利主義,就是那一階級的功利主義。
我們是無產階級的革命的功利主義者,我們是以佔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廣大羣眾的目前利益和將來利益的統一為出發點的,所以我們是以最廣和最遠為目標的革命的功利主義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狹隘的功利主義者。”
由此可見,真正的問題並不在“什麼樣的藝術表現才更接近(絕對意義上的)現實”,而在“什麼樣的藝術表現才代表了更符合我們階級(百分之九十以上最廣大羣眾)利益的現實”。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左翼的文藝家和理論家們讓文藝的“工具論”“武器論”有了堅實的立論基礎。這並不是説文藝創作就可以像某些抗日神劇、主旋律爛片一樣隨心所欲地篡改現實,或全然不顧生活邏輯、性格發展合理與否,讓作品單純成為革命思想的“傳聲筒”,這恰恰是馬克思所批判的一種違背現實主義藝術規律的“席勒式”創作。
我們所需要的是真實性和傾向性的統一,也即在儘可能尊重現實原型、符合歷史邏輯的基礎上,當故事呈現既有這種可能、又有那種可能的時候,去選擇更具社會意義、更符合階級利益、更能為人民的自由與解放而鬥爭的那一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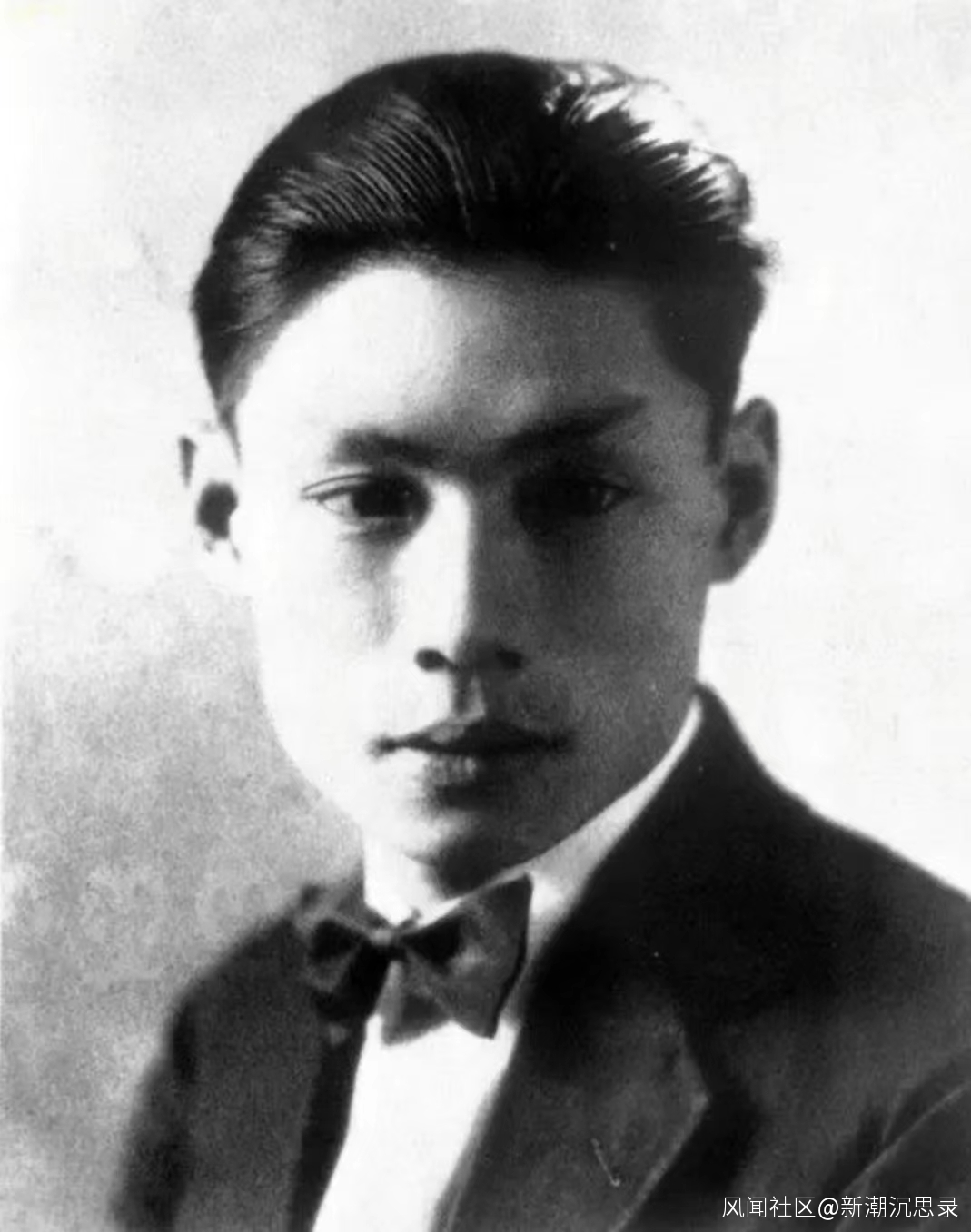
回到上文中提到的兩部作品,儘管圍繞《二舅》的討論以及作者本人的回應大多聚焦於信息“真實度”的問題,關於《隱入塵煙》的爭議同樣圍繞着它是否能代表真實的中國農村和中國農民,但歸根結底,一切質疑的真正出發點仍在於——批評者看來,這樣一種敍事並不符合他所認為的階級利益。
為什麼偏偏糾結於《隱入塵煙》中的農民是否真有那麼窮、那麼慘?因為一旦在社會輿論中以個體真實替代了整體真實,就有可能抹殺掉扶貧工程的成就和基層工作者的辛勞,尤其當作品走上國際舞台、代表中國形象時,還有可能被某些媒體拿來借題發揮,為國際關係中的小動作提供口實,進而影響整體國民利益。
為什麼“二舅的殘疾到底是因打針所致還是由於自身的小兒麻痹症”如此重要?因為給二舅打針的人有一個特殊歷史身份——赤腳醫生,如果在大範圍傳播中讓那些不瞭解歷史的人將故事中個別醫生的過錯歸結為赤腳醫生羣體的過錯,乃至制度的過錯、時代的過錯,那麼將會造成一種對早期社會主義醫療保障制度的極大誤解,而這種制度原本是在當時歷史條件下最符合於廣大工農階級利益、挽救了無數生命的。

以上批評當然有其合理性,現實案例(如《方方日記》)也的確並不少見。但正如另一方所擔心的那樣,如果將這種思維邏輯不加分辨地簡化和極端化為電影中就不能有任何負面形象或任何涉及國家、政府的批評聲音,那顯然也是不符合人民利益的,而不過是藉着愛國、反霸權的名義掩蓋內部矛盾,為上層階級塗脂抹粉。
那麼,判斷的界限到底在哪裏呢?筆者看來,最重要的從來不是藝術作品表現了什麼,而是它為何表現以及如何表現。
那些被大眾所排斥、具有明顯東方主義色彩的作品,最大的問題其實不是他們自己所標榜的“講了真話、暴露了黑暗”,而是他們的暴露並非真正為了給人民尋找(或沒有準確尋找到)社會的癥結與出路。他們不過是以某些獵奇的刻板印象將矛頭指向了所謂的“民族劣根性”或“共產主義原罪論”,如部分第五代電影中那些充斥着偽民俗與性變態的異國情調,部分第六代電影中作為“社會邊緣人”“政治異見者”的隱晦自指,都正與後冷戰時代新自由主義“審判失敗者”的邏輯不謀而合。
可是假如一部作品中沒有出現上述特點,也即作者沒有懷着自我殖民的意識和對共產主義的偏見,那麼他的暴露和批判就極有可能是出於對社會問題的嚴肅思考和對底層人民的真誠關注。我們可以通過這些作品對現實矛盾的揭露來發現問題、解決問題,進而喚醒民眾覺醒、推動社會革新,這正是30年代左翼電影藝術家們所努力探尋的道路,也是《熔爐》《我不是藥神》等電影能被大眾所珍視、推崇的根本原因。

依照上述方法,大家都可做出自己的判斷,而就筆者個人觀感而言,《隱入塵煙》雖然在出現時機和場合上有瓜田李下之嫌,但作品本身並沒有將悲劇歸罪於籠統的“體制”或“時代”,而是將批判鋒芒指向了拖欠農民工資的“吸血者”和那些不顧實際情況、盲目執行政策的官僚蛀蟲,在這一點上其實與某些特供電影是有着本質不同的。反倒是《二舅》提及了赤腳醫生卻沒有為可能造成的誤導稍加註解,則略有刻意之嫌,落入了某些傷痕文學的窠臼。
可是,儘管《隱入塵煙》中關於社會醜惡的種種揭露尚可理解為站在人民立場上對資本主義、官僚主義的批判,但正如許多網友所説,影片中除主角之外的村民形象也一概如此醜惡就多少有點難以服眾了。這就來到了另一個問題,我們的文藝是否應該表現人民羣眾的“醜惡”?
這同樣是一個重點不在表現什麼,而在為何表現、如何表現的問題。固然人民羣眾也有缺點,乃至人性之惡,但這些缺點往往是由歷史原因、階級地位和生存困境所共同造成的,並且個體之惡也無法改變作為整體的人民羣眾是推動歷史發展的動力的客觀事實。
因而,當一個左翼藝術家秉承着人民史觀去為人民解放而創作時,大多會盡其所能地讚美和鼓舞人民,用作品去提示、喚醒他們身上所能迸發的另一種可能性。即使表現人民身上的“醜惡”,也是出於幫助他們認識自己和改變自己的目的,所以這種表現也應是合乎邏輯、豐滿立體、能夠讓人去共情和理解的。魯迅筆下的人物就是如此,祥林嫂、孔乙己、華老栓、阿Q、豆腐西施……他們有愚昧的一面、市儈的一面,甚至根本不討人喜歡,但每一個都彷彿是現實中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而不是腦門上貼着“冷漠”“麻木”等標籤的人偶面具。

從這一點來看,《隱入塵煙》也許未必是有意醜化人民,但主角之外“全員惡人”的設定又確實顯露出創作者潛意識中,似乎其他貧困村民便不再是值得關注與同情的,因而這種對於底層人民的愛也是有條件和有限度的,是唯獨聚焦於馬有鐵和曹貴英這兩個最純潔的靈魂身上的。
同樣有着純潔靈魂的還有“二舅”,《二舅》作者為二舅專門挑選了一個詞叫“莊敬自強”,但對許多觀眾來説,“莊敬自強”的另一個名字是“逆來順受”,因而也就引發了無數關於“美化苦難”的批評。這並不是指二舅現實中的人生,而是指作者為二舅塑造的那樣一個底層中的聖人形象——他歷經坎坷卻不改初衷,只要在勞動就能安頓好自己的心、擁有最純粹的快樂。

的確,在這裏我們看到了一種最美好的未被異化的勞動形態,但這種勞動是否足以為二舅的全部生計提供長久保障?或者,即使二舅有女兒和外甥作為後盾,那其他沒有這種幸運的人呢?他們又要靠什麼來治好自己的“精神內耗”?靠道德修養嗎?
《隱入塵煙》中的馬有鐵被資本家吸了血,還要一碼歸一碼地還他錢,他和二舅一樣看似有着最完美的道德,卻實際上是一種封建主義的道德,武訓式的道德。如陽和平所説,“共產主義者要是無私,他幹嘛反抗資本家的壓迫呢?幹嘛不讓大家無私地向資本家奉獻呢?為什麼白毛女不無私地獻給黃世仁呢?”作為階級社會里的被剝削者,無私奉獻不是道德,奮起反抗才是道德,錙銖必較才是道德。

如果活在魯迅筆下,他們或許會成為那些令讀者“恨其不幸,怒其不爭”的人民中的未覺醒者,他們的苦難是給整個社會的一聲吶喊、一記警鐘,而在今日卻成了一曲田園牧歌或絕美愛情的背景與註腳。總有人會爭論,藝術到底應該揭露殘酷的現實,還是傳播積極向上的正能量?兩者看似矛盾,但其實常常是殊途同歸的,《隱入塵煙》有個令人絕望的結局,《二舅》卻給人以温情的希望,但它們都默認了同一個邏輯——社會現實是不可改變的。
這就是為什麼筆者認為這兩部作品都已具備了左翼藝術的表象,卻缺乏左翼藝術的內核。你在其中能夠看到無產階級的貧窮與苦難、平凡與偉大,因而它才收穫瞭如此多的共鳴,但是,卻獨獨看不到覺醒與出路。我們需要絕望的吶喊,但不是“我怎麼這麼苦”,而是“你憑什麼”;我們也需要有温情和力量,但不是“莊敬自強,把一手爛牌打好”,而是“英特納雄耐爾,一定要實現”。
也許有人會拿出審查制度、創作自由做擋箭牌,聲稱如此這般還能過審嗎?或者這跟樣板戲有什麼區別?那就太低估左翼藝術家的勇氣、才華和創造力了。這裏沒有篇幅過多展開,或許以後有時間可以向大家專門介紹那些兼具人民立場和批判深度,並在藝術魅力上毫不遜色於文青套餐的的優秀作品。
至於《隱入塵煙》和《二舅》,批評是該有的,但筆者並不認同對其趕盡殺絕,因為要説“反動”的話,我們的主流文化中觸目可及到處是反動的“雞湯”和“毒雞湯”。在這樣的文化環境中,能看到一點左翼藝術的表象都已實屬難得。它們所受到的熱捧正説明了“人民需要左翼藝術”,而它們所招致的批評同樣宣告着“人民需要更貨真價實的左翼藝術”。
無論怎麼看,這都是一件好事。我們要有信心,更要積極發聲,讓那些幕後數錢的投資者們明白,以後還想賺到觀眾錢,只有出賣“吊死自己的絞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