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好,他倆沒結婚_風聞
ins生活-ins生活官方账号-生活的理想,就是理想的生活2022-10-21 10:25
作者 | 巖蕊
來源 | ins生活原創

成年人的真心,都藏在玩笑裏。
2019年,大學生電影節開幕式,有記者跑到後台找明星們,追憶青春。
大家互相開着玩笑,鏡頭給到段奕宏時,他卻一本正經地衝着鏡頭大聲説:
「我暗戀的人在後面呢,我們班陶虹。」

陶虹也調侃的回應,「他不早説呢,唉,錯過錯過。」

這遲來20多年的「示愛」,是因為上學時的段奕宏,不敢言。
段奕宏來自西北邊陲的小城市,爸媽都是普通工人,但他卻有了想要成為演員的夢想。
歷經坎坷考入中戲後,卻又因為貧寒的出身自卑不已。
班裏同學大多都是高富帥,而他矮窮矬一個**。**
很多同學都嘲笑他,也不願意找他搭戲,只有班花陶虹給了他很多温暖。
他們關係很好,有次陶虹給他帶了芒果。這是段奕宏第一次見這種水果,他不知道怎麼吃。陶虹看出了他的窘迫,就主動幫他剝了皮。但他不知道里面還有核,一口咬下去就咬到了核上,陶虹沒有恥笑他。
從這一刻,他便暗暗對陶虹產生了情愫。
但他沒有勇氣面對心愛的女孩,他怕自己拍不好戲,沒錢、沒地位,甚至都不敢在片場驕傲地抬起頭。
段奕宏試着拼命努力,但無論怎麼掙扎,自卑感都始終圍繞着他。
那時青春懵懂的他一定想不到,曾經溢出來的自卑差點毀了他,卻也在某種程度上成就了他。
2006年,段奕宏33歲。
他憑藉《士兵突擊》裏的袁朗一角,被大眾所熟知。
只要他一出鏡,整個畫面都亮了一格!

在第一集的片尾,他搖搖頭,甩落一地的水珠,更是迷倒眾人!

他專業過硬,卻總不按常理出牌。

段奕宏通過反差化處理,將袁朗的邪魅和正義集於一身。把一個本不討喜的角色,演成了觀眾最喜歡的人物。
大家看的熱血沸騰,後來便用**“一見袁朗誤終身”**的極高評價來表達對他演技的肯定。

段奕宏火了後,很多人都説他是一夜爆紅。
其實不然,這「一夜」他走了15年之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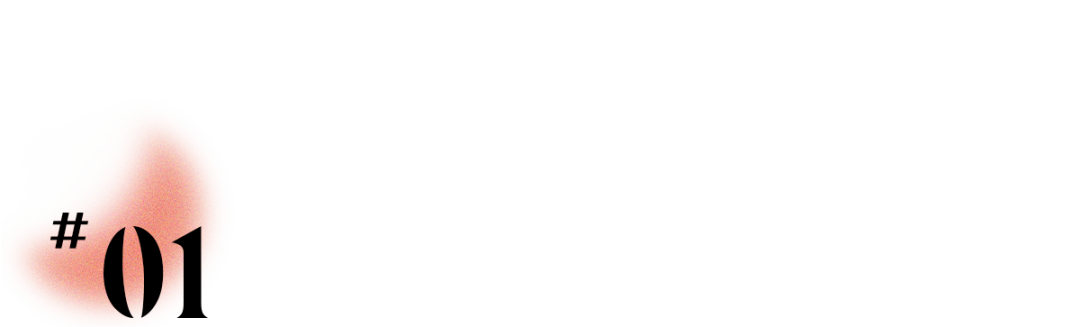
奴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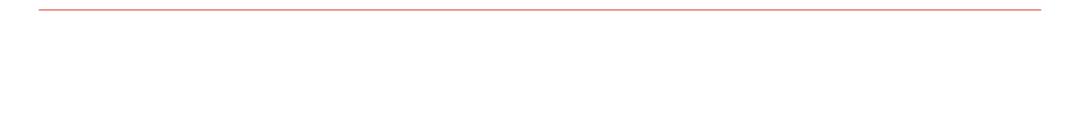
你別看銀幕上他張揚跳脱,但其實他「奴性」很重。
他願意做戲的奴隸。
剛畢業時,為了在警匪劇《刑警本色》中演好殺手羅陽的角色,他把一個掏槍的動作練了上千遍。

拍攝《二弟》,為了把角色演活,他特意去街邊和小混混待在一起,別人坐5小時,他站5小時,還時不時給他們遞煙。第二天來的時候,他也換成了緊身牛仔褲,尖頭皮鞋,吃喝玩樂都和小混混一起。

在《細偉》中,為了角色需要,他從72公斤瘦到了59公斤,減了26斤。

拍《烈日灼心》,段奕宏為了演好伊谷春這個角色,春節沒回家,而是去派出所體驗了15天的警察生活。
交通事故、民事糾紛、掃黃打非,能去的案子他都跟着去。

用體驗生活的方式進入角色,對他來説不是笨辦法,而是捷徑。
段奕宏在片場還有一個習慣:每演一遍都會自己看回放,他看到他自己不滿意的,就要再來一遍。
他的這種**「難搞」**,讓很多導演又愛又恨。
段奕宏常常會因為一句台詞、一個調度,跟導演吹鬍子瞪眼,叫板兩三個小時。
比如角色喝不喝水,現場到底是放蘋果還是梨,這些細節他弄不清楚就不演。
《記憶大師》的導演陳正道曾多次提到,再也不想和段奕宏合作了,因為他常常被段奕宏「虐到」心累,但又忍不住在下一次再給他寫角色。

他拍過最危險的鏡頭是**《西風烈》中,兩輛車並行,淨3米寬,他需要從一輛車跳到並行的另一輛車上。而拍攝時的車速是五六十邁**,跳不好是有可能致死的。
有人問過他:“這種危險的動作完全可以找替身,你犯得上冒生命危險去做嗎?”
他説:“我覺得犯得上。”

段奕宏討厭玩兒命,卻又次次玩兒命。
在拍《烈日灼心》時,有個鏡頭是他和鄧超掉到了深井裏去,段奕宏下去撈他。他要在三米多的水底掛着鉛塊,完成掰腿、掏槍、上子彈、打槍、把腿拿出來、一起出水面等9個動作。
練習的時候,他只完成了5個動作,但他不停地告訴自己「老段,你必須得扛過去。」
結果,他超額完成了12個動作。

《我的團長我的團》裏,有一場法庭審判戲。足足400多字的台詞,段奕宏一次性就把所有的台詞自然地表達了出來,而且感情到位。

編劇這樣形容龍文章:「諸葛亮智似半妖,龍文章也就是個妖孽,妖是智,孽是逆流激進。」
戲裏戲外,段奕宏都是**「妖孽」**。

如今,《我的團》開播已超過10年,但B站評分仍高達9.9分。
這是時間在他身上的作用,他想拍出留得住的作品。

2015年,42歲的段奕宏獲得了人生的第二個影帝。
他舉着獎盃,在台上哽咽着説:
「直到今天,我已經出道了二十四年了。我不願為拿獎演戲,因為我無法預判這個結果。這個結果不是我做事的初衷,作為一個演員,我願意為戲為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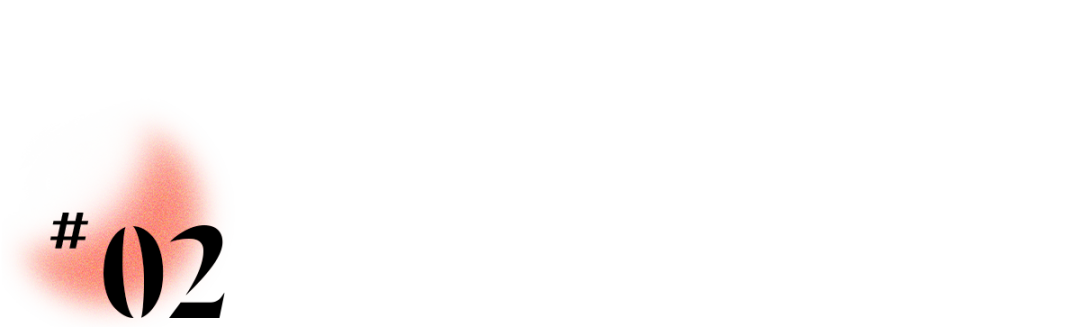
緊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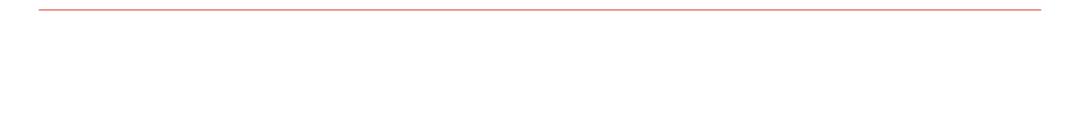
「奴性」下包裹着的,是他始終擺脱不掉的緊繃感。
段奕宏出生於新疆伊犁,父母都是普通工人。
他小時候很皮,也不喜歡學習,爸媽覺得他這樣子,以後能當個伐木工都不錯了。
但沒想到,上高中時參加的一次文藝匯演,改變了他的命運軌跡。
當時他自編自演的小品在當地火了一把,恰巧還被一位上戲的老師看到了。這個老師就託話劇團團長給段奕宏帶話説,「這孩子有天賦,可以讓他去考表演系。」
演了出小品,老師的一句話,就讓他堅定了做演員的夢想。

但當年的段奕宏,就像是新疆鄉野裏隨處可見的一塊兒石頭,不光沒特色,而且土氣又倔強。
家裏沒人搞過藝術,爸媽都認為這事兒不靠譜。
但他才不管,一心只顧着逃離這裏。
每天一有空就對着鏡子練台詞與眼神,寒暑假一邊在果脯廠打工,一邊練習表演。
到了藝考的時間,段奕宏給爸媽撂了句狠話:
「你們要不讓去,我就恨你們一輩子。」
説完這句話,他揣着一張去烏魯木齊的班車票就出了門。

伊犁到烏魯木齊,班車24小時。烏魯木齊到北京,綠皮火車78小時。
段奕宏沒錢買卧鋪,就只能坐硬坐,還沒到北京小腿就腫脹到一按一個窩。火車上人多要排隊上廁所,有時碰上排水系統不好,糞便就會堆成山,「我沒感覺苦,我顧及不到」。
他從中國地圖的雞尾巴一路坐到了雞脖子,換來的卻是不到20分的成績。
他找了個理由説服自己,決定第二年再來一次。
第二年進了三試,但最終還是被刷了下來。
他不甘心,跑去問老師原因,老師説:「退一萬步講,你也考不上中戲。你一看就是上進的好孩子,別耽誤自己了。」

段奕宏軸得很,中戲老師的那句「退一萬步也考不上」非但沒有嚇唬住他,反而成為了他屢敗屢戰的動力。
1993年,他報考了表演培訓班,學費4000元。為了不給爸媽添負擔,他跑去工廠裏洗蘋果,每天工作12小時,一天一頓飯,幹了一個月,賺了40塊錢。
經過培訓後,94年他又去考了第三次。
終於,21歲的他在千軍萬馬中,擠進了璞玉如雲的中戲,跟印小天,小陶虹,塗松巖一個班。

第三次來北京,他看北京人開始流行就着煎餅果子喝可樂了。他也就趕時髦,左手煎餅,右手可樂。
段奕宏太想融入這裏了。
他內心有更加尖鋭和直接的東西,他想靠自己的業務能力在這個世界上謀得一席之地。同時,你也會一下看到他身上的那種自卑---一般人會藏起來的東西。
進入中戲後,同班同學大多都來自大城市。優渥的家庭讓他們從小就去過很多地方,讀過很多書,看過很多電影。
而段奕宏受到的課外教育卻少之又少,同學們在一邊聊天,他常常是插不上嘴的那一個。
當班裏其他同學都開始跑組時,卻始終沒人找他拍戲。甚至還有人斷言,段奕宏只能“走農村路線”。
他每天都被自卑包裹着,怯生生地往前走。

回家的車票太貴,段奕宏4年都沒回過家。
大二那年,小陶虹拉着他去家裏吃了頓年夜飯。段奕宏硬是要把欠的人情還回去,後來在宿舍裏用電爐給她做了一頓手抓飯。
「那時我自卑的心理,讓我不願意跟人交流,甚至你請我一頓飯,我一定要還。」
小陶虹能感受到他內心的敏感和自卑,「那時候的段奕宏就像是一根繃緊的繩子,隨時會斷掉的樣子。」

中戲表演繫有一年的甄別期,如果有兩門掛科,就要被退學。
拼盡全力才抓住命運的尾巴,他不允許自己再被甩下去。
既然沒有機會拍戲,那就踏踏實實做好眼前事。
為了獲得好成績,段奕宏經常在排練場通宵排戲,臨近熄燈時就躲在道具後面,等巡夜的老師檢查完後,再偷偷出來,獨自排練。天一亮,就從窗户翻出去練晨功,風雨無阻。
時間久了,他開始收到老師的讚譽,全校學生也都開始期待看他的作業。

段奕宏的能力和優秀,讓他找到了安放之處。
1998年,段奕宏以全優的成績從中戲畢業,進入了中國國家話劇院。
他在話劇舞台上如魚得水,所以本能地對影視表演產生了抗拒心理。
直到2003年,他出演了婁燁的電影《頤和園》。同年,因為喜歡《二弟》的劇本和角色,再次出現在銀幕上,逐漸被大眾所熟知。
本來再來兩三部片子,他立馬就立住了。
但他不。
因為一部《戀愛的犀牛》的話劇,他又回到了話劇舞台。
段奕宏在話劇舞台上不瘋魔不成活,他這個版本的馬路,才氣與痴氣並存,無可替代。

話劇可以磨練一個演員的演技,可未必能加快出名的速度。
直到06年的《士兵突擊》,段奕宏才在演藝圈中「一夜」爆紅。
這一夜,他走了15年。

他太想證明自己的好了,所以那種緊繃感始終裹挾着他。
即使已經進了國家話劇院,即使已經有了成熟的作品,即使一次又一次拿下影帝。
他都依然甘願,為戲為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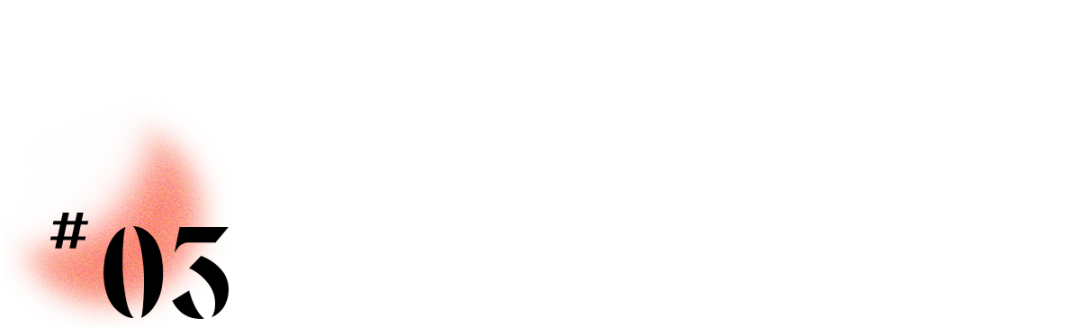
鬆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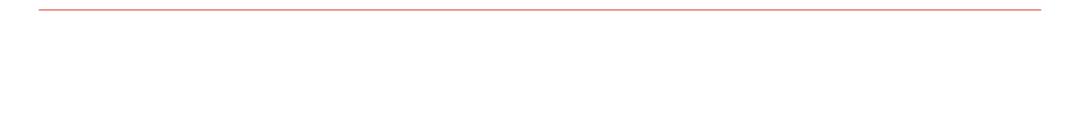
段奕宏以往的作品都是偏重動作戲和硬漢角色,但近幾年的作品中,我們看到了更多他在感情戲、內心戲上面的呈現。
而這也離不開他年齡的增長,以及成長的蜕變。
他開始變得「鬆弛」了。

段奕宏有一陣子很恐懼時間。他看着父母一點點老下去,很害怕。
每年他都會把父母接來家裏住一段時間,有次陪爸媽在樓下遛彎,回去換了雙鞋的工夫,爸媽就不見了。他突然控制不住地喊,「爸?媽?」,慢慢地聲音越來越大,那一刻他無法想象爸媽不在了會是怎樣。但那次,老兩口只是走錯了樓。
短暫地「失去」,讓段奕宏突然明白,18歲時極力想擺脱的那些,到了中年,反而成了最珍貴的存在。

東京電影節開始的前一天,段奕宏接到了父親病危的電話。他趕最早一班飛機回到了伊犁,到醫院時父親已經走了。
他忽然回想起,父母每次都勸他,「你很忙,不要回來,不要顧我們,你不要掛念我們」,他慢慢地就相信了這樣的話。
這件事讓他陷入了自我懷疑,「我之前一直是馬不停蹄的、跟頭把式的追逐我的夢想,我甚至冷落了我的親人、家人,放下我的生活,直奔一個結果。我到了那兒又能怎麼樣,我能維持多久?我連最起碼的父子感情,我都沒有深深地去體悟和感悟。」

父親的後事是段奕宏一手操辦的。這次回家,他發現自己忽然成了被需要的那個人,曾經調皮搗蛋的小男孩,現在成了需要做決定的那個。
真的送走父親後,段奕宏突然也不再懼怕時間。他悟到了生和死,也是生命中的一種體驗。

2018年,段奕宏回新疆住了一段時間。
在這段時間裏,他才發現自己對這片生長的土地一無所知。
「我沒有聞過草原的花,沒住過蒙古包,我回到這裏,突然放鬆了,我教我媽媽做預防老年痴呆的手指操,我鬆弛且放下了。」
他把時間留給家人,想多陪陪母親。
「這不是孝道,是我需要她,媽媽今年88歲了,我覺得我需要變得會表達一些。」

他回到自己的中學,在這裏回憶起了學生時代的場景。第二節下課後的大課間,他總是跑着下樓去小賣部買零食。和朋友倚在欄杆上,看着進進出出的女孩子,討論各自喜歡的類型。
談起這些時,段奕宏笑得像個孩子,他在黑板上寫下一行字:
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過隙,忽然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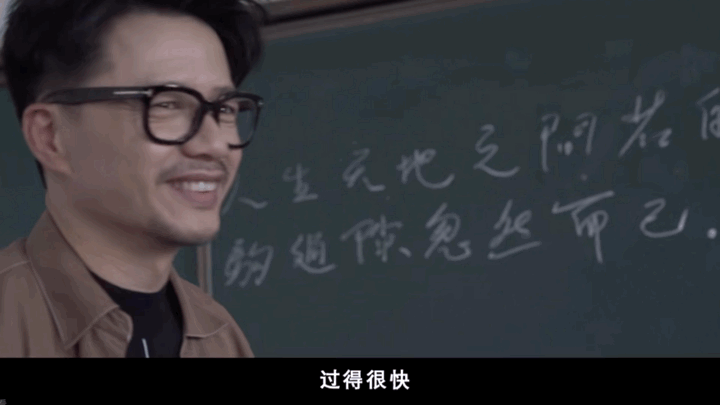
段奕宏內心所偏執的東西,隨着年齡的增加也在不斷變化。
19歲,他拼命想逃離,想掙脱,想去融入更大的世界,去拍戲。
44歲,他開始抽離,回到曾經最想逃離的家鄉,這裏有家人,有愛,還有生活。

但無論如何變化,他內心所珍視的東西,都容不得商量。
過去如此,現在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