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的出路在何方?_風聞
秦朔朋友圈-秦朔朋友圈官方账号-2022-10-21 08:09

· 這是第4761篇原創首發文章 字數 6k+ ·
· 劉子 | 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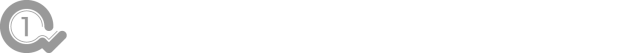
温州候鳥
疫情給我國實體製造業、中小企業帶來的衝擊,許多媒體、專家都有數據反應。而在我看來,這不僅是數據,更是我老家許多親人的現實生計。
我老家就有許多親戚在外打工,比如我小姑姑和姑父在温州打工就有二十多年了,這兩年,他們過起了一種“温州-老家”的“候鳥式生活”。他們所在的小型鞋廠,只有30多人,近年來訂單嚴重下滑且不穩定,去年10~11月就放了兩個月假;沒幹幾個月就過年,今年3月才開工;陸陸續續做一段時間又休個十來天,直到今年國慶前又放了一個月假;國慶後過去工作了一個禮拜,廠裏説做十來天又要放假……如此斷斷續續,彷彿得了腎結石,就沒個暢快的時候。
事實上,他們這樣幾十個人的小廠,可能佔了温州企業的一半,情況都差不多。他們隔壁一家中美合資的外貿鞋廠,有幾百人規模,生產倒是正常維持,但去年開始就從4班輪崗壓縮到2班,後來就沒招過人,相當於減員一半。
收入是多少呢?他們基本都是計件制,以往普工有個5000元左右(不交金、不交社保),今年下降至4500元,還有許多人在排隊。技術工種或小主管高一些,有個五六千元,但因為工作量下降,收入同步下降。
沒有活兒的時候怎麼辦?時間短就宅在幾平米的出租屋刷手機、發呆,有個十來天間隔期就另外找份代工做做,上了一個月,乾脆回老家歇歇,畢竟老家生活成本低一點,等到工廠有活了再回温州……當然,這些不會反映到就業統計數據中。
回老家也不是辦法,老家工廠月收入2000多元,何況基本只招收45歲以下青壯年,他們已經淘汰,回去也找不到穩定工作;種田?他們家四口,原本有四畝田,其中一畝旱地,幾年前建房又抵掉幾分地,現在耕地只剩下兩畝一分,按每畝年產1200斤糧食,最優質粳稻、全國平均收購價1.31元/斤算,約合年產值3300元,即便採用目前流行的再生稻技術,還能補收最多三分之一,那就是合計產值4400元,平均到每月367元,一家人吃飯都是問題……
以往年頭,只有耐不住性子的80、90後第二代農民工做“候鳥”,這兩年,連我姑姑這批60、70後,最能吃苦、最穩定的第一代農民工都不得已變成“候鳥”了。而且,他們心中明白,這樣的“候鳥”生活也只能維持個兩三年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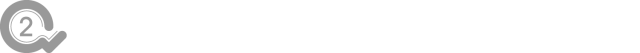
他們的出路在何方?
按照七普存活人口統計,我國60後人口約2.17億人,70後約2.24億人,結合我國2022年52.57%的户籍城鎮化率,而他們這兩代人城鎮化率肯定會更低,就按50%算,意味着有2.2億的我姑姑這樣的“他們”,佔中國逾七分之一的人口!
當下,每一代人的就業問題都比較嚴峻,但對缺乏出路和保障、日益無力、不可逆轉的2.2億“他們”來説,這種嚴峻性無疑更加殘忍且燃眉。
中國類似這樣亟待解決的具體問題還有很多,知識界、媒體界不應陷在意識形態、“國際風雲”、乃至左右之爭中,喋喋不休乃至怨天尤人,因為還有許多實際問題需要大家一起去面對、探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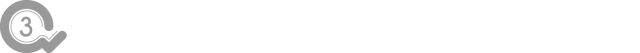
土地產權是不是問題?
長期以來,知識界對鄉村問題有一個常見毛病,就是一談到鄉村,就陷入到土地、產權、城鎮化這些問題,彷彿這些問題不解決,鄉村就無解——可惜,這些問題短期確實無解,那就卡在這,不繼續往下研究了嗎?
篇幅有限,在此我們集中説產權的事兒。
我國當下鄉村土地制度大致可以概述為集體所有、家庭承包、鼓勵流轉、嚴禁非農化,其中各界爭論的焦點在於產權集體所有。拋開理論,從現實來看,我有以下幾個觀點:
首先,鄉村土地集體所有制沒有根本問題。
在鄉村土地集體所有制的背景下,像我姑姑、姑父一樣的中國農民,有一個很多國家都羨慕的優勢——他們可以在城市反覆“博一把”,博輸了照樣可以回老家,等機會更好的時候再出來“博”,直到有能力在城市安頓下來……
也許有人又要拿出“自由”的帽子,讓農民擁有選擇的權利——比如可以自由賣地、賣宅基地、賣集體權益,拿這個錢去城裏買房不好嗎?
其一、你先問問城裏的房價答不答應。
其二、借用毛姆的話回答:“人民大眾不需要自由,安全感才是他們最深切的希望。”對精英階層來説,“自由”的正向收益更高,但對底層人民來説,自由往往是把“雙刃劍”。
其次,當下集體產權制度有其優越性。
舉個例子,我老家小村,是典型的三無(無資源、無風景、無風貌)農村,既不窮也遠遠説不上富裕的農村。但如果放到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來看,變化無疑是翻天覆地的。
譬如,我們村還算規整,基本上只有兩條水泥路,每户人家的房子都整整齊齊地碼在兩邊,還算整潔、亮堂。而這兩條路之所以能修成,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土地集體所有制。
要是放在私有制下,加上中國農民的小農意識,當初修路的時候肯定有人不願拆老房子,這路就修不成!
也許有人會説,私有制下,修路可以協商、給他補償啊?想多了,在我們那樣的小村,修這兩條小路都是政府“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掏的錢,沒有任何經濟效益,誰會給你補償?如果有人硬要向政府要補償,而政府肯定不想開這個頭,這路基本就修不成。其結果,一定是不好的話就大家都不好,牽涉到集體利益、公共利益的事,就很難辦成。
再舉一個例子,浙江麗水市松陽縣的鄉村保護與旅遊開發。松陽縣是浙江最偏遠的縣之一,大山深處保留了很多傳統古村落。前些年山上有一個村整體搬遷,土地性質轉化為國有商業用地,一家文旅運營商整村開發,把舊村拆除,繼而改造為一棟一棟的現代化休閒度假村,並拿出一部分銷售。但這個做法很快停止,為什麼?
按照市場邏輯,“拆除-新建”的成本往往低於古建築修復、維護,在規模效益指引下,一旦土地私有,大概率會導致整村新建,其結果,必然導致古村“現代化”,原住民也肯定會被開發商想方設法遷離。如此,這些古村大概率會被房地產化、度假村化,就再也見不到深山裏的古村原生風貌,以及在裏面開工作室、開書店的藝術家們與原住民們其樂融融的和諧之境,今天的遊客們恐怕也要失望了。
當前的土地集體所有制下,大多數情況中集體和私人的產權邊界都相對清晰。而且,今時不同往日,個體權益保護其實是上升的:在集體所有制下,集體侵犯個體利益時,一定會受到個體的反彈,而個人利益明顯侵犯集體利益時,也會有其他人或組織站出來,相對平衡;而如果不是集體所有制,那麼當個人利益干擾集體利益時,除非影響太大,就很難有制約力量出現。
所以,農村的集體產權制有其優越性,這也被越來越多的學者看到。
第三,鄉村土地產權問題在變化。
在我老家那樣缺乏市場價值的小村,壓根就沒人關心土地產權問題,甚至土地壓根就沒人願意種。即便產權私有了,可以賣了,也賣不了幾個錢,又有什麼意義呢?
那有市場價值的鄉村呢?在我調研過的許多鄉村,土地產權制度已經在隨着市場發展在演進。譬如城郊農村,可以按照市場化、房地產方式變更土地性質,拆遷“致富”,這個我們並不陌生;景區範圍內農村宅基地,可以進行長達40年的長租(城市商用物業產權也只有40年),比如離上海市區最遠的青浦區岑卜村,因為有一些城市人看中它的“偏僻”,集中前來生活,一棟農民房一年可以租到2-3萬元;還比如有一些地方已經在做三權分置(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分離)改革,甚至像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區九華鄉的農宅,還可以將使用權證精確到每一間(比城市還靈活),以便更靈活地流轉給市場主體經營“村民宿集”。
所以,有市場價值的地方,不管是市場資本還是民間資本,都已經在通過市場化的方法進入,它們不會因為產權集體所有就停止步伐。所以產權並不是市場化的根本障礙,有沒有市場價值才是!
第四,農民並不關心產權問題。
如果問我姑姑、姑父,他們最關心的事情是什麼?肯定輪不到土地問題。而且就那麼點地,就這麼個經濟水平,玩出花來也解決不了他們的根本問題!
如上,缺乏市場價值的地方,土地本來就不值錢,農民壓根就不會想產權這回事;有市場價值的地方,不需要賣產權也能變現,市場已經在定價,操產權那份閒心幹嘛。
如筆者在《不是隻有經濟常識才是常識》中闡述,現有產權制度下,農民已經實現了安居+“半樂業”,他們普遍關注的事情,主要有三個:一是“安居樂業”剩下的那半份“業”;二是養老;三是孩子的教育,我們去面對、探索其中任何一個問題,都比盯着產權問題更有意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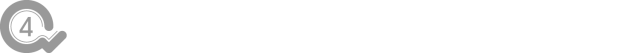
土地制度的幾個基本事實
土地制度研究學者劉守英教授,在其專著《土地制度與中國發展》中詳細介紹了中國土地制度的沿革、現實問題和一些經驗探索,他實際主張的是中國傳統的“田底權”(產權及收租權歸地主)和“田面權”(農民有永久使用、轉讓、收益權)的分離模式,即在遵守“田底權”制度(城市土地國有,鄉村土地集體所有)下,推進土地的“田面權化”、市場化,像城市住宅70年/商業40年的產權安排一樣,在保留土地集體所有的“名分”上,將農民對土地的承包權、宅基地使用權逐漸向財產權做實,這也被另一位三農學者賀雪峯批評為“實際上的私有化”。
我們暫不參與學術之爭,劉守英教授在研究中提出的幾個基本事實,我們需要首先看到:
**其一,土地私有並非絕對。**譬如,英國法理上所有土地都歸國王或女王所有,但90%的土地都歸私人所有,而在今年頒佈《租賃產權改革(地租)法》之前,購房者每年需向土地所有者支付一定的地租,也就相當於購房者也無法買到完整產權;在美國,58%的土地私有,但絕大部分森林、草地、保護地等由聯邦政府和州政府所有(分別佔31%和10%),另有1%的土地歸城市政府所有……所以,我們要防止一談土地產權改革、建立清晰產權,就掉入私有化的思維陷阱。
**其二,土地管制是大多數現代化國家的共同選擇。**美國、加拿大、日本稱之為“土地使用分區管制”,瑞典稱之為“土地使用管制”,英國稱為“土地規劃許可制”,法國、韓國稱為“建設開發許可制”,即便私有,但世界各國都重視土地資源管理、尤其是耕地保護,且都經過了由分權、分散多頭管理到集權、集中統一管理轉變的過程。所以,私有化並不意味着絕對的市場自由,仍需向公共利益求平衡。
**其三,我國的“世界工廠”成就,得益於低地價。**八九十年代珠三角、長三角之所以能成為“世界製造工廠”,得益於廉價農民工的貢獻,以及這些地區將近一半的集體存量建設用地的支撐;同期,各地政府“以地謀發展”,通過大量低價徵收、轉化土地性質,建工業園、招商引資,促進了各地工業的大發展。而2000~2011年,全國工業用地價格只提高了71.18%,與之相對的是,商業和居住地價水平分別提高了308.76%和528.1%。“低地價+低勞動力價格+低福利制度”,經過許多犧牲,才有了我國製造業的“世界工廠”地位。
**其四,土地制度是最基本的國策,是執政和社會穩定之基礎,任何簡單的市(私)場(有)化的思維,都是一廂情願,於己於人都是無益。**同時,土地只是工業化時代的三要素之一,在今天以科技、人才、創新為核心的新時代,重要性已經下降了很多,它也早就不是今天鄉村經濟的“命門”所在。
所以我們要探索的,更應該是現有制度下,如何跟上時代發展、人民實際需求的新時期土地改革路徑,且需堅定製度自信,以穩為主,漸進圖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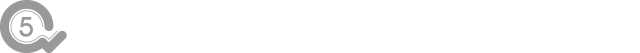
鄉村經濟的“命門”在哪裏?
綜上所述,知識界不應該再落伍地,繼續把鄉村問題焦點放在產權制度、城鎮化等老生常談的問題上,因為,這些問題,意義真的沒有大家想象的那麼大。
焦點在哪裏?還是得去解決農民們關心的,重要且緊急的問題。
鄉村教育和養老問題,我已經談過很多次,此不贅述。我國當下鄉村土地產權制度,保障了農民的基本生存,和社會不至於出現大動亂(“農民失地-大量湧入城市-貧民窟-社會治安惡化”)的問題,基本盤穩住後,關鍵還是發展乏力和產業升級的問題——即我姑姑、姑父為代表的第一代農民工,和我老家許多堂兄、表弟為代表的第二代農民工,共同面臨、且日益加劇的沒活幹、沒有好工作可以乾的問題。
解決方向只能是產業升級:
第一,農業需要繼續升級。
中國以往的農村經濟發展路徑大致是,80年代搞聯產承包做一產——90年代後發展二產製造業(各種工業園區建設、農產品加工等)——2010年後搞三產(如農村電商、鄉村民宿等),總體是進步的,但實踐下來,都有各自問題。那麼接下來的思路就必須是“三產融合”,單獨搞某一個產業都沒有出路,只有融合起來一起搞!
這方面,其實有大量實踐案例等着我們去了解和探索。
第二,繼續以工業帶動農業。
梁漱溟指出,中國鄉村幾千年來的核心問題是“缺技術+組織”:缺技術,所以只能看天吃飯;缺組織,所以無法聯合起來爭取利益,包括對接市場。要解決這兩個痛點,目前最好的辦法還是通過工業化組織生產的路徑。
譬如幾千年來,中國農民搞養殖都是分散的,每家養十隻八隻雞、兩三頭豬,一半賣一半自己吃,這樣,一不市場化,二抗風險能力約等於零,來了雞瘟、豬瘟就束手無策。當然,損失不算特別大,也就不敏感,缺乏動力去搞科研、防範機制。而目前,中國雞、鴨、豬等養殖業都日益產業化,大型養殖企業對產業化的改造、公司+農户模式的帶動、種養一體化、集中力量搞科研等市場化行為,對傳統養殖業的改造都是根本性的。
農業也分很多類,糧食安全、耕地遵循國家管理,作為保底存在,而經濟作物、養殖業走向產業化,再結合區域特色農業,發展老年精品農業,走三產融合之路,才是中國農業發展的根本出路。
第三,科技持續升級,實現新的就業轉換。
比如網約車、快遞、外賣的出現,為青壯年農民進城提供了大量的、較為體面的就業。但是,下一個新的、高質量的就業點在哪裏?這個問題就比空談城鎮化更有意義。
所以,中國鄉村經濟的“命門”,與城市經濟、國家發展的困難是統一的,那就是如何加快產業轉型升級,為社會提供更多的、更優質的就業。廣大知識分子、媒體,應當面對實際問題、與時俱進,與其困惑、到處炒熱點甚至忙於爭吵,不如多去研究、發掘、報道,甚至參與中國轉型升級的具體辦法。
當然,作為一名鄉村研究者,我更歡迎大家多關注和參與鄉村。因為,5.8億農民依然是中國最大的羣體,261萬村莊依然是中國最基礎的社會組織,知識界、媒體界、財經界不去關心我們最大的羣體,不能不説是一種遺憾。

作者:民間觀察派,獨立思考者。專欄作者,撰稿人,鄉村振興&縣域經濟學者。個人公號:劉子的自留地。
參考資料:
劉守英,《土地制度與中國發展》;
賀雪峯,《農地私有化行不通——劉守英教授錯在哪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