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民謠2022》明晚開播,民謠出頭只剩“一日之遙”?_風聞
音乐先声-音乐先声官方账号-解读音乐产业,见证黄金年代。2022-12-22 22:16
作者 | 朋朋 編輯 | 範志輝
昨天,《我們民謠2022》正式官宣定檔,被催播了這麼久,終於確認本週五晚8點在愛奇藝正式上線。
細看陣容,水木年華、葉蓓、萬曉利、小河、張瑋瑋、周雲蓬、陳鴻宇、陳粒、房東的貓、好妹妹、柳爽、謝春花、蔣先貴等民謠圈“老中青”三代的29組民謠音樂人相聚在一起,就知道這一波等待值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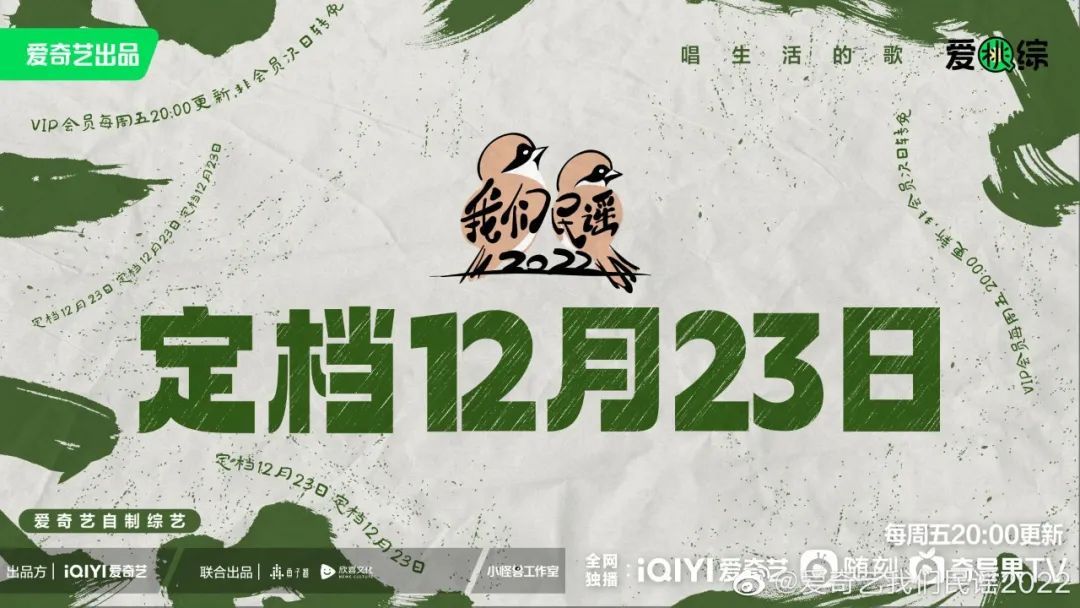
這29組音樂人構成了中國民謠30年的敍事和流變。 葉蓓的歌是物慾的滾滾煙塵中,那永遠不染塵埃的白衣飄飄;周雲蓬的歌是屬於詩歌的時代落幕後,那淚水全無的歌手和嗚咽的琴聲;萬曉利的歌是時代車輪轟然向前時,那大智若愚的調侃與戲謔;蔣先貴的歌是城市化與現代化進程的洪流中,那唱給縣城中浪漫愁雲的頌歌……
肇始於90年代中期,民謠音樂就在漸趨碎片、多元的中國流行文化譜系中佔據了一席顯位。作為一樁文化事件、一股文化潮流,民謠音樂靜靜地流淌過一個又一個時代,像一支虔誠的筆,記錄着每一個時代的詩情和浪漫。
民謠,綿延三十年的敍事
20世紀90年代末,受到中國台灣民歌運動的影響,在內地各個高校的校園中出現了一羣抱着吉他唱歌的青年。他們不再談論家國和英雄,不再歌頌歷史和理想,而是將目光落在瑣碎的日常,體味日常生活的治癒和温情,大地唱片黃小茂將他們所唱的歌曲稱為“校園民謠”。

1994年1月,大地唱片發行了名為《校園民謠1》的專輯。《同桌的你》、《睡在我上鋪的兄弟》、《流浪歌手的情人》等歌曲從校園廣播站一路唱,飄蕩在學校的操場、草坪,一直傳遍大街小巷。
就像專輯封面上所言,“每一首歌都來自一個動人的故事,每個故事都發生在你生活的四周”。
這些剛剛離開校園的人回望青春時期,以簡單質樸的語言向聽眾訴説這一代人的故事。當迅猛發展的經濟誘發浮躁、消費主義等時代病,那代人中思考最活躍、情緒最敏感的一批人開始彈琴歌唱,他們懷着純真的詩意,歌唱理想,也歌唱初入社會的迷茫。
隨着千禧年的來臨,在北京三里屯一家名為“河”的酒吧開門了。以萬曉利、周雲蓬、小河、張佺、張瑋瑋、郭龍為代表的遷居在北京的“異鄉客”們,從校園民謠人手中接棒,開啓了新民謠的時期。面對着同樣的北京,以及劇烈變化的社會環境,新民謠少了些白衣飄飄時代的風花雪月,多了些知識分子式的吶喊與反思,也開始從本土的民間音樂元素汲取養分。

攝影: 安娜伊思 馬田 Anais Martane
回首這一代民謠人,周雲蓬是悲鳴命運的抗爭者,萬曉利是人性寓言故事的戲謔譏諷者,小河則是摒棄了一切限制,單純為幸福而歌的避世者。正如樂評人郭小寒所説,“他們曾經是漂泊的城市波西米亞人,是河酒吧浪漫時代的深情狂歡客。”
2010年以後,最新一代的民謠人在互聯網和電視選秀時代更迅速地成長起來。他們在前人的基礎上,順應更多的時代議題,情緒更加私人化。他們不再悲苦糾結而是隨性親和,用音樂表達自己的所思所想所愛所恨,少了幾分前人音樂中的抗爭,但不少的是生活細緻、多情的審視。

比如趙雷,他的歌詞中既有對消費主義的逃離,也有在都市生活中的肆意與快活;或如好妹妹,音樂中摒棄了沉重話題,像是車載電台中温柔的都市人趣談;比如陳粒,她在歌詞中從不遮掩自己性格中的不羈和剛烈,將女性聲音與話語轉化為隨時爆炸的“超新星”;再比如柳爽,在快節奏的生活中,民謠音樂的釀酒者,不急不緩就道盡了人間繁華。
當年,**李宗盛試圖定義民謠時用了三要素:一樣樂器,一場人生,一個故事。**通常來説,民謠演出就是用一把吉他,將一段人生化作一個故事講給你聽,你為這故事感動,你就會成為他的粉絲。民謠從不歌唱生活,它就是生活本身。
民謠,綿延三十年的書寫
1976年,留美歸來的李雙澤把可樂瓶子擲碎在這淡江大學的禮堂裏,使得“唱自己的歌”成為了校園民歌運動時期的時代最強音。後來,中國台灣民歌一路北上,影響着內地的民謠創作,“唱自己的歌”這一精神內核就在民謠音樂人間延續了下來。
樂評人郭小寒在回憶她與甘肅民謠歌手張瑋瑋一起梳理中國當代民謠發展史時,曾頗為感慨地寫下了這樣一段話:“我跟他一起,細緻地梳理了這段中國民謠的歷史,逐漸意識到這樣一個地方,這樣一羣人,對於中國的音樂文化意味着什麼。在這些人身上,你可以看到當代民謠不是工業化的產物,而是自然生長出來的———異鄉人被音樂感召,來北京圓夢,從酒吧翻唱開始逐漸有了‘唱自己的歌’的意識。”

換句話説,民謠始終在表達“我”,不媚俗,也不討巧,而是讓音樂從自身的生活生長出來。當一代音樂人集結在一起時,正從“我”綴連成“我們”,綴連成一代又一代人的時代圖景、集體記憶。
最近一兩年間,出現了許多針對民謠的紀錄片式的專題節目。例如,央視推出的節目《踏歌行》,將民謠音樂人放置於他們成長和創作的鄉土,感受一方水土一方歌的魅力;愛奇藝的紀錄片《我行我樂》的鏡頭中,野孩子是温暖且粗糲的民謠劍客,柳爽在夢想與現實的光影處,尋找民謠音樂的真諦。

即將開播的《我們民謠2022》也是如此,將老中青三代民謠人集結在一起,感受不同時代的音樂人的文化書寫和故事底藴。
我們可以在水木年華身上看到20世紀90年代的校園民謠,代表着學院派和唱片工業的精英;可以在萬曉利身上看到千禧年後的城市新民謠,將民謠音樂演繹成一場公路電影;也能在柳爽、好妹妹身上看到互聯網時代的新民謠,看到新一代民謠歌者的快活和肆意。
如果説此前在綜藝節目中掀起的民謠翻唱熱潮,不過是民謠商業價值提升的佐證,那麼,在隨後幾年間民謠風格的寂寞,也並不代表着屬於民謠的時代已經過去。反過來,如今面向民謠音樂人的紀錄片、專題節目正是佐證了民謠音樂的頑強生命力,這種生命力來源於民謠中的煙火氣和生活氛圍感,來源於生活,在舞台上綻放光彩。

從“多少人曾愛慕你年輕時的容顏,可知誰願承受歲月無情的變遷”,到“和我到成都的街頭走一走,直到所有的燈都熄滅了也不停留”,再到“如果有時間,你會來看一看我吧”,民謠中的那些人生、故鄉、理想都很鮮活,從不曲高和寡,每一代人、每一個人都可以在民謠中找到人生某一片段的體悟,從而共情。

像周雲蓬説的那樣,“一切都是從生活出發”,像小河説的那樣,“關注一些瑣碎的、身邊的事情,是你皮膚真的能感覺到的”。三十年的文化書寫,淬鍊了民謠的包容,它像當代人的精神烏托邦,描繪着人間百態,容納着每一代人的精神小憩。
民謠,共赴一場久違了的Live
從校園草坪上彈琴而歌到河酒吧的深情狂歡,再到民謠音樂節和livehouse中的熱淚與感動,民謠現場有着不可比擬的浪漫,而如何將線下的這份浪漫與感動還原到線上,無疑有着不小的難度。
為此,《我們民謠2022》集齊了民謠圈“三代頂流”,全程還原了Livehouse的表演模式,將綜藝節目與線下演出場景疊加,讓線下演出時候的沉醉與肆意都精準地帶到了節目當中。
與其説是一檔民謠綜藝節目,不如説是邀請觀眾共赴一場久違了的Live。

近日,在《我們民謠2022》看片會現場,節目總製作人姜濱如此概括節目的初衷:“做民謠綜藝希望它的寬度和刻板印象的民謠不太一樣,我們希望在今天也互相關照一下大家的情緒,關照一下大家的生活,把節奏放慢下來。”

《我們民謠2022》的誠意就在於此,也是每個時代始終需要民謠的價值所在。在快節奏的生活中,在都市的鋼筋水泥之間,民謠的淺吟低唱足以慰藉那些疲憊的情緒,在沉醉的live中收穫一場治癒之旅,其共情力和治癒力也都成倍放大。
此前,音樂先聲曾赴長沙蔘與了節目第一階段的錄製,對此頗有感觸。在那兩天的舞台上,那些被傳唱了幾十年的經典,聽來依舊會感動,讓人心頭一顫;而尚未發佈的新歌,聽來也是不俗的品質,不少都有大眾傳唱潛質。

而在催播了許久以後,《我們民謠2022》終於正式官宣定檔12月23日(本週五)晚8點,屆時將會有哪些驚喜舞台、治癒金曲,李宇春、張亞東、呼蘭、徐志勝、老狼5位民謠好友與29組民謠音樂人又將碰撞出怎樣的化學反應,非常值得期待。
最後,希望《我們民謠2022》讓所有情懷都復甦,所有熱愛都醒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