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修延|城市敍事關乎未來_風聞
探索与争鸣-《探索与争鸣》杂志官方账号-2022-12-27 19:23
傅修延|江西師範大學資深教授
本文原載《探索與爭鳴》2022年第10期
非經註明,文中圖片均來自網絡

傅修延教授
敍事即講故事,漢語中“故事”的本義為業已發生之事,講故事因此在一些地方又被稱為“講古”。然而一切未來皆伏源於過去,選擇什麼樣的故事來講述,把什麼樣的事件當作一座城市最有意義的集體記憶,常常寄寓着城市中人對未來的憧憬。這也就是説,城市敍事關乎未來,對過去的講述雖然不會改變昨日的世界,卻有可能通過影響人們的作為而讓明天變得更為美好。
“講”與“做”
討論城市敍事,首先需要深入瞭解“敍事”這個關鍵概念。一般理解敍事是對涉事信息的傳播,但筆者注意到古漢語中“敍”“序”相通,最早出現在《周禮》中的“敍事”,指的是按次序處理公務,因此那時的“敍事”實際上是“依序行事”。由於處理公務先要對相關事件做陳述介紹,這才慢慢形成了後來意義上的敍事。我們現在經常説的“講好中國故事”,其實就是回到了“敍事”即“行事”的初義:從字面上看,這句話説的是“講”好中國的故事,更深一層的意思卻指“做”好中國的工作。以此類推,“講”好某個城市的故事,也有“做”好該市工作的意涵在內****。此類表述的激勵作用,在於讓人意識到我們正在創造自己的歷史,正在用實際行動上演一幕幕時代大劇。正是這種把自己看成故事主人公的感覺,讓“講”與“做”這兩條平行線發生交會。薩特在其代表作《噁心》中也説:“一個人永遠是講故事者,他生活在自己的故事和別人的故事之中。”
明白了“講”與“做”之間的互滲關係,就會看到城市敍事是兩者協同互動的結果。城市形象固然需要通過媒體宣傳來“打造”,但用城市的實際發展來體現才更重要,這不僅是因為沒有“做”就無法“講”,更在於“做”本身就是一種無聲之“講”。英國分析哲學家J.L.奧斯汀提出過一種述行理論,**其中説到“作為”(perform)也是一種“表達”(utterance),這意味着“做”有時候就是“講”,“行事”與“敍事”之間沒有一條清晰的界線。**我們在現實中也看到,中國許多城市中發生的一切,如高樓大廈的拔地而起和道路交通的日新月異等,實際上都是在一頁一頁地譜寫城市建設的新篇章,向外界宣示自己的發展路徑,這些都可以看成城市對自己未來所作的“表達”。
由此可以得出這樣的認識,一座城市如果少有作為甚至停止作為,它便失去了自己的未來。借用語言學的術語來表述,城市敍事其實是有時態的,像倫敦這樣的城市儘管歷盡滄桑,但它總能在疫癘和兵燹之後浴火重生,因此人們説它“代表着進行時,至少,它代表着開始”。與此相反,有的城市雖然年輕卻發展乏力,像是進入了現在完成時。**這樣來看城市又有動靜之分,靜態的城市死氣沉沉、無事可敍,富有動感的城市卻有講述不完的新聞。**筆者所在的南昌市在2006年被評為國際十大動感城市之一,一道入選的還有幾座經濟表現並不是那麼搶眼的城市,筆者針對當時人們的納悶給出了一種解釋:動感城市就像是足球場上那種跑動十分積極但尚未建功立業的年輕球員,有經驗的球探之所以看好他們,是相信這樣的進取狀態總有一天會創造出奇蹟。
回眸與前瞻
**敍事一般指講述人的故事,城市敍事雖然以城市為講述對象,但講述者往往把它當作一種有生命的主體。**為莎士比亞、狄更斯和牛頓等作過傳的英國作家彼得•阿克羅伊德,給倫敦寫過一部《倫敦傳》,該書序章的題目便是“城市 如人體”。不過城市與人體有個根本性的不同:人類的血肉之軀抵禦不住時光的無情侵蝕,而一些經磨歷劫的城市卻似乎能與天壤共久,北京、南京和西安等古都已經成為中國城市中的常青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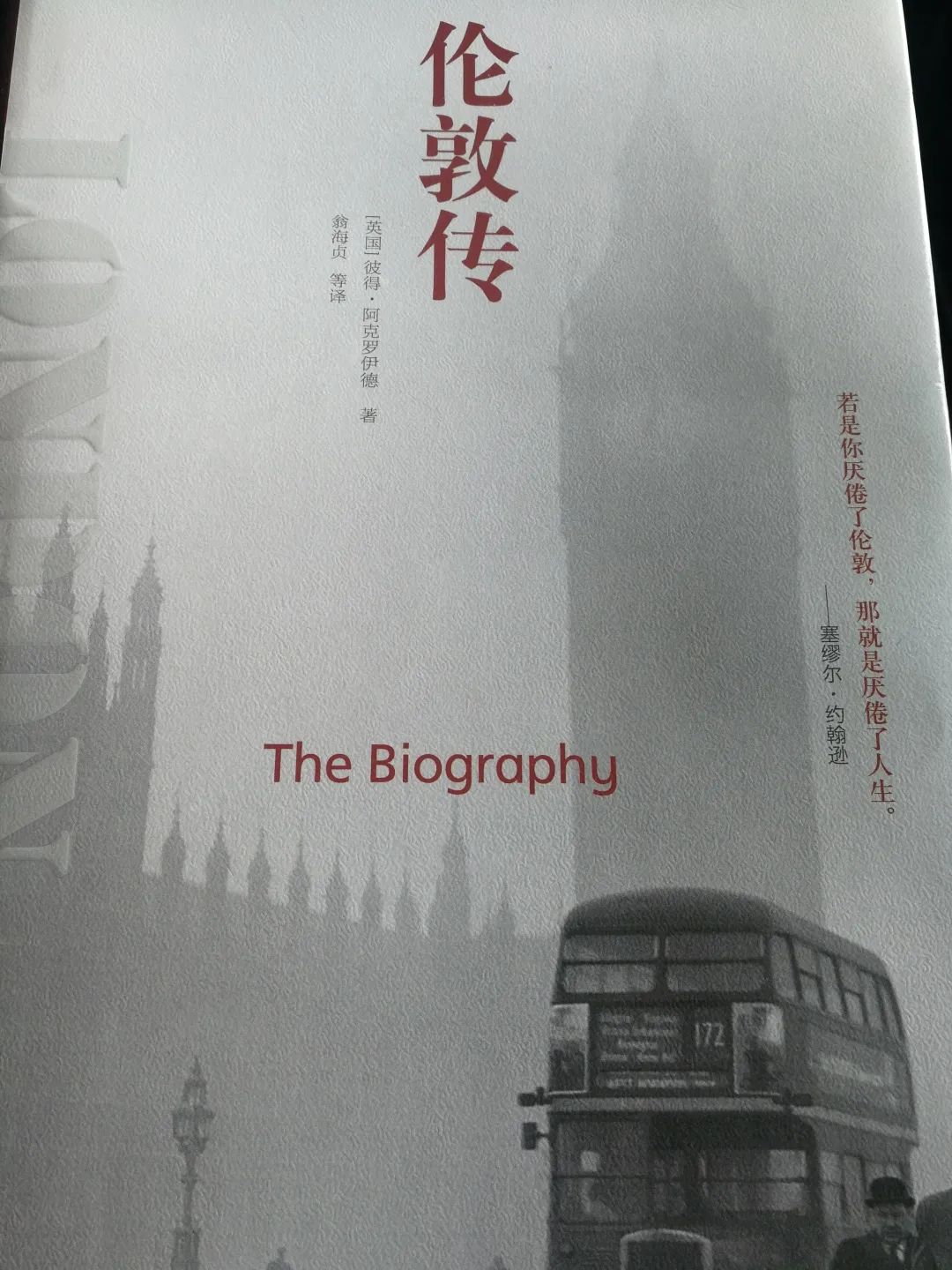
當然沒有哪座城市能真正做到長盛不衰,所有幸存下來的城市實際上都遭遇過各種挫折和失敗,只不過它們今日的榮光掩蓋了昔日的不堪。這些**城市之所以能完成一次又一次的重新崛起,應該説與其前瞻性敍事大有關係。**我們知道一位長者如果沉湎於回憶之中不能自拔,總在講述自己那點陳年往事,就不會為其晚年生活提供多少精神動力,但是如果他還在計劃做點什麼並付諸實際行動(這裏我們又一次看到敍事與行事難以分開),那麼,這樣的人還不能説真正進入了衰老階段。城市的情況也是如此,當一座城市不斷談論自己的發展目標和遠景規劃,特別是還有一場舉世矚目的重大活動列在議事日程上時(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為2008年奧運會、2021冬奧會之前的北京以及2010年世博會之前的上海),它會變得比往日更有活力、更加生氣勃勃。改革開放以來,不少城市就是憑藉這樣的活動讓自己的面貌煥然一新,更重要的是其內部凝聚力也因此大為增強。
正是因為看到了前瞻性敍事可以為城市發展賦能,筆者才特別贊成將南昌定位為“白鶴之城”。白鶴的繁殖地在西伯利亞凍土圈內,每年秋天全球白鶴的絕大部分都飛來南昌城外的鄱陽湖濕地越冬,因此地方誌上有白鶴仙女下凡洗浴並與當地人結親的記載,這個故事屬於亞歐非三大洲廣泛傳播的羽衣仙女傳説類型,學界一致認定它的起源地就在古代中國的豫章地區。②白鶴故事無疑發生在過去,講述白鶴之城的故事卻是面向未來的——江西省這些年確定了生態興省的發展方針,讓白鶴這種對棲息環境極為挑剔的鳥兒成為省會城市的logo,有利於彰顯江西生態環境的優越與贛鄱人民打造生態文明先行區的決心。南昌既有的城市敍事大多屬回眸性質,我認為當前亟需白鶴之城這種富有前瞻性的敍事,讓魚米之鄉的人們經常想到自己的明天。城市需要logo,也需要夢想,人類目前正面臨着由農業文明、工業文明向生態文明的過渡,江西的夢想和前景就是在生態文明建設中充當排頭兵,在全國率先走出一條環境保護和經濟發展相輔相成的新路。

“白鶴之城”南昌
有限與無限
但是筆者又不主張南昌只傳播白鶴之城這一種敍事,**每種敍事只能反映對象的一個側面,只展示某個側面等於強行把對象納入某個類別,符號化的後果是有限替換了無限,對象的其他側面通通都被遮蔽。**前面提到城市如人,我們知道要想在敍事作品中塑造出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需要講述一系列事件以激發某種人格特徵,如“撕扇子作千金一笑”等事件突出賈寶玉愛在女孩中間廝混,“火燒新野”和“草船借箭”等事件讓人欽佩諸葛亮的神機妙算,但如果僅憑這些就給他們貼上“娘娘腔”和“智術過人”的類別化標籤,對這兩個人物來説未免又有點不大公正(雖然現實生活中“賈寶玉”“諸葛亮”這樣的名字確實會被用作某類人物的標籤),因為他們並不是福斯特在《小説面面觀》中所説的扁平人物——《紅樓夢》和《三國演義》中還有大量其他類型的事件反映這兩人性格的無比豐富與複雜。如果一定要作歸納提煉,或許“率真任性”和“忠心耿耿”才分別是他們最有代表性的人格特徵。似此,城市敍事也應當迴歸事物的無限豐富性和複雜性,只有多側面、多方位,甚至是多維度的敍事,才能反映出一座城市的千姿百態與萬種風情。
從這個角度説,南昌與八一起義有關的英雄城敍事,與許遜治水有關的萬壽宮敍事(象徵洪水的孽龍被許遜鎖在鐵柱上),以及人們圍繞滕王閣、孺子亭和城中十大鄉賢路等開展的講述,都是城市敍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這些講述在筆者看來多多益善,它們把城市形象烘托得既細緻生動又豐滿厚實,人們正是憑藉這些領略到城市歷史的諸多細微方面,僅用幾個詞或幾句話無法達到這種效果。根據這一認識,**城市敍事不但有時態之分,而且還是一種複數形式的表達:一座城市的敍事可以説是以往無數講述的疊加與複合,各個時期的講述合起來成了一場為城市畫像的接力賽。**由於後人的畫筆永遠是在前人的基礎上塗抹,層累性成為城市敍事最明顯的特徵。毋庸諱言,層累性意味着越早的敍事越是會被層層疊壓,然而是金子總會閃光,有價值的集體記憶不管沉澱多深,總會被後人發掘出來賦予新的意義,就像前面提到的白鶴仙女傳説。那些未被髮掘和激活的也不能説完全被人們遺忘了,它們如同油畫上最先塗抹上去的油彩,每一筆都為畫面增添了厚度與密度。就此而言,每個講述過的故事都不可能是白講,除了少數特別突出的成為城市亮點之外,其他統統都會融入城市的背景與底色。
以上所論旨在顯示,城市中發生和講述過的一切,雖然可能被覆蓋或疊壓,但未來就是在這樣的基礎上生長,沒有人能想到自己生身立命的城市最終會被“畫”成什麼模樣。使用複數形式意在表明城市敍事具有多種可能性,人類有限的想象力無法窮盡城市所有的存在方式及其發展路徑。卡爾維諾有部小説名為《看不見的城市》,説的是走遍天下的馬可·波羅向忽必烈大汗講述他所看到的城市,忽必烈希望馬可·波羅能告訴他一些有限的元素與規則,憑藉這些他可以在頭腦中搭建起一座樣板之城,同時利用這些“常規元件”組合出各類城市。然而馬可·波羅告訴他,城市是由許多不確定、不合常理和不講邏輯的東西組成的,想象、偶然和機緣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很難從中找到什麼共同規律,因此他只能向大汗介紹一座座面貌各異的具體城市。卡爾維諾這篇小説簡直像是為今日的中國而寫,因為我們國家目前存在着嚴重的千城一面現象,許多新興城市就是搭積木般用有限的“常規元件”組合而成,有的城區管理者甚至比忽必烈還缺乏想象力——他們要求街道兩邊的店鋪招牌也必須採取統一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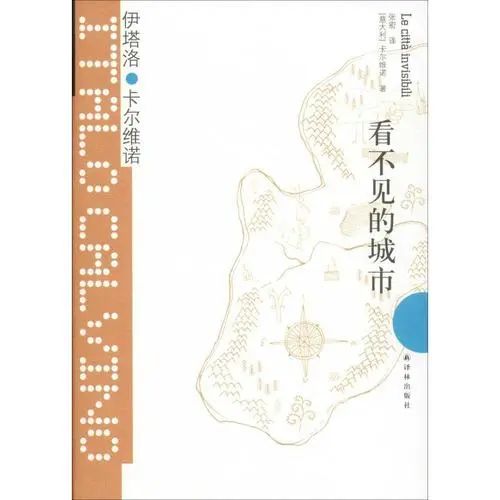
《看不見的城市》的最妙之處在於其結尾:忽必烈指責馬可·波羅講述了55座城市卻從未提到威尼斯,馬可·波羅卻説這些城市各自反映出威尼斯的一個側面,言下之意是他實際上並未忘掉自己的家鄉。**筆者理解馬可·波羅採用這種委婉敍述,是想表達樣板城市只包藏了有限的可能,而威尼斯這種理想之城卻能容納無限的可能——既然它有那麼多側面對應世界上的各個城市,那麼它就是一個萬象森羅、無所不包的城市集合體。**講故事在筆者看來是一個創造“可能的世界”(possible world)的過程,卡爾維諾更把自己的生花妙筆探向了“不可能的世界”,他給我們的啓示是每個城市都應當有儘可能多的側面或曰發展面向,只有包容一切可能性的城市才有前途無限的未來。《倫敦傳》最後一章名為“我將再起”,筆者願用該章最後一段話為本文畫上句號:“倫敦超越了任何邊界或者傳統。它包含了所有曾被説過的話、許過的願,所有曾被做過的動作、比劃過的手勢,所有曾表達過的或刺耳或高尚的宣言。它不可窮盡。它就是無限的倫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