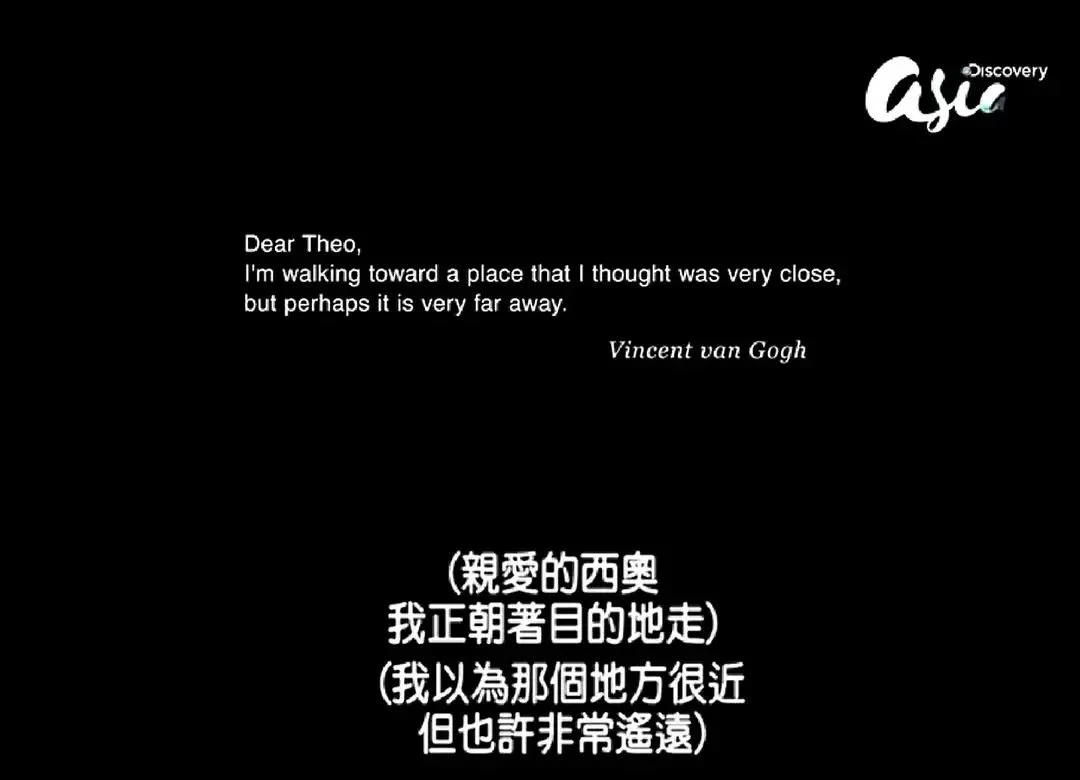靠“造假”月入過萬,他們被稱為中國梵高_風聞
心之龙城飞将-2022-12-28 00:14
鳳凰週刊
2022年12月27日 18:39:55 來自浙江

很難相信,這居然是藝術創作的場景——
幾個裸着上半身的畫工,在一間不算寬敞民房裏工作。
他們熟練調色,在畫紙上一筆筆添上自己分配到的工序,一幅新人工仿製名畫,就這樣慢慢完稿。

而他們周圍,屋內不算乾淨的牆面上,梵高的《星空》、《杏花》、《向日葵》,密密麻麻成堆懸掛着。

這間不大的屋子是他們的畫室,他們在這裏畫畫、吃飯、睡覺。
困了就席地而眠,醒來就繼續揮毫……

這裏就是深圳大芬,世界知名的仿製畫工廠。
成噸的藝術在這裏被複制,無數經典在這裏被量產。
2016年,一位荷蘭攝影師把這裏的故事拍成了紀錄片《中國梵高》。

這部電影只有幾千人看過,最近卻在網上掀起一陣新的波瀾。
有人説,這是一個流水線畫工精神覺醒的故事。
從臨摹走向原創,從生存走向意義。
很多人在主人公趙小勇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最懂梵高的人”
世界油畫市場中,80%的油畫來自中國。
而這80%中,有60%都來自深圳大芬村。
一羣畫工聚集在這裏,靠重複臨摹着名畫謀生。
趙小勇就是深圳大芬的一位畫工,與眾不同的是,他有一道隱形的卓著功勳:
他畫過10萬張梵高的畫。

趙小勇1996年就來到了深圳大芬,那時候油畫複製業方興,他成了這裏最早畫畫的一批人。
對當時的大芬畫工來説,畫畫並不是靈感的碰撞,而是一套新奇的生產範式:
這是一條高效的仿製畫生產流水線。

趙小勇和二十個人是一個整體,他們被分成三組,每組7個人,共同作畫。
他們每個人需要臨摹畫的一部分,也只畫這一部分,然後迅速交給下一個人,後者再在前面的基礎上完成自己的那部分畫作。
就像排隊傳遞東西,或者像工廠加工零件,一幅畫被拆解成局部,又組合成整體。

比如一幅《蒙娜麗莎》,每個人只需要臨摹其中的一個部位,一隻鼻子,或者一隻左眼——
連一雙眼睛都是由不同的人來完成的,因為這樣重複畫單一的片段,很快能讓畫工在最短時間內形成肌肉記憶,下筆飛快,成稿逼真。
這樣下來,一幅蒙娜麗莎,或許在一個熟練藝術家的筆下要一天才能復刻;
而這羣熟練畫工,他們一天可以臨摹十幅。
經過趙小勇們流水作業的作品,從大芬流入市場,遠銷海外,成為高級的“手工油畫”。
那些年,趙小勇們畫盡了梵高、莫奈、達芬奇,他簡單算了算:“畫了可能有三十萬張。”

現在,趙小勇已經有了自己的畫室,和自己的客户羣體。
他拉來妻子、弟弟和小舅,跟他一起畫梵高。
妻子擅長畫星空,小舅子擅長畫向日葵。
就這樣小作坊一般的工作室,已經臨摹出過十萬張梵高的畫作。

對於趙曉勇而言,這些年,梵高的畫早就在他腦內熟透了。
他畫了那麼多年,買過書,碟片,對着網上的高清圖研究許久,他畫梵高從來不用草圖,可以直接落筆,最多的時候一天能畫十張;
梵高畫的筆觸、每一抹顏色的明度和純度、每一個用筆的細節……他都爛熟於心。

徒弟求他教,周圍人學他,畫商青睞他。每年有很多訂單送到他手中。
趙小勇有荷蘭的客户,在盧浮宮旁邊有畫廊。
那些來自趙小勇的畫,遠渡重洋後會在這裏被展出,被買家反覆摩挲,然後被視若珍寶地搬回家。
像是一種神秘的期許和連結。
他從未見過真跡,他的作品卻被當作上等的藝術品展銷。
他沒有去過荷蘭,這裏賣的卻是他的作品。
他沒接觸過梵高,梵高已經成了他在這個世界上最熟悉的人。


離藝術遠,離生存近
大芬村村口有個標語牌,上書: “藝術與市場在這裏對接,才華與財富在這裏轉換。”
這被認為是對大芬村最好的詮釋。
像趙小勇一樣的家庭工作室,經常會出現這樣的場景:
人們坐在不同的畫布前,手裏只有一種顏色的顏料。
一幅風景畫,男人畫樹,女人畫天空,大孩子畫土地,小孩子畫花草,一家人流水線一般地完成一遍,再由大師傅統一調整。
末了,將一張張半乾的油畫晾在自家陽台上,遠遠看過去,大的像彩色牀單,小的像孩子的尿片。

大芬村的名頭漸響,學術界和藝術界對這裏的評判開始出現了。
專業人士批評這裏只是複製、毫無靈魂;
業餘人士認為這裏銅臭味太重、根本不配沾染“藝術”。
其實趙小勇最初來大芬,不是為了別的,就是單純為賺錢。
他的老家在湖南農村,因為太窮,連初中都沒上完就出來打工。

在老家的時候,趙小勇從來沒接觸過油畫,只是聽説深圳大芬有很多人畫畫,他想賺錢,想去試試。
如果如果把趙小勇的經歷拉遠看,他其實是“大芬奇蹟”這個代名詞的一枚齒輪。
上個世紀末,一位叫黃江的商人來到大芬。
他發現這裏毗鄰香港、交通便利,又地處關外、人工成本低廉,於是他租下了民房,帶領了一二十個工人,開始做起了油畫臨摹出口的生意。
一幅畫批發價格28元港幣,給畫師6元人民幣,賣到美國29美元,大家都能賺到錢。
黃江開始招募更多的年輕畫工,給他們培訓,讓他們臨摹,再將產出的一張張油畫,遠銷重洋。

就這樣,大芬村的名號打了出去,吸引了像趙小勇這樣的人。
曾經倒是也有專業院校的學生來到這裏。
他們每天抓耳撓腮構思原創,好幾天、十幾天才能畫一幅,那廂普通畫工一天能畫五六幅臨摹圖,結果掛上畫廊以後,臨摹畫和原創畫都賣300塊。

不同的付出,被標上的相同的市場價值,天平就會慢慢傾斜,很多藝術院校的人,住不過3個月就走。
反而在趙小勇眼裏,那種流水線式的集約工作場景,太適合他這種人不過:
“梵高的畫線條簡單,畫得快,農民扔下鋤頭就可以畫了,他活着的話要氣死了。”

留在這裏成為大芬畫工的人,過着簡單、魔幻、流水線一般生活。
有時趙小勇會接到急單。有荷蘭的客户,在40天內加急定了800張複製畫,他叮囑下去:“加一點班,安排安排時間畫完。”
幾十張畫紙被鋪開,十幾張梵高的畫像連成一條線,在赤膊的工人手裏,能做消消樂;
畫室是畫工們的全部活動空間,他們在這裏吃飯、畫畫,困了就席地而睡,打個盹再起來畫;
有新來的學徒抓形不準,被告知得改,得練,得重畫。

他們自稱“畫工”,也不説自己是藝術家,畫畫就像擰螺絲、上零件、焊電板一樣,是一件機械需要完成的工作,完成了就有飯吃、有錢賺。
這個不是為了藝術而生的地方,包攬了世界絕大多數的“名畫”創作。
這裏離藝術更遠,離生存更近。
閒暇時候,趙小勇會帶着小弟們看梵高的紀錄片。
黑暗裏煙霧繚繞,身旁掛着畫完的梵高,眼前是荷蘭的風光,畫工們咀嚼着梵高的一生,內裏有什麼東西開始悄悄鬆土。

畢竟即使開始的目的是温飽,畫了10萬張梵高之後,總會想摸到一些更高的東西。
有一天晚上,趙小勇夢見了梵高,夢見梵高問他,小勇,你現在畫我的作品怎麼樣呢?
趙小勇高興地説,我已經進入你的狀態了。
他開心地伸出手去,梵高不見了,趙小勇的夢也醒了。

從那時候開始,趙小勇開始有了新的夢想,他想出國,想去荷蘭,想看看梵高的真跡。
然而最現實的原因永遠是錢,路費很貴,開銷很大,工作室單子源源不斷,孩子還在上學。

趙小勇憋得太難受,實在沒轍,一家人只好去了一趟世界之窗。
他坐在荷蘭園裏,讓妻子孩子拍了很多張照。

在這裏,他似乎離世界很近,又好像離世界更遠。
雖然平替,但不解渴,反而有什麼東西鑽得更深。
趙小勇枕着自己的荷蘭夢睡着了,明天醒來,還有別的畫要畫。

夢醒
機會還是來了。在客户的邀請下,趙小勇一家人前往阿姆斯特丹,他終於能見到心心念唸的梵高了。
來到阿姆斯特丹的街上,趙小勇遠眺那些熟悉又陌生的街景,興奮而激動,這裏是真正的荷蘭,離梵高最近的地方。
他舉着手機四處拍照,突然發現了客户的店。
在櫥窗裏懸掛着的,不正是他曾經一筆一畫臨摹出的作品嗎?

趙小勇走進這個全是自己熟悉畫作的地方,卻隱隱感到失落:
合作那麼久,他一直以為客户開的是畫廊,自己的作品是被當作高端畫作銷售的。

趙小勇沒想到,這裏居然是一個人來人往、自由選購、和大芬一樣的,紀念品商店。
老闆倒是熱情地擁抱了他,説他的畫“如果和美術館裏的調換,別人肯定完全看不出真偽”。
趙小勇只有苦笑。
第二天,趙小勇終於去了美術館。
這次他終於能站在梵高的真跡面前,趙小勇反覆凝視咫尺之隔的畫作,杏花,夜幕下的咖啡店,自畫像……

趙小勇欣賞了很久很久,最後失望地説:
“顏色不一樣。”

顏色不一樣,什麼都不對。
他和美術館的保鏢聊天,説自己畫了20年的梵高。
對方很興奮,問他,那你自己有什麼作品?
趙小勇答不上來,因為他沒有自己的畫。

他的信念有些崩塌。二十年,他只幹了一件事,就是模仿梵高。
他原以為自己已經爐火純青已臻化境,站在大師真跡面前,明顯的巨大差距還是給他帶來了巨大沖擊。
他自認為心意相通,結果大師的畫在美術館受人瞻仰,自己的畫擺在紀念品銷售處。
就像一個取經路上的人,終於拿到了真經卷宗,才發現自己過往念出的每一個音節都不對。
趙小勇絕望了,他不知道自己要怎麼回去,以後要怎麼畫畫。

最後,兜兜轉轉,趙小勇來到了奧維墓園,他在梵高的墓碑前點了三根香煙,靜靜地看它們燃完,飛回了中國。


畫中即自己
回到大芬以後,迷茫的趙小勇久久不知道將自己的心如何安放。
“我到底能不能成為一個藝術家?”
“我到底有沒有什麼東西值得別人欣賞?”
直到有一天,他發現除了梵高的向日葵,他好像還會畫自己的馬蹄蓮。
即使顏色不如大師畫作悦目,形狀也不那麼準確,但這是自己的畫。
趙小勇開始畫原創了。
他的第一幅畫,內容就是那間畫室。

那間他用了十年的畫室裏,有成疊的仿製畫,有星空,有杏花,有學徒,有妻子,有梵高,也有他自己。
妻子指着畫紙,興奮地和他講,在這個角落發生過什麼故事,那裏曾經是她的“工位”……

他開始畫老家的巷子,畫年邁的奶奶。
趙小勇想明白了,畫一年也好,兩年也好,創造出一副放進了自己思想的作品就好。
“我的生活,就是我的藝術。”

鏡頭拉遠,聲音減弱,自畫像裏的梵高目光炯炯,眼神神秘鋭利,凝視着趙小勇的過去、現在、和未來。

《中國梵高》紀錄片的故事,到這裏就結束了。
當然,世界上沒那麼多童話故事,現實不會開金手指。
臨摹了20年梵高的趙小勇,即使幡然醒悟開始原創,也不會立馬躋身最偉大的藝術家之列,從此被業界敬仰。
趙小勇同樣不夠出名,《中國梵高》這部紀錄片只有6000人標記看過,他的個人主頁不到1萬粉絲,只有被來大芬村的遊客詢問時,街坊會説一句:
哦,他是之前那個“中國梵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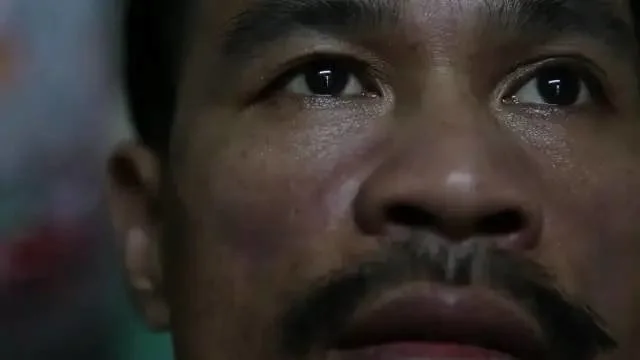
藝術品市場的殘酷現實是,沒什麼人願意花錢購買一個不出名畫家的原創作品。
紀錄片播出後的這6年,趙小勇逃離過大芬村,最終又回到了大芬村。
但是趙小勇,還在努力成為趙小勇:
有網友再訪大芬時發現,趙小勇已經是一位簽約畫家,他的主頁也掛着不少原創作品,有鄉景,有麥田,有人像,還有以《中國梵高》為主題創造的油畫。

有人説,《中國梵高》講的是一個藝術家精神覺醒的故事。
可我卻覺得,這個故事説的不只是藝術家。
生活中有太多這樣的“趙小勇”,做着重複機械的工作,為了生存奔波勞碌,是小鎮裏的做題家,也是人海中的打工者。
他們也曾在某個夜晚思考人生的意義,自我的價值,也曾舉目向上望去,試圖抬頭看一看梵高、摘一摘星空。
也許一輩子都無法追尋到答案,終一生也不會“功成名就”,但誰又能説這尋找的過程毫無意義?
電影結束了,生活還在繼續。
或許我們永遠也成為不了梵高,但是能成為一個“中國梵高”,已經是平凡生活的偉大夢想了。
畢竟,握着六便士的人,同樣可以仰望月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