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韋諾:香港“不問政治”,可以嗎?
【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梁韋諾】
前言
關注香港的讀者,相信都聽過“香港是個經濟城市”這句話。放眼全球,很少有城市會像香港般時常被稱為“經濟城市”。即使是與香港合稱為“紐倫港”的紐約和倫敦,也沒有這“待遇”。
“經濟城市”通常伴隨着一個具有相反意思的概念:“政治城市”。同樣地,除了香港,我們甚少聽到一個城市被稱呼為“政治城市”。“經濟城市論”者也常常把港人形容為不問政治的“經濟動物”。
“經濟城市論”者認為,香港本質上是個經濟城市,而非政治城市,批評迴歸後香港出現政治化,政爭內耗不斷,已由“經濟城市”淪為“政治城市”。
中央出手制定《香港國安法》和完善香港特區選舉制度後,“經濟城市論”者興高采烈地表示,香港終於重回“經濟城市”,並呼籲往後不要談政治。
政治與經濟之間的辯證關係
不難發現,“經濟城市論”者的做法,是先把“經濟”與“政治”截然分割開來,然後將“經濟”等同於穩定、團結、和平、理性、務實,再把“政治”等同於對抗、分化、暴力、不理性、務虛。久而久之,“政治”就被污名化,“政治化”也變成負面標籤。
香港的不少從政者,包括政治任命官員、議員、政黨人士,都彷彿患上“政治潔癖症”,將“政治”視作壞東西,紛紛迴避政治。當中最出名的,莫過於新民黨立法會議員容海恩的一句“議會內外都不應該牽涉太多政治”[1]。
事實上,“經濟城市/政治城市”這種二分是不能成立的。以筆者對馬克思主義的粗淺認識來看,政治與經濟,兩者既有區別,又存在着辯證關係,不可能截然分割開來。政治屬於建立在經濟基礎之上的上層建築範疇,經濟是政治的基礎,政治又反作用於經濟基礎。
恩格斯在致瓦·博爾吉烏斯的信中指出:“政治、法、哲學、宗教、文學、藝術等等的發展是以經濟發展為基礎的。但是,它們又都互相作用並對經濟基礎發生作用。”[2]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張宇認為,“沒有離開政治的經濟,也沒有離開經濟的政治。”[3]
因此,從來不存在“經濟城市”,也不存在“政治城市”,每一城市都必然存在着政治與經濟。
列寧進一步強調政治的主導地位和作用,指出:“政治同經濟相比不能不佔首位。不肯定這一點,就是忘記了馬克思主義的最起碼的常識……一個階級如果不從政治上正確地看問題,就不能維持它的統治,因而也就不能完成它的生產任務。”[4]
英殖時期的香港不問政治?
“經濟城市論”者認為,英殖時期的香港是個“經濟城市”,而港人就是“經濟動物”。他們相信,不問政治正是造就香港繁榮的關鍵;反之,“政治化”就是破壞香港繁榮的元兇。
孫中山先生指出:“政治兩字的意思,淺而言之,政就是眾人之事,治就是管理,管理眾人的事便是政治。”[5]香港這個有如此多人和事要管理的地方,又豈會不問政治呢?
“經濟城市論”者經常引用金耀基教授的“行政吸納政治”,認為在英殖時期,政治已被行政吸納,自然就不存在政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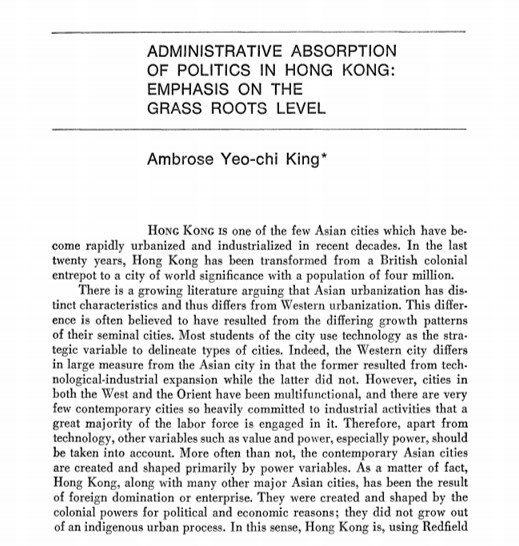
金耀基教授的“行政吸納政治”論文
強世功教授曾對這一理論作出精闢分析,指出:“‘行政吸納政治’這個動賓結構句式缺少了主語,只有把主語找出來,才能把真正的政治問題揭示出來。其實,誰都知道港英政府最大的政治就在於港督的殖民統治,這個政治是‘行政’無法吸納的。……香港政治的殖民性質就在於英國人的支配政治吸納了中國人的參與政治。”[6]
換言之,英殖時期的香港不是不問政治的,也不是不以政治為主導的,英國的殖民統治就是最大的、最根本的、主導着整個香港(包括經濟、社會各方面)的政治。經濟發展的方向、經濟利益的歸屬、社會民生改善與否,都是由殖民統治所決定的。
七十年代是“經濟城市論”者最為津津樂道的時期。他們相信,正因為當時整個香港都不問政治,才得以成功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形成繁榮安定的環境。
事實是,殖民政治一直主導着香港的經濟和社會發展。以七十年代為例,當時香港的經濟和社會發展,與英國的外交政治有着莫大關係。1974年5月,總督麥理浩在一份名為《管治香港的目標》的外交通訊中指出:
“我認為我們應該盡一切方法打造香港為一個達國際地位、具備高質素教育、科技與文化,以及有高水平工業、商業、財經設備的模範城市,以至在它身上中國既能得益,但又因為考慮到對這些實質利益的需要和本身國內條件之不同,而不願意把香港收回。”
“這可幫助爭取額外的時間,令中國的情況逐步演進,甚至影響中國政府令它考慮或者日後在其主權之下繼續給予香港的一個特殊地位,而這樣在一定程度可保障市民的生活方式和英國與其他國家在這殖民地的利益……”
“基於這些政治考慮,而無論如何我亦相信我們的政府會認識到上述意見本身的意義,我們會選擇發展香港為一模範城市。但我們應該低調進行,少説話,不對中國做出表面的挑戰。”[7]
李彭廣教授翻查當時的英國解密檔案,也發現英國政府“計劃以最短的時間,把香港各方面的發展和生活水平儘量拋離中國內地,並突出香港社會和制度的優勢,從而影響中國政府在處理香港問題的態度和政策。”[8]
同時,英殖推行社會改革,也與來自倫敦的政治壓力有關。香港製造業的成功發展,引起了英國工商界及工會的關注,他們批評香港欠缺勞工保障和福利使港商可以大幅減低生產成本,以低價將產品輸出外地,包括英國本土,損害英國工商業。

麥理浩,圖片來源:wiki
與工黨政府有密切關係的智庫“費邊社”發表《香港:英國責任》的報告,大肆抨擊香港漠視勞工權益。面對龐大的政治壓力,英國外交部1976年制訂《香港計劃書》,要求港府必須全力改善勞工福利。雖然麥理浩抗拒《計劃書》提出的大幅度改革,但為了滿足倫敦的要求,也開始大幅增加福利開支。[9]
因此,呂大樂教授指出:“‘麥理浩時代’及其管治的最大特點,不是不談政治,只重視行政管理,而是有十分清楚的政治目的。基於他的外交政治的考慮,他將香港社會經濟發展連繫到一個有目標、方向及中、長期考慮的框架。”[10]
英殖時期的香港,政治從來都主導着經濟和社會。所謂以經濟為主導、不問政治的“經濟城市”,只是英殖用以淡化和粉飾殖民統治的假象。
不是沒有政治,而是沒有民主政治
壟斷着政治權力的英國,一方面把極少數的華人精英吸納到體制內,另一方面把絕大多數的華人排除在體制外。
政治是管理眾人之事,而民主則是人民的統治、人民當家作主。換言之,民主政治就是人民能夠當家作主,有權參與公共事務的管理和決策。與此相對的,就是殖民者從人民手中剝奪政治權力、繼而壟斷政治權力的殖民統治。因此,英殖時期的香港不是沒有政治,而是沒有民主政治,殖民政治排斥了民主政治。
吳增定教授指出:“儘管極少數華人富商巨賈和權勢人物有可能幸運地獲得參政、議政的資格,但絕大多數華人則被排除在政治之外,淪為純粹‘經濟的動物’。”[11]
吳教授用上“淪為”二字是極之準確的,他指出了港人不是天生不理政治,而是被英殖剝奪了政治權力,導致他們在體制內幾乎無渠道參與政治,漸漸形成一種儘量不問政治的社會氛圍。
事實上,“經濟動物”這一形象不是一件光彩的、值得褒獎的東西,而是殖民統治創造的不正常、不健康的產物,也是精神文明低下的表現,是造成港人對政治無知的重要原因之一。
雖然港人長期被排除在體制外,但不代表他們完全沒有參與政治的意欲和行動。
林蔚文教授通過對1949至1979年各大報章對社會政治活動的報道的梳理,發現這段時期香港出現的社會政治活動頗為活躍,五十和七十年代均發生了約二百次社會政治活動,而六十年代也有百多宗社會政治活動,更遑論1966、67年出現的兩次大規模的反殖抗爭行動。[12]

香港“六七暴動”時的英國士兵,圖片來源:wiki
只不過,由於當時的政治活動受到英殖的嚴密監控和打壓,參與者常將自己包裝成政治中立者,強調進行的是無關政治的自發行動,但沒有改變這些活動本身所包含的政治性。
的確,二戰後大量內地移民為逃避戰亂和政治運動而來港,形成“移民社會”。既然這些內地移民是為避開政治運動而來港,自然對政治大多采取疏離和冷漠的態度,而且他們不以香港為家,只視香港為“借來的地方”,自然也無心關注本地政治。
然而,在冷戰氛圍下,國共及第三勢力一直在香港進行大量政治活動,社會也存在各種政治主張和思潮,只不過受到英殖的嚴密監控和打壓。
英殖可能希望香港永遠是個“經濟城市”、港人永遠是“經濟動物”,但到了六十年代,在香港土生土長的“嬰兒潮”一代,對香港產生一種歸屬感,視香港為家,開始關心本地政治。
七十年代,隨着經濟及社會發展,港人蔘與政治的意識、訴求和行動日漸增加。假如將政治化狹義地理解為大眾的政治參與,當時香港社會已經開始政治化了。
金耀基教授在提出“行政吸納政治”的同一篇文章中指出:“今日,香港不止是一經濟城市,也是一政治城市,更多的大眾,特別是年輕的知識人,對政治的關注已漸漸增高,他們的香港的認同亦漸漸加深。”[13]
當然,筆者不同意金教授這種經濟城市和政治城市的論述,但他確實承認了香港的政治化趨勢,當時正值被視為香港經濟起飛的繁榮期,而這種政治化趨勢與經濟繁榮狀態是並存的,這個情況卻偏偏被熱衷引用金教授觀點的“經濟城市論”者所忽略。
為了應對這個政治化趨勢,英殖也大大加強對大眾的政治工作。最明顯的,是1968年反英抗暴被鎮壓後成立的民政主任計劃,在港九市區設立民政署,內置民政主任。
表面上,民政主任負責的是民生事務,但他們實際上進行大量政治工作。當時負責推行民政主任計劃的華民政務司何禮文在計劃正式推行後一再強調:“民政主任是‘政治事務官’,因此,民政主任不但要‘儘量與所屬地區內的市民保持聯繫’,也要‘評估政府政策的整體影響’,以及‘向普羅大眾解釋這些政策,和政府在處理這些難題上的成效’。”[14]
1982年地方行政計劃推出後,英殖更把新界理民府和港九市區民政署兩套制度二合為一,改稱為政務處,主管為政務專員,並由政務總署統籌,下分港九政務署和新界政務署。
因此,“香港是不問政治的經濟城市”、“港人是不問政治的經濟動物”,這都是英國殖民統治建構出來的假象。
政治發展出問題,還是政治本身是問題?
迴歸二十多年,香港的政治發展無可否認出了問題,政治生態不斷惡化,政爭嚴重阻礙發展經濟和改善民生。“經濟城市論”者會問,這不就是“政治化”的惡果嗎?
首先要弄清的,是政治發展過程出了問題,還是政治本身就是問題。這兩種觀點會引申出截然不同的結論。假如認為是政治發展過程出了問題,那我們的工作,就是對政治發展過程作出修正和調整。假如認為香港是經濟城市,不是政治城市,應該不問政治,那就要馬上展開去政治化,只搞經濟,不問政治。
如上述,六、七十年代起,隨着港人的歸屬感和社會經濟發展,港人的政治意識日益增加,“政治化”已經是不爭的現實。“九七回歸”更是推進香港政治發展的最大因素。
《白皮書》強調,迴歸祖國開啓了香港民主的新紀元。在文章《香港需要怎樣的民主理念?重新認識“民主迴歸”》中,筆者也曾指出:“百多年前英國侵佔作為中國土地的香港,實行殖民統治,導致在香港的中國人民淪為被統治者,這樣又何來民主可言?因此,迴歸象徵着中國恢復對港行使主權,結束英國殖民統治,讓中國人民重新當家作主。”香港迴歸祖國必然改變殖民統治,讓在港的中國人當家作主,參與管理人民的事務,使民主政治取代殖民政治。
因此,政治化是必然的趨勢,也不一定是壞事。關鍵在於,政治發展是否有序平穩。
《白皮書》指出:“英國殖民統治不但沒有給香港帶來任何真正的民主,反而為香港迴歸祖國後民主的發展埋下了禍根。”所謂“禍根”,是英殖在迴歸前夕引入開放式競爭性選舉。這就是導致迴歸後香港政治發展出現問題的主要原因。
引入開放式競爭性選舉的惡果,在於其導致各方都將選舉政治等同於民主政治,將選舉的開放及競爭程度視作量度民主程度的唯一指標。
迴歸後,香港的選舉政治不斷發展,選舉的開放及競爭程度不斷提高,加劇社會撕裂及對立,開放程度之高,甚至誇張到可以任由反中亂港分子,通過開放的選舉進入特區的管治架構。
選舉政治劣化所導致的亂象,相信無須筆者花篇幅作具體介紹。換言之,不是政治及政治發展本身是問題,而是政治發展過程中,出現了引入開放式競爭性選舉所導致的唯選舉論,以及否決政治、激進政治、暴力政治及民粹政治。
香港政治問題的核心:力量對比問題
從根本上説,香港政治問題的核心,不是有沒有政治、談不談政治的問題,更不是政治、政治矛盾和政治鬥爭出現與否的問題,而是在政治鬥爭之中的力量對比問題:誰掌握了香港的政治領導權(hegemony)和政治話語權(discourse of power)?誰主導香港的政治發展?是中央、特區及愛國勢力,還是外部勢力與反中亂港勢力?
事實上,英殖引入開放式競爭性選舉,目的都是“企圖把香港變成獨立或半獨立的政治實體,阻礙中國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並實行有效管治,延續英國對香港迴歸後的政治影響。”[15]
因此,迴歸二十多年,香港政治發展出了問題,關鍵是在中央授予高度自主權的情況下,特區及愛國勢力未能實際上(不是名義上)掌握政治領導權和政治話語權,無法確保香港政治有序平穩發展,也無法確保我方的政治思想在意識形態中占主導地位。
造成這個現象的因素很多,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我方長期不問政治、迴避政治的態度。已故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劉乃強指出:“香港的亂局,並非出於我們講政治,而是自己多年不講政治,讓反對勢力大講政治。解決方法是我們也講我們的政治。”[16]換言之,問題不在政治或政治化本身,而是我方沒有搞好政治,沒有牢牢掌握政治領導權和政治話語權。
揮之不去的政治問題
2019年“黑暴事件”後,中央出手制定《香港國安法》和完善香港特區選舉制度,香港政治生態大變。“經濟城市論”者認為,香港自此便重回“經濟城市”,無需再理會政治。
的確,中央運用法律和行政手段,成功將反中亂港勢力壓下去,改變了雙方的力量對比,但不代表自此一勞永逸,無需要理會政治。事實上,中央強調“愛國者治港”,從硬性的法律及制度建設,到軟性的愛國主義教育,都是在重新確立基本的政治原則。
政治、政治矛盾和政治鬥爭必然長期存在,這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而鬥爭雙方的力量對比關係在不斷和迅速地變化着。此消不一定彼長。況且,在“港人治港”下,香港的從政者總不能期望凡事由中央出手解決。這意味着治港者有很多政治問題要處理,有很多政治工作要做。
現在,反中亂港勢力雖然被壓下去,但香港社會民情基本不變,支持或同情反中亂港勢力的港人實際上仍不在少數,如果加上“中立”的,甚至要超過半數,反中亂港勢力則伺機而動。
“顏色革命”之父吉恩·夏普指出:“在民眾感到無能為力和恐懼的情況下,最初交給公眾的任務必須是低風險、建立信心的任務。這類行動——例如以不同尋常的方式穿衣——可以公開表達異議,並給公眾一個以引人注目的方式參與異議行動的機會。在另一些情況下,可以以(表面上)比較次要的非政治性議題(例如爭取安全供水)作為集體行動的焦點。戰略家們應當選擇這樣的議題:其價值能夠得到廣泛認可而又難以拒絕。在有限的運動中取得勝利不僅能解決具體的不滿,還能使民眾確信他們真正擁有潛能。”[17]
吉恩·夏普相信,這類行動“有助於確保取得一系列勝利,不僅對士氣有利,也有助於在長期鬥爭中逐步增加自己的優勢,轉變力量對比。”[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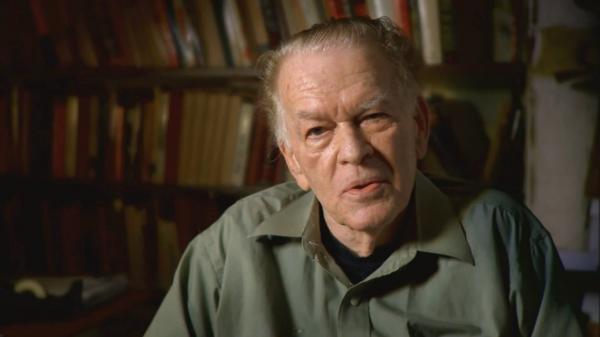
吉恩·夏普,圖片來源:prio.org
從反中亂港勢力對於野豬問題及防疫抗疫工作的宣傳炒作,包括呼籲市民拒絕接種疫苗和使用“安心出行”應用程序,以及將撲殺倉鼠的措施説成是“大屠殺”,可以看到他們的行動相當符合吉恩·夏普的“政治反抗”策略,利用看似非政治性議題進行政治炒作。
而且,外部勢力不會停止打“香港牌”,必定會繼續利用香港抑制國家發展,繼續“搞局”。因此,政治鬥爭肯定不會消失,而政治工作、對治港者的政治要求,包括政治判斷力、政治領悟力、政治執行力,以及對政治人才的需求(而造成香港政治人才匱乏,正是英國的殖民統治),也肯定不會比以往少。香港的部分從政者如果繼續過去那種不問政治的態度,恐怕會再次釀成錯誤。
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以至抗疫都是政治問題
習近平總書記既強調“民心是最大的政治”[19],也強調“民生是最大的政治”。可見,民心與民生這兩個“最大的政治”是相通的、統一的。
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是爭取民心的重點,表面上是非政治性議題,但本質上就是政治:
宏觀而言,經濟向什麼方向發展、民生要惠及那些民眾,這些都是政治。例如,港府與愛國陣營經常強調香港要“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但何謂“國家發展大局”?如何融入?融入的目的是單純以自身利益出發去“佔便宜”,還是為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努力?面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又該如何應對?這都是政治問題。[20]沒有思想政治引領,欠缺政治思維,經濟發展就會迷失方向;
微觀而言,處理經濟民生問題,當中牽涉不同持分者和利益集團,如何處理各方力量之間的關係和矛盾,如何化解各種阻力,這也是政治。不問政治、空談經濟,是不可能做好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的。
哪怕是現時面對來勢洶洶的新一波疫情,特區政府的抗疫路線到底是選擇內地的“動態清零”策略,還是選擇西方的“與病毒共存(實為‘對病毒躺平’)”,特區政府的抗疫措施是選擇向內地學習,還是選擇繼續抗拒內地的防疫做法,這些都是政治問題。
事實上,現時香港就有些人以“抗疫政治化”為由,揚言關於香港抗疫策略的討論變得“政治化”和“意識形態化”,批評“動態清零”是不科學、不切實際的政治口號,從而鼓吹“與病毒共存”;也有些人十分抗拒內地的抗疫做法,揚言“若全部由內地派員來港處理,更可能打擊一國兩制”。假如不正視這些政治言論,任由其發酵,將會繼續影響社會和市民,不利特區政府的抗疫策略及工作。
抗疫當然有很重要的科學因素,但不是1+1=2那般“純粹”,而是政策的選擇。選擇某種政策,就有可能要民眾讓渡某些權利,採取另一種,則可能讓更多的人健康受損,甚至失去生命,也可能導致長期不能與內地順暢通關,引發更多經濟民生問題,這些孰輕孰重的判斷,怎麼不是“政治”?
民主政治發展可能引致的政治問題
《白皮書》指出,“一個政治民主、法治健全、自由開放、包容和諧、繁榮穩定、胸懷祖國、面向世界的香港必將更好地呈現在世人面前”,這顯示了中央沒有否定民主政治,認為只是民主政治的發展過程出了問題,而非民主政治本身是問題。
作出調整後,中央仍然肯定民主政治發展,強調發展香港民主政治的目標和決心不變。這意味着治港者將會繼續面對民主政治的發展會導致的各種政治問題。
如上述,香港政治問題的核心是力量對比問題。中央、特區及愛國勢力實際上能否掌握政治領導權是重中之重。然而,民主政治的發展過程可能引致的各種政治問題,如果不好好處理,便有可能對社會造成不穩,成為對力量對比產生變化的因素。
首先,民主政治的意思,是人民當家作主,有權參與管理公共事務。讓人民羣眾“弘揚主人翁精神,發揮主體作用”,積極主動參與選舉、協商、決策、監督等,在各個層級、各個領域參與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的管理,是民主政治不可或缺的元素。民主政治的發展需要民眾廣泛的政治參與。
然而,面對着過去英殖對港人的影響(包括對政治無知,以及對開放式競爭性選舉的迷信),加上社會民情基本不變的情況,如何在促進民眾的政治參與意識,發展民主政治的同時,確保民眾有序參與政治,使民主政治有序發展,這就是政治問題。
更重要的是,《白皮書》提到“中央政府將繼續……為最終實現行政長官和全部立法會議員由普選產生的目標而共同努力。”這意味着,中央仍然肯定普選,仍然把實現雙普選視為香港民主發展的“既定方向”[21]。
如何處理普選的開放性及競爭性與社會穩定性之間的矛盾,如何管控選舉政治的發展,如何處理香港社會、因過去引入開放式競爭性選舉而產生對選舉民主的根深蒂固的迷信,這都是一連串需要面對的政治問題,考驗着治港者的政治智慧。
然而,無論如何,期望香港能重回“經濟城市”、期望港人重新成為不問政治的“經濟動物”,不單隻不符現實,而且與民主政治相違背。
結語
“香港是個經濟城市”,這已是老生常談。不過,政治與經濟本來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辯證關係,不可能將兩者截然對立開來,也不存在所謂的“經濟城市”或“政治城市”。
2019年後,中央將反中亂港勢力壓下去,改變了雙方的力量對比,但不代表自此無需理會政治。政治、政治矛盾和政治鬥爭會長期存在,鬥爭雙方的力量對比在不斷和迅速地變化着,而經濟民生本質上也是政治,意味着治港者仍有很多政治問題要處理,有很多政治工作要做。面對政治、重視政治,不但不是壞事,而且是必須的,因為我們根本無法迴避政治。
最後,本文謹以毛澤東同志的一段話作結:“政治向經濟的統一,政治和技術的統一,這是毫無疑義的,年年如此,永遠如此。……不注意思想和政治,成天忙於事務,那會成為迷失方向的經濟家和技術家,很危險。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經濟工作和技術工作的保證,它們是為經濟基礎服務的。思想和政治又是統帥,是靈魂。”[22]
註釋:
1. 沙半山:“【政壇諸事町】容海恩金句成熱話 自抽:唔講政治都要譴責許智峯”,《香港01》,2018年5月1日。
2. 《恩格斯致瓦·博爾吉烏斯》,1894年1月25日。
3. 張宇:“深刻把握社會主義條件下經濟與政治的辯證法”,《人民日報》,2016年12月15日。
4. 列寧:《再論工會、目前局勢及托洛茨基同志和布哈林同志的錯誤》,1921年1月25日。
5. 孫中山:《民權主義第一講——三民主義》,1924年3月9日。
6. 強世功:《“行政吸納政治”的反思》,2014年12月13日。
7. 呂大樂:《那似似曾相識的七十年代》,中華書局(香港),2012,頁154。
8. 李彭廣:《管治香港:英國解密檔案的啓示》,牛津大學出版社:香港,2012,頁62。
9. 呂大樂:《那似曾相識的七十年代》,中華書局(香港),2012,頁161-165。
10. 呂大樂:《那似曾相識的七十年代》,中華書局(香港),2012,頁182-184。
11. 吳增定:《行政的歸行政,政治的歸政治》,《二十一世紀》2002年12月號總第七十四期。
12. Lam Wai-man, Understanding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Hong Kong: The Paradox of Activism and Depoliticization (Armonk. NY: M. E. Sharpe, 2004).
13. 金耀基:《行政吸納政治:香港的政治模式》,《香港之發展經驗》,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5,頁15。
14. 曾鋭生:《管治香港:政務官與良好管治的建立》,牛津大學出版社,2007,頁82。
15.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一國兩制”下香港的民主發展》白皮書,2021年12月。
16. 劉乃強:《宣傳愛國要從反殖入手》,2016年8月21日。
17. 吉恩·夏普:《從獨裁到民主——解放運動的概念框架》,1993年。
18. 同上。
19. 習近平:“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學習時報》,2015年8月3日。
20. 邵善波:“香港是如何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信報》,2022年1月20日
21. 張勇:“‘雙普選’”仍是香港民主發展既定方向,《星島環球網》,2021年3月30日。
22. 毛澤東:《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1958年1月31日。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台觀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關注觀察者網微信guanchacn,每日閲讀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