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衞·保羅·戈德曼:中美文明起點不同,但應該互相理解
【文/大衞·保羅·戈德曼 譯/李碧琪】
文揚教授最近寫了一本新書:《文明的邏輯:中西文明的博弈與未來》。該書指出,中國五千年的文明不能用西方的標準來理解,也不能用西方的標準去評判。相反,它是一種自成一格的現象,有自己的歷史、邏輯和自我理解。
中國和西方的差異是如此之深,以至於西方人很難理解。對西方人來説,文明專指西方文明,是希臘哲學、羅馬法和希伯來啓示錄的產物。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直到18世紀末也是最富裕的國家。但是,在孟德斯鳩、黑格爾、約翰·斯圖亞特·密爾和馬克思等各種各樣的西方思想家所宣揚的一種觀點看來,它被看作是一潭反常的死水,從來不變的實行“東方專制”的地區。
20世紀的美國對中國的看法帶有基督教傳教士的印記,他們認為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需要救贖的靈魂聚集地。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提出的在全世界宣傳美國民主的計劃,在主導美國東亞政策制定的基督教傳教士身上找到了向中國宣傳的辦法。在俗世中,這種新教對中國的看法轉變為美國人的共識,即隨着中國在21世紀初變得更加繁榮,其政治制度將演變為類似於美國的民主制度。中國未能達到美國的期望,讓美國的期望落空,這是如今中美摩擦的一個重要原因。
作為中國頂級的文明理論家,文教授提出了截然相反的觀點:文明首先是一箇中國問題,而不是一個西方問題。中國文明已經延續了5000年;相比之下,1000多年前入侵的蠻族與羅馬帝國的殘餘相遇時,西方的民族國家才剛開始形成胚胎。直到500年前簽訂《威斯特伐利亞條約》,西方民族國家的法律基礎才得以形成。文教授寫道,將文明史與西方歷史等同起來,忽略了中華文明在更長時間內的持久性和延續性。
西方人會發現文教授的論述具有挑戰性。自從西方從羅馬帝國的廢墟上產生以來,它自身的生成原則是普遍主義的,那種存在着根本上不同的文明模式的説法與西方的自我理解是相悖的。從某個十分不同的角度來説,中國的文明也是普遍主義的。
中國還有兩個特點使其龐大而多樣的人口融合在一起:考試製度的擇優錄取,以及國家基礎設施。對此,萊布尼茨非常敬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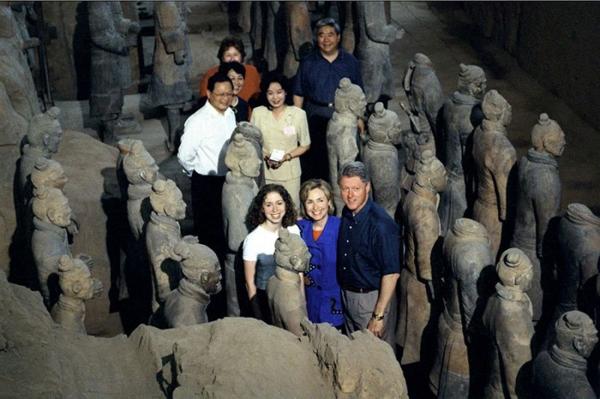
1998年6月美國總統克林頓參觀秦始皇兵馬俑(來源:人民網)
中國的地理環境使得中央集權的國家不可或缺。美國的建國文件從“自然和自然之神”所賦予的個人權利出發,將國家視為個人為相互保護和利益而自由同意的契約,並以每個人自己追求幸福的方式、説出自己的想法,以及在公共實體的最低限度干預下生活的權利為限。而在中國,有國才有家,國家是所有人幸福生活的前提條件。
正如文教授所強調的那樣,中國濃縮了幾千年的定居經驗;中國人是一個定居的農耕民族,已有近四千年的歷史,而今天西方人的祖先——哥特人、匈奴人、維京人、斯拉夫人和其他在羅馬帝國崩潰後來到歐洲的人,仍然是移民。如果説中國是定居文化的縮影,那麼美國則是遷徙文化的典範。
我們的文化充斥着這種經驗,從我們的民族小説《哈克貝利·費恩歷險記》及其只能重新開始的旅程,或弗雷德裏克·傑克遜·特納關於邊疆的文章,或斯蒂芬·文森特·貝內特1943年的史詩《西部之星》及其開頭的格言“美國人總是在移動”,都可以看出我們文化的這一特徵。好萊塢使向西部的遷移成為救贖的隱喻,如約翰·福特1939年的電影《驛站》。在美國的旅程中,重要的不是目的地,而是旅程,而這一旅程從本質上講是無法到達目的地的,因為在地球上找不到天堂之城。
文教授對西方代表一種文明規範的觀點進行了抨擊。他是完全正確的:文明的規範,如果我們所説的“規範”是指最常見的結果,那就是滅亡。語言學家估計,自人類誕生以來,地球上有近15萬種語言;其中有幾千種語言仍在使用,這個數字在一個世紀左右就會減少到幾百種。但中國甚至違背了這種規範性的定義;它的定義不是口語,而是一種書面語言,它傳達的意義不是通過聲音—意義的關聯,而是通過視覺表現。
文明必須找到方法來同化講不同語言的無數部落。美國在過去解決了這個問題,將移民同化為具有共同語言的共同文化,這樣一來,祖輩生活在波蘭或越南的美國人仍然分享林肯所説的“記憶的神秘和絃,從每一個戰場,每一個愛國者的墳墓,延伸到每一個活生生的人和家庭”。它是否會繼續這樣做還有待觀察,現在美國正受到理論家的攻擊,他們聲稱美國的建立是為了促進非洲奴隸制和其他形式的帝國壓迫。
中國從黃河流域的小文明發展到包括整個領土,囊括從西部的沙漠和喜馬拉雅山,南部的叢林,北部的冰凍荒原,到東部的海洋。它吸收了使用六種主要語言和三百種小眾語言的人民。
在這方面,中國和美國的共同點比其他任何兩個國家都多。它們找到了將不同民族融入一個共同政體的解決方案,儘管採取的是截然不同的手段。但是,這些解決方案是如此的不同,以至於產生了兩種文化,並導致了溝通上有很大的困難。
文教授在“定居”的中國文明和“遊居”的西方文明之間劃出了一條明線。他寫道:“當使用‘定居’和‘遊居’來對不同文明進行概括,指的是這些文明在整個文明史的尺度上看的一個總的性質。舉個例子,比如概括兩個人的不同人生,説一個人是‘流浪者’的一生,另一個人是‘坐地户’的一生,意思就是前者一生的大部分時間都在四處流浪,後者一生的大部分時間都未離開過本地……‘流浪者’的一生與‘坐地户’的一生就是截然不同的兩種人生,兩個人的人生經驗和感悟,各自的性格、氣質、舉止甚至相貌,都會有顯著差別。若‘流浪者’的流浪生涯主要是打家劫舍、殺人越貨、霸佔他人家園,那就更是如此了。”
文教授認為,中國是一個“定居文明”,而“西方、東正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文明是遊牧文明或移民文明”。“在中華文明方面,從5000年的尺度上和這個文明的主體部分來看,都是連續定居在以中原地區為中心的一個近乎圓形的地理範圍內的。而今天所説的西方文明則完全不同,這個文明實際上是在舊文明的廢墟上重新滋生出來的一個第三代文明,而它的起源、生長和壯大無不伴隨着整個社會的大規模遷徙和入侵,所對應的重大歷史事件分別就是公元5世紀前後的蠻族入侵羅馬帝國、11-13世紀的‘十字軍東侵’和15世紀之後的大航海和新世界大殖民。在這個文明從誕生至今的整個文明歷史上,這三次大遷徙就是它的主線,被利奧波德·蘭克概括為‘三次深呼吸’,這也是它區別於中華文明從來沒有整體上離開過原居地這個定居歷史的最顯著之處。”
他總結道:“除了中華文明,佔據了世界上大部分地區的其他幾大文明都不是在連續的、大規模的定居農耕歷史中形成的,都在文明出現之後的很長時期內仍然延續着史前人類遊居採獵生產生活方式;從古代中國人的角度看,都是周代時期‘四夷’的同類。因為關於蠻族的定義正是由最早發育出社會複雜性和成熟文字系統的定居社會給出的,從連續的定居農耕社會的角度看,居無定所、長期遷徙的遊居社會,無論是騎馬民族還是海上民族,都是蠻族。古代中國人將這類社會統稱為‘行國’,屬於‘夷狄’,區別於中國‘華夏’這樣的‘居國’。”
文教授認為,“定居”的中國文明和“遷徙”的西方文明在與周圍世界的接觸方面存在根本差異。西方人應該讀讀《文明的邏輯》這本書,仔細聽文教授的話,努力用他的眼光看中國。
(本文發表於2022年3月1日《中國日報》網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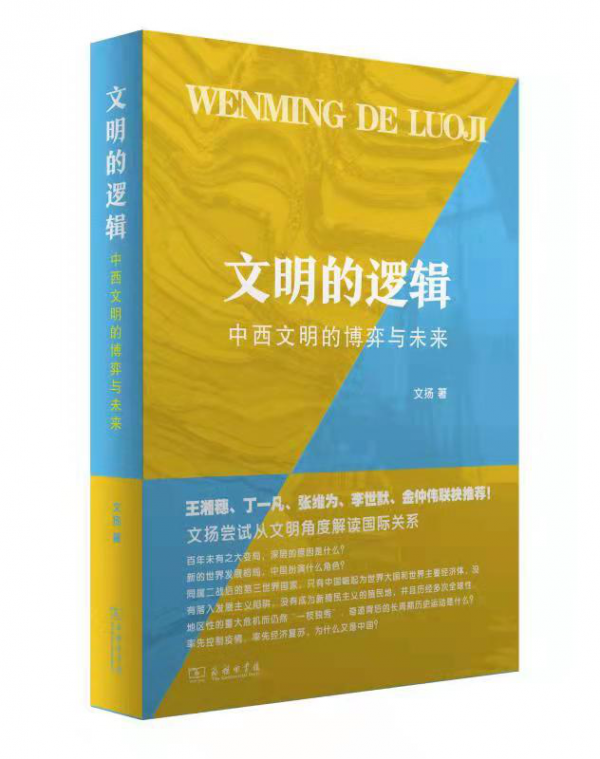
《文明的邏輯》,文揚著,商務印書館出版
圖書鏈接:http://product.dangdang.com/29317638.html
https://item.jd.com/10039153698103.html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59561187986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台觀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關注觀察者網微信guanchacn,每日閲讀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