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睿:台灣強推“雙語”與國際接軌?這是文化自我殖民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王睿】
近日,明清史學者徐泓老師在社交媒體感嘆:“台師大瘋了,中文系開全英語課程!同理,英語系應開全中文課程?”
其實,台灣師範大學今年2月還有另一項創舉,那就是以台語(閩南語)、馬祖語(閩東語)、客語、原住民語(高山族語)或台灣手語等“本土語”授課的教師,將獲得50%的課時費獎勵,等同現行英語授課獎勵的規模。
也就是説,無論用什麼語言,也無論教學雙方是否同意,總之中文普通話是不受優待的教學語言。
粗糙推行的“雙語”政策
為了“2030雙語國家”的夢想,台灣教育部門指定台灣大學、台灣師範大學、成功大學、中山大學等四所高校為重點培育的“標竿大學”。

截圖來自徐泓老師微博
其目標是2024年至少25%的大二學生英語能力達到CEFR(歐洲共同語言參考標準)的B2(中高級)以上,同時其當年所修學分的20%以上為EMI(全英語課程)。到2030年,則要求上述學生英語能力(CEFR)B2和EMI修習的比率都達到50%。
問題在於,CEFR的能力級距過寬,B2在歐洲是中學生的等級;在歐洲以外國家的英語檢定標準,則多不是以CEFR為基礎。何況,即便這四間重點大學在2030年能達標,又如何保證已經必修“本土語”的台澎金馬中小學生在未來8年的“雙語”能力?還有扣除學生之外的社會羣眾,如何在8年內同步邁入“雙語國家”的水平?B2和50%,真是“雙語國家”的標準?
台灣教育部門自去年起計劃在4年內投入400億台幣,聲稱“2030年全面達到雙語教育環境”。除了預告上述大學的英語能力之外,同時推出“高中雙語實驗班與國外姊妹校在線教學計劃”,而且限定“五眼聯盟”的學校為簽約對象,據説因此有93校申請參加。不過,雖然是“主動相親”、“倒貼”,但因時差問題而起早貪黑、相處困難,自今年暑後又開放為62個能通英語的國家就行。
如此草率、粗糙的算法和作為,難道不是以語文教育和獨尊英語為籌碼,來交換某種政治連結?否則所謂“國際化”,為何侷限於美國隊和英語?若只是為了提升台灣學生的英語能力,參照新世紀以來台灣小學“本土語”課程的實踐結果,那只是大量虛應其事、排擠效應和漢語中文能力低落而已。
原因很簡單,語言環境不足而強行製造浸潤式學習,必然因為脱離現實和多數羣眾而適得其反。
根據台師大英語系教授陳浩然公佈的數據,中國大陸、台灣與韓國都從小學三年級開始安排英語課。整個小學英語授課時數,韓國是200、中國大陸190、台灣150,都多於日本的100小時;但初中英語授課時數,日本是350小時、韓國340、中國大陸315,都多於台灣的250小時。顯然,台灣的英語課時不足,相應的資源也跟不上。
況且,還有個所謂的“國家語言發展法”。台灣當局規定自今年8月起,所有小學、初中和高中學生都必修前述的“本土語”。這就與原先小學必選修“本土語/新住民語”的新課綱相牴觸,於是新課綱還得繼續更新,可更新的新課綱又必然擠壓不把30萬陸配(大陸籍配偶)母語算在內的“新住民語”。
起初為了“新南向”,為了東南亞新住民的選票,越南、印尼、泰國、緬甸、柬埔寨、馬來西亞及菲律賓等七國語言都湧向台灣新課綱,彷彿這些東南亞新娘是來台灣生孩子學自己母國的語言。但在“國家語言發展法”的“太上”課綱下,她們見識到故國母語位階低於台灣“本土語”的現實,更不用説那些沒有選票收益的陸配了。
如果説,“新南向”在精神上是一種“次帝國”想象;那麼,台灣商界、政界、學界最近熱議的“新東向”,則是一種精神上的“次殖民地”想象。
項莊舞劍的語文教育
現在“2030雙語國家”的令箭一出,大家恍然明白,所謂“母語”、“本土語”,不過是對沖的角色,真正擔綱對決的主角還是英語,而對象就是被稱為“國語”、“國文”的漢語中文。換句話説,“多元語言政策”的實質目的和結果,不論對沖或對決,只能是擠壓漢語中文。但最後的下場卻是,什麼語文都沒學好,只換得“多元化”的皮相。
試看印度,其境內有1652種母語和為數更多的方言。雖然印度憲法規定的官方語言“只有”22種,但在廣播和成人寫教育方面共使用104種語言,其中有87種語言用於印刷出版,且沒有任何一種印度本土語的使用者超過全國人口的半數。在這種多族多語的情況下,印度境內各精英階層使用的唯一共同語,卻是外來的被定位成“副官方語言”的英語,這是作為前殖民地國家的悲哀。
如此來看所謂“雙語”,不過是改造政治社會體質的一種過渡工具,其意在“國家”,則“中文系”如何可能不成為眼中釘?一旦“雙語國家”成真,英語系就不再是“外語學院”,其位階更凌駕新住民語和“本土語”之上,而成為“國語”。
那麼,素來作為響應政策先鋒的台灣師範大學,其獎勵“本土語”、其中文系開設EMI,也就不難理解了。台師大中文系徐姓教授解釋説,是為了接軌國際漢學、引進新興科學方法來研究中國文學,並讓學生熟讀、借鑑、參照西方文學,所以中文系才要開設EMI云云。
但是,根據“台師大課程地圖”所示,其中文系的5項“教育目標”完全沒有“國際漢學”的説法;其16項“學生核心能力”也完全沒有徐教授的説法,反而是圍繞着中國的語言、文學、思想、學術、文獻。或許另一種説法,也就是中文系已成為台師大EMI的“釘子户”,實在對付不過去了,才轉身以“國際漢學”的角度來説事,是比較可信的解釋吧。
徐教授事後也在自己的社交媒體上説,中文系EMI的理想是讓研究和教學發生化學變化、形成學術槓桿,但大前提是牢固根本──“深厚的國學基礎、精湛的文學修養及鴻博的專業知識”,“全英語教學,不能本末倒置呀!”可見,無論温厚的徐教授對外如何苦口高大上,他自己卻陷入矛盾尷尬的婆心。
畢竟,作為培育台灣中等學校教師的搖籃,台師大中文系喂的卻是“國際”奶水,難道漢語中文將異化為“漢學”般的他者?那時的自己又是誰?
從“他殺”到“自殺未遂”
一些不甘自欺的學者,如中華傳播學會理事長、政大傳播學院院長郭力昕批評,台灣的英語崇拜現象是一種“文化自我殖民”——郭教授無意或是有意間點出了新殖民地社會的特性。台大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院長廖鹹浩則指出,“雙語國家”政策必然走上“揚英抑中”之路,造成受眾認同混亂、擴大階級差異、壟斷國際視野、弱化中文能力、阻礙高階思考──這是新舊殖民地社會的通病。
與此同時,台灣語文學會發起“反對2030雙語國家”聯署,迄今已獲得近兩千名人士的支持,其中半數是各級學校教師。不過,有位外語系教授何某的論述頗為特別。
何某説:日據台灣時期推行“國語政策”,獨尊日語;國民黨政府遷台推行“國語政策”,獨尊華語;如今民進黨政府進行第三次“國語政策”,則是獨尊英語。
他又説:前兩次是對台灣本土語言文化的“他殺”,這一次是“自殺”,但“自殺未遂”,因有諸多學者強力制止。何某主張“兼顧台灣在法律上有20種國家語言及英語為國際共通語的事實”,改以“多語台灣,英語友善”的雙贏策略。
這種説法,專屬以“多元文化”為掩護的偽本土派,包藏着過時的後殖民語境“本土/外來”概念──即“本土語/外來的日語、華語、英語”,但又開通“英語友善”的後門來加碼本土“自殺”的實際。所謂“兼顧台灣在法律上有20種國家語言及英語為國際共通語的事實”,不是教唆台灣語文印度化的“自殺”?所謂“多語台灣,英語友善”,確定不是擠壓漢語中文的雙輸主張?
台灣的“本土”意識形態化於1990年代,成為抽離和對抗中國元素的政治工具。操弄語文教育的人,毫不在乎年輕世代因而普遍失去高能思考和創造的後果,為台海話題平添“智統”的素材。
偽本土派無視中華民族光復台灣,台灣人爭學國語的熱潮開始於國民黨政府遷台以前的史實,不但扭曲國民黨“遷台推行國語”的歷史,並編造“台灣華語”的説詞,無非為了編派“國語/台語”=“外來/本土”的認知宣傳。
然而對當時的台灣人來説,“國語”就是中國本土的共同語、通用語或普通話,而非外來的“他者”;台灣光復時的“國語政策”更非“他殺”,而是復活。
換句話説,台灣本土語言文化分別在殖民地和新殖民地兩個時期遭遇“他殺”與“自殺”;其間,民國政府推行“國語”,恰恰是要恢復台灣本土的語言文化。
台灣聲韻學家竺家寧指出,“國語”是華夏民族的共同語,或叫雅言,或叫通語,或叫官話,其實是同一指稱對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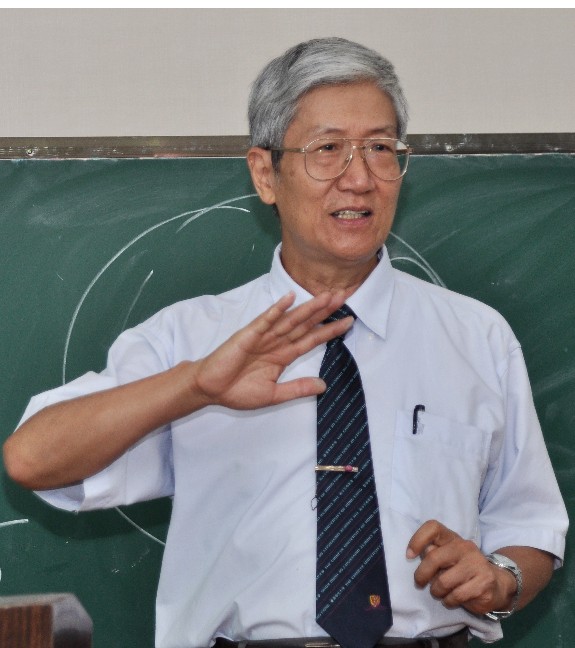
竺家寧教授講學。資料圖
所以,“國語”在台灣甚至早於閩南方言,在元順帝設置澎湖巡檢司時就已開始流傳。這就可以解釋《馬關條約》後,為什麼日殖總督府學務長伊澤修二會帶一批通曉中國“國語”的翻譯人員來台,顯然親歷明治新政統一國語的他,固以為北京話在台灣是多數人的共同語。
1945年台灣人既恢復華夏身分,自然也恢復華夏共同語的使用權利。1946年,“台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正式成立,北京大學畢業的魏建功與何容在台擔任正、副主委。他們面對日殖半世紀後台灣人的“失語”現象,提出《何以要提倡從台灣話學習國語》、《從方言學國語的理論》等文章。
還有在台山東人王炬擔任語委會的訓練宣傳組組長,他著作的《國語運動的理論與實際》指出:“國語因方言而擴充其詞彙語彙;方言因國語而發揚其優點。”
已故台灣史研究者曾健民解説,光復初期國語運動者的共同點在於認識到“台灣話(閩南方言)”與“國語”屬於同一民族語言,只是前者在日殖時代受到壓迫而變質,喪失瞭如同華夏社會各地方言的應有地位。而國語運動目的就在於驅逐日語壟斷,恢復台灣包括閩南方言和國語在內的民族語言,並在方法上強調“從方言學國語”、“用方言的思路寫文章”。
這種務實的科學態度,豈是偽本土派自編的“他殺”?
“搶救國文教育聯盟”的經驗
新殖民地偽本土派排斥“國語”,否認“台灣話”為中國方言,不過是因為“國語→北京話→國都→中國”的地緣政治關係,所以把同屬漢語的“國語”、“本土語”對立起來。現在歷史科和公民科的“脱中”教育都已到位,社會上湧動公務員廢考國文、大學生廢修國文的輿論氛圍,確實是以“本土語”、“多語”、“雙語”之名,對半殘的語文教育施以最終打擊的機會。
至於某“中研院”學者所謂“南島語言”是“台灣國際化的軟實力”之説,可見“多語台灣,英語友善”的支持者成分龐雜,“反對2030雙語國家”的人士也多是各取所需。
無論他們自以為南島語、本土語、新住民語、母語、多語或英語能接軌國際和強化競爭力,其實都無法超越“語言政治”(politics of language)的宰制。
新殖民地時期和殖民地時期一樣,語言只是權力結構的展現,而不是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需求,當權派並不在乎任何一種“本土/外來”語言本身的發展,而且無一例外的結果是兔死狗烹:權力達陣=語文衰微。
台灣光復前夕的1944年,全台日語普及率達到71%,但卻有45萬名公學校畢業生不能自如地使用日語。這是因為日殖當局實施“皇民化”的目的在於役使台灣勞動力,而不在於讓台灣人具備以日語思考的能力,這也説明日殖台灣時期高學歷者集中在醫、農、工的現象。現在英語“自殺”本土,則是因為依附美國隊的權力結構使然,與日殖台灣時期的依附階級推崇日語,如出一轍。
因此,當前台灣學生的最大問題,是語文整體及相應思考能力的衰殘,其病態是多元自視,其病根是中文不行,而病因是政治屠宰。
早在2005年,已故詩人余光中就發起成立“搶救國文教育聯盟”,聯署人士超過一萬名,共同發起人遍及台灣、大陸、香港、美國等地。
以如此聲勢訴求增加學生國文課時、提高古詩文比例、恢復中華文化基本教材,尚且全數失敗,至今僅存小眾的古詩文背誦與吟唱比賽而已。年輕世代的國文教師為求生存計,則紛紛報名補修“本土語”或“雙語”資格。
“搶救國文教育聯盟”的經驗,預示了“反對2030雙語國家”最多是熱鬧收場。台灣當局自1990年代改造歷史教育以來,從沒忘記改造思辨歷史能力的語文教育,這是奔着改造身分認同而來的政治工程。凡是沒有這種認識和相應行動的異議者,註定無疾而終;凡是違逆這項工程的挑戰者,必然遭遇精神鎮壓,例如曾經熱心兩岸合編語文教材的教授和相關學校。
在這樣的氛圍下,執掌台灣語文教育牛耳的師範大學中文系,只能以順為正地走向“本末倒置”的EMI課程,更無人再為台灣教改下的語文教育撥亂反正。
台灣教改從“八八課綱”、“九五暫綱”、“九八課綱”、“一○一課綱”、“一○三課綱微調”、乃至“一○八新課綱”,平均幾乎每3年換一次課綱,每次都重點爭議和更改中文課時、文言/白話比例、核心古文篇數和取材、《中華文化基本教材》的課程屬性乃至存廢。
如今在號稱“素養導向”的新課綱下,台灣小學國語課本3個版本中,平均六年只有6首古詩文;而大陸地區小學統編版語文課本,六年共有112首古詩文。相形之下,加諸“雙語國家”政策的台灣學生,將被導向廖鹹浩教授所説的“文化的貧乏與創造力的平庸”,而這正是新殖民宗主國所需要的“殖民地素養”。
去殖民地化必光復語文
當年日殖總督府就是採用吸納、混同“雙語”的教育方法,來轉化或錯亂台灣人的身份認同。比如1896年在國語傳習所增設日式漢文課,內容甚至包括刪去孟子民本內容的四書五經;1897年還規定公學校每週12小時的漢文課程,但教材是漢譯版日文讀本。後來隨着日語文教育的順利擴張,而逐步縮減漢文課時數,終至完全廢止漢語中文。
據李登輝自述,他在1947年1月擔任台大學生會聯合會議主席時,已經不會説中文,講的是日本話,由他的入黨介紹人吳克泰擔任翻譯。由此可見,日殖當局以“雙語”教育達成“同化”的成效。
不過,日殖時期許多台灣書房表面奉行日式《漢文讀本》,暗地卻使用大陸出版的國語文教科書;與此相應,許多家長白天送孩子上公學校,晚上又送孩子到書房補習,以保存民族根苗。有些經過書房時代的師生,後來不同程度地體現中華民族意識,如連橫、林獻堂、莊嵩、洪棄生、李偉光、蔣渭水、張我軍、賴和、潘貫等人便是。
這種殖民地經驗,豈不預示台灣學生無法在“雙語”的公學環境學好漢語中文,而必須求助私學?一旦台灣的語文環境步入印度化,估計補習中文普通話將是台灣學生未來要走的路吧,就像台灣光復時他們爭學國語的祖先。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台觀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關注觀察者網微信guanchacn,每日閲讀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