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馬斯·博伊基:越健康越富裕?中國傳染病防治創造了人口紅利機遇期
【文/托馬斯·博伊基】
兒童生存革命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以下簡稱“兒基會”)最初叫作聯合國國際兒童緊急救助基金會(United Nations International Children’s Emergency Fund),後來雖然去掉了“國際”和“緊急”的字眼,但保留了原來的首字母縮略詞。兒基會原先是一項臨時倡議,目的是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廢墟中的歐洲提供衣物、奶粉和基本醫療保健服務。
到了1953年,該機構成為聯合國系統的一個永久組成部分,並將工作範圍擴展至全球,為生育、餵養和營養項目,根除瘧疾行動,以及兒童免疫接種計劃等提供基本物品保障和支持。
1980年吉姆·格蘭特剛到兒基會時,它是一個高度分散化的組織,其有限的預算大部分用於以改善健康狀況和滿足基本需求為目標的小型社區項目。消滅瘧疾項目失利後,彼時的國際衞生界正專注於在全球範圍內建立初級醫療衞生體系。
格蘭特是“二戰”老兵、律師和前美國援助機構官員。他的童年時光在中國的農村度過,父親曾是洛克菲勒基金會派駐在當地的醫務人員。據同事説,格蘭特是個工作狂,看到苦難中的兒童時並不會流露太多情感,但他滿懷激情地相信,無論情況如何,即使是在極端貧困的環境中也能有所作為。
某次會議上發表的一份報告給格蘭特留下了深刻印象。這份報告認為,在發展中國家,通過採取較低成本的預防措施可以減少近一半的兒童死亡。該文章的作者喬恩·羅德寫道:“通往健康之路的確存在捷徑。”
當時,麻疹、百日咳、破傷風和脊髓灰質炎每年造成四五百萬名兒童死亡,不過能夠預防這些疾病的疫苗已經問世。在這篇文章的鼓舞下,格蘭特努力克服了世衞組織起初對兒基會擴大兒童免疫接種工作的抵制。儘管世衞組織於1974年啓動了自己的擴大免疫規劃(EPI),但這項計劃僅僅覆蓋了全球10%-15%的兒童,且進展緩慢。
最終,兒基會和世衞組織達成了一項協議,雙方在世界銀行和國際扶輪社(Rotary International)的支持下,於1982年發起了兒童生存革命(Child Survival Revolution)。這是一項雄心勃勃的全球計劃,在此計劃下,各組織承諾加大力度監測兒童的生長發育情況,分發口服補液鹽溶液以減少腹瀉導致的死亡,提倡母乳餵養,並在8年內為全球70%的兒童接種6種主要兒科傳染病的疫苗,包括麻疹、腮腺炎、破傷風、百日咳、白喉和脊髓灰質炎。這項一攬子組合干預措施也被叫作GOBI(生長監測、口服補液、母乳餵養和免疫接種的英文首字母縮略詞),目標是實現使全球兒童死亡人數減半。
這一行動於1984年在哥倫比亞波哥大拉開序幕。在20世紀80年代剩餘的時間裏,格蘭特帶着自己的法寶走遍世界。他的法寶是脊髓灰質炎疫苗滴管、口服補液鹽和兒童生長發育表。格蘭特會見了各國元首,其中有將軍和民主領袖,也有反對派指揮官和年邁的君主。
他説服這些人作出免疫接種的書面承諾,使這項行動得以開展,並且爭取到了當地官員的幫助。在薩爾瓦多,開展疫苗接種運動意味着僅僅為了給兒童進行預防接種,就要促成雙方在長達14年的殘酷內戰中停火。其他的非政府組織和聯合國機構負責人不會去面見心狠手辣的統治者,比如海地的“小醫生”讓-克洛德·杜瓦利埃和埃塞俄比亞的門格斯圖· 海爾·馬里亞姆。但是格蘭特會這麼做,並且能夠讓這些人相信,預防接種運動將提高他們的民意支持。格蘭特認為,兒基會所做的這些工作是為了“有所作為,而不是表明立場”。
即使獲得了地方領袖和政府的政治支持,疫苗接種運動仍然是一項浩大的工程。它需要在全球偏遠地區建立温控供應鏈。此外,還要依靠成千上萬的志願者和英勇的疫苗接種人員冒險深入戰爭波及的地區。格蘭特將其描述為和平時期全世界規模最大的一場動員。僅1990年一年,該計劃就在150個國家為1億名兒童完成了至少6次疫苗接種。

1987年吉姆·格蘭特在塞內加爾首都達喀爾的登巴·迪奧普國家體育場(Demba Diop National Stadium呼籲提升兒童生存水平。
資料來源:約翰·艾薩克(John Isaac),攝於1987年;圖片由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提供。
這場行動實現了既定目標,它與兒基會的水和營養項目共同開展,據估計挽救了2500萬名兒童的生命。到了1990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只有十幾個國家的每千名5歲以下兒童死亡人數達到175人。在許多低收入國家,1歲以下兒童完全接種的比例超過80%,已經追平甚至超過了一些富裕國家的覆蓋率水平。這個令人難以置信的事實鮮有人知,然而故事並沒有就此結束。
在低收入國家,國際社會擴大傳染病免疫接種範圍的努力仍在繼續,其他機構也在着手開展這些工作。到了1999年,已有4.7億名5歲以下兒童完成了接種。
2000年,在蓋茨基金會等援助機構的支持下,全球疫苗免疫聯盟正式啓動,並將免疫計劃進一步擴大,從而覆蓋新近研發的針對黃熱病、乙型肝炎等疾病的疫苗。全球疫苗免疫聯盟開展的項目覆蓋70多個國家。
從2002年到2016年末,全球疫苗免疫聯盟累計募集了約90億美元,來源包括捐贈資金、匹配捐贈和聯合融資。這項投資帶來了驚人的回報,自該機構成立以來已經挽救了900萬名兒童的生命。
成立30多年來,兒童生存革命計劃始終名副其實。全球疫苗接種覆蓋率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麻疹、白喉、百日咳、破傷風和結核病疫苗在2016年的接種率均達到或超過85%。例如,在過去的15年中,麻疹造成的兒童死亡人數減少了79%;據估計,僅此一種疫苗的擴大使用就挽救了2030萬人的生命。在這些兒童疫苗和其他全球健康倡議的幫助下,5歲以下兒童每年的死亡人數從990萬減少到590萬,下降了近一半。儘管減少不必要的兒童死亡仍然需要付出大量努力,但兒童生存革命率先推動的這一進步無疑是一項了不起的成果。
這些令人矚目的健康成就正在重塑世界人口的區域和年齡分佈。巨大的人口變化為低收入國家增加經濟財富提供了短暫而重要的機會。但是如果不抓住這個機會,後果可能會非常棘手。為了解釋其中的原因,我們需要回顧當年發生在中國的故事。
中國的飛躍
1976年的中國是當時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其人均GDP(以現價美元計算)要低於乍得、貝寧和尼日爾。就在此前15年,中國剛剛遭遇了一場饑荒,這場饑荒造成大量人員死亡。1958—1961年,政府嘗試通過讓人們從農業生產轉向大鍊鋼鐵來實現對西方的趕超,這項運動成為導致糧食短缺的一個因素。
1976年之前,中國仍處於“文革”的風暴之中,這場政治運動導致許多人受到影響,學校被迫停課,數百萬知識青年被安排到農村插隊。
有關中國的非凡故事中,人們耳熟能詳的部分就是,在1978年開始改革開放後,這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在不到40年的時間裏一躍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之一,讓5.6億人擺脱了極端貧困。
故事中還有一部分鮮有人知,那就是到1976年,中國的人均預期壽命已經實現了令人矚目的連續16年的增長,增幅達到了驚人的21歲。 1960年,中國的新生兒預期平均只能活到44歲。 到了1976年,國家仍處於動亂之中,後來的經濟繁榮尚未發生,但當時新生兒的預期壽命已經能夠達到65歲。
這是怎麼發生呢?第一,預期壽命,或者更確切地説應該是出生時的人均預期壽命,像是一張瞬間快照。過去時間裏發生的死亡不會影響以後出生嬰兒的預期壽命。第二,也是這個故事中更為重要的一點,預期壽命也是反映過去健康進步的一項滯後指標。
1949—1978年,中國發動了一場以農村地區為中心的針對傳染病的全面戰爭,大大降低了本國的兒童死亡率。1949年,中國開展了一項為期3年的突擊行動,為本國龐大的人口接種天花疫苗,隨後又實施了針對結核病和白喉的免疫接種計劃。1952年,政府發起了愛國衞生運動。這項大規模的衞生運動具體包括修建廁所、開展健康教育,以及用筷子從村莊附近的溝渠中夾走攜帶寄生蟲的釘螺。

《送瘟神》畫冊。資料來源: 北京: 中共中央南方十三省( 市、 區) 血防領導小組辦公室, 1978 年,第 65 頁。
注: 與這張愛國衞生運動照片所體現的情況不同的是, 根據中國研究學者米里亞姆· 格勞斯( Miriam Gross) 的説法, 用筷子夾除釘螺的煩瑣工作大部分由女性和老年人完成。
從20世紀50年代初開始,一批經過初步培訓的醫護人員被從農村的人民公社招募過來,負責協助衞生院的醫生指導農村衞生工作並分發抗生素。中國還建立了上千個衞生院和防疫站。
1968年,在“文革”高峯時期,這項醫療援助計劃正式確立,其中的醫療人員得名“赤腳醫生”。這些“赤腳醫生”對女性進行孕期指導,在她們分娩時提供護理,並教母親如何更好地照護她們的孩子。他們還收集了大量糞便樣本,每個樣本都用紙或樹葉包裹起來,外面寫上病人的名字,以至一些村民開始戲稱他們為“收糞醫生”。
血吸蟲病也被稱作釘螺熱,是一種致命的寄生蟲肝病,而化驗這些糞便樣本正是全國血吸蟲病防治運動的一部分。毛澤東主席為江西餘江縣消滅了血吸病欣然命筆,題為《七律二首· 送瘟神》。詩的結尾寫道:“借問瘟君欲何往,紙船明燭照天燒。”毛澤東給血吸蟲病的送別還只是暫時的——1958 年,包括該病和結核病在內的傳染病在中國依然時有發生。
20世紀50年代末,政府又發起了一場消滅“四害”(麻雀、老鼠、蒼蠅和蚊子)的全民運動。雖然中國政府控制傳染病的努力並非都有回報,但總體上取得了巨大的進步。那個年代出生的孩子中,一些原本按照過去的情況可能已經離世的孩子,在20年後都長大成人,幫助中國重返世界經濟強國之列。
更健康意味着更富裕?
中國在提升人均預期壽命後實現了驚人的經濟增長,這一案例常常被援引,作為健康改善帶來財富增長的證據。但是,該理論並不存在一邊倒的實證依據。
一方面,人們傾向於憑直覺認為,更健康的工人有着更高的生產力。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羅伯特· 福格爾估計,從體重和卡路里攝入的變化來看,從1780年到1980年,英國國民營養狀況的改善使適齡勞動人口的勞動產出幾乎翻了一番。還有研究表明,鈎蟲感染和營養不足會對兒童未來的收入和教育水平產生長遠影響。
由《柳葉刀》組織、美國前財政部長拉里·薩默斯領導的一個委員會得出的結論是,在 2000—2011年,人均壽命的提升貢獻了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全收入”增長額的24%,該委員會將這裏的“全收入”增長額定義為國民收入增長與死亡率降低的價值之和。2015年,來自44個國家的267位經濟學家,包括薩默斯在內,在《紐約時報》上聯名簽署了一封公開信,表示全民健康覆蓋“對於消除極端貧困至關重要”。 另一方面,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家達倫·阿西莫格魯和西蒙·約翰遜在一項多國研究中發現,人均收入隨着壽命的延長而略有下降。
這是由於預期壽命提升所帶來的經濟增長相對有限,而且還會因人口增加進一步稀釋。經濟學家誇姆羅·阿什拉夫、艾什莉·萊斯特和大衞·韋爾研究得出的結論是,從長期來看,預期壽命從40歲提高到60歲將使一國的人均GDP增長15%,但人均收入在短期內反而會由於兒童生存率提高“拖累”經濟而降低。
考慮到影響經濟的因素多種多樣,想要單獨研究良好健康的影響始終十分困難。但是,試圖在傳染病減少與未來財富增加之間尋找一種直接的、機械式的關係,來思考健康對經濟發展的潛在貢獻,無疑是錯誤的方式。吉姆·格蘭特的兒童生存革命和毛澤東的“赤腳醫生”大軍之所以重要,是因為這些行動減少了數百萬名兒童的死亡。除此之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那就是它們創造了一個黃金機遇。這一機遇配以正確的社會和產業政策,能夠令低收入國家的經濟邁上新台階。
潛在的人口紅利
哈佛大學公共衞生學院教授大衞·布魯姆整個職業生涯都在思考人口與經濟的互動作用。他和同事開展的多項研究表明,從年齡結構而不是人口數量的方面思考人口在促進經濟增長中的作用,才是真正恰當的方式。
布魯姆認為,如果一個國家年齡在15-64歲之間的適齡勞動人口比例極高,那麼這個國家將具有經濟優勢,他稱這種經濟優勢為人口紅利。人口紅利之所以存在,是因為這種年齡結構意味着能夠從事生產和創造收入的潛在工人更多,單純消費產品的受扶養者(兒童和老人)更少。儘管有些讀者可能會質疑布魯姆和其他人口學家劃定老年和工作年齡的界限是否妥當,但中國的故事的確為布魯姆的整體觀點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證據。
從1949年開始,中國的傳染病大幅減少,兒童生存狀況顯著改善,但早期的出生率居高不下。1955年,中國衞生部提出了適當節制生育的計劃,但三年經濟困難和“文革”中斷了這些計劃的實施。
中國的生育率在20世紀50年代中期有所降低,在此後10年的大部分時間裏保持上升,但到了20世紀70年代初開始急劇下降。隨着越來越多的孩子存活下來,中國的母親們不再需要生育那麼多的子女。
中國採取了降低出生率的措施,推行計劃生育政策和獨生子女政策。中國還通過推行獨生子女政策等措施降低出生率。在三年經濟困難期間死亡的人口中,嬰兒佔到了1/3。這些因素的疊加意味着,出生於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中期並度過了三年經濟困難的成年人口有所增加,而隨後的幾十年中兒童數量則有所減少。這樣的結果是,等到1978年改革開放將大量製造業就業崗位帶到中國時,國內龐大的適齡勞動人口已經蓄勢待發。
到了2000年,東亞地區15-64歲的人口占到了總人口的2/3以上。中國等東亞國家在這個奇蹟時代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經濟增長,據布魯姆等人估計,其中有1/3到一半要歸功於人口紅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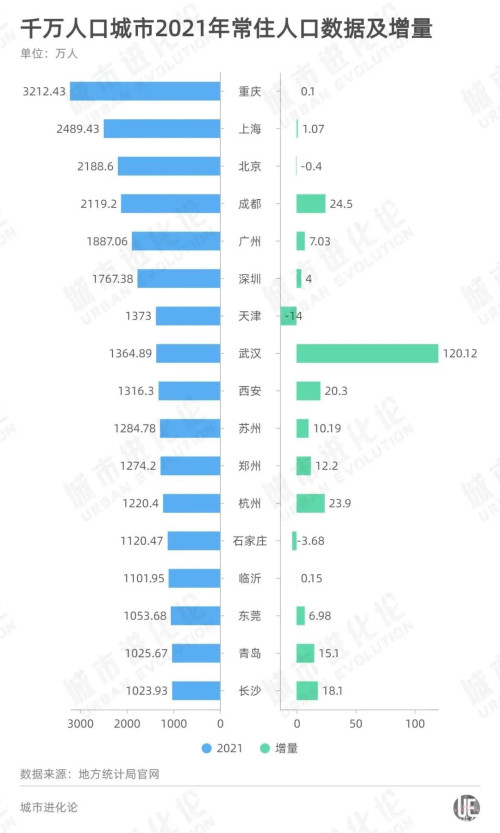
經濟學家、諾貝爾獎獲得者保羅·克魯格曼在1994年的《外交事務》雜誌上發表了《亞洲奇蹟的秘密》一文,他也表示,該地區令人驚歎的經濟增長大多歸功於勞動力投入的增加,而非生產效率的激增。
經濟學家羅伯特·戈登同樣表達了類似的觀點,他認為,1890—1950年嬰兒死亡率的急劇下降,是“美國經濟發展史上最重要的事實之一”。在過去50年實現經濟持續繁榮的國家中,大多數都有數量龐大且比例不斷上升的適齡勞動人口。對於那些傳染病持續減少且兒童生存狀況不斷改善的低收入國家,上述研究和東亞國家的成功故事提供了三條經驗。
第一條經驗,也是一個好消息,即一個國家傳染病的迅速減少,加之生育率的下降,能夠對本國的經濟發展產生巨大影響。勞動力是一國經濟發展的重要生產要素,適齡勞動人口的較高比例為加快經濟發展創造了可能。
各國無須效仿中國推行的政策。日本、韓國和新加坡在20世紀50年代依靠自願措施降低了生育率。從東亞地區總體情況來看,每千名活產嬰兒死亡數從1950年的181例下降到2000 年的34例。事實表明,兒童存活率的提升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女性的生育選擇,這種情況在低收入國家表現得尤為明顯。
然而,儘管大多數東亞國家都在20世紀50年代經歷了傳染病減少、兒童生存率提高和生育率下降的情況,但不是所有的國家或地區都從人口紅利中獲得了相同的經濟收益。中國(包括台灣地區)、新加坡和韓國的經濟蓬勃發展。泰國的經濟增長相對緩慢一些,菲律賓的發展則依然遲緩。在該地區以外,許多拉丁美洲和北非國家因年齡結構變化而獲得的經濟收益更是十分有限。
通過這些迥異的結果,我們可以從東亞地區的人口紅利中得出第二條經驗。人口轉變提升了經濟政策的重要性,放大了政策選擇的優缺點所產生的影響。由於適齡勞動人口比例提高,潛在工人數量,也就是勞動力的供給隨之增加。
一個國家需要良好的政策、充足的投資和可靠的機構來創造高質量的教育、職業培訓機會和更高的健康水平,而這些特徵可以使增加的那部分勞動力隊伍在就業市場上更具競爭力。同樣,要想讓不斷擴大的勞動力供給有效發揮作用,就需要有良好的道路、可靠的電力、法治以及合理的監管,這些因素能夠使開辦工廠和企業家創業更加便利。
傳染病的減少一定程度上使得勞動力供給迅速擴大。採取上述這些審慎的政策之後,迅速擴大的勞動力供給可以極大地促進經濟的長期增長。東亞國家之所以能夠享受到本國的人口紅利,是因為這些國家的政府將人口的快速轉變與針對性的職業培訓和出口導向的製造業政策成功結合。這提高了勞動人口的就業競爭力,使這些國家能夠利用日益增長的需求來充分吸納本國的勞動人口。
同時,中國和這些東亞國家也是幸運的,這一點引出了我們能夠從東亞人口紅利奇蹟中提煉出的第三條經驗。如果沒有一個有利的全球經貿環境,人口紅利的收益大部分將會被浪費掉。毫無疑問,中國作出了許多審慎的決策,以利用其傳染病負擔不斷減輕所創造的機會。
喬·史塔威爾在他的著作《亞洲大趨勢》( How Asia Works)一書中着重強調了三項決策 :利用技術推廣服務來提高農作物產量,對企業家和技術升級給予國家支持以擴大本國製造業規模,為長期發展和學習提供融資。
中國當時的司法體制尚不健全,對外國投資者的政策也不夠開放。中國在1978年的公民平均受教育年限要低於當今大多數低收入國家的水平。現如今,對於一個希望利用人口紅利並發展為強大經濟體的國家,中國當年採用的那種政策和投資組合未必是當下最優的選擇了。
不過,中國的幸運之處在於,它能夠在全球經濟發展相對平衡的時期享受本國的人口紅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幾十年中,日本、韓國和中國台灣等國家或地區必須建立廣泛而深厚的工業基礎,才能從製造收音機和其他廉價的消費類電子產品開始,依靠自身努力逐步朝着全球價值鏈的頂端攀升,生產具有全球市場競爭力的高端商品,從而提供報酬更高的就業崗位。
所有這一切都隨着標準化集裝箱的發明和關税的降低而發生了改變,因為這種改變使得企業可以將製造過程中的許多環節外包,將勞動密集型的零部件製造和許多消費品的組裝工作交給全球範圍內工資水平較低地區的製造商。中國、越南和其他發展中國家能夠通過參與這些全球供應鏈,釋放本國的人口紅利並進入全球市場競爭,從而使本國數以億計的人民擺脱赤貧。
拉丁美洲國家則沒有那麼幸運。它們也擴大了兒童疫苗接種的範圍,實施了更好的公共衞生政策以降低傳染病的發病率。這些舉措最終帶來了生育率的降低。但是,這些國家陷入了國際和國內債務的泥潭,並遭受了高通脹的困擾。
對此,國際債權方要求它們強化預算約束並採取財政緊縮措施,這一點加劇了各國的經濟困境並促使它們削減了教育和衞生方面的預算。包括巴西在內的一些國家試圖通過開放本國經濟來吸引貿易和外部投資,然而這種應對措施無法為其快速增長的勞動力創造足夠多的就業機會。研究人員將拉丁美洲至今仍然十分突出的經濟不平等現象歸因於該地區未能跟上自身不斷變化的人口特徵。
簡而言之,人口紅利不是註定發生的事情,也不是經濟增長的保證。例如,如果出生率下降緩慢,那麼政府和家庭就不得不放棄一些必要的教育投資,因為它們為每個孩子平均能夠投入的資源更加有限。如果經濟改革不成功,沒有創造生產性崗位,那麼從事有報酬工作的適齡勞動人口的數量和收入就不會增加。
人口紅利創造的機遇期也相對較短。近年來實現傳染病負擔減輕和兒童生存狀況改善的國家必須採取快速、有力的行動。對於過去為取得這些健康收益曾進行投資的政府和援助機構而言,它們同樣應投資實施必要的計劃生育政策,將人口增速降低到可持續的水平,同時推動經濟和社會改革,從而在這些有利的人口狀況依然存在的時候加以利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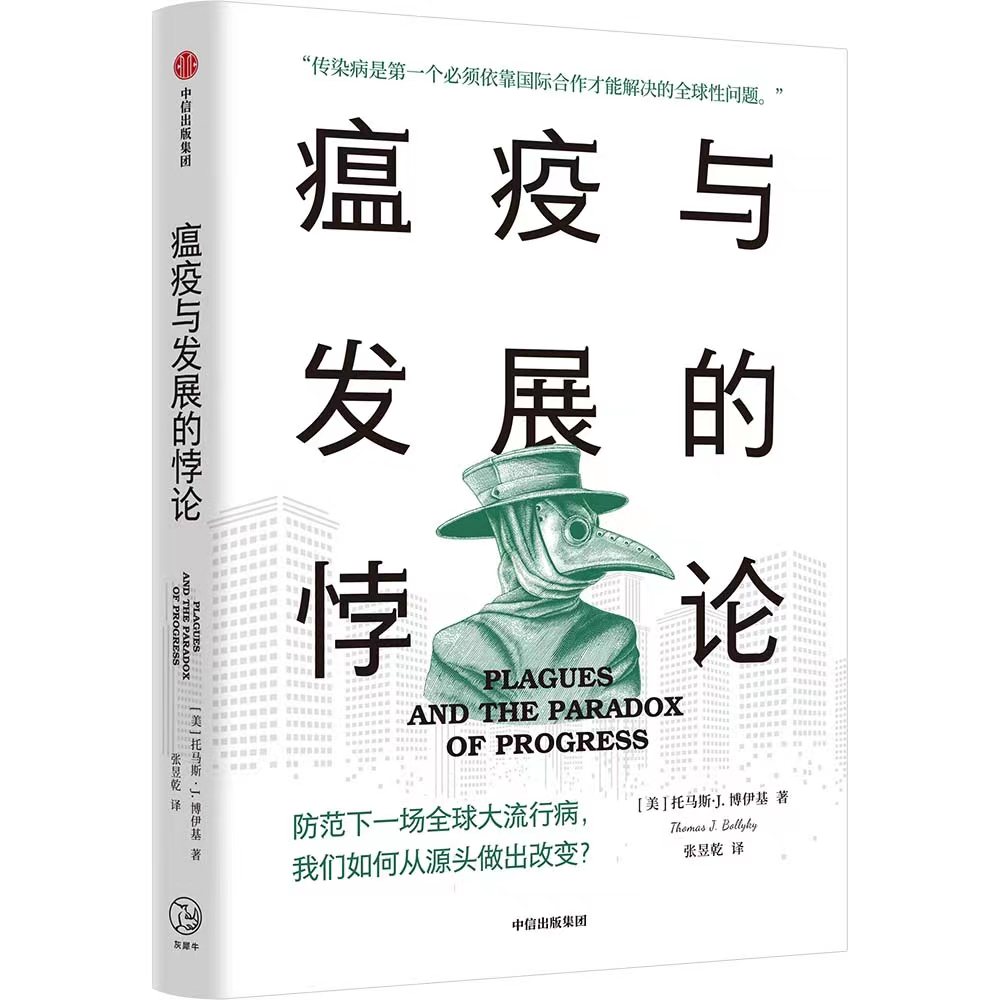
[美]托馬斯·J.博伊基:《瘟疫與發展的悖論》,張昱乾譯,中信出版集團202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