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縱橫:美容診所暴利47億,揭開一場羣體操控的迷局
【文/黃燕華】
問題緣起
自20世紀80年代後期以來,整形美容行業在我國蓬勃發展。
據相關報告,“整形美容是指運用手術、藥物、醫療器械以及其他醫學技術方法對人的容貌和人體各部位形態進行修復和再塑,進而增強人體外在美感為目的的科學性、技術性與藝術性極強的醫學科學。通俗地講,整形美容就是人體雕刻”。

2017年,中國已經成為僅次於美國的全球第二大醫美市場,2018年中國整形美容市場規模為1220億元,據估算,中國有望在2021年超越美國成為醫美第一大市場。
從選擇整形的人羣的年齡來看,佔比最大的是25-30歲這個年齡段,佔總人數的38%,30-35歲的佔31%,25歲以下的佔19%,大於35歲的僅佔12%。而從選擇整形的人羣的性別來看,根據全球整形數據統計,2016年女性進行了約2036.3萬次整形,佔到整形總數的86.2%;男性進行了約326.4萬次整形,佔整形總數的13.8%。
然而,與中國整形美容市場迅猛發展態勢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整個行業經營和技術的良莠不齊,相關醫療事故頻頻發生。有關整形毀容、甚至致死的新聞層出不窮,令人觸目驚心。2010年,因湖南衞視“超級女聲”選秀節目而被大眾所熟知的某歌手在接受面部磨骨手術過程中大出血,血液通過喉部進入氣管造成窒息,在搶救無效後死亡。國家衞生部對此事件高度重視,表示將加大對整形美容行業的監管力度。

“超女”王貝生前照片(資料圖)
整形毀容的案例更是數不勝數,早在2004年,新浪網就曾登載過一則《整形美容:10年毀掉了20萬張臉》的報道,雖然該數據的準確性遭到質疑,但該現象卻引起了社會的廣大關注。近幾年來,隨着網絡經濟的發展,一批在網絡走紅的女性由於整形擁有相似的面孔而被冠上“網紅臉”的稱號,“網紅臉”經常被用作貶義詞,有時候甚至與低俗劃等號。

相關報道截圖
為什麼整形會有如此大的市場,其背後的社會語境是什麼,在整形市場如此混亂的情況下,是什麼因素促使女性寧願冒着毀容、甚至死亡的風險去整形,她們決定整形的具體過程是怎樣的,整形會給女性帶來什麼結果?這些問題構成了本文的研究起點。
本研究嘗試以後現代女性主義為視角分析現代消費文化背景中的整形女性。本研究主要關注以下問題:
女性如何確認自己的長相“醜”或“有缺陷”,什麼因素最終促使女性甘願承擔風險作出整形的決定;
女性如何從整形當中獲得舒適和自我認同感,又是如何陷入更深的自我迷失和痛苦之中;
女性整形是自主救贖還是被迫選擇,這些自主或被迫的、快樂或痛苦的整形經歷如何與更宏觀層面的權力與不平等相關聯。
在本研究中,筆者總共對6位有整形經歷的女性進行了深度訪談,並對相關網絡版面中的17位討論參與者的整形經歷自述及相關看法進行了批判話語分析。對這些討論者來説,筆者是虛擬環境中的“潛伏”的研究者。
本研究的受訪者及匿名討論者整形的年齡均在16-40歲之間,目前都處於學習或工作狀態,她們的整形項目包括:雙眼皮手術、去皮去脂、開眼角、膨體隆鼻、耳軟骨延伸鼻尖、縮小鼻翼、上眼臉提肌、面部吸脂、墊下巴、瘦臉、抗衰老等。
需要整形:“自我救贖”還是被迫選擇?
社會互動和消費文化在女性形成長相“醜”或“有缺陷”的自我認知以及最終決定整形中起着關鍵作用。通過材料分析發現,整形並不是女性的“自我救贖”,而是一種被迫選擇。
(一)對“醜”或“有缺陷”的自我認知
認識到自己長得“醜”或“有缺陷”是社會互動的結果。庫利(Charles Horton Cooley)符號互動論中的“鏡中我”認為,人的行為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對自我的認識,而這種認識主要通過與他人的社會互動形成,他人對自己的評價和態度是反映自我的一面“鏡子”,個人通過這面“鏡子”認識和把握自己。人們關於自己的身份認同是社會互動的產物。
兒童和青少年時期社會互動中所產生的人際困難和兩性關係是讓女性意識到自己“醜”或“有缺陷”的最主要因素。
在社會化環境中,外貌對自己生活的妨礙是女性將長相“醜”或“有缺陷”視為一種需要被對待和隔離的疾病或者個人錯誤的根源。大多數受訪者和相關話題討論者都談到自己在兒童和青少年時期因為外貌而遭受的人際交往方面的困擾及痛苦。圓圓自述自己小學時原本是個活潑開朗、討人喜歡的孩子,但後來由於自己長相上的“缺陷”而遭受到了“校園暴力”,從那以後,她開始注意別人的目光和評價。
我開始注意到自己長相上的缺陷,並且過分誇大它們的不足,我單眼皮腫泡眼,覺得自己臉方,嘴唇厚,帶着一副黑框眼鏡。記得有天我取下眼鏡,班裏一個女生直接説我不戴眼鏡的樣子很醜,我深受打擊,從那之後的七年……我的初中和高中,主基調就是孤獨和自卑……(圓圓)

影視資料圖
兩性關係發展受挫是女性認識到自己“醜”或“有缺陷”的另一個關鍵原因。
上了大學的圓圓開始打扮和減肥,並嘗試通過提高“內在美”來讓自己變得“更強大”和“像個正常的大學生”。然而,在喜歡的男生找了好看的女朋友之後,她開始變得越來越自閉。
我喜歡上了一個男生,凝聚所有勇氣去表白了,被拒絕後,他不久就有了一個女朋友……長得太好看了,讓我又開始有些自卑,我沒有在愛而不得的情緒裏走不出來,因為我一直覺得自己不配擁有愛的。(圓圓)
鈺彤則因為前男友出軌“長得漂亮”的女生而情緒崩潰。她説,
“前男友出軌,(小)三是一個名聲不好、會撒嬌賣嗲的下屬,不得不承認她長得漂亮,他輕易地放棄了近六年的感情,激發了我原生的自卑,重度抑鬱,不斷否定自己”。
外貌在人際關係和兩性關係中遭受的挫折激發了女性對自己的否定。“孤獨”“自卑”“抑鬱”“情緒崩潰”“不配擁有愛”“每一天都好漫長,活着也沒有任何期望”是這些女性在感知自己長相“醜”或者“有缺陷”之後的遭遇和感受。對她們來説,長相“醜”或者“有缺陷”是一種社會障礙,一種阻止她們充分享受生活,讓她們感到羞恥、不自信和痛苦的東西。外貌成了女性自我價值評判的核心,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這些女性十分渴望能夠改變自己。
(二)決定整形
在形成“醜”或“有缺陷”的自我認知之後,整形技術的發展、消費文化對美的建構和同伴壓力成為促使女性作出整形決定的三個關鍵因素。
埃裏克森(Erik Hombuxger Erikson)認為,青少年時期是塑造個人自我認同的重要時期。青少年時期因外貌在社會互動中遭受的挫折使女性產生了深刻的自我懷疑,“醜”成了女性自我認同中最關鍵的部分。因此,通過整形獲取“美”對女性來説顯得極為必要,它可以讓女性不再遭到同伴的嘲笑,不再自卑,也可以讓女性有機會收穫愛情、重獲新生。
從我知道這個世界上還有整容這麼回子事的時候就已經下定決心要整,終於不用靠自殺重新投胎來改變容貌了,心裏的一塊巨石放下了,那會估計也不過八、九歲吧。(少奕)
原本認為整容手術就像是“中差等生作弊考出和優等生一樣的成績”而排斥整形手術的圓圓在發現自己化妝、貼雙眼皮變得好看之後,也決定整形改變自己,“我想,整容對我來説是早晚的事。也許這不能使我好起來,但我想好起來,不論這感覺多麼短暫,我本能的反應卻是想擁有。”
整形技術的發展給女性帶來了“重獲新生”的希望,而消費文化對美的建構以及同伴壓力則促使女性最終作出整形的決定。
在某種程度上,“美”的標準是社會建構的,它隨着時代的不同而不同。當前消費文化中的審美標準是通過媒體中年輕男女的精修圖來推廣的。根據鮑德里亞(Jean Baudrillard)的概念,這些由媒體建構的身體形象只是一個擬像,其本身就是一個沒有實際參考對象的複製品。然而,媒體所推廣的身體形象卻成了所有人都應該以此為參照來嚮往、形塑和打造的模板,這讓絕大多數女性對自己的外貌感到不滿意,她們因此焦慮、痛苦和迷茫,最終作出整形的決定。

隨着消費文化所建構的身體理想型的推廣,整形在某種程度上變得常態化,身邊朋友、同學和網絡紅人的成功整形案例進一步激發了年輕女性潛藏的不自信,誘使女性作出整形的決定。
安晴做過割雙眼皮手術,談及“是什麼時候決定整形的”,她提到了自己所感受到的同伴壓力,“當結交了好看的女性閨蜜的時候,大概是高中的時候,身邊的女孩子都太好看了,你由內而外的自卑感到達頂點想要改變的時候。”同伴壓力不僅存在於線下的社會互動中,還來源於線上。
隨着微博、直播軟件什麼的盛行,湧現出各種各樣的網紅,有段時間網紅們紛紛自曝自己的整容史,當時我在讀大學,身邊已經開始有朋友因為整形變美。(曉澤)
一些國外學者認為,當整形開始變得常態化,成為一種非常自然的、可負擔的和常規的步驟時,女性就會被鼓勵去整形,以作為個人享樂和消費自由的表達。而當整形變成一種常態,那些不選擇整形的女性就會被污名化,進而成為“越軌者”。“網紅”的引導、同伴羣體整形的成功促使女性決定整形以期改變人生。
不管是由於何種壓力而整形,我們都能看到,從童年期或青少年期就貫穿於女性生活中的“美貌”話語給女性帶來的巨大壓力;而整形可能給女性帶來的對約束、限制的超越則進一步體現了“美”對女性的重要性。這樣看來,那些標榜自己的整形行為是自主選擇的女性其實都是“美貌”話語的受害者,整形是一種被迫選擇。
整形之後:“虛假自我”、主體的分裂與羣體的分化
消費文化將選擇、自由和整形相類比,這不僅使女性被“虛假的自我”所激勵,抹去了整形前、整形中和整形後女性所承擔的困擾、風險與痛苦,還抹去了女性在整形實踐中所遭遇的性別、資本等方面的不平等。
(一)“重生的喜悦”
消費文化對身體理想型的推廣以及同伴羣體整形的成功促使女性作出整形的決定,她們渴望通過整形獲取美貌以擁有更多的協商生活的能力,進而通往美好的生活,成功整形所帶來的“美”對她們來説等於“重獲新生”。整形確實給一部分女性帶來了某些積極的改變,這些改變包括自身性格的改變和生活上的實質性改善。
在線上、線下的同伴壓力之下,曉澤最終決定整形,她十分感謝自己的整形經歷。
現在還是在恢復期,我看着自己的臉一天比一天自然,我一天比一天更喜歡自己的新樣子,我覺得人生是美好的……相由心生,反過來外貌也會對一個人的內心產生很大的影響。這些年來我從一個內向自卑、沉默寡言的小孩變成這樣一個喜歡交朋友、喜歡笑,能夠知道自己想要什麼的成年人。(曉澤)
另一位整形女性思妍也自述了整形給自己帶來的在親密關係和工作上的驚喜改變。
身邊的異性緣也好了起來,開始慢慢有人追。去年我還鬼使神差地去航空公司面試,並且成功了。我從來沒想過自己會成為一名空姐,因為在我的潛意識裏,這是離我很遙遠的職業,都不敢去想象的那種。或許整容就是這樣,它讓你變得漂亮,擁有不一樣的人生,甚至實現階級跨越。(思妍)
成功整形不僅給予這些女性夢寐以求的“美”以及隨之而來的生活方方面面的改善,還被這些女性視為是對自己人生的自由選擇和主動把控。
我想我也要變美,不是為了別人,是為了自己,我不想繼續這樣自卑,我想像別的正常的女孩子一樣可愛開朗,在最美的年齡做最美的自己……其實我不認為整容會上癮,這樣的説法其實是在説自己要求越來越高了,每個人都想變成更完美的自己,都在不停追求更好的生活罷了。(曉澤)
這是我自己的臉,別再一廂情願覺得我就是個受整形醫生和虛榮矇騙的傻大姐,每個人想法都不一樣。(辰欣)
然而,對所謂的“自主選擇”和成功整形所帶來的自信、快樂的強調讓人們低估和忽視了女性在整形前以及整形中所遭遇的痛苦和風險。女性有選擇做整形手術的權利和經濟能力,但她們是否同時擁有選擇不做整形手術的社會環境,她們是否擁有制定和選擇整形標準的權利?
正如相關學者所説,如果説女性擁有整形選擇的話,那麼這種選擇一定是發生在意識形態真空中的,因為沒有人會選擇被嘲笑、奚落、拒絕和拋棄,更沒有人會選擇手術刀、藥物和針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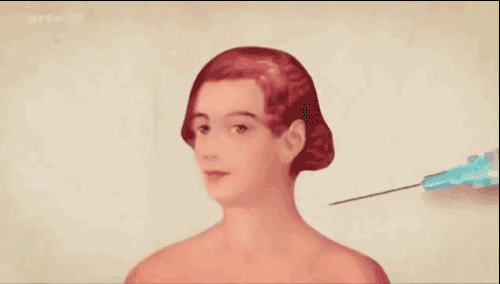
(二)“虛假的自我”
社會互動中的困擾以及消費文化對身體理想型的建構與推廣讓女性深刻感受到自己的身體與它應該看起來的樣子之間存在着巨大差距,這導致女性產生一種羞恥、內疚和焦慮的感覺。
然而,當前消費文化是以利益為驅動,以自由、選擇等新自由主義話語為包裝的,它在指出女性身體的問題和不足的同時,為女性提供了各種各樣的解決問題的思路和方法,但也把責任和風險留給了女性。儘管整形給部分女性帶來了生活某些方面的積極改變,但無論從整形的標準,還是從整形的過程和結果來看,整形給女性帶來更多的是風險和絕望。
接下來,筆者將圍繞整形標準、整形過程以及可能的風險和結果來討論整形給女性帶來的焦慮、痛苦甚或是對人生更深的絕望。
1.整形標準的單一化和西化
“網紅臉”是在關於整形的網絡版面以及訪談中經常被涉及的話題之一。之所以稱之為“網紅臉”,是因為目前在網絡走紅、依靠身體和臉追名逐利的很多女性都擁有受訪者口中的“千篇一律”的整容臉。這些“千篇一律”的整容臉的基本特徵是歐式雙眼皮、大眼睛、高鼻樑、深眼窩、白皮膚、豐乳細腰等。
近代以來,由於西方文化的影響,中國在服飾裝扮方面都致力於與西方接軌,因此改造中國女性身體的技術、程序和標準也以西方為參照。改革開放後,中國進一步與西方消費社會接軌,這使得中國女性受到了以西方消費意識形態為主導的父權制下的“美麗迷思”的規訓。正如摩根所説的,整形的手術刀是父權制下的魔術刀、歐洲中心主義的魔術刀以及白人至上的魔術刀。
筆者訪談的幾位受訪者都感受到了這種西式的整形標準與本土的審美標準在某種程度上的錯位。
肖穎在國外上的大學,畢業後特意回國削骨,找的是一位在某知名醫院工作的知名醫生,但這段經歷令她無比悔恨。
也不知道當時怎麼魔怔了去削骨。我身邊當時都是西方人、華裔還有其他種族的人,幾乎都是小臉的(至少當時的自己這麼覺得)……我社交的時候有些不自信,我都怪在我的臉型上……當時就各種不滿意。削骨以後……我的下巴和下唇的肌肉僵硬,感覺怪異,又痛又酸,笑起來很怪異。(肖穎)
另一位被訪者薛楊告訴筆者,她割雙眼皮後她身邊的男性朋友告訴她,“你單眼皮挺好看的”“割了(雙眼皮)以後顯老”,這使她感到十分困擾。而王麗在選擇雙眼皮標準時刻意選擇了她認為更適合自己的“小一點、自然一點的(雙眼皮)”,因為“歐式啥的,看着有點奇怪”。
這種整形標準與本土審美的錯位在某種程度上印證了這種標準的非本土化特徵,體現了女性整形實踐中的後殖民主義特徵,即西方國家在整個主流文化中的主體地位以及非西方國家的“他者”地位。

此外,不僅僅是整形標準西化,筆者發現女性對自己身體的觀念也體現出了非本土的特徵。薛楊這樣説道,“我還是我,身體跟名字一樣,不會影響本質的我……而且我覺得整形也是一種體驗,人生體驗啊,就是多一種經歷。”
這種關於身體的觀點顯然深受西方世界的影響,身體被看成一個處於“形成”(becoming)過程中的實體,是一項應當進行形塑、打磨等種種嘗試的規劃,它顯然與中國傳統文化中“身體髮膚授之於父母”的觀念不同。也正是在這個層面上,中國女性的整形實踐經歷中呈現出了後殖民主義的特徵。
西方國家的這種主體位置正是後現代女性主義批判的矛頭所向。後現代女性主義認為,所有女性的經歷不應該被簡化成單一的受壓迫模式,並不存在普世的、沒有差異的自我。
2.整形的痛苦與風險
從生理的角度來看,以白人為標準的整容模板在某種程度上與中國女性的身體條件存在較大差距,要想符合這個所謂“標準”的身體理想型,女性的“最佳選擇”就是整形。筆者認為,我們不應該對部分女性因整形帶來的生活的積極改變持過於樂觀的態度,而應該進一步關注整形前、整形中和整形失敗後女性所經歷的痛苦、風險乃至對生活更深的絕望。
薛楊和暮雲在整形前和整形中就經歷了個人的心理掙扎和朋友的勸阻。
上手術枱還會瞎想呢,萬一手術失敗了,以後怎麼工作,怎麼面對那麼多人。(薛楊)
當我堅定了整容的想法之後,幾乎所有知道我打算的朋友都在勸我不要整容,她們會列出一長串後遺症、併發症來告誡我將要面臨的問題,甚至死亡。真的不需要,這是我自己的臉,我比誰都想對它好點,這些後遺症我在做功課的時候都瞭解得一清二楚。(暮雲)
整形的痛苦與風險包括但不限於藥物副作用、長時間的痛苦、毀容、併發症甚至死亡。從上述材料可以看到,決定整形的女性對這些可能的痛苦和風險都有所瞭解,但她們仍然選擇躺在手術枱上。整形的痛苦和風險有多大,她們改變自己的決心就有多強烈。
在“虛假的自我”的激勵下,女性決定冒險整形以實現“自我救贖”。然而,並不是所有的整形都能給女性帶來“重生的喜悦”。對做了“削骨”的肖穎來説,整形不僅沒有帶來“重生”,還剝奪了她正常生活的機會,使她陷入了更深的絕望之中。
我的咬合本來就不完美,削了骨之後就更難恢復了,現在下頜關節嚴重紊亂,天天吃半流食,不能出去玩,不能受涼,不能跑步,各種限制,上班一個星期頂多20個小時,原來的職業規劃統統打了水漂。我做夢都想吃點正常的東西,吃點堅果,牛排之類的……本來是奔着做經理去的,現在下頜關節廢了,在零售崗位也耗不起了。最好的三年我全部獻給了削骨和後遺症,之後還有更長的鬥爭……要是時光倒流我是絕對不會削骨的。(肖穎)
對肖穎來説,整形前變美的心願在後遺症的折磨前已經蕩然無存。為什麼在瞭解整形的後遺症後,女性仍要承受如此巨大的風險去整形?如前所述,答案在於當前消費文化和父權制承諾“美貌”女性予一系列的社會特權和經濟回報。
女性就像是在自我監視下的囚徒一樣投入到強迫性的自我規訓和自我管制中,而現在這種自我規訓和管制背後的父權制被強調個體、自由、選擇的新自由主義話語以及女性“虛假的自我”給掩蓋了。如吉爾所説,這是一種比“客體化”更深刻的利用形式,男性的凝視被內化成一種新的規訓體制,從外在的、男性的凝視轉向內在的、自我的凝視;女性主體被以更私密、細微的方式規訓着,選擇、自由等這些概念是這個規訓工程的核心。

(三)女性主體的分裂與羣體的分化
從對“醜”的自我認知到決定整形,再到整形的標準、過程和結果來看,整形並不是女性所謂的“自主選擇”,而是在隱藏於社會互動和消費文化中的父權制壓迫下作出的決定。
對女性整形經歷中的自主選擇的強調讓我們忽視了女性整形前後生活中的絕望以及整形實踐中存在的權力與不平等。隱藏於消費文化中的父權制以更隱蔽的方式對女性進行規訓,它不僅使女性深陷於“美貌神話”中,還製造了女性主體的分裂和羣體的分化。
1.對整形的嚮往與道德譴責
“網紅臉”之所以被稱為“網紅臉”是因為目前在網絡中走紅的、“依靠身材和臉蛋追名逐利”的很多女性都擁有“千篇一律”的整容臉。在大眾文化中,“網紅臉”已然是個貶義詞,有時候甚至與低俗劃等號。在對“網紅臉”的討論中,不少話題討論參與者表示自己不喜歡、討厭甚至嫉妒網紅臉。
網紅臉是把急功近利的心思全寫在臉上了……網紅臉追求的根本不是美。網紅臉追求的是高鼻樑、大眼睛、尖下巴。也就是在追求別人的認同、讚美和誇獎。甚至這種追求中帶着“我可以把別人踩下去”的急切期待。這些人散發出的氣場,讓我退避三舍。(林娟)
流水線產品,網紅上位,沒文化卻能夠佔有資源。(王林)
從上述材料中,我們可以通過“急功近利”“退避三舍”“沒文化”“上位”等詞彙看到一些女性對“網紅臉”的貶損與敵對態度。除了“網紅臉”並不完全符合中式審美以外,女性認為通過整形來獲取利益的行為具有非正當性,潛意識裏拒絕與美貌綁定在一起的價值。美貌的確不應該成為一種勞動力,因為對美貌的關注與強調標誌着對女性的壓迫。
然而矛盾的是,選擇整成“網紅臉”的原因也是這些與美貌綁定在一起的價值。在探討為什麼有部分人想整成網紅臉時,娜華和寧寧提出了自己的觀點。
網紅臉在展現大部分人都會羨慕的“大眼睛、高鼻樑”的同時,也會展現大多數人都向往的白富美生活,變美、有錢、買買買、跟男神在一起、過着小公舉一樣的生活……只要你整容,就可以變美,只要你變美,你的人生就會一片坦途。(娜華)
我們對網紅臉的憧憬和追逐,是因為看到網紅背後衍生的顏值經濟。除了擁有美貌外,還能被欣賞、認同和喜歡,虛榮心大大地被滿足。同時,一呼百應的流量、權貴的追求、經濟的獨立幾乎是所有女生內心的“完美人生”。(寧寧)
我們可以從中看到女性對整形的矛盾態度,女性深陷於對立的兩端之間:一端是女性對符合父權制要求的美麗身體外表的嚮往,她們顯然十分渴望“網紅臉”所能帶來的社會資源和社會認可;另一端則是對美麗外表下的道德品質敗壞的指責。她們在潛意識裏拒絕與美貌綁定在一起的價值,並不認為通過整形來獲取利益的行為具有正當性。在這對立的兩端之間,女性主體出現了分裂,女性羣體之間也不斷地產生敵意和分化。
值得注意的是,女性是有可能通過整形擁有迷人的身體進而獲取豐厚回報,但並非所有女性都擁有相關的資源和機會來徹底重構身體。
2.“美”與“醜”的對立分化
媒體時代,有關重構身體的知識廣為流傳,但並不是所有人都有資源對自己的身體實施控制和照看,沒有資源但掌握這種知識的女性會在主觀上感到被剝奪感。由於女性所擁有的資本存在差異,她們並非都擁有自主選擇整形的機會。
儘管“網紅臉”可能給女性帶來一些社會資源和認可,但由於它所參照的整形模板的單一化和西化,“網紅臉”並不是真正受推崇的“美貌”,因為它與中國女性的身體條件存在較大差距,不夠“自然”,且“千篇一律”,不夠有辨識度。娜華和莉莎對此表達了自己的看法。
要想像明星一樣又美、又自然,就必須要有過硬的底子、審美以及錢包,這樣才能在這條整容變美的道路上走下去。(娜華)
美是稀缺資源,網紅的美女放在大的人口總數里,依然是稀缺資源,我們覺得膩了,是因為曝光得多了。(莉莎)
只能整形成“網紅臉”的原因在於並非所有女性都擁有足夠的整形資源和機會,她們只能選擇前面談到的單一化、西化的整形模板。
以布迪厄所説的經濟資本為例,擁有足夠經濟資本的女性更有可能通過整形獲得更自然的、高級的美貌,從而獲得更高的回報。擁有一般經濟資本的大多數女性只能購買所謂的“整形快餐”,即模板化的整形標準和程序,將自己改造成所謂的“網紅臉”。
“千篇一律”的網紅臉顯然不如高級、自然的美貌受歡迎,因為它易得、不夠稀缺。但它仍可能為女性帶來回報,因為在媒體高度發達的消費文化中,擁有一個更符合大眾審美標準的外表仍有機會獲利,這也許是很多女性明知道自己可能被整成“網紅臉”,卻仍然要作出整形選擇的原因。

而那些缺乏經濟資本的女性只能維持自己原來的樣子,正如斐依所説的:“貧窮不允許我有這種(整形)決定”。女性當然明白身體資本能夠轉化為其他資本,因為所有的廣告、雜誌等大眾媒體都這樣告訴她們,但是在考慮身體資本轉化為其他資本之前,女性需要考慮其是否擁有足夠的經濟資本去整形從而獲得身體資本。
在對女性的身體進行明碼標價的父權制文化中,女性必須去競爭掌握在男性手中的資源,在這種情況下,擁有不同身體資本的女性之間便會產生更深刻的且伴有明顯敵對情緒的分化。因此,從宏觀層面上來講,由於女性個體在資本獲取和資本轉化上的不平等,整形會加大女性間的分化。這種階層分化的形成過程十分迂迴和隱蔽,因為它超越了階層分類的傳統測量方法。
正是在美貌與道德敗壞的兩端之間、美與醜的對立和競爭狀態下,女性主體出現了分裂,女性羣體陷入了敵對的、競爭狀態下的分化。
結論與討論
本研究運用深入訪談和虛擬民族誌方法對青年整形女性進行研究,探討社會互動和消費文化如何促使青年女性形成長相“醜”或“有缺陷”的自我認知並作出整形的決定以及整形的過程和結果。社會互動中所產生的人際困難和兩性關係是讓女性意識到自己長相“醜”或“有缺陷”的關鍵因素。
對女性來説,長相“醜”或者“有缺陷”是一種阻礙她們享受生活的社會障礙。因為“醜”而在社會互動中遭受的挫折激發了女性對自己的否定,外貌成為女性對自己進行價值評判的核心。在對自己形成“醜”的自我認知之後,整形技術的發展、消費文化對美的建構和同伴壓力是促使女性作出整形決定的三個關鍵因素。
整形給部分女性帶來生活上的積極改變,甚至被女性視為對自己人生的自由選擇和把握。然而,無論從整形的標準還是從整形的過程和結果來看,整形給女性帶來的更多是“虛假的自我”、主體的分裂和羣體的分化。
正如沃爾夫所説,父權制對女性的控制現在都轉置到了女性的身體和臉上,這種父權控制經由消費文化,藉助手術刀、藥物、針筒等工具,最終由被“虛假的自我”所激勵的女性施加在自己身上。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很難説整形是女性的自主選擇。
隨着女性社會經濟境況的改善,女性生活的方方面面確實有了提升。然而,新自由主義和消費文化對傳統性別符號資源的開拓不僅使女性不斷被客體化和商品化,其對自由、選擇等部分女性主義元素的收編更使傳統的女性主義失去批判力,女性主義概念亟待更新。
筆者不贊同傳統女性主義學者將女性視為全然被動的父權制的受害者或消費文化的“傀儡”的立場,也不贊同對女性在整形過程中的個體能動性持過於樂觀的態度。這種“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傾向不僅可能讓我們忽略女性個體與結構性壓迫之間博弈的動態過程,還讓我們簡化甚至無視其他對女性造成壓迫的結構性因素以及所處社會語境的發展變遷。
就國內語境而言,相較於西方女性運動,中國的“男女平等”是通過國家政治、行政手段以自上而下的方式實現和深受西方文化影響的,未經女性主義大潮衝擊的中國女性,始終缺乏對社會性別觀念的理解,她們甚至對女性主義充滿偏見和誤解。
改革開放後,伴隨着對改革開放前“男女都一樣”的性別話語的批判,對“男女不一樣”的強調演變成了“迴歸女性”的性別話語。對“迴歸女性”的渴望,以及對男性中心文化的警覺的缺乏,使得中國女性毫無抵抗力地投入到西方消費社會所創造的性別文化中,成為商品經濟剝削和利用的對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