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C.斯科特:中國的秦,展示出一種宏大至極的願景-詹姆斯· C. 斯科特、田雷
【文/詹姆斯· C. 斯科特 譯/田雷】
在早期國家形成的過程中,為了處理勞力、穀物、土地和配給的計量單位,某種方式的標準化和概念化就是必須的,且構成了一整套的操作。要實現上述的標準化,早期國家必須發明出一套標準的命名法,將所有基本的類別包括進來,比如收據、施工指令、勞役通知等——而這一過程,是通過書寫或文字來完成的。起草一部成文法典,並適用於整個城邦境內,就取代了地方上口頭的裁判,而且成文立法本身就是一種消弭距離的技術,其力量可以支配早期國家並不廣遠的國土範圍。
針對耕田、耙地或播種這些農業勞作的任務,國家發展出了勞動的標準,某種類似“工分”的設計也被創造出來,顯示出工作分配中的任務履行或拖欠。對於魚、油和紡織物來説,分類和質量的標準也有了詳細的規定,以紡織物為例,就是通過重量和密度來進行區分的。至於牲畜、奴隸和苦工,也通過性別和年齡加以分類。即便國家此時仍處在“襁褓”之中,它的佔取之心就已顯露出來,總在設法從所佔有的土地和人口處汲取更多的資源,而對於國家而言至關重要的“統計學”也已經浮現出來。這種嚴格控制的努力雖思之令人驚歎,但至於它在田間地頭又要如何落實,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至於文字出現在中國的黃河沿岸,還要再等上至少一千年。中國的文字可能始於二里頭文化區,只是沒有證據遺存下來。舉世聞名的中國文字出現在商代(約公元前1600年至公元前1046年),考古學家發現了用於占卜的甲骨文。從那時起,經過戰國時期(約公元前475年至公元前221年),中國人一直在使用文字,尤其是用於國家管理的目的。不過只有等到聲名顯赫、鋭意改革但卻曇花一現的秦代(公元前221年至公元前206年),才能最清楚地看到文字和國家建構之間的聯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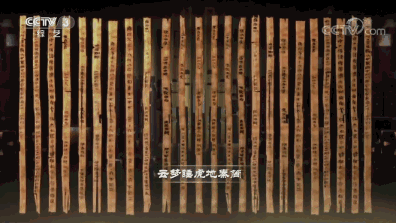
雲夢睡虎地秦簡資料圖,圖自《國家寶藏》
中國的秦,就像美索不達米亞的烏爾第三王朝,作為一個政權,它追求系統化,迷戀秩序,展示出一種宏大至極的願景,要實現國家資源的總動員。至少在書面上,秦的雄心壯志一覽無餘。無論是在中國,還是美索不達米亞,追究文字的起源,它從一開始就不是表達語音的某種方式。
對於秦來説,要追求標準化和簡略化,就要先完成一項工作,通過改革將書寫文字統一起來——最終,秦政權刪消了四分之一的表意文字,使字的筆畫更為平直,並將其推行到國土的全境。由於中文的書面文字並不是某種方言語音的抄錄,所以中文與生俱來就有某種普遍性。如同別處的早期早成國家,秦所推動的標準化的過程,也適用於鑄幣以及度量衡的單位,以之丈量土地,稱重穀物。之所以這麼做,目的在於廢除大量原屬地方的、各國間不相容的度量衡慣例,如此一來,中央的統治者才能史無前例地看清楚他的國家,知道他手中掌握的財富、物產以及人力資源。
秦的理想不只是成為一個強大的邦國——只要偶爾向周圍一些半獨立的衞星市鎮索取貢品,也就心滿意足了,而是創造出一個大權集於中央的國家。到了漢代,宮廷歷史學家司馬遷回望歷史,就讚賞了商鞅在秦的成就,將秦王國變成了一部質樸的戰爭機器:“為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税平。平鬥桶權衡丈尺。”後來,就連勞作的規範以及工具也被標準化了。

商鞅戟,圖自上海博物館
早期國家處在列國的包圍中,所面對的環境是區域性的軍事競爭,故而當務之急就是在自己的領土上壓榨出儘可能多的資源。這就意味着,要盡現有技術條件之可能,建立起一份儘可能完整的資源詳目,並隨時更新。對於國家來説,能象徵其權勢的,不僅是為數眾多且不斷增長的人口,還包括細緻的家户登記,後者便於徵收人頭税以及徵兵。戰爭中抓來的俘虜,都被安置到距離宮廷不遠處,各種管理也限制人口的流動。説起早期農業王國,它們招牌式的治國之道就是讓人口留在原地,防止任何未經授權的遷徙。對於税務人員來説,人口的流動和分散是件頭疼的事。
讓收税官員欣慰的是,土地幸好不會移動。然而,由於秦承認私人對土地的所有,國家就要進行詳盡的地籍調查工作,在每一塊莊稼地與某一位所有者/納税人之間建立起聯結。根據土壤質量、播種作物以及降雨量的差異,國家對土地進行分類,這樣一來,税收官員就能估算出一塊地預期的產量,然後得出它的税率。按照秦的税制,還規定了對生長中的作物進行年度的評估,如此就可以根據實際的收成來調整税負,至少在理論上是如此。
行文至此,我們都在關注國家官員的標準化努力,他們意圖通過書寫、統計、普查和度量衡,擺脱此前純粹的掠奪行徑,轉而以更理性的方式去汲取屬民的勞力和食物資源。早期國家總在進行種種努力,塑造所轄國土的地貌,使其更富饒、更可識別,也更適於資源佔取,在種種舉措中,度量工程或許是最重要的,但卻不可能是唯一的政策。
雖説灌溉以及治水並非早期國家的發明,但國家出現後,確實擴展了灌溉和溝渠系統,以促進運輸並擴大種糧土地的面積。只要情況允許,早期國家也會對下轄屬民以及戰俘進行強制的重新安置,以增加生產人口的數量並加強國家對他們的識別。在很大程度上,秦之所以有“均田”的概念,就是為了保證所有的子民都有足夠的土地,這樣才有收成可徵税,才能形成徵兵所需的人口基數。
有秦一代,國家非常重視人口,這表現在國家不僅禁止民眾棄地而逃,還推行鼓勵生育的政策,對於生育的婦人及其家庭有税收寬減的優惠。新石器時代晚期多物種混居營,是最早期國家得以發端的“內核”,但説起早期國家的治國之道,很多都是某種巧妙的、政治性的地貌改造,目的就在於促進對資源的佔取:比方説,更大面積的糧田,數量更多、密度更大的人口,還有某種“信息軟件”,其編碼就是書寫的成文記錄,有了它,國家就能獲取更多更廣的信息。然而,成敗或在一線間,這種政治性的雄心壯志,追求地貌景觀的徹底改造,也導致了最有野心的早期國家在彈指間灰飛煙滅。烏爾第三王朝痴迷於各項事務井井有條,其延續不過一個世紀,而秦代更是十五載而亡。
既然早期的文字是附隨於國家建構的,兩者之間密不可分,那麼當國家消失時,文字會發生什麼變化?
對此,我們所握有的證據着實不多,然而呈現出的跡象都是,如果沒有了官員體系、行政記錄以及層級間的交流,文字的讀寫能力就算不會完全消失,也會大大減弱。其實,我們對此不必訝異,畢竟,在最早期的國家中,能讀寫文字符號的,僅限於人口中的鳳毛麟角——其中大多數都是官員。從大約公元前1200年至公元前800年,古希臘的城邦聯盟崩潰,進入了我們所知的“黑暗時代”。當讀寫能力再度出現時,文字所採取的不再是“線性文字B”的舊形式,而是一套從腓尼基人那裏借來的全新書寫字母。
當然,在那個過渡期,並不是説希臘文化已經消失得無影無蹤。準確地説,文化轉成了口頭的形式,我們今天所讀到的《奧德賽》和《伊利亞德》,最初就形成於這一階段,只是後來轉錄為文字。就文學的傳統來説,羅馬帝國有着更為廣遠的輻射,但即便是羅馬帝國,當它在5世紀分崩離析後,拉丁語的讀寫也近乎絕跡,只有在一些宗教機構內還留有星星之火。在此不妨推測,在最早期的國家中,文字最初的發展,乃是作為一種治國的技術,既然如此,文字作為一種成就,也就同國家本身一樣,脆弱且短暫易逝了。
説到這裏,我們能否換個想法,是否可以把最早的文字讀寫視為一種交流溝通的技術,就好像作物種植一樣,也是眾多生存技術中的一種?就作物種植的技術而言,在它們獲得廣泛運用之前,早已為先民所知,而且即便推廣後,也僅限於特定的生態和人口環境。同理,整個世界在文字發明之前也並非“萬古如夜”,而在文字出現後,也並非所有的社會都採用或者渴望採用文字的形式。最初的文字書寫之所以出現,就是因為國家建構、人口集中,以及國土規模擴大。換到其他的環境中,文字也是沒用的。一位研究美索不達米亞早期文字的學者曾嘗試推斷其中的奧秘,在他看來,文字之所以一到別地就受到抵制,正是因為文字與國家以及税收之間有着抹不去的關聯,這就好像在田間的耕作之所以長期受到抵制,就是因為一分耕耘就是一分勞苦,兩者之間的關聯壓根無法遮掩。
根據考古發掘,許多處在邊緣地帶的文化都曾接觸過美索不達米亞南部社會的複雜,但為什麼每一個各有不同的社羣都會拒絕使用文字呢?一個可能的回答是,這種對複雜的拒絕乃是一種自覺的行為。這麼做的理由何在呢?……很有可能,邊緣的羣落並不是在智力上不夠格,無法應對那種複雜,而是他們實在太聰明瞭,他們是在設法避開這種沉重的命令結構,事實證明,他們躲過了至少五百年,直至最終在軍事征服後被接管……在任何一個例子中,我們都能看到,邊緣社羣即便在感知到外部的複雜後,一開始仍會拒絕採納這種複雜……正是因為這麼做,他們才能躲開國家的牢籠,又自在地過了五百年。
【本文節選自《作繭自縛:人類早期國家的深層歷史》第四章“穀物立國:早期國家的農業生態”,標題系編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