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妮妮:農協抹平了日本城鄉之間的恩怨?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潘妮妮】
在討論中國三農問題時,日本農協經常被作為比較對象提出。國內對日本農協的評價也落在兩極:一邊是強調農協的合作性質,認同它在緩和城鄉差距中發揮的作用;另一邊則是強調農協經營的“壟斷性”和組織的“僵化性”,甚至上升到是日本經濟復興與體制改革的“巨大障礙”的程度。
由於相關研究甚多,本文不再多評價農協的功過,而重點想討論農協成敗的“客觀環境條件”。畢竟同樣的組織形態,在不同的環境下所發揮的作用大不相同,加上評價體系的變化,更是蜜糖砒霜的霧裏看花了。

日本方西瓜(資料圖)
農協並非從天而降
農協,全稱“農業協同組合”,依據1947年制定的《農業協同組合法》設立。根據2022年公佈的2020年統計粗算,農協共有正式成員與“準成員”10418人,地方組織共587個。資產合計117兆3066億日元,2020各項經營收益1兆7101億日元。
日本戰後的農協實際分為專業農協和綜合農協,前者是生產同種農產品而自願組成的農民合作組織。而平時我們説的“農協”更多是後一種,即區域內絕大多數農民參與的合作經濟組織。其業務範圍涉及區域內生產主要農產品,同時為會員提供全方位服務——不但包括專業農協也涉及的產品銷售、農資購買和技術指導,還會廣泛提供與經營、生活相關的金融信貸、互助保險等服務。在2016年《農業協同組合法》大修前,農協內部存在自上而下的組織性管理,因此實際發揮了地方自治、遊説/配合國家政策等社會及政治功能。
農協並非二戰後從天而降,其基本形態在戰前就已經形成。
明治維新之前,日本農村的封建莊園經濟形態決定了在領主的統治下,農民有結社與領主互動的必要性。當然此時的農村合作組織內部關係也是封建性的,以地主或大家族為主導。而到了明治維新,一方面政府自上而下地推行“文明開化”,強制對農村移風易俗;但另一方面,由於沒有社會革命,所以政府的移風易俗又離不開傳統社會主導階層/團體的承認或支持。所以,從明治維新到戰爭結束,這一時期的日本農會組織,就是兩種力量不斷拉鋸的產物。
值得一提的是,這種拉鋸不能簡單地被描述為“進步資本主義”對“落後封建主義”的鬥爭,因為日本政府的“文明開化”政策同樣大量地依靠傳統封建關係資源,而農村的封建自組織在特定的情況下也發揮了維護農民集體權益,局部緩和資本主義原始積累過程對農村侵害的作用。

資料圖
今天的日本農協仍然繼承了這種複雜性。
在這樣一種歷史邏輯下,19世紀末期,日本政府先後頒佈了一系列法律,目的是對農村的自組織形式進行規範,排除國家與農民間存在的勢力,建立農會組織和農村產業組織,將農村納入國家的整體發展的規劃網絡中。
在20世紀初,日本農村各地已經出現了生產、信貸、銷售、購置生產資料等多種合作形式,系統性的合作社建設也在多處展開。但同時政府的管制也在加強,尤其是進入總體戰體制後,1943年,日本頒佈《農業團體法》,強制地方農會和產業組織合併為農業會,完全從屬於政府進行戰爭資源動員的需求。
戰後,農協為何能助力日本經濟?
從這段歷史看,如果將1943年的《農業團體法》看作是城市政府與地方農村的“拉鋸”過程被打斷,轉為政府強制主導。那麼戰後的“農協”組織可以看作是又回到了明治維新現代化的“拉鋸”思路上,即,一方面農民通過自組織維護既有的權益和鄉村、地域認同;另一方面政府力求將農村納入國家經濟與社會發展的內循環中。
基本思路相同,決定了日本戰後成立農協組織是歷史發展自然的路徑依賴,甚至我們極端點可以説是“換湯不換藥”。然而,正是因為“湯”,也就是戰後的客觀環境條件發生了一些重大變化,使得農協組織發揮了促進農村現代化發展、縮小城鄉差距的積極作用。這些“湯”包括以下這些方面:
首先,戰後,美軍司令部(GHQ)將“農民解放”作為日本“民主化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
GHQ指令的農地改革廢除了寄生地主制,轉為小農户為主的農業結構和農業流通體制。而1947年實行的《農業協同組合法》也規定,農協原則上應保障成員選擇的自由、確立和尊重農民利益的主體性,建立農業生產合作體。這就使得農協組織具有了不同於戰前的利益出發點,具有了“民主社會”之大義。
其次,戰後日本的經濟模式也發生變化。戰前日本曾被人調侃為“貧窮的帝國主義”,其經濟政策要服務於國家工業化和對外爭奪帝國主義利益的需要。因此,農村和農業組織自然都會逐漸成為城市資本主義工業和帝國主義國家的雙重掠奪對象。而戰後,日本將國防交給美日同盟,在美國援助與自身工業底子的支持下,順理地發展外向型經濟。從而使日本具備了保護國內農業、縮小城鄉差距的物質基礎。
再次是日本國內的政治競爭態勢。1950年代到1980年代,日本的右派保守政黨都將農村視為自己的穩定票倉。而由於保守黨長期執政,也樂意給農村給予政策支持與保護。同時,由於明治維新以來農村與城市地區的複雜“恩怨”,農村地區同樣存在自我保護、不滿執政勢力的潛在心理,使得左派革新政治力量有可能對農村施加影響,又進一步促進了保守政府對農村的政治傾斜。
最後,還有一個隱性條件。由於日本的戰敗,戰前的“愛國心”消失,而“鄉土”與“傳統”取而代之成為民族心靈的一種寄託。這樣一種文化氣氛減少了城市民眾對政策傾斜的牴觸情緒。

《海街日記》劇照
在以上條件的加持下,看似延續自戰前的農協組織發揮出了與戰前截然不同的積極作用。具體的內容已經有太多的研究言及,本文不多贅述,只簡單歸納為三點:
首先,在日本這樣資源匱乏且一度政治動盪的追趕型國家,農協合作化體系以及其它形式的國家政策保護是完全必要的。它保障了農村經濟恢復,保障了地方穩定的向城市輸出勞動力,避免了社會差距過大帶來的撕裂,有利於城市化進程。
其次,農村雖然是自民黨的穩定票倉,但是以農協為代表的農村自組織形式仍然發揮着很強的自治功能,有利於推動執政者實施有利於社會平等的積極政策。
最後,為了配合保護農村經濟的政策,日本媒體對農產品和農村風土的宣傳和精神謳歌,客觀上也促進了日本戰後民族自信心的恢復。
“前之蜜糖,今之砒霜”?
到了1980年代,農協發揮積極作用的外部環境逐漸發生了重大變化。
首先是經濟狀況的變化。日本經濟增速放緩,被迫開始對國內社會福利動刀,弱勢羣體之間的矛盾萌芽;同時,日美貿易摩擦加深,美國利益集團要求日本開放農業市場的呼聲增大;以及,第三世界國家廉價產品的衝擊,都客觀降低了日本內部的農村/農業保護能力。
其次,政黨方針轉換。隨着城市化的基本完成,農村人口數量縮減。
中曾根政府時期,自民黨研判認為,自己近來的選舉大勝得益於吸引了更多的都市選票,農村基本盤的重要性已經降低。同時認為,在未來,以“改革”和“開放”姿態吸引城市搖擺層的政治家會更加受到青睞。在這樣的研判下,加上美國的壓力,自民黨要人們開始公開表達對農協的不滿,這就促進了日本媒體放開了對農協的負面報道與批判,改變了社會空氣。

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新華社資料圖)
最後,在泡沫經濟崩潰後,日本民眾對日本式政治經濟體制的不滿噴發出來了。
泡沫經濟中,農協的金融部門也大量介入保險、信用等金融業務,泡沫經濟崩潰後自然出現大量壞賬,而自民黨議員出於選票的需要給予補救和政策優惠。這一現象進一步讓輿論將農協視為日本“秘密政治”和“國家壟斷資本”的象徵,同時也帶來了成員本身對組織的不信任情緒。社會對農協的總體評價持續走低。
在批判聲中,學者也總結出日本農協的幾大問題:屬地原則;高度組織化;業務的綜合性和壟斷性,通過全方位的服務形成農村經濟的閉環和獨佔;對自民黨的政治依附。
這個總結毫無疑問是“正確”的,但是想想似乎又有哪裏不對。這些“問題”,不也正是戰後日本農協發揮積極作用的關鍵要素嗎?農協還是那個農協,而之所以前之蜜糖,今之砒霜,其關鍵在於國家的政策目標與大眾輿論的評價標準發生了變化。
當日本國家和大眾把“保護脆弱的農村/農業/農民”作為明確的目標時,那麼顯然,農村的合作化就是必然的選擇,而基於日本農村的資源稟賦和歷史條件,前面所列的“問題”,恰恰是實現合作化、自我保護的理性選擇。農村只有結成一個“利益團體”,尋求政策傾斜,才能分享自民黨、官僚、財團主導的經濟發展成果。這個選擇,是當時的政界與農村自治力量共同推動,又得到了當時輿論的認可。
當然,農協的“利益團體”化,必然埋下與其它利益相沖突的伏筆。1980年代之後,日本國家政策目標變成從經濟停滯中“復興”,政府也一步步向里根式的新自由主義靠攏,首相權力逐步加強。再加上農村票倉的萎縮,那麼毫無疑問,對農協的評價重點也會從關注它的“社會自治,社會穩定功能”逐漸轉向關注它的“經濟效率,經濟收益”。
與此同時,日本城市化基本完成已多年,民眾的“鄉土情結”逐漸消亡,農村從老一輩文藝創作者筆下“保存赤誠與希望的創造性空間”,轉變為新一代創作者描寫的“提供心靈休憩的獵奇對象”。當城市青壯年一代以為農村的景象是“本來就存在的寧靜”,而不知道是“戰後合作化與組織性鬥爭的成果”,自然很難對農協再有正面評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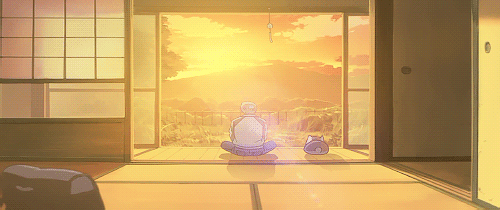
《夏目友人帳》片段
農協的“新自由主義”改革
在內外壓力下,1988年到1991年,日本確立了改革計劃。
首先是組織整頓,精兵簡政,旨在削減成本,提升事業營運的經濟效率。都道府縣級經濟聯合組織與全國農業協同組合聯合會(JA全農)整合,大部分(32個)都道府縣級經濟聯合組織轉型為全農地方本部,7個縣整合為單一農協,另有8個道縣保留經濟聯合會。在把部分縣級機構職能轉化給基層農協的同時,削減基層農協數量,從1990年的3561個減少到2020年的587個。
其次是組織內部的“組織力強化”,即發展農協下屬各類組織的活力,除了傳統設置的產業組織、青年組織、女性組織,還發展直銷機構、農協注資法人,以及各種成員或“準成員”的協作性小組等。加強活動支持、人才培育和獎勵制度等。
最後是面向市場,改革對農業的經營指導以及銷售事業體制。通過精簡優化農機農資業務、開展直營業務、加速發展智慧農業、積極開闢國際供銷渠道。其實筆者讀書的時候,對於“農協直送”也多有利用,體驗還是比較良好的。

而站在日本政府的角度看,他們當然不滿足於這種程度的改革。農協改革對自民黨政府而言,既可以改善自己的政治形象,吸引城市選民;又能推動新自由主義的“體制改革”;同時能夠加強日美同盟,還可以為日本主導亞太區域經濟合作體制增加籌碼。這一石三鳥的舉措,不可不積極嘗試。
1995年,日本政府頒佈了新糧食法,結束了持續半個世紀的糧食統購制度,打破了農協在糧食流通領域的壟斷地位。第二次安倍政府時期,在TPP談判過程中,官方推動了農協同意開放市場。2016年4月1日,日本正式實施《農業協同組合法》修訂案,形式上看,改革基本的“反壟斷”思路不變,就是削弱農協的地方社會自治功能,向純粹的市場經濟組織轉型。重點內容包括:
2019年3月前廢除日本全國農業協同組合中央委員會(JA全中)對旗下團體的強制約束力,後者最長10年內轉換為自願性團體。
JA全農改製為股份公司。
都道府縣一級農協改組為一般自願法人團體,廢除其對基層農協的糾紛調解權。
廢除基層農協的地域准入限制,強化其作為市場競爭主體的獨立地位,取消基層農協的“非盈利性”限制,允許農協針對特定業務成立股份公司。並接受專業會計師事務所審計。
改革基層農協治理結構,基層農協不再以自身名義開展金融活動,其金融事業功能整合進專門的金融機構農林中央金庫。提升骨幹農户在農協中的決策話語權。
從財務報表上看,對農協的“新自由主義”改革,的確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降低成本、增加經營收益的作用。但它同樣有必然的缺陷:在日本這個自然資源匱乏,農村與農業組織存在路徑依賴的國家,在當前日本國內面臨普遍的“資產負債表衰退”,缺乏經濟增長點的情況下,用制度安排來推進農村經濟的“市場化”,真的是一種“理性選擇”嗎?事實上,農協的企業化改制進程緩慢,而社會自治功能顯著退化,對國家政策的依賴性卻並沒有明顯降低。
也許,單純用二戰後年輕的經濟學“理性”去衡量農村發展問題,並不是一個太“理性”的選擇。日本決策者又何嘗不知?受制於眾多客觀條件而已。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台觀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關注觀察者網微信guanchacn,每日閲讀趣味文章。